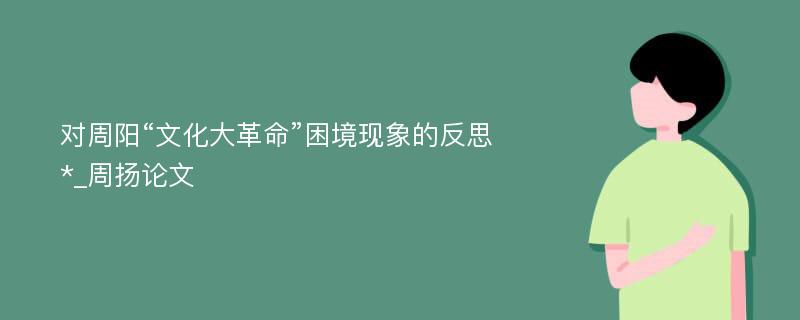
周扬“文革”落难现象之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革论文,现象论文,周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香港的新闻记者赵浩生曾在一篇访问记中说过,“周扬是一个和中国现代文艺运动分不开的名字。这个名字贯穿着近半个世纪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历史”。(注:《周扬笑谈历史功过》,载《新文学史料》1979年2期。)假如我们抛开赵浩生这段话里的溢美和夸大成分,那么不得不承认,他的表述中蕴含了一些真理性的内容。至少,从本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周扬是一个显赫的人物,也是一个志得意满的胜利者。从这一段时间里走过来的文化人都十分清楚,他靠着自己的精明强干,靠着一般文化人所缺少的权谋,平步青云,一直走到文化势力的顶端。并无多少实力的周扬能够落坐在主帅账中,对所有的文化人气指颐使,一呼百应,这实在是耐人琢磨的奇迹。在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上难得找出一个人可以与他匹敌,便是鲁迅,虽然和郭沫若、梁实秋等交战起来游刃有余,碰到周扬,却不时感到棘手。周扬的非常战法让他气愤,同时又常常让他流露出无可奈何的哀叹。
周扬在建国后,发展了他的非常战法,借助于文艺思想斗争或曰革命大批判,将三、四十年代的宿敌胡风、冯雪峰、丁玲及鲁迅的几乎所有弟子,加上新的异端,全部送上了审判台。这又给他的名字增加了异样的威严。
二
今天看来,鲁迅对周扬下的轻蔑断语需要作些修正。仅仅用“学问”这种纯文化眼光估量不出周扬的价值。从批判《武训传》、《红楼梦》研究,胡风文艺思想、反“右”斗争、反修斗争到文化大革命,我们能够理出一条逐渐演进的线索。而且,他的某些观点为“文革”提供了或直接或间接的理论依据。象他的可以对英雄人物理想化、把塑造英雄形象当作“最重要的、最中心的任务”(注: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第11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的观点,后来就演化成“四人帮”的“根本任务论”和“三突出”的创作原则。他批判丁玲、冯雪峰时创造的“民主革命同路人”的说法,后来就发展成为“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极“左”理论,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这一点来衡量,周扬其人莫可等闲视之。他和一些人在建构“左”倾文化模式方面,走到了历史的前面。只是一个偶然契机把他推到了极“左”文化路线的反面,他才尝到了自己营造的苦果。
三
对于周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落难,人们怀着不只是同情的十分奇异的感情。
无法否认人们对周扬遭难而升起的复杂感情。要是稀释了人们的复杂感情,生活反倒失去了耐人琢磨的戏剧性内容,失去了独有的色彩和浓度。而对人们情感所作的辩护不会给批判他的人留下藏身之地,更不会为他们的行为提供出“合理性”的证明。追根究底,批判者是更恶的存在。他们的批判不是在正义和良心的轨道上运行,因而树立不起正面的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换句话说,他们没有惩罚周扬应该受到惩罚的东西,相反在新的历史层面上重复它们,使恶变得更恶。他们采用的方式不但显示出道德伦理的彻底堕落,而且显示出政治品质的彻底沦丧。
四
我们翻阅了“文革”中几乎所有批判周扬的文章,它们低劣得出奇。在洋洋数十万言的文字中。除了一、两个事例可以证明周扬确实是反鲁迅的而外,你简直找不到一个事实能够说明周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有周扬的政治罪恶全是拼贴、剪辑、硬凑出来的。批判文章摘引的周扬“反党黑话”,没一句可称为完整的。它们或三、五个字、或一两个字,掐头去尾,没有任何背景。就是希望周扬受到惩罚的人,看了这些“引文”,也会大失所望,扬长而去。还有许多“引文”明显地是周扬在肯定了成就、肯定了既定的方针政策、肯定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肯定了意识形态领域中“左”的观念和做法之后、为了表示一点辩证观点而不得不虚与委蛇地作出的补充说明。从五、六十年代的文化模式中走出来的人都熟知,这种补充顶多起到堵漏作用,有时还起着“引蛇出洞”的“阳谋”作用。把周扬这些准备作钓鱼的东西拿来作为反党的佐证进行批判,怎么能叫人相信呢?批判者的观念和被批判的对象是大水淹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批判者所以诛杀同类,肯定有更大的阴谋。这就是我们重新读到那些批判文字后楔人脑中的第一个想法。
五
在全部拼凑的罪证中,姚文元的拼凑是最离奇、最出人意料的。姚文元为了证明周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说他早就抵制、反对毛泽东的文艺路线。证据何在?是他按兵不动,还是压制批判文章,或者打报告劝阻?全不是,只是摘引了周扬批判《武训传》的长文(《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的一段话:“我自己很早就看了电影《武训传》,但并没有能够充分地认识和及早地指出它的严重的政治上的反动性。”(注:《周扬文集》第二卷9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白,周扬一是检讨自己认识能力有问题,二是说明毛泽东高瞻远瞩的目光。思想正常的人不会觉出周扬的话里有什么抵触和反对的情绪,因为后面跟接着就用了两万言的篇幅猛批《武训传》。如果按着姚文元的逻辑,认识不到就意味着反对,那么,十亿人中没有一个人是拥护毛泽东的。就是毛泽东自己也成了他的敌人。原因是他不可能时时明确他下一步的思想活动,他下一个行动会是什么。因而象姚文元这种“反推”、“反证”完全属于莫须有的构陷。我当然不是肯定对《武训传》的批判,只是证明姚文元的论证方式纯系捏造、拼凑。
六
但对周扬罪行的剪贴、拼凑还不算骇人听闻的,最让人吃惊的是批判者对人人都清楚的周扬历史的篡改。姚文元《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注:载《红旗》1967年第1期。)堪称这方面的典型。
周扬到底是一面派还是两面派,表面上看似乎不大容易说清楚。姚文元认定他是两面派,他自己好象也能接受这个认定。在同赵浩生的谈话中,他曾做过表白:“整风以后我写的文章很多都是主席看过的,所以后来他们批判我的时候引我的文章并不多,都是引我的讲话。因为文章都是一句句看过,写得冠冕堂皇,而日常谈话最能表现你的思想……,而且死无对证。我在个别谈话中间是讲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东西。后来我也想通了,他们的批评的对嘛。”(注:《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第240页。)周扬的这段话文字不长,内容很深。我们暂且放下“很多文章都是主席看过”、“死无对证”两句所表现出来的狡诈不谈,细细体味一下他对姚文元批判的认同。那绝不是在原有层面的接受,而是在时代观念发生了变化、价值标准出现了位移之后承认“日常谈话最能表现你的思想”的。这个承认埋伏了很深的东西,即我被批判的日常谈话表现了我真实的思想,而那些写在《反人民、反历史的内容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我们必须战斗》、《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里冠冕堂皇的话是假的,它们不能代表我的思想。这个对“两面派”的承认及承认过程中的掉包确实要比“文革”前那个通过正面形式表现出来的周扬
可我却宁愿相信周扬是一面派,或主要是一面派。而这一面派的文化、政治形貌又必须根据他公开发表的文章来确定。周扬在下面可能讲的很多,可它们没对我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什么影响。作为几十年文艺思想斗争的领导者,他主要是靠那些大报告、大总结和我们见面的,正是他的那些大报告、大总结促成和推进了一次又一次当代文艺思想的斗争,写成了一部惊心动魄又残酷无情的历史。鲁迅说得好:“用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想以“冠冕堂皇”、“应付”、“假话”之类的语言轻松地勾掉一段历史或一段历史影印出来的文化人格恐怕不大容易。而象姚文元那样,为打倒周扬,硬说他对建国后几次大的文艺批判运动全部采取消极态度,甚至还和胡风、丁玲、冯雪峰有着共同的反革命文艺观点,同样颠倒不了历史。和周扬论战了几十年,把他精神、思想观点吃得透透的胡风对姚文元的捏造斥之以鼻。当他在监狱里看到姚文元的文章时,他义正词严地斥责姚文元“是在胡说八道”,他拒绝揭发周扬“右”的罪状,拒绝承认周扬对自己、对“胡风反革命集团”采取保护、包庇的立场,因而失去了一个所谓“立功赎罪”的机会。众所周知,早在三、四十年代,周扬就和胡风、冯雪峰、丁玲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胡风代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
椅子说,有你小资产阶级一把坐的,如果乱说乱动,就要打!狠狠地打!”(注:胡风:《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载《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4期第11页。)正象胡风所揭露的,他们“晓得我不肯无原则地随声附和,所以用办法使我不敢工作,不能工作,但却说我不肯工作,在群众中间也散布着我不肯工作的空气。到我参加工作了,用谨慎小心和委曲求全的态度也还是得到了不能工作的结果。党要我用文字为人民服务的,我自己也有一身劳动热情和要求,但客观情况却使我不能劳动……终于造成了我已经完全不能发表文字的情势,但在群众中间又流传着我不肯写文章、消极怠工的空气。”(注:胡风:《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载《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4期第30-31页。)胡风凭直觉预感的“情况……还正在发展,要更进一步发展的”,果然应验。到1955年他们把胡风对林默涵、何其芳五个观点的批判说成是对毛泽东的批判,即胡风把思想改造、深入工农生活等说成是五把刀子,以挑起毛泽东的仇恨。又将张中晓针对旧社会说的话“我恨一切人”掐头去尾汇报给毛泽东,让毛泽东感到他们仇恨新社会,仇恨自己、仇恨一切人,终于下决心把胡风打成死敌。从这一系列情况,我们可以摸清一个问题,在被胡风打成
批判胡风,周扬是如此。批判丁玲、冯雪峰,周扬同样不差毫厘。还在反“右”斗争之前,他们就给丁玲戴上了反党集团的帽子,即便上面发现这是一起错案,他们也迟迟不予纠正,结果拖到反“右”,使丁玲等罪上加罪。打倒“四人帮”后,当党和政府已经承认丁玲的党员身份,作协党组和文联党组的“当事人思想”仍未转变过来,丁玲在作协的党籍也就仍然未得到恢复。非但如此,他们还百般挑剔丁玲庆喜自己“归队”的文章,说她有意“向党组施加压力”。(注:陈明:《丁玲在推迟手术的一年里》,载《新文学史料》1991年1期第117页。)这里的当事人究竟指哪些人,陈明的文章没有具体说明,其实用不着说明。周扬的态度至关重要。从甘露的回忆录《丁玲会见周扬》(注: 载《新文学史料》1991年3期。)所透露的周扬那种冷淡无礼的高慢神情里,还有周扬同赵浩生谈话时仍然对丁玲在延安时期的观点耿耿于怀的口吻中,我们可知周扬其人成见之深、猜忌之重。而这更能证明,周扬在丁玲、冯雪峰问题上投入的精力绝不象姚文元所说,是借机捞取政治资本的假象。如果说周扬处理他们时有过试探、迟疑,那根本不能用来坐实周扬想要放松他们,主要是他对上面的精神不把握,怕弄过杠了反而使自己陷进去。
所以纵论周扬的一贯表现,实际是一面派,而且是和当时的批判者一样的革命派。顶多可以说他在整人时有两面手法。但就思想政治品质和文化品格而言,他还是一面派。而绝不是两面派或“摇荡的秋千”。从三十年代中后期,到文化大革命兴起前,他激进的革命面孔留给人们的印象太深了。抹煞如此一个昭彰的事实,对于“文革”中的批判者来说是极其不利的。他们任意践踏事实、信口雌黄的行为激起了人们对其所谓革命观念的怀疑,同时感受到了他们诛杀同类的残忍。
七
一个曾经令人因惑的问题是,周扬怎么会成了阶下囚。要知道他一直很得毛泽东的赏识。周扬这句话说得较真,“主席对我确实关系很深,确实对我很热情、爱护、培养。整风以后我写的文章很多都是主席看过的”。(注 :《周扬笑谈历史功过》,载《新文学史料》1979年2期。)六十年代初,毛泽东还对他第三次文代会的报告批示道:“这个报告很好,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读了以后令人神往”。(注:《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第450页。)可是事情刚刚过去两年,怎么忽然连发两道金牌,严厉指责文化部门“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注:《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第484页。)并终于一步步逼近周扬、揪出周扬呢?
有一个事实直到今天仍未被人们以明确的语言揭破,这就是周扬在毛泽东领导“文化革命”期间所作的最后一次选择,他追随周恩来想要落实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纠正文艺界一直存在的“左”的倾向。从1961年到1962年不满两年的时间里,他先后领导召开了北京新侨会议、广州会议、大连会议。亲自主持制定了《文艺八条》、参与起草了《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社论,还作了一些报告和讲话。而无论文件、社论、讲话、文章,都是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制定出来、写作出来的。
我们尚无足够的材料确认周扬出于什么目的和动机作出了这种选择。是确确实实想执行中央的精神?还是感到了毛泽东已成为象他自己所说的岌岌可危的少数派,因而急忙投向极有势力的一边?抑或真的觉出了文艺界的问题,试图对自己的工作加以纠正?但无论属于哪种情况,他这一次的选择都是明智的辉煌的选择。周扬一生干了不少惊天动地的大事,他的名字因此而声播海内外。只是他过去的行为没有几个能经得住历史的检视。相反还和日丹诺夫一样成为“左”的符号和象征。亏得历史出现了一次机缘,周恩来以严肃的口吻命令他纠正以往的错误,他的灵魂才获得了救赎和重铸的可能,人们才给他一些谅解和宽恕,否则他会落入深渊永劫不复。周扬转得也快,在前不久的第三次文代会上他还十分卖力地推行极“左”的文艺路线,会后又掀起了批判李何林、巴人等的反修浪潮;而今天他又祭起反“左”的旗帜,把建国后被批判的东西作了一番修整,重新确立了它们作为艺术真理的地位。比如要给作家以创作的民主与自由,要允许反映社会生活的阴暗面、“写真实”,要允许人物、题材多样化、要扩大文艺服务范围、由为工农兵到为全体人民,等等。周扬还公开承认“胡风一向的确抓到了我们文艺运动中真的弱点,这是公式概念化”,“机械论
周扬等的文艺思想的变化能否在他们旧有的储存库里找到依据,我们且不去管它。就说他们的行为里掺杂了一种机会主义的服从,也没什么关系。它们妨碍不了我们对此变化作出的肯定性评价。因为无论从艺术价值论来说还是从社会价值论来说,它都是对真理的实践,都是对美和善的正常秩序的建立。即使实践者抱着不良的动机参与到新秩序的建立中,他也会在人类新的文化方式和文化氛围中获得灵魂的净化和升华。人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存在物,他得不断地在人类的生存关系中谐调自己的行为,抑制自己的恶,张扬群体的、也是自己的善。
姚文元之类的批判家是纯牌的恶魔。他们助纣为虐,为恶而生、为恶而死,从不设法拯救自己的灵魂。他们自己拒绝忏悔,也不准别人良心发现、皈依上帝。他们对周扬执行的审判,追到底,是因为他作出了洗刷灵魂的选择。在那些胜过火烧、油炸的惩罚文字中,你可以摸到他们攻击的焦点——周扬在1961年至1962年的活动。姚文元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设置了两个重要论题,其一是抨击他建国后几次大批判中的表现,其二便是攻伐他在61-62两年里的所作所为,题目叫“大风大浪里”。为什么叫“大风大浪”?难道批判胡风、反右斗争算是小风小浪吗?问题当然不能这样看,但在他们眼里,六十年代初的风风雨雨,更是非比寻常。表面上看周扬的“重大罪过”是遵从周恩来的指示,提出“为人民服务”(姚文元等批之为“全民文艺”)的口号。这个口号相对于“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来说,确实有些调整。但认真考察起来,仍是一个政治色彩很浓的口号,而且还脱胎于毛泽东本人的著作。他纪念张思德的文章叫《为人民服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他把“为人民服务”与“为工农兵服务”并提。此外周扬等对“人民”这个概念的阐释,完全遵照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提法。“为人民服务”* 周扬在“文革”中的落难,为我们提供了一面历史的镜子,它一方面让我们看到:无情地批判别人未见得就能保全自己,另一方面又告示我们“左”的极端:能够不惜牺牲一切来达到自己的目标。这是值得人们深入反思和深刻照察的。
本文是作者专著《文艺批判的背反与人格——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问题研究》中的一节。该书的大部分篇幅将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在1998年内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