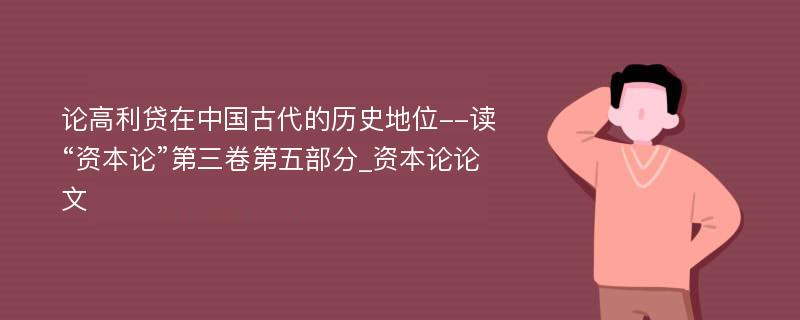
关于中国古代高利贷资本的历史作用——读《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论论文,高利贷论文,第三卷论文,中国古代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编中,首先探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前提下生息资本的形成及构成,然后对这种资本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表现形式即高利贷资本也进行了定性研究,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生息资本理论。在这一理论指导下,随着近年来有关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尤其出土材料、档案材料及民间契约文书的发掘和整理,中国古代高利贷资本的研究得到了较大的进展。随之在几个整体性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如关于高利贷资本的概念,中国古代高利贷资本的历史作用,高利贷资本向近代借贷资本的转化等。而分歧的形成既与材料掌握的不同有关,更与对马克思的这一理论的认识和理解有关。以下拟以历史作用问题为例,主要结合明清高利贷资本的有关事实,从理论上作一些清理工作。
一
因高利贷资本中的相当部分利率高昂、剥削残酷,而且采取了多种手段获取额外收入,在债务人不能及时偿还时,还常常夺取债务人土地、房产及其他财物,甚至差押债务人及其家人为奴为仆,因而不但引起各个历史时期官府的限制、打击,社会各阶层对高利贷资本也常加谴责和攻击。在西方,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认为:“高利贷受人憎恨完全理所当然,因为在这里,货币本身成为赢利的源泉,没有用于发明它的时候的用途……”;“因此,在所有的赢利部门中,这个部门是最违反自然的。”(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一篇第10章。)西方中世纪,高利贷一直被教会视为非法而遭禁止;在伊斯兰教经典中,放债取息也是一种被禁止的行为。至16世纪路德还大声疾呼:“在世界上人类再没有比守财奴和高利贷者更大的敌人了”;“高利贷者和守财奴绝不是正直的人,他们作恶多端,毫无人道,他必然是一只恶狼,比一切暴君、杀人犯和强盗还凶狠……应该把一切高利贷者处以磔车刑和斩首。”(注:路德:《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转引自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第596—597页。)这种观点虽然反映了高利贷受害者的某种义愤之情,但却并未对它的历史的、经济的作用进行科学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全面分析了高利贷资本的本质和历史作用,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经济史学界对中国古代高利贷资本历史作用问题亦作了很多的分析。这些观点,从整体上说以否定为主。首先是一种全盘否定的观点,有些还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联系起来。早期的观点,如刘兴唐以唐代为例说:“这种高利贷,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很可以看出它是阻止了商业资本之发展。在某一个时期中,它固然加速了农村经济破产之过程……”;“政府的高利贷事业,对于农村经济之摧毁,是比私营和寺营来得特别凶狠。”(注:刘兴唐:《唐代之高利贷事业》,《食货半月刊》一卷10 期, 1935年。)傅筑夫论及战国秦汉的高利贷资本时认为:“高利贷资本却从头到尾是社会经济的一种强烈的腐朽剂,它所起的是纯粹的破坏作用”。高利贷资本“是从战国年间开始突出发展起来的货币经济这样一棵毒藤,结出的如此硕大的毒瓜之一”(注: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下册,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545—546页。)。黄冕堂先生在研究清代高利贷资本时亦指出:“作为生息资本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内的表现形态高利贷资本的社会作用全然是消极的。”它总是“迫使再生产在日益悲惨的条件下进行”。“使生产力呈麻痹和萎缩状况。”“高利贷资本越发展,活动越猖獗,则社会生产必定愈加停滞不前。”(注:黄冕堂:《清史治要》,齐鲁书社1990年版,第460—461页。)其次,一些观点虽然从社会意义上肯定了它的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整体上说仍然是否定的或基本否定的。如王彦辉探讨汉代豪民私债的社会影响时指出:“豪民私债被用于生产消费时,客观上具有扶持社会生产的作用。”“有时也能起到支助政府救济灾荒、筹措军费等作用。”但是“它对社会机体的侵蚀性,对社会生产的破坏性是其存在价值的主要方面。因为它加深了官僚政治的腐败,造成了农民大批破产流亡,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注:王彦辉:《汉代豪民私债》,《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 2期。)。乔幼梅则以元代高利贷资本为例指出:“高利贷是促使残余奴隶制得以扩大的有力杠杆”,但是另一方面,“元代的高利贷资本之有力地冲击了旧的土地势力,使这个势力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动摇和衰落”(注:《宋元时期高利贷资本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 3期。)。韩大成研究明代高利贷资本后指出:高利贷资本是“加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重要手段”,“它使小生产者处境更坏更苦,从而使部分社会再生产,不得不在更加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它使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和激化。”(注:《关于时代高利贷资本的几个问题》,载《明代社会经济初探》,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当然不同的观点也是存在的,方行在探讨清代农村高利贷资本时说:“农村高利贷正是以小农经济的存在为条件。”“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高利贷资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作用的增大是一种经济必然性”,虽然因利息率很高,高利贷往往给小农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因而对农民的危害是很严重的,但高利贷资本往往存在一个利率较低的部分,而农民的收入却往往是个变量,因而偿债能力提高、通过借贷维持甚至促进社会再生产也是可能的。(注:方行:“清代前期农村高利贷资本问题”,《经济研究》1981年第4期。 )而在商业货币经济更为发达的一些先进地区,如江南地区,农民的米麦花豆丝的质押借贷可以说是近代企业为生产进行抵押借贷的萌芽状态,高利贷资本发展所形成的金融业由于包括有农民的生产借贷,可以说已开始具有若干成份的资金市场的性质,它扩大了维持农民生产周转的作用。(注:方行:“清代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历史研究》1987年第2 期。)笔者在具体探讨清代前期城市高利贷资本中的生活消费性与经营性、资本性借贷之后,指出:清代前期不但商人的贩运、开铺需要经常地进行资本借贷,手工业、矿业、航运业的生产者及经营者也常进行借贷,表明清代工矿业及商业的运行与高利贷资本息息相关,清代高利贷资本已经开始向近代借贷资本转化。(注:刘秋根:“清代城市高利贷资本”,《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4期。 )陈支平在分析清代闽南乡村借贷契约时指出:“清代福建农村的高利贷,它既从各个方面严重地侵蚀着小农经济,但不可能完全吞噬小农经济,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维持了濒临破产的小农经济的继续运转。”“那种认为在高利贷网罗下小农经济纷纷破家的观点,显然带有很大的片面性。”(注:陈支平:“清代福建乡村借贷关系举证分析”,载《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27页。 )那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又究竟是怎样评价高利贷资本的历史作用的呢?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又在多大的程度上适合于中国古代的情况呢?我想以下三点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第一,马克思正确地评价了高利贷资本的保守性。他指出:“高利贷资本有资本的剥削方式,但没有资本的生产方式。”(注:《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76页。)“高利贷和商业一样,是剥削已有的生产方式,而不是创造这种生产方式,它是从外部和这种生产方式发生关系。高利贷力图直接维持这种生产方式,是为了不断重新对它进行剥削。”(注:《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第689 页。)也就是说,高利贷资本曾经在极不相同的社会形态中存在,不论在哪种社会形态之中,它都与这种社会形态之下的生产和商品流通发生或多或少的关系,但是从整体上说,不但高利贷资本主要源于地租收入、商业利润收入及诸种形式的其他个人及团体的收入,而且其对生产、流通的放贷具有极大的偶然性。也就是说,它是从外部与某种特定的生产方式发生联系的,与社会生产、流通并无本质的联系。因此,生产方式的变革与否并不能由高利贷资本本身来说明;相反地,高利贷资本本身的变革与否,倒必须由生产方式的变革来说明。也就是说,高利贷资本只是破坏小生产者仍然是自己生产条件的所有者的生产方式,因而使货币财富集中起来。但在历史条件并不具备,即生产方式本身并不发生本质变化时,这种破坏及集中作用是不足以成为一种新生产方式产生的媒介的。“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其他条件已经具备的地方和时候,高利贷才表现为形成新生产方式的一种手段;这一方面是由于封建主和小生产遭到毁灭,另一方面是由于劳动条件集中于资本。”(注:《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75页。)
第二,马克思对前资本主义社会高利贷资本历史作用的探讨是从生产方式变革,即由小生产方式向现代社会化大生产转变,或者说从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源的角度所做的一种整体估价,它并没有对高利贷资本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再生产、商业资本运行的关系作具体的研究。当然,《资本论》作为一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不可能也没必要作这样的实证研究。从以上所述马克思对高利贷资本保守性的估计及以下将要叙述的马克思对两种高利贷形式的作用及性质的估价皆可证明这一点。
第三,马克思在评价前资本主义社会高利贷资本的历史作用时,主要只是针对高利贷的两种形式,这就是,“第一,是对那些大肆挥霍的显贵,主要是对地主放的高利贷;第二是对那些自己拥有劳动条件的小生产者放的高利贷。这种小生产包括手工业者,但主要是农民”(注:《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72页。)。因此其历史作用也主要是表现在:“一方面,高利贷对于古代和封建的财富,对于古代和封建的所有制,发生破坏和解体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又破坏和毁灭小农民和小市民的生产,总之,破坏和毁灭生产者仍然是自己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的一切形式”(注:《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75年版,第674页。)。因此, 一方面高利贷资本使小生产方式陷入贫困的境地,因为其利率的高昂足以剥夺小生产者的全部剩余劳动,“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使生产力萎缩,同时使这种悲惨的状态永久化,在这种悲惨的状态中,劳动的社会生产率不能象在资本主义生产中那样靠牺牲劳动本身而发展”(注:《资本论》第3卷,第673—674页。);另一方面它又使奴隶主或封建主陷入高利贷之中, 使他们对劳动者的压迫更加残酷,“因为他自己被压榨得更厉害了”(注:《资本论》第3卷,第675页。)。显然这两个方面都表现为一种消极的作用。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消极作用又表现为一种积极的形式,因为他瓦解和破坏这些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形式,“而政治制度正是建立在这些所有制形式的牢固基础和它们同一形式的不断再生产上的”(注:《资本论》第3卷,第675页。)。同时,如上所述,在其他条件具备的地方,这种破坏还表现为形成新生产方式的一种手段。
综上所述,马克思对高利贷资本历史作用的论述,主要是从生产方式变革角度进行的,他正确估价了高利贷资本的保守性,主要针对高利贷中的两种具有特征的形式,谴责了高利贷资本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小生产方式的冲击和破坏作用。
二
应该说,马克思的这种估价主要是依据西方古代中世纪的历史情况作出的。这一估价理论性极强,因而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也有其局限性。我们必须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对中国古代高利贷资本的历史作用作出新的理论及实证的研究,而不是局限于马克思这些具体结论。
从这一角度看,我想以下几点是应该注意的:首先,西方古代中世纪的历史发展道路与中国是完全不同的。在西方中世纪,城市与乡村是对立的,作为商业、货币资本主要活动领域的城市是独立的,10世纪至11世纪城市商品经济复兴以后,拥有货币权力的城市商人、手工业者和高利贷者通过赎买乃至武装对抗,至12世纪,终于获得城市自治权,形成了初期的市民社会,城市与乡村开始分离。城乡的这种分离和对立,既削弱了封建领主的权力,更有利于城市经济交流和商品流通;相反在中国却并没有产生这种对立和运动。中国古代,在秦汉时代,也与罗马时代一样,“上层社会的田园理想渗透着整个社会,由于地主乡绅从社会上、政治上和文化上支配着农村和城市。城市本身不是一个有机体,而是在城市——农村连续统一体的更广泛发展过程中一个机构”(注:《欧洲经济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1页。)。因此,虽然在19世纪以前,中国的城市化程度可能并不比西方低,但是因为中国没有经历类似西方的历史运动,这种“城市与乡村无差别的统一”(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引尼布尔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78页。)也就没有被打破, 城市始终基本上是各级封建政治和军事中心,商人、手工业者、高利贷者虽然拥有货币权力,但他们没有自己独立的活动地盘,没有相适应的行政、司法权力的保护,也就不可能形成相适应的市民社会,他们只有仰仗封建的特权,与封建主权力融为一体,才有可能得到保障和发展。与这种情况相对应,中国封建社会在生产上形成了小农和小手工业牢固结合的结构;在流通中市场的狭隘性,缺乏大规模的国际贸易市场;在分配上则形成了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的体制。(注:参见《资本主义的萌芽》第六章,人民出版社1985年。)
处于这种不同的整体社会经济条件下的高利贷资本,其活动形式、内容及其历史作用与西方当然是有区别的。我们应该充分考虑到这种区别。
其次,既然马克思在这里所评价的只是高利贷资本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两种“具有特征的形式”,所谓“具有特征的形式”无非是说,这两种形式是高利贷资本作为生息资本最适应以自耕农和小手工业主占优势的生产方式的要求,反映高利贷资本与这种生产方式的联系的本质的形式;那么很自然的一个问题就是,既有“具有特征的形式”,就应该还有不具有特征的形式,或者说“从属的形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并未对后者进行具体的研究,因而对其作用也就没有加以评论。但马克思并未否认它的存在。如马克思言:“商人借货币,是为了用这个货币牟取利润,是为了把它作为资本使用,也就是为了把它作为资本耗费。因此,即使在以前的社会形式内,贷款人对于商人的关系,也完全和它对于现代资本家的关系一样。”(注:《资本论》第3卷,第671页。)也就是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也存在商人为了牟取利润而借货币的形式。那么与以上两种“具有特征的形式”相比,这种形式的地位怎么样呢?马克思在谈到以上两种“具有特征的形式”之后说:“我说的是具有特征的形式。同一些形式会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再现,但只是作为从属的形式。”(注:《资本论》第3卷,第672页。这种联系的本质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它是从外部与这种生产方式发生联系,与生产过程并无本质联系;二是主要适应小生产者的支付需求。)由此可见,既然前资本主义社会高利贷资本存在“具有特征的形式”,而这种形式会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作为“从属的形式”再现,那么我们应该说,前资本主义社会高利贷资本也存在“从属的形式”,而且这种形式会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作为“具有特征的形式”再现。这一关系可图示如下:
放贷形式及属性 对小生产者及 对商人的放贷
资本种类地主显贵的放贷
高利贷资本具有特征的形式 从属的形式
↓ ↓ ↓
近代借贷资本 从属的形式
具有特征的形式
表中,箭头表示资本之间及资本的不同形式之间存在着转化的关系,即高利贷资本会转化为近代借贷资本;高利贷资本中的“具有特征的形式”会转化为近代资本下的“从属的形式”;前者中的“从属的形式”会转化为后者中的“具有特征的形式”。
第三,如果抛开马克思对历史作用的估计(即其保守性的估计)不论,则其对高利贷资本中“具有特征的形式”,即对小生产者、地主的放贷的经济作用是作了完全消极的估计的。马克思甚至特别针对亚洲说:“在亚洲的各种形式下,高利贷能够长期延续,这除了造成经济的衰落和政治的腐败以外,没有造成别的结果。”(注:《资本论》第3 卷,第675页。)马克思对亚洲(印度、中国、 伊斯兰地区)高利贷资本有多少了解,我们不太清楚,但这些具体论述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于中国则是我们必须考虑的。这里且不谈高利贷资本对地主的消费放贷的作用问题,只就其对小生产者主要是小农的生产性、生活性放贷的作用作些探讨。我们知道,中国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是一种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的模式,或者说是一种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相结合以追求温饱的模式。在这种生产模式下,小农首先必须确保自给性的生产,但同时它也有一定的甚至是规模比较大的商品性生产。(注:方行:《清代经济史》(打印稿)。小农经济篇第二章、第七章。)小农的生产及消费都是在家庭内部实现的,这里既有实物的平衡,也有价值的平衡,这种经济的运行既有实物的运动,也有资金的运动。随着封建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资金运动的地位日渐突出,这样作为货币资本运动形态的高利贷资本在小农的再生产和生活中的地位便提高了,至少从宋代开始,关于小生产的生产与生活普遍地依赖于借贷的言论便屡屡见于文献之中。这种借贷的作用怎么样呢?需要分别予以论述。如果是纯粹的应急性的生活性借贷,他们可以借此延续家庭人口的生存,使再生产在原有的或缩小的规模上反复;如果是生产性的借贷,尤其是在一些经济性作物或开发性、经营性农业生产中的借贷,则有可能维持原有规模的再生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再生产。
当然,这一切是否成为可能,还得考虑以下两个因素:一是利率的高低,如果利率特别高,不但占有了农民的剩余劳动,还要占有其必要劳动,这样便只能使再生产条件越来越恶化;二是,借贷之后,是否还有其他的意外因素的冲击,如官府临时的急征暴敛、水旱蝗灾、战争动乱以及家庭人员的疾病死亡等。这些因素既是导致小农借高利贷的重要原因,又是促使小农借贷的回旋余地缩小的重要因素。因此,如果利率特别高,而且与其他意外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小农便只有走向破产,甚至生存都会成为问题,即使历尽千辛万苦维持了再生产,也会在高利贷网罗下,永世难得翻身。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高利贷都会使借贷的小农走向破产,因为利率适中或较低、各种天灾人祸较少的情况也同样是普遍的,因而通过借贷维持乃至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再生产也同样是普遍的。尤其是在封建社会后期,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小农家庭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获得货币收入,提高偿债能力;另一方面小农的纯生产性的借贷在增加,这种借贷,尤其是其中经济性作物种植或开发性农业而进行的借贷,因借贷额较大,风险相对较小,且其中一部分还与其经营收入相关,故利率相对较低。在这种情况下,高利贷资本对小生产者发挥积极作用的可能性也就增大了。总而言之,我们对高利贷资本在小农及小生产者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必须注意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第四,如上所述,马克思对高利贷资本中不具特征的形式即商人的经营性、资本性借贷并未具体研究,那么对中国古代高利贷资本中这种借贷形式的作用我们又该怎样估价呢?对于这一点,学术界尚无专门探讨。笔者曾在一篇论文中详细叙述了清代城市工商业乃至航运业中依赖借贷经营的情形,然对其作用亦未作具体评价(注: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4期。)。这里结合中国古代城市商品经济的特点, 谈几点浅见。
在中国古代,与生产中农业手工业紧密结合及生产的分散性相适应,中国封建社会的流通市场也是狭隘的。整体上说,这种市场共有四种类型:即地方性小市场(墟集贸易)、城市市场、区域市场和全国性市场(长距离贩运贸易)。其中城市市场是以贵族、官僚、士兵、奴仆的消费需要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因此这种贸易并不反映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发展,大部分城市是封建政治、军事中心;虽然明代以来,兴起了一大批商业城市,但直至近代仍不占优势;而区域市场则反映的是各地区因不同的地理条件和生活习惯形成的特产贸易,虽属商品经济,在相当程度上也残留有自然经济的痕迹;全国性市场自宋代以后有所发展,表现在粮食、日常生活用品长途贩运得到发展,主要是粮食和手工业产品之间的交换。但这种市场直至明清时期仍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很少反映农业的地区分工。因此,封建社会市场是以地方性小市场为主的,在这种市场上活跃着的是以中小商人甚至小商小贩为主的商人队伍,他们的主要来源是离开生产的农村人口。这种中、小商人的资本规模是狭小的,许多小商小贩甚至没有多少资本核算,其营运资本和家财界限并不很清楚,而其资金也是经常匮乏的。为此,他们采取了争取亲朋好友帮助、与人合伙、领取有钱人资本(注:必须定期交纳利钱。)、借贷资金等方式,但其中使用最广的还是最后这种借贷资金的办法。当然大商人的经营也是需要借贷的,尤其是他们对流动资本的需要更是经常性的。因此,中国古代高利贷资本对商人的资本放贷便相当发达。虽然比较具体的、时间比较早的商人帐册非常罕见,但从其他方面的一些文字记载也发现,至少在明清以后,商人通过借贷或与人合伙获得经营资金相当普遍。因此,如果说封建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有赖于商业资本总量的扩展和单个资本规模的增加的话,那么,这种扩展和增加在相当程度上是与高利贷资本的活动分不开的。
【收稿日期】 1999—03—15
标签:资本论论文; 高利贷论文; 资本有机构成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古代货币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生产方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