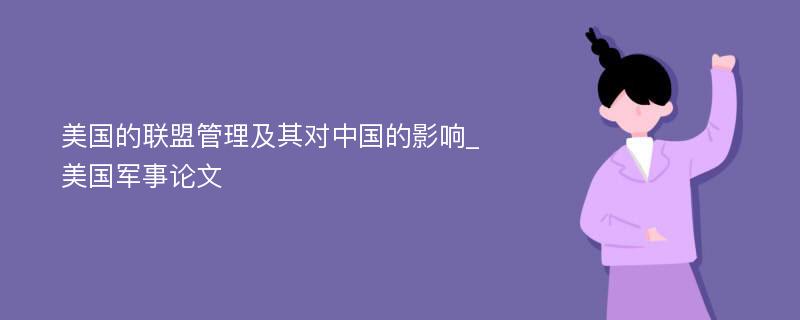
美国的联盟管理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中国论文,联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当今国际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拥有正式和非正式盟友最多的国家,其盟友遍布全球。由于一些联盟条约和协议的保密性,也由于联盟关系的实质会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而出现巨大变动,对于哪些国家是美国的盟友,美国政府也没有做出确切的界定。在美国领导人和官方文件的表述中,盟友和伙伴这两种安全关系通常被并列在一起讨论。①结合美国国务院发布的防务条约目录和国际关系学者常用的联盟数据库来看,在北半球,美国自冷战初期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经过数次扩大,已成为其领导下最大规模的多边军事联盟,成员国多达28个。在亚太地区,美国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保持着双边联盟关系。在拉美,美国与21个拉美国家签订有《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在中东地区,美国与以色列维持着众所周知的非正式联盟关系。②如果说这些联盟成立之初是以某个或某些国家作为假想敌,旨在应对共同的安全威胁,那么今天它们更多地提供了维持美国全球主导地位、推进全球战略目标的平台。 在维持这些双边和多边联盟的过程中,如何维护和管理盟友一直是美国决策者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甚至是一个难题。联盟管理既涉及战略规划、防务部署、军事合作、成本分摊等联盟内部事务,也涉及对盟友与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管理,尤其是防止盟友卷入美国不希望介入的冲突之中、调解两个有矛盾的盟友之间的关系以及促使盟友在大多数国际和地区事务上与自身保持政策一致性。鉴于有关美国联盟管理的既有研究多关注于某一具体的双边或多边联盟的内部关系,对美国进行联盟管理的目标、手段及其限度的探讨并不多见,本文试图从总体上探讨美国的联盟管理及其对中国周边环境和对外关系的影响。 一、联盟管理:美国联盟体系的核心目标 在国际政治中,联盟作为国家间组合与合作的一种形式始终占据核心地位。乔治·利斯卡在1962年出版的首部尝试系统建构联盟理论的著作中写道:“讨论国际关系不可能不涉及联盟,二者只是名字上的区别。”③之所以将联盟与国际关系画等号,是因为在利斯卡看来,国际关系本质上就是各国合纵连横寻找朋友以共同应对威胁和谋求利益的活动,结盟和反结盟是最为基本的国际关系现象。尽管当今时代联盟的性质和具体形态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联盟仍然是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实际上,美国与俄罗斯正在欧亚大陆展开的竞争和较量是围绕推进或阻止北约持续东扩展开的,而在东亚地区,美国也在强化与各个盟友的关系,推进其“亚太再平衡”战略以防范中国对美国主导地位的挑战。 冷战结束之后,有人一度认为联盟失去了意义,特别是对美国这个超级大国而言,无需再维持庞大的联盟义务,北约和其他联盟将难以为继。这种观点建立在现实主义关于联盟形成和瓦解的理论之上,认为“联盟通常是为了应对外部威胁而组建,它们的凝聚力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威胁的强度和持续时间……导致它们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最初共同抵御的外部威胁减弱或消失”。④而现实是美国所主导的一系列双边和多边联盟不仅没有解体,还在不断调整战略目标、接纳新成员、扩展势力范围。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的这些双边和多边联盟是分立而非统一的联盟,但是由于联盟在美国对外战略中被当作一个不可或缺的整体来进行规划,在学术讨论中将以美国为中心的联盟关系视为美国主导的联盟网络或联盟体系仍然是适当的。在美国政府发布的一系列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报告中,盟友的重要性都得到了反复强调。2010年奥巴马政府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报告“国际秩序”一节,专门论及确保强有力的联盟关系的重要性,指出“美国、地区及全球安全的基础仍然建立在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关系之上,而我们对他们的安全承诺不可动摇”。⑤美国国防部于2014年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则将美国的实力优势、强大的联盟和伙伴网络以及美军的人力资本与尖端技术并列为美国可以依靠的三大比较优势。⑥从这些官方表述可以看出,对美国而言,联盟体系不是传统意义上应对明确和潜在军事威胁的手段,而是维持其全球领导地位及其所主导的国际秩序的重要工具。布热津斯基也曾不禁感慨:“美国在全球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由一个确实覆盖全球的联盟所组成的精细体系组成的。”⑦ 在关于美国联盟体系的研究中,一个值得探讨但缺少关注的问题是:美国如何维护和管理其规模庞大、成员众多的联盟体系?在联盟政治研究领域,这个问题属于联盟管理(alliance management)的范畴。⑧从狭义上看,联盟管理是指联盟内部成员国之间对各自承担义务、应对威胁等的分配,主要依据的是所签署联盟条约的具体条款和规定;而在广义上,联盟管理包括联盟成员为协调各自行为而做出的正式或非正式安排。在此,我们从广义上讨论美国的联盟管理,因为美国不仅希望其盟友承担联盟条约所规定的义务,还试图在更广泛的议题上塑造盟友的政策和行动。 当前,美国进行联盟管理的需求是由美国的总体战略目标以及联盟关系在其中的定位决定的。由于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全球战略的主要目标是霸权护持,即维护其霸权地位、防范和压制潜在竞争对手,⑨美国的联盟管理也主要服务于这一目标。比较当今美国的联盟体系与历史上的大国包括美国自身的结盟行为,我们也可以发现当前美国联盟管理目标的差异。历史上,作为防范威胁、保障安全的一种手段,即使防范对象会发生转变且盟友也会变换,联盟所针对的安全威胁都是相对明确的。而在后冷战时代,没有哪个国家或国家集团能够在实力上与美国相匹敌,进而也无法对其国家安全和生存构成实质威胁,美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推进任何战略目标。在这种情况下,联盟管理问题不完全是由安全承诺的范围和限度所引起的,“受牵连”与“被抛弃”这对经典的联盟困境也不是美国决策者在思考联盟管理时的主要考量因素。⑩相反,集体行动问题在美国领导的非对称联盟中表现更为突出,除非国家安全明显受到威胁,否则联盟成员都有减少为集体利益作贡献的动机,导致美国必须就诸多问题与那些较小的盟友进行讨价还价。(11) 在缺少共同安全威胁这一最重要的联盟“黏合剂”的情况下,美国维持庞大的联盟体系就需要根据形势变化为联盟确定新的目标,比如支持北约一步步东扩的理由是防范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恐怖主义、防止核生化武器扩散和进行人道主义干预,而执行这些任务被美国官方认为是“维护公正而可持续的国际秩序”。(12)但正如一些研究所指出的,美国维持对欧洲的主导、牵制德国和打压俄罗斯等权力政治思维仍然是支配北约持续扩张的动力。(13)不难理解,当北约不断向中东欧地带扩展、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时,俄罗斯只能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使用武力以阻止它们加入北约,防止安全环境持续恶化。(14) 联盟使命的扩展和泛化实际上加大了联盟维持的难度和联盟管理的必要性。美国无法时刻用一个确定的共同安全威胁来团结盟友,而又希望它们能够服从美国的战略需要,这导致不同盟友在处理与其他国家(包括美国的其他盟友)之间的关系、应对具体的国际和地区事务方面都很容易产生政策分歧。因此,在霸权护持这一总体目标下,美国进行联盟管理的具体目标是让一个或多个盟友在特定议题上采取美国所期望的立场、政策和行动,特别是在美国与盟友之间出现意见分歧时协调和管理盟友,从而使它们服从于美国的战略需要。比如,自冷战以来,成本分担问题一直是美国与其欧洲盟友之间产生矛盾的主要焦点,美国官员常常批评欧洲国家的国防投入不足以抵御威胁、将安全保障重任都推给美国,并敦促它们提高国防开支、增加军备采购和研发。当然,美国也不希望欧洲国家防务走上独立自主之路,因此在欧盟发展自主防务问题上采取了有限支持的立场。此外,在美国历次对外军事干涉行动中,美国决策者都需要说服尽可能多的盟友追随美国,从口头到物质上提供各类支持,包括政治表态、派遣军队、后勤补给、情报共享、经费分担等。 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主导的双边和多边联盟处于不断调整转型之中,通过扩展任务范围、调整军力部署来寻求更好地适应新的战略环境和战略目标。伴随国际形势变化和联盟自身调整,联盟管理的需求更加突出,成为维系联盟体系、使其按照美国意愿运转的主要难题,而联盟管理进程也始终体现于美国与其盟友的互动之中。 二、美国联盟管理的模式与手段 在维持联盟过程中,联盟成员之间的利益需求容易出现不一致,而联盟成员又拥有独立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的自主性,这是引发联盟管理问题的主要症结。为了避免内部意见分歧和政策不协调,维持联盟的凝聚力、协调性和有效性,使其在应对特定威胁或其他议题时能够正常运转,不同类型的联盟通常有正式或非正式的管理方式。根据联盟成员间协调方式的差异,联盟管理在理论上可以分为三种模式,分别是利益协调式管理、制度规则式管理和霸权主导式管理。 第一种模式强调联盟成员国之间就各自的需求展开协调,达成新的利益共识。共同利益是联盟形成的基础,也是联盟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当然,联盟成员之间由于受各自外交政策目标、国内政治体制以及领导人等因素影响,必然会出现各自利益冲突甚至对立的情况,也就是说,联盟的形成和运作始终伴随着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博弈。基于共同利益协调的联盟管理强调各国之间进行讨价还价,在博弈过程中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即“帕累托最优”。与此同时,成员国在博弈中的地位取决于对联盟的需求、承诺以及议题关联程度。(15)在这三方面占据优势的国家具备较强的讨价还价能力,可以促使其他成员做出更多让步。这种联盟管理模式通常出现在实力相对均衡的国家组成的对称性联盟中,彼此间相互制约较强,愿意就利益分歧展开协商。(16) 第二种模式将联盟视为一种安全制度,关注规则安排在联盟管理中的作用。按照这种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联盟观,联盟与其他领域的国际制度和机制安排类似,为成员国提供了有效沟通、交换信息的平台。(17)联盟将成员国之间的安全合作制度化,并且形成了各个成员都需要遵守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只有遵循相关的行为准则,联盟才能作为一个组织最大限度地发挥效用,增进联盟成员的利益最大化。因此,联盟本身的制度安排以及相应的一系列行为规范为联盟成员解决分歧提供了依据。 第三种模式强调美国作为霸权国或等级体系的主导国对盟友进行管理和控制的功能。根据近来兴起的等级理论,当今国际体系实际上是美国领导的等级体系,非独立的联盟关系是等级的一个重要维度。(18)作为等级体系的主导国,美国为成员提供安全保护和市场准入这两项重要的公共产品,换取它们对美国霸权地位的认可。在这种体系下,从属国愿意接受美国的领导,而美国享有较高的权威和威望。按照这种观点,美国主要通过仁慈地对待盟友(从属国)来让它们尊重美国的权力和理念,只有在必要情况下,才使用强制手段对盟友发号施令。(19) 上述三种联盟管理模式的理论分歧涉及如何看待美国领导的联盟体系的性质问题:它是一个基于共同利益的联合?或是一项正式的制度安排?抑或是霸权的附属?在现实中,美国的联盟体系可能是一种混合物,这三个维度都有所体现。就不同的联盟关系而言,上述三种模式的表现并不一致。一些学者认为,北约作为多边联盟的制度安排更多地体现出美国将北约盟国视为平等伙伴的意愿,而美国与亚太盟友的双边联盟明显是一种支配—从属关系。(20) 在具体议题上,美国采取的联盟管理方式也会存在差异,比如美国与盟友就战略目标、成本分担、军事部署等问题经常通过协商和讨价还价达成解决方案,而获取盟友在更广泛的议题上的支持,则需要动用更多的激励手段。在处理与盟友关系的实践中,美国通常会使用说服、诱导和强迫这三类手段,以弥合和协调与盟友之间的政策分歧,让盟友采取一致行动。 说服作为一种言语行为是美国最常用的联盟管理手段。在面对特定的国际事件或局势时,美国领导人、高级官员和政府发言人通常会做出表态,要求或敦促盟友支持美国的政策和行动。这类寻求盟友支持的表态通常表达了美国的期望以及维护共同利益和价值的愿景。另外,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国会也会经常以出台修正案和决议案的方式,就美国与盟友之间的成本分担问题发表意见,敦促美国盟友增加国防开支。1984年,参议员山姆·纳恩和威廉·罗思首次提出美国应在欧洲撤军以迫使欧洲盟友加强军备的《纳恩-罗思修正案》,在美国国内和欧洲盟友间引起巨大争议,尽管该修正案当年未获通过,但自1985年起参议院就经常性地通过此类修正案和决议案。(21)在2001年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前,美国曾利用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威胁对盟友和其他国家展开游说,试图组成规模庞大的联合阵线来展开军事行动。在美国的努力之下,在这两场战争中,分别有48国和40国参加了最初的军事打击,或者提供了情报和财力上的支持。(22)当然,这种口头表态通常不涉及后果和代价,也可能得不到盟友的支持,在使用武力这一争议问题上更是如此。伊拉克战争之前,尽管美国投入相当大的资源对德国、法国、加拿大等北约内部的主要盟友进行游说,但是这些国家坚持对伊拉克进行军事打击应首先获得联合国授权。 为了让盟友服从美国的意志,美国在多数情况下会给盟友许诺或提供实质性的回报,主要是给予更多经济和军事援助、对其出口尖端军事装备等,以正面诱导和激励保证它们对美国的拥护和支持。20世纪70年代末,为了支持埃及和以色列的和解,美国承诺对这两个国家提供长期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并且为此而投入了大量资源。这两个国家在达成和解之后所获得的美援数额曾一度占美国全年对外经济援助总额的40%左右,而且在2001年“9·11”事件发生以前,埃及和以色列一直是每年获得美国经济援助最多的两个国家,且军事援助也呈现类似趋势。(23)2002年,美国因伊朗核问题加强对伊朗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制裁,并且允许对与伊朗央行结算石油进口费用的外国金融机构实施制裁。当时,日本是伊朗石油的第二大买家,而其他主要买家也集中在亚洲国家,美国曾派高官赴日本、韩国和印度等国游说,鼓动这些国家减少对伊朗原油的依赖。在日本同意大幅度减少进口伊朗石油之后,美国使日本和10个欧盟国家的金融机构免受伊朗金融制裁。(24) 尽管美国在多数情况下倾向于使用言语行为和正面激励的手段来促使其盟友按照美国的意愿行事,但在必要时美国也会对不服从其指令的盟友采取惩罚措施,威胁或实际采取制裁措施以强迫它们服从美国的要求。比较典型的例子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抵制战争的美国盟友最初都被排除在伊拉克重建项目之外,美国国防部还于2003年12月5日发布了一份有资格参与竞标的63国名单,这被普遍视为美国对不支持伊拉克战争的法国、德国和加拿大等国的惩罚。(25)在实践中,美国的惩罚性措施包括削减经济和军事援助,威胁在冲突中不提供联盟义务所承诺的支持,暂停诸如军备交易、技术合作、高层对话等军事合作。与非盟友相比,美国不太可能威胁或实际使用武力来改变其盟友的政策,动用这些惩罚性手段可以让盟友付出潜在或实际的代价。当然,比较来看,对盟友使用武力并非不可能,冷战时期苏联就曾出兵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两个华约成员国,也曾对中国动武。 三、美国联盟管理的成效及其限度 在考察美国管理盟友的手段基础上,我们有必要对其管理的效果进行评估。美国的联盟管理是否取得了成效?如果从美国霸权护持的总体目标来看,答案是肯定的。有学者注意到,美国向盟友提供安全保护和市场准入这两项公共产品,促使它们在两个关键问题上有助于美国维持其主导的等级或朝贡体系:一是承认美国的霸权地位,二是愿意效仿美国的政治体制和理念。(26)另外,从防范潜在竞争对手角度来看,美国推动北约东扩的进程也得到了北约盟友的支持,极大压制了俄罗斯的战略空间。 如果考察促使盟友在重大问题上与美国立场一致的具体目标,我们可以发现美国的联盟管理记录好坏参半。考虑到美国的盟友众多,在此,我们以美国一英国和美国一以色列这两对盟友关系,来展示美国在管理盟友方面的具体实践及其成效,进而分析美国在支配盟友行动问题上面临的制约因素。 早在1944年,时任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就提出英美是一对“特殊关系”,(27)此后两国领导人对提及英美特殊关系也从不避讳。由于两国拥有共同的文化、价值、历史联系,也经常具有相似的战略目标,自冷战以来,英国的外交政策总体上都采取了追随美国的政策。这对关系之特殊,莫过于伊拉克战争期间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为极力支持小布什而撒谎,以致深为英国民众所诟病。不过,从二战后英美关系的发展来看,两国在重大问题上意见相左、行动相悖的情形并不少见。就美国的联盟管理而言,1956年美国未能阻止英国和法国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针对埃及的军事行动是一次重要事件。是年7月,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英法为夺回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将苏伊士运河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安理会否决了英法要求埃及接受“国际管理”制度的提案。在此背景下,英法决定以武力解决苏伊士运河的所有权问题。1956年10月,英法和以色列一起发动了向埃及的进攻,“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从另一方面看,尽管未能制止英国发动此次战争,在事件发展过程中,美国还是为迫使英国撤军做出了努力。通过在联合国谴责英国、对英国实行非正式的石油禁运以及实施经济制裁等方式,美国迫使英国于一周之后同意撤军,并于同年11月全部撤离埃及。 美国与以色列是一种备受争议的特殊联盟关系。长期以来,美国在巴以问题上不分是非曲直地支持以色列的行动,使一些美国学者也批评以色列借助在美国的庞大犹太人和游说集团“绑架”了美国外交政策。(28)根据杰弗里·普利斯曼的研究,美国至少在三次重大事件中未能阻止以色列的行动,分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色列发展核武器、1967年发动中东战争以及1982年入侵黎巴嫩。在这些事件中,美国并没有过于激烈地表态或制裁。而在1973年以色列曾试图对埃及和叙利亚发动先发制人打击和1977年计划入侵黎巴嫩的行动中,美国领导人都曾威胁削减对以色列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从而改变了以色列的计划。(29)下文还会论及,2005年为了阻止以色列向中国交还中方委托以方维修的无人机,美国动用了非常严厉的制裁措施,部分达到了限制以色列对华军事出口的目的。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美国试图通过联盟内的政策协商和成本收益预期调整来管理盟友,这些努力的成效并不一致。仅从美英和美以两对关系来看,当美国仅仅在言语上敦促或表态时,比较难以达到限制盟友行动尤其是其进行军事行动的目的,而在美国可能或实际动用制裁手段的情况下,这些盟友通常会克制自己的行动或支持美国的行动。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利益契合度、安全与自主性在联盟关系中的权衡取舍、盟友之间存在的矛盾以及美国国内政治制约等因素,影响着美国管理盟友的意愿、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效果。 第一,美国与其盟友在具体问题上的利益分歧难以弥合,导致它们之间无法就政策矛盾达成一致。追求和实现自身利益是国家制定和执行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每个国家的领导人和政府都会对本国的国家利益有基本的认知和排序,而在具体问题上的利益分歧容易导致盟友间出现政策不一致甚至冲突。显然,一个盟友追求自我利益的需求和意愿越强烈,对联盟的离心倾向越大,美国与其之间的利益契合度就会越低,通过协调来管理分歧也会更有难度。例如,1951年美国通过签订《澳新美安全条约》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立了正式同盟关系,美国为新西兰提供安全保护,新西兰则在对抗苏联和越战中给予美国支持。越战结束后,随着新西兰国内对越战的反思以及对美国核动力航母访新的担忧,新西兰开始强调摆脱美国的控制并制定独立的地区政策。同时,新西兰国内工党上台,执行坚定的反核政策,拒绝美国军舰访问新西兰的要求,由此导致两国于1987年实际中止或冻结了联盟关系。(30) 第二,安全与自主性之间的矛盾加剧了美国盟友的离心倾向,而那些拥有较强实力、具有独立外交传统或强势政治家的盟友尤其会让美国的联盟管理效果大打折扣。詹姆斯·莫罗的研究发现,联盟关系存在着安全和自主性两项价值的交易,在非对称联盟中,小国需要牺牲更多的自主性来换取主导国的安全保护。莫罗就此认为,实力不对等的国家之间形成的联盟更容易维持。(31)但问题是,在多数情况下一国所面对的威胁来源和程度并不是确定而紧迫的,当安全威胁比较模糊时成员国的安全需求会得到缓解,追求自主性的倾向就会增强。二战后,法国外交的主要任务是在美苏对抗中维护法国的独立和主权,并恢复其大国地位。结合外部的经济援助和自身的经济计划,法国的经济快速恢复并迅猛发展,良好的经济形势为戴高乐推行独立的外交政策提供了物质保障,在此基础上,戴高乐坚持发展独立核力量。美国虽一度试图将法国的核武器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保持其核垄断地位,但是未能奏效。20世纪60年代,戴高乐领导的法国之所以退出北约组织,主要是因为戴高乐认为,维护法国外交政策的自主性比同美国一道对抗苏联更重要,而退出军事一体化不会对法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32)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所针对的威胁变得更加不确定,在欧洲尤其如此。在新世纪以来美国进行的多次海外干涉行动中。施罗德和默克尔领导下的德国越来越倾向于不支持甚至是反对。 第三,美国的盟友之间可能存在根深蒂固的矛盾,在特定议题上难以协调一致,甚至可能引起联盟内部的冲突。(33)美国的盟友存在潜在和实际冲突的情形有两种:一种是冲突方之间因参与美国主导的多边联盟而存在联盟关系,比如希腊和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曾围绕塞浦路斯问题展开争夺;另一种是冲突方与美国是盟友、但两国之间并没有联盟关系,比如韩国和日本之间就存在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美国盟友间的矛盾在严重情况下会导致激烈冲突,阻碍美国协调盟友行动的努力。近年来,美国积极推动韩国和日本的安全合作,其中三方在军事领域情报共享是一个重要议题,但由于韩国国内对日本的反感和担忧,韩日之间无法就军事情报共享达成协议。 第四,由于美国国内政治体制和外交决策模式的影响,国内因素也会制约美国管理联盟的意愿和成效。这些国内政治因素主要涉及政府与国会之间的分歧、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掣肘和国内舆论等。上文提及的1984年《纳恩-罗思修正案》引发的争论表明,在美国国会内部、国会与行政部门之间,有时也难以就威胁与盟友达成一致。而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通过对以色列院外游说集团的深入研究指出,国内政治确实制约了美国对以色列政策和在中东问题上的总体政策,让美国在以色列涉及的绝大多数议题上选择义无反顾甚至毫无道理地支持它,阻碍了美国推进巴以和解的决心,也使得中东问题长期陷入恶性循环。(34) 综合上述因素,美国的超强实力并不意味着美国的指令都能得到贯彻,其协调盟友采取一致立场的努力并不总是奏效,当需要盟友牺牲自身利益、放弃外交政策自主性时尤其如此。 四、美国联盟管理实践与中美关系 自冷战时期以来,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形成和演变就与中美关系的发展密切关联。在中国崛起过程中,这一联盟体系也是中国必须面对的地区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管理亚太盟友以及其他盟友的实践,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双边关系以及中国在地区合作中的作用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尽管美国的联盟管理行为在防止地区冲突升级方面能够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通过管理盟友来防范和牵制中国的意图比较明显,在中国实力崛起和地区影响力扩展的背景下,这一点显得更加突出。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看,美国的联盟管理对中国的影响突出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美国在亚太地区加强联盟管理的举措冲击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影响中国的战略安全态势。无论是在冷战时期还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调整了与中国存在争端的盟友的安全关系,通过强化联盟承诺、提供军事支持等方式提高盟友对抗中国的能力,从而导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紧张、恶化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关系。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联盟体系和军事存在是美国塑造地区安全格局、参与地区权力竞争的主要依托。当前,美国正在进行局部战略收缩、削减国防开支,与此同时,美国试图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和资源投入,鼓励盟友承担更多义务。(35)在奥巴马政府积极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进程中,加强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这五个亚太盟友的安全合作是美国亚太战略的主要支柱之一。美国将这些联盟关系视为“亚洲安全的基石和亚太地区繁荣的基础”,并希望通过它们塑造一系列地区安全议程,包括“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恐怖主义、气候变化、国际海盗、传染性疾病与网络安全”。(36) 在日本本土、冲绳、韩国、关岛、菲律宾、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美国加紧军事调整和部署,并且与东亚盟友频繁举行军事演习,试图对潜在对手进行威慑。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东亚盟友和安全伙伴也担心不得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改变原来大多数国家采取战略对冲或两面下注的格局。东亚国家希望引入美国来制衡中国的影响力,而美国也积极向相关国家提供支持,这两方面的合力导致美国的东亚盟友和安全伙伴在安全上更加倚靠美国。 第二,美国对日本、菲律宾等东亚盟友的安全承诺潜在地介入中国与相关国家的主权争议。当前,随着东亚地区国家间领土、领海和海洋权益争端愈加突出,尤其是日本、菲律宾等美国盟友在钓鱼岛、黄岩岛等问题上挑起事端,美国通过重申其联盟承诺、表达潜在介入的可能性,从而支持和鼓励了这些国家的行为。日本和菲律宾等美国盟国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美国在这些争端中强化了与盟友的安全合作,甚至表达了介入的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为其盟友在领土争端中的挑衅行为撑腰。对于美国借盟友关系介入中国与相关国家的领土主权争议的行为,中国官方表达了反对意见。2013年10月7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第五次美日澳三边战略对话部长级会议发表涉及东海、南海问题内容的联合声明答记者问时指出,“美、日、澳彼此是盟友关系,但这不应成为介入领土主权争议的借口,否则只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损害各方利益。”(37)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最近在美国发表演讲时也指出,“双边联盟不应损害任何第三方利益,也不应影响地区和平与稳定。”(38)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心态也存在矛盾。一方面,美国希望盟友在防范中国方面承担更多责任,因此美国支持这些盟友增加国防预算和采购尖端军事装备,也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另一方面,美国希望稳定中美关系,不希望被盟友的行动打乱其战略部署,尤其不希望卷入自己不希望的军事冲突。(39)由于这种矛盾,美国的联盟管理也可能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比如有学者就指出,美国的联盟管理牵制了日本在国防和军事上的自主性,使得日本无法成为一个有核武器武装的独立大国。(40)另外,在涉及钓鱼岛和南海的领土争端中,美国也有意愿约束日本、菲律宾的举动,让这些国家不至于滥用美国的安全保障。鉴于美国的矛盾心态和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中国在涉及美国盟友的争端中仍然需要对美国施加压力,敦促美国管理好它的盟友,发挥其良性作用。 第三,美国利用其联盟关系限制和阻碍中国与相关国家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尤其是进行正常的防务合作与军品贸易,阻挠中国从一些国家进口高技术装备,同时也阻止盟友从中国进口武器装备。长期以来,美国自己限制对华出口高新技术装备,使得中美两国在军事领域合作受到阻碍。此外,美国也不允许其盟友对华出口高技术武器。 美国在这一方面管理盟友的典型案例是阻止欧盟解禁对华军售,阻碍欧盟国家和以色列等国家向中国输出高技术武器。尽管欧盟解禁并不一定导致欧盟国家对华军售出口在数量和质量上显著增长,而且法国、英国等国与中国也一直保持军贸关系,但是解禁仍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在法国、德国等国的敦促下,2004年12月,欧洲理事会考虑就解除对华军售禁令通过决议。然而,美国对欧盟这一决议表示反对。2005年,包括时任总统小布什、国务卿赖斯在内的政府高官和白宫发言人多次表态,对欧盟解禁对华军售表示担忧,并威胁其会损害美国与欧盟之间的经贸关系以及与北约盟友之间的防务合作。在这一背景下,欧盟解禁事宜不了了之。与此同时,美国还多次阻挠包括欧盟国家和以色列在内的盟友向中国出口尖端军事科技。2000年,在中国和以色列已经就进口“费尔康”预警系统达成合同并支付预付款的情况下,美国向以色列施加压力,迫使以色列取消了这一交易。更有甚者,2005年,在中国将早前从以色列进口的“哈比”无人攻击机组件送交以色列进行维修之后,美国无理要求以色列扣押这批武器,不准其交还中国。为了达到目的,美国威胁减少对以色列的经济援助,暂停以色列空军参与新一代F-35联合战斗机的研制计划,停止向以色列军队提供夜视仪等装备和技术合作以及推迟美以高层军事交流。(41)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当时的以色列巴拉克政府决定将没有进行维修的“哈比”无人机交还中国。此后一段时间,以色列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收紧了与中国之间的正常军事装备贸易。 类似的事件也发生在中国推动军事装备对外出口的过程之中。随着中国国防装备实力的迅速提升,中国近年来积极拓展对外军备出口。然而,中国向美国盟友出售军事装备也遭到美国的无端干涉,导致已经中标的交易被迫流产或拖延。2013年9月26日,土耳其国防部宣布中国精密进出口公司的“FD-2000”防空导弹系统击败了一同竞标的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的“S-400”防空导弹、欧洲导弹公司的“紫菀”防空导弹以及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爱国者”防空导弹,取得土耳其陆军长程防空导弹系统的订单。在这一消息初步发布后,美国声称一旦土耳其采购中国导弹系统将可能无法融入北约的系统,并警告北约将不会与土耳其分享弹道导弹的情报信息。在美欧的压力之下,土耳其也无法拒绝中国导弹系统的优惠报价和优越性能,只能选择一再延长宣布远程防空导弹系统采购竞标结果的最后期限。目前,土耳其已将投标结果的最终决定推迟到2014年12月31日。 第四,美国利用联盟关系限制其盟友与中国在经贸和地区一体化进程中的合作。尤其是在中国近年来提出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等地区性合作倡议后,美国积极影响其盟友在这些倡议中的态度。 联盟本质上是一种安全合作关系,主要集中于军事安全和传统安全领域。但是,国际安全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相结合形成的研究成果也表明,联盟纽带会影响联盟成员内部的经济联系以及它们的对外经济战略,尤其是在美国主导的等级体系下,等级内部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关系都会发生重塑。(42)正是依靠联盟体系所形成的紧密政治关系和协商渠道,美国积极推进其主导的环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由此阻止和制约中国与周边国家形成更紧密的经济联系。最近几个月,在中国积极推动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过程中,美国也对其盟友施加压力,促使它们不加入中国倡导的这一新机制。根据一些国际媒体的报道,最初对这一计划感兴趣的韩国、印尼和澳大利亚三国由于美国的游说而缺席2014年10月24日在北京举行的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备忘录签署仪式。(43)实际上,美国在东亚地区一体化问题上历来有自己的盘算,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曾阻止日本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构想。(44)可以预见,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积极推动相关地区性合作倡议的进程不会一帆风顺,美国也会对其盟友施加类似的压力,以阻止中国拓展地区影响力。 总体上看,近年来美国越来越强化其在亚太地区的联盟关系,推动双边联盟的网络化和制度化协调,试图让盟友在安全保障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既是美国出于削减军事力量的考虑,也是由于美国担心中国与其争夺主导地位。在亚太地区以外,美国也在积极利用联盟关系限制中国与其他国家开展正常的军备贸易和尖端军事技术合作。这些作为都清楚地表现出美国防范和牵制中国的意图,也反映了美国联盟体系对中国和平发展不利的一面。但是,美国按照自身战略意图塑造盟友对华政策和行动的努力也不无困难。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中国与美国大多数盟友的利益纽带越来越强,在一些具体议题上这些国家需要权衡利益得失,不可能一味顺从美国。此外,美国的盟友之间也存在矛盾,尤其是日本和韩国围绕领土和历史问题的争议不利于美国协调亚太盟友的立场。 五、结语 遍及全球的联盟网络是美国实施其全球战略最为倚重的手段之一,面对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美国在各个时期能够按照自己的战略意图塑造其主导的联盟体系的发展方向,而大多数盟友也能够在应对诸多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为美国提供支持。此外,美国仍在欧洲地区推进北约东扩,在亚太地区促成双边联盟的网络化和制度化,并且在应对全球性和地区性事务时寻求盟友的支持。整体来看,美国在这些问题上的政策和行动能够得到大多数盟友的支持和合作,联盟管理的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不过,随着逐步削减其国防预算,美国会越来越多地要求盟友承担更多责任,围绕防务开支、军力配置、协调机制等问题存在的传统矛盾仍然会制约美国进行联盟管理,而美国在众多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要求盟友配合美国行动也面临难题。 当前,中国正致力于与美国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从本文的研究来看,由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联盟体系和军事存在,这一新型关系的建立不仅涉及中美两国双边关系的发展,也涉及美国如何推动和塑造其亚太地区盟友的对华关系。由于美国的超强实力,美国与这些国家已形成了安全保护关系,同时也有着更密切的政治联系,美国的联盟管理实践也会影响到中国当前大力推进周边外交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成效。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在欧洲和亚太地区的大多数盟友与中国有着紧密的经贸关系,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合作的范围和程度也会影响美国开展联盟管理的动机。总体看来,针对不同议题领域的问题,中国可以与美国就联盟管理问题展开磋商。对于盟友利用美国安全承诺进行挑衅的行为,中国需要积极敦促美国管理好自己的盟友,克制自己对盟友的承诺,以免其遭到滥用,损害中美关系发展。而对于美国利用联盟关系,阻碍中国开展正常的对外军事合作、经济联系,中国则要努力与美国的盟友发展更加稳定和紧密的双边关系,形成更加强劲的利益纽带,缓解美国施加的干扰和冲击。与此同时,在具体议题上深入探讨和研究美国联盟关系的手段、方式和路径,对于我们应对其不利影响、发挥其积极作用也大有裨益。 *感谢陈志瑞、左希迎、董柞壮和任娟对论文初稿提出的有益意见。文章的疏漏由作者自负。 注释: ①这种表述在历届美国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等官方文件中频繁出现,例如,奥巴马政府2010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有26处提及盟友,其中23处以“亲密朋友和盟友”或“盟友与伙伴”的方式并列出现。参见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DC:The White House,May 2010;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Sustaining U.S.Global Leadership: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Washington,DC: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January 2012。 ②美国国务院网站列出了美国签订并且有效的七项共同防务条约,分别是《北大西洋公约》、澳新美协定、《美菲条约》、东南亚条约、美日条约、美韩条约和里约条约,参见http://www.state.gov/s/l/treaty/collectivedefense/。但是,这份目录难以作为美国现有联盟关系的准确统计,因为东南亚条约组织已经解散。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新西兰与美国的防务合作也已中止,而里约条约中的不少国家都持反美立场。一些国际关系中的常用数据库如“战争相关因素”(COW)和“联盟条约义务与条款数据库”(ATOP)等也列出了与美国有联盟关系的国家名单。 ③George Liska,Nations in Alliance:The Limits of Interdependence,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62,p.3. ④Robert B.McCalla,"NATO's Persistence after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0,No.3,1996,p.450. ⑤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p.41. ⑥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2014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Washington,DC,March 2014,p.III. ⑦[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6-37页。 ⑧在既有文献中,管理(management)、控制(control)、约束(restraint)等词语都被用于联盟管理的讨论。相关研究可参见Glenn H.Snyder,Alliance Politics,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 Jeremy Pressman,Warring Friends:Alliance Restrain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8; Thomas J.Christensen,Worse than A Monolith:Alliance Politics and Problems of Coercive Diplomacy in Asia,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苏若林、唐世平:《相互制约:联盟管理的核心机制》,《当代亚太》,2012年第3期,第6-38页。 ⑨学术界一般以战略目标来界定美国的全球战略,尽管表述不同,比如“霸权护持”(hegemonic maintenance)、“美国主导”(U.S.primacy)等,但实际上都强调美国意图维持其全球主导地位。对美国全球战略的表述,可参见Barry R.Posen and Andrew L.Ross,"Competing Visions for U.S.Grand Strateg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1,No.3,1996/97,pp.5-53;许嘉、陈志瑞主编:《取舍:美国战略调整与霸权护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⑩“受牵连”与“被抛弃”是格伦·斯奈德所说的“联盟困境”,参见Glenn H.Snyder,"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World Politics,Vol.36,No.4,1984,pp.461-495。有关美国面临的联盟困境的分析,可参见左希迎:《美国战略收缩与亚太秩序的未来》,《当代亚太》,2014年第4期,第17页;周方银:《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与中国的应对》,《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1期,第18-19页。 (11)这是奥尔森等人对联盟经济理论的阐释,参见Mancur Olson,Jr.and Richard Zeckhauser,"An Economic Theory of Alliances",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48,No.3,1966,pp.266-279。 (12)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p.12. (13)参见刘丰:《联盟、制度与后冷战时代的北约》,《国际论坛》,2005年第2期,第13-17页;周丕启:《合法性与大战略:北约体系内美国的霸权护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14)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详细讨论了俄罗斯阻止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策略及其成效,尽管最近一段时间关于乌克兰的案例又有新的发展,但其中的基本判断仍然是成立的,即俄罗斯在必要情况下会使用武力阻止这些国家加入北约。参见刘丰:《分化对手联盟:战略、机制与案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期,第48-65页。 (15)Glenn H.Snyder,Alliance Politics,pp.165-200. (16)苏若林、唐世平:《相互制约:联盟管理的核心机制》,第6-38页。 (17)新自由制度主义学者倾向于将联盟视为一项“安全制度”(security institution),参见Celeste A.Wallender and Robert Keohane,"Risk,Threat and Security Institutions",in Helga Heflebdorn,Robert O.Keohane,and Celeste A.Wallander,eds.,Imperfect Unions:Security Institutions over Time and Spac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21-47。类似的分析还可参见孙德刚:《多元平衡与“准联盟”理论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07年,第46页。 (18)David A.Lake,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9;孙学峰:《东亚准无政府体系与中国的东亚安全政策》,《外交评论》,2011年第6期,第32-48页;孙学峰、黄宇兴:《中国崛起与东亚地区秩序演变》,《当代亚太》,2011年第1期,第26-28页。 (19)邝云峰:《美国的朝贡体系》,《国际政治科学》,2013年第4期,第65-66页。 (20)不少研究论及“为何亚洲没有北约”这一问题,而上述观点是基于建构主义的认同观得出的。参见Christopher Hemmer and Peter J.Katzenstein,"Why is There No NATO in Asia? Collective Identity,Regionalism,and the Origins of Multilateralis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6,No.3,2002,pp.575-607。其他观点可参见Victor D.Cha,"Powerplay:Origins of the U.S.Alliance System in Asia",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4,No.3,2009/10,pp.158-196; Kai He and Huiyun Feng,"'Why is There No NATO in Asia?' Revisited:Prospect Theory,Balance of Threat,and US Alliance Strategie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8,No.2,2012,pp.227-250。 (21)对纳恩和罗斯修正案的介绍,可参见Lawrence S.Kaplan,NATO Divided,NATO United:The Evolution of an Alliance,Westport,CT:Praeger,2004,pp.96-97。 (22)刘丰:《联合阵线与美国军事干涉》,《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6期,第122页。 (23)数据来源可参见U.S.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Database,http://usoda.eads.usaidallnet.gov。 (24)"Japan to Win Exemption from Iran Sanctions by U.S.:Report",Reuters,February 20,2012,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2/02/20/us-japan-usa-sanctions-idUSTRE81J1FK20120220. (25)该文件可以在《华盛顿邮报》下载,参见"The Detemination and Findings",December 5,2003,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srv/world/documents/iraqcontracts_dod20031205.pdf。 (26)邝云峰:《美国的朝贡体系》,第37页。 (27)"Special Relationship",http://www.phrases.org.uk/meanings/special-relationship.html. (28)[美]约翰·米尔斯海默、斯蒂芬·沃尔特:《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王传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29)Jeremy Pressman,Warring Friends:Alliance Restrain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p.78,100. (30)对美新中止联盟关系的理论分析,可参见Amy L.Catalinac,"Why New Zealand Took Itself out of ANZUS:Observing 'Opposition for Autonomy' in Asymmetric Alliances",Foreign Policy Analysis,Vol.6,No.4,2010,pp.317-338。 (31)James D.Morrow,"Alliances and Asymmetry:An Alternative to the Capability Aggregation Model of Alliances",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35,No.4,1991,pp.916-920. (32)Stephen A.Kocs,Autonomy or Power? The Franco-German Relationship and Europe's Strategic Choices,1955-1995,Westport,CT:Praeger,1995,Chapter 2. (33)Ronald R.Krebs,"Perverse Institutionalism:NATO and the Greco-Turkish Conflict",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3,No.2,1999,pp.343-377. (34)米尔斯海默、沃尔特:《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第二章。 (35)关于美国全球战略和亚太战略调整,尤其是对其“战略收缩”的论述,可参见达巍:《全球再平衡: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战略再思考》,《外交评论》,2014年第2期,第55-77页;左希迎:《美国战略收缩与亚太秩序的未来》,第4-28页。有关“亚太再平衡”与美国亚太联盟体系发展。可参见周方银:《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与中国的应对》,第4-24页。 (36)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p.42. (37)《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10月8日,第4版。 (38)"Ambassador Cui Tiankai Spoke on China-US Relations and the Future of Asia",April 8,2014,http://www.china-embassy.org/eng/sgxw/t1145555.htm. (39)Shannon Tiezzi,"The X Factors:How Third Parties Destabilize US-China Relations",March 13,2014,http://thediplomat.com/2014/03/the-x-factors-how-third-parties-destabilize-us-china-relations/; Sheena Chestnut Greitens,"U.S.-China Relations and America's Alliances in Asia",Brookings East Asia Commentary,June 11,2013,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opinions/2013/06/11-us-china-relations-asia-alliances-greitens#_ftn15. (40)Richard J.Samuels,"Wing Walking:The US-Japan Alliance",Global Asia,Vol.4,No.1,2009,p.17. (41)"US Acts over Israeli Arms Sales to China",The Guardian,June 12,2005,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5/jun/13/usa.israel. (42)杨毅:《联盟体系下的经济事务与国家安全——一项分析框架》,《国际论坛》,2010年第6期,第42-47页;邝云峰:《美国的朝贡体系》,第36-88页。 (43)"Three Major Nations Absent as China Launches World Bank Rival in Asia",Reuters,November 5,2014,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4/11/05/us-china-aiib-idUSKCN0ID08U20141105;"Deal Set on China-Led Infrastructure Bank",October 24,2014,http://www.nytimes.com/2014/10/25/world/asia/chinasigns-agreement-with-20-other-nations-to-establish-international-development-bank.html?_r=0. (44)David P.Rapkin,"The United States,Japan,and the Power to Block:The APEC and AMF Cases",The Pacific Review,Vol.14,No.3,2001,pp.373-410.标签:美国军事论文; 安全联盟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伊拉克战争论文;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