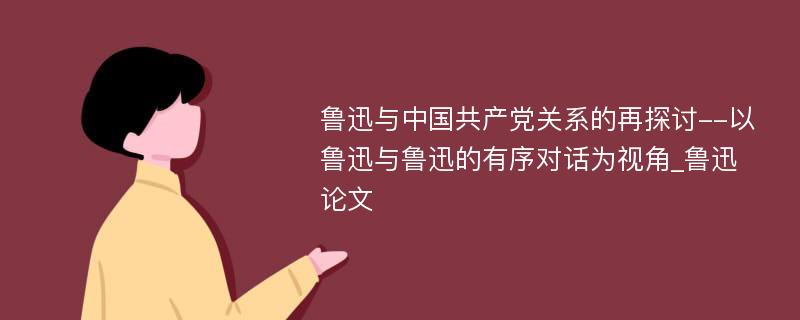
鲁迅与中共关系再探——从鲁迅与瞿秋白订交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中共论文,关系论文,瞿秋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23X(2005)06—0044—05
一 与瞿秋白订交:踏入政治漩涡还是一个新的起点?
1932年底与1933年初与鲁迅有关的两件事值得引起注意:一是瞿秋白、杨之华夫妇因避难居住在鲁迅家中达一个月之久,两人开始密切往还;二是中苏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南京国民政府至少在表面上开始接纳苏联,“中俄文字之交”进一步加深,鲁迅与茅盾等57人向苏联发了《中国著作家为中苏复交致苏联电》。实际上这两件事都在说明同一个问题,即鲁迅与共产党的关系日渐亲密,鲁迅的精神世界与共产主义思想在发生某种共鸣,一句话,此时鲁迅亲共倾向已经不容置疑。其实这又是一个颇为敏感的话题,也是一个十分缠绕的问题,许多论者大都采取回避或轻描淡写的策略,但若探究20世纪30年代鲁迅的思想和创作,真正读懂鲁迅后期所作的那些曲折而又激情的文字,这个问题不得不谈;甚至只有辨析清楚这个历史缠绕方能进入这个时期的鲁迅世界。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谁都知道,这是鲁迅从清人何瓦琴集句中录出的一联题赠给瞿秋白的条幅,历来被视为鲁迅、瞿秋白二人友情笃深的一个明证,业已成为文学史和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话。这也是鲁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密切的一个人所共知的例证。可是也有论者却以为鲁迅与瞿秋白订交,乃至公开和上海文化界的共产党来来往往,虽成全一段文字上的佳话,但对鲁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有所污损,因为从此鲁迅便踏入政治斗争的“漩涡”。鲁迅摆出了一副与前明显不同的“新姿态”,是为了换取生存,不惜牺牲自己的确信。① 同一件事情,居然产生截然相反的结论。所采纳的即便是几乎相同的材料,研究对象也是同一时空的文学史现象,而叙述竟然如此异样,可见历史的幽明莫辨,同时也激起我们再探历史真相的兴味。
有论者以为,鲁迅与苏俄及苏俄文学的亲和无非是“寻找一个身外的精神寄托。越是意识到与官方的力量悬殊,意识到自己的速胜的无望,他就越需要构造一个理想,来证明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徒劳地和官方对抗。”[1](P480) 而与中共公开结盟,是因为看到敌人的强大,急于寻找盟友。因为“他自己和国民党政府为敌了,对一切也与国民党为敌的人,就本能地产生好感。在三十年代的中国,与国民党对抗最激烈的势力,就是共产党,鲁迅看待它的目光,也就最为亲切。”[1](P491) 而共产党同鲁迅联合的理由主要是因为看中了“他那一枝笔,和那个令人眼亮的名字。”[1](P492) 把鲁迅的亲共亲苏归结为感到自己身单力孤,寻找战斗的同盟军,或许是符合人之常情的,但论者把这种急于找同盟军的逻辑起点定位为鲁迅的“心理危机”② 未免是一种不情之论。
生逢乱世,身处鬼蜮般的人间,到处鬼影幢幢,难免心存“鬼气”。鲁迅毫不讳饰这种心理的阴暗面,多次提到他内心的“毒气”、“鬼气”、“黑暗”等等,但若捉住鲁迅自己的诚恳自剖而大肆发挥、随意渲染,进而依次揣测鲁迅30年代领导左翼力量,开展各种文化论争,并倾向于红色政权,完全出于心理病态,急于驱鬼所致,此种诛心之论实在虚妄不实。剔除重要的社会因素,不去细致梳理复杂的历史缠绕,辨析各种社会话语交锋的文化框架和生成语境,而是纠缠于所谓“心理漩涡”,斤斤计较当事人具体环境下所说的几句颇有针对性的言语,由此生发开去,靠着“文采想像”,遽下断语,不免厚诬前人。究其实,近年来揄扬沈从文、张爱玲、周作人而贬抑鲁迅、郭沫若、茅盾的研究思路也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交锋的表现,透过现代性、后现代性、审美主体性、艺术性、普遍人性等时尚或已不时尚的词汇依稀感受到鲁迅在30年代所提出的系列命题,所引发的各种思想交锋在今天仍在讨论、争执、展开……
所谓“太阳底下无新事”,鉴古知今的老话实在不脱其警世功用。重温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的言论,再度回到那个烽烟翻卷、激情炽燃的时代,可能更能明察当下各种思想和话语对话与交锋的历史根由,更能加深理解鲁迅在现代中国错综的文化网格中的位置和作用。如果沿着历史的纹路细细寻绎,不难发现以鲁迅为代表的一群现代知识分子在探询中国独立富强之路中,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与共产党走到一起,并发现惟有共产之路才能切实拯救中国,并非偶然之举。尽管有的学者羞于谈及鲁迅与共产党的交往,耻于谈及鲁迅对伟大的苏俄的向往,仿佛这样会伤害鲁迅,损害鲁迅的形象,但事实上鲁迅在30年代已经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这也是毋庸讳言的。值得反思的倒是:什么力量和习惯势力致使鲁迅30年代的红色言行成了新的“话语禁忌”?学术潮汐涨落得如此之快倒更耐人寻味。禁忌也罢,时尚也好,都难以遮住已经成为白纸黑字的记载;文化资本也罢,后现代历史观也好,想凭空抹掉已经深入历史的记忆恐怕也非易事。
1932年11月底,瞿秋白及其夫人杨之华搬进了鲁迅在上海北四川路的寓所中避难,到年末他们方才离开。在这近一个月的朝夕相处中,鲁迅和瞿秋白有了更深的交流和理解。1933年3月瞿秋白住进了东照里新居, 鲁迅也由北四川路迁入施高塔路大陆新村9号,两家接宇望衡,自然交往更为密切。 杨之华回忆道:“鲁迅几乎每天到东照里来看望我们,和秋白谈论政治、时事、文艺各方面的事情,乐而忘返。秋白一见鲁迅,就立刻改变了不爱说话的性情,两人边说边笑,有时哈哈大笑,冲破了像牢笼似的小亭子间里不自由的空气。”[2] 在这段交往中,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之间的文字交流。除了瞿秋白为鲁迅编选《杂感选集》并写了上万字的序言外,1933年5月至10月间,瞿秋白陆续写成杂文12篇,即《王道诗话》、《苦闷的答复》(后由鲁迅改题为《申冤》)、《曲的解放》、《迎头经》、《出卖灵魂的秘诀》、《最艺术的国家》、《内外》、《透底》、《人才难得》(后由鲁迅改题为《大观园的人才》)、《关于女人》、《真假董吉诃德》(后由鲁迅改题为《真假唐吉诃德》)和《中国人与中国文》。这些文章是经过两人交流,形成主题后,由瞿秋白执笔写成,并经过鲁迅修改,请人抄写,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为了便于保存和流传,鲁迅将他们编入自己的文集。前9篇载《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收入《伪自由书》;最后两篇载《申报月刊》,署名洛人,收入《南腔北调集》;《中国人与中国文》载《申报·自由谈》,署名余铭,收入《准风月谈》。③ 从上述杂文篇什的予唱汝和、彼此呼应,甚至“瞿冠鲁戴”来观察,1933年以后的鲁迅叱咤中国文坛之上,纵横严密文网之间的矫健姿态显然与获得瞿秋白及其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有力支持不无关联。当然鲁迅也敏锐地观察到上海的中共作家团体内也良莠不齐,成分尤为复杂,并对某些人和现象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此一点稍后再作分疏。
二 有学者问,他为什么一生都深情地盯着北极圈这片伟大肥沃的黑土?
另外还有一件事显然进一步坚定了鲁迅认同、接受、信仰共产主义思想的决心,即国民党政府在1927年12月24日同苏联断绝邦交的5年后,于1932年12月12 日宣布与苏联恢复外交关系。
鲁迅并没有天真地以为南京政府与苏联复交便是对中国左翼文化运动态度转变的契机,相反,他从这一现象看到了这个政权的虚弱,看到了某些自利者在即将遭到灭顶之灾时急于抓住救命稻草的仓惶。鲁迅抓住“复交”的由头,大做其“中俄文字之交”的文章。鲁迅赞道:“可祝贺的,是中俄的文字之交,……在近十年中,两国的绝交也好,复交也好,我们的读者大众却不因此而进退;译本的放任也好,禁压也好,我们的读者也不因此而盛衰。不但如常,而且扩大;不但虽绝交和禁压还是如常,而且虽绝交和禁压而更加扩大。这可见我们的读者大众,是一向不用自私的‘势利眼’来看俄国文学的。我们的读者大众,在朦胧中,早知道在伟大肥沃的‘黑土’里,要生长出什么东西来,而这‘黑土’却也确实生长了东西,给我们亲见了:忍受,呻吟,挣扎,反抗,战斗,变革,战斗,建设,战斗,成功。”[3](P462) 鲁迅盛赞俄国文学自有他独特的角度,他比较了英法美等国家的文学译介到中国的东西与俄国文学的不同,它们的读者的兴趣、它们在中国所起的作用的不同。鲁迅发现其他各国输入中国的只是包探、冒险家、英国姑娘、非洲野蛮故事,这些“是只能当醉饱之后,在发胀的身上搔搔痒的,然而我们的一部分的青年已经觉得压迫,只有痛楚,他要挣扎,用不着痒痒的抚摩,只在寻切实的指示了。”切实的指示在何方?这时,人们发现了俄国文学。鲁迅认为俄国文学给予中国的东西异常宝贵,“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辛酸,的挣扎,……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3](P460) 鲁迅并把这个发见看得与人类对火的发现和使用同等重要。
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他为什么一生都深情地盯着北极圈这片伟大肥沃的黑土,归纳起来大致两点,其一是俄国人正视人生灾难、惨苦的勇气,其二是俄国人与‘异常残酷性’相纠结的异常的‘慈悲性’、‘博爱’与‘牺牲’。”[4](P232) 鲁迅看重的自然是俄罗斯民族中对苦难的正视,以及对压迫者天然的悲悯感,但还应加上一点,那就是对压迫的抗争精神。既然世界上分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两种人,称赞和拥护为被压迫者伸张正义的政权——苏联也便是题中应有之义。在一本书的序言中,鲁迅这样证明苏联的好处:“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十年前,说过苏联怎么不行怎么无望的所谓文明国人,去年已在苏联的煤油和麦子面前发抖。而且我看见确凿的事实:他们是在吸中国的膏血,夺中国的土地,杀中国的人民。他们是大骗子,他们说苏联坏,要进攻苏联,就可见苏联是好的了。”[5](P427) 一个朴素的逻辑是:“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宝贝,那么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6](P430) 其实这并非是什么“非此即彼”、“二项对立”的思维方式的问题,而是在严酷的民族危机和生存灾难面前,作为受压迫者争取自己的生活权利免遭再度沦为奴隶的本能选择而已。
然而,事情的复杂性并不在于鲁迅是否真诚地拥护共产主义,赞成共产党的革命事业(这是无疑问的),而在于鲁迅为什么自1930年入左翼作家联盟之后与上海的一部分作家如瞿秋白、冯雪峰、胡风等人过从甚密,甚至达到知己的程度,而与另一部分共产党作家如周扬、田汉等则保持着相当微妙的关系,甚至到了1936年临终之际同他们闹翻?一般的文学史把这个问题归结为左翼作家中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指责周扬他们不注意内部团结,不懂得统一战线等等;另一些学者则抱怨鲁迅心胸狭窄,喜欢树旗帜、称大王,甚至心理病态、内心恐惧,抓住作领袖的感觉而自慰等等。前者之论似乎太过空泛冠冕,对论辩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省事却不切实;后者的论调并不新鲜,鲁迅的许多当时的论敌便用了这种心理揣度的方法,一味诛心,滥施攻击,只不过几十年后加上精神分析或心理诊疗等花样,仍不脱以毒攻毒的老调。
三 鲁迅的“梯子之论”
还是先听听鲁迅自己的诉说吧。
当听到有人称鲁迅加入自由同盟等组织是做“梯子”时,鲁迅很坦然,也很不以为然:“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对于此一节,我也曾熟虑,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国之可做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当谈及他的历来帮助青年的经验以及加入左联,尤其对先前对他施以攻击的“革命作家”,更是充满了警觉和不屑:“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飚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于会场中,一览可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7](P8) 其实,鲁迅哪里只是在背后议论那些“革命作家”,在当面,在正式场合他也是以说理的方式,以恳切的态度强调革命作家要与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不然“左翼”作家很容易变成“右翼”作家的。在左联的成立大会上,他要左翼作家应剔除罗曼蒂克的幻想,抛弃诗人或文学家高人一等的观念,要坚决、切实,持之不断,还要有韧性,不要把文学当作“敲门砖”,等功成名遂,有点小名即弃之不顾。[8](P233—239) 鲁迅说出这些中肯的意见,其实是他对其中的一些“革命作家”知之甚深:许多人并无操守,加入组织,只是趋势自利,一遇压迫,便露原形,走向革命的反面,做了帮凶和爪牙。后来在1933年的《申报·自由谈》上批判的杨邨人、叶灵凤等便是此等人物。
对于这部分人的见风使舵,东倒西歪的性质,鲁迅早就洞若观火,并有所防范,在给萧军、萧红的信中说:“分裂,高谈,故作激烈等等,四五年前也曾有过这现象,左联起来,将这压下去了,但病根未除,又添了新分子,于是现在老病就复发。但空谈之类,谈不久,也谈不出什么来,它终必被事实的镜子照出原形,拖出尾巴而去。”[9](P593) 在另一封给二萧的信中他又分析道:“我看中国有许多知识分子,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的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社会上这样的东西一多,社会要糟的。”但是鲁迅却怒中含怨,对来自背后自己阵营的暗箭表现出无可奈何:“敌人不足惧,最令人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因此,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我以为这境遇是可怕的。”[10](P116) 受到内部友军背后的攻击,鲁迅常常把自己这种痛状比喻为受伤的野兽。在给曹聚仁的信中也有类似的诉说:“今之青年,似乎比我们青年时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目前之益,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构陷,真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历来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难尽,但我是总如野兽一样,受了伤,就回头钻入草莽,舐干血迹,至多也不过呻吟几声的。”[11](P185)
“友军的冷箭”并非偶然为之,而是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特性,让鲁迅感到悲哀:“冷箭是上海‘作家’的特产,我有一大把拔在这里,现在在生病,俟愈后,要把它发表出来,给大家看看。即如最近,‘作家协会’发起人之一在他所编的刊物上说我是‘理想的奴才’,而别一发起人之一却劝我入会:他们以为我不知道那一枝冷箭是谁射的。”[12](P304) 对于上面提到的“作家协会”之类,鲁迅看出他们只是在玩花样,借以自利,令他既愤慨又痛心:“作家协会已改名为文艺家协会,其中热心者不多,大抵多数是敷衍,有些却想借此自利,或害人。……一出风头,就显病态……真令人痛心,我看这种自私心太重的青年,将来也得整顿一下才好。……上海的‘文学家’,真是不成样子,只会玩小花样,不知其他。我真想做一篇文章,至少五六万字,把历来所受的闷气,都说出来,这其实也是留给将来的一点遗产。”[13](P382—383) 但是,鲁迅终究没有把这五六万字的文章写出来。并非不能,是不为也。为什么?因为他考虑到这到底是内部的事,他们终究做出一些“于中国有益的事”,换句话说,鲁迅着眼于大局,他算的是大账、总账,而非小账、细账:“至于我的受人愚弄呢,那自然;但也不是第一次了,不过在他们还未露出原形,他们做事好像还于中国有益的时候,我是出力的。这是我历来做事的主意,根柢即在总账问题。即使第一次受骗了,第二次也有被骗的可能,我还是做,因为被人偷过一次,也不能疑心世界上全是偷儿,只好仍旧打杂。”[14](P226)
问题是除了冷箭之外,还有鞭子,还有铁索;除了小卒、喽啰之外,还有“工头”、“元帅”①。他说:“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地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地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15](P211) 正是在这样受鞭笞却不敢喊痛的苦境中,鲁迅才发现自己如受伤的野兽,只能自己悄悄扎好伤口,舐干污血,休息一会,再度上阵。
也正是发现了同一阵线中有拿着鞭子的呵斥者,也许便更觉得心心相印的知己的可贵,这就不难理解鲁迅与瞿秋白的友谊如此深厚,大概是经历了无数痛楚的经验,比较、鉴别而获得的吧。难怪鲁迅多次向友人由衷赞许瞿秋白:“像他那样的,我看中国现在少有。”[16](P158) 同样是共产党作家,鲁迅有亲有疏,有迎有拒,这表明他心中有是非,有判断,并非一味附和,无原则迁就,若说他做了共产党的附庸,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实在有失考辨。然而,对共产事业和左翼文学运动,鲁迅却抛却私怨,无论受到怎样中伤、“鞭打”,他只是咬紧牙关,自己包扎伤口,不怨尤,不向外人自揭伤疤,因为他算的是“总账”,只要他们做了“于中国有益的事情”,即便受骗,还是要做。由此,若说他跟共产党合作,投身于进步文化运动是为了自己“做领袖”,出风头,也是一种妄言。鲁迅甘心做“梯子”,即使受到“元帅”的鞭笞,他还是一味去做。也许,这是他的宿命。
由是观之,1930年以后鲁迅参与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并成为这个运动当然的精神领袖,经验了极为复杂的心路历程,他的思想和言论,他的行动与姿态无不表征了一个求真的知识分子对于那个时代的思考与感应。由此再来反观1933年鲁迅毅然投入新一轮的思想文化论争,再来分析他在《申报·自由谈》上那些精粹而有力的文字,便会更加了然其间的艺术力量和文化含量。
收稿日期:2005—05—21
注释:
① 参阅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二十年代晚期的鲁迅思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一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第456—494页。
② 王晓明认为,鲁迅走到共产党的阵营中,主要原因是他的多疑、易怒、冷漠、恐怖等心理病态所致,因为在1927年进入上海以后,鲁迅越来越产生一种“局外人的沮丧”,内心充满危机,为了驱除鬼气,鲁迅不得不抗争,但却“一脚踏进了政治漩涡”,身不由己的越卷越深,直至被推上与官方公开对抗的位置,人身安全岌岌可危,于是不得不靠拢共产党。参阅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二十年代晚期的鲁迅思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一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第456—494页。
③ 参阅《鲁迅年谱》(增订本)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396—397页。《瞿秋白文集》(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第414—443页。
④ 其实这个元帅或工头就是中共在上海的左联负责人周扬。到后来,鲁迅在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直接点名批评的“四条汉子”之一,这一文坛公案一直延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整个文化界,至今余波未平。可见其间隐伏的暗流何等汹涌。参阅鲁迅的另外几篇文章《三月的租界》、《〈出关〉的关》、《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鲁迅全集》第6卷,第513—516页、第517—523页、第586—589页、第590—59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