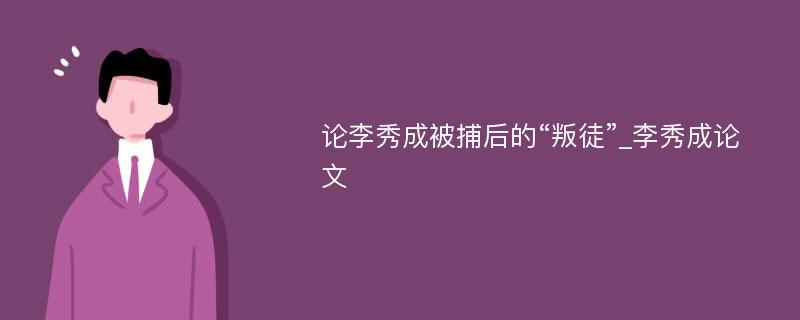
再论李秀成被俘后的“变节”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李秀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03)04-0094-07
忠王李秀成被俘后,在囚笼中写下了数万字的供词。(注:为了避讳,今之学者将起义者被俘后的供词改称“自述”或“自传”。按照辞书通行的解释,“供”字作“受审者的陈述”解,似乎本无贬义。李秀成则自称其亲笔供词为“书供”。本文采用“供词”一词。)围绕其供词中的内容,学术界在1949年后就李秀成伪降还是变节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甚至一度从单纯的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并且至今未有定论,成为太平天国史研究中最大的一桩悬案。笔者几年前曾经就此问题写过一篇短文[1],但由于受到篇幅的限制,未能展开论述。兹不揣浅陋,再度就此略陈管见。
一
李秀成是广西藤县大黎乡人,家境贫寒,儿时随舅父读过3年书,10岁开始种山帮工,以烧炭为业。1851年9月,西王萧朝贵率部路过大黎,时年29岁的李秀成应征入伍,随后参加了攻打永安的战斗,隶属石达开部。在此后的戎马生涯中,李秀成因战功显赫而不断升迁,从士兵直至跻身统帅层,37岁时被封为忠王,成为太平天国后期一员威震四方的名将,在军中的地位仅次于英王陈玉成。
1861年9月,在经过长达一年多的拉锯战后,安庆终告沦陷,陈玉成部主力折损殆尽,都城天京(今南京)上游屏障尽失。次年5月,陈玉成在寿州被皖北团练头目苗沛霖诱捕,6月在河南延津就义。从此,李秀成便成为太平军的首席大将。当时,太平天国所面临的局势已经异常严峻:曾国荃部湘军主力顺流而下直逼天京,李鸿章部淮军会同英法军队进攻上海外围,左宗棠部湘军从江西觊觎浙江,形成三路围攻之势,曾国藩则坐镇安庆指挥全局。曾国荃一路3万余人尤为气势汹汹,到1862年5月底,其水师已进泊天京护城河,陆师则进逼雨花台,兵临天京城下。同年10月中旬,李秀成从上海外围抽身,会同其他主力共13王约10余万人,兵分三路前来解天京之围。太平军与湘军在天京城南大战40余日,始终未能攻破敌雨花台营垒。
解围受挫后,洪秀全将李秀成严责革爵,令其“进北攻南”,即移兵皖北、鄂北,以调动围攻天京的南岸湘军上援。鉴于苏福省局势不稳,李秀成先赶回苏州安顿后方,直到1863年2月末才督师进军皖北。而此时湘军早已增兵设防,加上筹粮困难,李部征战不利。同年6月13日,天京雨花台石城等要塞失守。李秀成奉诏急返,结果在渡江时遭到湘军水师的拦截,所部损失惨重。28日,由于李鸿章、左宗棠大举进犯,苏、浙吃紧,李秀成又火速赶回苏州主持战局。
此时的李秀成几乎成了救火队长,哪里告急就赶到哪里,但因三面受敌,分身乏术,故而疲于奔命。同年8月,忠王返京督战,组织反扑未果。9月,又驰返苏州指挥攻防。12月1日,忠王撤离苏州。4日,纳王郜永宽等叛将刺杀慕王谭绍光,开门揖盗,将苏州拱手献给了李鸿章。数日后,无锡也告失守。李秀成率余部败走丹阳。苏南腹地的沦陷使天京失去了粮饷的主要供给地,加上京外残存据点的守军自顾不暇,天京解围的希望实际上已成镜花水月。因此,李秀成返京后,力劝天王“让城别走”,但遭到天王训斥,只得督兵死守。
1864年初春,湘军正式合围天京,封锁了所有粮道,并在城外开挖多处隧道,试图穴地攻城。李秀成指挥太平军以构筑月城和横挖暗壕的方法相拒,战况异常惨烈。6月1日,洪秀全病逝,终年51岁。7月19日午后,湘军攻破天京。李秀成火速赶到天朝宫殿护驾。他改骑一匹劣马,将自己的战马让给幼天王,于当夜率千余名将士打扮成清军,借着夜色的掩护,护卫幼天王从太平门缺口处突围。李秀成舍死领头冲锋,在冲到城外后与大队人马走散。天明时分,人困马乏的忠王潜抵城郊方山一破庙中暂避,结果因随身所带财物而暴露身份,于23日被两个奸民缚送清营。
为了泄恨,曾国荃随即下令对李秀成施以酷刑,用刀锥割其臀股,一时血流如注。李秀成“殊不动”,泰然自若。3天后,清军制成一个大木笼,将李秀成囚禁其中。8月7日傍晚,李秀成被曾国藩处死,时年42岁。在临刑前,李秀成毫无戚容,谈笑自若,并写有10句绝命诗,“叙其尽忠之意”。[2]
李秀成从被俘到被杀,前后仅有16天。在此期间,他曾历时9天,在囚笼中亲笔写下了数万字的供词,虽然文理欠通,但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详细叙述了太平天国的兴亡始末。与在此前后的表现判若两人的是,李秀成在供词中明显流露出乞降求抚之意。他对曾国藩和清王朝大加谀颂,谓“久悉中堂(指曾国藩,引者按)恩深量广,切救世人之心,玉驾出临瑶”,“久知中堂有仁爱惠四方,兼有德化之心,良可深佩”,表示“我见老中堂大义恩深,实大鸿才,心悔莫及”,自叹“一生屈错,未遇明良”。并将京城沦陷喻作“我主无谋,清朝有福”,认为“曾家亦有厚福,而辅清朝得此城而威扬天下,实中堂之谋,九帅(指曾国荃,引者按)之才谋算,将相用命而成全功也”。声称“今天国已亡,实大清皇上之福德,万幸之至”云云。他还提出“收齐章程”,自愿以“罪将”之身,出面代为招降太平军余部,从而“尽义对大清皇上,以酎旧日有罪愚民”,“免大清心腹之患再生”。(注:罗尔纲:《增补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0、219、377、385页。以下该书引文恕不一一注明。)
李秀成此举的动机和原因究竟是什么?这一历史之谜引起了史家的极大关注。以此为焦点,围绕李秀成的评价问题,学术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
根据其供词来评价李秀成,首先必然会牵涉到这份文献的真伪问题。当年曾国藩在处死李秀成后,随即与幕僚赵烈文对忠王亲供反复审核、删改,并加以分段。不久,曾国藩以“各处索阅逆供者多”为由,将删改过的忠王亲供在安庆刊刻,印成《李秀成供》一册,分送军机处备查和各地方大吏披阅,计27818字,即世传“九如堂本”。至于李秀成亲供手迹,曾国藩却讳莫如深,一直秘不示人,从而留下了许多悬念。
1944年,广西通志馆秘书吕集义在湘乡曾国藩故宅获见这一秘本,便据九如堂本与之对勘,补抄被曾国藩删除的5600余字(仍脱漏大约2880字),并摄影16页。罗尔纲从1931年起开始注释李秀成供词,此时便改以吕氏补抄本和照片四帧作为底本作注。1951年,罗氏《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一书由开明书店出版,很快一版再版,轰动一时。1956年,年子敏、束世澄撰文提出质疑,认为从内容来考察,李秀成不应向曾国藩乞降;笔迹上经法医鉴定,《自传原稿》与《李秀成谕李昭寿书》的笔迹相异,据此断言李秀成“自述”系曾国藩伪造,并非出自李秀成亲笔。[3]学术界就此展开了争论。罗尔纲根据“书家八法”的理论,将上述两件文书中的笔迹逐一拆开来比较,阐明了笔迹鉴定的有效性与限制性,判定这两件手迹表面相异但实际相同,进而断言李秀成“自述”确系真迹。1957年,根据吕集义当年拍摄的所有原稿照片,罗尔纲再次调整版本,由中华书局推出《笺证》一书的增订本。1962年,曾国藩的曾孙曾约农将秘藏的李秀成笔供原稿交台北世界书局影印出版,题签《李秀成亲供手迹》。《手迹》的篇幅比当年的安庆刻本多出9000余字,并且清晰地保留着曾国藩等人用朱笔、墨笔进行删改的痕迹。《手迹》的公布进一步印证了罗尔纲的结论,同时也宣告世传的20余种忠王供词版本从此作废。罗尔纲便第三次调整底本,198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一书。此时,仍有学者对李秀成供词手迹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推断台北影印出版的手稿并不是李秀成的真迹,而是曾国藩在删改忠王真迹后找人誊录的抄件。罗先生从其笔迹、内容等方面详作考证,指出这份文献虽不完整,有被曾国藩撕毁、删改和伪饰的地方,但确系出自李秀成手笔。这一结论最终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同。
几乎在辨别李秀成供词之真伪的同时,学术界就忠王在文中所流露出的乞降求抚之意展开了讨论。在1951年初版《笺证》一书中,罗尔纲提出了一个假设,认为忠王此举意在效仿蜀汉大将姜维伪降钟会故智,以图恢复太平天国。1957年出版的该书增订本依然持“伪降”说。1959年,赵矢元对此提出异议,强调李秀成“承认太平天国革命已经失败,消失了对革命前途的信心,要求曾国藩招降他的部众,这也是应该承认的”[4]。1961年,苑书义也刊文指出,李秀成此举是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和对封建势力产生幻想的表现,其性质是“妥协投降”。作者同时指出,“由于他并非想入伙为盗,加上乞降未成,招降未就,和临刑时表现尚好,所以还不应以叛徒论处。乞降固然给他的历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污点,却不能改变他对太平天国的巨大贡献依然是其一生主流的这一事实”[5]。对于上述两种不同的观点,学者们纷纷撰文表态,臧否不一。李秀成评价问题一时成为史学界的研究热点。
然而,这种正常的学术争鸣很快就被引入歧途。1964年,戚本禹之流断言忠王不“忠”,其自述“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并打着揪“叛徒”、彰“气节”的旗号,发起了一场批判李秀成的政治运动。于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被无端上升为政治问题,对李秀成持肯定态度的学者竟被视为“站错了立场”。罗尔纲因坚持认为李秀成此举是“苦肉缓兵计”而受到冲击;茅家琦、祁龙威等学者不同意戚本禹全盘否定李秀成的观点,认为李秀成虽晚节不保,但功大于过,结果也被扣上“叛徒李秀成辩护士”的大帽子,遭到打压。一时间,给历史人物贴政治标签成为人物研究风行的模式。按照这种模式,洪秀全被塑造成完美无缺的农民革命领袖,并以他的是非为是非,将杨秀清定性为“野心家”,韦昌辉为“阶级异己分子”,石达开为“分裂主义者”,李秀成为“叛徒”。简单化、脸谱化的研究被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对学术风气产生了恶劣影响。将李秀成简单地定性为“叛徒”不足为训。它是当时极左思潮的产物,其实质是搞影射史学,以便为后来借“叛徒”罪名打倒党内一大批功勋卓著的老干部制造舆论。
1981年,罗尔纲又以曾国藩曾外孙女俞大缜教授新近提供的“李秀成劝文正公当皇帝,文正公不敢”这一口碑为依据,再作考证,力持李秀成“伪降”说,认为李秀成劝曾国藩反清做皇帝是假,试图借此恢复太平天国是真。[6]
苏双碧则认为,李秀成在被俘前后,经历了一个从愚忠到不忠的质变,它的起点是被俘,终点则是写了“自述”,流露出“乞活偷生”之意。在“自述”中,李秀成奉承敌人、贬斥自己,其行为是对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背叛,属于“变节”,这是“白纸黑字,非常明白的事”。郭毅生也对“伪降”说提出了质疑,认为“由于李秀成写完自述,即被处死,他是否属于伪降,并无实践证明,只能就其生前表现而推考,难以作出定论。从《自述》本身看,应属求降或投降,无论其为何种动机,都是错误或有害的。这种错误既有个人的原因,也有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不过,苏、郭两位学者都主张就事论事,认为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李秀成。苏氏指出,“把李秀成打成‘可耻的叛徒’,而否认他的一生,那也不是实事求是的”。郭氏也不同意将李秀成定性为“叛徒”,强调不能脱离历史条件而苛求于前人,认为“历史的悲剧造成了李秀成的个人悲剧,而不是李秀成的晚节不终造成了太平天国覆亡的悲剧”。(注:参见苏双碧《论李秀成》,载《北方论坛》1979年第5期,郭毅生、任恒俊《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与李秀成伪降问题》,载《文史哲》1979年第4期。)
罗先生也承认李秀成学姜维用假投降计,有亏革命气节,不足为训,但他再三强调李秀成是“伪降”。这成为双方分歧的焦点。近20年来,随着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日趋冷落,有关李秀成评价问题的讨论逐渐归于沉寂,但学术界在此问题上的看法并没有取得一致。那么,究竟应当如何评价李秀成被俘后的“变节”问题呢?
二
作为国内太平天国史研究的一代宗师和学术带头人,罗尔纲先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为世人所景仰,《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便堪称当代考证学的经典之作,但就李秀成“伪降”说而论,似乎并不足以令人信服。罗先生列举了李秀成供词中的12处疑窦,诸如“假造与天王不和”、“遮掩天王对他的重任”等,将其中的乞降求抚之语一概解释成“伪饰的话”,坚持认为李秀成“是一个百折不挠的革命者”,“有坚定的革命立场与强烈的革命感情”。这种推断不免有以偏概全、曲意为尊者讳之嫌。
后期,以血缘和利害关系为纽带,李秀成等异姓诸王与王长次兄等洪氏宗室成员逐渐成为朝中分庭抗礼的两大派系。在经历了天京事变这场噩梦之后,心有余悸的洪秀全对异姓大臣猜忌甚深,倾向于重用自己的兄弟子侄。在辛酉十一年四五月间天王颁发的几道诏旨中,在受诏人名次的排列顺序上,洪氏宗室成员均赫然排在英王、忠王等异姓诸王之前,其亲疏厚薄一目了然。然而,洪氏亲属尽管地位显赫,但并无一人掌握兵权和地盘,而这些正是李秀成等人与前者抗衡的资本。洪秀全一心想营建自己的家天下,始终对异姓诸王抱有戒心,但他同时却又不得不在军事上借重后者,这是他无法回避的一个矛盾。无奈之下,洪秀全只好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但是,洪秀全性情暴烈而又固执,本不擅长协调人际关系,这使得他在处理朝内纷争时往往过于偏执和意气用事。这种用人思路上的摇摆不定既引发了异姓大臣的离心倾向和抵触情绪,同时又激化了异姓大臣与洪氏宗亲之间的矛盾,加之洪秀全在后期一味沉溺于宗教,无心亲理朝政,遂使这一局面更加失控。忠王对洪氏宗亲很不服气。他在供词中直斥王长次兄是“佞臣”,列数其鬻官纳贿、搜刮民财、玩弄权术等种种劣迹。他还愤愤不平地说,天王第一重用幼西王,第二重用王长次兄,第三重用干王,第四重用其驸马,第五重用英王,第六才轮到他李秀成。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时,洪氏宗室与异姓诸王之间的明争暗斗闹得沸沸扬扬,就连清方也有所耳闻。在同治元年九月廿三日的一份奏折中,左宗棠就此写道:“贼中伪王可数者共三十余,惟伪忠王李秀成、伪章王林绍璋与李侍(世)贤相投合,余则彼此猜疑,金陵逆首洪秀全之兄伪勇王洪仁达尤为各贼所恨。从前杨、韦两逆互相吞噬之事,不久必将复见。”[7](卷一四)李秀成在供词中检讨太平天国败亡的原因时,反复抱怨天王“不信外臣”、“不问政事”、“不用贤才”、“立政无章”,认为“我主用人不专,信人之不实,谗佞张扬,明贤偃避,豪杰不登,故有今之败”,虽言语偏激,但也确系有感而发。总之,忠王与天王不和是不争的事实,斑斑可考,并非出自前者的“假造”。
平心而论,李秀成也有自己的过失,诸如专注于经略苏杭,对天京上游的安危较为淡漠,缺乏全局意识;在朝内党争中多少有些意气用事;对怀有贰心的部将和亲友过于宽恕,甚至不惜牺牲大局来体现自己的所谓仁义,等等。但瑕不掩瑜,李秀成毕竟是太平天国后期的支柱之一,战功卓著。他体恤民情,减租薄赋,保护工商业,在苏南民间较有声望。当大局糜烂之际,李秀成更是疲于奔命,所部几乎成了救火队。然而,他却不时受到天王的猜忌和洪姓大臣的掣肘。为了获准回救苏杭,李秀成被迫将包括自己老母在内的家眷留在京城作为人质,并且捐助饷银十万两,便是一例。他所受的委屈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如此,李秀成依旧对天王忠心耿耿,忍辱负重,苦撑残局,乃至在京城沦陷后舍身救护幼天王,用他自己的话说,“尽心而救天王这点骨血,是尽我愚忠而为”。因此,在国破家亡、身陷囹圄之后,李秀成痛定思痛,如骨鲠在喉,难免就会在供词中倒苦水,发牢骚,其文字也难免会有些情绪化。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是李秀成真实心态的一种流露。认为李秀成始终忍辱负重,毫无怨言,即使是在兵败被俘之后,仍然使出假投降的计谋与清方进行周旋,以图恢复太平天国,这种假设明显带有个人主观的美好愿望在里面。认为忠王不会写出丧失革命气节的“自述”,进而断言这份文献是曾国藩伪造,也是出于类似的心理。
“伪降”说惟一直接的依据是曾家流传的“李秀成劝文正公做皇帝,文正公不敢”这一口碑。然而,口碑倘若没有文献资料作为佐证,便成了孤证,其可信程度也就大打折扣。现存的忠王供词原稿是一残本,结尾部分作“今我国末,亦是先天之定数,下民应劫难,如其此劫,何生天王而乱天下,何我不才而佐他乎?今已被拿在禁,非因天意使然,我亦不知我前世之来历,天下多少英雄才子,何不为此事而独我为,实我不知(原文衍一“知”字)也。如知”,就此戛然而止,卷末显然已被曾国藩撕毁。(注:据罗尔纲先生考证,李秀成供词原稿的篇幅为5万余字,其部分手迹已被曾国藩撕毁。近有学者认为,现存李秀成供词原稿实际上是完璧,并无被曾国藩撕毁的痕迹,仅有两处错简。参见姜涛《重读〈李秀成自述〉》,收入《太平天国史新论》,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著名学者陈寅恪当年曾经推测,曾国藩不肯将原稿公布,必有不可告人之隐。那么,被撕毁的部分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呢?这已是一个永远也无法破解的历史之谜了。不过,至少在残存的忠王供词原稿中,丝毫也看不到任何挑动曾国藩反清的痕迹,相反,“大清”、“大清皇上”之类的称谓倒并不少见。反过来说,即使口碑属实,也只能说明李秀成有心投效曾国藩,而不能据此断言李秀成这么做仅是一种手段,伺机恢复太平天国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将干王洪仁玕被俘后的表现与忠王李秀成作一对比,对我们思考这一问题不无启发。在先后被俘的太平天国诸王中,洪仁玕是惟一一位从满汉仇雠的角度为太平天国的败亡浩叹不已的人。从被俘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抱定杀身成仁的信念,决意效法文天祥。在狱中所写的绝命诗中,洪仁玕强调“春秋大义别华夷”,为“志在攮夷愿未酬”而抱恨终天。相比之下,李秀成从被俘直至被杀,始终没有在任何场合流露过华夷(汉满)有别之类的思想,可见所谓忠王效仿姜维伪降、意在挑动曾国藩反清的说法值得重新认识。此外,洪仁玕在就义前曾从江西巡抚沈葆桢处读到《李秀成供》,并就其相关章节签附反驳意见,是太平天国内部惟一一位读过《李秀成供》并对其加以评述的人。他在签驳时反复数落李秀成“变更不一”、“己多更张”、“变迁不常”、“变迁不一”,并提到苏州叛将向李鸿章献城一事,认为“即忠王亦几几不免”。[8](p496~498,p511~514)这实际上是洪仁玕对李秀成变节行为一种含蓄的谴责。
当然,李秀成之所以在供词中写下有辱其“忠王”封号的言辞,并非单纯出于对天王和洪氏宗亲的怨艾心理。李秀成在被俘后所产生的心理变化以及曾国藩对他的诱骗,都在这一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均是我们在研究时不应忽视的细节。
在被俘之后,李秀成最大的心理变化是对太平天国的前景感到彻底绝望。在亲笔供词中,包括在与曾国藩机要幕僚赵烈文的对话中,李秀成都流露出一种强烈的宿命意识。在被俘当晚与赵烈文进行的长谈中,李秀成将1861年错失解救安庆的良机解释为“天意”,并根据天上的星象,预言洋人在十余年后必成大患。赵烈文询问星名度数,李秀成便搬出民间的星宿八卦之说作了一通解释。[2]在亲笔供词中,类似的文字更是屡见不鲜。例如,他将当初太平天国的兴起解释为“此是天机,升平日久,应出此人(指天王,引者按),集传许多乱星下降”,将战场上的失利归结为“于今气数已满,谋而不中”,将太平天国最终的败亡解释为“五百年之大数转限数难逃”,“数尽国崩”。在谈到幼天王的下落时,他推断后者出城后凶多吉少,“十六岁幼童,自幼至长,并未骑过马,又未受过惊慌,九帅四方兵追,定然被杀矣”(注:不能简单地将这段话理解为李秀成刻意隐瞒幼天王的行踪。李秀成对幼天王的评判比较准确,后者确实十分稚嫩和软弱,后来在逃亡途中因险相环生,曾经数次试图自杀。)。在再三批评天王“一味靠天”、“言天说地”的同时,李秀成自己的宿命思想却急剧膨胀,这一矛盾现象恰好说明,此时的李秀成心如死灰,已对太平天国彻底感到绝望,断无伺机复国的念头。(注:后来的事实证明,李秀成对时局的判断是正确的。在逃到皖南广德以后,幼天王在十二三万太平军的护卫下开赴江西,拟与侍王李世贤等部会合,以便重整旗蚊。但由于士气低落,号令不一,在清军的围追堵截下,这支远征军最终全军覆没。幼天王、洪仁玕等被俘后,相继在南昌被凌迟处死。)
李秀成身经百战,九死一生,他当然不会怕死,但在被俘之后,他却多少显得有些贪生。这也不难理解,他曾经叱咤风云、威震四方,如今却束手就擒,生死仅在旦夕之间,这使他感到心有不甘,求生的欲望也陡然变得强烈起来。在后来上报清廷的奏折中,曾国藩谈了自己对李秀成的印象,认为他“献谀乞怜,无非图延旦夕之一命”[9](卷二一)。曾国荃也以一种胜利者的口吻,说李秀成“阱虎乞怜,曾狗鼠之不若,殊可嗤也”[10](卷五)。当然,这种言语明显带有夸张和泄恨的成分。赵烈文则在日记中记述了他在李秀成被俘当晚与后者进行长谈的内容。据载,当被问到“汝今计安出”时,忠王答道:“死耳。顾至江右者皆旧部,得以尺书散遣之,免戕贼彼此之命,则暝目无憾。”既做好了死的准备,同时又主动提出招降旧部,隐约流露出求生的念头。赵烈文觉察出忠王“言次有乞活之意”,便答复说:“汝罪大,当听中旨,此亦非统帅所得主也。”忠王听后低头不语。[2]日记是个人心灵的独白,因为不公开,所以也就没有刻意伪饰或夸张的必要。赵烈文在日记中便描述了湘军在攻陷天京后烧杀抢掠的种种暴行,认为“其乱如此,可为发指”。因此,他认为李秀成“有乞活之意”的判断应是可信的。李秀成亲笔供词中的内容也证实了这一点。
而老辣的曾国藩正是利用李秀成在被俘后产生的心理变化,抓住其性格中的弱点,使事态沿着自己设计的思路发展。
曾国藩将民人缚送李秀成吹嘘成湘军“生缚名王归夜半”,颇为洋洋自得。1864年7月26日,他在安庆上奏清廷说:“应否献俘,俟到金陵后察酌具奏。”[9](卷二○)28日下午,曾国藩赶到南京,几小时后便亲自审讯李秀成。曾国藩毕竟老谋深算,他并没有像曾国荃那样对李秀成动刑,而是对李秀成施展了攻心战,但随即便萌生了将李秀成就地处决的念头。在次日写给其子曾纪泽的信中,曾国藩相告:“伪忠王曾亲讯一次,拟即在此杀之。”[11](卷下)当然,他也清楚有一件事不可忽视,所以在同一天的日记里又特意写上“取伪忠王详供”这一条附记。
曾国藩的攻心策略果然收到了效果,李秀成自愿书写供词。李秀成是从7月30日开始动笔的。他在供词中写有这样一段话:“今自愿所呈此书,实见中堂之恩情厚义,中丞(指曾国荃,引者按)恩容,佩服良谋,我深足愿。所作之书供,定由列位师爷手过,恐有违犯字样,是烦劳清心改除可也。”文中的“师爷”指奉命会鞫李秀成的曾国藩的随从庞际云、李鸿裔等人。从李秀成说曾国藩“有仁爱”、“有德化之心”等语来判断,曾国藩肯定对李秀成表露过安抚之意。至于曾国藩究竟对李秀成有过什么暗示或许诺,令李秀成感到前者对他有“恩情厚义”,现已无从知晓。以李秀成的阅历,他绝不可能天真到对曾国藩深信不疑的地步,但他显然对后者抱有幻想。他在供词中自叹“一生屈错,未遇明良”,这可能掺杂着他当时的一些真实心态。他虽然不是怕死之辈,但因为哀莫大于心死,对太平天国已彻底感到绝望,对曾国藩抱有幻想,所以难免会流露出一些反常、复杂的心态和意识,萌发一丝求生的念头。至于李秀成求生的动机究竟是什么,这只有他本人清楚。更确切地说,或许连他自己也不十分清楚。李秀成明知自己活下去的希望极为渺茫,同时,他并不知道曾国藩在看了他的供词后会作出何种反应。这种命运的不确定性决定了他不可能对未来有什么具体的打算。他之所以流露出求生的欲望,更多的是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带有浓厚的听天由命的色彩。
李秀成是在一种恍若隔世百感交集的状态下,被困在囚笼中,在死亡的威胁下,冒着酷暑,以大约每天7000字的速度撰写这份供词的。这与在正常状态下的写作有着天壤之别。当写到三万七八千字时,李秀成用完了纸,写坏了笔,便提出再给一本纸簿和一支好笔,同时表示“烦各位师爷转禀老中堂及中丞大人宽限,我亦赶写”。可见李秀成尽管心存侥幸,但已预感到自己来日无多。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忠王在供词中有“我今临终之候”一语;在写出“收齐章程”之后,又自云“昨夜深惠厚情,死而足愿,欢乐归阴”,既抱定必死的信念,但同时却又对曾国藩表示感戴,从而真切地折射出忠王当时反常、复杂的心态。尽管他对昔日不共戴天之敌的谀颂之词多少有些言不由衷,所提的“招齐章程”多少带有保全旧部性命和避免生灵涂炭的意图,但就具体事实而论,这的确是李秀成晚节的一个污点。
可怜李秀成终究还是被曾国藩算计了。8月3日晚,曾国藩垂询赵烈文的意见,表示打算不等朝廷降旨,便将李秀成从速“正法”。赵烈文回答说:“生擒已十余日,众目共睹,且经中堂录供,当无人复疑,而此贼甚狡,不宜使入都。”两人不谋而合。
8月6日夜,曾国藩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与李秀成照面。据赵烈文讲,李秀成“有乞恩之意”,曾国藩“答以听旨,连日正踟蹰此事,俟定见后再相复”。
第二天,即8月7日,仍在赶写供词的李秀成写下了“昨夜承老中堂调至驾前讯问,承恩惠示,真报无由”、“昨夜深惠厚情”等语。结果墨迹未干,曾国藩就派李鸿裔向李秀成摊牌,表示“国法难逭,不能开脱”,并于当天傍晚将李秀成处死。[2]
清廷吩咐将李秀成押解来京的谕旨是8月1日发出的。而曾国藩却先斩后奏,捏称部将萧孚泗“生擒”李秀成后,乡民为了替他报仇,竟将亲兵王三清捉杀,投尸水中;又说李秀成被关进囚笼后,松王陈德凤被押到营中,一见李秀成便长跪请安。曾国藩据此解释说;“臣闻此二端,恶其民心之未去,党羽之尚坚,即决计就地正法。”他还辩解说,上谕被驿站误投到安庆,等转到南京时,李秀成已被处死。[9](卷二一)
曾国藩之所以擅杀李秀成,与他内心的担忧有很大关系。他早就认为李秀成“狡诈百端”,对他在供词中奉承自己的话并不当真。曾国藩心里清楚,一旦献俘到京城,他们兄弟二人欺瞒朝廷的一些事情,诸如李秀成被俘和曾国荃洗劫天京中饱私囊的真相,统统都会曝光,难免会落个欺君之罪。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他都不能留下李秀成这个活口。
于是,尽管早就动了杀气,但曾国藩仍然不露声色,抓住李秀成在绝望中的复杂心理,如愿以偿地骗取了李秀成的供状。事后,他又玩起文字游戏,凡是吹捧自己的话一字不删,对自己不利的段落则加以删改甚至撕毁。在曾国藩看来,能让李秀成这样的敌手如此心悦诚服地归顺自己,这是足以夸耀于世的资本。曾国藩既欺骗了李秀成,又欺骗了清廷,更折腾苦了后世的历史学家。在这件事情上,曾国藩手段极其卑劣,但却将自己粉饰成正人君子。不过,他也许没有料到,事情的真相在百年后依旧会大白于天下。这正应验了那句老话: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就在一手将李秀成送上黄泉路的时候,曾国藩仍然惺惺作态。他下令将李秀成斩首,其首级传示各省,尸身则用棺材装殓掩埋。但在次日写给清廷的奏折中,他却说已将李秀成就地“凌迟处死”。
同在8月8日,定下心来的曾国荃从城外大营入城,择定房屋,饮酒作乐。次日下午,清廷赏赐曾氏兄弟的消息已经传到南京。11日,谕旨正式颁到:曾国藩封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加太子太保,赏双眼花翎;曾国荃封一等威毅伯,加太子少保,赏双眼花翎。曾国藩顿时乐不可支。赵烈文打趣说:“此后当称中堂,抑称侯爷?”曾国藩笑曰:“君勿称猴子可矣。”[2]自从与太平军开战以来,曾国藩曾经屡遭惨败,先后在靖港投水自尽,在九江险被生擒,在祁门预写遗嘱以防不测。但他还是笑到了最后。
三
从对洪秀全、对太平天国一片愚忠,发展到被俘后在绝望心理的驱策下,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有所不忠,李秀成在生命尽头表现的起伏十分令人感喟。忠王不“忠”的现象从一个侧面说明,太平天国后期人心离散,士气低落,气数已尽,纵然有再多天才的将领和忠勇的士卒,也无法使太平天国摆脱败亡的厄运。
在后期兵败被俘的太平天国重要首领中,英王陈玉成、干王洪仁玕视死如归是一种模式,翼王石达开舍命以全三军是另一种模式,但他们都死得十分壮烈,属于太平天国没有瑕疵的英雄。而忠王李秀成的模式显然有悖于传统的“忠心不贰”、“气节”观念和今人心中的英雄情结。正因为学者们围绕李秀成“变节”问题所展开的争论既是一种政治评判,同时又掺杂着一种道德评判,这就使这场争论大有永无了期之势,使原本扑朔迷离的史实变得更加复杂。在我看来,将李秀成设想成完美无缺的英雄或寡廉鲜耻的叛徒都不免过于简单化。李秀成被俘后所产生的心理变化是合乎逻辑的,本来不难理解,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值得同情。这就是有血有肉、真实的李秀成,而不是我们刻意美化或丑化的李秀成。李秀成在供词中能够认真检讨太平天国覆灭的原因,对自己的一生进行回顾、反思,这何尝不需要几分勇气、冷静和思想呢?李秀成对太平天国败亡原因所作的分析,诸如“我主无谋”、“自惹而亡”、湘军“将相用命”等等,虽然字面有些刺眼,但总体上仍比较中肯和深刻。至于认为中国日后“要防鬼(指洋人,引者按)反为先”,确乎是过人之见。尽管他写了一些有辱气节的话,给他的晚节留下了污点,但他并没有一味地向曾国藩卑躬屈膝,并且最终慷慨赴死。就此而论,李秀成仍然不失为一个有污点的英雄。
当然,我们讨论李秀成被俘后的变节问题,是站在太平天国的角度来评判的。时下全盘否定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声音越来越强烈,或许有人会质疑道:难道李秀成只有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愚忠到底才算是没有污点吗?这就牵涉到如何评价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问题,已不在本文论述之列了。
[收稿日期]2003-08-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