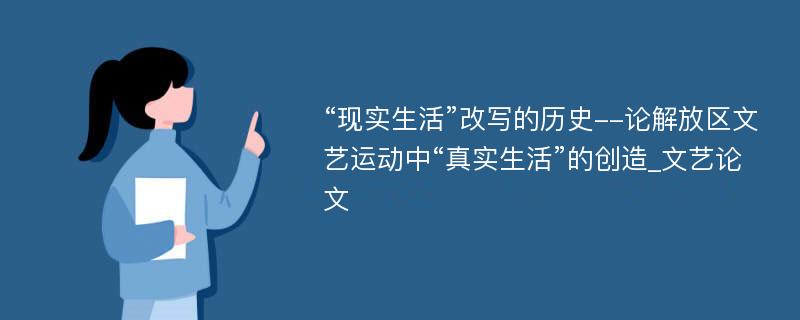
被“真人真事”改写的历史——论解放区文艺运动中的“真人真事”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真人真事论文,解放区论文,文艺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4)02-0065-09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晋察冀边区阜平高街村剧团创作的《穷人乐》取得了巨大成功。该剧被晋察冀边区作为“方向”在边区内推广,成为解放区文学中著名的“‘穷人乐’方向”。作为后期解放区文学中较有影响力的文艺思潮,“‘穷人乐’方向”可以用“群众文艺运动”来概括,不过这并没有说明问题的本质,在“穷人乐”为代表的群众文艺运动背后,有一个重要的支撑点,那便是“真人真事”创作。
“穷人乐”成功的经验,是让群众真正成为了“文艺运动”的主角,他们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一跃成为文艺的创造者(创)和执行者(演)。从理论上讲,普通群众要成为文艺的主角,至少需要两个条件——“权”和“能”。从“权”的角度而言,边区群众成为文艺运动的主角固然受到政治权力的支持,但要在创作过程中获得主动权,还必须具有表达和评价的优势,说到底,是要用事实证明群众创作比作家创作更具有优势。从“能”的角度,普通群众要参与创作,首先要克服在知识储备上的种种缺陷——在普通群众知识水平一时无法整体提高的情况下,要使群众创作成为可能,需要提供一种新的创作的可能。这两个问题,在“真人真事”的创作格局中得到了解决:当“真事真事”成为创作的标准,群众的“经验”就成为他们先天的优势,这既克服了创作中“权”的问题,也弥补了作者“能”的问题。在“真人真事”的创作标准下,知识分子的“知识”被消解为纯粹的“工具”,只能充当文艺运动中的“配角”。有了这个基础,群众文艺运动才可能成为事实。
经过“穷人乐”方向的推动,“真人真事”创作在边区成为一种潮流。不过,“真人真事”创作标准并不是在“穷人乐”方向推广后才开始出现的。有意识地使用“真人真事”创作标准的,首先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一部分试图表明立场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创作中用“真人真事”来证明自己“为工农兵服务”的立场①。而后,随着“真人真事”创作被一再提起,它在解放区文学中构成了一个立体体系。它包括三个部分:(1)题材的要求,这是“真人真事”创作的外在表现形式,即写作的题材必须是真人真事;(2)演出的要求,这是“穷人乐”方向所形成的一个传统,即用“真人演真事”;(3)创作的要求,即由真人来决定“真人真事”的艺术形态——这也是“穷人乐”方向所提倡的。由于包含了这三个方面,“真人真事”创作就不仅是群众文艺运动的一部分,也成为解放区文艺创作中一个独特的现象,值得研究和重视。
作为现象的“真人真事”创作,至少有两个问题首先需要探讨:第一,其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它为什么受到解放区文艺领导者的高度重视?第二,其对解放区文学(包括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关于这两个问题,已有部分学者进行了解释。有学者认为:“真人真事”创作是创造“典型”的必要途径——这实际已经指出了“真人真事”的理论渊源——左翼文艺运动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具体应用②。也有学者从反思的角度,指出:“‘真人真事’写作本质上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向工农兵大众的被动归化过程,工农兵型的‘真人真事’写作本质上是工农兵大众对革命意识的主动认同过程。”③这种分析既说明“真人真事”创作在延安造成的影响,也说明了其产生的根源。应该说,不管是提倡还是反思,两种分析都点明了问题的本质,但稍嫌遗憾的地方在于:如果将“真人真事”简单归结为左翼文艺理论的发展,那么它在延安时期发生的变化可能被忽略——而这恰恰是不能忽略的问题;再者,虽然学者们注意到“真人真事”对“知识分子”和“工农兵大众”产生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实现的过程没有得到充分展示,这势必影响我们对这一段历史反思的深刻程度。有鉴于此,本文拟从“题材”、“表演”和“创作”三个层面,对这一现象及其影响作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
一、知识分子的“摹写”运动:作为题材的“真人真事”
作为题材的“真人真事”,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左翼文学运动当中的“报告文学”创作。对中国左翼报告文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川口浩,在其《报告文学论》中说:“和他名称一样,报告文学的最大的力点,是在事实的报告。但是,这绝不是和照相机摄取物象一样地,机械地将现实用文字来表现。这,必然的具有一定的目的,和一定的倾向。这种目的和倾向是什么呢?不是别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目的。”④显然,无论是具体做法还是追求的效果,报告文学都可以说是延安“真人真事”创作的先声。“左联”将报告文学作为文学发展的重要方向,政治目的显而易见:“在某种事件的发生,能有通讯员的赤裸裸的记录,这便可以和我们的政治任务配合起来。”⑤也就是说,报告文学的好处是能直接与政治任务结合起来。报告文学能有这个效果,从实际创作的情形看,其优势大概在两个方面:一是“真实”形成的震撼性。报告文学有“类新闻”的效果,一旦真人真事经过艺术加工被广大读者知晓,其产生的效果往往比“虚构”的文学更有力量。二是能够“及时”反应社会问题,引起读者共鸣。胡风就曾经说:“剧激变化的社会生活使作家除了创作以外还不能不随时用素描或速写来批判地纪录各个角落里发生的社会现象,把具体的实在的样相(认识)传达给读者。”“它的特征是能够把变动的日常事故更迅速地更直接地反映,批判”,“它们不能代替创作,然而却负上了创作所不能够马上负起的任务。”⑥这种评价非常实际,报告文学能够跟踪社会热点,从而更迅速地与大众形成交流,这显然是革命文学应该具有的品质。
解放区文学中提倡作家以“真人真事”为题材,出发点和报告文学是一致的,相对于“虚构文学”,“真人真事”的优点依然在于“真实”的感召性和“及时”的引导性。周扬在谈“真人真事”创作时说:“我们写的真人真事大半是群众中的英雄模范人物和英雄模范事迹,他们本身就是新社会中的典型,就带有教育的意义。”⑦周扬在这里实际谈到了延安时期的“真人真事”与30年代“报告文学”在描写对象上的差别:前者主要歌颂边区的英雄模范人物,后者则主要暴露社会的黑暗面。但两者看待“真人真事”创作的视野是一致的。英雄模范人物在边区产生的初衷,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利用“真人真事”对一般大众产生感召作用;边区英雄模范人物往往伴随着各种群众运动产生,通过宣传英雄模范人物,又及时地向大众传递了社会的最新动向。
虽然“真人真事”创作在“左联”时期和延安时期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但在具体的“生产”当中,两者的差别更值得注意。周扬在谈论延安的“真人真事”创作时还说:“(真人真事创作)是‘文艺座谈会’以后文艺创作上的一个新现象,是文艺工作者走向工农兵,工农兵走向文艺的良好捷径。”⑧通过“真人真事”将作家、工农兵和文艺联系起来,这是30年代左翼文学没有触碰的问题,它可以说是延安“真人真事”创作的特点。
“真人真事”为什么能成为“文艺工作者走向工农兵,工农兵走向文艺的良好捷径”呢?这完全是由其写作对象决定的。30年代“报告文学”创作,虽然作家在创作之初便有一定的倾向性,但报告的对象、报告的内容,包括报告的方式,都是由作家自己决定的——作家所要追求的,是如何获得更加翔实的一手资料。延安的“真人真事”创作则不同,由于对象多是“英雄模范人物和英雄模范事迹”——这些人物已经在边区树立了较为明确的形象,作家在进行“再塑造”时,已经没有太多的空间。因此,延安时期的作家在进行“真人真事”创作时,思考的并不是如何获得一手资料,而是如何把已经“成型”的“真人真事”塑造得更加丰满。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创作状态,其对作家产生的影响自然不同。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待这个问题。30年代的报告文学,由于揭露了许多社会的黑暗面,也由于介绍了不少苏联的见闻,作品在社会上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和社会效应。如《包身工》、《黄包车!黄包车!》、《人在水银中,水银在人体中》、《萍踪忆语》等作品,今天读来依然有扑面而来的震撼力。正是由于作品的现实震撼力,报告文学获得了自身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反观延安时期的“真人真事”创作,如艾青创作的《吴满有》、《养羊英雄刘占海》,丁玲创作的《田保霖——靖边县新城区五乡民办合作社主任》,再如集体创作的《张治国》、《钟万财起家》、《刘胡兰》等作品,它们的影响力都不及当时新闻媒体对这些人物宣传造成的轰动效应。如果说这些作品有什么现实意义,只能说通过文艺的形式,这些英雄模范人物获得了更为广泛和持久的影响力——这是新闻媒体无法实现的效果⑨。可以说,虽然毛泽东专门称赞过丁玲的《田保霖》和欧阳山的《活在新社会》⑩,但其出发点主要在于“新文风”,而不是作品本身的现实效应。如果作品本身并不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那么“真人真事”在延安的意义如何理解呢?问题还要回到“文艺工作者走向工农兵,工农兵走向文艺的良好捷径”上来。
由于后文对“工农兵走向文艺”有专门论述,在这里我们就只探讨“真人真事”如何实现了“文艺工作者走向工农兵”的问题。首先,要界定一个词语——“工农兵”。这个在边区被赋予丰富涵义的词语,虽然和“大众”、“平民”有类似之处,但有更加确定的政治内涵。与其特殊的涵义相适应,当它们成为文学表现的对象,也不能简单地、一般地表现,必然有更丰富的审美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讲,《讲话》之后作家创作的“真人真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作家学习表现工农兵的“摹写”运动。
“临摹”是中国书画进行艺术传承和艺术教育的重要手段。南宋姜夔在《续书谱》中称:“唯初学书者,不得不摹,亦以节度其手,易于成就。皆须是古人名笔,置之几案,悬之座右,朝夕谛观,思其运笔之理,然后可以摹临。”(11)其中道出了“临摹”的重要意义,在于“节度其手”,而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和效果,临摹者必须对临摹对象“朝夕谛观,思其运笔之理”。《讲话》之后作家进行的“真人真事”写作之所以称为“摹写”,是因为他们写作的对象——英雄模范——已经在社会上确立了自己的“形象”,作家所能做的——不是“重写”这个形象——而是让这种形象永久地进入艺术的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作家如同“初学书者”,必然要“朝夕谛观,思其运笔之理,然后可以摹临”。我们可以通过艾青创作的《吴满有》来说明这个问题。
在《吴满有》的诗歌当中,艾青从9个方面对这位边区最大的生产英雄进行了描写:(1)写你在文化界的欢迎会上;(2)写你的苦日子;(3)写你翻身;(4)写你勤耕种;(5)写你发起来;(6)写你爱边区;(7)写你当了劳动英雄;(8)写你叫大家多生产;(9)写你的欢喜。然而,9个方面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没有超出当时新闻报道对吴满有塑造的范围。在艾青开始酝酿《吴满有》长诗时,吴满有已经是边区家喻户晓的人物。《解放日报》是率先发现这位生产英雄并把他推至政治高峰的媒体(12)。《解放日报》对吴满有的报道在内容上具有整体性和阶段性的特点。整体性是对其的基本定位,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生产英雄、公民典范和感恩典范。“生产英雄”针对他农业生产的技能以及现实生活的改善;“公民典范”重在报道他响应边区的号召,主动超额缴纳公粮;“感恩典范”则强调他对于党、对于革命——特别对于毛主席(这对整风非常重要)的感恩之心。阶段性是指在吴满有成为典范后,利用吴满有的声望,根据现实需要对他进行新的塑造,譬如将他塑造为拥军典范。无论是整体塑造还是阶段塑造的内容,都能在长诗《吴满有》中找到影子,而诗歌对吴满有的塑造也未超出这个范围,并没有进行新的创造。
在形式上,媒体对吴满有的报道常常用到对比叙事的方法,这种叙事方式在诗歌中也延续了下来。譬如,在报道《忘不了革命好处的人》中,有一长段其身世的介绍:“把十一岁的女儿,换得了二十四元的代价,卖给一个姓张的做童养媳了,但还是顾不上吃,又把三岁的女儿,向一个姓曹的人家,换得了五升粗粮。”“为了缴不出‘维持费’,吴满有被带到荒山里‘狠狠的揍了一顿’。”这种生活在革命后发生改善,吴满有感叹道:“妈的,穷人也有翻身的一天。”(13)这些“苦日子”和“翻身”的情景,在艾青的诗歌中也能看到。包括报道使用的语言方式,在诗歌中也能很明显地感受到。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在文风上发生了改变,在对吴满有的报道上,大量使用了民间口语,在讲述各种道理时也务求通俗易懂,这一点在诗歌《吴满有》的标题中,我们都能明显看到对这种文风的接受。
在长诗《吴满有》发表的时候,艾青还特别增加了描述写作过程的“附记”,再现了自己创作完成后向吴满有读诗征求意见的情景。在这个“附记”的字里行间,我们能明确感受到这是个“摹写”的过程:艾青逐字逐句向吴满有征求修改意见,其本质便是知识分子对现实生活中工农兵的“摹写”。在摹写过程中,知识分子并没有塑造的主动权,他们必须向工农兵学习;而如果联系到《解放日报》对吴满有的先行塑造,在艾青现实摹写的过程中,必然包含对被党塑造过的“工农兵”形象的摹写。说到底,它是知识分子对党的政策的“摹写”。正如姜夔所言,摹写的作用在于“节度其手”,在经过一个个“真人真事”的摹写之后,延安作家最终才能成为合格的“文艺工作者”。
周扬所说“文艺工作者走向工农兵”,其实就是一个“摹写”的过程。只有明确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让作家对英雄模范“二度创作”的意义所在,也才能体会它与30年代同样强调“真人真事”的报告文学的本质差别。
二、“真人演真事”:革命群众的自我塑造
在解放区兴起“真人真事”创作中,一个重要的方向是“真人演真事”。譬如在“穷人乐”创演中,英雄人物陈福全就是“真人演真事”。而在《晋察冀日报》关于“穷人乐”方向的社论中,这种做法显然也是值得推广的经验之一。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考察“穷人乐”演出成功后的边区群众文艺运动,“真人演真事”的事迹屡见不鲜。譬如,1944年12月9日,阜平县著名劳动英雄胡顺义亲自登台演出话剧《胡顺义》;1944年12月31日,行唐县荣军模范、民兵英雄康福山家乡的村剧团自编自演反映互助合作的戏剧《大拨工》;1945年,定唐县游击区东下素村自编自演了《血债》(14)。这些还只是有记录的“真人演真事”,如果考虑到“穷人乐”方向树立后蓬勃发展的乡村戏剧,这种做法存在的数量会更大。
“真人演真事”作为“穷人乐”方向的重要内容被推广,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权宜之举——乡村剧团演员缺乏,很多时候“演员扮演别人,总是演不像”,而戏剧表现的对象又是观众熟悉的“真人真事”,因此对演员的要求比虚构作品其实更高。这种条件下,“真人演真事”就成为解决演员问题的重要手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戏剧运动史上,“真人演真事”的例子并不鲜见,在戏剧环境极度恶劣的情况下,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苏区时期,由于戏剧人才奇缺,自己扮演自己的现象就曾发生过:苏区时期排演的《庐山之雪》,就采用了“兵演兵、将演将”的演出方式,军团的主要首长都登台演出,除敌方阵营由罗瑞卿演蒋介石,童小鹏演宋美龄,李卓然演德国顾问外,我方阵营都按实际的职位“将演将”:军团政委聂荣臻演红军政委,军团长林彪演红军司令员,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演红军政治部主任(15)。从发展群众文艺运动的角度,“真人演真事”可以获得意想不到的剧场效果:当观众看到熟悉的事件、熟悉的人物和熟悉的演员,就更容易参与到戏剧当中。从传播的角度,这更有利于戏剧内容的传播。
不过从“真人演真事”在边区发展的实际情形看,权宜之举绝非问题的全部。“真人演真事”发展到后期,俨然成为群众自我教育的重要手段。譬如,进入解放战争后,晋察冀野战军普遍开展“兵演兵”活动,战士们创作、演出大量生动活泼短小精悍的快板剧、小节目。67军某旅战士创作的《张金剑入党》、《一块白洋》(表现不搜俘虏腰包)、《团结爱兵》等快板剧,收到很好的效果。“兵演兵”成为活跃连队生活、战士进行自我教育的有力武器。专业文艺工作者深入连队,开展“兵演兵”运动,也从群众创作中吸收营养(16)。“兵演兵”能成为战士自我教育的有力武器,除了戏剧所表现的内容与部队日常工作和生活息息相关,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它将戏剧当作一种公共媒介,纳入了部队日常教育的惩戒系统。譬如,晋察冀野战军63军编排的《马鸿文的疙瘩解开了》,描写马鸿文怕艰苦想离队,经过帮助提高了觉悟,改正了错误思想的过程(17)。该剧采用了“真人演真事”的方法,马鸿文出演马鸿文,可以想象,虽然剧中的马鸿文是思想转变、改正错误的典型,但上演过程对于现实生活中的马鸿文必然是某种惩戒,毕竟他要将曾经的错误公之于众,而且还要重新示范。这样的做法必然会产生教育意义。当然有惩罚自然也会有弘扬,在表现英雄人物的“真人演真事”中,演出者除了获得荣誉,也为所有士兵树立了“兵”的楷模。肖向荣曾经就部队的文艺工作专业谈到“演兵”的问题,认为“演兵”重要的是创作演出上的表演问题,是对导演、演员和所有演出工作的同志,同时也是对所有搞创作的同志提出的。在部队中做这些工作的同志,都是把自己的研究主要地放到如何来表现兵的方面,创造真正符合军队的情感和军人姿态的军队形式和军队作风。这里,他特别强调了“创造真正符合于军队的情感和军人姿态的军队形式和军队作风”(18),也就是说“演兵”也是一种再创作,他是要将理想状态的“军人情感”和“军人姿态”演给广大官兵,为官兵树立一个楷模。
如果将“兵演兵”的例子还原到“真人演真事”当中,这种群众文艺运动的惩戒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譬如根据真人真事创作演出的《钟万财起家》,让钟万财演“二流子转变”的过程,其实和在群众大会上亮相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不过,从戏剧编剧的情况看,它利用了转变后回忆的叙述形式,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惩戒的残酷性,让群众更乐于接受这种说教的方式。而表现正面人物的作品,如《穷人乐》中的陈福全、《张治国》中的张治国、《胡顺义》中的胡顺义,正面示范的作用则更加明显。
其实,不管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真人演真事”都是边区革命群众自我塑造的行为,它不仅是对观众的塑造,参与其中的演员也得到了一种塑造。对观众的塑造比较好理解,那便是通过“真人演真事”非常具体地在观众中确立了一种道德观和价值观;不过,这种示范作用还不足以说明“真人演真事”的精髓:“真人演真事”的过程,也是对参与演出者的一种自我塑造,其结果便是将“真人”的示范性推进到更具体的日常细节。
司达克·杨在《表演艺术论》中说:“各种艺术都是一种演释的形式,某种东西就被它表现于另外的条件中,正如柏拉图(Plato)所说的,某种前所未有的东西就出现了。表演是把那直接从生活上或从那已由生活中创造出来的思想和动作的戏剧上得来的事实,在人本身——这种条件中演释出。”(19)在这个“演释”的过程中,不仅“真人真事”被传播出去,“真人”的情感和身体也得到了充分的塑造,它使革命的价值和道德直接进入到人的肉体当中。我们可以用《穷人乐》演出中的实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在《晋察冀日报》刊发的《沿着“穷人乐”的方向发展群众文艺运动》社论中,有很多表演的细节值得玩味和思考:
陈亲自上演之后,排戏场里空气为之一变,动作自然亲切,鼓励了大家自己演自己,这一来,许多新的创造就出现了。比如,开头,演员的说话,动作表现不自然,常忘台词,戏剧里所需要表演的“过程”,像演春天挨饿的情形,演员却愉快地说着这些事,忘记了当时的情形。但排上一两回,帮助排戏的同志再一启发,群众重新回到自己所经历的生活中,丰富生动的语言就涌现了,劳动动作也很自然了……在排演中央军南退时,帮助排戏的同志想用话剧形式来演,群众却提出,要唱他们刚刚学会的关于中央军退却的歌子,他们说:到吃紧的地方,说话没劲,非唱歌不行,这样演来,既省了许多麻烦,又非常动人。群众就是这样从生活的经验中,来选择了适合于表现生活的各种艺术形式,使“穷人乐”一剧,成了话剧,舞蹈,唱歌,快板等的综合形式。(20)
在这里有两处讲到表演和生活的差别:一处是表演春天挨饿的情形,一处是表现中央军南退。表现“春天挨饿”的情节,亲身经历的农民竟然进入不了演出的状态,其原因不是农民不会表演,而是随着叙述语境的变化,“真”也发生了变化:在农民心目中,“春天挨饿”可能就是日常生活,并没有太多的创伤和仇恨,而在戏剧中,它却是表现农民受压迫和剥削的“苦戏”,只有表现出痛苦和仇恨才算是“真实”。在这个排演的过程中,农民至少学会了释放情感的时机和方法,这是不参与演出的人难以切身体会的。在表现“中央军南退”的部分,这种宏大叙事对于百姓并没有太多感触,他们要用“唱歌”来表现“吃紧”的地方,看似自主的选择,其实少不了导演的启发——这是情节的高潮部分——而农民不过是嫁接了自己的情感方式而已。如此,个人情感再一次与宏大叙事结合在一起。这样的例子在“真人演真事”中不胜枚举:那些被塑造出来的基层英雄模范,其性格特征并不完全与革命需要吻合,而通过“真人演真事”,他们的“精气神”就符合了革命的标准,其返回日常生活,就会成为更加合格的“模范”。
“真人演真事”的这种影响力,在土改运动中的诉苦会上得到充分的表现。在土改之初,诉苦会往往开得并不成功,其原因除了农村的土地矛盾和阶级矛盾是否如此尖锐外,农民不能自觉地将自己的生活纳入“革命叙事”也是问题的关键:有的曾经受到过地主的压迫和剥削,但自己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还有的在诉苦中需要流露情绪的地方,并没有流露情绪,这样的诉苦就很难有感染力。而经过一场场的“真人演真事”后,后期的土改诉苦会就不再是这种场面:
在竞相诉苦,哭声一片,怒吼连连,群情激愤的时候,人们情绪相互感染,不断升温,再有一些“勇敢份子”大胆出手,还甚么事情不会发生呢?这时的人们实际上是进入了一种特定的剧场,主演们的表演感染着所有的人,人人(除了被斗者)都投入到剧情中,互相感染着,激励着,仇恨开始迭加,愤怒自然升级,群体一致的行动,高昂的情绪赋予了人们表演的“正当性”,驱使着人们做出平时根本无法想象的恐怖之举,剧场效应使得参与者不知不觉中步入了带有血腥味的狂欢。(21)
到了这种境界的时候,一个“革命群众”才算真正塑造成功了。
三、“真人真事”创作:被提升的“经验”
在“‘穷人乐’方向”中,群众自主创作被置于重要的地位。《晋察冀日报》关于《沿着“穷人乐”的方向发展群众文艺运动》的社论,关于《穷人乐》特点和优点的三点概括,最核心的要素还是让群众成为创作的主角——工农兵走进文艺。《穷人乐》的成功,在于它实现了“工农兵走向文艺”的可能性。在其成功的经验中,有一些是技术的环节,譬如“创作与演出”的结合,这种做法使不具备创作技能的“工农兵”能更直接地参与到创作当中;有一些则属于勇气的问题,譬如确定“穷人乐”主题,周富德力排众议,主张排演这个主题——这显然是勇气问题——让工农兵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且,在关于戏剧的主题和内容的选择上,高街村农民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这也是“勇气”的问题。所以说,“穷人乐”的示范作用,在于它用实际行动克服了工农兵创作中的“技术”和“勇气”问题,从而使“工农兵走向文艺”成为可能。
不可否认,《穷人乐》开启的群众文艺运动有其示范的意义和价值,工农兵也的确有参与创作的必要和意义,但当这种创作方式被当作政权的一种“方向”推广时,其背后的深意更值得深入挖掘。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要鼓励群众创作的勇气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思考的是,为什么群众没有创作的勇气呢?
群众没有创作的勇气,重要的原因在于没有掌握文学技能,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受制于“知识特权”。由于不具备文学技能,群众没有办法参与到文学创作中,也不敢对创作的过程指手画脚;而受制于“知识特权”,他们不仅无法参与创作,甚至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譬如“什么主题最能表达他们的心声”,这本该他们自己做主的问题,他们却不能也不敢表达。所以说,鼓励群众创作——让工农兵走进文艺,对于打破“知识特权”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在“穷人乐”方向的经验推广中,字里行间,鼓励群众创作并不在于仅仅打破“知识特权”,也有群众理所当然成为创作主角的意思。我们能够理解,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旗帜树立后,提升工农兵在文艺创作中的地位得到了政权的支持,但问题在于:即使工农兵在政治上获得了创作的权威性,但在文学技能缺陷真正克服之前,他们并不能在创作中确立自己的权威性——相反,会造成文艺的混乱。
在这样的背景下,“真人真事”的深意便凸显了出来。“真人真事”的重要作用在于消解作家“虚构”的权力——实际消解了作家“创造”的权力。失去虚构能力和权力的作家,只能成为现实生活的附庸——只能向工农兵学习。相应地,在“真人真事”的旗帜下,由于个人经验被提升,工农兵即使不具备创作能力,也能成为创作过程中的主导者。正是因为“真人真事”成为解放区文学中的一种创作法则,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作家在创作中,一定要征求当事者的意见。这不是作家们故作姿态,如果他们的作品不能得到“真人”的认可,整个作品就不成功。有“真人真事”的法则作为后盾,“穷人乐”方向在鼓励群众创作上就显得理直气壮。试想,如果群众都敢于创作了,专业作家岂不只有改弦易辙?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由于“真人真事”创作长时间地推广,作家们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有一些这样的作品,太被真人真事所局限了。事件不敢集中,情节不敢虚构,人物不敢放笔描写,于是整个的作品,苦于主题分散,结构平直,人物不够突出,高潮好像也高不起来。有的戏也大胆加了一些作者所假想的东西,但又遭到那位“真人”的抗议,说加的不是“真事”,甚至还有的“真人”,索性排斥了作家,自己写剧本了,这使作者十分苦恼。(22)
当作家的“虚构”权力被消解之后,解放区的文艺是否就进入到完全“纪实”的时代了呢?或者说,作家可不可能在纯粹的“真人真事”中获得一种超越的可能性呢?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也是考察“真人真事”创作与后期解放区文学走向之间联系的重要维度。在理论上讲,即使作家的“虚构”权力被消解,在众多的“真人真事”中,作家依然可能从现实中脱颖而出。但很可惜,在后期解放区文学中,我们并没有看到这样的作品。不仅如此,从今天的角度审视后期延安文学,其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真实性”,也是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什么不仅作家在“真人真事”当中失去了升华的力量,而且整个文学的“真实性”也成为怀疑的对象呢?我们不能不对“真人真事”做更深刻的认知。
问题的症结在于:“真人真事”瓦解了作家虚构的权力,但并没有瓦解“真人”虚构的权力。“真人”既可以在“真人真事”创作中自我美化,还拥有了在创作中虚构历史的权力。很多作家在进行“真人真事”创作中,都记录了“当事人”修改的细节。譬如,吴满有不满艾青说他是“老来红”,要求改成“劳动英雄”;李国瑞不满写他受到批评后“悲观失望”,而要求改为“不服气”(23)。这些改动,当事人显然有自我美化的意图,作为底层农民,为了表现自己的美好形象,自觉向政治潮流靠拢是必然的选择,而“真人真事”创作显然赋予了他们虚构自己的权力。也正是这个原因,在“真人真事”创作中,即使作家有意与创作潮流拉开距离,实际上也不可能行得通。而在“真人”创作——群众创作当中,又不乏虚构的例证。周而复在《边区的群众文艺运动》中回忆“真人真事”创作时说,由于真人真事运动的开展,群众创作获得了发展的机会。群众创作注重作品的真实性:“内容多半是实有其人,实有其事,有时甚至把真人真事编排到创作里去,从而不写虚无的故事。”“但也有时候,不完全根据真事和真人,而加上和综合一些别的地方的人和事,这样,又丰富了作品内容的典型性。”(24)韩塞在回忆平山县柴庄村剧团在编排《穷人翻身》时披露了这样的史实:“用的是真人真事,村里的受苦人,争着把自己难忘的苦水编上去,他们编了一个假名字的人,把大伙的事凑在他身上,让他从苦到乐生活下来。”(25)这里提到一种特殊的虚构方式,将“真事”拼贴在一起,这种做法看似每一个事件都“真实”,但当众多事件经某种逻辑成为叙事,虚构也就产生了。譬如《穷人乐》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戏剧最终反映了穷人翻身的故事,但如果从纯粹真实的角度来考察,至少有两个方面值得玩味:第一,如果仅仅从“真人真事”的角度进行编剧,高街村的故事可以形成“翻身”的效果,也可以不如此——这不仅因为生活的多面性,而且还存在叙事角度和方式的问题;第二,当众多反映旧社会苦的事例组合在一起,势必改变当时乡村阶级矛盾的事实,这是否符合现实主义的精神也值得推敲。所以说,“真人真事”并不一定就代表了客观和真实——“真实”只能表现在一定的层面上,并不存在绝对的“真实”。群众创作的作品,之所以没有形成丰富的效果,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能够获得创作权力的群众,本身已经在革命运动中选择了进步的立场,他们必然将笔调顺应到革命需要的路线上。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真人真事”成为一个有力的武器,在某种程度上主导了后期解放区文学的走向。
①譬如艾青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创作的《吴满有》、《养羊英雄刘占海》,丁玲创作的《田保霖——靖边县新城区五乡民办合作社主任》,这些创作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②张真:《从真人真事提高到典型——学习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札记》,《中国戏剧》1958年第24期。
③郭国昌:《“真人真事”写作与解放区文学生产体制的建立》,《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④川口浩:《报告文学论》,王荣纲编:《报告文学研究资料选编》下册,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85页。
⑤《文艺大众化问题座谈会》,《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
⑥胡风:《关于速写及其它》,《胡风选集》第1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8页。
⑦⑧周扬:《谈文艺问题》,《周扬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502,502页。
⑨“真人真事”的戏剧作品可能扩大了英雄模范人物的传播途径,它可以让不认识字的农民了解英雄模范人物,同时也制造了英雄模范人物的轰动效应,但这种影响还是不如英雄大会的影响力大。
⑩《致丁玲、欧阳山》,《毛泽东文艺论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85页。
(11)姜夔:《续书谱》,《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813册,第559页。
(12)在艾青创作《吴满有》之前,《解放日报》对吴满有的报道主要如下:1942年4月30日发表了人物通讯《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连年开荒收粮特多 影响群众积极春耕》,塑造了吴勤劳致富、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上交公粮的形象,也充分表述了贫苦大众土改后对共产党的拥戴之情。同日,还发表社论《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和莫艾采写的通讯《模范英雄吴满有是怎样发现的》。同年5月5日,刊发《政府号召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和《忘不了革命好处的人》等报道和通讯。同年5月6日,刊发《吴满有——模范公民》,号召整个解放区向吴满有学习。同年10月29日,刊发《今年丰收吴满有特别好》的消息。1943年1月8日,报纸刊发《劳动英雄吴满有计划今年扩大生产种地八十五垧努力发展副业勤锄草多施肥增产粮十余石》。同年1月11日,该报再次刊发《开展吴满有运动》的社论。同年1月26日,又刊发《吴满有捐款劳军积极领导优抗工作》。通过这些社论和消息,吴满有在边区已经形成了较为清晰的公众形象。
(13)《解放日报》1942年5月5日。
(14)张学新:《晋察冀文艺运动大事记(1937.7—1948.12)》,《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3期。
(15)左莱、梁化群:《苏区“红色戏剧”史话》,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第31页。
(16)张学新:《晋察冀文艺运动大事记(1937.7—1948.12)》,《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4期。
(17)张洪轩、韩荣实、姜坦:《从前哨剧社到六十三军文工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下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844—845页。
(18)肖向荣:《部队的文艺工作应该为兵服务》,《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下册,第474页。
(19)[法]司达克·杨著,章泯译:《表演艺术论》,上海:上海杂志公司,1939年,第1页。
(20)《穷人乐》,大连:大连大众书店,1946年,第100—101页。
(21)张鸣:《动员结构与运动模式——华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政治运作(1946-1949)》,《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3年6月30日。
(22)张真:《从真人真事提高到典型——学习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札记》,《中国戏剧》1958年第24期。
(23)杜烽:《〈李国瑞〉写作前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2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174页。
(24)周而复:《边区的群众文艺运动》,《群众》第10卷第3、4期(1945年2月26日)。
(25)韩塞:《回忆抗敌剧社与晋察冀边区戏剧运动》,《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2册,第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