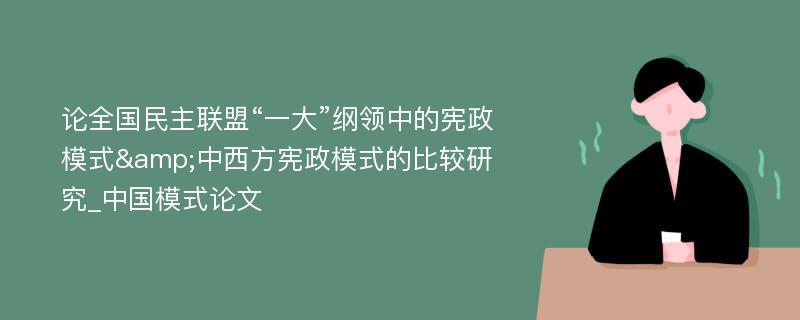
论民盟“一大”纲领中的宪政模式——中西宪政模式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宪政论文,模式论文,一大论文,纲领论文,中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民主潮流有了新的发展。怎样把握住战后这“千载一时的机会”,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十足地道的民主国家”[1](P71),成为中间党派关注的热点问题。1945年10月1日~12日,中间党派在重庆召开了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即“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通过的纲领、发表的宣言和政治报告中,中间党派设计出一套“中国型”的宪政模式。所谓“中国型”的宪政模式,就是中间党派一方面吸收了西方宪政中政治民主的内容后,另一方面又注入了经济民主的内容。本文试图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将中间党派所设计的这套“中国型”的宪政模式,与西方代议制政体模式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加以比较,从而说明中间党派所设计的这套“中国型”的宪政模式的特质。
一
就政治民主而言,中间党派认为,西方代议制政体模式是“建立中国民主制度的宝贵的参考材料[1](P76)。虽然,到了二十世纪,西方代议制政体模式已陷入重重危机,面临严峻挑战,但中间党派认为,这“不是从那种制度本身发出来的,而是在其社会经济制度缺乏调整”的情况下出现的。[1](P67)因此,在政治民主方面,中间党派就以西方代议制政体模式为蓝本,设计出英国式的议会制度、责任内阁制、地方自治制等一整套政治制度。
第一,英国式的议会制度。中间党派认为,英美的议会制度是“建立中国民主制度的宝贵的参考材料”。有了这种议会机构,人民就能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参预政府的决策,管理政府的财政和监督政府的行动。也可以说,有了这样的议会制度,人民才能作为国家的主人行使所拥有的权力,真正成为管理国家的主体。如果这种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人民在政府的决策、财政的管理诸方面没有实质性参与,也不能有效地监督政府的活动,那么,这就不是一种真正民主的制度,而只是拥有一个民主的空名。因此,中间党派在民盟“一大”纲领中引进了西方的议会制度。众所周知,由于各国阶级力量对比、历史传统、文化习俗、宗教信仰以及民族状况等因素的差异,各国议会的具体构成形式不尽相同。从议会的职能来看:西方议会大致分为英国式和美国式两类。所谓英国式的议会制度,即议会不仅是国家最高立法机关,而且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议会的法律地位居于行政和司法之上,政府对议会负责;所谓美国式的议会制度,即议会只是国家最高立法机关,而不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议会与总统、法院三者依法分权与制衡。从议会的组织机构来看:议会一般采用一院制或两院制。中间党派在民盟“一大”纲领中,就是根据西方议会的职权和组织结构设计出中国的国会,即“国会为代表人民行使主权之最高机关,由参议院及众议院合组之,国会有制定法律,通过预算、决算,规定常备军额,宣战、媾和,弹劾罢免官吏及宪法赋予之其他职权”。“国家最高行政机构采内阁制,对众议院负其责任。”[1]由此可见,民盟“一大”纲领中设计的国会,不仅是国家最高立法机关,而且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属英国式的议会制度。
第二,责任内阁制。近代西方三权分立的宪政构想,源于西方传统文化中对人性的否定性评价,即对人的不信任。人性的弱点必然体现在国家权力的运用中,对国家权力施以法律的约束就成为宪政必须具备的内容。为此,西方的思想家、政治家提出了分权制衡的理论。但由于各国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各国建立了不同的政体模式,特别是在行政体制中,形成了两个相互接近又相去甚远的典型形式:美国式的总统制和英国式的责任内阁制。两者的区别在于:一、前者议会只是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不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议会与行政机关、立法机关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后者议会不仅是国家最高立法机关,而且也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其法律地位实际上高于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而且内阁对议会负责,体现了“议会至尊”的精神。二、前者行政权属于总统,总统即是国家元首又是行政首脑,在行政体制中属一元行政体制;后者行政权属于内阁,君主或总统只体现了国家和政权机构的连续性,不负实际责任,属二元行政体制。中间党派在民盟“一大”纲领中,就是根据西方国家建制的政治原理,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部分,即“国会为代表人民行使主权之最高机关”,内阁为“国家最高行政机构”,“司法绝对独立,不受行政军事的干涉”。由于内阁掌握国家最高行政权,总统的设置就成为国家团结和连续性的象征,是“有职无权”的虚君,犹如英国的君主,属二元行政体制。又由于内阁向国会的众议院负责,这就使得国会在法律上取得了高于内阁的地位,内阁的权力受到国会极大的限制,形成了一种英国式的“议会至尊”。
第三,地方自治制。地方自治是实施宪政的重要条件,没有完备的地方自治,也就没有宪政。世界上任何一个实施宪政的国家,都是以地方自治为基础的。但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地方自治的程度与规模也就不尽相同。一般分为集权主义的地方自治和分权主义的地方自治两种。所谓集权主义的地方自治,即中央政府对于地方自治机关的事务有最终决定权,地方自治机关的官员兼有中央官员和地方官员双重身份,中央政府有权随时撤换他们。中央政府对地方自治机关的监督以行政监督为主,中央政府可随时向地方机关发布强制性指示,地方机关必须执行,否则中央政府可采取强制性措施。所谓分权主义的地方自治,即地方自治机关行使由法律确认的自治权时,中央政府一般不加过问,地方自治机关形式上独立于中央政府之外;地方自治机关的官员由当地居民选举产生,他们只具有地方官的身份,中央政府不得撤换他们;中央政府对地方自治机关的监督以立法监督为主,一般避免对其发布强制性指示。[2]中国应取何种形式的地方自治?民国以来,一直是中央政府与地方实力派争斗的焦点。从袁世凯到蒋介石的几代统治者都推行中央集权政策,其结果不是形成中央专制,就是造成地方割据。可谓“日日求中央集权,日日但见高级地方之省封殖武力”[3]。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由于中国地域广阔,各省地方人情风俗文化背景不同,不利于实行高度中央集权制;[1](P136)另一方面还由于中国的统治者对集权制的误用。中国历代统治者制度精神缺乏,法制观念淡薄,其推行的中央集权不是上述正确意义的中央集权,而是一种无理专制的极端集权主义,即中央不给地方任何自治权。没有地方自治的中央集权,就是没有宪政的封建专制或法西斯独裁。要实施宪政,就要摒弃这种极端集权主义。因此,民盟“一大”纲领明确规定:“中央与省、省与县之权限应以宪法明定其采分权制度”,“制定省宪”、“省长民选”[1](P66),即实行一种分权主义的地方自治。
从上述三个方面分析可以看出,中间党派在民盟“一大”纲领中设计的宪政模式,在政治民主方面,直接汲取西方代议制政体模式。然而,他们设计的宪政模式,并没有就此终结,在吸收了西方政治民主的内容后,又注入了经济民主的内容,以此构成了他们设计的“中国型”宪政模式的特色。
二
就经济民主而言,中间党派考察了欧美各立宪国家民主宪政与国民经济脱节带来的恶果后,认为只有实现国民的经济民主,国民的政治民主才能得以保障,社会经济才能有序增长,生产力才能重新无束缚地自由发展,这才是真正的或全民的民主,民主制度才有了一个完整的形态。他们认为,苏联的宪政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宪政,“其宪政对于国民经济的规定与措施”是“以享有此项国家主权的人民利益为前提”。因此,苏联的经济民主是“中国建设民主制度的极好的参考资料”,即“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1](P77),从而创造出一种“中国型”的民主宪政模式。
中间党派所设想的经济民主,具体讲就是“全国经济之生产与分配由国家制定统一经济计划”的计划经济模式。[1](P68)这种计划经济模式是不是就是中间党派所标榜的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呢?由于中间党派所设想的计划经济只是一种原则构想,至于如何实现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并无具体规范,笔者也就无从描述其计划经济的基本特征,并与苏联计划经济的特征加以比较,来论证两者之间的区别。但由于两者所凭藉的所有制基础不同,就决定了两者必定不是同一种类型的计划经济模式。
就所有制基础来看,中间党派主张国家应“确立公有及私有财产”[1](P68),“并鼓励奖励私营企业,使一切私有企业家得到自由竞争平等机会”[1](P85)。这就是说中间党派所设想的计划经济是建立在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并存,并维护私营企业的基础之上的。而1936年苏联通过的新宪法正式颁布“苏联之经济基础,为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及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并只承认这种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两种表现形式:“国家财产(全民财产);合作社集体农庄财产(各集体农庄财产、各合作社财产)”,完全排斥其他经济成分,仅“容许个体农民及手工业者小规模私有经济,但以自立经营,决不剥削他人劳动者为限”[4]。由此可见,苏联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计划经济模式是建立在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的。又由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苏联正处在备战和战争时期,使得苏联经济体制具有了高度中央集权的特征:即国家将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各个企业全部纳入国家统一指令性计划和行政管理的轨道。苏联计划经济的这一基本特征在私有制存在的社会经济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只要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的存在,各部门、各企业都会按照自认为最为有利的方式进行生产经营,不可能接受国家任何指令性的计划调节和行政手段的管理。因此,笔者认为,中间党派所设想的那种建立在维护私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模式与苏联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实行的建立在单一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模式有本质的区别。但如果将中间党派所主张的经济民主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加以比较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中间党派主张的经济民主吸收了许多民生主义思想中的内容。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是从中国的“贫”出发的。他认为中国“今日患贫,不患不均”[5](P381)。要解决这个“贫”,“在于发展实业之一事”,即通过“发达国家资本,振兴实业”,实现生产的工业化以求富。[6](P17)但为了避免中国重蹈欧美国家贫富不均的覆辙,就要通过“平均地权”,“节制私人资本”的方法,解决分配的社会化以求均。中间党派主张经济民主的着眼点在于财富的“不均”。他们看到欧美各国,由于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这些财产所有者,凭藉其经济上的实力,操纵了国家政权,使人民在政治上自由平等的权利“在许多方面就落空了,成了有名无实的空调”[1](P77)。因此,他们认为:“二十世纪的民主,经济的自由平等较政治的自由平等更为重要”。同时他们也认识到“倘中国再停留在一种原始的落伍的手工业时代,这不仅不能改善人民生活,并且不能保障国家的生存”。为此,今后中国要“增加社会生产力”,“在短期内达到工业化的目的”[1](P84)。可见,中间党派主张的经济民主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虽然出发点不同,但终极目标都是“均富”。那么,如何实现这个“均富”的目标呢?在思想理念和设计方法上,中间党派在不少地方吸收并发展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
第一,实现分配的社会化以求均。孙中山在他的民生主义思想中,首先提出的就是“平均地权”。他认为欧美社会问题没有解决好,是因为未能解决好土地问题。在中国“若能将平均地权做到,那么社会革命已成七八分了”[6](P17)。“平均地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城市土地采取“核定地价”、“照价收税”、“照价收买”、“涨价归公”的办法,以达到防止土地被私人垄断,促进土地利用,最后达到土地国有的最高原则;二是对农村要采取“耕者有其田”的办法,即对“农民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并为之整顿水利,移植荒缴以均地力”。“农民之缺乏资本至于高利贷以负债终身者,国家为之筹设调剂机关、农业银行等,供其匮乏。”[18]随后孙中山又提出了“节制资本”。其具体办法:一是通过划分国营与民营事业的范围,以杜绝私人垄断独占、操纵国民生计的机会。这是“节制私人资本”的一个重要步骤。二是通过征收累进率的直接税,节制私人资本无限增殖,以充实国家财力。孙中山认为:“直接征税是最近进化出来的社会方法。行这种方法,就是用累进率,多征资本家的所得税和遗产税等。施行这种税法,就可以令国家的财源多由资本家而来,资本家入息极多,国家直接征税,所谓多取之不为虐。”[5](P367)这是“节制私人资本”,平均社会财富的一个主要办法。
中间党派在平均社会财富解决社会分配问题时,也是从“土地”和“资本”这两个方面入手的。中间党派认为:“现代之政治问题,多半即为经济问题,而经济问题中之最重要者,实无过于土地问题,是以土地问题,苟无根本解决之办法,则一切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必在波荡动摇之中。”[7]那么,如何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呢?其方法:一是“切实保障贫农的土地使用权,以达到土地使用权与所有权的合理化与合一化”[1](P68)。这实际上与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并在此思想基础上,中间党派还明确提出了土地使用权与所有权合一化问题。二是“规定最高限度之土地私有额,凡超额之私有土地,国家于必要时,将以法定程序征购之,而已渐进方式完成土地国有之最高原则”[1](P68)。这是吸取了孙中山关于私有土地采取“照价收买”和“土地国有”的思想。在资本问题上,中间党派基本上吸收了孙中山“节制私人资本”的主张,并有所扩展。其一是规定“附属于土地之矿业、水利,在经济上可公共用者,均属国有”;“银行、交通、矿业、森林、水利动力、公用事业及独占性质企业,概以公营为原则,至其他一切企业,均可由私人经营。”其二是规定“税制应依据能担负之原则,并以累进方式征收遗产税、所得税及利得税”[1](P68),即利用税收来限制私人资本过分膨胀。以上两个方面主要指节制城市私人资本,中间党派在此基础上,还将“节制私人资本”从城市扩展到农村,即通过“实施减租”,“规定最高限度之土地私有额”[1](P68),来节制农村的私人资本,这可以说是对孙中山“节制私人资本”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第二,实现生产的工业化以求富。孙中山认为:“中国今日的情形是上下交困,大家都是一样的穷。”[6](P17)如何才能摆脱这种贫穷,实现工业化呢?其一是“发达国家资本”实现工业化。孙中山认为,欧美各国的工业化过程,包括两种工业革命。“易手工用机器”是第一工业革命;20世纪初那种“以经济集中代自由竞争”、“工业统一与国有”为第二工业革命。中国要两种革命同时并举,“既废手工采机器,又统一而国有之”[8]。这实际上就是发达国家资本,以国家经营加速工业化的道理。其二是利用外资发展实业,加速实现工业化。孙中山认为,“我国既有天然之富源,无量之工人,极大之市场,倘能借此机会,而利用欧美战后之机器与人才,则数年之后,吾国产业的发达,必能并驾欧美矣。”[9]可见,孙中山坚信利用外资是中国发展实业、实现工业化的捷径。
中间党派对中国的贫穷落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经济“陷于全部停顿崩溃的状态”有着清醒的认识,深感“一个工业落伍的国家,处在几个高度工业化国家的公共市场中,自身必成为他人的附庸,必受他人经济压迫与剥削”。因此,他们大声疾呼:“增加社会生产力”,“以促进国家的工业化”[1](P84)。其具体措施:一是通过实施对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以实现工业化。即“依照国家经济政策,及经济计划之规定,分别由国家或私人经营之”[1](P68)。他们认为,“在发展工业上,中国的经济政策必力求计划与自由经济相配合”,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够在短期内达到工业化的目的”[1](P84)。这与孙中山“发达国家资本”以实现工业化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二是引进外资以实现工业化。中间党派认为,“为了达到此目的起见,国家得依法律之规定,与外人以投资之便利”[1](P68)。由此可见,中间党派也认识到引进、利用外资是实现中国工业化的一条重要途径。
通过上述对民盟“一大”纲领中所体现的宪政模式的具体分析可以看出,在政治民主方面,中间党派直接引进了西方代议制政体中的责任内阁制;在经济民主方面,吸收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而不是苏联的经济民主——建立在单一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模式。中间党派所谓“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的主张,是他们对苏联经济民主的错误认识和理解。因此,笔者认为,民盟“一大”纲领中所体现的“中国型”的宪政模式,简单地说,就是英美的政治民主加上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但由于主客观诸种因素的影响,中间党派所设计的这套“中国型”的宪政模式并没有付诸实践。这是因为:就中间党派所追求的政治民主——西方代议制政体模式而言,在中国缺乏实施这一政体模式的经济基础、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就经济民主而言,由于连年的战争,使中国不具备实施民生主义的和平环境。尽管如此,中间党派试图在中国走出一条既不同于英美,又有别于苏俄的宪政道路,他们这种探索精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们设计的这套“中国型”的宪政模式,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宪政运动的走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