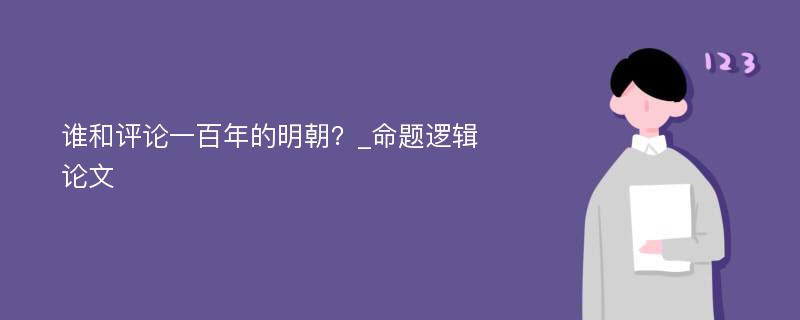
因明百年,谁与评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因明论文,谁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0)05-0098-05
在西方逻辑、中国墨辩和印度因明三大逻辑比较研究中,因明研究显得相对落后,在国际上至今仍是冷门学科,在中国曾经成为绝学。直至清末玄奘弟子窥基的《因明大疏》由日本回归东土,汉地的因明研究才有可能重续唐疏正脉。因明复苏虽说已有百十余年,成就斐然[1],但在因明与逻辑比较研究方面,却走了大半个世纪的弯路。不少因明研习者从20世纪初起便丢掉了唐疏的优良传统,邯郸学步,采取“拿来主义”,学日本、学欧美、学印度,照搬了许多现成的错误结论。
写下这个题目,正是希望全国更多的逻辑和佛学工作者进一步关注和评说最近一百多年来国内外因明与逻辑比较研究的状况。
先来引一段感人肺腑的遗言。周文英先生在《周文英学术著作自选集》中说:“在评述‘论式结构’和‘因三相’时有失误之处”,“这些说法当然不是我的自作主张,而是抄袭前人的,但不正确”。①这使我心灵震憾。我由衷地敬佩,敬佩一个襟怀坦荡的大学问家实事求是的治学品格。在自己赖以成名的研究领域,敢于检讨失误,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魄力。现在讲究学术规范,这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杰出的榜样。
抄错了的前人是谁,抄错了什么?周文英先生是“文革”以后较早发表因明研究论著的著名学者。他照搬了苏联科学院院士舍尔巴茨基的《佛教逻辑》和印度威提布萨那的《印度逻辑史》。
舍尔巴茨基的《佛教逻辑》认为,从古正理、古因明的五分作法到陈那、法称的新因明始终是演绎的。[2]这有两个错误:一是拔高了古正理、古因明的五分作法,否定了陈那的贡献。《大英百科全书》对《正理经》五分作法的评论与舍尔巴茨基完全相同[3];二是用法称因明来代替陈那因明,否定了法称的贡献。第一个错误被国内许多佛教哲学论著所采纳,同时又影响到了北京大学的两个《正理经》中译本的注解。第二个错误在国内影响巨大,被因明、逻辑工作者照搬了半个多世纪。
印度学者威提布萨那的《印度逻辑史》用后起的法称才提出的三种正因(自性因、果性因、不可得因)来解释和代替陈那的因三相规则,完全混淆了历史文献,错解了两位因明大师的历史贡献。
我发现这些错误在藏传因明的研究者中也有影响。著名藏传因明专家法尊法师、杨化群先生就误用陈那九句因来解释法称因明,再用法称因明来代替陈那因明。这样就混淆了陈那、法称各自的贡献。
国外的因明研究者除少数人(美国的理查德教授、欧洲的少数学者如德国的哲学博士孤鹤先生等)外,大多未能准确地刻画陈那因明的逻辑体系。以舍尔巴茨基的《佛教逻辑》为代表的种种错误解读,根源于违背了陈那因明和逻辑三段论这两方面的基本知识。第一,《佛教逻辑》依据的《正理门论》,是意大利学者杜齐从玄奘汉译转译而来的英译文。该英译总体很好,却漏译了第二相“于余同类,念此定有”中的“余”字。这一字漏译,便抹去了陈那因后二相除宗有法的重要规定;第二,因第一相的逻辑形式为“凡S是M”,衡以逻辑,S必然周延而M却不周延。舍氏却宣称违反因第一相的过失在于因法概念不周延(国内居然也有人以为第一相“遍是宗法性”相当于中词周延一次的规则);第三,他将第二相的逻辑形式与同喻体等同,认为第二相的主项是因同品而非宗同品,整个命题是全称判断而非特称判断;第四,认为因后二相相等,可以互换。换句话说,后二相可缺一;第五,认为陈那因明也容许同法式和异法式可单独成立(这与陈那三支作法必须同、异喻双陈的常识相违背),两者就是三段论的第一格和第二格;舍尔巴茨基在解释法称因明的同法式和异法式时说:“每一逻辑标志都有两个主要特征,只与同品(同类事物)相符而与异品(异类事物)相异。陈那认为这是同一个标志,决非两个标志。”[4]似乎陈那自己就认为同喻体和异喻体在逻辑上是可以等值互换的。舍尔巴茨基又说:“这整个的认识领域是由契合差异法所制约的。但既然其肯定与否定两方面是均衡的,只须表述其一方面也就够了。或者相异或者相符,其反对面都可以必然地暗示出来。这便是每一比量式均有两个格的原因所在。”[4](p.328)该书还指出,这两格就相当于三段论的两个公理。[4](p.331)第六,三支作法既是归纳的又是演绎的,因后二相和同、异喻体便构成了契合差异并用的归纳推理,等等。如是种种误读,却恰恰为国内的众多因明研究者全盘接受。我对这些误读的详细批评,多数已发表于他处。
国内只有少数几个人不完全照搬舍尔巴茨基的错误观点。巫寿康博士的《因明正理门论研究》认为陈那因明中的同、异品除宗有法,使得异品遍无性并非真正的全称命题,使得因三相不能必然证成宗。这对于判定陈那新因明三支作法的推理性质(种类)有重要意义。他还认为因三相是互相独立的。第五句因是满足第一相和第三相,只不满足第二相的因。第五句因的存在,就保证了因的第二相独立于第一相和第三相。但是巫寿康博士既然指出了同品、异品除宗有法使得因三相不能保证必然证成宗,本来他应该循此逻辑,判定陈那新因明三支为非演绎推理,但是他却根据陈那关于遵守因三相就能“生决定解”而判定其有演绎思想。巫博士为满足自己的主观要求,违反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替古人捉刀,修改异品定义,使异品不除宗有法(不除论题主项),以保证因三相必然证成宗。这一做法,非古籍研究之所宜,不是在研究逻辑史,而是在修改逻辑史。况且,修改后的体系包含许多矛盾。我的博士生发现异品不除宗有法的观点不是他的创见,在沈有鼎先生的文集中可以查到。但是沈先生只留下图解,没有文字说明,没有提出文献上的依据。而巫寿康却发挥了沈先生的这个想法,演绎为一个20世纪80年代的新因明体系,诚非历史研究之所宜,不足为训。
我的硕士研究生又发现,同品除宗而异品不除宗的观点又不是沈有鼎先生的首创,美国的齐思贻教授在其著作《佛教之形式论理学》中已经提出过了。不过,齐思贻曾明确指出,自己采用了法称的异品定义。陈那的同、异品定义都除宗有法,而法称都不除宗。齐思贻把两个不同体系中的同、异品概念各取其一,这样组合起来的体系既非陈那体系的原貌,也非法称体系的原貌。
还有一种观点则是认为,为他比量(悟他比量)的同品需要除宗有法,而为自比量(自悟比量)的同品不需要除宗有法。沈有鼎先生的《墨经的逻辑学》就曾指出:“对于同一的‘宗’(结论),‘自悟比量’(自己论证)和‘悟他比量’(说服人的论证)所用的‘因’(前提)不必相同。因为在‘悟他比量’中,‘因’必须‘共许’(双方承认)才行。”[5]
其实,陈那因明中的为自比量和为他比量,都是指的共比量而言。这种观点将为自比量与为他比量区别开来,可能是混淆了为自比量和自比量。但即便是自比量的同、异品也都要除宗有法。文轨的《庄严疏》对不共不定因过(第五句因)有一非常重要的疏解:“如佛弟子对声论立宗云:‘声是无常,因云所闻性故。’此因望自同异二品皆悉非有,望他声论即于异品声性是有,故是自不共也。”[6]这是说,对立论者而言,以“所闻性”因证“声无常”宗,也必须将“声”除外。除“声”以外,同、异二品都没有“所闻性”因。否则,任何人立自比量都可以当思想懒汉,只要把论题主项拿来当同品,第二相就满足了。轨疏这般强调同、异品必须除宗有法,并非多此一举。这应当视为玄奘的口义,阐明了在当时尚且生疏的学问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1](p.121)[7]
须知,除宗有法的同、异品是陈那因明逻辑体系的两个初始概念,是陈那因明中的“题中应有之义”。同、异品不除宗,陈那因明的整个逻辑体系都崩溃了,是无法理解的。同品不除宗,会导致循环论证,异品不除宗,同样会导致循环论证,即授论敌以反驳特权。逻辑学家、因明专家陈大齐(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早就指出,异品不除宗,异品遍无性不能满足,任立一量都无正因可言。于是,便得出任立一宗都无证成的可能的荒谬结论。
在同、异品除宗情况下判定陈那因明为演绎不合逻辑,而修改异品定义又走不通的情况下,我觉得应实事求是地按照陈那因明的本来面目刻划其逻辑体系。一个因只要遵守了因三相,它虽然能“生决定解”,即取得辩论的胜利,但离演绎还有一步之差。第二相同品定有性的命题形式是:有P且非S是M;第三相异品遍无性的命题形式是:所有非P且非S不是M。同、异喻体是除外命题。按照上述观点能一通百通、圆融无碍地解释陈那与法称两个逻辑体系的同异。反之,寸步难行,矛盾百出。近年来我连续发表了下列论文:《论因三相正本清源》、《再论因三相正本清源——兼与姚南强先生商榷》、《因明与逻辑比较研究百年述评》、《弘斯正理门妙尽自他共——论玄奘对因明的历史贡献》(与汤铭钧合作)、《汉传因明是解读印度新因明的钥匙》、《论印度佛教逻辑的两个高峰》、《论法称因明逻辑体系》、《因明与逻辑比较方法论研究——兼评黄志强现代因明研究之路》、《论因明研究的整体论方法——兼答沈剑英先生诘难》、《从集量论看陈那因明逻辑体系》等,多次对相关问题作了阐述。
除了苏联、印度的代表性著作对我国的因明研究有严重误导外,1906年日本文学博士大西祝的《论理学》译成中文出版,也对我国的因明研究发生了重大影响,长达一个世纪。大西祝对陈那新因明的基本概念的正确解读和对陈那《正理门论》逻辑体系的错误判定,对陈大齐教授有着深刻的影响。大西祝强调,陈那因明规定了同、异品必须除宗有法,否则建立因明论式便多此一举,并且正确地指明同、异品除宗有法,就难于保证宗的成立,就是说陈那的因三相无法保证三支作法是演绎的。这一点非常正确。但他又认为同、异喻体是全称命题,回避了因的后二相除宗有法与同、异喻体之为全称的矛盾,回避了这一矛盾的解决途径,简单地断言同、异喻体全称则能证成宗。[8]这一观点开了20世纪因明与逻辑比较研究重大失误的先例。
陈大齐是因明巨匠。他对陈那新因明的基本概念及其对整个体系的影响都具备较为正确、较为深入的认识,但令人遗憾的是,他百密一疏,临门一脚打偏了。陈大齐担心新因明虽然增加了喻体,但依然无所裨益。其实,除外命题已在最大限度上提升了不完全归纳的可靠程度,在辩论中能取得“决定解”,即获胜,这就是裨益。
陈大齐指出:“在逻辑内,演绎自演绎,归纳自归纳,各相独立,不联合在一起,所以归纳时不必顾及演绎,演绎时不必顾及归纳。因明则不然,寓归纳于演绎之中,每立一量,即须归纳一次。逻辑一度归纳确立原理以后,随时可以取来做立论的根据,所以逻辑的推理较为简便。因明每演绎一次,即须归纳一次,实在繁琐得很。”[9]这一说法不符合印度因明的理论和辩论实践,在任何因明典籍中都找不到每立一量必须当下归纳普遍原理的话。
“故欲同喻体真能奏证明之功,必须释此中的因同品为总摄所作义的全范围,未尝有所除外。归纳资料在实际上是有所剔除的,归纳所得的喻体在效用上不能不释为无所除外,这其间的空隙怎样填补呢?关于这一点,也只好仿照逻辑的说法,委之于归纳的飞跃。从一部分的事实飞跃到关于全部分的原理,这是归纳的特色。”[9]他希望在形式逻辑的领域内,凭借“归纳的飞跃”来弥补不完全归纳推理的漏洞,以消除同、异品除宗有法与同、异喻体之为全称的矛盾,显然不合逻辑。因为不完全归纳推理的结论是或然的。况且在佛教因明的原著里连“归纳的飞跃”的影子都见不到。
陈大齐认为因后二相本身就是推得同、异喻体的归纳推理,这不妥当。因后二相不过是两条规则,它们并没有表明自身是如何归纳出来的。它们表明,一个因要成为正因,就必须遵守这两条规则。正如三段论的规则“中词必须周延一次”和第一格的规则“大前提必须全称”一样,只是规定了一个正确的推论应当怎样,而没有交待自身如何得出,更不能以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归纳推理的过程。众所周知,三段论逻辑是吃现成饭的。在三段论理论中,没有一句话说到“大前提必须全称”是怎么来的。
我认为,陈那三支作法是类推,没有超出归纳的范围。当代的绝大多数学者都误认为陈那三支作法是演绎与归纳的结合。必须指出,这是一种调和折中的观点,既不敢于原原本本地按照陈那因明的体系,与传统的演绎说作彻底的告别;又总想在“演绎”中又另外找出归纳的因素,以此作为因明与西方三段论的区别。事实上,演绎与归纳的区别是质的区别,不是程度的区别。是演绎就不是归纳,即便是归纳,也只有完全归纳才达到了演绎的效果。
周文英先生在经过了一番深刻的反思之后,正是回到了这个折中的立场,认为因明的喻在喻体之外设喻依,这喻依作为例证,是归纳的标志,喻体是由喻依归纳而得到的。先生指出:“整个喻支就是一个假说的简略形式,它由假设句和相关事例合成,它是合归纳和演绎于一体的一种逻辑形式。这样解说的深层含义是突出喻依(即相关事例)在因明论式中的显著地位和重要作用。”同时,先生还指出:“特别是第二相同品定有的逻辑形式‘有同品是M’(如说,‘有瓶、锅、桌椅等是作成的’),其归纳性质,更是十分明显。这样就证定了因明三支式推理是不能脱离归纳的。因明三支式只能是演绎与归纳相结合的逻辑论式。”[10]
第一,陈那因明的推理规则因三相,是在元语言的层次上说的,推理过程本身则属于对象语言的层次。认为因第二相本身是一种归纳,或者干脆认为因的第二、第三相规则是归纳,似乎都混淆了元语言和对象语言这两个层次。况且,例证(同喻依)只是因第二相同品定有满足的标志,显示了同品中只要有一项有因便已足够,并不要求这一个例证能起到为一个近似普遍的命题提供论证的作用。
第二,在陈那的《理门论》、《集量论》等著作和商羯罗主的《入论》中,找不到每立一量必归纳一次的论述。因的后二相是从九句因中的二八正因概括出来的,但是,因的后二相的产生过程并非归纳过程。在九句因中,只是穷举了因与同、异品外延关系的九种情况。这是客观情况,而没有任何主观的归纳。陈那从未讨论过一个普遍命题由不完全归纳推理飞跃而成。归纳的飞跃只是现在的研究者的主观想法,用来代替古人则不恰当。每立一量则必先归纳一次,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都缺乏依据。
第三,在《集量论》中,陈那在讨论火与烟的无则不生关系的形成和运用时说:“‘因无错乱者,从法、于余显,彼成、则了解,具彼之有法。’谓火与烟,无则不生之系属,要先于余处显示之后(先在余处见到火与烟无则不生之关系),次于别处,虽唯见有烟,以若处有烟,则彼处有火。亦能显示成立有火。若不尔者,不能显示各别余处,所立火与烟,无则不生也。”[11]这一段话表明两点:一是除宗有法。“要先于余处显示之后(先在余处见到火与烟无则不生之关系)”,明言火与烟无则不生之关系不包括立论之际的此处。二是火与烟的无则不生关系是已有的经验,并非立论之际当下的经验总结。
第四,在法称的《正理滴论》中,法称指出正因必须是自性因或果性因。在一个具体论式中,所选择的因是否为自性因或果性因,也不是靠临时归纳得到的。法称建立同法式和异法式的两个喻体,也不是靠临时归纳推理得出的。法称明确指出:“如是一切能成立法,其为正因,当知唯由此能立法,若为实有,即能与其所成立法,相属不离。此义随宜,先由正量,已各成立。”[12]这是说,一切能立法只要它为实有的自性因法,便是正因,便能与所立法建立相属不离的普遍联系。这种普遍命题的真实性是由先前的“正量(现、比量)”证成的。这“正量”是已有的真实知识。相应的,依据果性因建立的同、异喻体,也不是当下临时归纳而来。照法上的解释,它们依照了“正、反两面的经验”。[13]这种经验是在立论之前就已具备的知识。因此,一个普遍命题的获得不应当从法称的比量形式或其规则(因三相)本身中去寻找根源。
印度佛教因明有两个高峰:陈那因明和法称因明。唐代玄奘在学成将还之际,代表了当时处于鼎盛时期的陈那因明的最高水平。陈那前期因明代表作《因明正理门论》梵本遗佚一千多年,至今唯有玄奘汉译本是研判陈那因明和逻辑体系的最可靠依据。玄奘忠实地译讲了陈那因明,他的弟子们所撰疏记保存有他的大量口义。由奘师开创的汉传因明是解读陈那因明的方便法门,又是方今借以打开陈那因明逻辑体系的一把钥匙,更是评判百年来因明与逻辑比较研究的一个重要标准。
百年来国外的因明研究者大多数不了解汉传因明的历史地位,对印度佛教因明的两个高峰有着种种误解。唯有充分地认识到汉传因明对陈那因明的正确解读,才能避免百年来的种种误解。意大利著名因明学者杜齐在为舍尔巴茨基的《佛教逻辑》撰写书评时就曾提到:“汉语文献对于研究佛教尤其是它的早期阶段的外部历史来说很有帮助,但是对于正确理解印度的哲学论典来说,藏文著作便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14]这代表了国际学界百年来的一般态度。
我为因明界有周文英先生那么深刻的反思而庆幸,但是我们还需要更加充分的检讨,还需要进一步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才能彻底翻过20世纪因明研究中“邯郸学步”的这一页,从而实现对因明的科学研究。印度学者威提布萨那在《印度逻辑史》中用法称的三类正因来诠释陈那《集量论》的因三相,这是张冠李戴。吕澂先生在其编译的《集量论释略抄》第二品的“附注第四”中明确指出这一严重误解:“费氏著书,引此二句(即《集量论·为自比量品》中“或说比余法,以因不乱故”)于破声量一段中,别以‘果性’、‘自性’、‘不可得’,释因三相,勘论无文。殆系误引法称之说以为陈那当尔也。”[15]吕徵先生在《因明纲要·引论》中提出因明研究的指导思想是“宜宗论而简疏”,就是说要读懂原,绝不随人转语。这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
美国的中国逻辑史学者陈汉生强调:“对中国古典哲学的文本中的一段话的解释必须与那一章的解释,以及与一本书的解释相一致。而对一本书的解释理论,必须是与作者的哲学理论相一致,必须是与作者所属的哲学学派的理论相一致,与当时的哲学环境相一致,与哲学的传统理论相一致,而这种哲学环境又必须形成与哲学自身本性的某种理论相一致。要检验那种解释的一致性,又与当时的政治活动、社会生活、宗教观念有关。我们比较各种解释,看它们在说明各个陈述时,其一致性、一贯性、简明性、优美性达到什么程度。”[16]只要我们承认陈那因明有一个完整的体系,那么这种“解释的一致性的方法论”显然也适用于这里。
任何一种对陈那因明的解释,都必须放到体系的整体的高度来衡量,其优劣得失,是否圆融无碍,便自然显示了出来。对陈那因明中某一点的解释,因而必须与整个体系相一致,哪怕有一处的解释作了任意的发挥,也将牵一发而动全身,以至于处处碰壁,捉襟见肘。这也是笔者所一贯强调的因明研究中的整体论方法。当我从汉传因明出发,对陈那因明获得了一个首尾一贯的解释,并以此为基础,对陈那、法称两个因明体系的异同有进一步理解时,我自信已能圆融无碍地解答因明研究中的大多数疑难。不管诤友们说我“哗众取宠、华而不实”也好,说我“急功近利、逞意而言”也好,批评我学识浅薄、未能“淹贯群籍”也好,我仍要坚定地走自己的路。我非常感谢诤友们的批评,正是有他们的鞭策,才不至于半途而废。
在三大逻辑研究中,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越是冷门越是能放卫星。搞西方逻辑的,搞墨辩逻辑的,都不敢像搞因明研究的那样夸海口,动辄解决千年难题,出口便是国际领先。可有谁知道,在许多论著中,逻辑和因明的常识错误却俯拾皆是。有的“创新”见解甚至不够批评的水平。有的论文的抄袭技巧真是匪夷所思,令人叹为观止!①究其原因有以下几条。“画鬼容易画人难”,此其一。只怪懂行的人太少,普天下的人都无法鉴赏其所画像与不像;在“百家争鸣”的旗帜庇护下,哪怕是奇谈怪论,只要有轰动效应便达到目的,就是一家之说,就有存在的理由,此其二。虽然众说纷纭,互相龃龉,但是碍于导师的面子,碍于作者的面子,你好,他好,大家好。相关领域专家们的不负责任的抬举,此其三。既得利益的驱使,错也要错到底,此其四。君不见西方数学史上根号2的发现者被抛到海里去了吗?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也是要被推翻的;以人为据、诉诸权威,此其五。不懂得历史主义的方法和整体研究方法,此其六。缺乏争鸣的宽松风气,此其七。
总之,讲清楚当代因明研究中各种观点的正误的根据何在,对纠正当代因明研究中的这种种不良学风,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注释:
①周文英,2002年:《周文英学术著作自选集》,第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周文英先生曾任中国逻辑史学会第二任主任、国家六·五重点项目《中国逻辑史》五卷本副主编。
②有的因明研习者完全仿照别人关于墨辩的论文写作因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