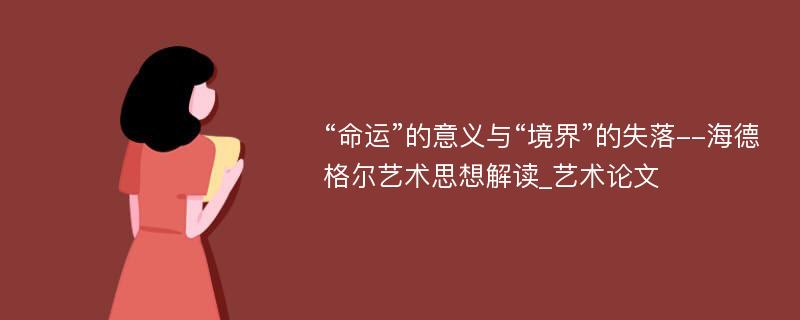
“命运”的属意与“境界”的失落———种对海德格尔艺术之思的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德格尔论文,境界论文,命运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海德格尔研究中,人们通常把其艺术之思视作美学。但美学作为行至真理半途而无“命运”发问的理论思路,在其存在之思中是没有地位的,特别是注重体验的现代美学及其艺术在他看来更是无根之说。用美学去阐释他的艺术之思是隔靴搔痒,尤其对《艺术作品的本源》这样貌似美学的论著说来更是如此。在《世界图像的时代》中,海德格尔认为艺术进入美学视野并成为体验的激发器,乃是现代的第三个根本现象。对他的这一断语,我们只有在其“返回”源头又带向前的林中路上筹划的存在之思的境域中,才能洞悉其意蕴——这意蕴关联着处于技术时代的他对技术“座架”的克服。在他看来,只有回到真理意义上的艺术才能成为救度现代技术僭越“存在之道作”的一个维度;惟有在“究元”的意义上,才能领悟此维度何以关联古希腊未可宰制的“天命”的力量:正是诉诸这种力量,使他属意“早先的”伟大艺术,把艺术作品的本源追溯到古希腊的“知”,提出对艺术的世界与大地相互争执的真理形态的理解,并从无蔽真理方面来思考艺术的本质。只有从此境域出发,结合思之转向,才能抉发出遮蔽在艺术之思中的底蕴,才能对他艺术之思的形上祈向及其时代忧患意识作出中肯评判,进而对其艺术之思因整个存在之思“境界”的缺失而丧失本有的人文关怀,并小觑人的心灵对“至善”价值的祈向,作出较为公允的裁断。
正是基于这一学理背景,笔者不揣浅陋,试图在“命运”与“境界”错落处领悟海德格尔艺术之思“究元”的意味。
一、行走在“命运”与“境界”“之间”的思考
海氏以此-在激情对存在及真理的追问,为价值平面化的技术时代重新提示一种神圣性,使生活在“洞穴”中的现代人获得“存在”之光的照耀。为此,他把哲学重新植根于存在经验的生成中,并把存在的力量与古希腊悲剧时代人们敏悟到的某种“命运”关联起来,使存在力量显现为“存在之天命”的君临。在他看来“存在”被遗忘且被抽象僵化为名词的时代,人类精神已经萎缩,整个文明已经退堕;他向源头的“回返”就是要为沉沦的时代注入力量,只是这力量与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命运”感关联着。因对某种与命运相关的存在之力的倾心,海德格尔就未能切近地诉诸对“至善”价值祈向的无待“境界”的开启。(注:“命运”与“境界”是人生躬身践履诉诸的两个不同的价值向度,具体内涵请参阅黄克剑先生《心蕴》等著述。)
无家可归是他对时代的命名,也是他对存在史的思。
直面现代文明的沦落,他试图以其思向人们喻说存在本有的那种赋有力感的动势,为新时代的开启做准备。这个时代需要的是“命运”笼罩下的强力(但不是尼采存在者意义上的强力意志),人以此为“存在之天命”所垂青而重获“命运”感,从而“天、地、神、人”共舞,使物成为物,使世界成为世界,人得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种对“命运”的祈向在他巡游古希腊时感受尤为强烈。海氏对古希腊以来延续的一种精神运动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这种理解在他一生中并无多大变化,其哲学史构图所确立的信念直到晚年都无本质性修正,那就是“伟大源头处的伟大”。来到他魂牵梦绕的精神故土,面对众神遁去的古希腊废墟,“源头”处的海氏感受着古希腊的命运,愈发坚定了他要以此来批判对抗沉沦世界的信念。“早先的”艺术成为他心目中开启未来的力量。这一信念深深蕴涵在他的艺术之思中。正是在对“存在之天命”的企盼中,艺术之思成为他筹划存在之思的一个亮点,这个亮点因其存在之思而染有了“命运”的色彩。
意义是科学无能为力而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在或此或彼的视角的切入中提示着终极性的人文关切。“历来的‘形而上学’对诸如‘始基’、‘实体’、 ‘本体’等范畴以认知方式的悬设都是带着价值祈向的;悬设或不免出于错觉,但涵贯在这错觉中的却是真切得多的对人文运会或人生意义的究底性寻问。从认知处看,传统形而上学留给人类的业绩似乎只是‘错觉’的相续;倘从价值维度上去领略,却体会得出这‘错觉’中所涵纳的一定时代和民族对‘命运’的判别或‘境界’的趣求的消息。”(黄克剑,第135页)海氏与之亲近的无疑是“命运”的话题,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对外向度存在力量运作的企望。这使他把矛头指向古希腊的思之源头——原初存在经验的鲜活在场,希望借助存在的力量把沉沦于世的人们拯救出来。正是在人文价值衰微之际,海德格尔以自己对真理形而上的守护来拒斥科学技术的僭越。但就其别有异彩的形而上学而言,他属意的不是对“至善”内向度价值的祈向,而是对外在力量——外向度“权力”的渴望(否则他就不会行走在通向叙拉古的路上了)。海德格尔“回返”始源存在经验,在“存在之道作”中有着契合“存在之天命”出场的时机的隐衷,更有对笼罩在早期希腊思想家头上“命运”的应合。就其思路而言,他不仅让早期思想家的思复生,更试图与这些思想家对话,让那些仍未表达出来、还未到来的东西得以涌现。他在倾听时,力求在“命运”突然到来中使西方思想开端处被遮蔽的东西显现。
诚然,“命运”的价值指向的是人文思考的有待的外向度,对“命运”的探问注定不可能有一最终确定的具体所指,但却可开出一片属于自己哲思的天空。海氏向古希腊源头处存在经验的“回返”就有着对古希腊“命运”的属意,他所钟情的赫拉克利特曾谓“一切都遵照命运而来,命运就是必然性”,“命运的本质就是那贯穿宇宙实体的‘逻各斯’”,这些说法充满了强烈的命运感。当了无生机的大地处于“之间”而突发出事件时,大地已是涌现的世界化的大地,即涌现入世界的敞开中。这表现为世界与大地的争执,于此争执的“之间”就产生着裂隙,而艺术就成全了作为争执的裂隙,艺术就是“大地之歌”。这“歌声”是一种本真的命运性的“痛苦”,这本真的“痛苦”又是一种真正的快乐。里尔克等贫困时代的诗人就曾道说过这种快乐,由此快乐就生成了诗人的本质。诗人因此“痛苦”而感受到深刻的愉悦,进而歌唱这种愉悦,这就是艺术何以可能的内核和根基。但此内涵是现代艺术无法涵盖的,更与现代艺术激发的感官快感无涉。它存在于始源的或“伟大的”艺术中。如显现了这种英雄主义“痛苦”的古希腊雕塑就为他所钟情,并被他称作“伟大的”艺术。他认为本真的诗既非柏拉图所说对“理念”的模仿和神灵附体,也非文艺学所说的“表现”或“象征”。它是一种命名或奠基——真理的创建,在命名中使其以真理形态显现出来。但诗人对神圣的命名同现代技术“座架”的肆虐妄为判然有别;它呼唤神圣,并不施以任何强制或压迫。只是,海德格尔的艺术之思对艺术本性的道说关联着“存在之天命”,这在内在性上吻合于他的存在之思,因此,他的艺术之思同样是行走在“命运”与“境界”“之间”,此“之间”作为一种裂隙,乃是居有“命运”,和“境界”的同一而凸显差异。只是作为一种价值祈向,它诉求的重心落在了外向度的“天命”上。
二、本真艺术何为?
海氏对艺术本源的追问不是回到哲学的开端,而是“返回”到为“存在之天命”笼罩下的思之源头。
在他看来,那早先的思、诗对我们当下而言仍是鲜活在场的。他的这一“返回”就使艺术何以可能这一追问获得了某种命运感;但在海氏又带向前的艺术之思的筹划中,始终有着超越现代体验美学与所谓本体论美学的形上诉求,有着明显的现实针对性。大陆唯心主义美学和体验美学都把艺术视为对象而置于现成的桎梏中,就连新康德主义美学因失去康德哲学的原初视野也把艺术作品看作一个被主体所附加上意义的物,认为艺术作品中物性起着基础作用,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一个虚幻的审美王国。正是针对这种基于物性的艺术形而上学美学观,海氏着手追问物的物性。他通过对哲学史上物的观念及物之物性的分析表明,质料与形式的区分之于艺术作品并无充足根据,它实现其规定性力量的存在者领域是作为人工制品的器具,这即是说质料与形式不是物之物性的原初规定性。但人们钟情于器具的存在方式和器具特别的中间地位,暗示器具是通过“生产”而进入存在的,这一点与艺术“带上前来”的揭蔽方式有着相似性。器具是通过人制作的产品,其本性在于它的有用性(制作-使用-上手)。在它与人的现实遭遇中,人对它想得越少,对它的意识越模糊,越是把它置于非对象的位置,它的存在就越真实自在。在此,海氏通过对梵·高的油画《农鞋》的读解揭示了这一特性:正是在鞋的有用性消逝隐去归于“无”时,敞开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农妇的世界:含辛茹苦,又痛又爱,饱含了血泪又浸透了幸福,充满了凄凉惆怅又交织着战胜苦难赢得收获的人生。这人生扎根于大地,又在农妇的世界得到持续和保存。梵·高的油画表明:不是有用性而是使有用性凸显的充实,才是器具本真的存在方式。这种充实被称之为可靠性;凭借可靠性,这器具把农妇置入大地无声的召唤中,农妇才把握了她的世界。事实上,只有在可靠性中,我们才发现器具的本真存在。不是当下实存的农鞋而是走进这幅作品,我们才突然进入另一个全然不同于我们惯常的存在。
与通常认为艺术品的特征在于它的物性和对象性的见解相反,海氏指出艺术品恰在于它的非对象性,它仅仅立足于自身中。艺术作品以自己的方式开启存在者存在。这种开启即揭蔽,亦即存在者真理是在作品中发生的。作品存在就是“建立世界”和“展示大地”,为此他通过把一座古希腊神殿作为他作品生成阐释的场域,来说明艺术真理的发生:
它单朴地置身于巨岩满布的岩谷中。这个建筑作品包含着神的形象,并在这种隐蔽状态中,通过敞开的圆柱式门厅让神的形象进入神圣的领域。贯通这座神庙,神在神庙中在场。神的这种现身在场是在自身中对一个神圣领域的扩展和勾勒。 (海德格尔,1994年,第262页)
在此,庙宇及神圣之域没有消逝在不确定性中。神殿敞开和建立一个世界,世界的建立不是当下现实中的某种筑造,不是一种纯然的设置,此建立乃是奉献和赞美意义上的树立。在建立作品时神圣作为神圣开启出来,神被唤入现身在场的敞开中;同时作品就在自身自立中开启出一个世界,并且在运作中永远守护这个世界。世界决不是立身我们面前让我们细细端详的对象,毋宁说是此在之此,只要诞生与死亡、祝福与亵渎不断地使我们进入存在,世界就始终是非对象性的有“命运”性的东西,而我们人就始终归属于它,此-在之历史的本质性决断才能发生。据此神殿才能从人类那里获得人类命运的形态,才是生与死、祸与福、胜利与屈辱、持久与衰竭的聚集,并因此生成为这个历史性民族的世界,而有此历史性使命的民族也才有世界。在此,大地与纯然物质观念和地质学、天文学观念无涉:“大地是一切涌现者的返身隐匿之所,并且是作为这样一种涌现把一切涌现者返身隐匿起来。在涌现者中,大地现身而为庇护者。”(同上,第263页)作品在开启世界时,同时把世界又置回大地的生-产中。大地不但是海氏艺术之思关乎时代的切己经验,有着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地缘,而且大地连同对大地的信仰还深深扎根在他的精神中,成为他生命中的一个支点,负载着他的力量和意义的这个观念在其运思中不断出现,成为其思想中的一个基本词汇。他的思始终保持着对大地的忠诚,从而与大地涌现的力量一体化,这力量成为他拯救精神萎顿、沉沦于世的无根的现代人的源泉。
因而,在其艺术之思看来,唯有艺术作品才使大地成为大地。正是神殿唤起了石块的重力,图画使色彩变得鲜艳,诗歌使词语成为道说。乍看,大地似乎是作品的质料,其实不然。农妇的世界是她又苦又甜的人生,她的大地是什么?是她脚下踏着的土地,但这已不再是天然之地,而是浸透了她的血泪、支撑了她人生心灵的土地。神殿的世界是生死、祝福、胜利和屈辱的聚集,它的大地是什么?是岩石又不再是岩石,而是那凝聚在岩石中血迹斑斑又光荣累累的民族历史。大地是作品自身回归涌现的出场,立于大地之上并在大地中,历史性的人类建立了他们在世界中的栖居。在世界的敞开中,大地得以涌现而在场。在作品把自身置回大地时,大地也被同时展示出来。这毋宁是始源“自然”合乎机缘的运作,在“自然”中大地不断退隐于作品的突然出现中,作品生-产这样恢复自我本身的大地,并使物在“自然”中契合其涌现的时机。在此意味上,海氏认同丢勒的话: “艺术存在于自然中,因此谁能把它从中取出,谁就拥有了艺术”。
依海氏的理解,维持在基本亲缘中的世界与大地在各自保持自身同时,又相依为命,并处于一种内涵饱满昂扬的争执中。唯此本质性争执才进入一种历史性当下生成的缘构境遇中,争执者双方相互进入其本质确立中而取得一种“命运”形态,一方力图超出自身包含另一方,争执就愈发激烈而愈凸显争执本身。由于作品建立一个世界并展示大地,故作品就是这种争执的诱因。但在这诱因中涌动着的却是源头处的“逻各斯”,“逻各斯”使争执双方的差异凸显并在场,但这个主宰“自然”的“逻各斯”吐露的却是“早先的”命运,因而,海氏谈艺术不是从漂浮半空的美学或艺术学切入,而是在坚实的地基上即真理生成的去蔽处切近的,故此艺术在其存在之思中就承担着真理生成并置入作品的职责,维护着真理澄明于几微中的玄机。所以,“世界-大地”的真理生成说,不仅使其艺术之思脱出形而上学及早期基础存在论,还把对文明异化及现代性的批判远远地推到了事情本身的根底处,而不仅止于理性的辩证上。真理发生于世界与大地的争执,争执的永不停息就揭示出更大的生存空隙,存在之光就从裂隙透射出来。这种裂隙乃是平板意识的断裂,于是进入作品就使自行遮蔽的存在被照亮了,但断裂仅是瞬间,故敞开就不是一劳永逸的一次性事件,真理的本质被否定支配,才使瞬间过后又落入常人意识的沉沦状态又被否定打破。从而争执就使作品处于时间涌现的生成中,真理既不能一次性完成这种无蔽,因而世界的敞开就不能穿透大地,而大地也就不能把世界完全遮蔽入庇护中。于此可见,在艺术为新时代端倪赋形的揭蔽中如何寓托了海氏心仪的“天命”意识。
三、艺术筹划的意义及启示
对古希腊思想来说,知的本质在于存在者之揭蔽。它承担和引导存在者走出遮蔽状态,被古希腊人经验的知就是存在者之生产,即把什么带出场,从来不是指制作活动。进而言之,“所谓知就是:能立于真理中,真理是在者的坦露,因此,知就是能立于在者的坦露中,坚持在者的坦露。”(海德格尔,1996年,第22页)海氏把艺术追溯到源头处古希腊的“知”,意在强调艺术是“存在之道作”的一种方式,而不是纯粹主体所为。艺术创作是一种带上前来,它的本质是源头处的“知”而非主体的制造;作为一种“知”,它关涉始源真理的敞开,又和“存在之天命”的君临关联。所以,海氏艺术之思是在源头处存在境域中展开的。他认为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是真理发生的一种根本性方式,它显现为真理进入作品是以存在者生产的方式来完成的。艺术作为这样一种生产,在生产过程中被制作的东西首先照亮它出现其中敞开领域的敞开性。作为这种带上前来,艺术创作就是在存在无蔽领域内的一种接收和获取。
但作品存在并不是自动实现的,它要被置于存在情境中来理解,这种“让作品成为作品”的理解就是作品之保藏,唯有这种保藏才是对艺术本性的葆真,在此中作品的被创作存在才成为现实。
在此,海氏同样把作品的保藏也追溯到存在的源头——真理的敞开中,唯保藏把作品重新置于生成性争执的无蔽中。他认为作品之保藏不是主体的审美体验或鉴赏行为,而是意味着:置身作品发生的存在者的敞开性中,即“存在之道作”把某物带出来的“知”中。一旦能“知”存在者,也就能“知”他在存在者中的意愿。在他看来,保持着意愿的知和保持着知的意愿,使生存着的人类进入存在无蔽状态时与存在的本真揭蔽相关涉。这种“知”作为意愿在作品真理中找到了自己的家园,可它并没有剥夺作品的自立性,也没有把作品拽入主体体验的领域,更谈不上把作品贬为体验激发器的角色,所以,他认为作为生-产的“知”和保藏的“知”关乎源头处的存在经验,是在真理澄明之境中显现的。
艺术作品的保藏是存在论历史地生成的,所以才能说作品创造了升华的大众,艺术照亮了沉沦状态中迷途知返的“常人”,使他们在存在之光引导下从“洞穴”中来到阳光下,期许能够为存在力量所击中,使其在“回返”存在源头而一跃为新时代端倪的开启准备好助跑的力量。如若艺术是作品的本源,则意味着艺术使作品本质上共属一体的创作者和保藏者都源出于作品本质,艺术本质先行就规定为真理之自行设置入作品。“艺术作品的本源,同时也就是创作者和保藏者的本源,也就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性此在的本源,乃是艺术。” (海德格尔,1994年,第298页)每当艺术发生,亦即有一个开端存在之际,就有一种冲力进入历史中,历史开始或者重又开始,因此艺术的每一次发生或揭蔽都关涉历史的可能,都与始源的“早先”相关联。美作为真理的闪光就不惟显现在狭义的艺术中,而是更多展现为现实当下的躬身践履,但它作为真理争执的一种形态也惟有在作品的作品存在——真理本源的存在方式中才能得到最充分洞察。因此,海氏如此不遗余力地思考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就不仅在于反驳、批判美学考察艺术的方式和形而上学的主体妄为,而是让艺术作一种审美筹划,从根本上使人类思维方式发生转向,以更新人类的内在生活状况;同时,更为现代人在技术时代何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以及为新时代的开启,为此-在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奠基。
对于海氏的艺术筹划,人们或许想到黑格尔的艺术分析。
黑格尔认为艺术是绝对精神借助直观和形象的一种展现,就其终究离不开感性手段而言,它还不是绝对精神自作把握的最佳形态。艺术在黑格尔那里只是绝对精神自我显现的一个环节式阶段,它终究是要“消亡”和被扬弃的,“就它的最高的职能来说,艺术对于我们现代人已是过去的事了。因此,它也已丧失了真正的真实和生命,已不能维持它从前在现实中的必需和崇高地位,毋宁说,它已转移到我们的观念世界里去了”。(黑格尔,第15页)与此相似,海氏也认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体验美学窒息了艺术,致使现代艺术渐趋离开人类而走向终结,只不过“这种终结发生得如此缓慢,以至于它需要经历数个世纪之久”(海德格尔,1994年,第300页)。其实,两种说法貌似相像,实则差异很大。但无论差异多大,他们在此问题上还保持着一种连续性,就“艺术终结”而言,海氏没有对此作简单裁决。究其底蕴,他在一种更深刻、内在的层面接续并推进了黑格尔的艺术观点。他问道:“艺术仍然是对我们的历史性此在来说决定性的真理的一种基本的和必然的发生方式吗?但如果艺术不再是这种方式了,那么问题是:何以会这样呢?”(同上,第301页)他认为问题的实质是黑格尔的艺术观奠基于自古希腊哲学开端以来的存在者真理领域,随着作为根据的最高存在者的变化,艺术就不再是此最高存在者的绝对需要,也就不再承担它所赋予的最高使命。而本真的艺术乃是有“命运”的,它是基于存在敞开领域的,只是现代艺术为技术“座架”所裹挟而鲜有“命运”,致使其日益堕落而至终结。对黑格尔来说,艺术作为历史上存在者真理的一次性发生就成了“曾在的东西”。而海氏把艺术置入存在真理的无蔽领域,伟大艺术作为历史性真理的一次奠基,它的发生不仅是历史的曾在的,而且还能时时回到“存在之道作”的运作中,而不执著于某一最高存在者。它为“存在之天命”所眷顾,因而,它向源头的回返也是指向未来,甚至是从未来走来,如荷尔德林的诗等。因此,海氏小觑“座架”中的现代艺术,而属意于“早先的”伟大艺术;在黑格尔意义上过去了的艺术,被海氏重新赋予了神圣使命而站立于存在敞开的真理中,但这不是寄望于黑格尔之后出现的诸多艺术形式和流派。海氏在黑格尔美学之后,试图重新把艺术与真理、时代及其历史使命关联起来,并使艺术承荷“存在之天命”君临的重负。在他看来,某些现代艺术在存在者真理意义上的萎缩和沉沦,并不妨碍本真艺术能够重新站立于存在真理的敞开中,并在“面对”中能够迎接诸神的风暴而为历史性此在奠基。
海氏认为,当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时,存在之光便显现出来。这种显现作为在作品中真理的存在方式就是美。美属于真理的自行发生。美之所以依据于形式,无非是因为形式一度从作为存在者存在状态那里获得了照亮,使美作为一种真理形态借助形式显现出来。相对于非本源地位的形式,至关重要的是存在澄明在作品中的显现,因澄明作品才处于林中空地中,才为存在之光所笼罩,这缕朗照之光即是真理的力量,是美之光。美是真理作为无蔽而显现的一种方式,是艺术光源之所在。
海氏的真理观和他对美的思考相互契合,成为人生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价值向度。因而,他把艺术提升到存在层面,并针对当下现代人沉沦状态下“境界”的失落而作的筹划,就不仅与人能够绽出地去生存,而且与人凭此进入存在澄明之境而诗意地栖居关联起来。被其从美学中解放出来的艺术,不再是人的审美对象,毋宁说就是此-在本真的生存维度。但在此须指出的是,因美和真理不是由人之内心开掘,而是源自“存在之道作”,人作为此-在固然是“道作”运作的重要维度之一,但它毕竟外在于人,因此,在此作为形而上价值的真理和美乃是一种外在于人的力量显现,不是由人的心灵生发的对“至善”价值的祈向,因而它们带有一种外在规定性,与存在的力量尤其与“存在之天命”关涉甚密。所以在海氏视野中,艺术作为真理发生方式之一,不是人之主体所为,人充其量仅是其生成中的重要一维。但他赋予艺术以最积极真诚的意义和特殊使命,艺术、真理和美奇妙地同一了,以此反拨现代美学之偏,就从根本上撼动了它早已危机四伏的基础。他在艺术之思的途中也把美学何以可能的根奠基于存在境域中,不仅与艺术生-产关联起来,还与人如何能够绽出以及真理、美的生成关涉起来,从而成为他存在之思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此之际,美学才会获得自己的根。
诚然,其艺术之思产生的影响是当下美学重构不可绕过的,但居于存在之思境域中的艺术之思的偏颇也昭然若揭。这自然关联其存在之思本身的偏颇。
其实,自人生内向度对“境界”祈向的开启成为主导的两千多年来,“命运”问题就不再像早期思想家那样成为哲学家所关注的中心,而是在“境界”笼罩下退居幕后,但“命运”之神从没有离开过人世间。它不仅在罗马时出现过,在莎士比亚和歌德那里出现过;尼采、斯宾格勒都是命运感极强的思想家,海氏更是少有的几个为“命运”问题萦绕的伟大思想家之一。但此刻崛起的“命运”已不再是古希腊“命运”之魂的附体,其间毕竟经过“境界”的洗礼及罗马公民权利意识的普及和个我意识的自觉。在诸神不在、“上帝死了”的20世纪,海氏以“存在之天命”的形式回应它,以提醒处于技术时代那些凭强力意志无所不胜的现代人不可妄为。他以批判现代性的反现代姿态傲立于20世纪思想家之列,乃是因这“现代”削弱了人的形上维度。这里虽凸显了差异,但海氏毕竟浸淫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和胡塞尔等大师的传统中,他是鉴于哲学“境界”被追逐于功利的形而上学(科学)所遮蔽而衰落,才开启“存在”来激活形而上学的;他敬畏“神秘”与“不幸”,以其思之强力和灵动来建构其逐本溯源的形而上诉求,因而,海氏的存在之思相对于哲学史(形而上学史)无论如何“反动”、 “脱出”,仍是在既定现实的地基上说话,而非凌空蹈虚之论。他积极致力于拯救或解放康德、黑格尔、胡塞尔思想中的非形而上学因素,在与他们对话中把被遗忘的存在带出场,同时使其存在之思脱出传统形而上学的窠臼。所以,同样应对文明危机和“境界”失落,海氏没成为斯宾格勒那样硬性的“命运论”者,而是在“命运”与“境界”的错落中走向历史深处。他虽不能洞悉老子“道”的真谛,但他以“道路”译之也颇值得玩味。其实,他以“另类”方式接通了人类思想史中的人文传统,特别是承续了神秘主义大师艾克哈特的传统。确切地说,他是行走在“命运”与“境界”“之间”的思想家。但他在踯躅“之间”的途中,因未能踏入“境界”的界域,反倒因其思之强力在“诸神之夜”再度加深了人们对精神内向度的价值维度的遗忘与遮蔽,可以说他是蔽于存在而不“知”人。因不“知”人而致对人之理性精神的蔑视,故在其人生定向中就缺乏一种精神的高贵性,恰恰这种高贵性本可保护他不在专制者身上实现对“命运”的信仰。因“境界”这一最为时代属意的内向度的价值祈向未进入他的视野,而使其哲学史构图出现偏颇。此偏颇也累及到他的艺术之思,使他所寄望的艺术缺失鲜明的价值指向,尤其在技术关联时代艺术本应成为克服现代技术僭越的一个维度,但因形上祈向的偏颇而使艺术沦入价值真空的空场,从而缺失一种引导人祈向“境界”的方向感,而使现实具体的人显得茫然无措,因而也不可能真正安顿人焦躁的灵魂。
艺术尽管在海德格尔那里达到真理的高度,成为“存在之道作”的揭蔽方式之一,但人生内向度的“境界”终究在其视野之外。倘若我们对这一偏颇有所体察,便不难理解海氏何以既赋予艺术以特殊使命和力量,赞颂贫困时代的诗人,却又不屑于人之“至善”的内在价值祈向,致使他对艺术的判断有时会显出不可名状的模棱两可,甚至使他过于注重力量下沉的思,却在一定程度上反倒对艺术力量有所忽视和犹疑。
标签:艺术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海德格尔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大地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古希腊论文; 美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 现象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