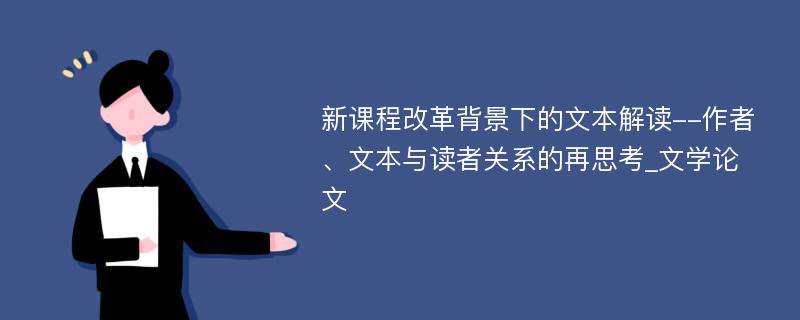
新课改背景下的文本解读——对作者、文本、读者三中心关系的再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本论文,新课改论文,读者论文,关系论文,作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课程知识观的改变。新课程不再把知识技能视为凝固、封闭起来供人掌握和贮存的东西,它合理地承认了知识技能的不确定性,认为知识技能的本质在于人们通过对多元文化的学习与交流来进行交流和反思,并由此构建出新的意义。而现代的课程文本论也否定了文本意义的确定性,而坚持文本意义的动态性和开放性,读者不再依附于文本的指示和作者的意图,而是独立自觉地参与对文本的理解与解释。
语文教学中涉及大量的文学作品的阅读感受和分析阐释,对于语文阅读教学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对文本的把握,因为“从教材到教材文本,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替换,而包含一个理念的质的转变:由传统传递作者、编者的意图的教材变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存在——教材文本。”
因此,作者、文本与读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成为了文本解读的重要主题,如何来认识它们之间的关系,在新课改背景下如何来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呢?
新课程标准在阅读教学中所倡导的取向是感受和理解,提出:“阅读教学是学生、教科书编者、文本之间的多重对话。”“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是发现和建构作品意义的过程。作品的文学价值是由读者在阅读鉴赏过程中得以实现的。”这个命题包含着两层含义:(1)阅读是读者与文本的主体间对话过程;(2)教学是教师与学生以及学生与学生的主体间对话过程。在此理念的指引下,语文阅读教学改革又迅速从作者中心、教材编写者中心转向读者中心。
读者中心主义认为:任何文本都有未定性,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召唤结构,具有很多的空白点,这对于读者来说就是一种不确定性。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调动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积极思维,完成自己个性化的阅读。读者对文本的理解不是追寻文本中隐含的作者意图,而是与读者自身的生存状态相关。
语文教材中选编的文章大多数文质兼美,饱含了作者独特的情感体验,这为学生提供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学生可以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去理解文本、感悟文本,不断扩展自我世界并发现生活的意义。学生与文本之间的对话具有内在的未完成性与自由开放性,这赋予了语文教学未定性论和无限的可能性。学生与文本之间存在双向的互动联系,学生对同一篇课文往往有不同的感受,作品中大量的描写性语言包含了诸多不确定的意义和空白,他们构成作品的召唤结构,召唤学生去想象,去实现作者的创作意图。因此语文课不应该是教师和学生进行冷静分析和解剖的对象,而是应该积极地投入其中,在阅读的动态过程中加深对课文的理解。师生通过在阅读过程中反复思考和探求,从中获得的也许是模糊的、说不明白的感受和体验,却有可能是有用的、至关重要的。对于语文课文主要内容的理解不在于概括得是否很准确、全面,也就是说不在于是否掌握最后结论性的内容,而在于让学生去体验和领会作者的思想感情,从中即使获得复杂、说不清楚的内容,也比让学生记住现成的、唯一的答案更重要。
但是随着新课改的推进,人们在大力提倡读者中心的时候,一方面把教师和学生从封闭、单一的教学形式中解放了出来,但一方面却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变成了主观主义的“读者中心”。承认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多元性并不等于读者可以随意解读文本,把文本看成是绝对自我的东西,任由我们凭个人的人生经验和知识背景去揣测,从作者中心一下子跳到读者中心。当我们失却了思想的高度统一性之后,我们迫切需要自由表达的空间,我们渴望自我生成和建构,于是我们拒绝否定,只要是学生说的,都是对的。在课堂上,有的老师对学生的观点不论是否符合文本意义都一律加以肯定。如笔者听过的一节公开课上,课文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老师问学生读诗后的感受,有学生说出海子的自杀是一种勇敢,是一种追求理想的方式,并表示自己很赞赏海子的这种勇气的时候,教师并没有对他的这种看法进行及时的纠正,反而对他的看法大加赞赏。教师的这种做法一方面固然体现了新课改中“充分尊重学生独特体验”的阅读教学理念,但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知道对于读者中心的理解还是会有误解。
在阅读教学中,对文本的理解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对文本充分、深入的理解,片面强调阅读主体的看法和观点,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言必“建构”、动辄“对话”,但就是无法真正进入文本、理解文本,而这个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在对文本还没有基本把握的情况下,简单片面地对文本进行判断和处理,就有可能造成阅读主体主观化的观点掩盖了文本本身所表达的内容”。
对于教材文本的解读应该正确理解教材文本的地位。“一方面,教材文本是作者、编者表达自己意图的媒体,是在一定程度上寄托着作者主观心理期待的客观化作品;另一方面,教材文本又是读者(教师和学生)理解活动指向的对象,正是通过对文本的解读,读者才得以实现自身历史性与作者历史性之间的超时空交接。让有关过去的真理融入到现时态生活之中,创生出文本的当代意义。”当我们不再把文本当作封闭的、不可更改的事物的时候,我们又因为过于强调读者中心、学生中心,而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文本本身。我们对于文本的解读虽然不必再依附于作者中心,但文本的自我实现必须进入文本解释与当下读者自我解释交流融合的过程和阅读过程。
因此,在语文阅读教学中,应该提倡以文本为中心的解读。要更好地理解以文本为中心,首先让我们再来理解一下文本的开放性。
文本结构是一个开放系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本向其他文本开放。从文本生成来看,任何文本都不是唯一的,单独存在的,而是继承、吸收其他文本的结果。文本作为一种特定的体裁,大多是在相互继承的前提下得到发展的,例如小说就是从神话——传说——传奇——话本——小说发展而来的,后一种体裁是对前一种的继承。不同的体裁之间还互相开放,很多体裁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如诗歌和散文之间有时候就很难划定分界线。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文本向读者的开放,离开了读者,文本就失去了意义,而每一个读者对同一个文本往往又有着不同的理解。从理论上说,读者可以赋予文本以无穷的解构,但在实践中由于读者总是处在一个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中,所以他只能赋予一个文本与他所处历史文化背景相符的结构。罗曼·英加登在《艺术和审美的价值》一文中说:“一部艺术作品需要一个外在于它的动因,这就是一位观赏者。艺术作品是艺术家有目的的活动的产品,作品的具体化不仅是观赏者进行的重建活动,也是作品本身的完成及潜在要素的实现。所以从某种角度来看,作品是艺术家和观赏者的共同产品。”
对于文本与读者关系的理解,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课堂教学这样一个特殊的客观环境。
首先,语文教学中的文本已经不是普遍意义上的文学文本,而是“经过了教科书编者的加工,被包围在‘鉴赏提示’‘课文注释’和‘课后练习’之间,在不知不觉中转变成了‘教学材料’,成为了一定知识体系的形象化示例,成为一定教学内容的载体——认知的、情感的甚至道德训诫的内容”。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就不能像处理一般文学作品那样处理出现在语文教材中的文本,它已经由纯文学作品变成了教学用文本了。
其次,语文课堂教学中的读者,也不是普通的读者,而是教育学意义上的被塑造者,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学生必须以一定的教学目标为旨归,学生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只是教学目标的实现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学生的鉴赏过程受制于教学目标的实现过程。所以在实际的阅读教学过程中,脱离文本,脱离教学目标的理想状态的、完全独立自由的鉴赏者是不存在的。
既然学生的理解不可能离开文本单独存在,那么学生与作品之间的“主体间性”的对话也是不自由的,不可能充分展开的。也就是说在语文教学中文本意义的敞开是相对的。提倡以文本为中心的解读,即不盲目追寻作者、编者的意图,也不完全以学生自我的理解为中心,而是以文本的意义为根基来解读教材文本。对阅读教学来说,仅仅有学生与文本的对话是不够的,当学生产生看法和疑问的时候,解决学生的疑问也成为阅读教学的重要任务,这个时候,教师可以通过对作品的教育性解读,有选择地打开学生与作品对话的一条通道,力求在解决学生问题的过程中实现既定教学目标。同时,学生与学生之间通过合作学习、互相交流而产生相互作用。这样在阅读教学中,就以文本为中心,教师、同伴协同一致,对学习者进行引导和纠偏,使主体间的对话成为学生、教师、文本之间的多重对话。
总之,在语文阅读教学过程中,必须处理好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阅读教学在强调读者中心的时候,更应该注意到文本才是一切阅读意义得以存在的中心。在语文教学中必须重视文本的意义,通过文本把读者与作者联系起来,并在教学中通过教师和学生与文本的多重对话来真正走进文本、理解文本,从而使文本和读者的意义都得到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