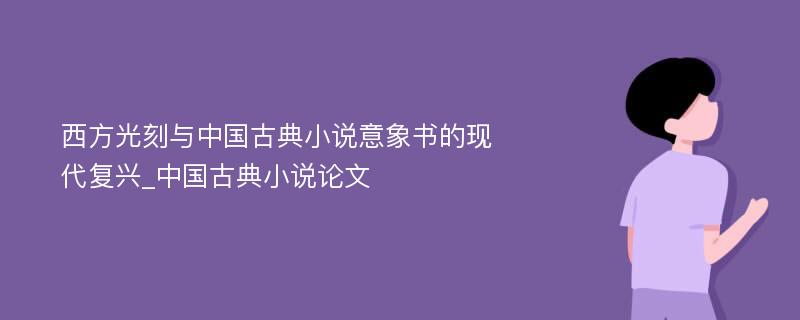
西洋照相石印术与中国古典小说图像本的近代复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洋论文,古典小说论文,中国论文,近代论文,图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3)06-0127-07
中国古典小说图像本始见于元代,存世有《全相三国志平话》、《全相武王伐纣平话》等元刊五种。晚明时期,小说戏曲方兴未艾,木刻版画亦进入“登峰造极,光芒万丈”的年代,“差不多无书不插图,无图不精工”,[1]合此两端,小说图像本遂臻于鼎盛,涌现出诸如容与堂本《忠义水浒传》、《新刻批评绣像金瓶梅》、雄飞馆本《英雄谱》等大量精美版本,并逐步形成建阳、金陵、徽州及苏州等风格不同的版画流派。至清代前期,小说图像本挟明末之势,仍有不俗表现。迨嘉庆以降,因内忧外患,国力日衰,木刻版画渐趋式微,小说图像本亦随之零落,大多绘摹拙劣,刀刻板滞,其末流更不堪寓目。①适值此时,西洋照相石印术(photo-lithography)开始传入中土,其神奇的照图功能,填补了图像出版的技术空缺,小说图像本迅速迎来了其发展史上的又一个繁盛期。
一、照相石印术的传入与石印图像本小说的出版
石印术(lithography)由德国人赛尼斐德(Aloys Senefelder)发明于19世纪初,清道光五年(1825)以后,始陆续传入中国之澳门、广州及上海地区。最早使用该技术进行中文印刷者,乃西方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麦都思(W.H.Medhurst)及合信(Benjamin Hobson)等人,[2]不过,由于技术及设备诸方面的原因,早期中文石印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极为有限。
真正将石印术推广到中国并产生社会影响的,是成立于光绪四年(1878)的上海《申报》馆下属机构——点石斋书局。考察点石斋书局的成功原因,一方面盖依托于《申报》馆的社会声誉,另一方面则在于引进了经过技术升级的石印新法,即“照相石印术”。石印术的基本原理,是利用油水相斥现象,先以脂肪性油墨将图文绘制于专用石版上,然后以水润湿石版表面,使空白区域(即没有图文区域)的石版细孔吸蓄水分,构成图文区域亲墨抗水,空白区域亲水抗墨;再经平压平或圆压平方法,将石版上的图文墨迹,刷印到纸张上。其中石版绘制环节最为关键,一般有两种方法,一是直接手工绘制,二是通过照相转写,即先以照相湿版摄制阴图,落样于特制的化学胶纸,再经专门设备转写于石版。②由于借用了照相的技术优势,照相石印术显示了超强的缩印与照图功能,这两项功能决定了近代中文石印业的主体业务:缩印功能主要应用于翻印大部古籍丛书,而照图功能则广泛使用于图像印刷。
光绪五年(1879)5月12日,点石斋书局在《申报》登载广告,向读者推出其精心策划的《鸿雪因缘图记》石印本。《鸿雪因缘图记》乃清完颜麟庆所撰游记集,有道光扬州精刻本,共三集240则,每集80则,每则文字配以插图一幅,每幅插图印以对开两页,精美绝伦,久为藏家所珍,然售价高达数十两银子,实非普通人所能承受。点石斋将此书按原本缩小照印,定价仅一元,价格优势极为明显。其出版广告云:
本馆自创设点石斋仿泰西照相石印之法以来,特不惜重资,购求原本,勒诸贞珉;又嫌原本之过大,而翻阅之累赘也,缩存四分之一,细于牛毛,密于茧丝,而深浅远近,仍复一一分明,与元本后先辉映。若此细图,即付手民雕刻,恐离娄复生,亦当望而却步矣。昔人以诗书画为三绝,今《鸿雪因缘图记》,图则擅写生之妙手,记则具赋物之清才,而点石斋之印工,又为开天辟地以来夺造化、转鸿钧之奇术,称为三绝,允当无愧。
石印本《鸿雪因缘图记》初版五千部,“不一年而售罄”,至光绪六年(1880)7月,点石斋予以重印,[3]获利当甚为可观。或受此鼓舞,《申报》馆开始关注小说图像本的出版业务。
目前所知第一部石印图像本小说,是光绪七年(1881)《申报》馆出版的《西湖拾遗》,其正文用铅字排印,唯书首“金牛献瑞”、“玉镜呈祥”、“西湖全图”及“西湖十景图”等图像,乃“用连史纸由石印照相法印出,弁诸简首,格外耀目”。[4]此书拉开了小说石印图像本的出版序幕:光绪八年(1882),点石斋石印《三国志全图演义》;光绪十年(1884),同文书局石印《增评补图石头记》;光绪十一年(1885),同文书局石印《增像三国全图演义》;光绪十二年(1886),同文书局石印《评注图像水浒传》、《详注聊斋志异图咏》;光绪十四年(1888),点石斋石印《绘图东周列国志》及《绘图镜花缘》,蜚英馆石印《绘图评点儿女英雄传》,鸿文书局石印《增像全图三国演义》及《新说西游记图像》,大同书局石印《图绘五才子奇书》,鸿宝斋书局石印《增补齐省堂儒林外史》;光绪十五年(1889),蜚英馆石印《详注聊斋志异图咏》,等等。
二、石印精本小说图像的新变化
检阅上述诸书,多属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然审其底本,皆为清代后期通行本,譬如点石斋本《三国志全图演义》,以清咸丰三年(1853)常熟顾氏小石山房刻毛评本为底本;同文书局本《评注图像水浒传》,以清王望如评注七十回本为底本;同文书局本《增评补图石头记》,以清王希廉、张新之、姚燮三家评本为底本。此种现象表明,石印本小说的出版重心,并非在于文字版本的珍稀性,这与之前铅印本小说的出版迥然有别。
兹以点石斋书局为例,它隶属于《申报》馆,该馆早在同治十三年(1874)就开始采用铅印术出版中国古典小说,截止光绪八年(1882),已出版《快心编》、《西游补》、《何典》等17种小说,然绝大部分为二三流的非名著作品,各书出版广告亦反复强调“向无刊本”、[5]“特向无刊板,故不传于世”、[6]“惜尚无刊本,绝少流传”[7]云云,显然,小说文本的稀见性乃其最重要的出版追求,这符合早期《申报》馆“搜求新奇艳异、幽僻瑰玮之书”[8]的出版宗旨。然而,等到点石斋书局出版石印小说时,该馆却完全改变了策略,将之前不屑一顾的名著通行本列为出版对象,充分利用照相石印术的照图功能,以大量精美的图像而非流传稀少的文本,作为吸引读者的最大亮点,其出版广告也突出了对小说图像的宣传:
《三国演义》一书,久已脍炙人口。惟坊间通行本字迹模糊,纸张粗劣,绣像只有四十页,阅者病之。本斋现出巨资购得善本,复请工书者照誊,校雠数过,然后用石印照相法印出。故是书格外清晰,一无讹字。为图凡二百有四十,分列于每回之首,其原图四十,仍列卷端,工致绝伦,不特为阅者消闲,兼可为画家取法。[9]
该时期由点石斋、同文书局、蜚英馆等书局出版的石印小说图像本,开本阔大,纸墨优良,图绘精美,确实代表了晚清石印小说的最高水平,其中大多数已被阿英《清末石印精图小说戏曲目》收录。与清代中后期的木刻本相比,上述石印精本小说的图像,呈现出几个引人注目的新变化。
其一,图像数量大幅增加。
由于采用了照相转写、机器印刷等技术,石印图像的技术难度及商业成本均大为降低,故单部小说的图像数量有了大幅增加,少则一二百幅,多则三四百幅,蔚为大观。譬如点石斋本《三国志全图演义》有280幅,同文书局本《增像三国全图演义》有384幅,点石斋本《绘图东周列国志》有264幅,同文书局本《评注图像水浒传》有160幅,同文书局本《详注聊斋志异图咏》多达445幅。此与清代中后期木刻本小说通常只有十数幅或数十幅图像(如咸丰三年顾氏小石山房刻本《三国志演义》仅有40幅人物绣像),形成强烈反差。同文书局本《详注聊斋志异图咏》更值得关注。蒲松龄《聊斋志异》自乾隆三十一年(1766)赵起杲青柯亭刻本问世之后,坊肆翻刻不断,有节选本,有满文译本,有朱墨套印本,林林总总,但未曾出版过图像本。直至光绪十二年(1886),同文书局“荟萃近时名手”,“每篇事迹,各画一图,分订每卷之前,其有二则三则者,亦并图之”,每图“题七绝一首,以当款字,风华简朴,各肖题情;并以篇名之字,篆为各式小印,钤之图中,尤为新隽可喜”。[10]此书石印之后,“阅者无不惬心”,[11]风靡一时,翻印不绝,充分展示了石印图像本小说的独特魅力。
其二,情节插图重新成为小说图像之主体。
中国古典小说文本所附图像,包括情节插图及人物绣像两类,从元刊全相平话,到晚明时期的木刻本小说,其图像大多为情节插图,其构图复杂,布景富丽,或将士战马,旌旗猎猎;或山川草木,亭台楼阁;或绣榻帐幔,花窗明几,不仅给人以美感,也包含丰富的社会文化信息。清乾隆以降,情节插图逐渐从小说文本中淡出,代之而起的则是模式化的人物绣像,这固然与清康乾时期《凌烟阁功臣图》、《无双谱》、《晚笑堂画传》及《百美新咏》等人物画谱的流行有关,但也是木刻版画艺术逐渐衰微,导致无力绘刻场景繁复之图的结果。然而令人欣喜的是,上文提及的石印精本小说,重又恢复了情节插图的绘制,而且情节插图数量远远超过人物绣像,成为小说图像的主体。譬如点石斋本《三国志全图演义》有图像280幅,其中情节插图240幅,人物绣像40幅;点石斋本《绘图东周列国志》有图像264幅,其中情节插图216幅,人物绣像48幅;而同文书局本《详注聊斋志异图咏》所绘445幅图像,均为情节插图,且在构图之繁复、绘摹之精细程度上,即便与晚明时期的小说图像本相比亦毫不逊色。
其三,图像绘制水平显著提高。
从技术层面来看,木刻本小说图像的优劣,取决于画师画样及刻工雕刻两个环节;而石印本小说图像,则因借助照相技术,省却雕刻一环,故其优劣基本上全由画师决定。清代后期的上海,恰恰凭借其特殊的政治文化及地理优势,迅速成为大江南北、尤其是江浙地区文人商贾的聚居地,其中就包括一批风格各异的书画家。清王韬《瀛壖杂志》(1874)卷五载:“沪上近当南北要冲,为人文渊薮。书画名家,多星聚于此间。向或下榻西园,兵燹后僦居城外,并皆渲染丹青,刻画金石,以争长于三绝,求者得其片纸尺幅以为荣。”[12]这些寄寓在上海的书画家们为了生存,需要寻找各种谋生手段,与书局合作、为古典小说绘制图像即为其中一项。譬如海上画派名家杨伯润,参与绘制了同文书局本《详注聊斋志异图咏》插图;苏州画家吴友如,参与绘制了鸿文书局本《新说西游记图像》插图;南京画家陈作梅,绘制了蜚英馆本《绘图评点儿女英雄传》插图;海上画派陆鹏,绘制了萃珍书屋本《今古奇观图咏》(此书文字铅印,图像石印)插图;四川寓沪画家杨文楼,绘制了文宜书局本《绘图富翁醒世传》插图,如此等等,不可胜举。[13]由于职业画家的参与,石印小说图像的艺术水平,较清代中后期木刻本有了显著提高。
三、石印精本小说图像分析
关于清代中后期木刻本小说图像之粗劣,戴不凡《小说见闻录·小说插图》曾云:“清人所刻,人物非歪嘴歪鼻歪眼,即多是线条硬梆梆者”,“清代坊刊小说多小本,前附绣像多不倩人绘制,而往往以‘缩放尺’自金古良之《无双谱》、上官周之《晚笑堂画传》、《芥子园画传四集·百美图》诸书中剽窃翻刻者。此等图谱中之人像与小说本来毫无关系,益以缩尺既不精密,刻工又复了草,往往成为‘奇观’。”[14]反观晚清石印精本小说图像,面貌焕然一新,不仅描绘精细,布局设计也多见匠心,体现出职业画家的专业水平,兹略举数例。
(一)同文书局本《详注聊斋志异图咏》所绘445幅情节插图均属原创,颇费斟酌,据书前“例言”,每图“俱就篇中最扼要处着笔,嬉笑怒骂,确肖神情,小有未洽,无不再三更改,以求至当。故所画无一幅可以移至他篇者”。[15]以卷一《画皮》为例,该篇最具代表性的情节乃王生隔窗窥鬼画皮一段,原文云:
(王生)无何至斋门,门内杜不得入,心疑所作,乃踰垝垣,则室门亦闭,蹑迹而窗窥之,见一狞鬼,面翠色,齿巉巉如锯,铺人皮于榻上,执彩笔而绘之。已而掷笔,举皮如振衣状,披于身,遂化为女子。睹此状大惧,兽伏而出。[16]
此篇插图站在局外观察者视点,绘一儒冠长衫的书生,立于窗前,以手轻拨窗棂,身体微倾,正从窗缝向室内偷窥。而透过房间的另一侧,阅者可以看到室内有个面目狰狞的恶鬼,正执笔作描绘状,桌面所铺人皮上,女子面容已基本画就。整幅插图紧扣小说情节而绘,惟妙惟肖,确实难以“移至他篇”。该幅插图题七言绝句云:“蓦看罗刹瘦西施,只要蛾眉样入时。如此妍皮如此骨,个中色相试参之。”诗借皮骨之叹,寓有深意,恰如《画皮》文本篇尾“异史氏”所曰:“愚哉世人!明明妖也而以为美;迷哉愚人!明明忠也而以为佞”,“天道好还,但愚而迷者不悟耳,可哀也夫”。诗末钤一椭圆形白文小章,所刻正是小说篇名“画皮”两字,谓之“新隽可喜”,[17]洵非溢美。
(二)南京画家陈作梅所绘蜚英馆本《儿女英雄传》插图82幅,每幅皆极为精美,而尤其值得称道者,画家对该小说的京旗色彩理解深入,插图中男女人物的发式服装、居家陈设、生活习惯等项,每多与小说情节所述及史料所载之满族文化相吻合:如男子多头戴瓜皮帽,脑后拖着长长的辫子;女子则手持烟杆,发式梳为旗人妇女典型的“两把头”;③室内多置炕床,上摆炕桌、引枕等物。显然,《儿女英雄传》的插图,不仅是小说情节内容的图像化,提供美术层面的鉴赏功能,而且也是小说文化风格的图像化,具有一定的社会民俗史价值。
(三)四川寓沪画家杨文楼所绘文宜书局本《富翁醒世传》人物绣像14幅,线条流畅,表情丰富。该书主人公“钱士命”,贪婪悭吝,嗜钱如命,其姓名谐音“钱是命”,乃小说作者重点抨击的无耻小人。杨文楼描绘之“钱士命”绣像,双手紧抱一枚巨大的钱币,盖住整个上半身,仅从钱币中间方孔中,露出一副贪婪奸诈面目,诙谐生动,寓意深刻,颇具现代漫画的艺术效果,此与清代人物图谱中僵化呆板的人物绣像,大异其趣。
值得一提的是,石印小说图像本的流行,还刺激了晚清画家据小说情节绘制画册的热情,催生出一批古典小说插图画册,有些幸运地流传至今。譬如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镜花缘图》,光绪十九年(1893)孙继芳绘,设色绢本,折装,十函20册,凡200幅,每幅纵39.6厘米,横33厘米,经对比,其中有半数乃据光绪十四年(1888)点石斋石印本《绘图镜花缘》摹绘而成。[18]又譬如辽宁旅顺博物馆藏有《红楼梦图册》,[19]光绪间河北丰润孙温、孙允谟绘制,设色绢本,24册,凡230幅(残缺第一百零四回至一百零八回的十幅,总数应为240幅),首幅为《石头记大观园全景》,次为每回插图,每幅纵约43.3厘米,横约76.5厘米,就其形制而言,明显受到晚清石印图像本《红楼梦》的影响。再譬如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聊斋图说》,光绪十九年(1893)前后绘成,设色纸本,存46册,凡725幅,情节涉及《聊斋》420篇故事,每幅纵45.7厘米,横34.7厘米,经对比,其蓝本乃光绪十二年(1886)同文书局石印本《详注聊斋志异图咏》。[20]这些开本阔大的小说画册,当年可能是为书局石印出版而绘制的,却由于某种原因未能付梓。从技术角度来看,为保证照相缩印后书籍仍然字画清晰,石印本小说的出版底稿,通常先由抄工抄成尺寸巨大的本子,譬如2009年5月中国书店拍卖了一套清末石印底稿本《绘图今古奇观》,纵47厘米,横30厘米,其开本尺寸正与上述小说画册相近。④
总之,晚清时期的石印精本小说,无论是从图像数量、类别还是艺术质量来看,都清晰地构成了对晚明小说图像本鼎盛风貌的一种复兴,两者的主要区别,只是印制技术——照相石印与木刻版画的差异而已。此处,有一个细节颇耐人寻味:光绪八年(1882)点石斋书局推出石印本《三国志全图演义》,其文字底本为清咸丰三年(1853)常熟顾氏小石山房刻毛评本,而图像底本却取诸晚明,经戴不凡比对,该书240幅情节插图,悉据明末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重绘而成。[21]这或许表明,晚清石印精本小说确立的出版目标,即是重振晚明小说图像本的繁盛与风姿,而从上述石印精本小说来看,此目标盖已基本实现。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自光绪十六年(1890)至二十四年(1898),乃上海地区石印书局开办最为集中,也是石印本小说出版最为鼎盛的时期,之后,石印本小说的出版数量与频率有所降低,但仍保持相当水平,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据日本丸山浩明《中国石印版小说目录》(稿)[22]不完全统计,清末民初出版的石印本小说共有499部(不包括同书异版),仅《红楼梦》一书的石印本就多达25种,其中大部分都附有一定数量的图像。受此激烈商业竞争的消极影响,光绪十六年之后出版的石印图像本小说,其总体质量较前期有明显下降,存在诸如开本窄小、纸墨欠精、图像数量大幅削减、绘印不够精美、盗印之风甚嚣尘上等弊端,导致石印本小说往往给人留下不佳印象。不过,尽管如此,照相石印术终究开创了中国古典小说图像本的中兴局面,也曾极大地促进了小说文本的近代传播,[23]其历史作用仍毋庸置疑。
四、值得重视的五彩石印本小说
由于新技术的应用,晚清石印小说图像本还取得了若干超越晚明的成绩,小说彩图本的印行即其一例。据研究,⑤至迟在元代,中国就已发明彩印术,至元六年(1340)资福寺所刊朱墨两色《金刚经注解》,乃目前所知最早的木刻套色印本。晚明时期,套印术获得长足发展,不仅所套色彩增至四色、五色,而且还出现了更为先进的“饾版”技术,印制出了一批精美的彩色书籍,其中有湖州凌闵两氏的套色印本、江宁吴发祥的《萝轩变古笺谱》以及休宁胡正言的《十竹斋笺谱》等代表作。然而,由于木刻彩印具有工序复杂、技术难度大、商业成本高等特点,其传播和普及程度均受到很大限制,用来印制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小说,就更是寥若晨星。今知中国古典小说的木刻彩图本,仅有清康熙年间出版的《西湖佳话》及《李笠翁评本三国志演义》两种而已。⑥
至晚清时期,一种操作简便、投资低廉的彩印技术——五彩石印术由欧洲传入中国,上海地区先后开设了富文阁、五彩画印有限公司、藻文书局等数十家五彩石印书局,[24]主要承担钱票、月份牌、商标、仿单及舆图之类的彩印业务,其间也曾出版了一批五彩石印本小说。光绪十七年(1891)5月,上海文玉山房委托五彩画印有限公司,“用西法五彩石印”[25]出版《绘图山海经》;6月,再次委托该公司代印《五彩增图东周列国志》,“描写精工,校对仔细”,[26]此乃目前所知时间最早的石印彩图本小说。之后陆续出版有:光绪三十年(1904)文宝书局本《五彩绘图廿四史演义》,光绪三十一年(1905)章福记书局五彩石印本《绘图东周列国志》,光绪三十二年(1906)上海焕文书局本《五彩绘图儿女英雄传正续》、《五彩绘图列国志演义》、《五彩绘图荡寇志》、《五彩绘图西游记》,[27]清末民初简青斋书局五彩石印本《增像全图三国志演义》、天宝书局五彩石印本《增像全图东周列国志》、扫叶山房五彩石印本《绘图彭公案全传》等等。据阿英《清末石印精图小说戏曲目》著录以及检阅寒斋藏本,⑦五彩石印本小说一般每叶(包含正背两幅)图像单色印刷,各叶图像则分别以红、绿、橙等色轮印;随着技术改进,后期也出现同一幅图像内套印多种颜色的情况,譬如扫叶山房五彩石印本《绘图彭公案全传》,其人物绣像服饰印以五色,交相辉映,甚是悦目。五彩石印本小说在当时颇受欢迎,售价也要超过普通墨色石印本。譬如光绪三十年(1904)8月2日及10月13日,文宝五彩石印书局分别在《申报》登载出版广告,前者列有《绘图廿四史演义》六册,价洋六角;后者列有《五彩绘图廿四史演义》,称“逐节绘图,以西法五彩石印,颜色鲜艳,图画精细”,“连图六大本,暂售工料洋九角”。同一部小说,同样是六册,但五彩石印本的售价要比普通墨色石印本贵出一半。五彩石印术实际使用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就被更为先进的彩色胶印技术所取代,因此,晚清时期出版的五彩石印本图书,数量非常有限,而保留至今的五彩石印本小说就更不多见,此类具有小说史及出版史双重价值的版本,值得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五、小结:印刷史层面的思考
最后,不妨回到印刷史层面作结。张秀民《中国印刷史》(增订版)曾提出过一个颇有意思的问题:“石印术1832年传入中国,但到1880年以后才得到普及,为什么在这50年内没有得到推广,这很值得思考。”⑧在我看来,根本原因或在于石印制版方法的改变,正是由于采用了照相制版技术,石印术才能在中文印刷领域充分发挥其独特的优势,尤其是缩印及照图两大优势。换言之,对中国近代文学和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是照相石印术,而非普通石印术。照相石印术在晚清时期的传入,恰好填补了因木刻版画衰落而造成的技术空缺,从而引发种种图像类书刊(包括书画碑帖、画谱、年画以及新兴的新闻画报等类)的出版臻于繁盛,小说图像本亦藉此重新焕发出晚明的光彩。当然,照相石印术的普及,也为盗印翻印提供了技术便利,导致小说出版业陷于良莠并存、鱼龙混杂的复杂环境。或许,完整地看到这两个方面,才能真正认识照相石印术对于中国古典小说近代传播的学术意义。
注释:
①关于小说版画史之论述,可参阅戴不凡:《小说见闻录·小说插图》,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94-298页;周心慧:《中国古小说版画史略》,收入其《中国古代版刻版画史论集》,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年,第33-64页。
②参见范慕韩主编:《中国印刷近代史初稿》第七章第二节“平版印刷工艺”,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95年,第565-567页;成都杨刚:《石版制版术》,石印传习所印行,时间未明,虞虞斋藏本。
③所谓“两把头”,即先将额前至耳后的长发束起,在头顶正中扎起一个“头座”,然后再把头座的长发分成左右两绺,编成小辫,绾成左右两个小发髻,最后把脑后的头发绾成一个燕尾式的长扁髻,压在后脖领上。小说对此种发式有详细的描写。参见李婷:《京旗人家——〈儿女英雄传〉与民俗文化》第四章“旗人的衣食住行”第一节,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0页。
④另据苏兴、苏铁戈、苏壮歌《记味潜斋石印本〈新说西游记图像〉》一文载,民国间大成书局《西游记》石印底稿本,其开本为纵50厘米,横34厘米,亦与《绘图今古奇观》相近。苏文载《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4期。
⑤参见顾廷龙、冀淑英:《套印和彩色印刷的发明与发展》,收入《装订源流和补遗》,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3年,第169-172页;张秀民著,韩琦增订:《中国印刷史》第二章“明代”之“湖州套印”、“南京彩印”等节,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上册第311-320页;马孟晶:《文人雅趣与商业书坊——十竹斋书画谱和笺谱的刊印与胡正言的出版事业》,《新史学》1999年总第10卷第3期。
⑥关于两书的彩印技法,可以参阅郑振铎:《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之九,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157—158页。
⑦寒斋藏本有光绪三十一年章福记书局五彩石印本《绘图东周列国志》、清末民初简青斋书局五彩石印本《增像全图三国志演义》、天宝书局五彩石印本《增像全图东周列国志》。
⑧张秀民著,韩琦增订:《中国印刷史》第一章之“石印”部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下册第443页。此问题实际上由韩琦提出,见韩琦、王扬宗:《石印术的传入与兴衰》,收入《装订源流和补遗》,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3年,第360页。
标签:中国古典小说论文; 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鸿雪因缘图记论文; 中国印刷史论文; 光绪论文; 读书论文; 申报论文; 五彩石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