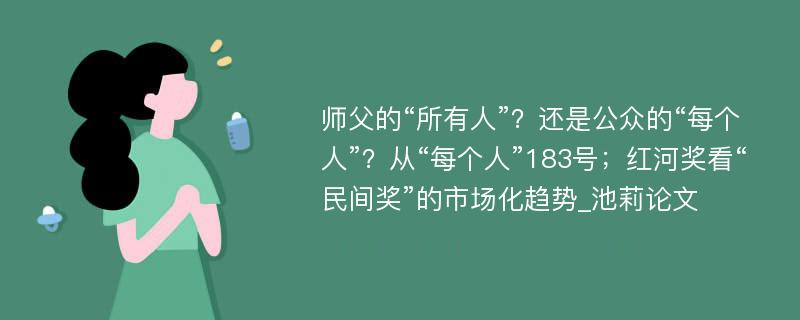
大师的《大家》?还是大众的“大家”?——从“《大家》#183;红河奖”的评选看“民间奖”的市场化倾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河论文,大众论文,倾向论文,民间论文,大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8年前后,中国作协主办的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和首届鲁迅文学奖引起诸多非议,政 府“三大奖”中与当代文学关系最为紧密的“五个一工程奖”评奖活动也处于暂停阶段 (注:“五个一工程”奖本为年度奖,但在第6届(1996年)和第7届(1999年)之间有3年的 间隔。)。与此同时,各种形式的民间文学评奖活动则不断涌现。如《北京文学》推出 的“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新世纪北京文学奖”;《当代》举办的“《当 代》文学拉力赛”、“春天文学奖”;《中国作家》举办的“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 ;“九头鸟”丛书(长江文艺出版社)设立的“九头鸟”长篇小说奖;上海作协等单位发 起组织的“90年代最有影响的10部作品”问卷调查活动;中国小说学会推出的“中国小 说排行榜”,等等。此外,世纪末前后,各种文学经典评选活动也层出不穷。各种新设 立的奖项形成一个相当活跃的“民间奖”阵营。虽然这些“民间奖”的“民间性”是相 对而言的——主办单位大部分仍是体制内文学期刊、出版社或文学组织机构,但在评选 原则和操作上毕竟与“政府奖”和“作协奖”有所不同。
这些“民间奖”具有双重特性,一方面,它们极力强调评奖在审美原则上纯粹的艺术 性。另一方面,这些新设立的“民间奖”——尤其是由文学期刊和出版社举办的文学大 奖,都有一个无法回避的背景,就是在“断奶”、“入世”、“民营出版”等几重压力 下,文学期刊和出版面临着的严峻的生存危机。作为“市场化”转型应对策略之一,“ 民间奖”从创意到操作本身就是集明确宗旨、扩大影响、招募优秀作品、甚至制造广告 效果为一体的商业运作的有机组成部分。有些大奖,如“《当代》文学拉力赛”(最高 奖金10万元,人民币,下同)、“新世纪北京文学奖”(总奖金18万元)、“九头鸟”长 篇小说奖(最高奖金10万元)都没有赞助,高额奖金是其运作成本的一部分,市场因素势 必会对大奖的评审原则和操作方式产生内在影响。
“民间奖”诞生的双重背景预设了其在操作中尴尬的处境。一方面,纯粹的艺术奖是 它们的基本立足点(至少是姿态)。但在举办过程中,纯文学原则与大众流行趣味之间的 对抗却更为凸显。可以说,纯文学旗帜越高扬,“市场化”的程度越深,二者之间的张 力就越大。这样的矛盾冲突突出表现在当代设立最早也影响最大的“民间大奖”——“ 《大家》·红河文学奖”的评选过程中。
二
《大家》在1994年1月的创刊号上就刊登出要设立“中国第一文学大奖”——“《大家 》文学奖”的启示,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虔诚仰视文学殿堂的肖像”为封面,以“ 寻找《大家》、造就《大家》”为口号,再加上10万元的巨额奖金,“《大家》文学奖 ”很自然地被视作中国的“小诺贝尔文学奖”,令不少文坛人士为之振奋。不过,作为 以市场方式操作的纯文学期刊,“《大家》文学奖”的创立还有另一重要目的,这就是 在纯文学普遍低迷的状态下,为“横空出世”的《大家》打造知名度,吸引优秀作家以 精心之作支持新刊物。云南红河卷烟厂在获知《大家》的意图后之所以能够立刻决定( 据说只用了10分钟的时间)主动捐助,也是由于在文学领域树立红河品牌的文化形象是 该企业的既定宣传策略(注:参见舒晋瑜:《文学期刊赛事知多少》,《中华读书报》2 002年11月6日。)。这样,10万元最高文学奖就与一流名人主持、一流撰稿人、一流版 式、一流纸张一样,成为既标明品位又吸引市场、以品位赢得市场的创意之一。
1995年底首届“《大家》·红河文学奖”揭晓,颁奖典礼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注:“《 大家》·红河文学奖”的历届颁奖典礼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在有关报道中,这个地点 也被一再强调。人民大会堂作为国家最高权威的标志在这里用来烘托大奖的权威性。但 是,在1995年以前,人民大会堂的一些场所就已可以被租用(大概是作为一种“创收” 形式),也曾经被一些烟酒厂家用来举办产品宣传会。“人民大会堂”与“红旗牌”轿 车一样,以其留在人民记忆里的权威性在商品社会成了在可以用金钱购买的“象征资本 ”,成为庄重、典雅的象征,高品质的保证。从人们普遍接受的市场逻辑来看,这不失 为一个成功的炒作策略。但若拿编者用以自比的“堂·吉诃德式”的标准来苛求,采用 这种企业家们惯用的方式则显得有点缺乏的“诗意的想像”,也缺乏“不一样”的“大 家风范”。),获奖作品是莫言的《丰乳肥臂》。《大家》编者称,此次颁奖使“《大 家》激励中国作家向世界文学巅峰发起冲击的愿望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注:《不一 样的<大家>编年史》,《大家》杂志1998年末随刊附页。)。莫言一向是被认为有可能 以中国特色的魔幻现实主义登上诺贝尔奖领奖台的“有潜力”的作家之一,但是,《丰 乳肥臀》这部作品却未获得很高的评价。评论界普遍认为这部作品无论在文化思考上还 是在叙述方式上都没有突破,“丰乳肥臀”的书名还被不少人认为是有商业炒做的嫌疑 。在世纪末前后,众多的“文学盘点”中,这部作品也一直未能榜上有名,说明“《大 家》·红河文学奖”首度垂青的作品并非公认的“《大家》之作”。不过,此时《大家 》创刊未久,参选作品必须是自己发表的作品,一时没有更合适的佳作也在情理之中。
根据“《大家》·红河文学奖”的评选规则,该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每届只评选一部 作品获得“大奖”。1998年初,第二届“《大家》·红河文学奖”颁奖典礼再次在人民 大会堂举行。为保证大奖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此次大奖宣布“空缺”。而第三届评选则 因种种原因一再推迟,“《大家》·红河文学奖”能否继续,最终花落谁家?成为文坛 的疑问和悬念。
2002年1月,第三届、第四届“《大家》·红河文学奖”同时揭晓。评选结果是,由于 “评委会再三推敲,未能评出一部有深刻影响的代表性的长篇小说”,第三届大奖再度 宣布空缺。而经两度空缺后,承担着“捍卫这一重奖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使命的第四届 大奖最终授予了市场号召力一向大于“圈内”影响力的作家池莉(注:参见邓凯:《巨奖呼唤大家——第三、四届大家·红河文学奖在京颁奖》,《大家》2002年第2期。), 她获奖的作品《看麦娘》是一部中篇小说,而非“一部有深刻影响的代表性的长篇小说 ”。这一出人意料的评选结果更引起了不少人的疑问。
“《大家》·红河文学奖”评委会对《看麦娘》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看麦娘》标 志着池莉已然从“新”写实走向了“心”写实,“她不再只是世俗生活的记录者和认同 者,《看麦娘》是她创作的一次涅槃,也是小说精神的一次升腾”(注:参见邓 凯:《巨奖呼唤大家——第三、四届大家·红河文学奖在京颁奖》,《大家》2002年第 2期。)。
《看麦娘》发表于《大家》2001年第6期。发表以来评论不多,在笔者所能查到的数篇 评论文章中,只有曾担任第三届、第四届“《大家》·红河文学奖”评委之一的王干对 这部作品大为称赞(注:参见王干:《重新回到当代——2001年中短篇小说述评》,《 南方文坛》2002年第1期。《伪之罪》,《文艺报》2002年2月26日。),其他的文章大 都持批评态度,有的用语还相当尖刻。比如李建军在《一锅热气腾腾的烂粥——评<看 麦娘>》一文中称:“《看麦娘》也显示着池莉试图摆脱过去创作模式的努力,但这种 努力由于缺乏博大的精神视境,由于缺乏坚实的思想支撑,由于缺乏圆熟的艺术形式, 而终归失败。”他因而认为第四届“《大家》·红河文学奖”的“商业意义大于文学意 义”(注:李建军:《一锅热气腾腾的烂粥——评<看麦娘>》,《南方文坛》,2002年 第3期。)。还有评论者认为,《看麦娘》的意义被过分夸大显示了批评家在畅销标准和 艺术标准之间的无所适从。如殷实在《狗尾草·看麦娘·池莉综合症》一文(注:殷实 :《狗尾草·看麦娘·池莉综合症》,《中国图书商报》2002年5月30日。)中说:“在 名噪今时的诸多小说作者中,池莉可能算是最为特殊的一个类型:在其作者的平庸无奇 与读者的无条件拥戴和崇拜之间,存在着难以理解的关系。这肯定会令那些找不到自己 见解的批评家感到头疼,因为他们既无法忽略狂热的、不可捉摸的大众因素,又找不出 池作的文学魔力——对读者的反应妄加怀疑,难免有感性迟钝、观念滞后之虞,说不定 会落得一个将先入的审美标准强加进读者头脑的可耻名声;而彻底抛开所谓的如潮好评 ,对其作品进行纯粹的文本解读或形而上沉思,若不是过分自欺的话,最终也会明白是 选错了材料。”殷实将这种现象称为“池莉综合症”,认为《看麦娘》受到推崇、奖励 和为众多读者青睐的情况正是这一症状的典型显现。
尽管评论者的看法可能见仁见智,但对于一位创作风格一向很稳定的作家来说,一次 偶然的变化和一次根本性的转型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在两者之间做出判断需要特别的 审慎,判断的结果也可以通过作家的后续作品来进行检验。
在《看麦娘》之后,池莉又接连出版了长篇小说《水与火的缠绵》(华艺出版社,2002 年4月版)和《有了快感你就喊》(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1月版)。这两部作品均未显 示出池莉在创作风格有什么重大的转变,王干自己在评论《水与火的缠绵》时也表示: “比之前不久获得‘《大家》文学奖’的《看麦娘》,池莉还是过于沉湎于她对现实的 体验和理解,她在零距离接近生活、接近读者的同时,少了些超越性,文学毕竟不是回 忆录,……”(注:王干:《温情主义,池莉的看家本领》,《中国图书商报》2002年5 月30日。)如此看来,《看麦娘》与池莉以往的作品纵使有较大区别,恐怕也只是一次 自我突破性的尝试,并谈不上本质上的超越,更谈不上“升腾”、涅槃。对于 作家这样的一次尝试,“《大家》·红河文学奖”匆匆以大奖的形式予以高度评价,显 示出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草率。而且,“《大家》·红河文学奖”第三、四届在评奖规 定上有一项重要的改变,即将过去以作品为单位参评的方式改为以作者为单位参评,目 的是“以便从作家一贯的人格力量和创作的整体走向及成就等多方面进行考察,真正评 出更具影响力、时代性和代表性的大奖”(注:参见邓凯:《巨奖呼唤大家——第三、 四届大家·红河文学奖在京颁奖》,《大家》2002年第2期。)。“《大家》·红河文学 奖”一向旨在鼓励“坚持先锋性和前卫性,坚持文本创新的文学《大家》”,而池莉一 贯的写实风格与之几乎是南辕北辙。并且,对于不久前还公开宣称自己创作只为“博得 老百姓的喜欢”,拒绝“取悦文学圈”(注:参见程永新、池莉:《访谈录》,收于池 莉:《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金收获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版。)的 池莉来说,“代表中国作家向世界文学顶峰发起冲击”恐怕既超出了她的能力,也不是 她的志愿。
然而,“《大家》·红河文学奖”的评委在经过两届慎重的空缺(甚至对于一向支持《 大家》、创作的先锋性受到公认的于坚、李洱也仅授予荣誉奖)之后,却独钟情于池莉 。而且,几乎是作品刚一发表就立即被授以桂冠(作品发表于2001年第6期,大奖于2002 年1月揭晓),给人的感觉是,大奖虽然高扬先锋大旗,但对传统的写实主义作家池莉的 创作却格外关注,殷殷期盼着她的超越、升腾。而所谓的超越、升腾也是相对于池莉自 己而言的,正如王干在称《看麦娘》为中国当代文学2001年度“最有价值的中篇”时所 说的:“说最有价值首先是对池莉而言,池莉的小说好看,鲜活,但往往拘泥于现实, 而这一篇小说一下子‘升腾’起来,……”(注:见王干:《伪之罪》,《文艺报》200 2年2月26日。)但问题是,为什么是池莉而不是别的作家可以自己和自己比?如果池莉没 有受到广大读者“无条件的拥戴”,她是否有可能受到大奖评委“无条件的关注”?在 这样的关注下评选出来的作品在审美标准上又会产生怎样的偏差?2002年3月中国小说协 会公布了该协会评选出的2001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中,上榜的中篇小说共有9篇,但未 包括刚刚获得“《大家》·红河文学奖”桂冠的《看麦娘》。该排行榜的评委全部是在 文坛上活跃的著名评论家,《看麦娘》的落选至少说明“《大家》·红河文学奖”对它 的高度评价在文学圈内不能得到公认。
要对第四届“《大家》·红河文学奖”出人意料的选择做出解释,大概只能从此次评 奖在学术性、厚重性、权威性之外,特别提出的“广泛性”这条标准来寻找原因。
在评选结果揭晓之前,关于评委身份是否“够格”的问题已经引起广泛的议论。据称 ,评委会在人员构成方面进行了有意识的改革,5位评委中除了作家余华、学者谢冕、 评论家王干之外,还特别聘请了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和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栏目主持 人李潘。议论的焦点正集中于后两者,虽然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在华人圈内的影响无人 能及,李潘主持的“读书时间”栏目也在文化界有着良好的口碑,但他们毕竟是通俗小 说大师和媒体主持人,他们在各自领域内的成就是否可“平移”为纯文学大奖评委的资 格?这一问题受到不少人的质疑,有批评者更直称,《大家》如此做法不过是借评委的 知名度吸引读者“眼球”,是一种明显的商业炒作方式(注:参见赵晨钰:《<大家>评 奖 金庸当评委不够格?》,《中华读书报》2002年11月6日。)。
《大家》主编李巍在谈到此项改革的初衷时谈到,评委构成在原来清一色的作家评论 家的基础上新增了媒体记者和海外著名华人学者两种身份,主要目的是让纯文学走出小 众,引起大众的关注。他的理论依据是,文学本身是一个变化的过程,纯文学的概念已 经日渐宽泛,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的关系其实就像艺术电影与商业电影一样,二者在 不断地靠近、互渗。因而该领域的评奖也必然会有变化,不该把自己封在小圈子里。金 庸先生的小说之所以畅销,自然有其原因,纯文学亦可以从中思考吸取某些东西。在此 问题上,其他几家纯文学刊物的负责人都对《大家》进行了“声援”。如《人民文学》 编辑部主任李敬泽称,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并不存在楚河汉界,二者在某个空间是可 以实现交流的。《收获》杂志副主编程永新也认为,金庸先生担任“《大家》·红河文 学奖”的评委是很正常的一件事。金庸在文化、历史上的修养,以及他对文学的看法、 判断都是具有一定水准的。他还表示,“就算《大家》此举有一定的商业炒作因素,那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注:参见赵晨钰:《<大家>评奖 金庸当评委不够格?》,《中华 读书报》2002年11月6日。)。
从以上的“声明”和“声援”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位当前中国最重要的纯文学期刊 负责人在有关“纯文学”概念的拓宽、雅俗文学界限的打破(而且只注重强调纯文学对 优秀的通俗文学应有所借鉴)等问题上持相似的观点,这样的观点与我们曾讨论过的《 北京文学》对“好看”的提倡以及以“好看”为“好刊”的价值取向有相同的理论基础 。而且,从诸如“情理之中”一类的说法中,我们可以感觉到,这样一种“共识”的形 成与纯文学期刊共同面临的生存压力之间有着的直接关系。但是在“情有可原”的同时 ,我们也不得不看到,当大众流行趣味不但影响到纯文学期刊的发表原则,甚至也渗透 到纯文学大奖的评审原则以后,纯文学的发展会陷入更深度的恶性循环。
如果说在“市场化”不断加深的文学环境下,像《大家》这样的大型纯文学期刊是少 数的几个“纯文学阵地”的话,“《大家》·红河文学奖”这样的文学大奖就堪称阵地 上的旗帜。如果说处于稿源限制和销量压力下的文学期刊,在发表作品时难免受到作家 创作风向和读者趣味的影响,两年一度的大奖则正可以比较单纯明确地标明刊物的价值 取向。“《大家》·红河文学奖”所谓的“《大家》”,到底是“大师”意义上的“《 大家》”,还是“大众”意义上的“《大家》”?这中间确实有着不可模糊的楚河汉界 。虽然确有不少大师在攀登文学顶峰的同时也赢得了当世大众的拥戴,但在纯文学的领 域,是否赢得大众丝毫不构成其能否成为“大师”的资格。相反,为生前寂寞的大师赢 得身后的大众,这正是权威大奖的最基本也是最神圣的职责。像“《大家》·红河文学 奖”这样的以“中国的诺贝尔奖”为自我期许的文学大奖,它所依据的毋庸置疑只能是 精英小众的审美原则,它所颁发的“象征资本”的权威性也正取决于它对于纯文学原则 恪守的严格性和把握的准确性,当然这首先要求评奖者对纯文学原则有着坚定的自信。
在“《大家》·红河文学奖”试图从“小众”走向“大众”的“突破”中,我们确实 可以看到“文学精英”们对于以往文学界奉行的纯文学原则的不自信。虽然所谓的纯文 学原则本身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中国当代文学中与“先锋小说”等文学实验相伴生 的“纯文学”概念本身就有许多先天不足之处,更需要拓宽和调整。但是调整拓宽并不 意味着“楚河汉界”的自我消解,更不意味着价值基础的自动倾斜。而“《大家》·红 河文学奖”向我们显示的调整方式基本上是对大众审美原则的直接引入——聘请通俗文 学大师和媒体主持人为评委(且比例占到2/5)是意图明显的手段,将大奖授予最有市场 号召力的作家是自然的结果。
在“文学精英”们对精英标准的质疑中,还伴有对读者标准的过分推崇和倚重。其实 ,并不存在真正“自然”的读者标准,所谓“自然标准”其实也是各个时期的专家标准 塑造的。如果在一个时期,读者标准与专家标准产生了巨大的差距,那么很可能是旧的 专家标准与新的专家标准之间的距离,这种情况在一个刚刚进行过重要形式变革的文学 环境中几乎是必然会出现的。在中国当前的文学环境下,年轻读者有可能比年老专家的 审美观念还要滞后,因为,读者的体验虽然是当下的,但审美趣味却可能是从前奠定的 。专家奖所起的正是一种“导读”的作用,通过褒奖那些对文学发展真正具有推进作用 的作品,使它们在读者中间产生广泛影响,从而使新的专家标准逐渐成为“自然的”读 者标准。这就要求专家标准必须具有严格性和独立性,并且在必要的时候敢于疏离、对 抗读者标准。读者只有基于对专家审美判断的信任,才会去购买阅读对自己文化准备具 有挑战性的作品,从而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也使纯文学生产进入良性循环。纯文学的 生存环境越恶劣,就越需要“象征资本”的支持。如果以“寻找《大家》、造就《大家 》”为宗旨的“《大家》奖”都转而青睐广受大众认同的作家,“中国《大家》”成长 的空间在哪里?“中国第一文学大奖”的立足点又在哪里?
“民间奖”出现的最大意义在于打破过去由“政府奖”、“作协奖”的单一垄断格局 。但保持多样化的基础是依据不同标准的文学奖“各守其职”,否则,很容易走向新的 “大一统”。目前,包括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和“五个一工程奖”等“政府三大奖 ”在内的“官方奖”也越来越把“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作为重要的评奖标准之一。 在“市场原则”的强势压力下,大众流行趣味可能是促成新“大一统”的最大的驱动力 量。
三
专家标准向大众趣味的倾向并非只出现在“《大家》·红河文学奖”的评奖活动中, 在其他文学大奖的评选中也相当程度地存在着。
中国由文学期刊或出版社设立的文学奖并不全是专家奖,其中有一部分基本可以算是 大众奖,如《小说月报》“百花奖”、《中篇小说选刊》奖、《小说选刊》奖、《小小 说选刊》奖,等等。其中于1984年设立、一年一度的《小说月报》“百花奖”,获奖作 品完全根据读者投票选出,是中国文学界最具连续性的大众文学奖。“布老虎”丛书也 曾于1997年设立了“金布老虎”奖,该奖的评委虽然都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但由于“ 布老虎”丛书畅销书的性质,评奖标准必然基于大众标准。
专家奖与大众奖的区别首先在评选标准上。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专家奖依据的只能是 专家标准,反映民意是大众奖的任务。正因为依据不同的标准,它们所颁发的“象征资 本”才具有不同的荣誉性质和不同的资本转化功能。大众奖是对读者认可的再认可,虽 然也是一种荣誉,但其性质类似于畅销排行榜或民意测验,在读者市场中引发的是一种 “从众”的效应。虽然获奖可以使作品更畅销,但即使不获奖,这类作品的市场价值也 可以获得较充分的实现。比如,开价100万元的“金布老虎奖”虽然由于铁凝的“婉拒 ”而落空,但总策划安波舜则宣称,包括铁凝的《大浴女》在内的几部“布老虎”小说 “实际上”都已获得了“金布老虎奖”,因为“金布老虎奖”是以100万元买断版权, 而这几部小说的版税都已达到了100万元(注:材料来源:笔者于2002年7月19日采访“ 布老虎”丛书前总策划安波舜先生后整理的《安波舜访谈录》,经安波舜审核,同意引 用。)。而专家奖所褒奖的作品事先却未必会自动获得读者的认可,大奖首先是一种巨 大的荣誉,但通过“象征资本”向市场资本的转化,也可以给作家带来物质上的利益。 世界上的文学大奖有的奖金颇高,如诺贝尔文学奖,有的奖金极低,如法国的龚古尔奖 ,据说奖金的票面价值在巴黎只够买一束鲜花。但低额奖金并不意味着奖励只是荣誉性 质的,《文学社会学》的作者罗贝尔·埃斯卡皮在谈到文学奖的作用时把它称为一种最 常见的、十分经济的政府资助方式:“奖金的价值在票面上是有限的,然而,得奖作品 可以保证得到畅销;作者的收入就此大增。”(注:[法]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 会学》,第73页,王美华、于沛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9月版。)一项大奖所颁发 的“象征资本”是否能有效地转化为市场资本,也是对它自身权威性的一种检验。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些新设立的“民间”大奖争相不惜重金,且对高额奖金过分渲染 和倚重,这本身就意味着其颁发的“象征资本”的“含金量”不足。中国官方性文学奖 项的奖金一般都不高,基本在数千到一万元之间。奖金最高的是冯牧文学奖,每位获奖 者的奖金为2万元。与之相比,“《大家》·红河文学奖”1994年首开先河的10万元大 奖确实对作家构成很大的吸引力。2000年启动的“《当代》文学拉力赛”也以10万元的 高额数目“跟进”。《美文》2001年举办的“全球华人少年美文写作征文大赛”总奖金 101万元,最高奖金10万元,关于中学生一篇作文值不值10万元的问题曾一时引起社会 上的广泛争论。2002年《收获》杂志宣称将联合几家企业打造“中国诺贝尔文学奖”— —“《收获》文学奖”(暂定名),每年在全球范围内奖励一位成就卓著的华语作家,而 用来与诺贝尔文学奖抗衡的主要筹码也在于100万元人民币的高额奖金。
《大家》和《当代》的负责人都曾表示过杂志尽管财政窘困但仍要重奖作家的决心。 《大家》主编李巍在首届“《大家》·红河文学奖”颁奖之后说,虽然《大家》在颁奖 时显得无比潇洒,但编辑部在日常经营中“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抠”。但他同时也表示 :“视潇洒为奢侈的我们,毕竟在人民大会堂云南厅,在首届《大家》·红河奖颁给莫 言的那一刻,让自己,也让所有清贫的文人都潇洒了一回。”(注:李巍:《主编絮语 》,《大家》1996年第1期。)第三届“《大家》·红河奖”虽然空缺,但10万元奖金仍 颁给了8名荣誉奖获得者。《当代》常务副主编常振家在“《当代》文学拉力赛”以转 让冠名权争取商家赞助的计划落空后表示,《当代》就是“勒紧腰带过日子”,也要从 办刊经费中每年拿出10万来颁奖。而且,即使“矮子里面拔将军”,也绝不令大奖空缺 。“以高额奖金掀起炒作热潮,又以‘空缺’方式一毛不拔的伎俩,《当代》是绝不会 的。”(注:《“<当代>文学拉力赛”2000年第一站竞赛纪实》,《当代》2000年第2期 。)
从以上表述中我们可以体味到,这些大奖表面上看似乎“财大气粗”,但背后则是囊 中羞涩的文学期刊的惨淡经营。但是,这样强烈的对比却越发强化了大奖票面价值的重 要性。虽然说在大奖设立的初期,足以引发新闻效应的奖金数额可以起到扩大知名度、 吸引作家的实际作用。但就长期而言,大奖的权威性只能建立在其获奖作品的权威性上 :大奖以其卓越的审美眼光不断评选出经得起文学史检验的优秀作品,从而使自己获得 对一个时期文学精品、甚至文学经典的命名权,使这些作品可以成为长久的畅销书。否 则,如果主要以“票面价值”吸引作家和舆论关注,不但无益于自身权威性的建立,而 且,随着畅销书收益的不断增加,在诸如“金布老虎”等轻易可以拿出一百万元的畅销 书巨奖的映衬下,靠“勒紧腰带”抠出的奖金也很快会失去其诱人的光辉。
“市场化”转型以后,中国当代“文学场”中发生的最显著的变化是读者地位的提升 。读者从被动的接受者变成了主动的消费者。读者的消费倾向不但影响了作家的创作原 则、文学期刊出版社的发表出版原则,也直接影响到文学批评和评奖的评审原则。但对 于“民间专家奖”而言,在赢得“广泛性”的同时也难免削弱其权威性。因为,这些“ 民间专家奖”的评奖标准是建立在与官方主流审美原则和大众流行趣味的双重对抗的基 础上的。正像前文所分析的,并不存在所谓“自然的读者标准”。今天“自然的读者标 准”正是昨天的权威标准,尤其是对曾发生过重要形式变革的当代文学而言,对还未生 根的新标准的放弃就意味着对依然强大的旧标准的屈从。应该说,纯文学在现实中的生 存处境越险恶,越需要“象征资本”的支持。如果纯文学大奖都唯民意是从,先锋探索 如何能在逆境中披荆斩棘?从更长远的角度说,今天的文学产品,喂养着明天的消费者 。今天的文学标准,塑造着明天的文学趣味。今天的单调平庸也将造成明天的贫瘠荒凉 。也正是在如此的意义上,“民间专家奖”虽然生逢困境,但仍难免被苛责承担守护文 学香火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