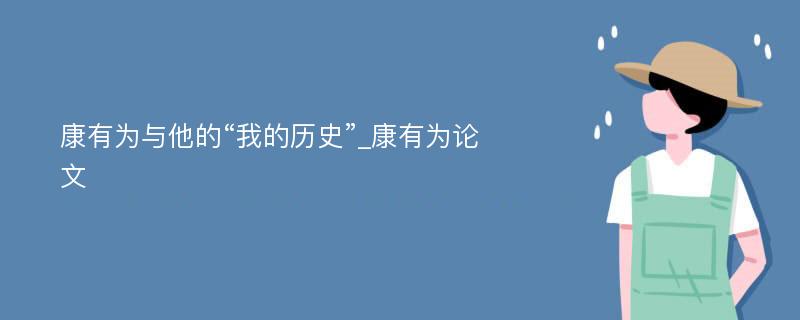
康有为与他的《我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康有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9)01-0094-16
很长时间以来,戊戌变法的研究,依据着三大史料:其一、康有为的《戊戌奏稿》;其二、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其三、康有为的《我史》,即《康南海自编年谱》。现有的主流看法与结论,很大程度上还是从这三种史料中得出来的,尽管许多研究先进对此有了已经不新的研究成果。
首先发现其中差误的,是台北的黄彰健,他依据1958年北京出版的《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发现了康有为在《戊戌奏稿》中作伪。黄彰健当时不能来北京看档案,他的贡献很大意义上是提出了假设;而1981年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的发现,为他提供了近乎完美的证明①。此时北京的孔祥吉,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研读中,多有贡献,大体完成了对康有为奏折查寻与核对。可以说,康有为在戊戌时期的真奏稿,现在已经有了可靠的本子。
其次是对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的研究,先后有刘凤翰、狭间直树、戚学民等多位研究先进投入工作,也出产了一批有价值的论文。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梁著的版本进行了核对,寻思其写作及改动的原因。通过他们的工作,今天的人们对于梁所称“将真迹放大”一语,有了“不放大”的体会:《戊戌政变记》虽不能作为研究戊戌变法的可靠史料,但可测量出梁说与史实之间的差距,由此而证明梁的内心世界及其变化。该书已成了研究梁启超思想的可靠史料。
然而,对于康有为的《我史》,却一直没有进行认真的整理。一方面研究者知道康在其中作伪;另一方面若对此一一进行史实查证,须得下笨功夫,工作量也相当大。比较聪明的办法,是绕开《我史》;等到实在绕不开时,选择《我史》中的个别章句,与已发现的档案、文献进行核对,说一些不那么饱满的话。我进入戊戌变法史的研究后,看见有人是这么做的,于是我也这么做了。
避开与绕行,总不是长久之计,我也想来一个干脆,索性花一点时间来进行整理。然当我真正下水时,才逐步发现水的实际深度,摸到底须先换一口气。于是,在工作中,我不再那么自信,而产生了种种怀疑:其一、这一种史实查证的工作是不可能是周全的,做得再好,也只是提供部分的相关史料,许多地方很有可能就是查无实证;其二、这类工作本应是全面的,但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查验完全部史料,由此随时会被新史料和新证明所推翻;其三、现在的研究时尚似不太在乎此类史实重建工作,在我此前的诸多研究先进的著作,都没有人去认真研读,关于戊戌变法流行的言论与结论仍然沿袭着康、梁的旧说,被康、梁牵着鼻子走。在此等风气之下,我再写出这一本繁琐考证的著作,何用之有?更何况其中的许多史实,我也不能予以肯定的证明。
我的这一项工作,也就是在这种越来越浓重的自我怀疑的精神状态下,一步步地渐行着。
手稿本、抄本与写作时间
康有为所撰《我史》,叙述了他从出生(咸丰八年,1858)到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十年的个人历史。按当时人的记岁方式,为虚龄四十一岁。
《我史》的手稿本,由罗静宜、罗晓虹捐赠,1961年由文化部文物局转藏于中国革命博物馆,该馆现并入中国国家博物馆。2006年10月,我有幸读之②。原来长期被我视为谜团的写作时间,一下子得以解开。
从手稿本所录11篇跋文中可以看出,康有为《我史》写于日本。而在手稿本末尾,也有康有为亲笔写的这段话:
诸子欲闻吾行事,请吾书此。此四十年乎,当地球文明之运,中外相通之时,诸教并出,新理大发之日,吾以一身备中原师友之传,当中国政变之事,为四千年未有之会;而穷理创义,立事变法,吾皆遭逢其会而自为之。学道救人,足为一世;生本无涯,道终未济。今已死耶,则已阅遍人天,亦自无碍,即作如是观也。后此玩心神明,更驰新义,即作断想,又为一生观也。九月十二日至日本,居东京已三月。岁暮书于牛込区早稻田四十二番之明夷阁。
康于此中明确说明,该书的写作时间是光绪二十四年的“岁暮”;地点是东京的“早稻田”;而此时康已来日本三个多月,由于清政府的要求,日本政府正打算礼送其出境,前往美洲。康为此受到巨大压力,只能表示同意(后将详述)。
康称其写作此书的动机是“诸子欲闻吾行事,请吾书此”,即离开日本之际康的追随者要求留下他个人的记录,于是便写下了这本书。这一说法不那么确切。随康赴日的弟子叶湘南在手稿本末作跋语,称言:
余年六十三得读先师手写年谱,如升其堂,如闻其语,悲喜交集……戊戌政变蒙难由香港东渡,同舟十日。弟子随行者,惟予一人,饮食起居,论学不辍,心境泰然。到日后,先师颜所居曰“明夷阁”。此谱写定,予闻而未之见也。及游历欧美,不复能追随矣……
叶湘南,字觉迈,号仲远,广东东莞人,举人,万木草堂学生。光绪二十三年曾随梁启超至湖南,为时务学堂分教习③。叶称此书“予闻而未之见”,与康说有着很大的差别。
《我史》的写作共用了多少天?康并没有说明,但《我史》近四万余字④,不是一挥而可就的。《我史》手稿本共计88页,其中78页是康有为的笔迹,另有10页为康有为口授,由其弟子韩文举笔录,约3600字。在该笔录最后一页的页末,有注文:
戊戌政变,先师出亡日本,先后奔随者不乏其人,文举亦与焉。某日某夜,先师口授政变情事,命笔述之。是时夜深矣。感怀旧事,迄今已三十余载矣。孝高适自上海来,携此册,促予书后。年已七十矣。计当时笔述凡十页
癸酉十月望后二日 韩文举记于香港⑤
韩文举(1864~1944),字树园,号孔庵,笔名扪蚤谈虎客,广东番禺人,监生。光绪十六年(1890)入万木草堂,号称长兴里十大弟子之一⑥。该跋语称,其流亡日本时,某日晚上康有为命其为之作笔录。在其笔录的10页纸上,有韩修改笔迹,也有康修改笔迹。一晚上录3600余字,可见当时康的精神状态十分兴奋,也可见韩熟悉此道而能胜任。若以此来计算,康有为的写作时间大约在十天左右。
从手稿本所录跋文可知,康有为离开日本时,并没有将手稿带走,而是交给其弟子罗普。罗普(1876~1949),原名文梯,字熙明,号孝高,麦孟华之妹婿。早年师从康有为,光绪二十三年(1897)入东京专门学校(即早稻田大学的前身)⑦。罗普此后一直将之随身携带。当时在东京的梁启超,肯定看过手稿本,其作《戊戌政变记》多以《我史》之意旨而散发,甚至大段直接引用《我史》。当然,康后来也看到了这部手稿本,并且在手稿上进行了修改。
就此而论,《我史》的写作时间十分确定,并没有什么问题。
我在这里插入一段关于《我史》抄录与传播之情况,然后再谈该书写作时间之疑问产生。
康有为的《我史》,生前没有发表,可以看到者,很可能只有罗普等极少数人。然在康去世后不久,各种抄本开始流传。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芮玛丽(Mary Wright)曾在康有为女儿康同璧家,将其所藏康有为资料拍成四个胶卷,现存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图书馆等处藏有复制本。其中即有《康南海自编年谱》,封面上并题“民国二十年六月付钞颉刚记”。“颉刚”,即顾颉刚,字体为顾的亲笔⑧。此为顾颉刚1931年抄本(以下简称“顾抄本”)⑨。顾抄本非常完美,其最佳之处,就是将原注、眉批、眉注,都照其格式,原模原样地搬了过来。在该抄本的最后,还抄有一段跋文:
此南海之自编年谱也。中缺丙申一年。乙未以前稿,据南海自跋,系抄没流落人间,为罗孝高所得。丁酉以后,乃戊戌岁暮在日本所作,亦归孝高。徐君善伯抄得副本。十八年,为任公作年谱,向之借录。此册中颇有误字,暇当借孝高原本为之一校也。
十八,五,十四,丁文江⑩
据此可以知道,顾抄本录自丁文江1929年抄本,丁文江抄本录自徐善伯抄本,徐善伯抄本录自罗普。徐善伯,名良,是康有为的大弟子徐勤(君勉)之子(11)。“丙申”,即光绪二十二年。
丁文江于1929年派人抄录《我史》,正是“为任公(梁启超)作年谱”作资料准备之用(12)。丁此项工作的主要助手是赵丰田(13)。赵丰田在1936年燕京大学《史学年报》第2卷第1期发表《康长素先生年谱稿》,在《引用及参考书目》中称:
《康南海自编年谱》,丁文江氏副钞本。(原钞本在罗孝高君手内)是谱起生年,止四十一岁(光绪廿四年)。乙未以前系旧作,丁、戊二年系戊戌十二月在日本补作,中缺丙申一年(14)。
可见赵所使用者,为丁文江抄本,并提出罗普处另有“原钞本”。顾抄本为何会在康同璧的文件中,尚不得知,由此却可知康同璧之所藏为顾抄本。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特藏室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油印本,题名为:“南海康先生自编年谱”。该版本很可能就是康同璧1958年或1959年在北京自费油印的。我将之与顾颉刚抄本一一相校,文字上基本相同。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有另一抄本,其封面从右向左竖题:“戊寅年四月初八日/康南海自编年谱/何凤儒题”(15)。从文字校对来看,很有可能是抄自顾颉刚抄本。
由此可知,康有为《我史》至少有罗普抄本、徐良抄本、丁文江抄本、顾颉刚抄本、何凤儒抄本、康同璧油印本。康有为弟子张伯桢著有《南海康先生传》,内容与《我史》几乎相同,由此可知张伯桢也有一抄本。
问题出在前引丁文江跋文称:“此南海之自编年谱也。中缺丙申一年。乙未以前稿,据南海自跋,系抄没流落人间,为罗孝高所得。丁酉以后,乃戊戌岁暮在日本所作,亦归孝高”。这段跋语中包含着太多的问题。丁的依据是,徐良抄本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结尾处,录有康有为眉批:
此谱为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前作,故叙事止于是岁。门人罗孝高不知从何得之,盖戊戌抄没,落于人间,而孝高得之也。更甡七十记。
“更甡”是康有为晚年之号,“七十”当为虚岁七十,时为1927年(民国十六年)。是年3月8日(二月初五)康有为在上海度过七十岁生日,数日后遂离沪去青岛,3月31日(二月二十八日)在青岛寓所病逝。这一眉批应是康逝世前不久添加的(16)。康有为此处宣称,他曾于光绪二十一年写过自传,且被抄没后,又被罗普所获。丁据此认为,康在光绪二十一年写完其前半,到日本后又作其后半。“更甡七十记”这段眉批,我所见到的各抄本、刊本皆录之。
然而我查看《我史》的手稿本,不仅没有这一条眉批,而且也不缺丙申一年,也就是说,康有为在日本完整地写下了从出生到光绪二十四年的内容;由此似又可推论,康在光绪二十一年很可能就没有写过自传。其中最有力的证据是,从手稿本所附11篇跋文中可知,1933年罗普先是在上海,后在广州与香港展示《我史》手稿本,请康有为弟子作跋语,如罗普真藏有光绪二十一年手稿本,定当同时展示,而所有的跋文都没有提到此事。
那么,康有为的这条眉批又写在何处?我以为,很可能是写在其中的一个抄本上的。就情理而言,不会写在徐良抄本上,最大的可能是写在罗普抄本上的。我可举出一条证据:即手稿本第64页眉左角,也就是韩文举笔录之起始,有康有为亲笔眉批:“可照抄。卷四”。“可照抄”三字,似为康给罗普下达的指示。
根据丁文江跋文可知,徐良的抄本有康有为的“更甡七十记”之眉批,同时缺“丙申”一年,张伯桢写《南海康先生传》也缺“丙申”一年,看来他们两人使用的是同一版本。丁不仅称“此册颇有误字”,还提出“暇当借孝高原本为之一校”,他是否又做到了呢?从顾颉刚抄本来看,顾氏是做到了。“丙申”年即光绪二十二年的内容,约二百余字,顾抄本是补抄在页眉上的(17)。至于丁氏所提到的“误字”,顾抄本共有眉注17条,以作为校注。
也正是康有为“更甡七十记”之眉批引出的岐意,使得《我史》的写作时间混乱不清。丁文江等人被康牵了鼻子走。我以为,丁文江、顾颉刚等人没有看到《我史》的手稿本,不然的话,以其才华识力,定会很快看出破绽。由此又可以推论,顾颉刚用于相较的不是手稿本而是罗普的抄本。我将顾抄本与手稿本相较对,发现只是个别文字上的差误,而没有内容上的差别,由此又可推知,罗抄本是忠实于手稿本的。
问题的要害是,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一年似未写其自传,罗普手中也没有光绪二十一年的手稿本,那么,康有为“更甡七十记”的用意究竟为何?从手稿本来看,康后来对《我史》有不小的修改和添加,大体改到光绪十八年;康已将手稿本分为五卷;康在手稿本有5处修改之贴条;据此似可以认为,康有为晚年打算较大规模地修改《我史》,并准备出版,但没有完成,便去世了。而康写“更牲七十记”一段眉批,很可能意味着他打算进行诸如《戊戌奏稿》一般的再造。
刊印与书名
康有为《我史》最初刊行于1953年。中国史学会编辑、神州国光社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以《康南海自编年谱》为题,第一次发表了《我史》。(以下简称《戊戌变法》本)在该书的《书目解题》中称:
《康有为自编年谱》,一册,康有为撰,钞本,赵丰田藏。
又在该年谱前加编者按:
此年谱系根据赵丰田所藏抄本录下,后经与康同璧所藏抄本对校。原文至光绪二十四年为止。(18)
也就是说,《康南海自编年谱》是根据两个抄本互校发表的,其一是赵丰田所藏抄本,其二是康同璧所藏抄本。前已叙明,赵丰田所藏抄本即丁文江抄本,康同璧所藏抄本即顾颉刚抄本。赵丰田、康同璧似都未意识到《我史》手稿本的存在。
1966年,台北文海出版社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第11卷辑入张伯桢《南海康先生传》、《康南海自订年谱》(19)。我对之进行了核对,《康南海自订年谱》的文字系录于《戊戌变法》本。1972年,文海出版社出《康南海自订年谱·康南海先生年谱续编》合订本一册,次年重印。其中《康南海自订年谱》为1966年版之影印。1976年,蒋贵麟主编《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台北:宏业书局),其第22册中收录《康南海自编年谱》,仍系影印1966年文海版。1992年楼字烈编:《康南海先生年谱(外二种)》(中华书局),1996年朱维铮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康有为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罗岗等编《我史》(江苏人民出版社),皆据《戊戌变法》本。可以说,现在刊行的版本,皆出自1953年神州国光社的《戊戌变法》本。
由此,我现在可以看到的,一共有五个版本,其一是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手稿本,其二是《戊戌变法》本,其三是顾抄本,其四是何凤儒抄本,其五是康同璧油印本,后两个版本又是以顾抄本为母本。各版本之间除了文字转抄中略有异误外,基本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现行的刊本、抄本与手稿本并无原则性的差别,只是看不到康有为亲笔修改之处。
至少在1929年丁文江抄录时,书名已用“康南海自编年谱”(20)。顾颉刚抄本、何凤翰抄本皆用此名。1953年神州国光社刊行时,以《康南海自编年谱》为书名,也是很自然的。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个书名是由后人名之而非康有为本人自题,康不可能自称为“康南海”。
然从手稿本来看,封面及内页并无题名。由于用的是年谱体,又是其亲写,中国革命博物馆将该件藏品命名为“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由此又可以解释,丁文江等抄本为何以此名之。
1958年,康有为女儿康同璧在任启圣的帮助下完成《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其《序》起首便称:
先君《自编年谱》,原名《我史》,止于戊戌,凡四十一年,后未续作。
此语中道出,该书康有为最初命名为《我史》(21)。而更早提到该书书名的,是康有为弟子张伯桢。1932年,他刻其著《南海康先生传》,称言:民国初年,康有为住在上海,“时伯桢拟刻丛书,先生知之,将平生诸稿编定见授”,其中提到:“《我史》,即年谱”(22)。张的这一说法,称该书有两个书名。康虽然没有直接将《我史》之题名写在手稿本上,但康同璧、张伯桢必然听见康本人说过。
前引“更甡七十记”之眉批称:“此谱为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前作,故叙事止于是岁。门人罗孝高不知从何得之……”(23)。此中的“谱”字,当作为“年谱”解。康以“此谱”称此书,也有可能将之题名为《自编年谱》。这与张伯桢的说法是一致的。
1996年,朱维铮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康有为卷》,将《康南海自编年谱》复名为《我史》,称言:
《我史》在成稿后半个世纪才刊布,书题被刊布时编者改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自有某种不得已的考虑,但也大失原著论旨,由原著结语可明。因此我将他作为康有为以“我”为核心的思想政见的自我总结收录本卷,并依据康同璧的佐证,恢复其原名(24)。
朱维铮关于《康南海自编年谱》名称的由来,稍有小误,但其中强调的主旨,我是很赞成的,《我史》这一名称是康有为的原意,也特别符合光绪二十四年岁暮康有为写作时的心情。
据此,本书亦恢复康有为原意中的题名《我史》。
《我史》“鉴注”的时段
康有为《我史》记录了其出生到戊戌变法失败共计四十年的历史,为其作鉴注,当然最好是四十年皆作。我也有过这一想法。但是,这么一来,我又遇到两个问题:
其一,康有为个人最辉煌的历史为从甲午到戊戌,即光绪二十年至二十四年(1894至1898年);其余的时间,政治活动并不多。尽管从其生平和思想而言,从戊午到癸巳,即咸丰八年至光绪二十三年(1858至1893年),也很重要;且今日今人之研究,更注重童年习性、教育背景与人际交往。但此一时期毕竟是康政治活动的准备期,康本人似也如此认为。《我史》共计近4万字,其戊午到癸巳的35年,计约14000字,而甲午到戊戌的5年,却计约25000字,而戊戌一年,尤为重中之重,接近18000字。今天的研究者引用《我史》,主要是戊戌年。且从《我史》手稿本中可知,光绪二十年之后的部分,康有为还来不及修改,大体保持为光绪二十四年末初写时的状态。
其二,也是更重要的,从戊午到癸巳的35年,康有为主要是在其家乡活动,也不太出名,除了光绪十四年至十五年(1888~1889)他到北京参加乡试外,政治活动内容很少。正因为如此,除了康自己的记录外,其他人的记录是很少的,可供参考的档案材料更是完全没有。若要为之作注,真是缺米下锅,事倍功半。康此期的思想与学术虽然重要,《我史》手稿本中的又能看出他后来的多处修改(25)。若要再加细细辨析鉴注,须得从经学、西学与“康学”的关系入手,而我对经学史却不太熟悉,为此需得再花上相当长的准备时间。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的主要活动为政治斗争,斗争的核心处所主要是北京,他已经从边缘进据到政治舞台的中心,官方档案中留下了大量的记载,私人记录也有相当大的数量。而我本人的研究兴趣恰是政治史,又有看档案经验,对清代档案相对熟悉。
于是,我便选择了康有为《我史》中从甲午到戊戌的后5年,一一作注。结果这约25000字的原稿,我的注释字数却达到了二三十倍。尽管我可以为这种割裂式的鉴注,举出相当“充分”的理由:从甲午到戊戌,是中国历史上的关键时刻,也是康有为个人历史的关键时期,更是《我史》的主体部分。然我仍不能掩盖的是:我对甲午以前康有为在广东时期的史料搜集以及掌握经学史上的门派路径,感到严重信心不足;更何况今天的史学理论也有了新的变化,似乎更重视历史的平常时分,而不是我所关注那些关键时刻。
我个人也寄希望于将来,等我对广东史料有着更多的认识后,等我能有一段新的相对空余时间后,再出一增订本,将康《我史》从戊午到癸巳的前35年,也一一作补注,同时还可以增补和修改我今稿中的忽略与错误。
《我史》的真实性
我为康有为《我史》作注,本来是因为康在其中作伪,以能一一予以鉴别之。然而,当我的工作将要完成时,我却又发现,康在《我史》中所记录的事件是大体可靠的,其之所以为不可信,在于他用了张扬的语词,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夸大自己的作用,并尽可能地将自己凌驾于当时朝廷高官之上。如果用当时的政治术语,即为“粉饰”。对于我的这一判断,我大体上是有几分把握的。
当然,在一些历史的关键时刻,如“公车上书”、托人保荐、密谋政变等等,康有为确实在《我史》中作伪,且康党会将相关的记录系统化,以使之不相矛盾。我也一直怀疑,康对刘歆的指责,使之在作伪的手法上更具完善。但是,康在《我史》中作伪次数还不是很多,似还不至于影响到我的结论:《我史》是一部可以小心利用的史料(26)。
康有为的这种张扬与自夸,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性情与性格。其在《我史》光绪四年(1878)中自称:
……然同学渐骇其不逊。至秋冬时,四库要书大义,略知其概,以日埋故纸堆中,汩其灵明,渐厌之。日有新思,思考据家著书满家,如戴东原,究复何用?因弃之而私心好求安心立命之所。忽绝学捐书,闭户谢友朋,静坐养心,同学大怪之。以先生尚躬行,恶禅学,无有为之者。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 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忽思有亲不事,何学为?则即束装归庐先墓上。同门见歌哭无常,以为狂而有心疾矣。至冬,辞九江先生,决归静坐焉。
这一段言论已是相当的惊世骇俗,若再查原稿本,则更让人惊心动魄!由于这一段话有多处多次修改,其最初的文字已无法完全复原,我推测此段最早之文字为:
……然自是也,日有新思,咸同门(感)骇其不逊,时日有新思,忽思孔子则自以为孔子焉,忽思考据学感(无用)何用,因弃之。(先生尚躬行、恶禅学)而私心好阳明。忽绝学捐书,闭户(静坐养心),谢弃友朋,静坐养心,同学大怪之。以先生尚躬行,恶禅学,无有为之者。(忽思祖父则拟)忽自以为孔子则(笑)欣(笑自)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忽思有亲不事,何学为,则即束装归庐墓上,同门皆以为狂而有心疾矣。至冬,决归静坐矣。(27)
康的修改,抹去了他心中的大秘密,即他自以为是“孔子”之再世!再来看光绪五年中的记载:
以西樵山水幽胜可习静,正月,遂入樵山,居白云洞,专讲道佛之书,养神明,弃渣滓。时或啸歌为诗文,徘徊散发,枕卧石窟瀑泉之间,席芳草,临清流,修柯遮云,清泉满听,常夜坐弥月不睡,恣意游思,天上人间,极苦极乐,皆现身试之。始则诸魔杂沓,继者诸梦皆息,神明超胜,欣然自得。习五胜道,见身外有我,又令我入身中,视身如骸,视人如豕。
由此再与手稿本核对,亦有多处之修改(28)。光绪四年时,康有为二十岁。前一年,他师从朱次琦,入礼山草堂,而终其生对朱次琦尊崇。也就在这学问精深之阶段,康亦处于人生的一个癫狂期。我在这里引用康有为的话,并不是为了探讨康在二十、二十一岁时的真实身体状况,而是为了说明,康在《我史》中使用如此的语言来描绘他人生的癫狂期,不正是可以清楚地看出康在写作期间即光绪二十四年岁暮时的性情与性格吗?康的大弟子梁启超称:
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摇动之。于学术亦然,于治事亦然,不肯迁就主义以徇事物,而每镕取事物,以佐其主义。常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概。故短先生者,谓其武断,谓其执拗,谓其专制,或非无因耶。然人有短长,而短即在于长之中,长即在短之内。先生所以不畏疑难,刚健果决,以旋撼世界者,皆此自信力为之也。(29)
又称:
康“乃至谓《史记》、《楚辞》经刘歆羼入者数十条,出土之钟鼎彝器,皆刘歆私铸埋藏以欺后世,此实为事理之万不可通者,而有为必力持之。实则其主张之要点,并不必借重于此等枝词强辩而始成立,而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 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其在事业上也有然,其在学问上也亦有然”。(30)
前一段话,梁启超说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康已离日本,梁处处为其师回护,然也道出于康为其“主义”而不顾“事物”的个性特点,即只顾其主观之认识,无视于客观之事实。后一段话写于1921年,康当时也健在,尽管师生之间有了一些缝隙,然大体尚还可过得去,一句“万事纯任主观”,将其师的性情与性格表露无遗。而康有为从上海到香港的逃亡途中,英国公使馆中文秘书戈颁(Henry Cockburn)一路陪同,三天中与康有多次谈话,他在随后的私信中说:康“真是个可怜人——一个狂热的人和空想家”(31)。如果由此而解之,康有为在《我史》中的许多张扬与自夸,非其特意造作,似乎是在不自觉之中的天性流露;尽管也有证据表明,他在某些地方是有意为之,故意作伪(32)。
人在顺利的时候,是不太会想到总结人生的;大多是在其经历了大风大雨后,才会回顾过去,做一点记录;而在世态炎凉的感慨之余,也很难指望作者还有保持客观性的自觉。这是人类本身的弱点所致。在一场大灾大难后,能够保持冷静与客观,给后人留下真实的记录,自当受到历史学家们的尊崇;而自我辩护、自我张扬甚至不惜于作伪,历史学家也无须予以太多的道德指责。由此而观,这些情况与康有为写作《我史》时的心情是相一致的。
礼送康有为出日本
戊戌政变时,康有为恰从天津塘沽南下上海,为英人所救,随后英国派军舰护送其搭乘之船前往香港。而就在香港,康有为犯下了他一生中的一大失误。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1898年10月6日)晚,康有为接受香港最大的英文报纸《德臣报》(China Mail)记者的采访(33)。在此次访谈中,康有为对慈禧太后大加攻击,称她只是一个妃子,光绪帝已经认识到慈禧太后不是他真正的母亲;又称光绪帝对其如何信任,夸大其本人在维新运动中的作用。最后,康还称光绪帝已给他密诏,让他去英国求救,恢复光绪帝的权力。在采访中,康有为知道他的谈话将会被发表。
尽管康有为自以为是地认为,他在利用媒体向英国政府求救,但似乎没有想到光绪帝还在北京,正在慈禧太后的掌控中。他的这些内容并不属实的谈话,将会对光绪帝非常不利,恰恰向慈禧太后证明了光绪帝仇恨慈禧太后,且不惜于利用英国以能让慈禧太后下台。若想要真帮助光绪帝,康应该在公开的场合赞颂光绪帝对慈禧太后的忠诚,但他却正好是掉过头来走。这是他政治经验幼稚的又一次表现(34)。
次日,即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二日(1989年10月7日),香港《德臣报》刊出了长篇报道,以英文公布了康有为的谈话。九月初一日(10月15日)上海《字林西报周刊》(North China Herald)刊登了这一篇英文报道,并加上了相关的消息。九月初二日(10月16日),上海的《申报》以中文发表了其中的主要内容。尽管《申报》予以声明“以上乃由西报摘译,其中所有干及皇太后之语,概节而不登”,但任何一个人都能看出光绪帝向康有为表白了其对慈禧太后的不满。九月初五日(19日),上海《新闻报》也刊出了康有为谈话的中文稿。九月初七、初八两日(21、22日),天津《国闻报》也简短报道了康有为谈话的内容(35)。此时,慈禧太后已有废光绪帝之心,刘坤一等大臣为保全光绪帝正尽心竭力。若康有为的谈话内容为慈禧太后所知,将有大不测。
湖广总督张之洞从《新闻报》上看到了康有为的这一谈话,大为震怒。他于九月初十日(10月24日)致电两江总督刘坤一、上海道蔡钧,要求与该报馆及保护该报馆的外国领事“切商”,“嘱其万勿再为传播”(36)。与此同时,张之洞即与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进行交涉,要求日本政府进行干预。此后,小田切万寿之助来到湖北,据他后来的报告称,他与张之洞有“五次会见”。在会见中,张之洞提到了日方所期盼的中日两国军事合作,条件是将康有为等人逐出日本(37)。
康有为到达日本时,日本的政坛已出现震荡。1898年11月8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第一次大隈重信内阁倒台,第二次山县有朋内阁成立。新任外相青木周藏认为清朝的政治已从政变时的混乱转向稳定,主张与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合作。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康有为并没有见到大隈重信、山县有朋、青木周藏等日本政府高层人士,与他打交道的是犬养毅、副岛种臣、品川弥二郎等非实任的政治家,经常交往者为日本外务省中下层官员与大陆浪人。康有为行前所设想的“申包胥秦庭七日之哭”,一无施展之机;反随着大隈的下台,由政府接待改为政党接待。日本陆军方面为了介入中国,也要求外务省答应张之洞的条件。
就在张之洞与小田切商议驱逐康有为的同时,清廷也得到了康有为在香港谈话内容的报告。九月十一日(10月25日),署理礼部侍郎、内阁学士准良看到天津《国闻报》转载的康有为谈话,上奏“报馆刊布邪说请饬查办折”(38)。清廷当日下旨直隶总督裕禄,称:《国闻报》“九月初七日述康逆问答之词,尤为肆逆不法”,“著裕禄派妥员密查明确,设法严禁。此等败类必应拿获惩办,毋得轻纵”(39)。十月初三日(11月16日),清廷下达了一道交片谕旨,暗令刘学询、庆宽赴日,刺杀康有为等人,此后又有一系列的密令(40)。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也得到了密报,并向青木外相作了报告(41)。
12月16日(十一月初四日),日本外务省翻译官楢原陈政背着大隈重信一派,以个人身份访问梁启超,劝康、梁等人离开日本。梁启超对此十分不解,表示拒绝。12月20日(十一月初八日),楢原再次访问梁启超,称李鸿章曾与伊藤博文会见时要求驱逐康有为等人,否则会在外交上产生不快,最好在此之前往美国或英国,旅费由其负责。梁启超对此再一次拒绝。此后,楢原还多次给梁启超写信,要求康、梁等人离开日本。
楢原陈政的工作虽被拒绝,但青木周藏外相则通过康、梁的保护人,实行迂回。他将此事委托伊藤博文,伊藤又将此事交给犬养毅,犬养毅对此提出折中方法,即康离境,梁不离境,另送康旅费。犬养让柏原文太郎去说服梁启超,而柏原正是照顾康、梁起居生活的人(42)。1899年1月19日(十二月初八日),近卫笃麿公爵也出面干预此事。他将梁启超叫到其住处,明确告诉:康有为逗留日本有碍日中两国保持邦交,即使逗留也不易实现他的目的,最好漫游到欧美去(43)。
在此压力下,康有为只能同意离日(44)。
光绪二十四年岁暮康有为写作时的心情
康有为称其写《我史》时间为: “九月十二日至日本,居东京已三月,岁暮书于……”(45)。九月十二日为1898年10月26日,三个月后即十二月十二日,即1899年1月23日,该年的除夕是1899年2月9日,如果以其十天的写作时间来计算的话,那么,似可推测在十二月初八日之后到除夕之间。
康有为写作之期也就是他将被迫离开日本之时(46)。在东京的三个月,并不是康人生的高峰而是其低谷,写《我史》时又恰处于谷底,他的心情之不快是容易想见的(47)。也因为如此,《我史》写了诸多在北京乃至在上海、香港的经历,唯独对长达三个月日本生活却不置一词。最能明显地表达他生活场景与心情状态的,是于此时写的一首诗,题《冬月夜坐》:
门径萧条犬吠悲,微茫淡月挂松枝。
纸屏板屋孤灯下,白发逋臣独咏诗。(48)
夜晚的“门径”本应当是萧条的,而此处的“萧条”似不止是夜晚。犬声就是犬声,从犬声中听出悲哀的,是本心的悲哀。这个时候的他,是寂寥的,是惆怅的,是孤独的,而这种孤独的心情引发出来的,是一种孤芳自赏,是对自己往日英雄史诗般的历程,自我作一番英雄史诗般的舒展。在这种文字的书写中,康有为感到了自我的完美,自我的净化,自我的超然,没有了人人皆有的私念,没有了弥漫于政坛中的种种阴谋,以力图表明自己“以救中国”,乃至于“以救地球,区区中国,杀身无益”的伟大抱负与高尚情怀。在这个冬月夜晚的“纸屏板屋孤灯下”,在这一个“白发逋臣”奋笔中,自我咏唱着已被理想化神圣化纯洁化美丽化的英雄史诗,其名称也起得十分了得非同凡响——《我史》!现实中的屈曲伸发出他意念中的张扬,何等样的高官,何等样的对手,都在他的笔下蜷伏着,而他自身,尽管已经是一个失败者,伤痕累累,却凌凌然于绝顶之上。在这样的场景下写出来的诗歌或可以千古流唱,写出来的散文或可以不朽,然写出来的历史却似不可能是完全可靠的信史,更何况康有为又是一个“万事纯任主观”的人,“一个狂热的人和空想家”。
由此而形成了康有为在《我史》中的第一定理:康是正确的,没有任何错误;是一个神秘政治图谱的发现者,发现了“伪经”,更发现了“改制”;是一个经历灾难而不死的人,仅从北京的逃亡途中“凡十一死”,而“曲线巧奇,曲曲生之”。康在《我史》的尾歌中,激情地唱道:“吾以一身备中原师友之传,当中国政变之事,为四千年未有之会,而穷理创义,立事变法……”,就在这个“纸屏板屋孤灯下”的冬月夜。
由此而形成了康有为在《我史》中的第二定理:康虽然是失败者,但失败的原因是守旧者的阻碍,是当政者未能听从其谋。尽管康还是一个“布衣”、还是一个举人、还是一个进士、还是一个学习主事、还是一个未上任的总理衙门章京,实属微员;但他的对手一开始就很高位:徐桐、孙毓汶、李联英、李文田、徐用仪、刚毅、许应骙、荣禄乃至于慈禧太后本人,与此高位重权人士相争而败,非为人算而只不过是形势使然;对李鸿章、张之洞、翁同龢、张荫桓、廖寿恒、孙家鼐,《我史》也采用了一种略高一等的口气,指责他们未能听从其意,尤其是翁同龢,经常使用下达命令的语气。
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康有为能够成就这一番大事业也属偶然。康的团体,即康党,是一个很小的团体,支持者也不多,力量应当说是很小的(49)。他能够登上政治舞台,很大程度上在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即德国、俄国、英国等国在租借地、借款等方面咄咄逼人的压迫,使清朝感到了极大的压力。在召见康有为的当天,光绪帝也召见了张元济,说了一番颇有感触的话。张在后来的私信中透露:
玉音垂问,仅三十余言。大旨谓外患凭陵,宜筹保御,廷臣唯喏,不达时务(讲求西学人太少,言之者三)。旧党阻挠,部议拘执,帖括无用,铁路当兴。一一皆亲切言之。(50)
也正是光绪帝的这种认识,采用了康有为的一些主张,开始了中国历史上色彩煊斓悲情催泪的一幕——戊戌变法;康有为及其党人由此乘风扬帆,激情浩荡。戊戌变法之失败,当然是由于慈禧太后的政变,但我仍然能够感到,根据康有为派的政治力量,按照康有为派的政改方案,若慈禧太后未在八月初六日发动政变,他们似乎也不可能走得很远……
我也由此找到了解读《我史》的方式:降低康有为的声调,查找他的私念,指出他的错误。这表面上似乎是将康有为“矮小化”,我却以为,这是力图将之还原为“真实”(51)。
“真实”虽是历史学家难以企及的彼岸,但毕竟是他们心中不灭的梦境。
注释:
①《杰士上书汇录》尚未能影印,但目前方便利用的有三个版本。其一为黄明同、吴熙钊编著:《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该书附有《杰士上书汇录》,并标明卷数,总理衙门代奏原折亦照录;其二是孔祥吉编:《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其三是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4集。后两种书收入《杰士上书汇录》和其他康有为代拟的奏议,卷数有所打乱。以上三种版本,文字与标点稍有差异,但不影响使用。
②参见拙文:《〈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阅读报告》,北京:《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
③康有为到达日本时,兵库县知事大森致电日本首相兼外相大隈重信:“康有为一行共七名中国人、两名日本人安全地从河内丸上陆,乘方才6时的火车前往东京。(上述七名支那人是:康有为、梁铁君、康同照、何易一、桑湖南、李唐、梁炜。以上是根据西山警视总监的报告)”(1898年10月25日10时15分发,《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东京: 日本国际连合协会,1954年,第693页)。其中的桑湖南,即为叶湘南之误。繁写体“葉”与“桑”有相似之处。叶湘南颇为康有为所信任,梁启超等留日弟子与革命党人接近,主张孙、康合作,徐勤等人告之康,康即命叶携款赴日本,命梁赴檀香山办保皇会。
④若不含后来所加的标点符号,《我史》的实际字数约三万八千字。
⑤癸酉,即1933年,望日为十五,“望后二日”即十七日,时为1933年12月3日。
⑥韩文举在万木草堂中“助编”《新学伪经考》、《孔于改制考》,曾任万木草堂“学长”。后任湖南长沙时务学堂教习,澳门《知新报》撰述。流亡日本后,协助梁启超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横滨大同学校。民国初年在广州办南强公学、觉是草堂,后留寓香港,有《树园先生遗集》。冯自由在《戊戌前孙康两派之关系》中称“韩文举号乘参”。参,曾参,字子舆。冯又在《康门十三太保与革命党》中称,康有为离日后,梁启超等留日弟子与孙中山越走越近,有合并之意。梁启超等十三人写信给康有为,表示其意。此十三人被称为“十三太保”,其中有梁启超、韩文举、欧榘甲、罗普、罗伯雅5位大弟子。冯还称韩文举“在民国后,隐居乡井,以教读自给,闻今尚生存,年已七十余矣”(冯自由:《革命逸史》,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初集,第47页;第2集,第28~33页)。
⑦戊戌政变后,罗普离开早稻田,随梁启超等编《清议报》、《新民丛报》,并作《日本维新三十年史》等,也是“十三太保”之一(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第31页)。其后参加创办《时报》、《舆论日报》,并应江宁提学使之聘,任图书科长等职。民国建立后,任多职,其中有广东实业厅长、京师图书馆主任,并任职于河北省政府、平汉路、平绥路等。
⑧顾颉刚(1893~1980),江苏吴县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杰出历史学家。1929年任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决计清理旧古史,学术思想上与康相近。顾潮编《顾颉刚年谱》,记:1929年6月16日,“与丁文江去康同薇家。欲作康有为年谱并编康氏遗集,故经丁文江介绍,识康之女儿,与彼商此事”。11月19日,“与冼玉清同到康同璧家,并见康同薇,取康有为稿两包归”。1930年,“是年续理康有为遗稿,点《新学伪经考》。以其遗稿但多政治性文件,非学术文字,十一月交赵丰田整理。彼后以半年之力,成《康长素先生年谱稿》,为其毕业论文”。1931年6月,“审查赵丰田所作《康长素先生年谱稿》毕”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74~175、177、190、194页)。赵丰田在《康长素先生年谱稿》的引用及参考书目中称:“《康南海遗稿》,皆原写稿本而未经整理者。以奉顾先生命为排比年月次第备出版,得见之”(燕京大学《史学年报》第2卷(1934)第1期,香港崇文书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参考资料》第六编,1975年影印本,第67页)。由此可见,顾对此多有介入。然因顾、赵师生关系,顾可能从赵处借得丁文江抄本再抄。
⑨顾颉刚抄本共计119页,抄在“东明号”格稿纸上的,每页上下两面,每面八行,每行二十字。标点注于字旁。顾请了两位书手,一位抄了前92页,另一位抄了后27页。书手姓名不详。
⑩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分指光绪二十一、二、三、四年(1895-1898)。“十八年”系民国十八年即1929年。
(11)徐良早年留学日本、美国。康有为七十岁寿辰时,他奉前清皇帝溥仪所赠匾额、玉如意到上海致贺。溥仪在《我的前半生》叙有徐良事。徐良后任天津中原银行经理,汪伪政府外交次长、驻日本大使等,1943年辞职。
(12)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江苏泰兴人。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创始人之一,先后留学日本与英国。1917年与梁启超同赴欧洲,出席巴黎和会,交甚善。梁去世后,为其编年谱。
(13)赵丰田1931年由燕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毕业论文题目为由顾颉刚指导的《康长素先生年谱稿》。陆志韦、顾颉刚因此将赵介绍给丁文江。丁去世后,赵在翁文灏的指导下,完成了《梁任公年谱》的初稿。
(14)赵丰田:《康长素先生年谱稿》,香港崇文书局影印本,第67页。然而,赵丰田自相矛盾的是,其编年谱仍然有“丙申”一年,其文曰:“讲学于广府学宫万木草堂,以徐勤、王镜如为学长。续成《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春秋学》。七月与有溥君游罗浮,八月游香港,十月至澳门,与何穗田创办《知新报》。穗田慷慨好义,力任报事。先生将赴南洋,未果。复还粤”。并注明其出处为《自编年谱》。赵的这一段文字,与《我史》光绪二十二年基本相同,他可能已用了其师顾颉刚抄本。又,在该文的弁言,赵丰田称:“此为丰田民国二十年所作毕业论文,当时时间仓促,材料缺乏,体例亦未允洽。其后尝多方搜罗,近复辑《梁任公先生年谱》,所得资料,较前文多至一倍有奇……民国二十三年八月十六日书于北平图书馆”。李文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论文室查到了赵丰田的毕业论文之原本,《引用及参考书目》中《康南海自编年谱》一条,文字与刊印本完全相同。由此可知,其刊印本中参考书目《康南海自编年谱》一条,是其先前写的,发表时未及修改。
(15)“戊寅年”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四月初八日”为阳历5月7日。该本抄在春成纸店的稿纸上,《续修四库全书》将之影印出版。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传纪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58册。又,谢巍编撰《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615页)“《康南海自编年谱》(我史)”条下称言,年谱原稿藏于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即指此抄本,将抄本误为原本。
(16)参见马忠文:《康有为自编年谱的成书时间及相关问题》,《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
(17)然究竟是丁文江派人所补还是顾颉刚派人所补,仅看顾抄本,还得不出结论来,但据常理来判断,很可能是顾颉刚所补。因为若由丁文江派人所补,顾抄本应抄在正文,而不是抄在页眉了。这里还不能完全回避一种可能,即顾抄本是完全按照丁抄本的,因丁抄本在页眉而故意抄在页眉。
(1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616、107页。编者也相信了康有为的“更甡七十记”,作书目解题称:“是书系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一年乙未以前所作,叙事至是年为止。原稿在戊戌抄没,辗转落于其门人罗孝高手中。戊戌十二月,作者流亡日本,复将乙未以后事补作而成是编”。
(19)然其内文仍以《康南海自编年谱》为题。该本封面书名与内文书名有一字的差误,我以为,很可能是校对不精而引起的。1973年,该书又重印。
(20)赵丰田《康长素先生年谱稿》,在引用及参考书目中称:“《康南海自编年谱》,丁文江氏副钞本” (香港崇文书局影印本,第67页)。
(21)康文珮编:《康南海先生年谱续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第1页。
(22)《南海康先生传》,北平琉璃厂文楷斋刻印(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图书馆藏本上盖有朱印:“民国二十一年旧历四月八日初版,民国二十一年旧历五月五日再版”,及张伯桢的印章),第57、68页。
(23)此处据顾抄本,《戊戌变法》本该眉批中的“此谱”作“此书”。此中所用的“书”字,并不涉及到书名(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136页)。
(24)朱维铮又称:“《我史》,今刊本题作《康南海自编年谱》。但康同璧《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序称《我史》乃康有为所题原名,今据正,并保留传世刊本名称,作为副题”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康有为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5、812页)。此后罗岗等1999年再编《我史》,也以康同璧语为据。
(25)其中最重要的修改,我已在拙文《〈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阅读报告》(北京:《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中予以说明。
(26)若将康著《我史》与此期梁著《戊戌政变记》相比较,我认为,《我史》的可靠性远远超出《戊戌政变记》。梁在《戊戌政变记》中大量用想像来代替材料,甚至故意作伪,远远超出“真迹放大”的范围,所言许多事情根本不存在。《我史》所言之事,大体存在,只是叙述方式过于自夸,康有意作伪者,仅是少数。
(27)括号内为康有为原删文字,从笔锋、墨迹来看,此为写作时的随时修改。黑体是我所标,以引注目。
(28)我推测其最初的原稿可能为:“以□人慕西樵山水幽胜可习静,正月,遂入樵山,居白鹿洞,历讲道佛之书,养神明,弃渣滓。时或啸歌为诗文,静坐堂,经徘徊石窟瀑泉之间,起坐无□,席芳草,临清流,修柯遮云,清泉满听,□常静坐,弥月不睡,始则诸魔杂沓,继者魂梦皆息,欣然自得”。中间有多处添加。而“习五胜道,见身外有我,又令我入身中,视身如骸,视人如豕。既而以事出城,遂断此学”一段为添加,补在页眉,并在其后删“复以民生多艰,□□我才力聪明,当往拯之”一句。
(29)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87~88页。
(30)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第8册,《专集》之三十四,第56~57页。
(31)戈颁致莫理循,1898年10月19日,《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里循通信集》,上册,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122~123页。以下简称《清末民初政情内幕》。又,戈颁另一中文译名为“贾克凭”。
(32)关于康有为的性情与性格,时人与后人有着许多评论,此处不再一一述之;然我以为,最值得注意的有两条:一是萧公权说:“作为一个不设防的人,康氏自有其缺点与错误,他并不是圣人。他的努力失败,不能说是英雄。虽一度颇受人注目,但情况迅即转变。历史总是以现实的社会与政治标准衡量人。一个先知的预见不能成为事实,便得不到掌声。但是在思想的领域内,现实的裁判并不很相关。康有为的改革与乌托邦思想毕竟对中国思想史有重要贡献”(《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第31~32页)。一是黄彰健说:“一个人目空一世,也往往由于他的学识才干确较普通人高出一筹。这种人的态度虽可厌恶,但当国者却不可以人废言”(《戊戌变法史研究》,第71页)。从中可以看出同情与理解,但是萧、黄两先生如此说,是将康当作思想家来看待,当作建策者来看待,而作为政治家,康的这种性情与性格显然成事不足。《我史》主要是讲康的政治生涯,我为此做鉴注,也不得不坚持对政治家的评价方式,即会对他有更多的批评。
(33)该报道的中文译本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戊戌变法》,第3册,第499~513页。并称:“为我们作翻译的绅士,一位有名的买办……”康有为恰于当天从香港中环警署搬到了怡和洋行买办何东的家中,在采访时担任翻译者,为何东本人。
(34)康有为后来也没有感到其行为的危险性,在向《台湾日日新报》的供稿中,在康党主办的《知新报》中,发表了大量此类言论。他还在日本利用邮件的方式,向国内寄《奉诏求救文》及其编造的谭嗣同遗书、遗言、光绪帝乃至咸丰帝的密诏。到美洲以后,光绪帝仇恨慈禧太后,成为他在海外宣传的主题。他似乎始终未认识到,他的这种“保皇”,实际上恰是“害皇”。
(35)该报并加尾注说明:“以上康主事之言,洋洋数万字,本报不能尽述,只择其要译出。仓猝之间,言词不无诘曲,未暇修削。想阅者必能共谅也”。又,《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再刊《德臣报》报道中康有为觐见时与光绪帝之交谈言论。
(36)《张文襄公全集》,中国书店影印,1990年,第3册,第763页。刘坤一对此回电表示完全同意(同上书,第764页)。刘在致林稗眉信中更明确表示态度:“顷奉惠书并《新闻报》一纸,具见关怀大局,义正词严。此报早经寓目,当饬蔡道照会英领事严行查禁,并将前报更正;该领事亦以为然,可见公道自在人心。该犯用心至毒,为计至愚,此等诬蔑之辞,徒自彰其背叛之罪,不啻自画招供也。西报每谓康党止图变法,并无逆谋,今有此书,正成确证。若因《新闻报》妄缀议论,遂与中报一律查禁销售,转不足以释外人之疑,非徒虑滋纷纭也”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遗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册,第2230页)。九月十三日,上海《申报》刊出梁鼎芬《驳叛犯康有为逆书》,二十四日,《申报》再刊刘坤一《息邪说论》,对康的说法予以驳斥(叶德辉辑:《觉迷要录》,光绪三十一年刊刻本,录三,第1~7页)。
(37)小田切万寿之助通过日本驻汉口领事发电给日本外相青木周藏“张之洞要求我秘密报告日本政府:康有为及其同党在日逗留,不仅伤害了两国业已存在的友好情谊,而且也妨碍他实施诸如由日本军事顾问训练军队的计划,由此应将他们逐出日本……”(1898年12月2日下午9时30分汉口发,3日晚12时30分收到)。青木外相立即对此作出了反应,于6日复电:“交上海代理总领事。你可以答复张之洞:帝国政府甚不愿为康有为及其党人提供政治避难,由于国际惯例,也不可能违背其意愿将其遣送出境;但将尽一切努力以达此目的……”(《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723~724页)。
(38)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部:《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482~483页。准良于八月二十五日接替萨廉,署任礼部右侍郎,该折不见于军机处《随手档》,很可能另有渠道递上。又,是年九月,缪润绂上条陈,所附“钞单”摘录了一些康有为与《德臣报》记者的谈话内容(同上书,第485~487页)。
(39)军机处《随手档》、《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一日。
(40)该交片称:“已革候选道刘学询,著赏给知府衔,已革内务府员外郎庆宽,著赏给员外郎衔,庆宽并准其入内务府汉军旗籍。所有该二员呈请自备资斧,亲历外洋内地考察商务等语,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察核办理”(军机处《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三日)。初六日,又下达谕旨:“知府衔刘学询、员外郎庆宽均署自备斧资,亲历外洋内地,考察商务” (军机处《洋务档》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六日)。二十二日,清廷密旨沿海沿江各督抚:“康有为、梁启超、王照等罪大恶极,均应按名弋获。朝廷不惜破格之赏,以待有功”(军机处《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该密谕为了保密,不用电报,而用“六百里加急”的方式送达各督抚。张之洞收到密旨后,于12月25日发电总理衙门,上报其与小田切万寿之助的密谋,并告:小田切称“令人讽伊自去赴美国,日本政府助以川资”;“近或一两礼拜,远亦不过两月”(《张文襄公全集》,第2册,第363页)。同在二十二日,清廷密电驻日公使李盛铎:“闻康有为、梁启超、王照诸逆现在遁迹日本,有无其事?该逆等日久稽诛,虑有后患。如果实在日本,应即妥为设法,密速办理。总期不动声色,不露形迹,预杜日人籍口,斯为妥善。果能得手,朝廷亦不惜重赏也”(军机处《电寄档》,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41)矢野文雄致青木周藏,第237号电报,称:“各种渠道的报告声称,慈禧太后于12月6日通过总理衙门秘密命令清驻日本公使,运用一切手段将康及其党人捕拿或暗杀”(1898年12月9日发,《外务省记录》1-6-1-4-2-2“光绪二十四年政变、光绪帝及西太后崩御、袁世凯免官”,第3册)。
(42)12月28日,犬养毅致信柏原文郎:“多次不辞遥远造访寒舍,万分感谢。康有为之事与伊藤侯相议。伊藤侯可能转告青木。其要旨是给康有为配备翻译一同前往外国,而王照与梁启超则留在日本。七千元为其旅费。上述事情大概已经谈妥,可领会其意思办理可也。木堂。二十八日。我知此事伊藤乃受青木委托,我已将此事写信给早稻田翁”。同日,又致信大隈:“昨日伊藤侯突然来旅店访问,其目的乃是为康有为一事而来。相议之结果,遂只将康有为一人遣送外国,送其七千日元左右的旅费。但是,伊藤侯的意思是这笔钱应以我们有志者的名义来赠与。上述事情伊藤侯则尽快通知青木外务大臣。我以为上述之事乃青木所托。至于让梁启超留在日本以增长学问之事,晚生也表示赞同。近日康有为谒见阁下时,请酌情将此事相告。草草。廿八日。大隈伯阁下。犬养毅” (转引自永井算已:《清末在日康梁派的政治动静》,见《中国近代政治史论集》,东京:汲古书院,1983年,第1~31页)。而相关的研究除永井算已论文外,又可参见伊原泽周:《由近卫日记看康有为的滞日问题》,《从“笔谈外交”到“以史为鉴”:中日近代关系史探研》,中华书局,2003年;翟新:《东亚同文会与清末变法运动:以应对康、梁派的活动为中心》,《近代以来日本民间涉外活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43)李廷江编:《近卫篤麿と清末要人:近卫篤麿宛来简集成》,东京:原书房,2004年,录有梁启超所写文字,注明1899年1月19日,似为当日的笔谈。其中称:“康先生亦久有一游欧米之志,然所以迟迟者,亦有故。其一以日本同为东方关系之国,利害相同,故深欲使两国社会上之交日亲,以为往欧米之关系,不如贵国,故欲滞贵国也。若欧米之行,于阅历及增长学识,所得甚多,然所以有难者,其中琐琐之故,柏原君略能知之。此行期之所以不能速也。今承明公之相告,想必敝政府有责言,而贵政府有难处之故欤,乞见示”。“盛意敬闻命矣,谨当复命于康先生。即约译人,译人既至,便当西游。至敝邦之事,回复未有豫期。康先生一游欧米一年数月之后,仍欲归滞于贵邦,专讲两邦社会联合之义务,未知可否?”(第48、394~395页)又,近卫此次谈话前,曾与清朝官员邹凌翰、外务次官都筑馨六、外务省翻译官揂原陈政交换过意见;并对梁启超说明,他与大隈商量过。
(44)1899年1月23日,梁启超写信给近卫篤麿,称:“一昨拜谒,承示谆谆,归而述之于康先生。先生深感厚情,即已发邮书电信往上海,与容君同行矣。昨中西、柏原两君来,已面告一切,托达于座下。今更作书奉告,并陈感激之忱。康先生命代笔致候”(《近卫篤麿と清末要人:近卫篤麿宛来简集成》,第49、395页)。“容君”,容闳;“中西”,中西正树,康有为同行译员;“柏原”,柏原文太郎。
(45)康有为是1898年10月25日(即九月十一日)深夜11时半到达东京居所的,称九月十二日也大致不错。
(46)康于1899年3月22日(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十一日)离开日本横滨,日本方面给予旅费,并派中西正树作为翻译陪同其赴美。
(47)陪同康有为从香港到日本的浪人宫崎寅藏,对此评论道:“……他心中暗自有所期许,以为以自己的地位一定会说服大臣(大隈)同情自己,允许派兵牵制守旧派,以便挽回自己的势力的。这种自负心是由信赖心产生的,这是过于相信自己。而这种过信自己的反作用,就变成失望与怨恨,这也是人类自然的道理……过了不久,以前待康先生以上宾的我国人士,对他的为人逐渐感到厌腻而疏远了”(佚名初译,林启彦改译、注释,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局香港分店、花城出版社联合出版,1981年,第148页)。
(48)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文献研究部编:《康有为遗稿·万木草堂诗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98页。以下简称《遗稿·万木草堂诗集》。
(49)除去万木草堂的学生与下层拥护者,我以为,康党在政治上能起作用的核心成员为:梁启超(举人,后给予六品衔)、谭嗣同(候补道,后授军机章京参与新政)、杨深秀(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徐致靖(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学士,后署理礼部右侍郎)、徐仁铸(翰林院编修、湖南学政)、徐仁镜(翰林院编修)、徐仁録(徐致靖之侄)、林旭(内阁候补中书,后授军机章京参预新政)、黄遵宪(湖南盐法道,署理按察使,后改驻日公使,未上任)、李端棻(仓场侍郎,后为礼部尚书),仅此11人,其中李端棻、黄遵宪也未必从命。他的支持者为翁同龢(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尚书,后罢免)、张荫桓(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左侍郎)、张元济(总理衙门章京)、李岳瑞(总理衙门章京)、王照(礼部主事,后为候补四品京堂),然这些人并非会以全力相助。还有许多人反对康有为的思想和学术,但有可能支持他的某些政策,如张之洞(湖广总督)、陈宝箴(湖南巡抚)、孙家鼐(大学士、工部尚书)、李鸿章(大学士、总理衙门大臣)。又,当时的守旧派与维新派在许多地方是权力斗争,而非在政治理念。孙宝瑄在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八日记:“余主持议院之说,询之守旧老儒,每多以为是者。而与喜谈新政诸公言之,反皆目为缓图。余自是不敢薄视旧党”(《忘山庐日记》,上册,第279页)。
(50)张元济复沈曾植书,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八日,张树年、张人凤编:《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97年,中册,第675页。
(51)李云光在其著作中称言: “……康有为的时代已经过去,影响力逐渐消失,不必颂扬,也不必诛伐了。要写文章只有一条可行之道,便是搜集新出的资料,站在一个新的基础上,以求真的态度,朴实的笔法,对他不要擦粉,也不要抹黑,移开那些庄严的法相,还他个有血有肉的世俗之身,写几篇无憎无爱的平淡之文。为历史添几条素材,为国族爱惜一个人物”(《康有为晚年思想及生活新证:康有为家书考释》,香港:汇文阁书店,1979年,第2页)。李云光,康有为之女康同环的女婿。康门后辈,能出此言,欣闻而敬之。
标签:康有为论文; 戊戌变法论文; 日本南海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丁文江论文; 光绪论文; 顾颉刚论文; 康同璧论文; 丁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