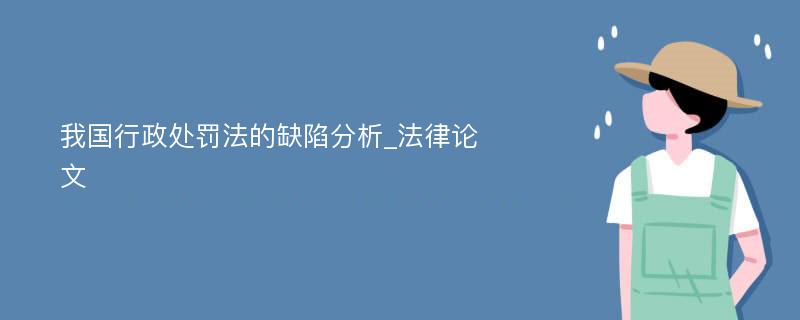
我国《行政处罚法》的缺陷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行政处罚法论文,缺陷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行政处罚的种类和设定
行政处罚法在第一章总则中确定了该法的立法目的和宗旨及基本原则后,在第二章以专章形式规定了行政处罚的种类和设定。此章内容实际上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第8条规定的行政处罚七个种类;而第9条至第14条则是规定行政处罚的设定权限。
首先是行政处罚的种类问题。行政处罚法第8 条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为:(一)警告;(二)罚款;(三)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四)责令停产停业;(五)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六)行政拘留;(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除第(七)项作包容性规定外,前六项均是具体性的,这种以列举方式与包容概括方式并用的形式,在立法技术上不存在大的逻辑纰漏,就我国行政立法的现状而言,也可算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了。但前六项以列举方式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大体上按照我国现有的行政处罚罚则在立法中规定的频率来划分、排列〔1〕, 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行政处罚实施的基本状况,却没有达到制定行政处罚法的根本目的,在实施过程中难免产生大量的“疑难杂症”。
第一,在行政处罚中的人身罚种类上仅以第(六)项规定“行政拘留”而论,有悖于行政处罚法“规范行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立法宗旨。行政拘留是行政处罚法“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中最为严格的一种,应该由也只能由法律设定(第9条)。但从我国目前对人身自由予以限制的处罚措施来看, 行政拘留并不具备此特征。有一种观点认为:195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和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中所规定的“劳动教养”制度,从性质上说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不属于行政处罚,“同时劳动教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需要全面研究,目前不宜在行政处罚法上明确作出规定”〔2〕。笔者认为, 行政处罚法的立法宗旨已明确要规范行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却在最重要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种类上较牵强地回避了亟需规范的“劳动教养”问题,将它解释为一种“行政强制措施”而不作规定,这对行政处罚法实施过程中要规范的前六种处罚种类,尤其是第(六)项“行政拘留”产生了极大的负面作用。因为若是对限制人身自由期限最长为15日的“行政拘留”要予以规范,而却对同样是行政机关可以不经过司法程序即能作出限制人身自由的期限最长可达3年的“劳动教养”决定无须规范, 这岂非容易产生公安机关在执法时规避行政处罚中的“行政拘留”,而趋作“劳动教养”这种“强制措施”的严重问题?“行政拘留”既列为行政处罚之一种,笔者认为“劳动教养”绝非单纯的行政强制措施,从性质、形式乃至程序上的特征看两者均具极相似的内容,立法上不应避重就轻地只限定已较为规范的种类而忽略尚未够规范的种类,否则将严重影响立法的实施甚至带来不良后果。因此,行政处罚法实施后,应当及时总结研究“劳动教养”的经验和教训,力争早日通过立法将之规范化。
第二、在行政处罚中的行为罚种类上新增了“暂扣”许可证、执照的种类,混淆了行政处罚与行政强制措施之间的界限,在实施过程中极易造成凌乱后果。“暂扣”证照,顾名思义,此种措施具有暂时性。在行政处罚的基本原理上,行为罚(也称能力罚)是对管理相对人的行为权进行限制或者剥夺的一种制裁措施〔3〕。 从制裁措施的实质要件分析,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处罚措施均带有限制行为人某种权利实施的作用。但从制裁措施的形式要件分析,则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处罚措施之根本区别在于行政处罚措施往往带有终局性,而行政强制措施却往往是暂时性、非终局性的,行政强制措施对行为人的实质性权利并不一定予以剥夺或限制。如公安交警暂扣违章驾驶车辆的驾驶员所持有的驾驶执照,在暂扣执照期间,被扣证的驾驶员仍可凭暂扣回执驾驶车辆离开违章地点并等候接受处理。因此,“暂扣”许可证或者执照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而不是一种处罚措施,它并无完全限制或剥夺行为人从事某种行为的能力。倘若“暂扣”证照的措施带来限制或剥夺行为权的后果,则“暂扣”与“吊销”除在时间效力上仍可区分外;但对行为人的权利而言却无实质区别。笔者认为,“暂扣”证照的措施若已在行政处罚法中明确为行为罚的一种,则在行政强制措施中则应予以明确排除。否则在行政处罚法的实施过程中仍可能存在“暂扣”证照时以行政强制措施来施行而规避行政处罚的弊端。
第三、在行政处罚的种类之间没有明确“转移罚”的规范,实际执法过程中可能束缚了行政机关正确运用行政处罚措施制裁违法行为职能的充分发挥。在行政执法体制较为合理的国家和地区,立法上通常规定,较轻的行政处罚措施未能有效制裁违法行为,且违法行为人可能变本加厉地实施进一步违法活动时,可依法给予较重种类的处罚甚至科以刑罚的制度。学理上称之为“转移罚”制度。我国《行政处罚法》虽在总则及第7条明确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但对于行政处罚不同种类的轻重顺序及适用时能否“转移”均无规定。笔者认为,在行政处罚法实施之前杂乱无章的行政处罚需要进行严格的限制,不宜扩大或随意加重处罚,但在实施行政处罚法后以法律形式确定处罚种类之间适用规则是完全必要的。行政处罚的种类哪些是单一适用的,哪些是可以有条件合并适用的,其适用条件基本规则有哪些等问题,都应当在立法中明确规范,以避免适用行政处罚的随意性和割裂性,保障行政机关严格实施行政处罚和依法履行职责。
其次是行政处罚的设定权问题。行政处罚法第9条至第14 条分别明确了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国务院部、委规章、省级人民政府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在设定行政处罚上的权限,并明确除此之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处罚。就目前我国立法体系而言,这些规定几乎已足能规限各种层次的行政处罚设定权,但却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遗漏。众所周知,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于1992年至1995年分别通过决定授权深圳市、厦门市、珠海市和汕头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市人民政府制定在特区实施的法规和规章,而这四个市人大和政府根据授权决定制定的经济特区法规和规章并不在行政处罚法第9条至第13 条所列可以设定行政处罚的规范性文件范围内。这一立法遗漏无疑对四个经济特区的法规和规章在探索行政管理的新路子,发挥立法试验方面的作用带来了极大的干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决定中,这四个特区所在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规,市人民政府制定规章,是“根据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遵循宪法的规定以及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行使授予的职权的。行政处罚法是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但其第14条规定“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处罚”是否属于“基本原则”范畴?倘若答案是肯定的,则四个特区的法规和规章均不能设定行政处罚;倘若第14条规定不属于“基本原则”,则四个特区的法规和规章均可设定行政处罚,但设定权的限制定位于第11条、13条“必须在法律、规行政法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呢,还是可以更进一步把第11条和13条的这种限制性规定均不视为行政处罚法的“基本原则”而可予以突破?这一遗漏问题毫无疑问已在极大程度上困扰四个特区所在市的立法机构,更严重的是可能导致这四个特区的行政管理呈现执法依据“窒息”。在行政处罚法颁布实施后特区立法的地位若还无明确的界定,则将导致特区立法的试验场濒临“停产停业”的局面。
二、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与行政处罚的主体资格
《行政处罚法》第15条规定:“行政处罚由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意在界定行政处罚的一般主体资格。但此条规定过于原则,无疑给行政处罚的实施带来了多种理解而易产生歧意。“行政机关”一词在我国宪法的规定中是相对于立法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而言,指的是国务院(宪法第85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宪法第105条)和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政府(宪法第112条)。同时,现行宪法中特别规定的行政机关体系中的“审计机关”(第91、109条)和“公安机关”(第135条)仍用“机关”外,其余均称“部门”。 由于现行宪法中并未完全明确“行政机关”的大范畴,因而使行政处罚法中“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的小范畴也是无法明确的,“行政机关”取得行政处罚主体资格的条件也就更无法明确。有的观点拟从行政机关内是否具有外部管理职能来作为是否具备处罚主体资格的条件之一〔4〕,这从实质意义上无可厚非, 但实际上并不能解决行政机关哪些部门具有处罚主体资格的问题。因为内部管理职能与外部管理职能是相对而言的,且可在法定条件下产生转化。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趋势下,强调行政机关的服务职能将使更多原仅有内部管理职能的部门推向外部化,以外部管理职能作为取得行政处罚主体资格的条件是毫无实际意义的。
更令人迷惑的是,《行政处罚法》第四章“行政处罚的管辖和适用”中开宗明义以第20条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这样我国为数众多的乡、镇一级人民政府是否具有行政处罚的管辖权?仅以同行政处罚法同日实施的行政法规《城市道路管理条例》为例。该条例第6 条规定“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工程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道路管理工作”,这样,镇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违反该条例的违法行为如擅自在人行道上建临时建筑物的行为连给予警告的权力都不具有了。这对于基层人民政府在行政管理上的作用发挥是否限制过严,颇值得深入加以研究。
三、行政处罚的决定和执行
行政处罚的程度分为决定程序和执行程序,在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作出规定,其中涉及的实施问题就更多更复杂了。由于篇幅的关系,本文不可能逐一加以详尽剖析,仅列举一些重要的问题以供研讨。
首先是决定程序。行政处罚的决定程序条文中包括了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和听证程序三节内容,存在的问题也依次递增。
第一、在简易程序中首次出现“执法人员”的概念,但“执法”并非具有严格法律意义的词汇,凡是执行法律的均可称之为执法,则“执法人员”的外延难于确定。
第二、在一般程序中规定:“必要时,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进行检查”。“检查”在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手段,但对于检查的程序要求,行政处罚法却连原则都未加规定,仅在第37条限定了不得少于两人,须出示证件和制作笔录。在实际操作中,调查取证应已涵括检查措施,在该条文中特别列出必要时得依法律、法规进行,是否应有更严格的限制?检查与调查、搜查、巡查又如何区分和界定?
第三、一般程序中还出现“行政机关负责人”的概念,此概念也是颇具弹性的。现行宪法规定“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各部、各委员会实行部长、主任负责制”(第86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实行省长、市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负责制(第105条)。 宪法的这些规定对于理解“行政机关负责人”的概念是否具有决定性意义?行政机关的副职领导人员是否仍属于“负责人”的范畴?行政机关负责人决定行政处罚可否委托副职行使职责?如何委托?等等。仅行政处罚法的一条内容是无法完全解决这些实际操作中存在的问题的。
其次是执行程序。行政处罚法确立了作出罚款决定的行政机关与收缴罚款的机构分离的制度,其意义是深远的。但在实际执行的程序中仍有方法和步骤问题亟待解决,其中最关键的在于决定罚款的行政机关与收缴罚款的机构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明确。《行政处罚法》第46条规定:“当事人应当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指定的银行缴纳罚款。银行应当收受罚款,并将罚款直接上缴国库”。按照这一规定精神,行政机关应当首先指定银行收受罚款,而“指定”银行与作出罚款决定的行政机关是否存在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是由作出罚款决定的机关自行“指定”,还是由某一级政府或由人民代表大会“指定”?被“指定”的银行是一家还是多家,有无数量限制?被“指定”的银行收受罚款时是否应当查验相关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或留存处罚决定书的副本(复印件)?等等,此等程序看似琐碎,但对于明确行政机关、银行和当事人在执行行政处罚决定过程中的权利义务,避免相互推诿责任是至关重要的,否则行政处罚法确立的行政处罚决定机关与收缴罚款的机构相分离的制度就难以落实。
注释:
〔1 〕见汪永清编著《行政处罚法适用手册》, 中国方正出版社1996年4月版,第44—45页。
〔2 〕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行政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讲话》,法律出版社1996年4月版, 第35页。
〔3 〕见汪永清编著《行政处罚法适用手册》, 中国方正出版社1996年4月版,第45页。
〔4 〕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行政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讲话》,法律出版社1996年4月版, 第5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