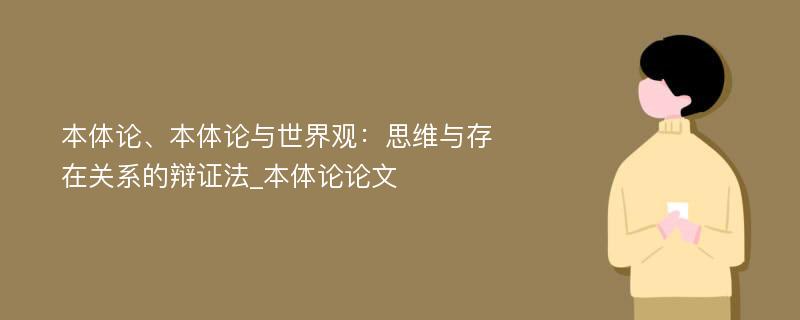
存在论、本体论和世界观:“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辩证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体论论文,辩证法论文,世界观论文,思维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什么是哲学意义的存在论、本体论和世界观?哲学意义的存在论、本体论和世界观与辩证法是何关系?本文试图以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为聚焦点,澄清三者的内涵,厘清三者的关系,进而阐释这三者与辩证法的内在关联。 一、存在论的辩证法或辩证法的存在论 如果我们承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就不能不首先关切什么是哲学意义上的“思维”和“存在”。对“思维”和“存在”的理解,直接关系到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理解;或者反过来说,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理解,直接地取决于对“思维”和“存在”的理解。 1.“存在”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存在”,从概念的外延和内涵上看,是一个最具矛盾性的概念:它的外延是最宽泛的——一切皆在;它的内涵又是最稀薄的—— 一切皆无。外延最宽泛而内涵又最稀薄、一切皆在而又一切皆无的“存在”,被黑格尔解说为“无规定性的直接性,先于一切规定性的无规定性,最原始的无规定性”。(黑格尔,第190页)这种“最原始的无规定性”,显然不是对“存在”本身而言的,而只能是对“思维”而言的,因此,黑格尔在《逻辑学》的开端,用三个“纯”字来解释作为“最原始的无规定性”的“存在”:“纯有”“纯无”和“纯思”。探索哲学意义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不能不首先反思“纯思”对“纯在”的关系。 “存在”作为“一切皆在”,就是“纯有”——没有任何规定性的纯粹的“有”;“存在”作为“一切皆无”,就是“纯无”——没有任何规定性的纯粹的“无”;“存在”作为“一切皆在”和“一切皆无”的“纯有”和“纯无”,就是“纯思”——“先于一切确立性之直接性”的纯粹的“思”。因此,“最原始的无确定性”的“思维”和“存在”,具有自在的“同一性”——“纯有”就是“纯思”,“纯思”就是“纯有”。 黑格尔在《逻辑学》的“开端”,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首先揭示为“纯思”与“纯有”的关系问题,这决不是唯心主义的“臆想”,而是哲学思维的理论自觉,也就是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理论自觉。这种理论自觉,在“开端”的意义上,也就是在黑格尔所说的“最原始的无确定性”的意义上,不仅揭示了人类认识史和个体认识史的“开端”,而且揭示了“思维”的能动性的“开端”,从而为理解“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奠定了“先于一切确定性之直接性”的哲学基础。 作为“最原始的无确定性”,与“纯思”相对待的“纯有”和“纯无”,“纯有”就是“纯无”,“纯无”就是“纯有”,这里的“思”与“在”、“有”与“无”,是“直接同一”的。然而,“思”与“在”、“有”与“无”,这本身不就是“有区别”、“非同一”的吗?因此,在“纯存在”的意义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就构成了一种根本性的矛盾:应该有区别,实际无区别。这个根本性的矛盾,既揭示了人类认识史和个体认识史的“开端”,又揭示了思维的能动性的“开端”,也揭示了作为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开端”。这个“开端”,就是“存在论”的“辩证法”或“辩证法”的“存在论”。 作为人类认识史的开端,“纯存在”所体现的乃是人类思维从无到有(即从动物的意识到人类的思维)的演变过程。在这个演变过程中,人类思维处于萌芽的、潜在的状态。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极其贫乏的,但同时又包含了人类认识运动的所有矛盾的胚芽,所以,以“纯存在”为开端,就是以人类思维的萌芽状态为开端。 作为个体认识史的开端,“纯存在”所体现的乃是个体天赋的思维能力在其未进行具体的认识活动之前的潜在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个体的思维能力作为天赋的生理—心理机能,只是一种单纯的、没有表现出来的认识能力。它的内容和形式也都是极其贫乏的,但是,这种天赋的能力却是其后来的丰富多彩的认识活动的基础。所以,以“纯存在”为开端,又是以个体天赋的思维能力为开端。 “纯存在”所包含的有与无的直接同一,正是萌芽状态的人类思维和潜在状态的个体思维的逻辑表现。在这种状态下,人类已经萌发了区别于动物的思维能力,个体已经在类的遗传中具有了天赋的思维能力,所以说它是“有”;但是,人类形成过程中的思维还没有取得完全独立的地位,个体在遗传中获得的思维能力还没有通过具体的认识活动而显示其现实性,所以又说它是“无”。亦此亦彼,既有又无,这就是“纯存在”这个范畴所表现的人类认识和个体认识的萌芽或潜在状态的本质特征,它蕴含着“思维和存在”的全部“关系问题”的“胚芽”。 2.“在者”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作为“纯有”“纯无”“纯思”的“纯存在”,只是黑格尔所说的“思维”和“存在”的“最原始的无确定性”,也就是没有任何“规定性”和“区别性”的“存在”。对此,黑格尔指出,“我们说在这个世界中一切皆有,外此无物,这样我们便抹煞了所有的特定的东西,于是我们所得的,便只是绝对的空无,而不是绝对的富有了”。(黑格尔,第194页)“所有特定的东西”,都是具有“规定性”和“区别性”的存在,也就是“规定”自己而又“区别”于他者的存在。这就是“在者”。 “存在”被区分为“纯在”(无规定性的存在)与“在者”(有规定性的存在),由此就构成了“思维和存在”的双重关系:一是“思维”与“纯在”的关系,一是“思维”与“在者”的关系。因此,理解“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需要诉诸“思维”与“存在”的双重关系,既不能以“思维”与“纯在”的关系取代“思维”与“在者”的关系,也不能以“思维”与“在者”的关系取代“思维”与“纯在”的关系。“纯在”是“思维”对全部规定性的存在即“在者”的最高抽象。在这种最高抽象中,“在者”被“蒸发”掉了全部的规定性,变成了没有任何规定性的“纯粹的存在”。思维以这种“纯在”为出发点去把握全部的“在者”,具有双重的重大意义:其一是显示了“思维”的最具根本性的“能动性”——在思维中构成全部的具有规定性的“在者”或构成“在者”的全部规定性;其二是显示了“思维”的最具根本性的“现实性”——思维以概念及其逻辑运动展现“在者”及其运动的逻辑。对于这种最高的抽象,马克思作出自己的唯物主义解释:“在抽象的最后阶段,一切事物都成为逻辑范畴”,“正如我们通过抽象把一切事物变成逻辑范畴一样,我们只要抽出各种各样的运动的一切特征,就可得到抽象形态的运动,纯粹形式上的运动,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5-106页)因此,“范畴逻辑运动的根据,就在于它是现实的事物运动的抽象,是以逻辑公式表现出来的事物运动”。(同上,第108页)黑格尔“颠倒”了这个关系,把范畴的逻辑运动引向了“神秘主义”;但是,黑格尔所揭示的“思维”与“纯在”的关系,可以启发我们重新理解“思维”把握和展现“存在”的双重特性:“能动性”和“现实性”。 在“思维”对“存在”的关系中,一切有规定性的存在即“在者”,并不是“自在”的存在,而是“自为”的存在,即被思维赋予内涵(规定性)的存在,即“概念”“范畴”的存在。因此,“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意义上的“思维”对“存在”的关系,就是“思维”对“概念”的关系,就是“思维运动”与“概念运动”的关系。在《哲学笔记》中,列宁在摘录黑格尔关于“理解运动,就是用概念的形式来表述运动的本质”之后,进而作出这样的论断:“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运动,而在于如何在概念的逻辑中表达它。”(列宁,第281页)对此,列宁又引证黑格尔的话说,“从来造成困难的总是思维,因为思维把一个对象的实际上联结在一起的各个环节彼此分隔开来考察”。(同上,第285页)因此,列宁在“辩证法是什么”的标题下作出如下的论断:“概念之间的对立面的同一。”(同上,第210页)列宁还特别强调地指出,概念、范畴并不是认识的“工具”,而是人类认识的“阶梯”和“支撑点”。正是在概念、范畴的辩证发展中,才实现了“思维和存在”的历史性的统一。这表明,列宁不仅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上理解“存在”,也不仅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上理解把握“存在”的“概念”,而且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上实现了“辩证法”与“存在论”的统一。在黑格尔、马克思和列宁的意义上,“存在论”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的辩证法。离开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反思,就构不成哲学意义的“存在论”。 3.“此在”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对“存在”的分析表明,思维所把握的“存在”具有双重含义:一是赋予规定性的存在,它就是“在者”;二是没有规定性的存在,这就是“纯在”。前者构成思想的内容,后者则是作为“纯思”的抽象力。然而,无论是构成思想内容的“在者”,还是作为“纯思”的“纯在”,都意味着有一个特殊的“存在”:意识到存在的存在——具有自我意识的存在,向存在发问的存在。借用海德格尔的说法,这就是“此在”。 海德格尔提出,如果我们要探寻“存在”,就必须首先向自己发问:“我们应当在哪种存在者身上破解存在的意义?我们应当把哪种存在者作为出发点,好让存在开展出来?出发点是随意的吗?抑或在拟定存在问题的时候,某种确定的存在者就具有优先地位?这种作为范本的存在者是什么?它在何种意义上具有优先地位?”(海德格尔,1987年,第9页)对这个问题,海德格尔的回答是:“观看、领会和理解、选择、通达,这些活动都是发问的构成部分,所以它们本身就是某种特定的存在者的存在样式,也就是我们这些发问者本身向来所是的那种存在者的存在样式。因此,彻底解答存在问题就等于说:就某种存在者——即发问的存在者——的存在,使这种存在者透彻可见。……这种存在者,就是我们自己向来所是的存在者,就是除了其它存在的可能性外还能够发问存在的存在者,我们用此在这个术语来称呼这种存在者。”(海德格尔,1987年,第9-10页)海德格尔的设问与回答表明,他所规定的在存在论上具有优先地位的“此在”,就是意识到自身存在的存在,也就是人的存在。 “此在”不是某个个体的存在,而是“类”的存在。在论述“我”的时候,黑格尔说:“就思维被认作主体而言,便是能思者,存在着的能思的主体的简称就叫作我。”(黑格尔,第68页)对于作为主体的“我”,黑格尔又进一步提出,“因为每一个其他的人也仍然是一个我,当我自己称自己为‘我’时,虽然我无疑地是指这个个别的我自己,但同时我也说出了一个完全普通的东西”。(同上,第81页)这就是说,“我”作为独立的个体的存在,“我”就是我自己;“我”作为类分子而存在,“我”又是我们。“我”是个别与普遍的对立统一。 “我们”的存在,使“存在”区分为“主体”的存在与“客体”的存在。主客体关系的存在,是以人作为主体的“此在”的存在为前提的。这就是主体之于客体的逻辑上的先在性。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曾极为深刻地指出:“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说来,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5页)这就是说,“关系”之所以作为“关系”而存在,必须以“我”的存在为前提,必须在“我”的自我意识中构成主客体关系。这种主客体关系,就是“此在”对“存在”的关系,也就是“我们”的“思维”对“存在”的关系。这表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就是现实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就是现实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辩证法。 主体对客体的关系,是以主体的逻辑上的先在为前提的。在主客体关系中,“思维”对“存在”具有逻辑的先在性:存在作为思维的对象,是被思维把握到的存在。既包括具有规定性的“在者”,又包括没有规定性的“纯在”。思维对存在的规定性即对“在者”的把握是一个不可穷尽的过程,而思维对没有规定性的存在即对“纯存在”的把握则意味着思维和存在的统一的无限的可能性——思维自身所具有的能动性。思维以自身的能动性把握存在,是实现思存统一的内在根据;思维把存在把握为具有规定性的存在,则必须诉诸创造和变革概念、范畴的历史过程,以概念、范畴作为认识的“阶梯”和“支撑点”,不断地拓展和深化对存在的规定性的认识。黑格尔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视为“全体的自由性”与“环节的必然性”的统一,并以概念辩证法展现思维和存在从“自在”到“自为”再到“自在自为”的统一,在其合理性上,就是思维的能动性与认识的现实性的统一。通过对“存在”、“在者”和“此在”的反思与分析,我们应当得出的基本认识是:哲学意义的“存在论”,既不是单纯的关于“纯在”之论,也不是单纯的关于“在者”之论,而是以“此在”的逻辑上的先在性为前提所构成的“思维”对“存在”的双重关系:一是揭示思维“能动性”的思维对存在的关系,一是揭示思维“现实性”的思维对在者的关系。这两种关系实现为“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本质上则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哲学意义的“存在论”,就是以“存在”为反思对象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辩证法。 二、本体论的辩证法或辩证法的本体论 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中,思维的能动性,不仅在于它不断地构成关于“在者”的规定性,而且在于它总是追究“在者”何以存在的根据,总是指向“此在”何以存在的根据。正是这种“追究”和“指向”,显示了哲学意义的“存在论”的一种特殊内涵——本体论。 这样提出问题,有强烈的针对性。在当代哲学中,关于“存在论”与“本体论”的关系,有这样两种值得关切的观点:一种是把“存在论”等同于“本体论”,以“存在论”之名而阐述“本体论”;另一种则是把“存在论”与“本体论”对立起来,以“存在论”之名而讨伐“本体论”。然而,这两种似乎截然相反的观点,却隐含着一系列未揭示出来的共同的前提。 首先,“本体”是“有”还是“无”?在当代哲学中产生广泛而深远影响的奎因的观点,表明了讨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奎因提出,关于本体论问题,必须分为“本体论事实”与“本体论承诺”这样两个问题,前者是“何物存在”的问题,后者则是“我们说何物存在”的问题。在通常的解释中,认为离开后者而讲前者,就是离开认识论的本体论,因而是独断论的本体论;以后者为前提而讨论前者,就是以认识论为基础的本体论,因而是达到了“没有认识论的本体论为无效”的理论自觉。然而,我们对奎因提出的问题是:无论是“何物存在”还是“说何物存在”,这里的“何物”究竟是什么?“何物”是有规定性的“在者”,还是没有规定性的“纯在”?如果“何物”就是“在者”,它在什么意义上是“本体论”?如果“何物”是指“纯在”,它又在什么意义上是“何物”?毋庸置疑的是,奎因所说的“何物”,就是有规定性的“在者”,而不是无规定性的“纯在”。在奎因这里,作为“本体”的“存在”,并不是哲学反思所构成的存在,而只是日常语言中的存在。奎因把常识的存在与哲学的存在混为一谈,因而也把“存在”与“本体”混为一谈了。 作为“本体”的“存在”,并不是存在着的“在者”,而是作为“纯思”的“纯在”。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海德格尔极为深刻地揭示了这个问题。他的问题是:“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海德格尔,1996年,第3页)海德格尔在这里所说的“无”,按照他本人的解释,主要包括三层含义:一是涵括“现在的现成存在者”“以往的曾在者”和“未来的终在者”;二是追问“在者由何根据而来”“在者处于何根据之上”和“在者照何根据行事”;三是“唯有一种在者,即提出这一问题的人,总是不断在这一追问中引人注目”。这就是说,海德格尔所说的“无”,就是“提出这一问题的人”对“在者”的“根据”的“追问”,而不是“在者”的“存在”。在海德格尔这里,“本体”不是“有”而是“无”,不是“在者”之“在”,而是“在者”之为“在者”的“根据”。因此,本体论是并且只是关于“何以可能”的哲学理论。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人为何要追究作为“无”的“本体”?人是现实的存在,人的认识对象都是具有规定性的存在,人与世界的现实关系只能是“此在”与“在者”的关系,而不是“纯思”与“纯在”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就是“思维和存在”如何统一的问题,也就是“构成思想”的问题。然而,人类是以思维的能动性而实现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对“思维”本身的追问,就构成了思维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的反思,就构成了反思中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这个“关系问题”中,成为“问题”的就不是“存在”的“规定性”,而是思维把握存在的“根据”。因此,在作为本体论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中,“在者”被彻底地抽象了,变成了“存在”何以存在的“根据”。 其次,“本体”是不是“本原”或“本质”?“本体论”是不是“本原论”或“本质论”?在哲学史上,追寻“本体”有两种最基本的思路:一种是寻求万物所由来和万物所复归的“始基”和“基质”,这是把“本体”视为“本原”的路子;另一种则是寻求现象背后的本质,从逻辑关系上把“本体”视为“本质”的路子。前一种路子试图以某一种“在者”而解释全部的“在者”,也就是以一种特殊的存在而解释全部的特殊的存在,这就必然转向以“质”的同一性而解释“量”的多样性,因此必然导致第二种路子——把“本质”作为“本体”。反思这两种“路子”会发现,把“本质”作为“本体”的“本体论”,有三个根本性的思想前提:其一,就其思想本质来说,是把存在本身同存在的现象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认为经验观察到的现象并非存在本身,存在本身是那种隐藏在经验现象背后的超验的存在;其二,就其思想原则来说,是把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对立起来,把哲学所追求和承诺的“本体”视为某种超出人类或高于人类的本质、与人类的历史状况无关的自我存在的实体,力图剥除全部主观性,归还存在的本来面目;其三,就其追求目标来说,是把绝对与相对分割开来,企图从某种直觉中把握了的最高确定性即作为支配宇宙的最普遍的原则或原理出发,使人类经验中的各种各样的事物得到最彻底的统一性解释,从而为人类提供一种终极的永恒真理。 从上述三个思想前提可以看到,以追究“本原”或“本质”为本体论的哲学模式,是由于把本质与现象分离开来、主观与客观割裂开来、相对与绝对对立起来而产生的。它的实质,是要求哲学为人类揭示出宇宙的绝对之真、至上之善和最高之美。这就是传统哲学关于“存在本身”的“本体论”。由于近代哲学的发展,以探寻存在本身为理论硬核的本体论哲学模式,被以反省人类认识为理论硬核的认识论哲学模式所取代;以追求纯粹客观性为目标、并把主观性与客观性绝对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被探索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如何统一的辩证法理论所扬弃。独立存在的本体论哲学及其所代表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已经被德国古典哲学及其所代表的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所否定。批判地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以及实践基础上的人类认识活动,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人类所获得的全部认识成果,包括哲学层面的本体论追求,总是具有相对的性质;但同时,人类的实践和认识又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总是向着全体自由性的目标迈进。恩格斯明确地指出,以人的实践为基础的人的思维,是“至上”与“非至上”的辩证统一,“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6页)哲学的本体论追求正是植根于人类思维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即植根于人类思维的“至上”性。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否定传统本体论占有绝对真理的幻想,但并不拒绝基于人类实践本性和人类思维本性的本体论追求。 在对哲学本体论的理解中,值得深思的问题是,“本体”的寻求即是矛盾。“本体论”指向对人及其思维与世界内在统一的“基本原理”的终极占有和终极解释,力图以这种“基本原理”为人类的存在和发展提供永恒的“最高支撑点”,而人类的历史发展却总是不断地向这种终极解释提出挑战,动摇它所提供的“最高支撑点”的权威性和有效性,由此构成哲学本体论与人类历史发展的矛盾;“本体论”以自己所承诺的“本体”或“基本原理”作为判断、解释和评价一切的根据、标准和尺度,从而造成自身无法解脱的解释循环,因此,哲学家们总是在相互批判中揭露对方的本体论的内在矛盾,使本体论的解释循环跃迁到高一级层次,这又构成哲学本体论的自我矛盾。在现代哲学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去看待哲学,哲学的“本体论”就发生了真正的革命:人类在自身的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判断、解释和评价一切事物并规范自己思想和行为的“本体”观念,既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性,又是一种历史的局限性,因而它孕育着新的历史可能性。这深切地表明,“本体”作为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根据和标准,它永远是作为中介而自我扬弃的。 “本体论”不是关于“在者”的学问,而只是一种“追问”:对“在者之在”、“是其所是”、“何以可能”的追问。对“本体”的追问和追寻,是人类思维的追根溯源的意向性追求,是人类为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寻求根据、标准和尺度的不懈追求。因此,作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本体论”,它的“指向”和“追求”具有双重意义:既是以“思维”的“至上性”去追寻和构建规范人的全部思想和行为的“最高的支撑点”,又是以“思维”的“至上性”去反思和批判它所构建的“最高的支撑点”。这就是本体论批判的辩证法。 三、世界观的辩证法或辩证法的世界观 在哲学研究中,人们不仅经常不加区别地使用“存在论”和“本体论”,而且经常不加区别地使用“存在论”“本体论”和“世界观”,或者把“世界观”解说为“存在论”,或者把“世界观”解说为“本体论”。厘清“世界观”与“存在论”“本体论”的关系,对于深入理解“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从而深切把握哲学的特殊理论性质和独特社会机能,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 “世界”不等于“存在”。“世界”是有规定性的存在,而不是无规定性的“存在”。“存在”,可以是区分为无规定性的“存在”与有规定性的“在者”;“世界”,则必须以某种规定性为标准而区分为各类不同的“世界”。这是“世界”与“存在”的原则性区别。“世界”是规定性的存在,因而是具有特定内涵的观念。由“存在”的观念而转换为“世界”的观念,“存在”就由“纯思”而转换为被思维把握到的存在、被思维赋予规定的存在、被思维划分为“界”的存在。“世界”是“有界”的,而“存在”是“无界”的。“有界”的“世界”,被区分为不同的“世界”。 一是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这是最通常的对“世界”的二分法。在这种划界中,把“存在”区分为“物质”的存在和“精神”的存在。然而,在这种以“物质”和“精神”来划界的“世界”观念中,有两个重要问题是必须予以反思的:其一,“物质”的规定性。在常识的观念中,“物质”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个意义的“物质”,也就是常识观念中的“存在”。与常识观念不同,自然科学的“物质”观念,是指物质的基本形态、构成要素和层次结构。这个意义的“物质”,仍然是经验的对象,但却是以各种实践方法、手段为中介而构成的经验对象。与经验常识和经验科学不同,哲学观念中的“物质”,是对“精神”之外的“在者”的最高抽象。对此,列宁作出了最为明确的回答:“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它的“客观实在性”。上述分析表明,在常识的、自然科学的和哲学的观念中,“物质”作为人类把握世界、构成思想的基本观念,各有不同的规定性。在不同的视域中对“物质世界”作出不同的“划界”,而又在视域融合中对“物质世界”形成不同层次的基本观念,才能恰当地以“物质”观念构成关于“物质世界”的思想。其二,“精神”的规定性。与“物质”相对待的“精神”,通常指的是“意识”,即“意识”是人脑这种特殊“物质”的机能和属性,也是“物质”在人脑中的“反映”。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意识”的“精神”就是“观念”的存在,而“观念的东西不过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2页)作为“观念的东西”,既包括观念的形式,又包括观念的内容。从观念的形式上看,“精神”包括感觉与知觉、表象与抽象、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联想与想象、直觉与逻辑等多样形式;而“精神”作为“社会意识”,则又包括宗教、艺术、科学、哲学等多种“社会意识形式”;由不同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观念内容,又构成人的“神话世界”“宗教世界”“艺术世界”“科学世界”和“哲学世界”。人的“精神世界”是“意义世界”,并以对象化的实践活动而构成“文化世界”。“文化世界”已经不再是“物质”与“精神”二分的两个世界,而是与“自在世界”相区分的“属人世界”。 二是自在世界与文化世界。这是以人对世界的关系所划分的“世界”。所谓“自在的世界”,既因为它外在于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存在,更因我们在这里还没有从人对世界的关系去看世界。一旦从人对世界的关系去看世界,世界,就成了人的“对象世界”,就成了人的“世界图景”。“世界图景”,是世界显现给人的图景,是人以自己的方式把握到的图景,也就是人在自己的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关于世界的图景。人的关于世界的图景,当然是关于“自在世界”即世界本身的图景;但是,人的关于世界的图景,却只能是人以自己把握世界的各种方式为中介而形成的关于世界的图景。因此,人的“世界图景”具有不可或缺的双重内涵:其一,“世界图景”是关于世界本身的图景,而不是虚构的图景;其二,“世界图景”并不是“自在的世界”,而是人以自己的方式所形成的关于世界的图景。这表明,人类形成怎样的“世界图景”,是同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密不可分的;只有搞清楚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才能懂得人类关于世界的图景。因此,“世界图景”意义上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又必须引入“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基本方式”的问题。 “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就是人类把“自在世界”变成自己的“世界图景”的方式,最为直接地是为人类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日新月异的“世界图景”,即常识的、宗教的、艺术的、伦理的、科学的和哲学的“世界图景”。人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去看世界,都会形成各种不同的“世界图景”。在“常识的世界图景”中,我们会看到一种源于经验而又适用于经验的“世界图景”:在“宗教的世界图景”中,我们会看到一个与“现实世界”“世俗世界”“此岸世界”相分裂的“天国世界”“神灵世界”“彼岸世界”;在“艺术的世界图景”中,我们会看到一个“诗意的”“审美的”“象征的”世界;在“伦理的世界图景”中,我们会看到一个充满“矛盾”而又趋于“和谐”、相互“冲突”而又显示“秩序”的世界;在“科学的世界图景”中,我们会看到一个首尾一贯、秩序井然的“符号系统”和“概念框架”所表述的世界;而在“哲学的世界图景”中,我们会看到人为自己的思想与行为所悬设的诸种“前提”“根据”“尺度”和“标准”。由人类把握的各种基本方式而构成的作为“文化世界”的“世界图景”,显示了“思维”对“存在”的复杂的矛盾关系。 三是人类生活的“三重世界”。人类以自己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为中介而与世界发生关系,不仅仅是为人类提供了“丰富多彩”和“日新月异”的世界,而且是使人自己生活于“三重世界”之中。人的实践活动把世界“分化”为“自在的世界”与“自为的世界”、“自然的世界”与“属人的世界”。人类不仅仅是生活于“自然世界”之中,而且生活于自己所创造的“文化世界”和“意义世界”之中: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同其他生物一样生存于“自然世界”;人作为超越自然的社会存在物,生活于自己所创造的“文化世界”;人作为社会—文化存在物,既被历史文化所占有,又在自己的历史活动中展现新的可能性,因而又生活于历史与个人的视域相融合的“意义世界”。“自然世界”“文化世界”和“意义世界”,就是人类生活的三重世界。人类生活的三重世界,把“有界”的世界区分为三类“在者”,也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区分为三种基本关系:(1)思维与“自然世界”的关系;(2)思维与“文化世界”的关系;(3)思维与“意义世界”的关系。由此所构成的就是现实化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辩证法。 四、存在论、本体论和世界观:“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辩证法 哲学意义的存在论、本体论和世界观,是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为聚焦点所构成的辩证法理论。离开存在论、本体论和世界观,辩证法就会沦为无内容的方法;离开辩证法,存在论、本体论和世界观就会成为相互割裂的实证知识。 哲学问题,说到底是“人之为人”的问题,也就是“此在”何以存在、如何存在和应当怎样存在的问题。这就是哲学意义的“存在论”。构成“存在论”的前提,是人的“存在”的特殊性——人的“思维”对“存在”的“反思”。因此,“存在论”并不是离开“思维”的“存在”问题,而恰恰是在思维的反思中所构成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由此我们可以对“存在论”作出三点初步的规定:其一,存在论是思维以存在为对象的反思,离开反思的自觉就构不成哲学意义的存在论;其二,思维反思存在的存在论,它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离开这个“基本问题”就构不成哲学意义的存在论;其三,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为“基本问题”的存在论,是反思思维与存在的矛盾关系,离开辩证法就构不成哲学意义的存在论。因此,“存在论”就是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辩证法。在《逻辑学》中,黑格尔把存在论的辩证法展现为思维和存在由“自在”到“自为”再到“自在自为”的辩证运动,展现为由“存在论”到“本质论”再到“概念论”的辩证发展,由此构成了黑格尔的存在论、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一致”的辩证法。 人的“存在”的特殊性,直接地体现为“思维”的能动性。思维的能动性,不仅体现在思维对存在的“肯定”,也就是在思维的运动中获得越来越丰富的“规定性”,而且体现在思维对存在的“否定”,也就是在思维的运动中不断深入地追究存在的“可能性”。追究存在的“可能性”,就是追究“规定性”的“根据”,就是追究思想构成自己的“前提”。思想构成自己的“根据”或“前提”,既不是“无规定性”的“纯在”,也不是“有规定性”的“在者”,而是“隐匿”于思想之中的“存在”。它制约和规范人们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但却是思想中的“看不见的手”和“幕后的操纵者”。思想中的这个既是“有”又是“无”的“存在”,就是“本体”的“存在”——规范人的全部思想和行为的“存在”,作为人的全部思想和行为的根据、标准和尺度的“存在”,也就是构成思想的前提的“存在”。因此,“本体论”不是关于思维规定的“存在论”,而是反思思维规定的“存在论”;不是“肯定性”的“存在论”,而是“否定性”的“存在论”;不是“现实性”的“存在论”,而是“理想性”的“存在论”。这种“反思性”“否定性”“理想性”的“存在论”,不是一般意义的“对思想的思想”,而是特殊意义的“对思想的前提批判”。“对思想的前提批判”,构成哲学意义的“本体论”,构成哲学意义的本体论批判的辩证法。 思维的“能动性”,集中地体现在“人给自己构成世界的客观图画”。这个“客观图画”,被称为哲学的“关于整个世界”的“世界观”。然而,在对“世界观”的理解中,却必须深切地思考两个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其一,不能“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世界观”,而必须“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去理解,把“世界观”理解为思维与存在辩证运动的产物;其二,不能只是从“现实性”,而且必须从“可能性”去理解世界观。“世界”不仅是作为思维所把握到的“在者”而存在,而且是作为思维的目的性要求的“非存在”而存在。这是思维的“现实性”与“可能性”的对立统一,更是思维的实践基础的“现实性”与“可能性”的对立统一。人是现实的存在,但“人之为人”的特殊性就在于,人是把“理想”变为“现实”的存在,把“现实”变为“理想”的存在。这是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的统一,也是思维对存在的否定性的统一。 因此,哲学意义的“世界观”就不只是反思存在的“存在论”,而且是反思“思想前提”的“本体论”。这个“世界观”,是“此在”的人生在世和人在途中的人的目光。它是把理想变为现实的人的目光,也是把现实变为理想的人的目光。作为“人的目光”的“世界观”,它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它的实质性的理论性质是“存在论”和“本体论”的统一,它的根本性的社会功能是引导人们“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否定的理解”,从而为人类的理想性追求敞开广阔的和开放的思想空间。哲学意义的存在论、本体论和世界观,就是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为实质内容的辩证法;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为聚焦点去透视哲学意义的存在论、本体论和世界观,才能深切地理解以辩证法为实质内容的哲学。标签:本体论论文; 存在论论文; 能动性论文; 黑格尔辩证法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世界观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论文; 唯物辩证法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海德格尔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 现象学论文; 思维模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