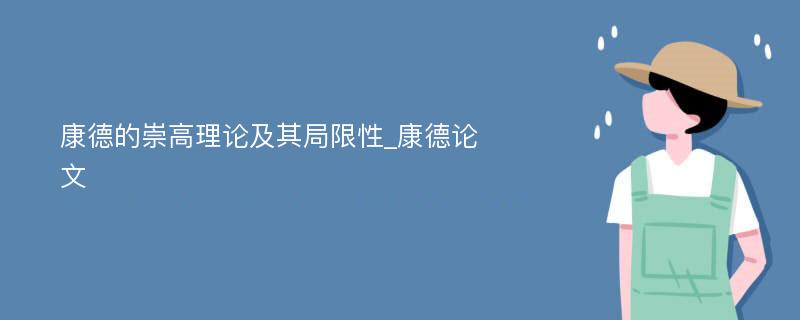
康德的崇高理论及其局限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康德论文,局限性论文,崇高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513(2003)02-0005-05
康德的崇高理论在美学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康德以其特有的哲学沉思,在柏克的基础上,把崇高理论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程度。正是因此,康德的崇高理论在其后一度成为西方崇高理论的主流。学习康德的崇高理论是非常必要的,甚至是必须的。但时代既然已经发展到今天,就为我们了解崇高理论提供了更多的资料,这样就具有了对历史上的崇高理论进行比较的更多的可能性。本文正是试图把康德的崇高理论放在历史的序列中来理解,以期更恰当地理解这一理论——它的理论要点,它的成就,它的不足,这种不足的原因,它在崇高理论发展历史中的位置等等。经过这样一些考察,有助于我们把握康德的崇高理论及其局限性。下面就谈谈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康德崇高理论的要点
康德崇高理论的要点有五个方面:关于能给人崇高感的客体,关于能得到崇高感的主体,关于客体与主体的关系,关于形成崇高感的过程,关于得到崇高感后的效果等五个方面的理论。在第一个方面,康德的客体指自然事物,尤其指自然事物的物理性质,这个特点从康德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具体说来,自然事物的物理性质表现为体积的大或威力的强,由此他分崇高为数学的崇高和力学的崇高。康德的能得到崇高感的主体指的是有相当文化修养和意志能力的主体,即理性的主体。他说:“心意对于崇高的情调要求着心意有一对于诸观念的感受性……事实上,若是没有道德诸观念的演进发展,那么,我们受过文化陶冶的人所称为崇高的对象,对于粗陋的人只显得可怖。他将大自然在破坏中显示暴力的地方,在它的巨大规模的威力面前,他自己的力量消失于虚无时,他看到的将只是艰难,危险,困乏,包围着深陷在里面的人们。”[1](P105)只有有理性和意志能力强的人才能在观念中抵御感官中的暴力,否则就会被这威力吓倒,康德是很强调主体的理性能力的。
在主客体关系方面,自然客体是作为人的对立面而出现,给主体以恐惧、惊骇等痛感。他举例说:“高耸而下垂威胁着人的断岩,天边层层堆叠的乌云里面挟着闪电与雷鸣,火山在狂暴肆虐之中,飓风带着它摧毁了的荒墙……诸如此类的景象,在和它们的较量里,我们对它们的抵拒的力量显得太渺小了。”[1](P101)这类事物使人感到可怕,作为人的对立面而出现,给人以感官上的痛感,但经历一个“暗换”的过程后却能体会到崇高,就是说,主体虽不能在感官中,但能在观念中把握、战胜客体,得到胜利的喜悦,于是主体经历了由痛感转化为快感的过程。对这个过程康德有详细论述。在列举了种种可怕的景象后,康德就接着指出:“但是假使发现我们自己却是在安全地带,那么,这景象越可怕,就越对我们有吸引力。我们称这些现象为崇高,因它们提高了我们的精神力量越过平常的尺度,而让我们在内心里发现另一种类的抵抗的能力,这付与我们勇气来和自然界的全能威力的假象较量一下。”[1](P101)“崇高情绪的质是:一种不愉快感,……这不愉快感在这里却同时是作为合目的的被表象着:这是因此而可能的,即那自己的无能发现着这同一主体的意识到它自身的无限制的机能(即通过无能之感发现着自身的无限能力)。”[1](P99)“对象将作为崇高而用愉快来欣赏着,这愉快却是由不愉快的媒介才可能的。”[1](P100)最后的效果是主体理性力量得到了增强,主体在观念上得到了提升。在对崇高的分析中康德多次表达了这一意思:崇高不存在于自然的事物里,而只能在我们的观念里寻找。“真正的崇高只能在评判者的心里寻找,不是在自然对象里。……谁会把杂乱无章的山岳群,它们的冰峰相互乱叠着,或阴惨的狂野的海洋唤作崇高呢?但是心情感到在它的欣赏里自己被提高了。”[1](P95)“所以,自然界在这里称作崇高,只是因为它提升想象力达到表述那些场合,在那场合里心情能够使自己感觉到它的使命的自身的崇高性超越了出来。”[1](P102)归为一句话:崇高的效果不是在自然客体上发现了崇高的因素,而是主体的理性能力的自我欣赏和提高。
二、康德崇高理论的局限
康德的理论受到了柏克的很大影响,又有很多不同。相比之下,康德把柏克的崇高理论的客体涉及很多方面,包括社会、自然、艺术等方面缩小为仅关于自然的物理性质方面。在主体方面,理性的力量更突出了。在关系、过程、效果方面则和柏克很相似,区别只在于康德更为强调理性。康德因此在前人基础上达到了相当的深刻性。但同时也正是由此而具有了局限性。下面将谈谈这一理论的不足之处。
首先,在关于客体方面,康德仅以自然物的物理性质来作为谈论崇高的客体是远远不够的。崇高的客体还有很多。柏克的崇高客体不限于自然事物,他曾以社会事物和艺术形象作为谈论崇高的客体。在社会事物方面他以专制政府,异教徒的寺庙为例说:“建立在人们的情感,主要是恐怖情感之上的专制政府,不使自己的领袖在公开场合露面”[2](P116),给人以一种可怖的神秘性。同样,在异教徒的寺庙里,它们的偶像都立在黑暗之中,也具有可怖的神秘,在诗歌中,维吉尔和密尔顿诗歌中的魔鬼或冥界君王由于其可怖性,也具有崇高的性质。
不但如此,形体不大,威力不猛的动物,人为物和人本身都可能成为崇高的客体。屠格涅夫散文《麻雀》中为保护幼雀不惜牺牲生命的老雀,伴随遇难主人而去始终忠诚如一的狗都给人以崇高感。这是什么原因呢?作者分析说:“这麻雀会被认为是崇高的,那么是什么使它成为崇高的呢?答曰:完全不是它躯体的庞大,而是它的爱和勇气。……这爱和勇气的异常伟大,不单靠爱和勇气的质,还靠质中的量,这正是崇高之所在。……小小的麻雀因超过或压倒大而来的崇高,毫不亚于苍穹和大海的崇高。然而这不是范围的大,而毋宁说是力量的大,在这种情况里,是一种精神力量的大。诗云:‘爱的力量比死大,完全压倒了使其忍痛离开的本能。’司各特和华兹华斯诗歌中的狗也是这样,它的主人在享维思的山崖中遇难,三月之后,它也在其主人的尸体旁被发现了。诗云‘昼夜抚育相伴,岂忘爱之崇高?情感力量化血肉,伟大谁能料想?’”[3](P44-45)在这里,形体不大,威力不猛但道德力量很高的麻雀和狗成了崇高的客体。人为物也可以成为崇高的客体。原始社会的图腾作为原始人安全、力量和信心的象征,同时又带有不可把握的神秘性质,在原始人眼中是令人恐惧而崇高的。“图腾既是人的力量被歪曲的表现,又是对自己周围自然的一种非理性和理性概括。原始人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把未知自然表现在图腾和神话里。原始图腾是人为的,又是外在于人的。……图腾艺术作为崇高是原始思维的产物”[2](P114)。可见,在特定条件下,人有可能自己造出某件象征物而对之顶礼膜拜,这也表明,出于人的思维的事物也可以成为崇高的客体。
除了人以外的事物,人自身也能成为崇高的客体。西方道德力量很高的人,如苏格拉底在死亡面前的平静态度使人感到了他的崇高。这一点在中国尤其明显,中国古代给人以“大”的感觉的人,都具有崇高的性质。这种人可包括帝王圣人,仁人君子,英雄豪杰等。孔子说过:“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孟子也表示,仁人君子只要保持自己的“善端”,养其“浩然之气”,就能达到“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即崇高的境界。此外,英雄豪杰也因其永世之业,金石之功和甘愿“留取丹心照汗青”的道德而使人感到了崇高。这些都可表明崇高客体的多样性。
其次,在关于主体方面,得到崇高感的主体也并不一定是康德所认为的有文化修养、理性能力很强的人。理性能力并不强、甚至多数情况下处于非理性状态下的原始人从他们的图腾象征物中能感受到近乎迷狂的崇高。黑格尔说原始人“他们尽情地向神,向一切值得赞赏的对象抛舍自己”[4](P87),从而在对崇高的对象的敬畏中获得力量和信心。除理性能力并不强的原始人以外,现代西方表现主义的创作主体在其“有意味的形式”中也可以感到对于终极、永恒等对象的崇高甚至狂喜。贝尔说:“所谓‘有意味的形式’就是我们可以得到某种对‘终极实在’之感受的形式。”[5](P36)而这种对终极实在追求的实质是:“在一个与自然脱节的世界上,焦虑不安的灵魂通过创造形式并在这抽象形式中安居,从而获得终极的宁静和崇高以及狂喜。”[6](P971)这种主体带有很明显的非理性色彩。在中国情况更是如此,在通常情况下,经封建礼乐和规范教化、对“大”人生出崇敬感的主体都是理性能力并不强甚至很谦卑的平凡主体。从音乐理论中可以看到主体的受动特点。《乐记》就认为有什么样的“声”就必定唤起什么样的“心”,“心”决定于“声”。《乐记·乐言》说:“志微噍杀之言作而民思忧,惮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之言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言作而民淫乱。”显然,在庄严崇高的礼乐面前,“民”的理性能力是并不很强的。
第三,在关于客体与主体关系方面,二者的关系多样,并不都是对立的。在康德那里,崇高与美不能统一,美的对象与人协调,而崇高的对象与人对立。但在很多情况下,崇高与美可以统一。崇高的客体不必一定要是完全与人对立的可恐怖之物。飓风、毁灭性的暴风雨固然是崇高的,但与人的感觉协调的物的形象,如平静宽阔的海面,宁静广袤的星空,高大挺拔、枝叶茂密的大树,也是崇高的。宗教中理解的比有原罪的人优越而非对立的物,也是崇高的。“就人也是来自上帝的创造而言,崇高的东西与人在根本上不是敌对的,从人的始祖亚当、夏娃使人永远带有原罪来说,崇高的东西是比人优越的。崇高之物不管是反面的洪水,还是正面的高山和高耸入云的哥特教堂,人们对它们的感受最首要的应当是敬畏。”[2](P125)前文所提及的道德力量很高的动物,功业盛大,修养亦高的君师合一型的人物,圣人贤良,君子英雄等都是正面的崇高客体,与主体并不对立。不仅不对立,主体对客体还可能是“心向往之”的。司马迁赞扬孔子就说过:“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从中可见主体努力向客体靠近的趋势。
中国的山水观尤其能体现出自然物与人合一的特点。古人从高山大水中感到的不是对立和刺激,而是自然、社会、人的内在和谐一致,因此中国古人见到山水时是“乐”的。孔子说“知者乐山,仁者乐水。”《荀子》记载孔子观东流之水而体会君子的道德,得出了“君子见大水必观”的结论。《庄子·秋水》认为海是无形的道的体现,魏晋时期的宗炳则认为“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他还说:“余眷恋庐、衡,契阔荆、巫,不知老之将至。”而且,中国古人好壮游,“求天下奇闻壮观”,以充实自己。总之,“在中国,高山大河作为崇高客体,不是与人敌对的可怖形象,也非违反上帝原则的丑陋造型,没有在黑格尔体系中的卑下地位,而乃是会天地之阳刚正气,是人的江山之助。”[2](P135)
第四,在关于过程方面,感到崇高的过程可以是没有痛感向快感的转移,甚或就是没有痛感的。原始人在图腾前充满敬畏感,虽然他们从图腾中获得了力量和信心,但并没有愉悦感。一般人在崇高的伟大人物面前会有自谦甚至自卑感。孟子描述过这种感觉:“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主体最后产生了要向崇高境界迈进的愿望,但这也不是愉悦感。中国古人在山水中比德、悟道、畅神,则始终充满了乐感,没有经历由痛感向快感的转变过程。
在朗吉弩斯那里,与自然的斗争始终充满积极昂扬求胜欲望和得胜后的狂喜,没有消极的痛感的产生。他说:“作庸俗卑陋的生物并不是大自然为我们人类所制定的计划,它生了我们,把我们既做它丰功伟绩的观众,又做它雄心勃勃、力争上游的竞赛者,……当我们观察整个生命的领域,看到它处处富于精妙、堂皇、美丽的事物时,我们就立刻体会到人生的真正目标究竟是什么了……总而言之,一切为日常所必须的事物,人们视之为平淡无奇,他们真正关注的,却永远是惊心动魄的事物。”[7](P129)“崇高语言对听众的效果不是说服,而是狂喜,一切使人惊叹的东西无往而不使仅仅讲得有理,说得悦耳的东西黯然失色。相信或不相信,惯常可以自己做主;而崇高却起着横扫千军,不可抗拒的作用,它会操纵一切读者,不论其愿从与否。”[7](P122)可见,在朗吉弩斯那里,强烈的竞争欲望和摧枯拉朽式的胜利使得痛感向快感的转移为斗争中的惊心动魄和如愿以偿的胜利狂喜所代替。
第五,在关于效果方面,康德认为最后的效果是主体理性力量得到了增强,主体在观念上得到了提升。然而,布拉德雷说:“惊惧、狂喜、敬畏,甚至自我谦卑都在崇高引起的情感之中。”[3](P38)原始人的祈敬感,宗教信徒在上帝面前的敬畏感,朗吉弩斯那里的狂喜,西方现代非理性创作主体体会到终极实在后的宁静或狂喜,一般人在大人物、历史、力量等崇高客体面前的渺小感,都不是理性的胜利者强化了对自己的信心。因为在这些情况下,主体或是没有很强的理性,或是最终得到的不是理性的胜利。这里仅举中国古人为例。陈子昂在《登幽州台歌》中云:“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在这里,主体把自己置身于深邃的历史力量面前、广远的空间范围面前,不可把握的时空感交织在一个人身上,使主体产生了崇高感。但主体最终怅然自失,以致于流泪。虽然由此可能会升腾起提高自己境界的愿望,或体验到这种崇高感本身说明了主体的心灵的崇高,但从最后的效果讲,很难说是理性主体的胜利,甚至这主体并不是以理性的观念把握作为崇高客体的时空的,而更多的是心灵的体验,他并没有把握或超越它们,而是为它们折服,感到了自身的微小。由此可见崇高效果的多样性。
三、形成这些局限性的原因和它在历史上的位置
以上从五个方面分析了康德崇高理论的局限性。造成这种局限性是有其时代和社会原因的。当时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理性精神的发展,自然科学的发现大大增强了人们对理性的崇拜,而且西方本有重视理性的传统,而康德更是一个尤其注重主观思辨的人,这样,他仍然从理性的角度来理解美和崇高就显得毫不奇怪了。康德认为:“审美的判断力在评定美是把想象力在它的自由活动中联系着悟性,以便和它的一般概念相合致;它(审美的判断力)使这同一机能在评定一对象作为崇高时联系着理性,以便主观地和它相合致。”[1](P95)从引文可见,康德虽然大大促进了把审美从道德和实用等羁绊下解放出来、使审美独立化和纯粹化的过程,但为了其哲学体系,他却把这种进展始终和理性联系在一起。而这样做的结果是,他不仅主观地把审美领域置于自然王国和理性王国之间,作为知解力和理性的桥梁,这种“中介”地位在实际上导致独立审美领域名存实亡了,而且康德在论述美和崇高时总要和知性的概念或理性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甚至认为,没有抽象的概念,就没有客观的判断,这就不仅使美感和崇高感的直接性消失了,而且还使康德论美和崇高的观点表现出折中、有时候却也不免是自相矛盾的特点。这一特点在他论美和崇高的具体特征时都可以看到。
把康德的崇高理论进行纵的和横的比较有助于理解这一理论的位置。在西方,原始、古代、近代、现代都可以有不同要点的崇高理论,和康德有很大不同。如果把康德的理论要点列为五个条件,则五个条件的相互联系大致如下:
1.体积大或力量强的自然客体,它导致
2.理性和意志能力很强的主体引起
3.恐怖、紧张等痛感,然而
4.主体理性战胜、超越了可怖客体,痛感转化为快感,因而最后
5.理性主体的能力进一步得到提升,增强了信心。
但原始图腾的崇高没有1、2、4,古代悲剧的崇高没有1、4,现代以抽象形式对终极实在进行把握的崇高没有1、2、3、4、5。因此从纵的方面看,康德的理论是近代西方的典型产物。
从横的方向与中国古代进行比较,则康德理论的五个条件除第一个部分具有外,其他根本不能适合,甚至正好相反。究其原因,在于中国古人眼中的自然和西方近代人眼中的自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前者是建立在气化和谐基础上的人物一体观,后者却是主客二分基础上的改造自然论,中西文化精神的不同使中西理论表现出相当不同的特点,康德的崇高理论在中国的尴尬只是一个小小的例证。
由此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康德的崇高理论,尤其是要把握它的局限性和历史位置。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得不说,康德的理论仍然是崇高理论中的主流,其中达到的深刻程度和对人类充满的前所未有的信心对目前的我们来说都还是很缺乏的,从这个角度看,康德本人就可以说是一个境界崇高的“大”人,这是毫不夸张的。
收稿日期:2002-1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