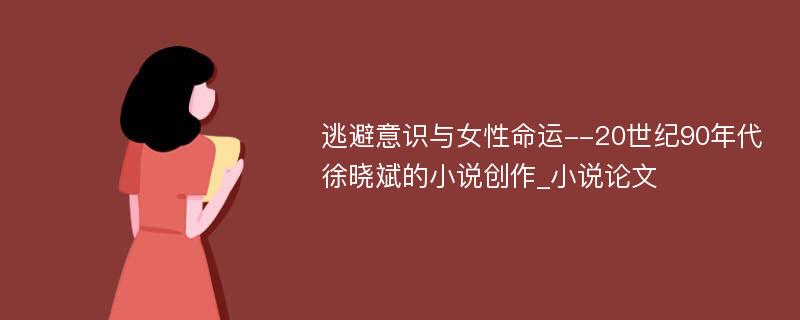
逃离意识与女性宿命——徐小斌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宿命论文,意识论文,女性论文,小说论文,徐小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徐小斌的小说创作,于九十年代的文学来说,是一个相当独特的现象。她的独特不仅在于她奇丽的想象,对神秘与未然的情有独钟,也不仅表现在她作为女性作家对女性意识的格外自觉,同时还表现在她意识与文本中的深刻矛盾。这些特点,使徐小斌的小说在整体上敏锐地传达了她对当下生活的深切体验;她既身陷其中又难以亲近,既向往逃离又宿命般地无力自拔。因此,她只能以想象的方式一次次地自我救赎,一次次地“生活在别处”,然后再重临起点,让她的乌托邦在想象中不断辉煌。另一方面,在这些特点中我们也明确地感到,她在努力超越自己八十年代创作的过程中,仍有依然可感的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的遗风流韵。
徐小斌的小说创作始于八十年代初期。但今天,无论作者本人还是评论界,对她那一年代的创作似乎有意保持缄默,其实大可不必。无庸讳言,那是被一体化的理想主义所哺育的年代,无论现实生活怎样,我们都愿意以明丽、纯粹的叙事再造生活,以期许的方式表达现实。徐小斌作为那一时代的年轻人自然不能幸免,她的《请收下这束鲜花》、《那淡蓝色的水泡子》、《这是一片宁静的海滩》、《河两岸是生命之树》等,就明显带有那一时代理想主义的印记。它们都以天真的心态和叙事视角表达着作者的愿望,但现实却远非如此。旧理想主义在九十年代的全面坍塌,仿佛在一夜之间,如梦方醒的人们不再相信它。因此,旧理想主义的危机并不止发生徐小斌一个作家身上。所以,徐小斌对“理想主义已经陷入了绝望的困境”[①a]的反省,恰恰是对支配了一个时代文学观念的反省。
九十年的生活变得坦率而赤裸,再也没有堂皇的面纱,行动的时代使人们无需再饶舌。但徐小斌仍深陷焦虑与矛盾之中:“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已经被商业主义神话笼罩和淹没了”[②a]的感慨,显然使她仍有欲说还休的巨大孤寂和悲凉。她与现实的无法妥协,也使她命定般地陷入自我设定的矛盾之中,于是,她选择了逃离,她曾作过如下自述:
我很早就拥有了一种内心秘密。这种秘密使我和周围的小伙伴们游离开来,我很怕别人知道我的秘密,很怕在现实中与别人不同,于是我很早就学会了掩饰,用一种无限顺从的趋同性来掩饰。这种掩饰被荣格称为人格面具。这是我的武器,一种可以从外部世界成功逃遁的武器。正是依靠这种武器我度过了我一生中最为痛苦的那些岁月,包括在黑龙江兵团那些难以忍受的艰难困苦。我始终注视着内部世界,以至外部世界的记忆变得支离破碎,就像“没活过”似的。这就是:逃离。[①b]她的压抑和无助的痛苦,源于深刻的童年记忆,由于家庭不睦,使她在很小的时候,就有许多奇想突发,她甚至希望靶场的流弹将她击中,以死来唤起家人的重视和悲伤。因此,当她有了用小说的形式倾述情感的能力时,她无意识地使用了一个祈求的句式作为她小说的题目——“请收下这束鲜花”,一个无助而孤苦的少女祈望能得到一个年轻医生的爱。那时,她采用了许多想象的场景,哀婉动人的故事,借以述说个人的不幸,她真实地希望能靠那个似懂非懂的爱情来获得自我救还。那时她笔下的男人都青春勃发,才华横溢,面对这些男性的女主人公们,甚至多少还有些自卑、有些不自信,但她们都发自内心的爱着他们。这就是徐小斌早期小说的基本模型,它是放大了的“安徒生童话”。在这样的想象中,作者找到了自己魂灵的临时避难所,她逃离了现实的丑恶和污浊。
然而,无论是作家还是普通人,那单纯明丽“宁静的海滩”,从来就不曾有也永远不会有,它可以临时补偿现实的缺憾与失望,却永远不能指望它的兑现。旧理想主义者致命的要害,就在于它坚信理想是可以实现的。九十年代,徐小斌不再持有这样的情怀,她的小说在面貌上发生了判若两人的变化,她的小说更复杂,更理性化,因此也更成熟。她的《双鱼星座》、《迷幻花园》和《敦煌遗梦》等作品曾风靡一时,她本人亦被命名为“风头正健”的“才女”。
徐小斌九十年代小说最大的变化,就在于她不再以想象的方式实现精神救助,她否定了自己先前对善与美缺乏节制的赞美与向往,而对人性之恶充满了深刻的失望。《双鱼星座》曾有这样一个情节:一年一度的献血,是老板最头疼的事,这时他想到了卜零,他以诚恳动人的态度打动了卜零,答应献血。然后,他送来了大包慰问品,讲了六个笑话,但这并不是老板的真正目的,他要说的是:“有件事我不能不告诉你,下个月你就不要去单位上班了。”卜零被辞退了,老板说了一堆理由,但“卜零看着他的眼睛说老板你说的时间不对吧,我想裁人的决定应该在我献血之前,我猜的对吗?”老板的回答却是“你真聪明”。这一情节相当经典地揭示了充满了陷阱的人际关系,它表达了作者对现实不再抱有任何幻想的极端暗示。如果说上下级的关系是一种利用关系尚可理解的话,那么夫妻关系也并不比这种关系更让人信任,《迷幻花园》中的金和芬是夫妇,久别相聚时两人则同床异梦:“当金进入她身体的时候,她其实毫无快感但努力装出一脸陶醉。她闭上眼睛不愿看那张离她很近的黄脸,她竭力想象着一个理想中的男人。”而金这时则不断喃喃着,“但金的自语实际上与芬的肉体毫无关系。他在少年时代便有了的那种灵魂游离的状态现在愈演愈烈。他背诵零和与非零和博弈的目的在于逃避对这具已使用过的肉体的厌恶”。在生活中似乎已没有真实可言。在这些情节中,让人深刻地感到存在主义对作者的影响与支配。《敦煌遗梦》中,她甚至直接使用了萨特的言论:“爱是个枉费心机的企图,这个企图就是要占有一个自由。”用作者的话来说,“寻找真品太难了,现在确实是个代用品的时代,一切都可以代用”[②b]。这种感慨不仅传达了作者的失望,同时也传达了她的无奈,她甚至也失去了对其解释的兴趣。
徐小斌小说引人注意的另一变化,是对男权中心的批判,抑或说是女性意识的支配。先前的小说,她的女主人公大多是脆弱的、依附的,有时还是病态的。她曾多次选用医院作为情节展开的场景,那些女主人公多为“病人,而疗治她们的医生则是男性。这种无意识安排恰恰从一个方面表现了男性/女性的关系,他们成了疗治与被疗治、救助与被救助的关系,男性成了女性渴求的宿地。九十年代,作者断然否定了这些幻觉,她甚至愤然地说:“一个完全成熟的女人是埋藏在男性世界中的定时炸弹,是摧毁男性世界的极为危险的敌人。”[①c]她的女性主义写作密切地联系着前面谈过的存在主义哲学。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女性视角既表达了作者女性意识的觉醒,同时又不经意地设定了女性的压抑力量——男性中心。于是,拆解与颠覆这个中心,就成了徐小斌小说的主要策略之一。这也是九十年代许多女性作家普遍采用的叙事策略。
《双鱼星座》的副标题是“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古老故事”,但这绝不是个古老的故事,它的中心情节,并没有设定于多角追逐、风花雪月或男欢女爱的框架之中。这三个男性,分别被作者处理成了权力、欲望与金钱的象征,他们仅仅成了三种不同的符码,这些世俗化的概念成了男人的全部。那个纯美无比的女性卜零,还未出场就被赋予了抨击、拒斥、挑战这些男性的使命和义务。这些男人,要么阴险无比,要么懦弱自私,要么先天不足没有生育能力,……男人的所有光环和伟岸,在作者笔下逐一暗淡坍塌;而卜零则几近完美无缺,她虽然无所事事,主要承担着挑剔,指责男性的权责,但她内心丰富,举止高雅,穿着法国摩根丝的曳地长裙并十分性感,既典雅又摩登。《迷幻花园》中的芬和怡,也都气质不凡,倾国倾城沉鱼落雁,而金则粗俗不堪,男人的命运几乎都没有逃脱被女人抛弃。更有甚者,在女人面前,男人几乎都没有自尊可言:
……卜零全身赤裸着站在他面前了。石捂住了脸。但指缝里仍能看到他红得要冒血的脸,他的眼睛又出现了那种潮红,潮湿得仿佛要渗出水来。卜零毫不留情地把他的手扯开。卜零的眼睛像星星一样在他眼前飘闪聚散,卜零轻轻在问:我美吗?石的潮红的眼睛里全是乞求,石的眼前一片红雾什么也看不清,但卜零并没有放过他,卜零恶狠狠地揪住他的头发:说啊,回答我啊!连这句话都不敢说,你是男人吗?!这个被命名为石的家伙,卑微无比,在这位女神面前,他早已不战自败。而卜零的“全身心都在享受着复仇的快感。在两性战争中,她觉得战胜对方比实际占有还要令人兴奋得多”。
应该说,在这样的叙事中,作者确实实现了一次对男性的有效颠覆,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由衷的快乐。在九十年代的女性文学写作中,这种颠覆和置换,犹如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它动摇乃至摧毁了男性的霸权和优越。然而,所有的问题都“发生在革命的第二天”,当卜零们放逐了一个个的男性之后,这些专革男性命的“女革命者”又如何呢,摧毁了男性就真的意味着女性的解放吗?徐小斌显然也不这样认为,否则她会让自己心爱的主人公们无所忧虑地沉浸于女儿国的欢乐中。事实上,她的女主人们都语焉不详、下落不明:卜零孑然一身去了石寨;星星被她打发到印度去了;而芬和怡则周而复始,从开篇的序号“0”,又回到了“0”,这些愤然的抗争和拒斥仅仅成了没有结果的过程。于是我发现,作者愤然拒绝的不仅仅是作为异类的男性,同时还有她深刻感悟过的这个现实。然而她又无可奈何,只好按着前辈的路数,让这些女人们远走他乡。但他乡也仍有男性的固执存在,卜零们还会怎样呢?
作者显然再次陷入深刻的矛盾。无论对两性还是现实,作者都深怀恐惧和困惑,在难以求解的困扰中,她终于走上了神秘主义的道路。于是,这便构成了徐小斌小说的第三个特点:对神秘主义的情有独钟。翻开作者的小说,她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是诸如“梦幻”、“迷幻”、“末日”、“末世”、“佛”等超验的,难以用现有认知解释的别一世界。她在一部小说集的“后记”中,曾表达过她对波伏娃关于写作是一种对呼唤的回答的理解,她认为这种呼唤,“说到底,这是一种神祗的呼唤”[①d]。她的朋友铭今在一篇文章中也证实,她的许多灵感来自梦境,她相信藏传密宗中关于“银带”的说法,“银带”就是人的灵魂,人在入睡的时候,灵魂是游离于身体之外的。灵魂的遭际便形成了梦。这些解释,我们这些俗人很难理解,它无从证实,因此也只能聊备一格不作深究。但她钟情的神秘主义,不同于民间数术、奇门遁甲或街头占卜也是事实。她的神秘主义,多与宗教尤其是佛教文化相关,她对敦煌的热爱或多或少地解释了这一点。
然而,在我看来,这神秘主义是徐小斌对现实给以解脱而选择逃离的最后停泊地。人生的诸多烦乱有如宿命般地不可避免,她想象中的一切逐一被现实所粉碎,为了逃离现实的一切,她只能在神秘主义中得抚慰和平息。这种选择我们无须做出评价。值得注意的是,它作为一种叙事策略,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它使我们有理由确认,她的小说是东方土壤孕育的文本,她的话语,是现代中国的本土话语,她的神秘主义正是现实挤压的直接后果。值得庆幸的是,徐小斌并不沉迷于东方神秘主义的幻像中,事实上,她已经找到了既表达个人倾向、又关怀人间现实的结合部。她有影响的一些作品,或者说九十年代以来的作品,她关注的焦点始终是现代人或者说是现代女性精神焦虑和情感挫折。但小说并非是人生指南,她所有人物的结局或出路,亦不等同于她为女性开出的十全大补药方。但我固执地认为,一个作家只要真诚地表达了他对现代人的生存处境和精神处境的关怀,表达了他哪怕深陷绝望但仍在抗争的努力和勇气,表达了他对人类基本价值维护的承诺,她的作品终会被人阅读并且热爱。在这个意义上,徐小斌的作品也体现出了我所说的“新理想主义”的全部特征。
作上述分析,旨在表达我对徐小斌小说创作的一种解释或肯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条件地全部同意她要表述的一切,尤其她的女性主义文学观。她在一篇“创作谈”中说:“父权制强加给女性的被动品格由女性自身得以发展,女性的才华往往被描述为被男性‘注入’或者由男性‘塑造’,而不是来源于和女性缪斯的感性交往。……除非将来有一天,创世纪的神话被彻底推翻,女性或许会完成父权制选择的某种颠覆。”女性主义本应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话语,或者女性的一种理想话语。但它东方化之后,却成为谋杀、指控、颠覆男性的至高法则,哪部作品如果不对男性怀有仇恨并将其“杀死”,就会被认为很不“女性主义文学”,其实这实在是个误解。即便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也已超越了“性别对抗”的阶段,她们不模仿男性,不反抗男性,而是以自立的方式表达他们对这个两性共有的世界的看法。事实亦如此,你越是逼近你反抗的目标,而获得的常是不自觉的陷落。就《双鱼星座》来说,卜零虽然以不同的方式“杀死”了三个男性,但她的反抗策略并没有超出男人的施虐框架,前面引述的卜零对石的报复,只不过是一种逆向的性别报复,她并没有找到超出男性的其它方式。这篇小说之成功,其实并不在于作者的什么“女性主义文学观”,而恰恰是它表达了现代人共同面临的处境和心态。因此,大可不必先在地设定女性的压抑源于男性,颠覆了男性就意味着女性的解放。事实是,两性共同面临的问题尚未解决,便急于优先考虑女性问题,确实是奢侈了些。
我在谈论女性文学的另一篇文章中曾指出:“本质先于存在”的观念、逆向的“等级”观念、夸大“差异”等,已成为一种普遍的意志,女性文学的限度也正是为这样的意志决定的[①e]。现在我仍持有这样的看法。就徐小斌的创作而言,她的逃离意识表达了她的痛苦,厌倦和无可奈何,然而,她又命定地让她的女主人公们不断地同男人生活在一个世界上,一次次出走,还要一次次回来,这就是女性的宿命。
注释:
①a②a 徐小斌:《逃离意识与我的创作》,《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6期。
①b 徐小斌:《逃离意识与我的创作》。
②b 徐小斌:《敦煌遗梦·附录》。
①c 徐小斌:《逃离意识与我的创作》。
①d 徐小斌:《呼唤与回答》,《如影随形·代跋》,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4月版。
①e 参见笔者《女性文学话语实践的期待与限度》,《文学自由谈》1995年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