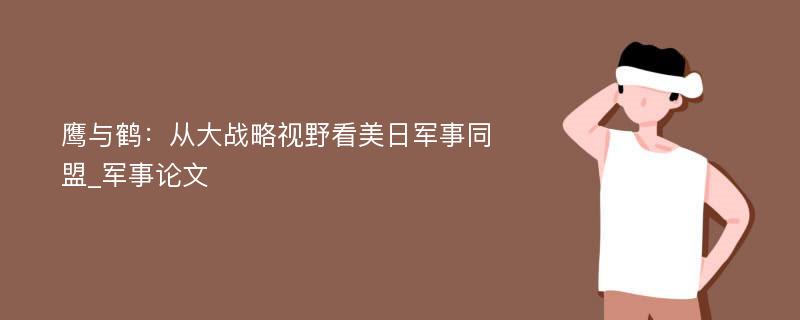
鹰与鹤:从大战略视野看美日军事同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日论文,同盟论文,视野论文,大战略论文,军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美日安保联合宣言》和《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相继出台,以及与之相配套的美日战区导弹防御方案的产生,美日军事同盟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特定意义上说,今后的美日军事同盟,就是亚太地区的“北约”。
近几年,随着《美日安保联合宣言》和《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相继出台,以及与之相配套的美日战区导弹防御方案的产生,美日军事同盟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今天的美日军事同盟,已经不是局限在对付前苏联威胁的双边合作关系上,也不是单纯的“保护”与“被保护”军事意义上的合作关系,而是朝着控制亚太地区并对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军事联盟集团的方向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后的美日军事同盟,就是亚太地区的“北约”。这一新意义上的军事同盟关系的出现,将会加重亚太地区战略格局的军事色彩,把亚太地区通过正常范围或合理方式就可处理的矛盾导入军事解决的轨道,甚至有可能在亚太地区造成新的冷战局面,给亚太地区的安全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认真分析美日建立新的军事同盟关系的战略企图,从战略层面上审视美日军事同盟实质内容和今后的走向。
一、美国的战略企图
(一)凸现美国全球战略的“亚太重心”
美国的全球战略,就是要建立自己称霸的单极世界,而建立这一单极世界的重要手段,就是要充分利用自己拥有的军事优势,借助各地区军事同盟关系,形成美国全球范围的“军事存在”,实现其对世界的军事控制。
亚太地区对美国来说至关重要。这种重要性主要表现在安全与经济两个方面:第一,美国人认为,亚太地区国家所拥有的军事力量和这个地区核扩散的趋势,会给美国的生存安全带来威胁。亚太地区的矛盾、冲突和其他一些不稳定因素,会威胁美国海外基地和海外通路的安全,会再次把美国拖入一场类似朝鲜、越南那样的战略。第二,美国在亚洲具有重大的经济利益。尼克松曾经谈到:“亚洲是世界上最有生命力的经济区域。在未来的几十年里,重大行动都将在那里产生”。美国太平洋总司令拉林上将谈到:“美国有36%的贸易在亚太地区,是美国同拉美贸易的3倍,同欧洲贸易的1.5倍。美国1992年的出口总额为4480亿美元,其中30%出口到亚太国家,这些出口为美国创造了250万个就业机会。”另据资料统计,1993年美国与亚太地区贸易总额高达3740亿美元,为美国创造了280万个就业机会。近几年来,美国在亚洲的投资迅速增加。美国前商务部长布朗谈到:亚太地区不仅是我们命运的归宿,也是我们目前财富的来源。
因此,判断亚太地区对美国的重要程度,是冷战后美国战略家们一直关心的问题。美国战略权威人士称,美国与亚太地区悠久的文化、经济和安全联系,反映了美国根本的国家利益,未来若干年,这种利益的份量只会与日俱增。美日军事同盟的重新定义或者说在一个新的意义上建立,表明美国全球战略的“亚太重心”开始凸现。
(二)在亚太地区建立符合美国利益的地区安全机制
美国要在亚太地区实现其全球称霸的战略目的,需要扮演一种亚洲人或亚洲人能够和乐意接受的角色,在亚洲的政治论坛上和合作组织内占有决定性的一席之地,并且尽可能夸大与亚洲各国的“共同利益”,最大范围地参与进亚洲的地区事务。与此同时,美国要设计一种符合美国利益和战略意图的地区安全机制,把亚太地区的战略问题纳入美国的思维模式之中。为此,美国曾提出“新太平洋共同体”的战略构想,企图把亚洲国家拉入一种类似北约的条约组织中去。这一构想包括安全、经济和“民主”三个部分,企图“三管齐下”,形成防核扩散、美国主导和支持民主改革的“三个支柱”。显然,美国建立美日军事同盟,有着这一深层战略目的,也可以说这一军事同盟是其未来“新太平洋共同体”的前身或核心。
1994年6月,美国国防部弹道导弹防御局局长奥尼尔中将向日本提出了四种战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方案。这些方案设计的战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包括四个部分:一是地面低空防御系统,由500多枚“爱国者2型”或“爱国者3型”低空反弹道导弹构成;二是地面高空防御系统,由5-6个战区超高空防御系统构成;三是海上高空防御系统,由配备有大约70多枚战区反弹道导弹的多艘“宙斯盾”驱逐舰构成;四是警戒管制系统,由4架装有红外监视跟踪装置的E-767预警机和地面监视雷达构成。这四个方案分A、B、C、D四类,它们的区别主要是力量部署不同,其假想敌是中国和北朝鲜。美国方面强调说,这些方案都已经过有效性检验,对战区弹道导弹的击毁率均在90%以上。美国推行TMD计划,其利用军事同盟关系控制亚太地区的战略企图十分明显。TMD成员国(地区)之间由此构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依赖、互相制约的军事体系,形成了能够控制亚太地区的军事同盟的关系。
(三)保持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存在
保持前沿存在,驻留10万重兵,是美国建立美日军事同盟的一个重要考虑。在美国看来,在亚太地区保持军事上前沿存在,是美国参与亚太地区事务并对这一地区问题拥有决定性发言权以及对潜在对手保持战略威慑的带有实质性的一个行动。美国通过其前沿存在,可以提高自己对亚洲突发事件的战略应变能力,提高军队的快速反应能力,弥补从美国本土到亚洲事发地点战略距离过远的不足。为此,美国有这样一种所谓“扇形”的战略构想,即由本土(扇底),经美国在日、韩等地军事基地(扇骨),向整个亚洲辐射。从经济实惠的角度看,美国推行其“前沿存在”的战略,不仅不吃亏,而且还占便宜。现在,日本政府每年要支出60多亿美元的基地维持等费用,占美驻军费用总额的75%左右。有人计算过,由于日本提供了财政支援,美国在日本驻军要比在国内维持这部分军队划算得多。关于美国“前沿存在”的战略意义,还有一点需要强调,就是这种存在可以让日本继续享受到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消除亚洲其他国家对日本的畏惧,并将这种戒心更多地转向他所担心的另一个大国。
(四)牢牢控制住日本
日本在美国的全球战略棋盘中是一个实力和位置都很重要的棋子。用美国人的话来说,美日关系可以用“一个关键”、“两个最大”和“三个支柱”来概括。“一个关键”是美日联盟在美国亚洲政策中具有关键的作用。“两个最大”则指日本是美国在亚洲最大的盟友和最大的潜在对手。“三个支柱”是安全联盟、政治合作和经济贸易。美国对日本的战略说起来并不复杂,其基点就是用美日同盟条约框住日本。这个条约对日本既是一个保护伞,同时又是一个枷锁。美国对日战略技巧主要表现在两点:一个是给日本设计既不强大(军事上自卫、不说“不”、中等国家的外交“低姿态”)又不软弱(能在安全上帮美国一些忙,并常给亚洲国家一些安全上的顾虑,增强它们对美国军事力量的依赖);另一个是同日本既合作又对抗,这要根据美国在亚洲整体利益的“平衡点”的移动情况而定,这不仅表现在经济交往中相互要价,而且可能根据亚洲战略格局变化和安全需要,在政治上对日本表现出时软时硬的态度。
(五)遏制中国
美国担心会在亚太地区出现某个强大的战略对手,对美国在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领导权威提出挑战。亚洲是美、俄、中、日四个大国的利益交汇地区,并且亚洲经济强劲发展为本地区大国崛起提供了有利条件。美国担心的这个可能成为它的战略对手的亚洲大国,不仅具有与美国相抗衡的经济、军事实力,而且还有着与美国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念的感召力。这个对手的出现,将会造成亚太地区力量失衡,置美国于不利的战略地位。在美国决策者看来,中国是这一战略对手的首要侯选者。
在这方面,美国还有着亚太地区力量均衡的考虑,这种力量均衡关系主要表现在中、日、美三角关系上。美国的战略目标就是不使其他两个顶点靠近和其中任何一点突出。对此,基辛格谈到:良好的美中关系,也是良好的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这是一个三角,其中任何一方若想抛弃其他两方,都必须要冒极大的风险。这也是一种阵线不明的格局,美国对此很不舒服,因为这不合它的脾性,它喜欢干干脆脆地把别国或是当作朋友,或是当作敌人。那么,美国要时常考虑自己未来的战略对手是中国,还是日本——这是观察美国亚洲战略的关键问题。美日军事同盟的建立,表明了这种三角关系的距离出现了极不对等的状态,在中、日、美三者力量对比上出现严重的失衡,而这正是美国处于遏制中国的战略所希望和所要求的。
在美国建立新的军事同盟关系达成遏制中国的战略目的方面,最为明显的表现是将台湾纳入这一同盟考虑的范围之中。在美国看来,遏制中国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提高台湾自身的防御能力,增强台湾与大陆抗衡实力。据有关资料报道,台湾与美国的军事合作获得重大进展,以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闻名的美国雷声公司,在台湾设立了亚太导弹维修中心,协助台湾提高导弹制造维修技术,并作为亚太地区的导弹后勤支援基地。其中具体谈到:为了提高台湾导弹制造技术,雷声公司今年已投资300万美元,与台湾欣欣科技公司合作在桃园建立了导弹用热电池生产线,除供应台湾军队的各型导弹使用外,部分已回销到美国的母厂。
二、日本的战略企图
(一)利用军事同盟关系,掩盖或缓和与美国的经济矛盾,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
日本把经济发展看得非常重要,甚至将经济发展视为立国之本和谋求其他方面利益的最可靠和最有效的手段。因此,日本的主要战略目标就是加速发展经济,保持住自己经济大国的地位。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达4.7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外贸总额5500多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对外纯资产达3800多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日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但是,日本自身的经济问题也是比较突出的,一是严重地依赖国外资源,尤其是能源。如果国外的资源失去控制,这对于日本来说是致命的;二是经济发展稳定性较差甚至是带有某种程度的脆弱性,一方面对世界市场过分依赖(在某种意义上是对需求者、购买者的依赖),在世界各国和地区增强保护措施的情况下,遇到的挑战增多,并加剧了与国外的经济摩擦;另一方面是资产结构“架空虚拟”,日元币值浮动和股票时价,标示着脱离实物经济的虚拟资本达到了惊人的膨胀程度,给日本的经济造成了巨大隐患。日本最为苦恼的是,近些年来与美国这一经济大国在经济利益的摩擦增多,甚至有时到了互不妥协、难以相让的地步。日本需要与美国加强联系,利用经济之外的手段,缓解经济矛盾;利用经济之外的亲密感,淡化经济上的敌视感。
(二)利用军事同盟关系,增强自身的军事实力
通过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建立新的与美国军事结盟的框架,日本可以进一步得到美国军事保护,同时,还能够相应提高自己的军事地位,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对于日本来说,建立新的美日军事同盟关系的战略企图,在后一种要求上体现得更为明显。从长远来看,日本人对自己的安全维系在别人身上的作法,对为了安全而不得不牺牲自己其他利益而违心说“是”的举动,不仅心理上难以接受,而且也很难让他们感到放心。自90年代开始,日本将由日美合作为主向日美合作与自主防卫并重转移。日本军费的年增长率高达5%以上,居西方国家之首。日本在扩大军备力量方面已经不需要任何人来督促。为加速武器更新换代,日本逐年增加装备购置费在防务开支中所占比重。在此期间,海军着眼提高其远洋作战能力;空军着重完善战斗机、防空导弹和雷达系统“三位一体”的整体作战能力;陆军重点更新坦克、火炮和直升机等主战装备,目前更新率达70%。就日本的利益而言,军事实力的增强,被日本人看作是保障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形成政治大国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今后迫使敌方满足自己领土要求的强硬手段。
(三)利用军事同盟关系,谋求政治大国地位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日本具有与德国一样的利益需求,就是改变自己的国际形象,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但由于历史和其他方面的原因,亚洲国家并没有象欧洲国家接纳德国那样,形成一个以日本为主导的“亚洲联盟”。因此,与德国所不同的是,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需求更为强烈,朝这个方向迈进的步子也更大更急。
日本需要改变自己的形象(这种形象包括“侵略者”和“经济动物”形象),需要确立大国的地位,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国际权力。日本正在利用国际战略格局重新分化组合的有利时期,积极为自己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一位日本前首相曾明确地谈到,要加强日本在世界政治中的发言权,日本不仅要做经济大国,而且要增加日本作为政治大国的份量。从利益分析的角度上看,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意图,基于四种利益上的考虑:一是在国际社会中直接获取政治权力;二是得到与其他国家平等的地位,可以明确说“不”,维护自己的利益;三是参与国际事务,为自己创造有利的国际秩序和机会;四是通过确立自己政治大国的地位来改变自己过去不佳的形象。在这些方面,日本以下几种战略动向值得注意:一是强化日本国民的“民族情结”,获得国民支持;二是修改宪法,为今后由军事和政治上进入世界“正名”;三是积极参与国际新秩序的构想,确立自己“理想”的国际地位,争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日本同美国建立新的军事同盟关系,能够借助美国这一当今唯一超级大国的力量,为实现自己上述利益提供有利的条件。具体表现为:第一,争取获取美国这一超级大国对自己政治要求的支持;第二,利用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增大与周边国家讨价的砝码,必要时可借助美国的实力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第三,扩大自己政治、军事影响的范围,抬高自己在亚太地区的身份;第四,利用军事同盟关系,日本就可以把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灵活地“捆”在一起,通过经济手段获得政治、军事利益,实现自己的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梦”。
(四)利用军事同盟关系,使自己在大国关系中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
就一定意义上说,日本的利益是维系在大国的关系之中。从过去历史上看,日本是巧妙地利用大国间关系而生存和发展起来的。在今后,日本仍然要处理好与大国之间的关系。冷战结束后,日本与美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少了,而冲突利益多了。这因为,两国的共同利益更多地表现在安全方面,而冲突利益更多地表现在经济方面。日本与美国都需要维护住它们之间的同盟,美国需要日本拉住自己,保持美国在亚洲的存在,而日本需要美国安全保护和保持亚洲的力量均衡。所以,它们需要制造出一种“威胁”,也正是在所谓“中国威胁论”的基础上,它们得以多少修补了原有共同利益的裂痕。日本将会与美国的对华政策相协调,在竞争、猜疑中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与此同时,日本将会在美日军事同盟的限定框架中,保持与俄罗斯的往来,警惕地注视着俄今后的发展和远东政策;利用自己在美日军事同盟中的地位,积极参与欧洲事务,不等距离地发展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利用欧洲国家的矛盾向欧洲联盟渗透。总之,日本将会以美日军事同盟为基点,根据自己利益不间断地调整自己与其他国家间的距离,并且在这种距离调整中,使自己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维护和实现自己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