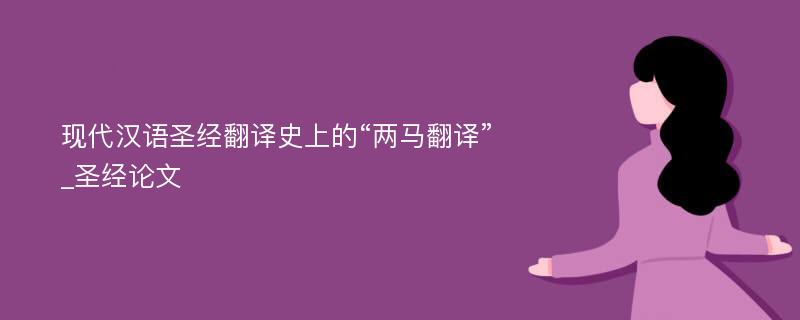
近代中文《圣经》翻译史上的“二马译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译本论文,史上论文,中文论文,圣经论文,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圣经》中文全译本的完成是近代基督教事业一大成功的标志。《圣经》是基督教经典,包括《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统称《新旧约全书》。《旧约》原是犹太教经典,用希伯来文写成,后被基督教接受,分为《律法书》、《历史书》、《智慧书》和《先知书》四部分,共39卷;《新约》是耶稣门徒的著述汇编,包括《福音书》、《使徒行传》、《使徒书信》和《启示录》部分,系用希腊文写成,共27卷。虽然东正教、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在神学观点上存在分歧,但它们都公认《圣经》为自己的经典。
《圣经》何时开始有中文译本,至今尚不能确定。但有论者认为,早在7世纪前半期,伴随景教传入唐朝,《圣经》即被带进中国,并至少把《新约》译成中文。[1](P4)其依据就是1625年在西安发现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1908年从敦煌石窟发现唐代景教文献《尊经》,从中可知已有30余部译成中文,这被认为是中国第一批汉译《圣经》经卷。[2]此后陆续又有《圣经》中译。但要么停留于对《圣经》的诠释,要么是对《圣经》史实的叙述,像1584年耶稣会士罗明坚的《天主圣教实录》、1959年利玛窦的《天主实义》、庞迪我的《受难始末》、1635年艾儒略的《天主降生言行纪略》、阳玛诺的《圣经直解》等,其中虽含有《圣经》经文,却不能称为正式的《圣经》中译本。直到19世纪基督新教开始大规模向中国及远东传播,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圣经》中文全译本。近代《圣经》中文翻译史上最早的两个著名译本,即马士曼译本和马礼逊译本,通常称为“二马译本”。[3](P15)
一、马士曼及其《圣经》中译本
马士曼 (Joshua Marshman 1768-1837),1768年4月24日生于英国威沙尔郡(Wiltshire)威斯堡赖镇(Westbury),其先祖曾在英国国会担任军职,他的父亲是一名纺织工人。马士曼自小家境贫寒,只在乡村小学就读,稍大后曾在书店帮忙,但不久即被迫回家帮助父亲从事纺织工作。马士曼天资聪慧且极勤奋,据说在18岁前他已读过5000多卷书。[4](P177)1794年他到布斯托尔城(Bristole)百乐麦(Brodmead)一个浸礼学校任教,同时到布里斯托尔学院兼习古典文学。他通晓希伯来文和叙利亚文,对希腊文也很精通。1792年英国浸信会第一位传教士威廉·卡莱(Wlliam Carley)到印度传教,取得了极大成功。马士曼受其鼓励,决心加入浸信传教会,献身于海外传教事业。1799年5月29日他与另一位传教士华德(William Ward)乘美国船赴印度,同年10月12日抵达加尔各答,旋往赛兰坡(Serampore)进行传教和设立学校,教育本地儿童、青年,同时从事多种语言的《圣经》翻译工作,曾将《圣经》译成多种印度文字,后来受到英国福特威廉神学院布郎牧师(Rev.Dr.Brown)的鼓励,从事把《圣经》译成中文的工作。据说马士曼起初对此很忧虑,他们保证有拉沙(Johannes Lassar)给予帮助,马士曼才应承下来。[5](P51)拉沙是出生在澳门的亚美尼亚人,他的中文很好,不仅能够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而且能用中文写作,[5](P70)曾经为葡萄牙政府与北京宫廷作过官方通信工作,[6](P51)足见拉沙的中文已颇有造诣。从1805年开始,马士曼就跟拉沙学习中文。由于他很勤奋,中文水平提高很快,在1809年就在赛兰坡出版了《儒家著作选》、《中国文法》等三本汉学著作,还撰写了一篇有关汉语文字和发音研究的博士论文。[7](P32)随着中文知识的提高,马士曼开始与拉沙合作翻译《圣经》。据英国浸礼会赛兰坡差会1808年的《译经备忘录》记载:他们依靠大约300多本中文参考书和包括康熙字典在内的几部中文字典进行翻译工作。他们的翻译相当繁琐,马士曼在1813年2月给英国圣经公会的信中,谈到了他的译经过程:
在他(拉沙)开始翻译前,共同诵读每天所规定的部分,直至他觉得这一做法并非必需。……当他译完一段后,我就手执格里斯巴哈(Griesback)的希腊文《新约》,逐句地斟酌修改。我将译文每节读过,说明我对于一些特别的字义的疑惑,于是就想出别的字作为替代。当一全章译完后,有时须费三四个小时之久,我把译文交给他,我就将格里斯巴哈的《圣经》用英文缓慢清晰地读出,同时他一面听着英文,一面注视着他的汉文翻译。如果还有疑问,要作第二次、甚至第三次的审阅。于是送交付印,其后又作一次新的审察。当双面的一页用铅版的活字排满后,我和另一位不懂英文的中国人同读。在一些地方他提议加以修改,使译文通畅明晓。在改正以后,又印了几份清样,交给一些人校读。以后,我一个人独坐阅读,再和希腊原文对照,有时也与别的人商讨。在我看来,这算是最严密的审查了。这时,我将所有觉得意义不甚明确之处,从两册《拉丁汉文字典》中逐一检查,这样对我最有帮助。然后再读希腊原文,与以前不同,以前足逐节读,现在是选取读一小段原文,再读那小段的汉文,……我将所建议的要改之处,以及那些似乎不合之处,在书边上写出之后,就与拉沙和那位中国助译者商议,共同解决。这步工作完成之后,又印一份清样,交给我的儿子约翰审阅,他对汉文语辞的知识,比我渊博。当他对这觉得满意之后,又印了另一次清样,一份给中国助译者,一份给拉沙,让他们各自阅读,指出他们各人认为不妥之处。此后,我又最后一次将译文与原文比较,查考是否有他们都未注意到的失误之处。这样的工作完成之后,我另将一份清样交给中国助译者,由他照汉文的意义加以句读,这些都经我的复核。假如他的意见与我相合,就可送印刷所。在印刷之前又送来一次清样,我先交给助译者,阅看其中是否有错误,然后又经拉沙先生过目,最后由我审阅。经过以上的种种手续,这才正式印刷。[1](P21-24)
可见马士曼译经的严谨,他说:“通过这种严格的检查,我只希望最后能译出最忠实于《圣经》的中文译本。”[7](P32)
马士曼和拉沙最早译出并出版的中文《圣经》为《新约》。第一章《马太福音》于1810年在赛兰坡出版,1811年又印行了《新约》第二章《马可福音》。《新约全书》于该年全部译毕,进入修改、待印阶段。到1813年,《旧约全书》也已翻译过半。经过16年的辛勤劳作,马士曼和拉沙把整部《圣经》全部译成中文,以《圣经》为名,于1822年在赛兰坡出版。[8](P2)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圣经》中文全译本。英国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伟烈亚力即指出:“此译本(指马士曼和拉沙译本)系目前所知的第一本完整的汉语《圣经》,是《圣经》流传史上的一座丰碑。”[9](P90)密立根也认为马士曼和拉沙1822年出版的译本是“新教所译的第一册汉语《圣经》”。[10](P164)
二、马礼逊及其《圣经》中译本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是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1782年1月5日生于英国诺森伯兰省(Northumberland)摩伯斯镇(Morpeth)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其父是位鞋匠,又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经常在家举行家庭祷告,并要求孩子们必须参加安息日的宗教礼拜。[11](P2)这使马礼逊从小就受到基督教的浸染。1798年马礼逊加入长老会,成为基督徒。1804年进入高斯坡(Gosport)神学院,立志做一名海外传教士,他在给伦敦传教会的请求中说:“求上帝将我置于困难最多和从人类眼光中看来最难成功的布道区域中。”[12]当时,伦敦会正准备派传教士去中国,但都视中国为畏途,拒绝前来。勃格牧师(Dr.Bogue)根据马礼逊在校表现及其坚韧不拔的毅力,认为马礼逊适合担任此职。几经斟酌,马礼逊放弃了到非洲的打算而决定到中国来。临行前伦敦会在给他的指示中说:“由于我们对你可能立足的地点不能肯定,要给你规定任何明确的指示限制你的行动是非常不恰当的。我们有必要完全授权予你,可根据你的机智和判断,在各种场合方便行事。……我们坚信你能住在广州而不致遭到反对,直至学会汉语。此目标完成后,可能不久你就开始把这一学识转化成对全世界有广泛作用的事业,你也许有幸编一本比以前存在的任何一本都更全面和更正确的中文字典,或更有幸地把《圣经》翻译成一种被人类三分之一的人所讲的语言。”[11](P96-97)从这一指示中可以看出,马礼逊来华的首要目的是翻译《圣经》。
由于东印度公司船只拒绝传教士搭乘,马礼逊只得取道美国来中国,1807年9月7日到达广州,不久就开始译经。马礼逊在译经过程中受天主教《圣经》译本的影响很大,这源自他在伦敦学习中文时,曾从大英博物院借来天主教的中文《新约》稿本,此抄本即是《四史攸编耶稣基利斯都福音之合编》,它原是法国天主教士巴设(J.Basset)所译,于1737年被东印度公司贺特逊(Hodgson)在广州购得,赠给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史路连爵士(Sir Hans Sloane),其后史路连又把此抄本转送大英博物院,所以称史路连抄本(Sloane Manscript)。马礼逊借来后同他的中文老师、当时到伦敦学英文的广东青年容三德(Yong-Sam-Tak)一边研究,一边誊抄了一遍,带到中国,成为他译经的蓝本。美国宗教史家赖德烈说:“天主教的《新约》译本被介绍给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用来学习中文,它无疑影响了马礼逊本人的《圣经》翻译,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后来许多新教徒译本。”[13](P190)马礼逊自己也说:“我把珍藏在大英博物院的中文《新约》译本誊抄一遍,它成为我翻译和编辑中文《新约》的基础。”[5](P118)在1814年的一封信中他又提到,他的一部分翻译是“根据某个不知名的人的著作,他的虔诚的劳动保存在大英博物院里,我冒昧地改正和补充了我所需要的东西。”[11](P395)这显然指的是巴设译本。
马礼逊把“God”译为“神”,即是受了巴设译本的影响。在巴设译本中,《约翰福音》第3章36节译为“盖神爱世人赐己独子,使凡信之者,不陨,乃得常生也。”《罗马书》第1章第1节译为“耶稣基督之仆,蒙神召为使徒,蒙择事神。”在马礼逊译本中,《约翰福音》第3章36节译为“盖神爱世,致赐己独子,使凡信之者不敢沉亡,乃得永常生也;”《罗马书》第1章第1节译为“耶稣基利斯督之仆保罗,被召为使徒,分派事神之福音。”[14](P48)可见,马礼逊在这里沿袭巴设译本,把“God”译为“神”,而且从译文中可以看出,马礼逊译本较巴设译本在句读上更符合中文习惯。当然,马礼逊所受天主教译本的影响不仅仅来自巴设译本,据说他为了学会表达基督教的中文词汇,到中国后还阅读了大量用中文写成的基督教书籍。[15](P111)
马礼逊在翻译中坚持使译文忠实、明达和简易,认为中国的经典文体如《四书》、《五经》等不适合于《圣经》翻译,他说:“中国有学问的人,像黑暗时代(指中世纪)欧洲有学问的人一样,认为每种受推崇的书籍,应当以拉丁文书写,不能用土著方言。朱夫子(朱熹)在他的哲理论文中始别开生面。因为新观念的传达,诚不如用浅白文字为好,中文经典式的古文辞,简略至甚,只可使旧观念复兴而已。若采用这种深奥坚涩的文体翻译《圣经》,……无异于古埃及的祭司们,据说他们用象形文字来书写他们的经文,除了他们自己或少数人能理解外,真是很难再找到理解的人;又无异兰斯《新约》英译本,里面保留了许多东方的、希腊的和拉丁文以及许多深奥词句,故意使一般人看不懂。”[5](P121)因此,他认为“我宁愿采用常用字而舍弃罕见的古典字。我努力避免使用异教哲理和异教经典中的术语,我宁愿被人视为俚俗不雅而不愿让人难以理解。在难懂的段落,我用我能达到的最文雅、最忠实、最不古怪的词使教义表达更为通俗”。[16](P96)
马礼逊为保证译本更适合中国语言习惯,他聘用中国学者为其校正修饰。梁发不仅是刻字印刷工,还是《圣经》中译本的润饰加工者;马礼逊的中文老师高先生也帮助校正译本中的语法。[11](P353)卫三畏在谈到马礼逊的译本时说,马礼逊及其同伴的翻译原则是忠实、明达、质朴。最忠实地把《圣经》翻译得合乎中国文法,使普通的读者也能理解。[17](P328)
《新约》为马礼逊独自完成,《旧约》则是和米怜合译,其中米怜翻译的部分是:《申命记》、《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约伯记》、《列王记》、《历代志》、《以斯贴记》、《尼希米记》等。[18](P376)全部《圣经》于1819年11月译完,1823年出版,取名为《神天圣书》,凡21卷,《旧约》称《旧遗诏书》,《新约》称《新遗诏书》。[8](P5)这是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部《圣经》中文全译本。
三、“二马译本”的影响
世界宗教史的发展业已证明,一种宗教的传播必然伴随其宗教经典的转译,而宗教经典的翻译反过来又会促进宗教的进一步巩固与发展。有论者以为,佛教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教,是与他有庄严的中文经,有极大的关系的”。[19](P76)《圣经》作为基督教经典,其中文全译本的出版,无疑对基督教在华人中的传播产生重要影响。新教传教士们不惮劳苦,执着于译经事业,也正是出于此念。马礼逊在谈到《圣经》译本对传教的作用时说:“一个外国人不精致的书面翻译,能够使一个当地人很清晰地理解《圣经》的思想和含义,比口头表达的效果要好得多。”[20](P8)伦敦会创始人勃格博士也认为马礼逊的“《圣经》中译本是实现传教目标的最重要的著作,为其他传教士的传教事业奠定了基础。”[20](P495)
梁发皈依基督教很大程度是《圣经》译本影响的结果。梁发是广东高明人,原是佛教徒,因会雕版、印刷工艺而结识马礼逊。马礼逊翻译的《新约》主要由梁发雕刻印刷。[12]梁发在刻板中,逐渐对基督教义产生印象,闲暇时,“自己查察《圣经》,见经中严禁不洁、欺骗、拜偶等罪过,于是我想:‘此是一部劝人离恶之好书。而此书之教训又得耶稣之奇迹以为证明,此书必为真经无疑’。以后我遂留心听解释圣经,而安息日读经时亦更为注意,而且求传教士为我解释”。[12]据说最感动他天良和追求真理之心的书是米怜的《耶稣传》,此书用简明的中文写成,米怜雇梁发为之雕板。无疑,这本有历史和地理背景并附着详细注解的故事,使梁发更清晰地认识了耶稣。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梁发逐步抛弃了自己原来的佛教信仰,而皈依基督教。他在1816年11月3日由米怜施洗,成为一名基督徒,并于1823年12月被马礼逊封为宣教师,成为中国第一位华人新教宣教师。
在梁发的影响下,他的妻子、儿子都信仰基督教。他还著述一些布道小册子,到处散发,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劝世良言》,此书对洪秀全以及太平天国的兴起和拜上帝教的产生都有重要影响。在谈到梁发对新教在中国传播所起的作用时,皮尧士说:“早期中国改正教(指基督新教,又称更正教或新教)教会之所以能够发达,显然有赖于梁发之力。他所作的小书和单张是破除迷信、开通思想的先锋。这位文字布道的先进,应当受今日一切从事此种工作的人的感谢。”[12]
马士曼译本因系在赛兰坡出版,所以在南洋尤其在瓜哇等地的华人中流传较广,产生了很大影响。[7])(P32)1813年以后用铅字活版印刷的各单行本《圣经》又陆续几次加印。这些中文《圣经》的一部分,通过不同的途径流传到中国,对中国教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浸礼会一派,曾长期使用马士曼、拉沙的《圣经》中译本。
此外,“二马译本”为以后新教徒从事《圣经》中译提供了蓝本。1835年,即由麦都思、郭实猎、裨治文和马礼逊之子马儒翰组成四人小组,重新翻译《圣经》。他们以马礼逊译本为蓝本而加以修订。《新约》部分于1835年完成,由麦都思作最后订正,1837年以《新遗诏书》为名,在巴达维亚以石版印行。在以后的10至12年间,中国的新教教会都以此为主要的《圣经》译本。[1](P29)《旧约》于1838年修订完成,1840年印行,大部分为郭实猎所译。郭实猎又把麦都思修订的《新约》再重新修订,以《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之名出版。此译本后来被太平天国军队采用,并且流传到民间。[3](P16)1843年英美新教各派在香港召开译经会议,决定翻译《圣经》“代表本”(或称“委办本”),马礼逊译本被列为重要的参考译本之一。马礼逊译本不仅在中国内地广为传布,据说其《新约》译本甚至流传到伊尔库次克及其他俄罗斯城市。[11](P546-547)
马士曼和拉沙译本对后世译经的作用亦不可低估。《圣经》“代表本”就把它列为重要的参考译本。由于浸礼会一派拒绝接受非浸礼会把Baptism译为“洗礼”,于是决定以马士曼和拉沙的译本为蓝本,重新修订一种属于自己的译本。1848年,高德牧师(Rev.Josiah Goddard)受美国浸礼会的派遣来到中国,专事修订马士曼和拉沙译本。他从修订《新约全书》开始,1851年在宁波出版《马太福音》,1852年在上海印行《约翰福音》。1853年,整部《新约全书》修订完成,在宁波印行。该译本后经罗尔梯博士(Edward C.Lord)修订,于1883年在上海印行,成为浸礼会的主要译本。惠志道博士(J.Wherry)在评价此修订本时认为,“通常而论,这比‘代表本’及麦都思译本,更接近原文文法的格式,但在汉语写作的文笔上,仍能做到清通易读,殊为难能可贵。”[10](P185-187)只可惜高德牧师因健康原因,只译出《旧约》中的《创世记》、《出埃及记》与《利未记》,其余由罗尔梯博士在廉牧师(Rev.William Deam)的帮助下,于1868年出齐。此外,英国浸礼会牧师胡德迈(Rev.Thomas Hall Hudson)来华后也对马士曼和拉沙的《新约》译本进行了修订,先后分卷出版。最早印行的《马可福音》于1850年出版于宁波,到1866年,将《新约全书》出齐。
尽管马士曼未曾来过中国,但凭他杰出的《圣经》中译工作已被誉为新教在华传教的先驱。[8](P1-2)人们对马士曼译本给以很高的评价,称它为“一个出色的译本,考虑其完成的情况,这个译本给他和他的助手带来很高的荣誉”。惠志道博士也认为“经过校订,它将成为一个仍然被人们阅读并获益良多的译本。令人吃惊的是这个译本中有那么多真实的内容应用了优秀的汉语标准语,很大一部分在以后的译本中被当作‘原话’(ipissimis Verbis)引用”。[6](P51,58)总之,它和马礼逊译本一起,奠定了以后中文《圣经》翻译的基础,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亦具有重要地位。
标签:圣经论文; 马礼逊论文; 基督教教义论文; 基督教教育论文; 新约全书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旧约论文; 传教士论文; 新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