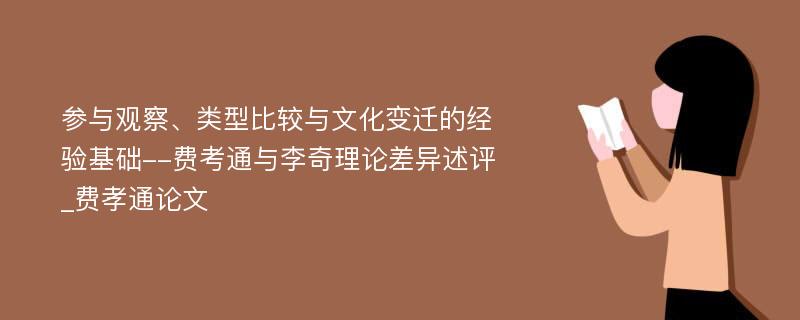
参与观察、类型比较和文化变迁的经验基础——评费考通与利奇之间的理论分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分歧论文,理论论文,类型论文,经验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最近发表的一个题为《重读〈江村经济·序言〉》的文章中,费孝通教授重述了对已故的老同学埃德荣·利奇提出的“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这一问题的某些论点。与此同时,他又批评了西方现代人类学常用的“三分法来定式”的“一般认识历史的标尺”。他说:
这种以时间里运行的一切事物总是按照先后次序一幕幕地层次井然地推演的认识框架在社会人类学里也出现了所谓社会演化规律。把人类的历史看成和其他事物的历史一般像一条流水线。这种方法的内容可以搞得很复杂,其实把人文世界看得太机械化和简单化了。(潘·马1996:24)
《重读〈江村经济·序言〉》一文的问世,给人类学家以一个重新审查现存有关从研究小型的社会发展出来的人类学理论方法的机会,他们可以研究也许是最重要的两位专家之间的争论。顺便说一下,读者还将看到科学界目前还普遍争论的一种观察类型。
费孝通关于“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这一问题的答复,人们都比较清楚了,也为大家普遍接受了。(潘·马1996:228;285)他坚持说,江村在某些方面不能离开中国其它农村而“自成一格的独秀”,江村虽然不代表全中国的农村,但可以代表中国农村的一种类型。如果用类型比较方法,将中国农村的各种类型逐个描述——参与观察通过对若干类型的认识逐步接近中国农村全貌的认识。他从不隐瞒自己的动机,他说:
“我确有了解中国农村生活、甚至整个中国人民生活的雄心……从个别出发是可以接近整体的。(费1996:132)
他很赞赏马林诺夫斯基一贯主张社会人类学就是要把人文世界从对个别的参与观察里把共相说出来的观点。
费孝通教授早在1985年根据自己的学术经历和体验来做为证据:
我常常说起为什么毛泽东同志,开了几个座谈会,到会的也不过几个人,他就能写出《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解决了中国革命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这是因为他靠两条:第一条是他出身于农村,并有意识地接近农民群众,亲身体验他们的生活,这就使他对农村经济状况、农民生活十分熟悉,并有直接的感受。第二条是他十分虔心地通过利益相同的农民去检验、核对自己的想法,使农民体会到他是为人民谋利的,因而取得了农民的信任,成了农民的知心朋友。(费1996:10)
由于这样理解参与观察,费孝通教授对中国农村与江村;个别社区与其它社区(整体)之间的关系做了如下解释:
在人文世界中所说的“整体”并不是数学上一个一个加起而成的总数,同一整体中的个体有点像从同一模子里印制出来的一个个糕饼,就是说个别是整体的复制品。(潘·马1996:14)
面对埃德蒙·利奇来说,就不是这么回事。费孝通说:
“Leach认为我们那种从农村入手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是不能概括中国国情的。在我看来,正是由于混淆了数学上的总数和人文世界的整体,同时忘记了社会人类学者研究的不是数学而是人文世界。”(潘·马1996:53)
费孝通教授讲到了以上的证据,他的批评意见,笔者认为还是有道理的。费孝通教授说,他和埃德蒙·利奇辩论的焦点在于江村能不能在某些方面代表一些中国的农村。也就是费孝通教授在开弦弓做的“参与观察”能不能观察到复杂的中国农村的一些特征?其难点是依据什么样指标去区别整体与个别社区。对西方文明背景的人类学家来说,整体与个别社区两者都缺乏明确的标准。两者的区分必须另找依据。仔细琢磨我们用以确定个别社区的方法,可以看出我们当成个别社区的群体就是某一群当地人(土著)谈出的自我称呼相同的人。当地人(土著)告诉你,说他们这一群体有历来相同的自我称呼。他还告诉你,你们与另一种或几种群体交往也是不可缺少的。如果我们称前者为个别社区,后者称为整体社会或其余社区,那我们的区分依据只是当地人(土著)关于自己行为的解释和习惯性分类。这当然是区分这一整体与另一种群的一种有效的方法。但社会科学的基本要求认识是,我们要努力极其小心地观察别人对自己所做所为都说明了什么话,才能区分他们所说的话是否可靠。或用E·迪尔凯姆的话说:
当社会科学家试图研究某一种类的社会事实时,他必须努力从社会事实脱离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而独立存在的侧面进行考察。(迪尔凯姆1995:64)
毫无疑问,科学地区分个别社区与某余社区(整体)涉及很多因素。但以下因素是我们必须加以考察。区分个别社区与其余社区(整体)的依据是什么?从人类学意义上看,个别社区(如江村)与其余社区(如中国的农村)之间的最广泛的区别就是一大一小或一先一后。用行话讲:江村与中国农村之间只有时间先后间隔(一先一后)或空间间隔不同(一大一小)的人类学区分。也就是它通过以下两个问题来体现的。比如多年前费孝通做的江村调查对现代中国人类学有何意义?江村调查对当时的中国农村问题概括程度如何?现实生活中,用时间间隔与空间间隔来区别文化事件的方法很普遍存在。比如,河东的/河西的、东方的/西方的;内部的/外部的、中国的/外国的;昨天的/今天的;过去的/现在的等等。没有这些人文时间与人文空间的区别,现实生活是很难想象的。利奇以这种区别或界限很早有精湛的论述:
当我们用象征(天论是语词,还是非语词方面)把一类事物或行为与另一类事物或行为区别开来时,就在某一“自然”连续的领域之中,创造一些人为的界限。(利奇·1991:38)
当然利奇是针对个人层次说的,也就普遍意义的抽象个人的意义上说的。他的目标不是某一群体而是全人类。如果,我们把这种时间间隔与空间间隔来区分事物和行为的方法用于社区(群体)这个层次(它不是抽象的个人,而是具体的群体)的文化事件时,个别社区与其余的社区(整体)的关系变成纯粹被时间间隔或空间间隔区分了的二元关系。社区的“文化类型”与“文化变迁”概念也获得新的意义:某一社区的文化事件相对于另一个社区(或几个社区)的文化事件进行对比时发现由于时间间隔不同而产生“文化变迁”(社区变迁),空间间隔不同而产生“文化类型”(社区类型)。也就是个别社区与其余社区之间的空间类型区别,还是时间类型区别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那么,这种个别社区与其余社区(整体)之间的区别的相对性概念对社会人类学会有什么样的新意义呢?
我们为获得清晰的概念不妨回忆一下泰利在100多年前提出的绝对的人文时空观。
秦利提出“初级——野蛮——高级”这个三段人类文化演化规律的前提是绝对地直线延伸的时间观念。他认为过去与现在,后进文化与先进文化的区别是绝对的,同时认为西方文化是唯一的参考系。与他的绝对延伸的时间观相对应的绝对膨胀的空间观,成为后来广泛流行的文化传播(diffwsian)概念的结实基础。绝对延伸的人文时间观与绝对膨胀的人文空间相结合时,形成了一种人文绝对中立参考体系——人类文化或某个群体的文化中存在一种绝对中立的参考体系,一切具体的文化或社区都跟它对齐。这种绝对中立的人文参考体系观是一切种族中心论产生的认识论根源。做为一名西方文明背景中成长的学者利奇始终没有摆脱英国社会人类学传统中的种族中心论的阴影。所以,费氏说:
“他在对待我们中国人研究中国农村时却忘记了这一条研究,人文世界的基本原理。……如果我像Leach教授一样安心于他对社会人类学的要求,自然可以安身立命于微型社区的观察了。(潘·马1996:15-33)
我们有了前面提到的个别社区与其余社区(整体)之间的区别相对概念之后,就有可能把各种种族中心主义藏身的最后一块禁地——绝对参考体系观念被彻底冲淡了。
利奇怀疑微型研究是否是概括中国国情的问题,实际上怀疑个别社区与其余社区(整体)之间的人文时空区别的相对性。他在《文化与交流》一书中首先区别了技术行为与表达行为、经济贸易与交流行为之后限定了他的研究范围:
个体间可直接观察到的相互作用,即功能派经验主义者感到是经济贸易的东西,被重新解释为交流行为……我们一般主题是交流。(利奇1991:7-8)
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论的基础假设是人类普遍存在“相当的永久性、普遍性及独立性”的人类活动体系或被称之为的“社会制度”,埃德蒙·利奇把老师的功能派思想,重新解释为表达与交流的信息体系并用“神话逻辑”概念来代替“社会制度”概念。他认为人类表达行为中存在某种系统和程序。那么,我们怎么样认识这个交流行为背后的整体呢?也就是怎么样观察这种普遍特征的系统程序呢?他在《文化与交流》一书中写到:
所有的社会人类学家把他们的研究课题当做人类文化和社会的变体。(利奇1991:5)
由于他预设了一种对整体或参考物。由于人类交流行为中存在普遍系统程序,他必定会变成这个彼岸世界虔诚的“奴隶”:他只能研究这个绝对彼岸世界的影子或变体。他评价中国人研究中国农村的人类学成果时这种绝对参考物的观念也必然影响他的具体观点。因为按照他的绝对参考物的观念,中国农村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或一个个社区加起来的总数。其中的某一个社区如江村总是整体中国农村的某一个变体。所以,他怀疑费孝通教授的《江村经济》能否概括中国农村的某一类型。
前面我们谈到泰利的绝对时空观与绝对参考物是一致的。西方文明中根深蒂固的机械的人文时空观是西方人类学的坚实基础,也是西方人文科学中时而复现在西方中心论调子的藏身之地。
个别社区与其余社区整体之间的相对关系表明,社区行为在利奇提出的象征层次或交流侧面上不存在绝对的参考物。因为对:
某种符号或象征,只有当它和其它某一对立符号或象征区分开来时,才获得意义。(利奇1991:54)
我们把利奇的表达行为或交流行为的这种规则再重新解释为经济贸易或技术行为就得到费孝通教授的一再提倡的“类型比较方法”,费孝通教授1938年《江村经济》的清样校阅完之后,匆匆回国,一到昆明就投身到内地农村的调查时找到了“一个没有手工业的农村”——禄村。他在《禄村农田》中写道:
我们的工作并没有以记载见闻为限,而想根据这个别性的现象来发现它所代表一种农村型式的共相。这是我所谓比较社会学的工作。(费·张1990:199)
后来费孝通可能发现他的这种“参与观察”和“类型比较”相结合微型研究的特点与一般的比较社会学的工作还不太一样,于是称它为“类型比较法”。他对类型比较法下了这样定义:
社区研究里,类型比较法就是在一个社区的社会结构里抓住某些相关项目,接着特具的搭配方式、综合成一个类型。然后再和不同的社区里见到的不同类型进行比较,揭示出它相似和相关的由来和所引起的不同后果。(费1996:267)
费孝通的社区研究或微观社会学有两个重要的理论来源。其中一部分来自异域文化的洋的成分;另一部分是来自本土文化的土的成分。他谈到微型研究时对“微”和“型”是这样解释的:
“微”是指深入到生活的实际,而不是泛泛地一般化的叙述,要做到有地点、有时间、有人、有行为。这样才能是“直接的观察”。“型”指把一个麻雀作为一个类型的代表,解剖得很清清楚楚,五脏六腑,如何搭配,如何活动,全面说明,而且要把这个麻雀的特点讲出来,它的别的麻雀有何不同,为何不同等等。(潘·马1996:55)
这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费孝通教授对“微”的论述和马氏的“参与观察”的精神是一致的。但关于“型”的论述在马氏的功能论中找不到相应的理论根据。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它是费孝通教授在中国农村的社区研究中总结出来的概念。“解剖麻雀”式的典型调查的方法是毛泽东在30年代研究中国农民问题时提出来的,后来在中国民族学调查工作中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1993年笔者听费孝通的学生谷苞教授给我们讲社会调查专题讲座课时,他也强调这个“解剖麻雀”方法。他说:
典型调查……也可叫作社区调查或社区研究。这种方法是属于解剖麻雀的方法,是解剖一只麻雀的方法,来了解其它所有的麻雀。这种方法所以能够成为一种科学的方法,是由于事物的共同性总是大于特殊性,共同性是通过特殊性来表现的。
谷苞教授虽然用了一些接近于哲学概念的词语,但他对“解剖麻雀”的方法的注解与费氏的对“型”的论述是十分一致的。所以与其说费孝通教授的“类型比较法”受了史禄国的影响,还不如说是中国本土文化的文物。中国农民问题的调查实践以及中国古代智慧的特点决定了人们对解剖麻雀式典型调查重视。这也成了费氏对微型研究中重视“微”的一面之外更重视“型”的一面的主要原因。(这也是他成为野马的重要因素)西方社会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来说,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很少涉及社区与社区之间关系。因为,西方社会人类学传统中的“标准”方法是西方学者从研究简单的小型的社会发展出来的。所以基本上不考虑社区与社区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由于这种原因,埃德蒙·利奇就研究像中国这样地域广大、历史悠久的复杂社会时单纯的“参与观察方法”能否够用产生了怀疑。实际上他的疑虑是有原因的。他作为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很清楚地知道马氏的“参与观察”分析的是对一个社区内在联系,而不是社区与社区之间的相互关系即类型关系。所以,从英国人类学传统的角度看,费孝通确是很像不受社会人类学传统约束的一匹野马。但从中国人文传统看他却受到了中国这个广大悠久的复杂社会的约束,他决没有随心所欲地四处乱闯,而在马氏的参与观察方法的基础上开拓了研究复杂社会的人类学新方法。
简言之,对费孝通与利奇的各自的理论和分歧作较详细的对比研究时发展费孝通教授的“类型比较”与利奇的“对立符号或象征”之间存在某种对应关系。这表明,人们用“对立符号或象征”去人为地创造的时间间隔(对立)与空间间隔(对立)是区分某一社区的社区类型或文化变迁的经验基础。这种结论会影响以下几点:
一、利奇和费孝通之间的理论分歧是表面的。从更大的理论背景看,费孝通与利奇的理论某些方面相容的。“类型比较”与“对立符号或象征”的对应体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二、只有充分地理解利奇所说的“经济贸易的交流侧面”这个角度,才能准确地把握马氏提出的“活历史”观或费氏的“三维一刻”时间观。
三、利奇与费孝通理论的主要区别在于利奇把他的老师的“人类活动体系”思想,重新解释为交流行为。而费氏明确区别“人类活动体系”与“社区”这两个概念,并肯定从个别社区可以逐步接近整体。
四、利奇与费孝通的理论虽然有很多不同点,但都从马林诺夫斯基那里继承了人类行为的互惠原则这一思想。类型的可比较性与“对立符号或象征”的可变换就是个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