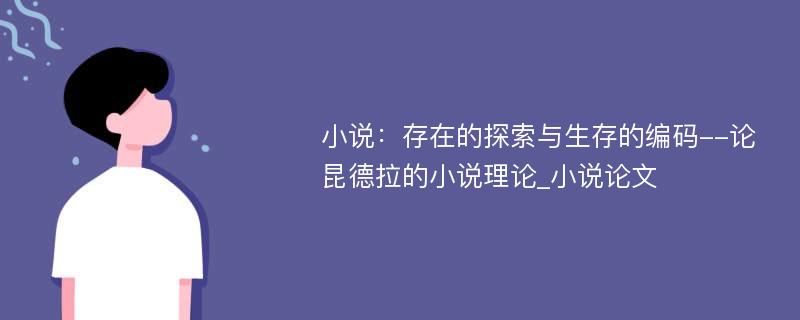
小说:对存在的勘探和对存在的编码——昆德拉小说理论管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说论文,理论论文,昆德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米兰·昆德拉(Mlian Kundera)说:“世界没有了最高法官,突然显现出一种可怕的模糊:唯一的神的真理解体了,变成了数百个被人们共同分享的相对真理。就这样,诞生了现代的世界和小说,以及与它同时它的形象与模式”[①]昆德拉的意思是,欧洲的现代小说——它等同于昆氏心目中的欧洲——起始于塞万提斯的伟大灵感。唐吉诃德就是在“没有最高法官”的世界里,呼吸“相对真理”空气的第一人:因为绝对的、唯一的真理自塞万提斯起已不复存在,善恶的界限也因之失却了衡量的准的。最伟大的激情,甚至包括据说是生生不已的爱情,在现代欧洲只剩下一具骷髅般的回忆。
不错,西方人曾经寻觅过不少欲使“绝对真理”青春常驻的秘方。他们首先找到了众神,从众神的住处找到了泉水,用泉水给绝对真理美容;后来,又从众神中找到了单独的一个神,似乎所有的嫦娥霜与洗面奶都在他手中,于是人人都呼它为“我主”、“上帝”。上帝对他的子民不赖,因为在上帝的天平前,一切都是清楚明白的“善就是善,恶就是恶,两者之间伴若泾渭,形同水火。但忘恩负义的人们逼了主的宫,让理性禅位继任新一届教主。西方人相信自己的理性可以穷尽世界,所谓“给我一个支点,就可以掀动地球”(阿基米德语),成了他们自信力的绝好写照。他们乐观进取,“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在对世界的体认中抵制了人与世界的分裂,一切都是清楚明白的:在理性神圣的法庭上,真伪、美丑、是非、善恶、曲直……纤毫毕现。而塞万提斯之后,米兰·昆德拉认为,欧洲,它开始进入自己的现代。现代的欧洲社会把人的“生活世界”,即胡塞尔所谓的die lebenswelt,仅仅折合成社会职能,人约等于某部机器上按步就班的螺丝钉。而历史,人类生生不息的感情的舞台,则被简化为若干事件:在近乎真空的沙漠上,孤零零飘动着的仅是事件的灰旗——人在事件之中,也被看作事件,人终于无可奈何地匿退了。这同螺丝钉的称谓并无实质性的不同。最要命的是,事件又被简化为有倾向的评注释:这种倾向来自于善恶失却绝对界限后,人们由此而产生的各执一端,亦即中国民谚所谓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昆德拉形象地称此过程为“人处在一个真正缩减的漩涡中。”[②]激情蜕变为骷髅,鲜活的感性转而为僵直的方程式,上帝的形象只差一点就印在纸钞上了,而自由倒真已印在纸烟盒上,被瘾君子完事后随手抛弃。[③]于是,唐吉诃德只得从家中出来,并不是到上帝给他指引的地方去,而是一头栽倒在风车前;帅克(哈谢克《好兵帅克》)把整个世界当作了一个巨大的筐子,装在里边的不是黄金,不是苹果,也不是万物之母,据说只是笑话;约瑟夫·K(卡夫卡《城堡》)在一纸过时聘书的召引下,以土地测量员的身份徘徊在城堡之外,终生不得其门而入,只好在城堡派出的两位联络员面前,毫无隐私权地宽衣、解带、做爱;普鲁斯特与乔伊斯只得命令自己的主人公从根基不稳的外部世界走向自己伟大的内心。可是,内心难道当真稳定如泰山么,在“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叶芝语)”之后?《追忆似水年华》和《尤利西斯》似乎早已对此作出了回答……。耶稣在十字架上呼天怆地地喊:“为什么抛弃我?(Whyhast thou forsaken me)?知识累积,工具发达,人类文明不断前进之后,迎来的不是人与世界的亲和而是分离,是绝对真理的丧失以及灵魂的惶惶不可终日。当然,还有枪声、大炮声,原子弹也把蘑菇云升在天空,说是让人避雨。真是“一夜湘君白发多”。且听东半球的王国维像是印证一般的声音吧:“人生过处惟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欲语此怀谁与共,鼾声回起斗离离!”[④]
昆德拉欧洲现代小说起源论,已逻辑地隐含了一个结论:要用小说为形式形象地展示这一“真正缩减的漩涡”。在昆德拉看来,这正是现代小说伦理学的最高道德律令。现代小说伦理学的内涵是:发现只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而且必需要有所发现;否则,被判为道德罪不言而喻。让人好笑的是,昆氏自称“绝对”早已丧夫,而“最高道德律令”又必需服从面对这一悖论,昆德拉认为,连续不断地发现,对从前小说未曾发现之物的发现,这一进程构成了两方的现代小说史。其实,所有真正的,伟大的小说莫不如是。昆德拉所谓的西方现代小说要去发现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是“自我”(ego)。“所有时代的所有小说都关注自我这个谜。”[⑤]昆德拉说。然而,现代小说特殊的“自我”又是什么?
古希腊的最高智慧据说由一句格言来承担:“认识你自己。”大约至少在那时,就已为西方关注自我的历史奠下了第一块基石。“我们是谁,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往何处去?”的问题曾深深苦恼过塔西提岛上的法国画家保罗·高更。[⑥]在漫长的西方史上,“自我”要么被理解为众神的旨意(古希腊、古罗马),要么被看作是一神上帝的法则(中世纪)。在此时,自我是确定的,因为它耸立在唯一的真理之上,唯一的世界之上。上帝被推翻后,自我失却依凭,笛卡尔一句:“我思故我在”,为惶惶有如丧家之犬的西方人指明了暂时的方向。在笛卡尔眼中,只有唯一的、确定的“我思”的自我才是唯一可凭的依据,人以此为自己设定世界。这一切莫不让人想起了古希腊的阿布德拉(Abdera)人普罗泰戈拉的宣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⑦]难怪老黑格尔要夸笛卡尔“勇敢”,昆德拉也认为黑格尔这么说“是对的”。但是,令西方理性主义遗憾的是,笛卡尔由“我思”出发,依然为上帝保留了地盘。上帝从笛卡尔理论的后门溜了进来,偷眼打量无可奈何又哭笑不得的理论创始人。其实,听笛卡尔的口气,“我思”不过是上帝的别名。[⑧]如此看来,人的自我,昆德拉所谓的欧洲现代小说要去发现的自我,显然不能在笛卡尔的自我中去寻找。因为不管怎样说,笛氏的“自我”依然是确定的;这与昆德拉眼中的现代精神不合拍。由于上帝(或以理性面目出现的继任上帝)的死去,真理便变得相对、模糊;与此相应,现代人的自我也应该是相对的、模糊的。然而,这个玩艺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昆德拉指出,自我是由对存在的疑问的本质决定的。疑问自然来自真理的相对性,模糊性。由此,小说要发现自我,就得去发现现代欧洲人的存在。当小说家在创造一个想象的存在时,就面临着这样两个难题:存在是什么?通过什么才能抓住这个存在?回答了这两个相关联的问题,小说要发现的东西就立在其中了。捉住存在,捉住那个自我对于存在的疑问的本质,也就同时发现了现时代的自我及其存在。昆德拉直截了当地供认:小说这个东西就是,就应该是建立在它上面。“小说家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预言家,他是存在的勘探者。”昆德拉说。[⑨]
海德格尔曾经骄傲地指出,存在问题由古希腊提出后,便一直处于遮蔽状态,现在该由他老人家来“去蔽”了。这口气宛若张载说自孟子后,儒学便被人忘记了。海德格尔把自己看作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经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⑩]的首选之士。但昆德拉轻蔑地否决了海氏的狂妄:“随着塞万提斯而形成的一个欧洲的伟大艺术不是别的,正是对这个被遗忘的存在所进行的勘探。”(11]存在,在昆德拉看来,就是当下时空中人的本真处境。这与在海氏处大有本体论性质的“存在”概念大异其趣。由于绝对真理的存在与否,直接导致了人的自我的或确定或模糊,按照昆德拉的说法,存在也因此有了确定与模糊之分。
二
小说中的人物,不是对一个活人的模拟,而是作家想象出来的人,是一个实验性的自我。这个实验性的自我对其存在进行追逼寻问时,存在本身显示出它在现代欧洲的相对和不确定。然而,小说如何以语言形式来塑造实验性的自我,来生成小说本身的?或者说,小说如何扑捉住这个自我,这个存在呢?用语言和形式为存在编码,昆德拉毫无迟疑的说,“给它一个词,捉住它”。(12]
任何小说都是以人物在其中的活动来展示自身,因而人物的行动堪称小说永恒的问题。人物在行动中生成自己的性格,因而一步步完成对存在的勘探。人物在小说中的行动构成情节,这不言而喻;情节与性格、与对存在的勘探三位一体,这就是昆德拉小说创作论的核心。不仅如此,情节本身还有个生动与否的问题,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因为它直接与小说要发现和展示的东西是否饱满,复杂密切相关。昆德拉坚持认为:“使一个人生动意味着,一直把他对存在的疑问追问到底。”(13]这就命定了人物的行动无休无止,与小说共呼吸相始终。因此,给存在编码,实际上就是给人物的行动编码。而所谓行动,亦不过是现代人对存在疑问的过程而已。因而,捉住存在,就是捉住人物的行动,并给该行动一个词——一个充分展示其存在范畴的词。
过往的小说家特别注重人物在行动中的巧合。“无巧不成拙”,“说是迟,那时快”,往往都是“巧合”的别名。它和读者之间有一个先验的合同:小说家应尽量给读者提供主人公尽可能多的信息,关于他的身世,他的外表,他的职业,他的七大姑八大姨;小说家应该给读者展示主人公过去的生活史,因为据说由此可以推知该主人公未来的行动。而这一切,差不多都在“无巧不成书”的奇遇、巧合中生成。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着《十日谈》就足够了。据说这样可以保证故事的完整性。在这种小说里,主导性人物,主导性情节,主导性情绪,一手遮天地独霸了作者和读者的视野,让人无法旁顾。但是,实际生活往往并不如此,并不符合这种主线因果导控的模式。一个人往往处在两个、三个、四个乃至更多更多的因果线索交叉之中。对于活生生的人,你不得不承认,每一线的因果之外还有大量其他的物事与物相呈现,并成为我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这样万端纷芸的因果网络里,小说的主线霸权(即无巧不成书带来的故事完整划一性)又有多少合法地位呢?(14]时值现代,人物的存在,因其相对和不确定的性质,在昆德拉这个新一代约伯的天平上,其范围与内涵已达到了无限复杂的境地;因而只把人物的行动建立在纯粹的巧合上,并满足对这一巧合作简单的叙述,很明显,它限制了小说对复杂、深层存在的有力挖掘,减少了小说对存在的认识能力。昆德拉对此极为不满,他认为,小说形式无限多样,才能适应于已趋无限复杂境地的存在。因此,对现时代的存在、行动的编码方式也必需多样化。对小说的形式(编码)进行深刻改革,此其时也。
昆德拉撕毁了合同。他首先要求自己在技术操作上,必须要有一个彻底剥离的新艺术方式。所谓剥离,就是离题。昆德拉的小说首先也要虚构故事,让人物在故事中行动、长大、穿着语言——符码的外衣;然后,便于其上构筑主题之巢——也就是直接进入了对存在的分析、勘探。主题与故事(行动)有时结合在一起,这与从前的小说并无二致;而有时,昆德拉强调,主题一味在故事中发展,人物一味在故事中行动,难免流于平淡。”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为了逃避平淡的宿命,昆氏干脆声称可以让主题与故事分离,让主题在故事的真空处独立发展。此即“离题”之谓。在昆氏长篇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作者抛弃正在叙述的故事,直接切入他要攻克的主题之一——媚俗。昆德拉把他的特丽莎的故事置诸脑后,专门分析人物内心深处,存在的本质深处的媚俗倾向,以及媚俗为人带来了怎样的后果。(15]这样一来,小说的话语空间陡然增大,人物的行动舞台平地起高楼,人物的性格在作者直接的阐释中更见丰满。你得承认,艺术恐怖主义分子昆德拉的确是成功了。
其次,昆德拉要求自己必须要有一个对位式的新艺术,即叙事与梦相连一体。这一特质,在“诗歌批评式”的《生活在别处》里表现得尤为突出。昆德拉专门为主人公、青年诗人雅罗米尔写了一章梦的传奇:雅罗米尔在梦中与一个已婚妇女偷情,并与妇人一道杀死了她的丈夫。鲜血染红了梦境。(16]这样做是为了深刻展现雅罗米尔不堪母爱而在潜意识深处对母爱的反抗。”如说卡夫卡是以差不多完全写实的手法展现人物在现实中合乎逻辑的“迷梦”,而这梦想不过是罩在叙事眉宇间的一层淡淡淄衣,那么,昆德拉可谓滑得更远:他直接写梦,写与整个故事看起来竟是毫无关系的梦。的确,雅罗米尔梦中出现的妇人在小说中再也不曾出现过;当然,她也仅是在梦中才能出现的无逻辑的人物和小说结构上有逻辑却不会再次出现的道具。昆德拉不要求故事的完整性,唯求人物对自身存在的追寻的完整;为此,他就得想办法拓展人物的生存空间,以便对存在的疑问于此尽情展示。只有这样,也许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雅罗米尔的生命中的每一段落都与诗人兰波、济慈、菜蒙托夫……等诗人生命中的某一段相对应,如同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戏中戏一样。在此,昆德拉造就了一个包纳整个欧洲的巨大舞台,让各各不同的存在共同具有着某一方面的相似,如此,也就把这一存在特质的普遍性推广到无限开去,并以此共同具有的方面加深了对存在的勘探。
再次,昆德拉要求自己必须要有一个专具小说特点的论文式的新艺术。昆德拉知道,对存在的追寻势必会让小说走向哲学。所谓“专具小说特点的论文式的新艺术”,就是对主人公的存在状态所做的哲学式分析。这一分析与叙事若即若离,作者像一个文学评论家一样,分析主人公行动中蕴藏的哲学意蕴,其实也就是存在的内涵。《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第二章一开始,昆德拉就对肉体与灵魂做了一个很长的评论。但是,作者的思索只是在分析作品中的人物——特丽莎。这种思索也只有在特丽莎身上才有作用,因为这是特丽莎看待事物的方法:她渴望肉体的展示,却又害怕展示;她渴望肉体的快感,却又害怕它无法与灵魂的愉悦合二为一。她的丈夫托马斯老想在不同女人的肉体上,寻求那宝贵的然而是可怜的百万分之一的不同。在托马斯处,性交与爱情、与灵魂风马牛不相及,八杆子打不着,而特丽莎于此却非常矛盾。就在这种思索中,特丽莎在当下时空中的本真境况被凸现了;而这,昆德拉告诉你,正是存在的定义。
人物的行动是在历史中,时间中的行动。对行动的编码,不可避免地将涉及到历史本身。在现代,欧洲有两种小说,一种被昆德拉谓之为“小说化历史编纂小说”,即“说明”一种历史境况的小说;另一种是审视“人类存在的历史维度的小说。”(17]前一种要求较为认真的写实态度,这种小说实际上是“历史事件的小说编码”。昆德拉认为自己的小说应该是后一种,它是“人的存在历史的编码”。正因为昆氏把自己的全部重心放在对存在史的揭示上,所以,他不大看重历史在小说中的份量。对于历史背景的描写,他尽量简化。在《为了告别的聚会》里,作者把其全部人物都置于捷克的政治高压这个大背景下。可昆德拉并没有正面写高压政治,高压政治的音容笑貌在一个反复出现的细节中行到了展示:政府号召捕杀城市中的狗,以及人们如何战战兢兢然而又是虔诚地执行这一命令。不断有逃亡的狗从故事中探出头来。在此背景下,昆德拉只抓住那些能给人物创造一个有揭示意义的存在境况的历史氛围。在《玩笑》中,卢德莱修对朋友开了一个政治玩笑,结果他看见,他所有的朋友与同学都轻松举手赞同将他从大学开除;这一景观使昆德拉让他的主人公悲哀的、清醒地知道,如有必要,他们也会举手同意将他送上绞刑架。经过这么一番简化描写,历史的境况跃然纸上,人在历史中的存在也被点化出来,据此,昆德拉顺着卢德莱的思路为人下了一个定义:“人,即一个能在任何情况下把身边人推向死亡的人。”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事吗?让人惊奇的是,这个结论只建立在对历史的简单叙述之上——他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了生存环境显透出的存在的意义本身。
历史在昆德拉眼中,不仅可为小说人物创造一种新的存在境况,而且历史本身也应当作为存在的境况而被分析和理解。在《生命中不断承受之轻》中,捷克领导人杜布切克被苏军逮捕后,被迫谈判。杜布切克回国发表了一次电视讲话,有着运动员体魂的捷克领导人讲话时不断喘气,在句子与句子之间做着漫长的停顿。这就是昆德拉揭示出的软弱,他认为,软弱是存在中一个很普遍的范畴。“在面对一个更强大的力量时,人总是软弱的。”(18]“布拉格之春”作为历史事件在昆德拉笔下被理解为“软弱——强大”的双螺旋:面对苏联,捷克弱软;要是苏联面对一个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捷克呢?软弱与强大将有不同的主人。这就是历史本身作为存在境况而被理解和分析。
昆德拉对存在、对历史采取了一种近乎残酷的幽默方式——让人无法会心一笑的幽默。卢德莱修开了政治玩笑而颠沛流离十数年,它不是悲剧,据说仅是个玩笑式的,残忍的幽默:号称为人民谋利益的政治,因为一句无伤大雅的玩笑而将玩笑制造者打入另册,这本身不是更大的玩笑又是什么?绝对真理失去了,世界处在相对性之中,而在地球某一处的某段时间里,政治充当着新上帝的角色。谢天谢地,它并没有完成自己充当绝对的、唯一的真理的使命,没有能解存在的相对性与不确定性于倒悬。“把极为严肃的问题与极端轻浮的形式结合在一起,”昆德拉说,“从来都是我的雄心。”(19]在他看来,幽默就是那极为轻浮的形式的眉宇间的高贵气质。历史,确确实实是婊子养的,它惩罚恶人,总在事后,它折磨良善,却总在进行之中。因此,昆德拉号召人们不要去相信“历史能评判一切”这句骗人的口号;它曾经为善人与恶人,弱者与强者找到了共同的借口。因此,对付这种东西,在除了以幽默的方式甚至调笑的方式揭露它的丑恶嘴脸外,难道还值得更严肃认真地对待吗?“幽默:天神之光,把世界揭示在它的道德的模棱两可中,将人暴露在判断他人时深深的无能为力中;幽默,为人间诸事的相对性陶然而醉,肯定世间无肯定而享奇乐。”(20]昆德拉大声赞美道。
所有这一切都在昆德拉所谓的“存在的编码”(行动的编码)中获得实现。他用许多不同的词汇作为范畴,捕捉到了不同的存在境况,并围绕着语词来阐释存在。在这里,存在就等同于语词。为表明他全部小说对存在的揭示,或者说对各种存在的揭示,昆德拉为自己的小说编了一个小词典《七十一个词》(21]。详细解释这七十一个词(存在的编码化)是昆德拉的而不是本文的任务。本文只是想说明昆德拉早已阐明过的:揭示存在,就是揭示行动,揭示人在行动中完成自己对存在的追问;小说在本来意义上是对存在的勘探,在技术操作意义上就是用特殊的词对存在的编码,对行动编码,小说家对行动与存在编码的关键仅在于:“给它一个词,促住它。”
注释:
①见昆德拉《被诋毁的塞万提斯的遗产》,载《小说的艺术》,三联书店,1995年,第5页。
②昆德拉《被诋毁的塞万提斯的遗产》,载《小说的艺术》,三联书店,1995.第16页。
③艾青在《智利的纸烟盒上》有生动的描述,见《艾青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④王国为《人间词》。
⑤《关于小说艺术的谈话》,载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第20页。
⑥毛姆《月亮与六便士》,见《毛姆文集》第三卷,伦敦,1980年。
⑦《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54页。
⑧参见张志扬《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4页。
⑨见昆德拉《被诋毁的塞万提斯的遗产》,载《小说的艺术》,三联书店,1995年,第13页。
⑩《近思录拾遗》,《张载集》,第376页。
(11)参见Essays on Compaiative Literature and Lingustics,Sterlingpublishers PTV.P98—101.
(12)《关于小说艺术的谈话》,载是德拉《小说的艺术》第28页。
(13)《关于小说艺术的谈话》,载是德拉《小说的艺术》第33页。
(14)参见韩少功《马桥词典·枫鬼》,载《小说罗》1996年第2期,参见L.S.D——APROFILE,伦敦,P30—34。
(15)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第十章,作家出版社,1993年。
(16)昆德拉《生活在别处》第二章,作家出版社,1993年。
(17)《关于小说艺术的谈话》,载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第34页。
(18)《关于小说艺术的谈话》,载是德拉《小说的艺术》第37页。
(19)昆德拉《关于结构艺术的谈话》,《小说的艺术》,第94页。
(20)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1页。
(21)参见昆德拉《七十一个词》,《小说的艺术》,第116—151页。
标签:小说论文;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论文; 文学论文; 小说的艺术论文; 米兰昆德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