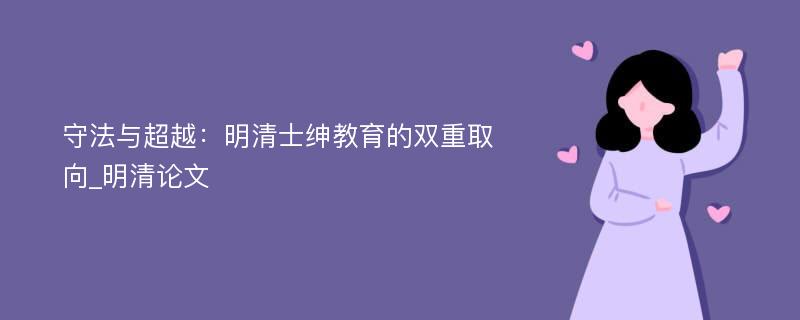
恪守与超越:明清士绅教化的双重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士绅论文,明清论文,取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08)05-0082-06
在政府自上而下的“单轨”式权力筑到县衙门便停止的传统行政制度下,士绅教化构成了明清乡村教化的主导形式和核心内容。处于转型时期的明清社会的士绅教化并非是对前代教化精神“单向度”的延承。事实上,它在内化前代教化合理性因子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明清时代的新质,是传统因素与时代特色相互作用而成的交融物。在新旧文化的冲突杂糅及社会转型未完成的背景下,明清时期的士绅教化生成了恪守与超越传统教化精神的二律背反的双重性格。明清士绅教化的双重性格,有力地解释了明清士绅教化图式嬗变的内外缘,集中体现了近代中国乡土社会变迁的轨迹,构成一个观察过渡性社会群体角色转型的深度历史透视点。
一、恪遵传统教化内核
明清士绅教化权力来源于官方赋权与自觉内生之间的博弈,是官方赋予士绅科举功名后在地方获得公共身份的产物。教化权力的来源机制直接塑构了教化图式,明清士绅教化权力的双重来源生成了士绅教化图式的一体两面——既有官方意识形态的一面,又有地方文化蕴意的一面。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经宋明理学家改造后的儒学依然是其确定社会秩序与解释现象的价值依据和心理本原。这种上下一致遵从儒学的传统使得明清士绅教化赋有浓厚的儒学余韵。
具体来说,一方面,明清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已经给社会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打上了某些烙印,但建立在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顽强结合基础上的“超稳定”的宗法专制制度,尚未进入全面瓦解的阶段。这种“超稳定”的宗法专制制度与根深蒂固的小农经济为传统教化精神的延续创设了极好的温床。另一方面,传统教化精神在明清乡野民间的盛行,还在于其背后有科举功名的支撑。1896年,王筠说:“教子者当别出手眼,应对进退,事事教之,孝悌忠信,时时教之。讲书时常为之提倡正史此等事,使之印证,且兼资博洽矣。学问既深,坐待功名;进固可战,退有可守;不可疾想功名。”[1] 在科举制度未废的前提下,士绅乃至预备士绅并不以渐趋腐朽的传统教化为耻,反以为荣。正如张仲礼先生所言:“官学和整个科举制度旨在迫使绅士以及谋取地位的人沉湎于“科举生涯”,将他们的思想导入以纲常名教为重点的官方思想渠道中去。再由接受灌输的绅士将这些儒学原则印入民众的头脑中,目的便是造就一个满足于清朝统治和现存社会结构的清平世界[2](P221)。概言之,大传统与小传统均未发生根本异动为明清士绅教化提供了传统意义上的价值基础。由于所传递的文化尚未失去效用,所以传统教化理念依然在明清时期得到社会的尊重与推行。
1.伦常道德教育
《说文解字》释“教”义为:“上所施下所效也。”“化”:“教行也”。教化由此可引申为教行迁善之义,其主旨是以自然的方式、在尊重个人自由的基础上,促使人的精神的成长、发展和自我生成,它包含着精神培育和精神的自我创造相结合的意蕴,道德教育是其本真形态的内在规定性和应然诉求。同前代一脉相承,明清士绅教化的首要任务就是依照儒家伦理培养子弟及乡民的高尚德行。王士禛追忆其高祖泺川公教子时说:“公教诸子最严,家训云:所存者必皆道义之心,非道义之心,勿汝存也,制之而已矣。所行者必皆道义之事,非道义之事,勿汝行也,慎之而已矣。”士绅希望通过这些被刻于“厅事屏壁间”的家训勉励子弟自修德行[3]。姚舜牧在《药言》的开篇语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此八字是八个柱子,有八柱始能成宇,有八字始克成人。”[4](P1) 与前代稍显不同的是,明清士绅教化更多地使用浅显易懂的文字表述族人需要遵守的规则,如歙县泽富王氏宗谱规定:“为子者必孝顺奉亲,为父者必慈祥而教子,为兄弟者必以友爱笃手足之情,为夫妇者必以恭敬尽宾对之礼。毋徇私乖义,毋逸游荒事,毋枉法犯宪,毋信妇言以间和气,毋削博弈以废光阴,毋耽酒色以乱德性。”[5] 此时,去抽象化的儒学伦理以具体的道德行为规范的形式进入了世俗生活世界。
明清时期儒学的世俗化或日常生活的德性化与朱熹密切相关。朱熹可能是继程颐之后,最自觉地将自己的思想世俗化、生活化,进而形成实际制度的一个学者。有学者指出,《朱子家礼》撰述的意义,“意在将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环节,诸如出生、婚礼、丧葬以及祖先祭祀,都纳入儒学的领域之内”,并显示了“宋代理学家怎样试图在行为领域,而不仅是在思想领域占据主导地位”[6]。从徽州的方志、家谱看,朱熹对徽州的思想秩序和生活秩序的影响是非常广泛而深远的,朱熹所制定的《家礼》,是徽州各族“家典”、“族规”的蓝本。族人如果能够身体力行这些礼仪规范,那么就被认为是有德性的人并受到人们的敬重。再如,《余姚江南徐氏宗范》对于家庭伦常有以下规定:“伏靓太祖圣谕: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务要子供子职,及时孝养,毋遗风木之悔。至如伯叔,去父母特一间耳。凡言动交结,俱宜礼,毋得简亵侮慢,以乖长幼之节。诂终故犯者,轻则槌之,重则呈官究罪。”[7](P271-274) 可见,此家规全面论述了家族成员需要遵守的日常行为规则,道德教化意蕴深刻浓厚。需指出的是,明清官方权力的介入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侵蚀了士绅教化的精神培育意蕴,但尚未解构士绅教化对道德诉求的本真形态。在士绅教化权力的笼罩下,一种从道德认知到道德实践的伦理道德同一性被逐渐建构起来,并奠定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世界。
2.人文主义情怀
明清士子获得士绅身份的前提是通过一定级别的科举考试。明清科举考试的内容依然以儒家经典为主体,因而士子对儒家经典必须有精深的阐释才能登科及第。儒家经典的特征之一是其蕴涵的倡人本、主仁义、重教育的人文理念,如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礼,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可见,儒家文化就是要在人的具体生命中凸显出这“几希”,以开启其内在于人的生命、生活中的人文世界。进一步说,儒家文化始终肯定在人的生命中有一个完全可以自我控制的道德主体,只要去做操持涵养的工夫,这个主体就会在生命中显现。因而粗略地说,儒家教化透显的是一种以“礼仁”为核心的人文教化。从此角度来看,饱受儒学教育的士绅必然受到儒家人文理念的浸透,其教化图式也将体现出人文主义特征。诚如马克斯·韦伯所言:“中国的官吏是或更正确地说,一开始就是类似于我们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一种以古代语言遗物来接受人文主义教育和考试的士……这一阶层由于它习惯于在古人之后亦步亦趋,这已决定了中国的整个命运……”[2](P4-5)
公允地说,儒学文化根基仅为士绅教化人本倾向的孕育提供了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化则要依赖于宽松的政治环境。有学者指出,明清时期的帝制中国存在着相对独立于国家的基层社会或乡土社会。笔者认为,正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二元结构催生了士绅人文教化的由隐转显,促使士绅教化生成了异于官方教化的自为风格。这种人文主义情怀主要表现为:士绅群体作为支配乡村“内生权利结构”的地方权威存在着与国家疏离、异构的一面,在一定场域内,他们依凭自己的教化理想及民众的主体需要实施教化。以惩罚方式为例,士绅对严重触犯家规族法的子弟的惩罚也体现出人文性的内涵。例如《郑氏规范》规定:“子孙倘若私置田业,私积货泉,事迹显然彰著,众得言之家长,家长率众告于祠堂,击鼓声罪而榜于此,更邀其所与亲朋告语之。所私即便拘纳公堂,有不服者告官,以不孝论”;“子孙赌博无赖及一应违于礼法之事,家长度其不可容,会众罚拜以愧之。但长一年者受三十拜,又不悛,则会众而痛棰之;又不悛,则陈于官而放绝之,仍告于祠堂,于宗图上削其名,三年能改者,复之”;“子孙倘有出仕,有以脏墨闻者,生则于谱图上削其名,死则不许入祠堂”[8]。这与“示众柱、绞刑架、断头台”等剥夺生命与践踏灵魂的惩罚工具相比,无疑凸显出明清士绅教化尊重民众生命存在及主体性的特征。当然,这种人文主义情怀具有明显的重人伦轻自然、重群体轻个体、重个人的义务和道德人格的独立性轻个人的权力和自由的倾向,其成立需借助于国家对地方较为专制的教化这一参照系统。换句话说,国家通过刑法对民众进行“惩罚”,而士绅则常常是通过教育进行“规训”,而后者正如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说的那种“严肃的戏剧”一样,“当盛大的公开处决的恐怖仪式逐渐让位给这种严肃的戏剧——后者的场面丰富多彩,更具有说服力,而且公众的记忆将会以传闻的形式复制法律的严峻话语。”[9](P275-276)
3.中介身份衍生的双重意义
明清士绅教化作为一种地方性实践,客观上催促了乡民对宏观的共有价值的认同与遵守,降低了政府治理地方的成本。然而,士绅教化不能因此被视为政权的延伸。士绅的中介身份意味着其教化的意义还在于遏制国家权力的膨胀、扩展宗族的威权及护佑乡土社会的自主性。事实上,士绅凭借长老权威,有效地制约了横暴的专制统治,构建了人心正、风俗美的和谐乡村。正如葛兆光认为:“士绅作为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中介,他们由于考试、仕宦、荫封等等途径,在地方上成为领袖,在与国家的协调中,他们也促进着国家的法律制度、道德伦理、文明观念的扩张,不过同时也在抵抗着国家对于民众个人的直接统治,有时成为民众利益的代言人,对抗着国家无限膨胀的权力。”[9](P276) 换言之,士绅这类支配着乡村的“内生权力结构”固然有着与专制国家共生、同构的一面,但也的确存在着与国家疏离、差异乃至紧张冲突的一面。
从文化层面来看,“修己”和“治人”是儒家君子的基本道德诉求,这两方面又是无法截然分开的。反求诸己是推己及人的前提,推己及人是反求诸己的外推。余英时认为,君子在道德修养方面必须不断地“反求诸己”,层层向内转。但是由于“君子之道”即是“仁道”,其目的不在自我解脱,而在“推己及人”,拯救天下[10]。也就是说,君子不能停留在“反求诸己”的内转层面,而要向外推。明清政府显然无法为那些有功名的士绅提供官方身份以满足他们安百姓的需要,士绅对推己及人品质的追求与现实供给出现了断层。因而在明清时期,具有儒家君子性格的士绅在推己及人层面与前代相比发生了一定形变。一方面,具有儒家君子性格的士绅不能承受遗失推己及人品质之重。另一方面,政府未能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政治资源以安人。两难困境迫使士绅退而求其次,即依托地方公共身份补偿官方身份的缺失,援借文化权力生成的教化达成“立人”、“达人”的道德与政治夙愿,继承“在朝则美政,下位则美俗”的传统遗风。“王者之儒学”在这里实现了向“教化之儒学”的转变。
由于士绅依凭以安人、安百姓为目标的儒学作为教化的价值依据,所以士绅无论是入仕,还是出仕,其教化活动都表征出鲜明的双重性,即对内维系了乡村的原生性,对外维护了国家对地方的控制。此外,明清时期部分士绅教化活动获得官方御批的现象更为强化了教化意义的双重性,如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徽州歙县朱氏宗族的祠规获得了官方的批准。湘阴县令也批准了狄氏的家规:“阅呈《家规》十六则,均极周备,准悬示众人,共知观法。俾合族子弟,咸兴礼让而远嚣陵,本县有厚望焉。”[7](P294-297) 官方权力的渗透不仅是因为宗法思想极为切合忠信孝悌的信仰,而且,宗族也可以规约其成员使其言行更符合封建社会的行为规范。所以尽管官府有时对宗族实力的膨胀持谨慎态度,但它更为欣赏宗族在农村中维持封建伦理秩序的作用。
明清士绅教化意义的双重性也可从士绅主导的“公共领域”作为国家政权与基层社会的广大中间地带得以诠释。明清士绅主导的“公共领域”是通过地方公共管理而不是通过公共舆论和国家的政治竞争来表达私人的利益和权利[11],其范围随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演变。当民间社会强势时,它可向上侵食国家政权的权力范围;当国家政权加强对社会控制时,它又可向下伸入民间社会的腹地。应当指出,明清士绅主导的公共领域不同于哈贝马斯话语体系下的“公共领域”,它并不构成“公共权威的抽象的对立面”,而是国家和社会互动的一个中间领域。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公”领域中,国家与民间社会之间保持着合理的张力,两者之间呈现的主要是合作与协调而不是对立与冲突的关系。从此视域看,明清士绅教化的意义在国家政权与民间社会之间的博弈下生成了亦民亦官的双重旨趣,规避了朝单向化轨道运行的可能性。
二、超越传统教化经纬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内部的经济和社会变动投射到思想意识领域,即体现为宋代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的式微,与此同时,一股与正统儒家观念背道而驰的启蒙思潮渐趋彰显成型。这一思潮强调人的伦理主体性、个人道德的物质基础以及个体社会存在的近代性格,凸显实践理性与实用知识的价值。明清士绅教化作为社会机体的敏感区域,无疑受到这一思潮的浸润并显露其印记。
1.“治生”论
明中叶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西学的东渐及教育思想自身的演进,形成了普遍性的带有启蒙意义的实学教育思潮。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清代的颜元、章学诚、龚自珍、魏源等。他们从实用理性与经世致用出发,揭露了一直占据中心的维护理想主义的政治和道德秩序的儒家学说,以及一直垄断了教育和考试权力的人文知识欠缺实效的痼疾,痛斥当时教育“不以经国济民为本”的病端,进而提倡解救时弊的实学教育,要求士子“知务实学”,以“致用”、“力行”替代理学、心学末流空谈之学风。在实学教育家的促推下,实学教育成为了明清教育发展史中的一大特色和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型。
如前所述,明清士绅主要依凭儒家伦理纲常对子弟进行道德教育,使其“做好人,走正道”。另一方面,由于受到传统社会与经济结构的变动及实学教育思潮萌生的冲击,明清士绅教化日益凸显出对个人道德的物质基础的重视。士绅教化中的尊德性、道问学位置的变化,使得儒家的“重义轻利”观点徘徊在突破传统的边缘上,并由此开辟了“研习儒家经典—升官—发财”实现社会流动之外的另一体现个体价值的重要渠道。如明代姚舜牧指出:“第一品格是读书,第一本等是务农,此外为工为商,皆可以治生,可以定志……惟游手好闲……大是可畏。劝我后人,毋为游手,毋交游手,毋收养游手之徒。”[4](P5) 可见,这一时期士绅教化的目标定位在子弟“治生”层面,“治生”成为评判知识的价值尺度,一切有助于“治生”的实用知识在此获得了解放与彰显,不再是孔子所说的:“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如果说姚舜牧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地颔首默许“治生”,李贽则狂飙突进式地反对虚伪和矫饰,完全不讳言“私”与“利”。他说:“夫私者,人之心也”、“虽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若不谋利,不正可矣……若不计功,道又何时而可明也?”[12] 至清代,“治生论”在士绅当中已有“靡然成风”之势了。
明清士绅之所以强调以“治生”为先务,是因为他们认为士必须在经济生活上首先获得独立自足的保证,然后才有可能维持个人的尊严和人格。每一个士都必须把“仰事俯育”看作自己最低限度的人生义务,而不能“待养于人”[13]。士绅教化对实用知识态度的变更折射出士绅阶层“义利观”的嬗变。明清一些开明士绅认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传统义利观并不是绝对的道德律令,道德与功利完全可以统一起来,“义利者,一合而不稍离,故凡真正利己之道,未有与道德违反者”[14](P69-71)。士绅阶层这种试图以近代功利主义价值观取代传统伦理价值观的实用理性倾向,为士绅教化中的崇商心态营造了社会心理氛围与舆论基础。
2.良贾何负闳儒
自秦以后,中国传统社会的等级结构体现为“士农工商”的金字塔状的基本格局。在这一社会等级结构中,“四民并列,士属先尊”,士绅和商人阶层,一个高居四民之首,备受尊崇;一个低置四民之末,受到社会的轻蔑与排挤,二者之间有着一条难以逾越的社会等级鸿沟。所谓“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时至明清,人们的社会等级观念开始异动,出现了“工商皆本”的新气象,似有“重新估价一切价值”、“良贾何负闳儒”之势。如明清之际的“新四民论”一反传统的重本抑末、崇士贱商的价值观念,根据社会分工协作的需要,将商业提升到与本业的地位,与农业并重,认为:“农商为国根本,民之命脉也”,“重本抑末之说固然,然本宜重,末亦不可轻。假今天下有农而无商,尚可以为国乎?”[14](P45-46) 在“地狭薄不足以食”的客观环境下,明清徽州士绅也逐渐重视商业,他们试图通过对传统价值观进行变通和改造的方式否认儒贵商卑,批判农本商末,倡导“士商异术而同志”,如明中叶刊刻的休宁《汪氏统宗谱》中说:“古者四民不分,故傅岩鱼盐中,良弼师保寓焉,贾何后于士哉!世远制殊,不特士贾分也。然士而贵其行,贾哉而修好其行,安知贾之不为士也。故业儒服贾各随其矩,而事道亦相为通,人之自律其身亦何艰于业哉?”[15] 明嘉靖万历年间的歙人汪道昆也说:“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其俗不儒则贾,相代若践更。要之,良贾何负闳儒!”[16]
可见,重商倾向是明清士绅教化的一大超越。伴随着商业的逐步解禁,其他可以修身齐家的职业也逐渐由边缘移向中心。白苧朱氏家规规定:“吾家颇有田园,安能常如今日。吾之子孙为士者,须笃志若学,以求仕进。为农商者,须勤耕远贾,以宁家事。其或贫乏不能存者,或以教授为业,或税田以耕,或贷本以贸,切不可习于下流,以玷门阅。”[7](P268-270) 可见,除了那些有辱家门以及违背儒学道德规范的“贱业”,其他职业都可以立身齐家。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徽州地区,家族对子弟职业的规定则显得更为开放,如休宁范氏《林塘宗规》其中一条是:“士农工商,各习所业安生理,以遵圣谕,乃祖宗垂训大要。四民之外俱属异端,家法所禁。……今族中乃有子孙为僧道者,违训甚矣。无后为大,当自思之。”[17]
士绅教化对士与商等值视之的根本原因,在于明清以来乡村迫于严峻的生存环境而形成的讲实际务实效的价值取向。其次,由农业宗法社会向工商业社会的转折中,金钱开始日渐代替功名,成为衡量社会成就和社会地位的尺度。人们逐渐用经济成就的大小而不是文章道德的高低来评判一个人的社会价值。新的社会现实要求与之相符的新的价值观念,权势垂青财富,文人趋近商人成为不可逆转的社会趋势。连向来贱商的清廷也不得不认同“弃士成商”已蔚然成时尚:“向来官场出资经商者颇不乏人,惟狃于积习,往往耻言贸易,或改换姓名,或寄托他人经理,以致官商终多隔阂。现在朝廷重视商政,亟宜破除成见,使官商不分畛域。”[14](P81) 再次,崇商心态与晚清科举制度的式微与终结密不可分。科举制度的废止,使“读书—升官—发财”三者之间失去了天经地义的必然联系,世人再无法抱有“侥幸得第之心”。迫于生计,他们不得不闯进传统意义上受到轻蔑的商业领域。
明清士绅教化中的超越并不意味着对传统教化理论的简单否定,而是从传统资源出发,在新旧之间寻找到一个价值取向的结合点。在士绅看来,教化中的开新变革并不是割裂于传统教化的毫无渊源的断层,事实上,它可以在传统资源中寻求价值本体与诠释,例如士绅教化中的崇商心态,与其说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不如说是孔子所谓“君子务本”的主张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的具体实践。正如学者所言:“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面对天崩地裂的变局,进入新的世界语境的传统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不得不重组自己的知识系统,而在这种力图谋求适应新世界的知识重构中,拥有相当深厚历史与传统资源的中国士人,常常采取重新诠释古典以回应新变的途径。”[9](P477-478) 士绅力图依凭传统资源解释教化中新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使其依附内化于传统资源系统,然后赋予这些知识合法性与合理性。这种“出位之思”的积极意义在于它缓和了教化中的开新变革带来的心理紧张,然而也正是这种僭越性的诠释,削弱了教化的启蒙意义,阻滞了传统道德教化向现代性道德教化的转型。
[收稿日期]2008-04-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