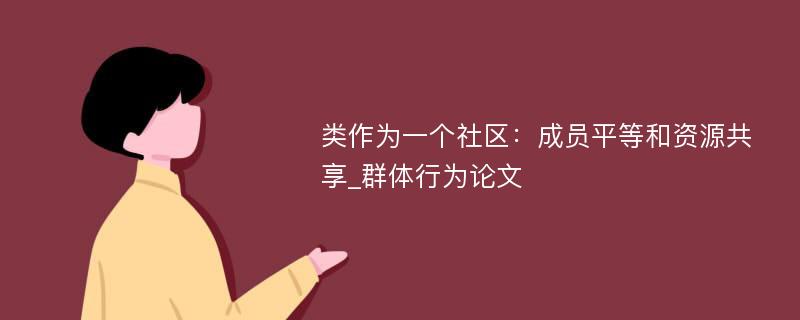
班级作为一个共同体:成员的相互平等和资源共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同体论文,作为一个论文,资源共享论文,班级论文,平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班级功能的再生和重心倾斜
当前,学校及其班级教学仍然主要维持着知识传授者的角色,但其功能似乎只是肤浅地维持着,很多时候只是把学生已经获得的许多知识再重复一遍并进行严格的评价而已。学生们从各个渠道获得知识,教师传授的系统知识只是占他们获得的知识的很少一部分。即使是这一小部分,也被各种类型的学习方式所代替,如各种定期的校外学习、网络学习等。而且当学校学习的知识逐渐由科学化、系统性、固定化向活动化、动态化、个人化发展时,建基于传授系统知识的班级教学,更是显示出越来越微弱的竞争力。当前,优秀学生只是在学校中运用自己已经获得的知识,而那些仅仅指望着在学校中、在班级教学中获得知识的儿童只能成为学习中的落后者,这正体现了班级教学传授知识之功能的失落。学校教育和班级教学的独特性和重要性似乎只是因为与考试和升学严密地结合起来了。试想,在当前这样一个信息发达的社会,如果不是因为班级教学与考试的紧密联系,学校教育与升学资格的认证的一致关系,如果各种网络学习的结果以及其他各种学习组织都能够有资格与升学相连,班级教学的优越性又能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因此,班级教学的独特性功能如果曾经是系统知识的垄断性传授,那么,当前这一功能已经并不能成为其独特存在的依据了。班级教学需要开发自己新的功能以维持自己的存在,在学校的当前功能彻底枯竭之前为它找到新的生存之本。
仔细考察,班级作为一个教育团体,它本然的功能就是教书与育人合二为一的,而它的育人方式是可以也应该充分发挥团体功能的。作为应当时代潮流而兴起的班级授课制,它既是顺应时代大规模的传授知识以适应社会对大量的“知识人”的需要而形成的,又是为培养适应大工业生产的交往方式和建立民主的社会的人的需要而产生的。班级的组织打破了儿童由血缘和地缘关系而组成的同伴关系,它使超越于亲缘关系的儿童组织得以形成。这种关系不是起源于近似自然本能的亲情,而是在非血缘的关系上靠理性和规则建立。这套规则以平等和相互尊重为根本组织原则,目的是建立一种更加民主和广泛的交往。这种广泛的平等交往就像知识的大面积传播和使用一样,是近代工业生产和民主社会对人的需要,是出于人们和平共处的社会普遍伦理的需要。
然而,自班级授课制以来,班级的显要功能一直是广泛地传播知识,班级所应该具有的让学生学会民主和平等交往的功能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它处在为获得知识获得服务的位置上,一直默默地在人们的意识之下自发地、非常不稳定地为儿童的社会性发展起着并不令人满意的效果。班级作为一个具有稳固性的群体,作为儿童长期生活于其中的早期社会组织,应该发挥它独特的群体性育人功能。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注:详见:(美)埃利奥特·阿伦森.社会性动物[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班级中的儿童并不是毫无关系的个人,而是群体中的相互交往、相互影响的人。特别是在家庭少子化的今天,儿童的学前交往和校外交往明显减少,班级的交往对儿童的社会性发展更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人的这些特征和教育的目标提供了对班级进行共同体化建设的需要和契机。作为为孩子的民主生活提供实践机会的班级生活,班级群体交往的性质对儿童的整个交往方式都将产生影响。因此,对于学校的真正的价值判断是:学校不应该是一个社会。然而它却成了一个“小社会”。“小社会”学校现状受到的批评是:它使教育关系、教育生活过早地具有了世俗社会的内涵,从而部分地丧失了这一特殊的社会组织的人文本性(注:樊浩.教育的伦理本性与伦理精神前提[J].教育研究,2001.1)。作为人文性的、非物质化的精神实体,班级应该在儿童的精神发育上体现自己的独特优势,在一个和谐的主体间性的交往中让儿童的精神丰满起来,在交往中习得责任感,学会关爱他人,尊重他人,并为建立更大的民主团体、适应更广泛的民主生活而努力。班级共同体的建立就是这样一个适合于学生的精神培养和民主个性培养的良好的组织途径。
二、把班级建设成为民主、平等的共同体
一个共同体并不等同于一个松散的个人集合体,集合体是一种自然组织,它缺乏管理和整体运行的规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随意的、自发的,缺乏共同理性,即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注:(美)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225.)。一个真正的共同体,是一个在自愿的基础上组织集合起来并由协商建立的、有规则运行的团体。它的首要特征是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平等关系和资源共享。斐迪南·滕尼斯指出,与一般的松散的社会组织相比,共同体这一人际结合具有自己的特性:它是积极的现实的有机的生命;使人拥有一切亲密的、秘密的、单纯的公共生活,使人休戚与共,同甘共苦,相互地赋有责任,相互地占有和享受共同的财产;它是人的一种真正的结合,在共同体里,尽管有着种种分离,但其显然的关系是结合(注:(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52.)。共同体中所建立的交往是一种亲密关系中的交往,是一种既能够充分地发展和发挥个性又能信奉和遵守规则的交往,是一种能够体验到自我的价值又有机会认识他人价值的交往,是一种在尊重他人的基础上获得他人尊重的交往。
班级就是要成为这样的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而且是有着独特性的共同体。与其他类型共同体相比,它的特殊性是,在更充分的意义上,它是一种文化共同体,一个精神共同体和伦理共同体。
(一)班级作为共同体的特征
第一,班级作为一个精神共同体。
在最根本的意义上班级是一个精神共同体,其功能主要是针对人的精神发展的。班级从来就不是一个物质实体,即以物的生产和分配为主要职责和目的实体,而是一个精神实体和道德实体,一个以形成人的精神为目的的活动群体,是一个时刻进行着精神交往和精神建设的实体。对于这样一个实体,它的发展目标就是达到学生精神的丰满和心理健康。说班级是一个精神共同体,就是说它要关注每个学生的精神发展,使儿童在精神上成为一个相互承认、相互关爱的统一体,使每一个儿童精神的健康发展都以其他儿童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为达到这一目标,一方面需要儿童获得智识上的发展,另一方面就是要让儿童在精神上相互信赖,促使他们获得对自己的满意感和对世界的信任。
第二,班级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
为了实现人的精神丰裕,人就必须生活在优良的文化中。这样班级不仅需要有着共同的显文化目标,传递社会的公约文化,包括为社会所承认和指向的系统的文本文化和行为文化,还需要处于一个更具有现实意义也更为流动的整体文化空间之中。这种文化就像空气一样让人沐浴其中,不得不时刻感受到它的存在。它是一种氛围、一种情绪,一种流动着的、穿行于个体之间的无形之物。它编织着儿童的现实关系之网,形成一个笼罩着个体身心的“钟型罩”。这是一个混沌多样的整体,然而能被个体精确地感知到。这种整体被称作情境。人们的全部经历和体验都要通过情境而实现(注:(德)赫尔曼·施密茨.新现象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25.)。班级作为一个共同体,就是要形成这样的能让儿童乐于身处其中的文化空间。
第三,班级作为一个伦理共同体。
为了实现人的精神增长,组建良好的文化空间,需要用伦理的关系原则如正义、平等、人道来建设班级,班级应该是在良好的伦理原则上形成的共同体,而不是建立在单纯的个人私利之上。要形成成员间良好的伦理关系,避免相互间的伤害,防止个体行为对公众的危害。对于个体而言,这种伦理关系既有既成性又有生成性,因为对它的感知和体验,既得力于别人对一定的伦理信条的信息传递,也得力于个体自己的内在特征和自我的生长和塑造。班级作为伦理共同体就是要以良好的伦理关系铸造健全的精神人格。
(二)班级共同体的形成
班级共同体的形成并不像一般的共同体那样是成员自由和自愿结合的结果,是由其成员在相互了解和认同的基础通过协商建立的。相反,班级是儿童们因一些偶然因素而“分配”到一起的散乱的“个人集”。他们不能挑选自己的共同体的组成成员,也不能任意地把某一个成员随便剔除出去,不能像一个自由组织的共同体一样可以不接纳他们认为不符合条件的人。班级形成之初,他们之间除了年龄相似以外,几乎没有已经形成的相同性。他们既不是因为共同的爱好和兴趣等联合在一起,也没有建立或认可一些真正的共同体所具有的共同的、自愿遵守的规则。他们组建共同体的前提是,必须在不改变人员组成的情况下,把班级建立成一个共同体。把班级内所有儿童都包括进来,并形成真正平等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班级共同体就是一个差异基础上的共同体。
因此,班级共同体建立的首要工作就是使成员从心理上产生集体认同,既把自己同时也把班级中的任何其他人认作是平等的一份子,在此基础上逐渐建立一致承认的规则。这里有几个必要的过程。
首先,在班级中,儿童要明确他与谁一起生活、工作。
其次,在民主、友好的氛围中逐步确立班级共同使用的规则,而成员资格的内涵具体指向什么,是成员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的共同的认识和理解决定的。
再次,在教师对规则的率先的正确使用和对学生的平等关注中形成良好的整体氛围。
最后,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在对规则的运用和对整体的文化氛围的感受中促使学生真正的相互认同和平等相待,包括对不影响班级共同活动的个体差异性的存在。
在这个共同体内,成员享有一致的权利,同时又被赋予一致的义务。儿童应该在班级这样一个共同体内学会平等待人以及对规则的正确遵守和维护,把规则运用到共同体内的每一个角落里。一个共同体要制定公正的程序使任何一个成员都具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使每一个想使自己的意见得以实现的人都首先把自己的意见公布于众,在说服大家并得到多数人认肯的情况下,使之成为公众的意志。这就是民主的过程。而且共同体内成员间的平等和对共同体之外的人的自由的尊重是同时进行、并行不悖的。共同体的活动宗旨就是贯彻一种非压制和非强迫性的活动方式,调动每个人对于活动的热情,对内如此,对外也是如此。当我们想把共同体内的规则向外推行的时候,就要运用协商的方法达到更大范围内的认同,而不能把共同体内承认的规则和内容等强迫性地运用共同体之外的其他人身上。
产生这种集体认同和民主的行为方式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而是充满了艰辛和波折,是在不断产生磨擦和达成和解的过程中、在对规则的误用和矫正中认识和学习的。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作为共同体的指导者、评判者和成员之一,他对其他成员的态度,对规则的运用、指导和评判等对共同体其他成员的成长和整个共同体的形成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此,教师是儿童行为的榜样。儿童作为一个需要教育的人,是在对他人的模仿中获得交往能力的。
三、共同体中资源的均衡分配和共有共享
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资源的共有共享或均衡分配。那么,班级要想成为一个共同体,应该怎样分配自己的资源?又有哪些资源可以分配或使用呢?
(一)班级共同体的一般资源的特殊性及其分配
班级作为一种非物质化的文化和精神共同体,几乎不存在物质财富分配均否的问题。那些被给予的物质用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按人数平均配给的,比如桌椅、课本等。其他一些物品,如班级的公共图书、各种活动用品等,一般也是为公众服务的目的而置备的。这些物品能否真正成为公用的,不是取决于为谁所有,而是取决于谁有更多的机会使用它们。因此,班级的公共资源更多地指向一些无形的、没有明确指向性的发展机会、条件和那些有助于学生成长的心理影响因素,具体地讲,如使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有价值的群体氛围,一种能尽可能地让所有人都能参与的活动方式,一种能让每个人都不断感受到进步和体会到优势的评价方式,使学生遭遇具有挑战性的学习任务甚至是经受失败的机会,必要的关爱、鼓励、帮助,相互之间的承认、认同、欣赏等。我们应该尽可能地使每个学生都能享受到这些,这既是对他们每个人的尊重,也是促使他们产生良好的自我感知的方式。
这些因素有着自身的特点:其一,其分配不像物质或金钱等可以通过精确的计算,并按照某种标准进行分割。不同的人在不同情况下的需要存在着巨大差别,比如他们同样需要关注,却需要不同的关注。其二,这些资源有着无限的可再生性。良好的共同体内部的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这种资源的提供者,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向他人提供资源的人。其三,这种资源的共享性特别高。关爱等就和权利、公共设施等一样具有弥散性,同时可以服务于众多的成员,而不是向某些东西那样一个人拥有就限制了其他人的使用。
(二)共同体资源的深度开发和共有共享
共同体的资源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既可能因为各种活动的组织和开展而大为增加,也可能因为活动开展的不当而丢失。把自己当成资源的惟一提供者和分配者,或者开展的活动仅指向或能包纳少数人,这些资源就成为极其有限的了。因此,教师——共同体中的领导者,就要开发各种潜在资源,使其成为学生发展的充分条件。
第一,创造性地组织各种活动以适应不同学生的不同需要,并力求使活动具有群众性,便于全员参与。笔者曾参加过几个班的中队活动,其中可以看出不同的活动方式对个体机会的影响。一个中队(以班级为中队单位)是以团体运动比赛的方式进行,通过开展各种便于全员参与的集体活动如拔河比赛、组队接力等来扩大参与的机会;另一个班级是演讲比赛,参与的人数范围极其有限,仅限于几个活跃的学生和班委等;另一个班级开展了多样性的活动,但“让每一个学生都有参与的机会”似乎并没有成为活动要考虑的问题,有些学生多次参与,而许多学生却没有任何活动。也许一次活动并不能代表学生的整个班级生活,但从各方面显示,活动的多样性和群体参与性并没有成为组织班级教学的原则之一。在现实中,有很多时候,因为参与的门槛过高或仅适合于少数人,各种机会都被少数几个人“承包”而与大多数学生无缘。就我国而言,许多教师的确没有把平等与均衡的理念体现在班级事务中,他们把班级变成了相互竞争、对抗甚至是诋毁的群体,而不是相互关爱、共同进步的共同体。为了班级之间的竞赛把组织和参与活动的机会给予“能者”,而放弃了对于“暂时不能者”的教育任务。这就是教学的目的观问题。机会与时间是大家共有的,应该尽量避免因过于个体化而导致群众中其他人的损失。当我们意识到机会均等、普遍化与共享的重要性时,活动的组织形式就应该朝着更具有群众性的方向开展。
第二,合理利用个体所拥有的潜在资源,使其成为共同体的共享资源和促进他人成长的有利条件。共同体的发展需要成员间的合作、互助,需要成员开创性的劳动并把这些劳动成果转化成公共资源和可以使每个人受益的公共福祉。共同体要形成这样一种机制和方法,它鼓励和帮助个人把个人的东西转化成可以使其他人受益的共同体的财富。苏联心理学博士和伟大的教育实践家阿莫那什维利就是这样一位懂得如何不断建设班级共同体的行家。他“引诱”学生们把自己的作品装订成册,画上优美的图画按期“出版”,然后挂在墙上供班级成员相互学习、欣赏。这是一个多么富有艺术性的工作啊!他巧妙地把众人的智慧汇集起来,不仅仅是写作方面的,还有合作的能力、智慧和技巧等。再比如有的教师鼓励学生把自己看到的美文抄写下来读给大家听,鼓励学生关注同学的行为并把他们的好行为介绍给大家等。教师就是这样一个时刻引导着共同体的建设,又时刻准备着把共同体的建设权利和权力教给和交给成员的人。共同体就是这样一个我们可以从中受益,同时也等待着我们去建设的团体。
第三,汇集班级共同体成员的外围资源,为共同体的发展提供帮助。班级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都是携带着许多的外围资源进入共同体的,是一组资源的交汇体。共同体拥有一个以共同体成员为点的外散网络——成员的父母、祖父母和其他的亲属,他们都携带着有利于共同体发展的资源,共同体应该充分地利用。当教师向学生家长征求意见、询问他们可以为孩子的班级做些什么时,他就是在充分地利用这一共同体的外围资源。当孩子的亲人们在向孩子们讲述着他们有趣的工作和不平凡的经历时,当他们中的作曲家提出愿意为孩子们谱写歌曲并教他们演奏时,当一位家长邀请孩子们参观他所在的工厂时,就是在建设着共同体。这种建设不仅使班级与家庭建立起亲密的联系,而且也使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密切起来。班级就是这样一个联系家庭与社会的一个核心,一个给予个体充分的发展机会的团体,一个不断地扩展自己、建立多方面的联系的活动着的有机体。它是整体的,又是开放的;它依赖于内部的活力,又得益于丰富多彩的外部世界。
四、防止用“服务”行为和学生的“才能”把学生类别化、等级化
目前家长们都非常重视自己的孩子在班级中担任什么职务,做个什么“官儿”。出现这种需求并不是因为家长们特别在意培养孩子为他人服务的意识,而是在于对一种发展资源的争夺。服务与被服务之间存在着发展机会的给予和剥夺,这也许是我国教育一个格外严重而又没有引起重视的问题。
我们按照惯常的习惯,进校伊始,就把孩子分成各种不同的群体。首先就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班委和非班委。班委是为班级服务的人,而非班委是被服务者。这样划分是出于管理的需要,然而却成为对孩子发展的限制,促成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不同心理的形成。在班级中,班委是一个特殊的团体,它似乎超越于一般学生之上,拥有一种特殊的存在方式和不同的心理状态。班干部身份首先就赋予人一种不同的即在关系和相应的关系心理。这种“被分配”的关系和心理是个体在团体中地位的起点。班委成员的身份一开始就表明相对于一般学生的优势,而且这种优势得到了群体的最高管理者——教师的认同和帮助。加之班干部的身份确实意味着一种特殊的发展机会和相应的发展结果,班干部或曰服务者自身的心理优势由此形成。笔者曾问一位一年级的小女班长是怎样当班长的,她说:“这还不容易,有事就报告老师,他们不听话我就打。”我震惊于她的理所当然,更恐惧她的“暴君”性格的形成。与此相对的是一般学生的被服务心理,他们由此形成的往往是一种“被动的主动”的放弃心理。在一般情况下,教师会把许多事务分派给班委成员去做,他们占有着许多活动的参与机会,而其他许多学生被无形地排斥在行为之外了。这种“旁观者”的位置给他们带来的心理,一开始可能会因不能参加活动的“愤愤不平”,久而久之就对这些不公平分配“坦然”地默认,把自己“份内”的事看成是“份外”的事,“自觉”地放弃了一些参与机会,从意识上把自己排除在共同体之外。这就促成了普通学生在心理上对自己的成员资格的消解,成为一个非参与者。这种自我排除心理特别容易发生在内向的、没有被给予任务或没有特殊才能的孩子身上。在一项活动面前,他会自觉地使任务“他者化”,即从心理上认为“这是班干部的事”、“这是有音乐才能的人的事”、“这是体育特长生的事”、“这是活跃分子的事”,从而找到正当的理由为自己的不参与“辩解”。这种任务他向化的心理很可能就是惯常性地在班级管理中把活动特殊化和小群体化的结果造成的。
这就是一种通过“关系场域”对不同的个体进行“型塑”的过程,“位置的空间仍然倾向于对立场的空间起到支配的作用”(注:(德)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41.)。“场域中位置的占据者用这些策略来保护或改善他们在场域中的位置,并强加一种对他们自身的产物最为有利的等级化原则。而行动者的策略又取决于他们在场域中的位置,即特定资本的分配。他们的策略还取决于他们所具有的对场域的认知,而后者又依赖于他们对场域所采取的观点,即从场域中某个位置点出发所采取的视角”(注:(德)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39~140.)。刚刚进入学校的孩子们一方面已经带有社会等级化的痕迹,然而由于他们成长的可能性和心灵的敏感性,他们又有着被重新形成的可能。
作为管理者和调节者的教师,应该让学生有一个“重新洗牌的机会”,想方设法消除儿童心理上已经形成的对人对己的不平等的体验,以及由此形成的排他情绪和排我意识,而不应该用各种做法使这些不平等、不公平的想法更加固定化。明智的教师对每个学生的供给都是公平的、均等的,同时,鉴于接受者的特殊性,供给的具体方式方法又应该是不同的。由于这种“方法”是基于生命科学之上的,它就不会是刻板的——这与它所确立的前提是相矛盾的。因为承认生命的存在就意味着愿意接受发展和变化,生命就意味着变动不居,显示着生长变化,意味着个性和艺术(注:(美)玛格丽特·E·斯蒂芬森.童年的秘密·序.玛利亚·蒙特梭利.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