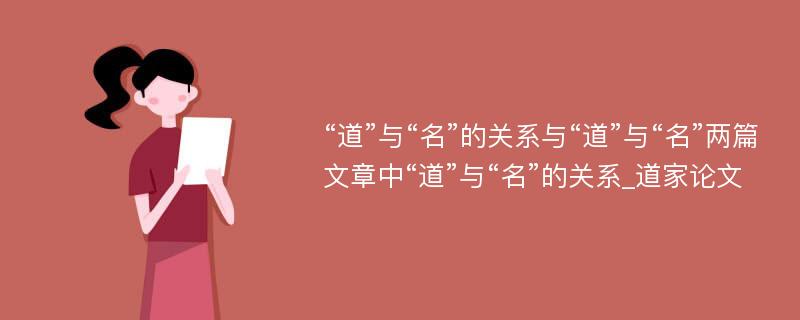
《韓非子》主道、揚權兩篇所見“道”與“名”的關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道论文,非子论文,揚權兩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道》、《揚權》是所謂的《韓非子》四篇(《主道》、《揚權》、《解老》、《喻老》)中的兩篇,因爲這四篇鼓吹君主虛静無爲,與純粹表述法家觀點的其他篇章區別明顯,所以學者們也往往把這四篇作爲一個整體來探討,如容肇祖、木村英一都認爲這四篇有共同思想傾向,認爲它非韓非子自作。容肇祖视其为“黄老或道家言混入韩非子书中者”①,木村英一将其定为“黄老思想に基けた韓非子后學(基于黄老思想的韓非子后學)”之作。②同《管子》四篇一樣,這四篇最大的特徵也是道家色彩濃厚,特別是《主道》、《揚權》二篇,將“道”與刑名法術的結合轉化爲一種實際政治理論,其關心點不在“心”、“氣”、“欲”等內在的問題上,而是道家和法家的直接結合,使其成爲在君臣關係的場合可以實際操作的君主統治術。③
一、黄老道家政治思想的基本特徵
正因爲這幾種文獻與道家的政治思想相關,所以在此有必要對道家政治思想的特徵作一簡單的概括,通過這樣的概括,我們可以看出“道”與“名”、“法”④爲什麽會結合到一起,什麽時候開始結合到一起,它們之間有著怎樣的分工,這是戰國秦漢思想史上極有意義的研究課題。
《史記·太史公自序》引司馬談“論六家要旨”的話說:“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這種以道爲思想原點或最高權威,以“陰陽”、“儒”、“墨”、“名”、“法”爲實用原理的政治思想,在戰國晚期到秦漢時期極爲流行。其倡導者在漢初被稱爲“道家”或“道法家”⑤,在今天則被許多學者稱爲黄老道家。說這種所謂的“道家”思想是博采了“陰陽”、“儒”、“墨”、“名”、“法”衆家之長,多多少少有司馬談加以理想化的成分。但如“道法家”之名稱所言,“道家”與“法家”(包括與法家接近的政論型名家⑥)的結合是其中的關鍵,而這種結合的要點是“撮名、法之要”,也就是說,“道”在上,“名”“法”在下。“道”居于優先的支配的地位,“名”“法”居于卑下的被支配的地位。
這種理論建立在“道”“物”(或“萬物”)二分的世界觀基礎之上,如“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老子》第一章)所言,“道”是“萬物”的生成者,同時也是“萬物”得以存在和運動的最高依據。“道”雖然是“無名”“無形”的,萬物却必須依賴“名”“形”纔能得以區分、認識和管理。因此“名”“法”只能建立在萬物的基礎之上,是爲了使萬物獲得秩序和規範纔應運而生的。由于“道”是“萬物”的生成者,因此,從原理上講,“道”也就是“名”“法”的生成者。在黄老道家那裏,聖人作爲理想的統治者,一定是體道、得道之人,由于“道”高于萬物,具有“無名”“無形”的特徵,因此,聖人不可能受到“名”、“法”的控制與束縛。相反,在需要“名”、“法”加以管理和規範的萬物層面,聖人没有必要加以干涉,反而要盡可能地讓“名”、“法”自發地、自主地發揮組織和管理的作用。
因此,“道”與“名”“法”雖然不在同一層面,但對一個希望建立一元化政治體制和高效率統治機構的國家來說,這兩者都是不可或缺的。“道”是一元化君主專制體制的法理依據,“名”、“法”是專制體制在臣下和百姓的層面得以順利推行的技術保障。我們雖然不能證明“道”“物”二分的世界觀很晚纔出現,但充分利用“道”“物”二分的世界觀,將其轉變爲一種實用、高效的政治理論,用于指導國家管理,應該是在渴求富國强兵和中央集權的戰國中晚期之後,纔應運而生並備受重視的。⑦
這種思想架構使得“道”和“萬物”之間出現必然的緊張和對立,使“道”和“萬物”成爲主宰和被主宰的關係。可以說這種傾向在戰國晚期及秦漢之際最爲强烈,因爲這段時期,建立在“道”“物”二分世界觀基礎之上的黄老道家及其所推崇的中央集權政治思想日益完善、日漸盛行,它通過“物物者非物”等口號,突出强調了君主是與“道”相應的存在,處于支配的地位,而“萬物”即天下臣民則必須無條件地接受作爲“執道者”(即君主)的統治。⑧例如,池田知久對此作過如下的描述:
“道”是使所有“萬物”存在、運動變化的世界主宰者,“萬物”則僅是因“道”而得以存在、得以運動變化的被主宰者。“道”是超越了時間、空間的存在形式,超越了人類各種價值的偉大存在,而“萬物”不過是跼蹐于時間、空間的存在形式之下,抓住人間各種價值不放的卑小的存在者。⑨
這種以黄老道家爲指導、以中央集權爲目的的政治思想,有內外兩方面的特徵,從外部看,它愈來愈趨向道家和法家、政論型名家的結合,即在對具體事務的認知、判斷、處理上,在對現實政治具有確定性意義之標準、規範的設立上,讓法家、政論型名家去發揮作用,同時高揚君主的主體性,强調君主與“道”一樣處于至上的、絶對的地位,因而只有君主能够把握、控制“名”“法”,並以“名”“法”爲媒介統治天下。從內部看,它强調君主與臣民在“知”的領域上有著根本性的不同。即如果將“道”視爲整體、普遍的話,那麽,“萬物”只能相當于個別、部份。臣民所知的只是“萬物”的個別、部份,只能通過經驗(不管是感性的還是理性的經驗)去認識萬物,再通過“言”、“說”的方式闡釋其內容和意義。君主則不同,他所把握的是“道”,是整體的、普遍的、終極的原理,因此君主的“知”也就必然與普通的“知”完全不同,是超越經驗之上的、無法用“言”、“說”表達的“無知之知”、“不言之言”。
如果不明確以上兩方面的特徵,對《韓非子》的《主道》、《揚權》兩篇的分析就難以正確展開。近年來,隨著對馬王堆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即所謂《黄帝四經》)等出土文獻的研究⑩,隨著對《尹文子》等傳統文獻的重新認識(11),我們發現,包括《老子》、《莊子》外雜篇、《淮南子》、《管子》四篇等在內,這些文獻在思想上有著密切的關係。這種關係的共同點就是都具有“道”“物”二分的世界認識,以“道”爲體,以“名”“法”爲用的理論結構,以及君主與臣民截然不同的認識原理。本文在試圖對這兩篇文獻所見“道”和“名”的關係做出分析時,也必須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展開。
《荀子·正名》篇雖然批判了那些“用名以亂名”、“用名以亂實”、“用實以亂名”的“辯者”、“察者”,强調王者“制名”,但在荀子看來,“正名”依然是通過認識途徑來把握的,只要“心合于道”,作爲“天君”的心就能有效地把握住“天官”即五官,使其在感知對象時不出偏差。因此無論是君子還是小人,只要條件許可,他都有可能正確地獲得“正名”。(12)然而,這對追求絶對權力的君主而言,並不是有利的條件,因爲君主既然需要通過認知的途徑去把握“名”,同普通人一樣做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那麽,在“名”的把握上,他就必須平等地對待其他的挑戰者,這樣君主要站到權力的頂端,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能把認知的途徑神秘化,使君主一人處于“心”的位置,使所有臣民都只能處于“體”的位置,那“心”就能自然而然地控制“體”。如果能使君主一人處于“道”的位置,即無法由“形”“名”來確定的位置,使所有的臣民都處于由“形”“名”確定的位置,那就能使君主藉助“道”的權威性,輕易地登上權力的頂峰,同時藉助“名”與“法”的自發作用實現無爲而治。這正是上述黄老道家使君主專制得以實現的理論基礎。筆者以爲,《管子》四篇在哲學上的探討,標誌著這種理論基礎已大致形成。(13)接下來要做的就是如何使其具體化,現實化,《韓非子》的《主道》、《揚權》兩篇之重點正在于此。《管子》四篇的重點在于君主與臣民在“知”的領域上有何根本性的不同。《韓非子》這兩篇的重點則在于“道”和“名”的關係是如何運用于君主的實戰理論的。至今爲止,關于《韓非子》四篇的並不少見,但還很少有學者從“道”與“名”關係的角度展開,本文就想做這方面的嘗試。
二、《主道》、《揚權》兩篇所見“道”與“名”的關係
在《韓非子》中,作爲一種政治思想的“名”的論述極爲豐富,它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建立在“名實一致”觀念基礎上的“循名責實”論。第二,建立在黄老道家思想基礎上的“君臣不同道”,“君操其名,臣效其形”之理論。這兩種理論都可以表現爲“形名參同”論,但後者顯然是在包含前者的基礎上形成的。
“形名參同”論有著非常確切的使用範圍,即在君臣之間。有著非常明確之政治目標,即在保障君主專制地位的前提下,使行政效率得到最大程度的提高。所以“形名參同”論是君主用來督責操縱臣下的權術理論。通過以下的用例可以看出,它可以分三個步驟進行。第一,“審名以定位”;第二,“循名以責實”;第三,據“名實”以定賞罰。這種政治思想,即便没有黄老道家思想背景,作爲一種純粹的法家理論,也可以充分展開,如下所示,《韓非子》中有很多的論述:
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定法》)
人主將欲禁奸,則審合刑名,刑名者,言與事也。爲人臣者陳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于)大功也,以爲不當名之害,甚于有大功,故罰。(《二柄》)(14)
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二柄》)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爲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群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二柄》)
其要旨就是,君主以臣下的“言”爲“名”,按其所言或按其所能嚴格地確定其職責範圍。然後要求臣下不折不扣地完成其職責。對于“功當其事”者給予獎賞,對于“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者,甚至“其言大而功小者”“其言小而功大者”也予處罰。
“形名參同”論的特徵在于實用性,追求實時的效果。在于確定性,追求非此即彼的效果。這種“名實關係”論,就産生的淵源而言,和建立在論辯基礎上的知識型名家無關,和爲言論和思想設立標準的荀子“正名”論無關,但在要求“名”具有確定性,“名”對“實”具有規定性方面,則完全一致。它是法家以法治國爲理念的“刑名論”的延伸,是君主專制主義發展的必然要求,是國家行政體制軍事化的産物。當然,“性惡論”和“分職論”也爲“形名參同”論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條件。特別是法家的“分職論”,鼓吹通過名分制度,使整個國家變成一臺尊卑關係和社會分工井然有序的,人人都明確自己地位、職責,義務的、高效率的政治機器。“循名責實”和“形名參同”的思想正是這臺機器的操作方式。
“形名參同”論的前提在于君主具有不可侵犯的最高權位,然而,“形名參同”本身只是一種“術”,它並不能說明君主在“循名責實”時,其權威來自于何處,以及如何保障其權位不受侵害。所以,對于君主專制體制而言,僅僅有“循名責實”的政治操作理論不够,還需要爲君主提供關于權力起源和正當性的理論。這就是所謂“君臣不同道”的理論,有了這一理論,“形名參同”論纔算是完整了。從這層意義上對“形名參同”論作出詳細論述的就是《韓非子》的四篇《主道》、《揚權》兩篇。
《主道》、《揚權》兩篇在理論上對《管子》四篇有相當多的繼承。其中最重要的是以“道”爲體,以“名”爲用的思維方式,將“道生萬物”的原理和“道”“物”二分理論引入政治哲學中。考察《韓非子》中具有典型法家思想傾向的篇章可知,法家本來反對包括道家在內的一切有害于“治”的言論。然而,在《韓非子》這兩篇中却不僅導入了道家思想,而且將其視爲政治指導思想的依據,加以全面的積極的吸收,其原因就在于“君臣不同道”,“道不同于萬物”,“君不同于群臣”的理論有助于將君臣關係的區別上升爲道物關係的區別,有利于君主專制的形成。對于《管子》四篇“毋代馬走,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静乃自得”(《心術上》)的政治哲學,《韓非子》做了最大程度的發揮。如《揚權》篇說:
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爲。使鶏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上有所長,事乃不方。矜而好能,下之所欺。辯惠好生,下因其材。上下易用,國故不治。
相反,如果君臣地位顛倒,就會發生君主的職權被侵奪的現象,在《韓非子》中,曾無數次從各種角度描述過這種不利于君主專制的局面,《主道》篇將其總結爲“五壅”:
臣閉其主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閉其主則主失位,臣制財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明,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
爲了避免“五壅”之類危害君權現象的發生,爲了鞏固君權至上的專制體制,最佳的政治局面就是“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揚權》)。爲此君主必須把握“道”,使自己居于“道”的位置。《主道》說:“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治紀以知善敗之端。”與君主相對應,臣下居于“物”的位置,“名”是君主通過“道”來把握“臣”的媒介。具體而言,就是通過“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即“形名參同”的操作方式,讓官僚系統自發地起作用,使君主能“無爲而治”。
用一之道,以名爲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静,使名自命,令事自定。(《揚權》)
故虛静以待,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静則知動者正。有言者自爲名,有事者自爲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主道》)
同《管子》四篇一樣(15),《韓非子》也强調君主對“名”不加干涉的態度。力圖“使名自命,令事自定”。(16)因爲黄老道家相信,在形而下的世界中,“物”、“名”、“事”都具有自發自爲、自我確定、自我監督、自我成就的效果,而最好的統治者正是充分利用這一點,以實現“天下無事”,“無爲而治”的。這就必然要求君主取“因”的姿勢,“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正與處之,使皆自定之”(《揚權》)。只有在“不知其名”的時候,纔“復修其形”(《揚權》)。
在“形名參同”中,君主必須取“虛”“静”的姿態,這兩篇中這方面的論述非常豐富,這裏不一一詳引。《管子》四篇中雖也多見這類論述,但設定的場合並不相同。《管子》雖然提到“君之位”“官之分”,但不像《韓非子》是典型的君臣關係論。《管子》談虛“心”,養“氣”,理“欲”,著眼點在于聖人如何通過養生接近“道”,然後通過“道”把握“名”。《韓非子》雖然也講“虛心以爲道舍”(《揚權》),但把重點放在君主如何藉助“道”控制臣下上。《韓非子》中雖然也有《解老》、《喻老》這類理論闡釋,但那只是爲現實政治尋求經典依據,在思想的體系性和論述得系統性上,遠不如《管子》四篇完整。
所以,在《韓非子》中,君主所取“虛”“静”的姿態,並不是虛“心”,養“氣”,理“欲”之後的結果,而是一種假象。並不是真正得“道”,而是一種類似于“道”的行爲方式。這樣就解决了平庸的君主如何居“道”之位,以駕御“名”“法”的問題。其具體方法是:
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將自雕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异。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智去舊,臣乃自備。(《主道》)
這種方法在《韓非子》其他篇章中也能見到,如《二柄》篇中有:
故君見惡,則群臣匿端,君見好,則群臣誣能。人主欲見,則群臣之情態得其資矣。
然而,《主道》篇明確指出,君主之所以要將“好惡”隱藏,因爲這是一種“道”的表現:
道在不可見,用在不可知。虛静無事,以暗見疵。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變勿更,以參合閱焉。官有一人,勿令通言,則萬物皆盡。函其迹,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絶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謹執其柄而固握之,絶其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
這裏的“道”,强調的不是作爲“萬物之始,是非之紀”的那個“道”,而是指“道”所具備的、用普通的感官和認知手段無法把握的特性,君主只要具備了“道”那種“不可見”,“不可知”之特性,處于“物”之位置上的臣下就不能控制君主了。
君主要把握這樣的“道”,並不需要類似《管子》四篇所論述的修練過程,《韓非子》並不把君主看作是超凡脫俗的人,他也認爲君主精力有限,所以,他主張“聖人之道,去智與巧。智巧不去,難以爲常”。(《揚權》)即君主必須完全脫離對具體事物的認知過程。這樣,平庸的君主也可以不必爲無法把握“道”而擔心了。
君主處于“不可見”、“不可知”的“道”的位置,利用可知可見的具有確定性意義的“名”“法”,以控制臣下,治理天下。《管子》四篇中複雜深奥的哲理,到了《韓非子》那裏,雖然結構依舊,但已簡化爲通俗易行的實戰理論了。
以“道”(虛無)爲體,以“名”“法”(因循)爲用的理論是黄老道家思想的根本所在,在《黄帝四經》及《鶡冠子》、《尹文子》以及《呂氏春秋》和《淮南子》的一些篇章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在戰國中晩期到秦漢爲止的時期內,曾大爲流行。但作爲一種爲配合君主專制的實戰理論,在《韓非子》中可以說發揮到極致了。司馬談爲“道家”所做的另一個定義,其實就是這種實戰理論的總結:
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埶,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巧),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奸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史記·太史公自序》)
注释:
①容肇祖:《韓非子考證》,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
②木村英一:《法家思想の研究》,附录“韩非子考证”,东京:弘文堂,1944年。
③《韓非子》四篇不像《管子》四篇那樣,具有思想上的相互照應。《韓非子》四篇雖然在以“道”爲首的總體思想上一致,但《解老》、《喻老》篇與《主道》、《揚權》篇没有直接的關係。對“道”“名”“法”關係也無論述。故本文主要以《主道》、《揚權》篇爲材料。此外,有學者認爲,《解老》、《喻老》篇的成書有可能晩于《主道》、《揚權》篇。容肇祖《韓非子考證》(前揭)認爲其中的“道”接近于《淮南子·原道》篇,故推測此二篇出自漢初道家之手。蔣伯潜:《諸子通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根據其體例,認爲它是西漢經師解釋《老子》之方式。
④戰國中晚期、秦漢之際,“名”與“法”往往對舉,兩者有著類似的性質、都被看作是政治上最高的最根本的法則。參曹峰:《戰國秦漢時期“名”“法”對舉思想現象研究》,《西北大學學報》2012年第6期。不過,場合不同,兩者的機能與分工也有所不同。如《黄帝四經》所見“名”與“法”,就兩者特徵言,“名”類似于制度,“法”類似于措施。就兩者作用言,“名”與規範的建立相關,“法”與規範的操作相關。參曹峰:《“名”是〈黄帝四經〉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兼論〈黄帝四經〉中的“道”“名”“法”關係》,《黄帝思想與道、理、法研討會論文集》,湖南大學,2013年4月。而在《尹文子》中,其作用可以用一縱一橫來表達。縱者“名”也,用“名”來確定社會的上下貴賤尊卑等級秩序。橫者“法”也,用“法”來確定上下貴賤尊卑不同階層都必須遵循的共同的秩序,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參曹峰:《〈尹文子〉所見名思想研究》,王中江主編:《新哲學》第8輯,開封:大象出版社,2008年。
⑤裘錫圭:《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並非〈黄帝四經〉》(《道家文化研究》第3輯(馬王堆帛書專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及《馬王堆〈老子〉甲乙本卷前後佚書與“道法家”——兼論〈心術上〉〈白心〉爲慎到田駢學派作品》(《中國哲學》第2輯,北京:三聯書店,1980年)有關于漢初“道家”或“道法家”情况的論述。
⑥這是筆者的定義,筆者將戰國時代的名家分爲兩種,一種是注重“事實判斷”、與今天所謂的語言學、邏輯學相聯繫的名家,可以稱之爲“知識型名家”,這種名家以《公孫龍子》、惠施、墨辯爲代表;一種是注重“價值判斷”、與今天所謂的政治學、倫理學相聯繫的名家,可以稱之爲“政論型名家”,這種名家以《荀子·正名》、《尹文子》、《鄧析子》爲代表。參見《對名家與名學的重新認識》,“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華東師範大學,2013年4月。《回到思想史——先秦名學研究的新路向》,《山東大學學報》2007年2期。
⑦另外一種道家,以《莊子》爲代表,雖然也以“道”“物”二分爲其思想基礎,但却不是將“道”和“物”對立起來的理論,而是提倡“萬物齊同”和“道通爲一”,目的在于消除作爲萬物之一的“人”所必然會具有的一己成心與彼我對立意識,打通物我的封界與壁壘,使得是非、成敗、生死,乃至天地萬物都在自然的流變中與大道融爲一體。從這樣一種道家理論當然開不出爲現實服務、追求實際效果的政治理論來。
⑧可參看池田知久著、王啓發、曹峰譯:《道家思想的新研究——以〈莊子〉爲中心》(開封: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六章《“道”的形而上學》第二節“‘物物者非物’的命題”。
⑨《道家思想的新研究——以〈莊子〉爲中心》,第209頁。
⑩可參曹峰:《“名”是〈黄帝四經〉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兼論〈黄帝四經〉中的“道”“名”“法”關係》,《黄帝思想與道、理、法研討會論文集》,湖南大學,2013年4月。
(11)筆者曾對《尹文子》所見“名”的思想作過詳盡研究,參曹峰:《〈尹文子〉所見名思想研究》,王中江主編:《新哲學》第8輯,開封:大象出版社,2008年。
(12)參見曹峰:《〈荀子·正名〉篇新論》,《儒林》第4輯,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8年。
(13)关于《管子》四篇所见“名”的思想,笔者在博士论文《中国古代における“名”の政治思想史研究》下编第三章中有详尽论述。
(14)“人主將欲禁奸,則審合刑名,刑名者,言异與事也”原作“人主將欲禁奸,則審合刑名者,言异事也”。“非不于大功也”原作“非不說大功也”。“爲不當名之害”,原作“爲不當名也害”。均據文意校改。參見陳奇猷:《韓非子集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
(15)《管子》四篇認爲,君主與“名”的關係中最需把握的是“因應”之道,如“不言之言,應也。應也者,以其爲之人者也。執其名,務其應,所以成之,應之道也。無爲之道,因也。因也者,無益無損也。以其形,因爲之名,此因之術也。名者,聖人所以紀萬物也。”(《心術上》)“以其爲之人者也”可能是“以其人爲之者也”之誤。
(16)關于“名自命”、“事自定”,在其他文獻中也可看到,這些文獻均與道家思想有關。如下:
凡事無小大,物自爲舍。逆順死生,物自爲名。名刑(形)已定,物自爲正。(《黄帝四經·經法·道法》)
勿(物)自正也,名自命也,事自定也。(《黄帝四經·經法·論》)
示人有餘者人奪之,示人不足者人與之。剛者折,危者覆。動者揺,静者安。名自正也,事自定也。是以有道者自名而正之,隨事而定之也…昔者堯者治天下也以名,其名正則天下治。桀之治天下也又以名,其名倚則天下亂,是以聖人之貴名正也。(《群書治要》所録《申子·大體》)
明王之治民也,事少而功立,身逸而國治,言寡而令行。事少而功多,守要也。身逸而國治,用賢也。言寡而令行,正名也。君人者,苛能正名,愚智盡情,執一以静,令名自正,令事自定。賞罰隨名,民莫不敬。(《尸子·分》)
明主者,南面而正,清虛而静,令名自命,物自定,如鑒之應,如衡之稱。(《賈誼新書·道術》)
聲自召也,貌自示也,名自命也,文自官也。《淮南子·繆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