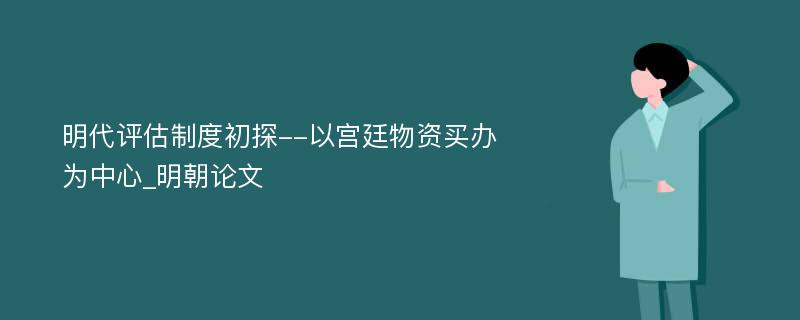
明代时估制度初探——以朝廷的物料买办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买办论文,朝廷论文,物料论文,明代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 129.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917(2008)04-0055-10
一、引言
所谓时估,在不同语境中含义略有差异,或指市场上各类物品的通行价格,或指有关部门对物品时价的估计,或指经有关部门估计确定的物品价格。确切地说,作为一项制度的时估,是指有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根据市场时价估定的官方价格。明代凡是比较重要的时估,往往要会同多人估定,称为“会估”。明代由六部分掌庶务,“以时估平物价”属于户部职掌之一①,但科道官以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官员,也经常参与会估。由中央部门根据北京市场价格确定的时估,称为“京估”。明代中叶以降,除在京召买之外,朝廷向各地派征物料,或从各地折征银两,也时常以京估为价格基准。
明代召买、籴买、征税、折收、折支、开中、变卖等财政活动,以及司法过程中折算赃物,皆要求以时估为准。针对不同项目的时估,其程序和方式也不尽相同,大致有这样几种情况:其一,有关部门按照制度规定,在相对固定的时间,常规性地进行时估,遇到买办、折算等情况,即以最近一次时估为基准;其二,遇到买办、折算等情况,有关部门按照规定召集相关人员进行时估,这种时估一般只适用于当次行动;其三,针对征税、计赃等特定用途,朝廷特命有关部门召集相关人员进行时估,这种时估往往会沿用一段时间。相对而言,明代时估最大的用途,是作为朝廷买办物料的价格标准,在这方面逐渐形成了一套规范化的会估制度。
关于明代的时估制度,《大明会典》等政书记载简略,而且迄今似乎尚无专文探讨。个别论著偶尔提及,亦往往语焉不详甚或存在舛误。比如,《剑桥中国明代史》在讨论价格与货币问题时指出:“官方不合理地固定的价格表确实存在,但只是从1570年起,才一年调整两次。但这些价格表一份都没有保存下来,所以我们不知其价值如何;可能价值不大,因为所列的价格可能是商人作为部分税赋必须卖给政府的售价。”[1]短短几句话就出现两个错误:其一,明代早就存在着价格调整机制(即会估),正式实行一年两估的时间,也是1552年(嘉靖三十一年)而非1570年(隆庆四年);其二,官定价格表并非“一份都没有保存下来”,如《大明会典》载有弘治二年的“计赃时估”②,《万历会计录》载有万历八年秋和万历九年粮草物料的会估价格,《工部厂库须知》更是记载了数百种物料价格[2]。本文以朝廷物料买办为中心,对明代时估制度略加考述。
二、明初的按月时估
据笔者初步检索,“时估”一词,始见于唐代,但官府估定物价之制,却起源甚早。《周礼·地官·质人》云:“质人掌成市之货贿。”据注疏:“古人会聚买卖,止为平物价而来,质人主为平定之,则有常估,不得妄为贵贱也。”③可见质人的主要职责,就是评定物价。云梦秦简《封诊式》提到“市正贾(价)”,当即官府确定的标准价格。到汉代,已形成了固定的时估制度。东汉郑众解释《周礼》“质剂”一词,“谓市中平贾,今时月平是也。”④虽不一定确切,但却透露汉代有“月平”之制。清孙诒让解释说:“月平者,汉时市价,盖每月平定贵贱,若今时朔望为长落也。”⑤另据《汉书·食货志》所记新莽之制,是每年评定四次:“诸司市常以四时中月实定所掌,为物上、中、下之贾,各自用为其市平,毋拘它所。”
唐代,时估制度十分周密。据《唐六典》记载,两京诸市署的重要职责,是“以三贾均市”,而所谓“三贾”,即“精为上贾,次为中贾,粗为下贾”⑥《唐律疏议》亦谈到:“依令,每月旬别三等估。”⑦可知唐代每旬都要评定物价,每种物品区分为精、次、粗三等,每等又估定上、次、下三种价格,这样一种物品共有九种估价。宋代时估制度也很完备。开宝六年(973)《西川两税折帛依时估诏》云:“应西川管内州府军县,自今将两税钱折匹帛者,并与依逐州三旬时估折纳。”⑧可见宋初即有“三旬时估”之制,后不断加密。大中祥符九年(1016)规定:“时估,于旬假日集行人定夺。”天禧二年(1018)进一步规定:“诸行铺人户,依先降条约,于旬假日齐集,定夺次旬诸般物色见卖价,状赴府司。候入旬一日,牒送杂买务。仍别写一本,具言诸行户某年月日分时估,已于某年月日赴杂买务通下,取本务官吏于状前批凿收领月日,送提举诸司库务司置簿抄上点检。”⑨金朝的时估,贞祐三年(1215)御史台奏言京师物价,提到“时估月再定之”[3],看来在京师是每月定时估两次。元代天历元年(1328),“命大都路定时估,每月朔望送广谊司,以酬物价”[4],亦是每月朔望各定时估一次。在地方上,则是每月一次定时估:“诸街市货物,皆令行人每月一平其直(值),其比前申有甚增减者,各须称说增减缘由,自司县申府州,由本路申户部,并要体度是实,保结申报。”⑩
明朝建立后,借鉴前代做法,制定了定时时估之制。洪武元年(1368)规定:“在京兵马指挥司并管市司,每三日一次,校勘街市斛斗秤尺,稽考牙侩姓名,时其物价。在外府州各城门兵马,一体兼领市司。”(11)明初除京师外,山西、河南、北平、凤阳等城亦曾设立兵马司,至洪武十三年撤罢(12),此后这些地方的市司,亦当由府州衙门管辖。大概考虑到三日一估过于频繁,洪武四年颁行的《宪纲》,又规定每月初旬勘定时估:“仰府州县行属,务要每月初旬,取勘诸物时估,逐一覆实,依期开报,毋致高抬少估,亏官损民。”洪武二十六年纂成的《诸司职掌》也规定:“凡民间市肆买卖一应货物价直(值),须从州县亲民衙门,按月从实申报合干上司,遇有买办军需等项,以凭照价收买。”(13)综合上述规定,明初的时估,是每月估定一次,具体事务由市司负责;而市司的主管部门,在京师为兵马司,在外地为府州县,这些部门要将时估按月申报上司。
在评定时估时,“行人物户”发挥着重要作用。《诸司职掌·都察院·刷卷》规定风宪官于巡历去处,照刷礼房文卷,必须稽查买办祭祀猪羊、果品、香烛等项“是何行人物户时估”。《大明律》中也有这样一款:“凡诸物行人评估物价,或贵或贱,令价不平者,计所增减之价论,坐赃论。”明代律注家对于律中之“诸物行人”,嘉靖以前未见以“牙人”解释“诸物行人”者,但嘉靖以后则多以“牙人”解释“行人”。如应槚《大明律释义》谓:“诸色行人,如米行、猪行之类牙人。”高举《大明律集解附例》谓:“诸物行人,谓诸色货物本行之牙人。”(14)姚思仁《大明律附例注解》亦解为“诸色货物牙行人”(15)。按:洪武初年,允许牙行存在,后曾严加禁绝,规定:“天下府州县镇店去处,不许有官牙、私牙……敢有称系官牙、私牙,许邻街坊厢拿获赴京,以凭迁徙化外。若系官牙,其该吏全家迁徙。”(16)但由于牙行有其现实功能,实难禁绝。洪武三十年(1397)定稿的《大明律》中,有“凡城市乡村诸色牙行及船埠头,并选有抵业人户充应……私充者杖六十,所得牙钱入官,官牙埠头容隐者,笞五十革去”之规定(17),可见此时又已准许设立官牙。不过,《大明律》在“私充牙行埠头”、“把持行市”等条款中,均径称“牙行”,而“市司评物价”一款却谓“诸物行人评估物价”,笔者认为,此款所谓“诸物行人”,可能并非牙行,而是“但卖物则当行”的行户。从后来的情况看,在一些场合,确实有让牙人估定的事例,如景泰四年,南京户部尚书沈翼奏言:“巡河风宪等官,每获运粮官军所载私货,即没入所在官司。及至支用,多有贸易侵欺。今后宜令牙侩当时估直(值),易米上仓。”从之。(18)但在更多的场合,尤其是在物料买办的场合,官府往往都是拘集各行铺户评估物价。
中国历代时估,多含有管理物价的意图。但实际上,除非遇到特殊情况(如发生饥荒需要平抑粮价等),政府一般不会干涉市场价格。明太祖建立时估制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规范政府的财务和政务运作。其中最大目的之一,是为政府买办物品确定一个相对合理的价格。
官府采买物品,自古有之。在官民交易过程中,经常出现“亏损下民”甚至“强行夺买”的现象。朱元璋熟谙民间疾苦,建国之后,力矫此弊。一方面,他以身作则,优待铺商,“宫禁中市物,视时估率加十钱”[5]。另一方面,他先后颁布一系列法令,要求官府市买物品,必须按照时估两平收买。洪武元年谕令:“今后但系光禄寺买办一应供用物件,比与民间交易价钱每多十文。且如肉果之数及诸项物件,民人交易一百文一斤,光禄寺买办须要一百十文,随物贵贱每加一分,卖物之人照依时估,多取十文利息。”(19)洪武二年规定:“凡内外军民官司,并不得指以和雇和买,扰害于民。如果官司缺用之物,照依时值对物,两平收买。或客商到来,中买物货,并仰随即给价。如或减驳价值,及不即给价者,从监察御史,按察司体察,或赴上司陈告,犯人以不应治罪。”(20)洪武四年颁行的《宪纲》中,也作出明确规定:“上司收买一应物料,仰本府州县,照依按月时估,两平收买,随即给价,毋致亏损于民,及纵令吏胥里甲铺户人等,因而克落作弊。”(21)洪武十九年颁布的《大诰续编》,对于假借和买害民的官吏,制定了更加严厉的惩罚措施:“许被扰之民,或千或百或十,将该吏拿赴京来,斩首以除民患。”(22)
洪武以后,除在光禄寺买办等少数场合外,按月时估之制逐渐废格不行。成化元年(1465),京城无赖与卖纸人强令囚犯高价买纸,事发问罪,刑部在题本中谈到:“缘无估定纸价,致使奸顽得计。今后本部按季行令顺天府,取拨铺户前来,将纸札照依时价,两平估计,晓谕各人遵守。”(23)由此可知,当时京城并无按月时估,否则不会“无估定纸价”,也用不着刑部行令顺天府按季估计纸价。外地情况亦然。弘治十五年(1502)九月至十七年四月间,陕西左布政使文贵、右布政使陈孜之子陈大纲,以及自称吏部马尚书舍人马须、巡抚大同都御史舍人刘瓒等,多次令咸阳县皮行商人以低价买办皮张,皮商“负累不过”,向巡按御史呈告。文贵在奏辩时捏称:“先买羔皮之时,访得民间出卖,每张不过价银半分。及查咸、长二县时估,每羔皮一张,值银二分,据此给价。”此案转行陕西巡抚杨一清勘问,“蒙行布政司及转行西安府并咸、长二县,各查无弘治十五九等年月分时估册籍”(24)。可见咸、长二县并未按月时估。也有地方官员试图恢复时估制度。如在福建惠安县,较勘斛斗称尺和时估制度久废不行,隆庆年间叶春及出任知县,除自家用度公平买卖外,还根据《宪纲》规定,“每月令老人估物,列于左方,官民一以为率”(25)。但这只是极个别的现象,恐怕也难以维持下去。
按月时估的停废,大约有两点原因:其一,洪武年间,法令严酷,“当是时,郡县之官,虽居穷乡绝塞之地,去京师万余里,皆悚然惊胆,如神明莅临,不敢稍弛”(26)。在这种情形下,时估制度应当运作得较好。但洪武以后,法令日益松弛,很多重要制度都沦为具文,时估并非紧要政务,当然更难按时举行。其二,市场行情变化无常,“物货价直(值)高下不一”,“官司与民贸易”可以“随时估计”(27),也没有必要在固定时点评估物价。
三、会估制度的形成
朱元璋力行节俭,爱惜民力,当时政府耗用物品较少,而且主要通过赋役系统征得,采买者较少。但洪武以后,采买项目和数量迅速增加。洪熙元年(1425),四川双流县知县孔友谅奏言:“古者征税徭役,量土地之宜,验人丁之数,务从宽省,以息民力。今自岁产贡赋、应纳税粮外,复有买办、采办等事。以朝廷视之,不过令有司支给官钱平买而已。然其中无赖之辈,往往致贿吏曹,交通揽纳,巧立辨验折耗之名,科取数倍,奸弊百端,重为民害。”(28)买办、采办名义上是“支给官钱平买”,其实并非自由的市场交易,除派令里甲办纳外,主要是强令城市铺行买办。永乐年间,明成祖曾谕令户部:“那军家每年街市开张铺面,做买卖,官府要些物件,他怎么不肯买办?你部里行文书,着应天府知道:今后若有买办,但是开铺面之家,不分军民人家,一体着他买办。敢有违了的,拿来不饶。”(29)除两京外,各地铺行都要承担买办任务。
明中叶以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白银的普遍行用,赋役制度发生了深刻变革。原来由各地输纳的本色物料,逐渐改为折征银两。“各省物料改征货币输京之举,当是正统元年(1436)南畿各省田赋折银之后逐渐盛行起来的,大概从成化到万历的一百四五十年才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其间以嘉靖时代为转折点”(30)。同时,因京师铺户负累太重,政府也逐步实行铺役改革,让铺行纳银代役,“其法计生理丰约,征银在官,每遇有事,官中召商径自买办”(31)。但物料折银之后,政府为图方便,所需物品皆召商买办,并非从市场直接购买,而所谓“召募”,很快就变为“皆径佥富人为之,不俟应募”(32)。政府佥召的商人,大多都是已纳过行银的铺商,因此铺商徒添纳银之累,却未能摆脱买办之苦(33)。
朝廷买办物料,在作预算和支付价款时,必须有一个价格标准。明初存在按月时估之制,遇到买办物料,自然无需临时估价,而可以“照依按月时估两平收买”。后来按月时估渐废,遇到派买物料,也就没有现成的时估可依,只能采取变通措施,于买办前后随时估价。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形成了一些固定化的会估办法。明代内府及各衙门的需求极其庞杂,其中买办数量最大的,一是光禄寺果品厨料,二是内府各库监局物料及各仓场草料。这两大系统的买办一直是独立进行的,会估形成的时间和办法也有很大差异。
“职司膳羞”的光禄寺,每年耗用大量果品厨料,“初则取给上林四署,继令买诸民间”。所谓“买诸民间”,有两种方式:一是本寺差人直接采买。永乐年间,“差内官一员,同本寺署官、厨役领钞,于在京附近州县,依时价两平收买。洪熙、宣德以来,止差署官、厨役,照前收买”。二是责令京城铺户买办。“凡本寺收纳一应物料,每月堂上官轮流一员,会同户科给事中、监察御史各一员,责令各行户买办,于本寺大烹门内验收”。(34)此外,因“供用不足”,正统初“始会派各省直”,规定:“光禄寺会计每年合用果品厨料等项,先期题请,行本(户)部分派各省府州县,支给官钱,照依时价收买本色,辨验堪中,点差殷实大户及选委有职人员解部,札付光禄寺上纳。”(35)即要求各省直按照当地时价,一律收买本色解纳。明代中叶以降,分派各省直的果品厨料陆续折银,到嘉靖五年(1526),令江西等处解纳的莲肉、胶枣、栗子等27种俱折银征纳(36),征解实物的项目已很少。随着折征的展开,光禄寺越来越依靠召商买办,嘉靖十九年,光禄寺官员指出:“本寺各项供用物料,俱系召商上纳。”(37)
无论是直接采买,还是令铺行或商人买办,朝廷都要求“依时价两平收买”。但在按月时估废弛的情况下,由个别当事人员估价,很容易出现随意高下的现象,甚至发生“光禄寺遣人于街坊市物,不复计直,概以势取”的事情(38)。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成化四年(1468)颁布法令,要求多官会估:“令(光禄寺)堂上官一员,及户科给事中、监察御史各一员,会同户部主事、顺天府官各一员,估计时价,钱钞兼支,具数奏领收买。如有奸弊,科道官指实参奏。”(39)那么,这些官员又是根据什么会估呢?嘉靖十九年(1540),巡视光禄寺监察御史商承学奏言:“该寺厨料,供公用之物,近年召商上纳,例该宛平、大兴二县,逐月委官,开具时估揭帖到寺。及臣查验,其间类多雷同迁就,难以服人。……乞敕顺天府,严督宛平、大兴二县官,每月朔望,各集经纪,谨较斗秤,备访物价,各具所闻实报,不必相同,以待估计之时,臣等参伍酌中,裒多益寡,上不损官,而俾价值之相应,下不损民,而致商贾之心服。”光禄寺回复亦云:“本寺各项供用物料,俱系召商上纳,逐月会同巡视科道,与户部主事、顺天府堂上,督同宛、大二县委官,照依市价,两平估计,给领银钱,比与民间多与一分,具载《会典》,相沿已久。”(40)据此可知,由于厨料需要经常买办,所以每月会估一次。定价的基本依据,是宛、大二县每月开报的时估,会估官员根据具体情况,可以上下调整。宛、大二县每月所报时估,应当只包括光禄寺各项供应物料,这与明初包括“民间市肆买卖一应货物价直”的按月时估大不相同。
需要指出的是,在各省直的果品厨料折征银两后,为了统一标准,嘉靖七年(1528)题准:“各项厨料,照依京师时估,定议则例,行各处查照发去价值,征解折色银两,送寺买办。”(41)这样,无论是在北京买办实物,还是向各府州县征收折银,便都以京师会估确定的价格为基准。光禄寺果品厨料之外,内府各库监局物料及各仓场草料,洪武以后也越来越倚重于买办。在买办过程中,抑价、拖欠等现象十分普遍。正统二年(1437),顺天府尹姜涛奏:“昨修灵济宫,市物民间,应给钞十二万贯。”英宗“命御史一人监给之”,并谕令“凡市物民间,所司即给直,毋迟缓以困民。”(42)是年,还正式规定了买办物料的会估之制:“买办物料,该部(即户部)委官一员,会同府县委官,拘集该行铺户,估计时价,关出官钱,仍委御史一员,会同给与铺行,收买送纳。”(43)尽管建立了会估制度,买办仍是铺户的沉重负担。成化十二年,顺天府尹邢简条称:“内府各监局并各部、光禄寺颜料、纸札等件,岁以万计,俱坐宛平、大兴二县并通州各项铺户预先买纳,然后估价领钞。铺户之贫者,不免称贷应用,比及关领,利归富家,民受侵损。”(44)为解决此类问题,陆续对给价方式做了一些调整,但收效不大。嘉靖二年,给事中汪应轸等疏言“今和买不给直”,请革京城铺户,认为“如不可革,则宜照例给价,务在两平”,户部议覆题准:“户、工二部凡办纳物料,皆当先给以价。”(45)
从有关记载看,正统二年出台的物料会估办法,在某些地方一直保持下来。如嘉靖前期任芜湖知县的张永明谈到:“内府每年取用物料,本县具申本府,会同科道、部司等官,约期估计,查照各年成案,参诸时估,两平无亏。”(46)但在京城买办的场合,物料价格的会估制度,似乎未能像光禄寺厨料的会估那样,顺利地执行下去。嘉靖七年,给事中蔡经等应诏陈言,其中一款“严时估以节浮费”云:“工部买办物料,每执先年定价,徇之则太重,减之则不足,出纳弗均,公私俱病。宜照光禄寺会估例,务合时宜,则事易集而浮费可省。”(47)可知,像光禄寺买办那样的会估办法,在工部买办中早已不复存在。
随着召买项目和数量的不断增加,买办价格脱离市场价格的现象越来越受到关注,不少官员提出改进意见。嘉靖五年,户部言:“山东、河南、北直隶粮草物料,近已题允征银,召商上纳。今秋成丰收,物价方平。请委官分投查访时值,及酌量脚价,示谕商人,俾赴总部等官告报完纳。如以后价有低昂,仍听总部官另行查访定夺,无得胶于一定。庶时价平准,召纳为便。”报可。(48)所谓“总部官”,即“山东、河南督理京粮道者”。当时各布政司都设有督粮道,而河南、山东二省在督粮道之外,还另设京粮道,“各有布政司官一员,在京总部钱粮”(49)。由于在京各仓场草料,“其商价俱于山东、河南粮道支给”(50),所以户部建议由总部官查访物价,以便根据时价变动情况调整召买价格。
嘉靖二十七年(1548),户部言:“京师召集诸商纳货取直(值),内则据诸司之通关实收,外则据两县、总部、九门官之时估,情法适中,公私均便。”(51)户部之言虽不无虚夸,但从中可以看出,此时的时估,并非由个别官员确定,而是由两县、总部、九门官共同估定。“总部”,即前述河南、山东二省总部京粮道。“两县”,即顺天府所属分辖京城东西地面的宛平、大兴二县。“九门官”,即户部“九门委官”。明代中叶以降,“在京九门及诸处收钞,已有内官同御史、主事、锦衣卫、五城兵马司官并铺户人等收受”(52),属于多头管理。到弘治十五年(1502),户部建议“京城九门所收商税,宜专委部属官主之,其守门内外官勿令干与”,孝宗允准(53)。由不同系统的官员会估定价,无疑有助于降低时估的随意性。
此外,在陪都南京,针对先买纳后估给价值的弊病,成化十八年(1482),南京监察御史徐完曾提出一项改革建议:“其铺行买办,宜按月时估给价,定限送纳,仍三年一次,造册送应天府,以备稽考。”经南京户部议覆题准。(54)这一建议明显对铺户有利,可惜虽经题准,但从有关记载看,似乎未能真正付诸实施。此后南京买办,仍是遇有需要,由地方官员拘集铺户随时估价,并不存在“按月时估给价”之制。如嘉靖十五年(1536),南京工部札令应天府买办纸张,应天府转行上元、江宁二县,“着落当该官吏,查照先年事例,即便拘集该行铺户到官,照依街市时直(值),从公估计”,二县遂委官“带领各行铺户,前赴会同馆,公同该府府尹孙懋,逐一体比街市两平,从公估计明白”(55)。
四、物料会估的定期化
如前所述,嘉靖以降,召买成为获取物料的主要途径,“国家内庭所需,强半召商买办以进”(56)。在这种情况下,时估是否合理,是关系到召买体制能否顺利运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嘉靖二十七年(1548),针对“入官应役者皆庸贩贱夫、漂流弱户”,“而富商即有一二置籍,往往诈称穷困,旋入旋出,无数年在官者”,户部建议每10年清审一次,给事中罗崇奎等上言:“部臣之说,意在革弊,而未悉弊源。臣等窃谓今日诸商所以重困者,其弊有四:夫物有贵贱,价有低昂,今当事之臣,贱则乐于减,贵则远嫌而不敢增,一也;诸商殚力经营,计早得公家之利,而收纳不时,一遭风雨,遂不可用,二也;既收之后,经管官更代不常,不即给直(值),或遂以况阁,三也;幸给直矣,而官司折阅于上,番校齮龁于下,名虽平估,然所得不能半之,四也。四弊不除,窃恐审编未久,而溃乱又随之矣。”(57)可见时估不平,抑价亏商,是导致商人“重困”的首要原因。为解决这些问题,有必要对时估制度做出较大改革。
嘉靖三十一年(1552),经户部议准,正式制定了定期化的时估办法:“自本年为始,每半年一次,将供用等库并各仓场一应合用物料粮草等项,山东、河南二道管粮官员查访,行令宛、大二县,造册六本,空立前件,二本送巡青科道,二本送巡视库藏科道,一本送巡视中城御史,一本送该司,与九门委官,公同参酌。如先估与市价相合,不必更易。其间物料时有贵贱,价有低昂,应增应减,务要酌量时宜,上半年不过正月,下半年不过七月,务依期照例时估。”(58)这一新规定,进一步扩大了会估官员的范围,除山东河南总部官、宛大二县官、九门委官外,巡青科道、巡视库藏科道、巡视中城御史,以及户部司官,也都参与价格估定,而且规定每半年会估一次,使时估成为一项周期性的常规制度。
新的会估办法出台后,所定时估不仅适用于召商买办,收纳各地解到物料亦以此为准。嘉靖三十二年(1553),户部尚书方钝题:“据广东解官吏目颜持思等告称,部解黑铅、油漆、银朱、芽叶茶、牛皮等料,官价与本部时估多寡不同,乞要通融折算抵数。合无以后查将解到物料,如一批有数项有原价浮于时估者,亦有时估浮于原价者,时估俱浮,则任其自补,原价俱浮,则照数扣官。时估、原价一低一昂,该补者多而该扣者少,无论扣数多寡,即与除免;该扣者多而该补者少,即与拨扣数以足该补,所余扣数,即送太仓银库交收。仍行浙江等十三司,查照一体施行。”(59)另据万历《明会典》,嘉靖三十二年议准:“行十三布政司、南北直隶所属,凡遇会派年例钱粮,务要以京估为准,有余者减,不足者增。”(60)
会估是否能及时进行,还有赖于法令的约束。嘉靖四十三年(1564),刑科给事中张岳建议:“每岁春秋二季,委官会估物价,以便官民,如有稽迟违误者,罪之。”(61)户部议覆:“行山东、河南粮储道,及行本部九门委官,并顺天府宛、大二县,将甲丁等库并仓场钱粮,每上下半年一次访估,各委官会同科道及本部该司,公同参酌,务使物价得平。其上半年时估定于正月内,下半年时估定于七月内各举行,如有稽迟潦草,听科道及委官查参究治。”(62)到隆庆四年(1570),户部又题请对会估办法进行调整:“物价与时低昂,而钱粮因时办纳,若先期估计,则贵贱无凭。或仓场远近,僦费多寡,遥度悬断,岂尽合宜。此后九门盐法委官,与十三司掌印官,及巡青科道估价,上半年定于五月,下半年定于八月,俱以十六日为期,务在随时估价,不得执一。其内库监局召买物料价,亦仿此。”(63)与以前的规定相比,新规定有两点不同:一是为使会估时间接近于召买时间,将会估时间由正、七月调整为五、八月,并规定了具体日期;二是参加会估的官员,有九门盐法委官、户部十三司掌印官和巡青科道,但不再包括山东、河南二粮道和宛、大二县。此外,在新规定中,以前的“九门委官”改称“九门盐法委官”,可知此时户部九门委官除商税外,还管理盐法事。史载万历年间,赵邦柱“授户部主事,司榷崇文门课,九门盐法秋毫不入槖”(64),即其例证。
半年一估的做法,一直持续到万历八年(1580)。万历九年,户部尚书张学颜疏请“酌定时估以厘商弊”,内云:“查得春秋两估,随时定价,故奸商每当会估,不惜重费,营求嘱托,估本不少而坚执以为少,估已渐多而尤益求其多,估一次求增一次。合无通行九门盐法委官,会同科道,将各仓场料草及各库物料,参酌往年近日旧册,某项费多利少,量为稍增;某项费少利多,量为稍减;某项原少,近日骤增太多,酌为量减。著为定规,以后非物价大相悬绝,每年不得再行会估。”奉旨允行。(65)根据此议,是年对时估全面厘定,以后物价如未发生剧烈波动,便不许再行会估。万历九年编纂的《万历会计录》,其卷30《内库供应》、卷36《仓场》,各附有一份“商价时估”,记录了内府各库司局和御马等仓应收纳物料粮草的会估价格。其按语云:“其递年上下二估,本部山东、河南等司官,九门盐法等委官,会同科道,照时岁丰歉,多寡不定,大约亦不甚远。今备录万历九年题准会估之数,以备查考。”除备录万历九年会估价外,凡物价与万历八年秋估不同者,还都标明了其增减之数,说明此年确实对物价进行了认真估定。
但市场价格起伏不定,停罢会估后,原就存在的“旧价不敷”现象变得更加严重,不少官员要求调整时估。万历十七年(1589),工部疏言“畿民铺商之役困累至极”,其原因之一是“先年裁减旧价,矫枉过直”,指出“惟将会估重加订正,则物价自平,众情自安矣”(66)。万历十九年,管理九门盐法主事马迈呈称:“各仓场库局召买料草,当因年岁丰啬增减价值。宜照万历八年以前一年两估,上半年拟于五月初旬,下半年拟于八月初旬,毋得徇私增减,致生弊端。”诏可。(67)这样,上下二估之制又得以恢复。
但不久,上下二估即变为一年一估。万历二十二年,户部覆刑科给事中马邦良疏,其中有一条“酌时价”:“甲丁等库召买物料与秋收物件,因岁丰歉,会估不同,合以上年估定之数为准。”(68)只言“上年估定之数”,而不区分春、秋估,可能此时已是一年一估。这种做法,持续到万历三十七年。《工部厂库须知》卷3《营缮司条议》云:“买办各项物料价值,载在《会估》。然亦与时低昂。往例年一行之,自三十七年后会估法废,未免偏肥偏枯,官商两碍。以后□以两年为限,公同科道备细估定,上下公平,庶措办易而督责易行。”(69)可知,召买物料的价格,万历三十七年前每年一估,自三十八年废止。至于所提以后每两年会估一次的建议,则未见实行。
各库买办停止会估后,由于物料“与时低昂”,未免病商,所以也曾对个别物料价格进行调整。如万历四十三年(1615),曾对木价进行会估。《工部厂库须知》卷4《修仓厂》一条夹注云:“一应木价,万历四十三年会估,每两加二钱。”同书卷5《神木厂》亦云:“今万历四十三年会估,木商苦称赔累,于长梁、柁木、松木每价一两各加银二钱,当照数补算。盖时价一二年间各有赢缩不等,故会估之法必须每年举行,□不失大常,不□小变,不能执一也。”天启元年(1621),户部尚书汪应蛟奏请“平估”,“谓京师物价腾贵,先年会估,较今价不啻天渊。容移知巡视诸臣,及札九门盐法部司等官,会同估直(值),照时价通融增减。”从之。(70)此次会估虽较全面,但仍属一次性举措。天启五年,巡视厂库工科给事中解学龙奏言“会估当议”,指出:“凡派买之钱粮,原无常额,而物料之贵贱,又无定衡。贵则病商,贱则病国。宜照年终会估之制,为价值画一之符,加意酌裁,低昂两协,务使后来任事之人,省一分可得一分之实用。”上然之,令着实举行。(71)这样,每年会估之制又得以恢复。
需要指出的是,在厂库物料会估改为“年一行之”后,仓场草料仍延续着每年两估。万历三十九年(1611),给事中周永春等曾谈到:“臣等巡青,节查每年两次会估,酌量丰歉,除散给各商外,大约上有赢余。”(72)天启三年(1623),给事中郭兴言等奏:“先年巡青商人,止供办草场草料,尚苦不支。后因十库商人巧为脱卸,致令巡青商人代办十库钱粮,贫役重累,膏尽血竭。查得万历四十八年以前,商人无十库之累,夏秋估价,毫不假借,每岁费银止二十七万余两。自天启元年代办十库钱粮,商人称苦,议价不免稍宽,岁费几至三十五万。目今正值春估之时,增之则病国,减之则病商,展转反复,计无所出。莫若查照旧规,免其代办,敕令巡视十库诸臣,照旧招商供办,事有专属,责无他诿,一举而两得矣。”(73)从这些题奏可知,各仓场草料一直是每年两估。天启五年,巡青给事中霍维华等“以商人苦累,酌议规则”,首条即为“议估价”:“物价与时消长,原无一定之理。乃从前估价,止就旧数,稍为增减,非平也。今议依季定估,不得故延后时,所估一照市价,不得一毫任意增减。”上命如议行。(74)这样,又由原来的每年两估,改为“依季定估”,即每年会估四次。
五、会估存在的问题
“夫物有贵贱,则价有低昂,此时估之法,所以防冒滥也”(75)。时估制度的规范化和定期化,无疑有助于使买办价格趋于合理,兼顾政府和铺商双方的利益。可惜的是,明代会估存在着不少问题,影响了其积极作用的发挥。
明代会估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会估人员敷衍了事,沿录旧卷。嘉靖十九年(1540),光禄寺指出:“迩来京师物价间多腾贵,科道时估,常欲樽节,不敢骤加,惟恐上亏官价,下招物议。”(76)万历三十九年(1611),工科给事中马从龙言:“厂库二次会估,不过据司厂送册裁酌,而司厂又凭旧卷开造。”(77)天启六年(1626),巡青给事中虞廷陛疏言:“查旧案,每岁派价,不论丰凶,概是相等,则陪费之苦,从何控诉?顷者估价,详访时值,量为增加。此后会估,定须与时高下,不得一概拘执。”(78)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吏治腐败,另一方面是因为明代赋税财政强调原额原则,会估亦受其影响,虽然要“照时岁丰歉,多寡不定”,但“大约亦不甚远”,即估价不能起伏太大,否则必须作出说明。如万历三十三年,巡青科道梁有年等因估价大增,上疏说明:“节年会估价值,多寡不大悬绝。近因水灾重大,菽草无收,市价腾踊,是以臣等所估,比之往时,有增四分之一,有三分之一,甚至特加一倍者。盖缘灾变非常,皇上且发冏金、免房号、平粜京通仓粮以拯救之,况此供役各商,安得执泥成规,驱之逋逃也。今后岁事稍丰,价值自应照旧,但勿令借口引援,为耗财病国之窦可耳。”(79)
会估存在的另一严重问题,是故意抬抑物价。嘉靖三十九年(1560),巡青科道官丘岳等请令“山东、河南二督粮官及宛、大二县估计价银,必虚心体访,以时低昂,毋令吏胥得高下其手”(80)。可见当时会估,有关官员往往不亲自访察,以致吏胥任意高下。在会估时,官员们为了节省朝廷开支,往往压抑价格。如隆庆三年(1569),“科道、部臣会估料价,每多避嫌过刻,令宜稍加从宽”(81)。万历十七年(1589),工部疏言“畿民铺商之役困累至极”,其中谈到:“查本部各役,万历十三年原佥四十余名,曾未三年,有削发为僧、弃家远遁者。祗因先年裁减旧价,矫枉过直。”(82)但也有的时候,有关人员故意高抬时估,从中牟利。如万历四年,礼科给事中武尚耕言:“内府甲乙等库,所以贮四海任土之贡,待朝廷不时之需,征解出纳,关系至重。其间利弊,不嫌指陈。各库急缺,例得题请召买,权也。乃射利之徒,见估价倍于时值,低价可以冒充,钻求召买。”(83)崇祯年间,户部尚书毕自严言:“召买之费,贵贱相权,本折相生,原属善政。今则高抬时估,从中侵渔,巨万金钱,半供飞销,此不可议节省乎?”(84)
此外,会估对物品的规格尺寸,往往规定得不够细致,致使当事官吏上下其手,冒支肥己。何士晋指出:“会估价值,所以示画一而杜纷争,法至详也。细玩其中,不无可议者。夫一木价也,前者可以比附,后者亦可比附,规则无定,价值溷淆,倘舞文者上下其手,而相去倍蓰矣。嗟嗟,此冒破之窦也!愚谓自今之急务,无如更定会估。木则以长短阔狭定为例,即比而不合者,亦按尺寸递为增减,毋得而假借焉。余物准是。庶奸胥无所庸其巧,而钱粮不至冒支矣。拔本塞源,此着吃紧,故旧估急宜更定也。”(85)其实,在吏治腐败的情况下,规定再细密,也总有罅漏可以利用,更定会估,只不过是治标之策而已。
六、小结
官府估定物价之制,很早就已出现,到唐代正式出现“时估”一词。明朝建立后,借鉴前代做法,建立了按月时估制度,要求在京兵马司、在外府州县每月初勘定时估,申报上司,凡遇买办物料等项,即以此作为价格依据。洪武以后,按月时估之制逐渐废格不行,遇到买办物料等项,因无现成时估可据,便采用随时估价的方式,而且一般都是令铺商买纳完毕再估价给值。明代中期,为了减少估价的随意性,针对光禄寺果品厨料和内府各库监局物料及各仓场草料,逐渐形成了各自独立的会估制度,由多个部门的官员共同估定价格。到嘉靖三十一年(1552),为了进一步规范物料的召买,规定每上、下半年各会估一次。至万历九年,每年两估之制停罢,万历十九年得以恢复,但不久即变为一年一估,此后又间有停罢。会估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买办价格的合理,但在会估过程中,也存在着沿录旧价、故意抬抑等弊端,常使铺商或国家蒙受重大损失。
注释:
①《明史》卷72《职官一》,孙承泽:《天府广记》卷13《户部》作“以时估约均输”。
②参见高寿仙:《明代北京三种物价资料的整理与分析》,载《明史研究》第9辑,黄山书社2005年版。
③《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上册,第737页。
④《十三经注疏》,上册,第654页。
⑤孙诒让:《周礼正义》卷5。
⑥《唐六典》卷20《太府寺》。
⑦《唐律疏议》卷4《名例律》“诸平赃者”条。
⑧《宋大诏令集》卷185《政事三十八·蠲复上》。
⑨《宋会要辑稿》食货64之42。
⑩《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卷26《户部十二·赋役·户役》。
(11)《明太祖实录》卷37,洪武元年十二月壬午条。“时其物价”,正德《明会典》卷36《户部二十一·斛斗秤尺》作“依时估定其物价”。
(12)《明太祖实录》卷129,洪武十三年正月庚子、己未条。
(13)《诸司职掌·户部·金科·权量》。
(14)参见邱澎生:《由市廛律例演变看明清政府对市场的法律规范》,载《史学:传承与变迁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历史系,1998年。
(15)姚思仁:《大明律附例注解》卷10《户律·市廛·市司评物价》。
(16)《大诰续编·牙行第八十二》。
(17)姚思仁:《大明律附例注解》卷10《户律·市廛·私充牙行埠头》。据姚思仁注解:“牙行,诸色各货所聚以为主者;埠头,诸色客货所泊以为主者。”
(18)《明英宗实录》卷232,景泰四年八月辛卯条。
(19)孙承泽:《天府广记》卷10《光禄寺》。
(20)万历《明会典》卷37《户部二十四·课程六·时估》。
(21)正德《明会典》卷36《户部二十一·时估》。
(22)《大诰续编·庆节和买第七十六》。
(23)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卷5《名例类》第2条《按季估计囚人纳纸价及禁约打搅囚人纳纸例》;卷20《户部类》第22条《内外人入官纸札不许增价卖纳》。
(24)杨一清:《关中奏议》卷6《巡抚类·一为分理诬枉事》。
(25)叶春及:《石洞集》卷8《公牍一·较勘斛斗称尺》、卷9《公牍二·时估》。
(26)方孝孺:《逊志斋集》卷14《送祝彦方致仕序》。
(27)万历《明会典》卷37《户部二十四·课程六·时估》。
(28)《明宣宗实录》卷11,洪熙元年十一月甲寅条。
(29)汪应轸:《恤民隐均偏累以安根本重地疏》,《明经世文编》卷191。
(30)陈诗启:《明代官手工业的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2页。并参阅高寿仙:《明代揽纳考论——以解京钱粮物料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
(31)沈榜:《宛署杂记》卷13《铺行》。
(32)《明世宗实录》卷66,嘉靖五年七月戊戌条。
(33)参阅佐佐木荣一:《商役の成立について——明代两京における买办体制の进展——》,《历史》第15号,1957年;佐藤学:《明末京师の商役优免问题について》,《集刊东洋学》第44号,1980年;许敏:《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召商买办”初探》,载《明史研究论丛》第一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4)万历《明会典》卷217《光禄寺》。
(35)《万历会计录》卷31《光禄寺供应·沿革事例》。
(36)万历《明会典》卷217《光禄寺》。
(37)梁材:《议勘光禄寺钱粮疏》,《明经世文编》卷102。
(38)《明宪宗实录》卷56,成化四年七月丙戌条。
(39)万历《明会典》卷217《光禄寺》。
(40)《明世宗实录》卷237,嘉靖十九年五月丁酉条;梁材:《议勘光禄寺钱粮疏》,《明经世文编》卷102。
(41)《万历会计录》卷31《光禄寺供应》。
(42)《明英宗实录》卷30,正统二年五月庚戌条。
(43)万历《明会典》卷37《户部二十四·课程六·时估》。
(44)《明宪宗实录》卷151,成化十二年三月甲寅条。
(45)《钦定续文献通考》卷25《市籴考·均输市易和买》。
(46)张永明:《张庄僖文集》卷2《议处铺行疏》。
(47)《明世宗实录》卷87,嘉靖七年四月庚申条。
(48)《明世宗实录》卷67,嘉靖五年八月壬戌条。
(49)参见《明世宗实录》卷514,嘉靖四十一年十月乙卯条;《明穆宗实录》卷46,隆庆四年六月甲辰条;《明穆宗实录》卷47,隆庆四年七月辛未条;《明神宗实录》卷101,万历八年六月丙午条。
(50)万历《明会典》卷23《户部十·仓庾三·马房等仓》。
(51)《明世宗实录》卷336,嘉靖二十七年五月癸巳条。
(52)《明英宗实录》卷27,正统二年二月乙酉条。
(53)《明孝宗实录》卷188,弘治十五年六月甲辰条。
(54)《明宪宗实录》卷224,成化十八年二月辛丑条。
(55)孙懋:《孙毅庵奏议》卷下《处以便官民疏》。
(56)沈榜:《宛署杂记》卷7《廊头》。
(57)《明世宗实录》卷336,嘉靖二十七年五月癸巳条。
(58)万历《明会典》卷37《户部二十四·课程六·时估》。
(59)《万历会计录》卷30《内库供应·沿革事例》。
(60)万历《明会典》卷37《户部二十四·课程六·时估》。
(61)《明世宗实录》卷540,嘉靖四十三年十一月戊午条。
(62)《万历会计录》卷30《内库供应·沿革事例》。
(63)《明穆宗实录》卷46,隆庆四年六月甲辰条。
(64)雍正《湖广通志》卷47《乡贤志》。此外,《明神宗实录》卷242,万历十九年十一月丙寅条提到“管理九门盐法主事马迈”,亦其例证。
(65)《万历会计录》卷30《内库供应·沿革事例》;卷三六《仓场·沿革事例》。
(66)《明神宗实录》卷207,万历十七年正月甲寅条。
(67)《明神宗实录》卷242,万历十九年十一月丙寅条。
(68)《明神宗实录》卷269,万历二十二年正月丙午条。
(69)《工部厂库须知》卷3《营缮司条议》。
(70)《钦定续文献通考》卷25《市籴考·均输市易和买》。
(71)《明熹宗实录》卷59,天启五年五月丙寅条。
(72)《明神宗实录》卷488,万历三十九年十月戊子条。
(73)《明熹宗实录》卷35,天启三年六月丁丑条。
(74)《明熹宗实录》卷61,天启五年七月庚申条。
(75)沈榜:《宛署杂记》卷13《铺行》。
(76)梁材:《议勘光禄寺钱粮疏》,《明经世文编》卷102。
(77)《明神宗实录》卷487,万历三十九年九月辛丑条。
(78)《明熹宗实录》卷78,天启六年十一月己丑条。
(79)《明神宗实录》卷405,万历三十三年正月癸巳条。
(80)《明世宗实录》卷483,嘉靖三十九年四月庚申条。
(81)《明穆宗实录》卷32,隆庆三年五月戊午条。
(82)《明神宗实录》卷207,万历十七年正月甲寅条。
(83)《明神宗实录》卷57,万历四年十二月壬午条。
(84)毕自严:《石隐园藏稿》卷6《题议主客兵饷疏》。
(85)《工部厂库须知》卷12《又附陵工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