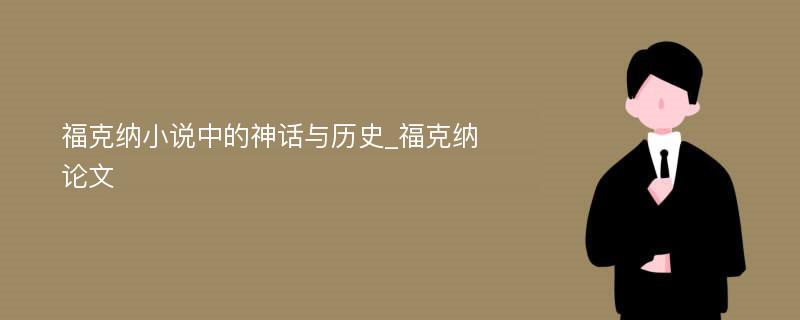
福克纳小说中的神话与历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神话论文,历史论文,福克纳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福克纳和乔伊斯、伍尔夫等作家一直被看作是现代主义文学成熟期的代表,而帕特里克·奥道纳尔最近发表的《福克纳与后现代主义》一文却探讨了福克纳小说中的后现代性,颇为引人注目。奥道纳尔认为,现代主义文学具有明显的神话倾向,因为现代主义作家大多以“艺术家上帝”自居,极力想用文字创造自己的神话世界,以取代那个失去了上帝和秩序的现代世界。这些神话世界包括乔伊斯的都柏林、伍尔夫的布卢姆伯里、叶芝的拜占庭、庞德的坦皮奥·马拉特斯等。和这些现代主义作家一样,福克纳也创造了自己的神话世界—约克纳帕塔法。但是,奥道纳尔指出,福克纳在其“最成熟的现代主义作品”《押沙龙,押沙龙!》之后写的《去吧,摩西》中,开始“复查并质疑他在约克纳帕塔法系列小说中建立起的那个现代神话‘世界’的结构成分”,包括那些确定起源和自我同一性的努力、把自然理想化以及把他者寓言化的倾向等,并开始尊重“历史的无可辩驳的物质性”,从而表现了明显的后现代性。[①]
奥纳道尔观点对于我们深入了解福克纳,尤其是福克纳的自我修改能力,无疑很有意义。然而,由于奥纳道尔的分析集中于《去吧,摩西》与《押沙龙,押沙龙!》之间的历史与神话的冲突,难免会引出这样的问题:《去吧,摩西》突出的批判性是否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奥纳道尔认为,福克纳的后现代性产生于福克纳的“修改能力”。那么,福克纳在《去吧,摩西》之前创作的《喧嚣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等作品的巨大魅力是否也与这种能力有关?[②]本文拟通过重点比较福克纳的三部都以南方贵族家史为题材的小说—《沙多里斯》、《喧嚣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试就这两个相关的问题做点探讨。
在使现代世界大成问题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步入文坛的福克纳,并非从一开始就有意要创造一个自己的神话世界。他的第一部小说《士兵的报酬》与海明威的处女作《太阳照样升起》一同于1926年发表,表现的也是当时较为流行的主题,即战争给人的身心留下的严重创伤。小说的男主角梅恩是一位军官,因在战争中头受重伤,几乎完全丧失了视力与记忆,退役回乡后,又遇上未婚妻赛西丽另有所爱,无法得到应得的关怀,最后在茫茫黑夜中死去。不过在这部作品中,我们也能找到促使福克纳日后创造自己的神话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即现代世界的混乱无序。小说女主角赛西丽不遵守战前与梅恩确立的婚约,朝三暮四,较集中地表现了战后的现实“象诺言一样空洞”,[③]法律和道德已丧失维护社会秩序的功用的可悲状况。梅恩因丧失视与记忆而不能观察、思考与行动,表现出人们面对这种新现实时的困惑与无奈。
意识已难以认知与控制存在的主题,在福克纳的第二部小说《群蚊》中,得到了更加集中和深入的处理。一群艺术家应邀登上了一只游艇,得以无忧无虑地探讨词与物、艺术与生活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然而,他们的高谈阔论却频频受到现实的无情嘲弄。雕塑家戈登在与酷似其艺术理想的帕特里克小姐恋爱的过程中莫名其妙被抛弃了。计划周全的塔里奥费罗追求珍妮小姐遭受巨大挫折,使谙于世故的小说家费尔恰尔德惊愕不已,宣称如此奇特的真实故事定会令巴尔扎克也羞于再苦思冥想。在这样的现实中,往日被誉为立法人、预言家的艺术家们变成了卑微无能的“群蚊”,只能哀叹文艺无法再现“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的现实生活,[④]哀叹语言活动非但不能传达意义,而且变成了一种将意义化为声音后再加以扼杀的“令人心碎的愚蠢行为”。[⑤]
梅列金斯其认为,神话在20世纪文学领域中的复兴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整个资本主义文明危机迫使人们诉诸人类共有的心理及玄学之本原,努力探寻超越社会-历史的限定以及空间-时间的限定的出路。二是神话因其固有的象征性,适合表现个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永恒模式以及人类和自然界中的某些基本规律。[⑥]福克纳的头两部作品就表明了这样两个促使他转而诉诸神话的类似原因:一方面是没有上帝的现代社会混乱无序;另一方面是语言的极度贫乏。
与许多现代主义作家一样,福克纳的神话创作也是立足于与现代社会形成某种对照的相对落后、稳定而又为自己熟悉的地域。因此,便有了他以故乡小镇奥克斯福特为原型创造的约克纳帕塔法郡杰弗逊镇。这个神话世界最先出现在他的第三部小说《沙多里斯》中。“从《沙多里斯》起,”福克纳说,“我发现我自己的那块邮票大小的土地值得一写,而且我今生今世决不会把他写尽。通过化实为虚,我就可以发挥我的那点儿才华。……所以我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地。”[⑦]正是在这个他以为完全是属于自己的天地里,福克纳要创造一个与前两部作品中的那个世界不同的井然有序的神话世界。
福克纳在《沙多里斯》中重建秩序的努力首先表现在他对贵族家族沙多里斯家族的神化上。小说里有两位沙多里斯家族神话的制造者。一位是老黑奴福尔斯。小说以对他的描写开篇,写他又来到老贝亚德的办公室,讲述后者的先父沙多里斯上校当年在内战中的英雄业绩。这种讲述已变成福尔斯的一种习惯。作者写到:“与往常一样,老人福尔斯又将约翰·沙多里斯带到这间屋里…。”福尔斯这次来不仅要重复沙多里斯上校的故事,还要将他保存50年之久的沙多里斯上校的烟斗移交老贝亚德继续保存。老黑奴福尔斯的这些纪念与赞美沙多里斯上校的重复性活动对于巩固对沙多里斯家族的统治地位,维护传统的秩序,无疑是很有必要的。
沙多里斯家族神话的第二位制造者是珍妮姨妈。珍妮姨妈“总是那么能说会道。…她的话生动有力,言简意赅。她用的大胆比喻连德摩斯梯尼也望尘莫及,连骡子也能心领神会…。”[⑧]她象福尔斯一样,也是反复地向多沙里斯家族的后代以及他人讲述沙多里斯上校及其弟弟的故事,为他们歌功颂德,“而且她年纪越大,故事本身也越丰富,变得象芳香、灿烂的美酒一般…”。[⑨]
当然,沙多里斯家族神话的总设计者是小说作者。《沙多里斯》实际上就是一部沙多里斯家族四代人的历史。这个家族中有大庄园主、内战中的上校、铁路大王、银行行长、一战中的英雄等。在这部小说中塑造出这样一个豪杰辈出的家族,并赋予它无上的权威,这对于此前曾反复表现现代社会缺乏权威、毫无秩序的作者来说,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与福尔斯和珍妮一样,作者也经常运用重复这一制造神话的手法。为了强调传统的优越性,他用了许多细节来反复表现骑马比开车更加气派与安全,传统医药比现代医药更加有效。他还用了“约翰”和“贝亚德”两个名字来命名四代沙多里斯中的六位男性,从而造成了较为独特的重名现象。这一现象似乎也与作者要使沙多里斯家族的统治地位保持不变的愿望有关。
作者要重建秩序的愿望还表现在对黑人和穷白人的抑制上。这些黑人和穷白人渴望自由和平等,从而对沙多里斯家族构成了威胁。老黑奴西门斯的儿子卡斯佩从战场上回来后,居功自傲,公然无视珍妮姨妈和老贝亚德的权威,拒绝为他们劳动,被老贝亚特一棒打倒在西门斯脚下,并挨了西门斯的一通责骂:“我一直告诉你,你的那些花花点子在这里行不通。你得感谢上帝给了你一个硬脑壳。你去套马吧。把你的那些关于黑人解放的言论留起来向城里人去说吧;他们或许能听的进去。再说了,我们这帮黑鬼要自由又干嘛呢?”[⑩]此后,卡斯佩再也没有任何不轨的言行。作者一边让西门斯训导儿子别存非分的想法,一边也把西门斯自己写成不知如何享用自由的人,写他一有空就去引诱一少女,结果在少女屋里被人砸开头颅。
与黑人相比,穷白人对沙多里斯家族的威胁更大。卡斯佩虽然说要找一个白人女子玩玩,但他只是说说而已,而穷白人司诺普斯却以实际行动向沙多里斯家族展开了挑战。他接二连三地寄发匿名情书,与小贝亚特争夺贵族小姐娜西萨丝的爱情。最后,作者象处理黑人的结局一样,也写了司诺普斯一败涂地。娜西萨斯最后嫁给了小贝亚特。司诺普斯背着小人、骗子、窃贼等恶名,拖着一条伤腿半夜三更仓皇逃离杰弗逊。
然而,无论作者怎样贬抑黑人和穷白人,褒扬贵族,他无法回避南北战争以后南方贵族家族普遍衰落的事实。小说中其实也提到沙多里斯家族丧失铁路所有权、小贝亚特不得不参加田间劳动等情况。但是,作者把沙多里斯家族的变故主要归咎于以被老贝亚特称为“毒蛇”的汽车为标志的现代科技。老贝亚特猝死在汽车里。小贝亚特开快车事故不断,最后和其孪生兄弟约翰一样,死在飞机上。作者的这种解释淡化了威胁他的那个神话世界的一个重要历史因素,即遭受压迫的黑人和穷白人争取自由平等的斗争。
福克纳在第一部约克纳帕塔法小说《沙多里斯》中制造的神话在他随后发表的《喧嚣与骚动》中得到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尽管这部小说仍以一贵族家族——康普生家族为中心,而且这个家族在历史上曾出过三位将军和一位州长,地位比沙多里斯家族显赫,但是作品描写的着重点却转到了这个贵族家族不可救药的衰败所带来的绝望与痛苦,以及他们为维护家族的声誉而做的最后挣扎之上。如果说沙多里斯家族还有发展的希望,因为《沙多里斯》最后写了第四代沙多里斯小贝亚特与贵族小姐成婚并生下一子,那么康普生家族的消亡到小说结束时已基本成为定局,因为第四代康普生的三位男性中无一人有家室。
《喧嚣与骚动》对《沙多里斯》的第二点修改是强调了康普生家族衰败的社会原因。尽管有评论认为康普生家族衰败的根本原因在康普生太太身上,[(11)]但小说表现了穷白人和黑人的难以被随意抑制的力量,与《沙多里斯》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照。在《沙多里斯》中,只有一个穷白人试图引诱一个贵族小姐,而且以失败告终。在《喧嚣与骚动》中,以流浪汉艾米斯·戴尔顿和戴红领结的无名演员为代表的许多穷白人引诱贵族小姐凯蒂和小昆丁都如愿以偿。在这部小说塑造的几个较为突出的黑人形象中,除了老黑奴迪尔西,大多不但象《沙多里斯》中刚退役返乡的卡斯佩那样好逸恶劳,而且还桀骜不驯,而白主人中已无人能象《沙多里斯》里的老贝亚特用棍子改造卡斯佩那样改造他们了。
《喧嚣与骚动》里的这个世界一个缺乏权威、分崩离析的世界,其状况如同昆丁在钟表店里所见到的那样:“橱窗里有大约一打手表,显示着12个不同的时刻,而且每只表都象我这只没有指针的表一样毫不含糊,各执一端。互相不断冲突。”[(12)]在这种情况下,作家除了表现贵族们视死如归的气度,难以象在《沙多里斯》中那样再神化他们了。这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福克纳在写了《喧嚣与骚动》以后,便将注意力由贵族转向下层人,如《我弥留之际》中的穷白人本特伦一家、《圣殿》中的贩卖私酒者波普埃、《八月之光》中的血统不明的孤儿克里思特姆斯、《塔标》中的飞行特技表演者们,等等。一直到《押沙龙,押沙龙!》,福克纳才又第三次捡起南方贵族生活的题材,写了塞特潘家族的历史,但这时的福克纳比在《喧嚣与骚动》中修改《沙多里斯》的神话的福克纳更加成熟了。
奥道纳尔在《福克纳与后现代主义》中强调《去吧,摩西》用历史对《押沙龙,押沙龙!》中的神话所进行的批判的同时,似乎低估了《押沙龙,押沙龙!》自身的批判力度,尽管奥道纳尔提到此书内部“有时”也会出现这种批判。[(13)]其实,《押沙龙,押沙龙!》对神话倾向具有有力的批判,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押沙龙,押沙龙!》中,福克纳不仅写了约克纳帕塔法郡最大的庄园主塞特潘的衰败史,而且还写了塞特潘的发迹史。这是福克纳对自己处理贵族家史的套路的一个颇有意味的突破。福尔纳写沙多里斯家族和康普生家族的历史时,只上溯到两个家族中最强盛的那一代。至于那一代人是如何强盛起来的,两部小说没作解释。作者似乎认为,这两个家族既以强盛开始,就理所当然地应保持这种强盛,任何威胁这种状态的力量都是无理的,这两个家族的任何衰微都是不幸的。可以说,作者的这种意识是这两部家族史在《沙多里斯》和《喧嚣与骚动》中得以发端的基本前提之一。这个前提类似于神话的一个基本前提,即神性是不容置疑的。而在《押沙龙,押沙龙!》中,那个神话般的“塞特潘百亩庄园”却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靠用从印地安人手中骗来的土地和黑奴们的血汗建立起来的。塞特潘也不是天生的庄园主。他出生在没有私有制、没有阶级的西弗吉尼亚深山老林里,随父亲迁到弗吉尼亚的泰德沃特后,才了解贫富差异,在因为贫穷而受到一个庄园主家的黑奴的轻辱后,才决意要当一个更大的庄园主,以洗雪耻辱。塞特潘的发迹过程出现在小说的后半部里。这样的安排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针对前半部里的叙事者对塞特潘的神化而作出的。
其次,《押沙龙,押沙龙!》对塞特潘家族衰败的社会原因,尤其是黑人的反抗,有着较为客观的揭示。在《沙多里斯》中,黑人受到丑化,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矛盾也被淡化了。对于南北战争这个黑人与白人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沙多里斯》中的白人和黑人都认为与蓄奴制无关,而且一点政治意味也没有,大家参战仅仅是闹着玩。沙多里斯家族的发言人珍妮姨妈说,南北战争中指挥官们追求的只是“纯粹的乐趣”:“杰伯·斯图亚特(将军)和贝亚德·沙多里斯的行为都清楚地表明,他们没有丝毫的政治目的。”[(14)]当老贝亚特问老黑奴福尔斯当年究竟为何随沙多里斯上校参战时,福尔斯答道:“我要是知道,我就不是人。”[(15)]因此,导致沙多里斯家族衰败的原因似乎只有现代科技和该家族的鲁莽天性。《喧嚣与骚动》虽然比《沙多里斯》写了更多的黑人的散漫与不驯,但作者认为康普生家族的衰败主要是由于内部原因。他曾把这本小说称为“一个关于血液出了毛病的故事”,[(16)]还不止一次地说这个故事写的是两个女人的堕落。[(17)]在小说中杰生羞辱那些推销员时曾提及他们家拥有许多黑奴的历史,[(18)]但仅这一次。而且如同《沙多里斯》,小说也回避了贵族家族的衰败与解放了黑奴的南北战争之间的关系,以至于有评论认为康普生家族的衰败与小说的南方背景没有什么关系。[(19)]而《押沙龙,押沙龙!》不但写了黑奴在建立“塞特潘百亩庄园”中的重要作用,也写了黑奴争取解放的斗争在这个庄园以及建立在黑奴劳动基础上的整个南方农业经济的崩溃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塞特潘家族的衰败始于被塞特潘离弃的混血妻子与儿女对他的报复。这一报复在小说中与南北战争几乎同时发生,并非是一种巧合;它传达了作者对南北战争性质的新认识。这种认识通过一些人物之口得到了清楚的表达。科尔德菲尔德先生和昆丁就曾明确地把南方在南北战争中的失败归咎于它“没有把其经济大厦建立在严格的道德这一坚实基础之上”[(20)]以及南方的“森严的等级制度”。[(21)]瓦因思坦对《押沙龙,押沙龙!》在描写黑人上的成就有较高的评价。他说,与福克纳以前的作品不同,在《押沙龙,押沙龙!》中,“黑人被置于一个广大的社会、经济和历史结构之中。”[(22)]
《押沙龙,押沙龙!》用历史批判神话的第三点表现,是作者在叙事结构上把这本小说写成了一个不断用史实多、神话少的叙述修改史实少、神话多的叙述,不断接近历史真相的过程。整部作品的叙述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的叙事者罗莎是塞特潘的小姨子,也是所有叙述者中唯一见过塞特潘的人。然而,她的叙述中的事实最少,而且她的叙述,就象《沙多里斯》和《喧嚣与骚动》对沙多里斯和康普生的家族史的叙述那样,基本上也是从塞特潘家族开始衰败以后起头的。因为不了解塞特潘的发迹经过,不了解她所叙述的那些事件的原由与关系,她解释塞特潘家族衰败原因时便大量地诉诸神话。其中主要的是把塞特潘说成恶魔的神话。她把塞特潘比作“童话中令孩子们害怕的恶魔与怪兽”,[(23)]说他是个“看不见光亮的蝙蝠样的形象,由于愿意受罪,被地下魔灯的强烈光亮给投射了上来…。”[(24)]
罗莎制造的神话受到了第二位叙述者康普生先生的修改。康普生先生虽然从未见过塞特潘,但他从父亲康普生将军以及其他知情人那里了解到比罗莎所经历的要多得多的知识。例如,关于塞特潘来杰弗逊建起当地最大的庄园这件事,罗莎只编造了这样的简短神话:“这个魔鬼——他名叫塞特潘…似乎没有来历,就这样骤然领着一帮陌生的黑鬼来到此地,…眨眼间就建起一个庄园”。[(25)]而康普生先生则了解塞特潘的来历以及他六年创业的经过。丰富的历史知识使得康普生先生不象罗莎那样绝对,把塞特潘只看作恶魔。他说:“你是否注意到,当我们重构男人们和女人们的动机时,我们是多么经常和惊讶地发现自己会得出这样的信念,这样可能得出的唯一信念,即那些动机起源于某些旧时的美德?小偷行窃并非出于贪婪,而是出于爱心;杀人者行凶并非出于私欲,而是出于同情?”[(26)]康普生先生的这种相当辩证的思维方式与罗莎片面、静止的思维方式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照。正是基于他尊重历史的态度,康普生先生在解释不了享利为何杀勃恩时,不象罗莎那样编造神话,把责任统统推到塞特潘身上,而是坦率地表示自己无能为力,承认“一定缺少了什么事实”。[(27)]
这个缺少了的事实在小说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没有它,不仅叙述者们无法解释享利为何杀勃恩、塞特潘家族为何会衰败这类重要问题,也会使小说的用历史修改神话的主题大为削弱。福克纳运用回避、省略等手法,把这一事实一直推迟到罗莎和康普生先生的叙述充分暴露出因缺少这一事实而存在的问题之后,才让第三位叙述者昆丁做出交代。这一作法本身就反映了作者想强调这一事实的重要性的意图。这个被悬置了近一年书的事实就是勃恩有黑人血统。塞特潘正是因为勃恩有黑人血统而不愿认这个儿子。勃恩则为了得到白人生父的承认而坚持斗争,直至提出要娶同父异母的白人妹妹失迪思。于是,塞特潘只得对儿子享利说了勃恩是黑人,使享利杀人黑人哥哥,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导致塞特潘家族灭亡的事件。《押沙龙,押沙龙!》对于南方庄园主的命运与黑人的命运之间这种密切关系的揭示,是对罗莎的叙述以及福克纳前期作品中有关庄园主的那些神话的一次较大修改。罗莎关于塞特潘是恶魔的神话掩盖了以塞特潘为代表的庄园主与以勃恩为代表的黑人之间的矛盾。福克纳最后写她在极度的困惑中死去,也能反映他这时对待神话的态度。
通过以上对《沙多里斯》、《喧嚣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的分析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福克纳不断用历史修改神话,从而使约克纳帕塔法这个神话世界变得更具体、更复杂、更接近历史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奥道纳尔所强调的福克纳在《去吧,摩西》中表现出的对现代主义神话倾向的批判精神,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的。至于如何给福克纳定性的问题,是把他继续看作现代主义作家,还是把他改定为后现代主义作家或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于一身的作家,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福克纳具有很强的自我修改能力。他能以很大的勇气和很快的速度不断修改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和自己的前期作品,从而能在贫穷落后的南方脱颖而出,成为一个富有特点的伟大作家。
注释:
① (13)Patrick O'Donnell,"Faulkner and Postmodernism",Philip M.Weinstein 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William Faulkn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P.49,36.
②斯托诺姆曾对贯穿福克纳创作生涯的自我批评精神做过较为全面、深入的讨论,但他的讨论侧重于福克纳的自我批评精神在其叙事手法的发展上的表现。见 Gary Lee Stonum:Faulkner's Career:An Internal Literary Histor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9.
③William Faulkner:Soldiers'Pay(London:Chatto and Windus,1974),p.85.
④⑤William Faulkner:Mosquitoes(New York:Liveright,1955),PP.181,186.
⑥叶·莫·梅列金斯基:《神话的诗学》,魏庆征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3—4页。
⑦ (16) (17)James B.Meriwether and Michael Millgate ed.,Lion in the Garde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68),255,PP.222,222—224.
⑧ ⑨ ⑩ (14) (15)William Faulkner:Sartoris (Random House,1956),PP.38,9,83,10,227.
(11)见 CLeanth Brooks:William Faulkner:The Yoknapatawpha Country(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333,334,344页。另见Andre Bleikasten:The Inkof Melancholy(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0),75页。
(12) (18) William Faulkner:The Sound and the Fury(Random House,1957),PP.104,256.
(19)见 William Faulkner:The Yoknapatawpha Country,334,344页。另见 Edmond L.Volpe:A Reader's Guide to William Faulkner(New York:Octagon Books,1981),95,104页。
(20) (21) (23) (24) (25) (26) (27) William Faulkner:Absalom,Absalom!(vintage,1972),PP.260,345,158,171,9,121,101.
(22)Philip M.Weinstein:Faulkner's Subject(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92),P.53.
标签:福克纳论文; 神话论文; 小说论文; 贵族精神论文; 贵族等级论文; 文学论文; 庄园经济论文; 押沙龙论文; 康普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