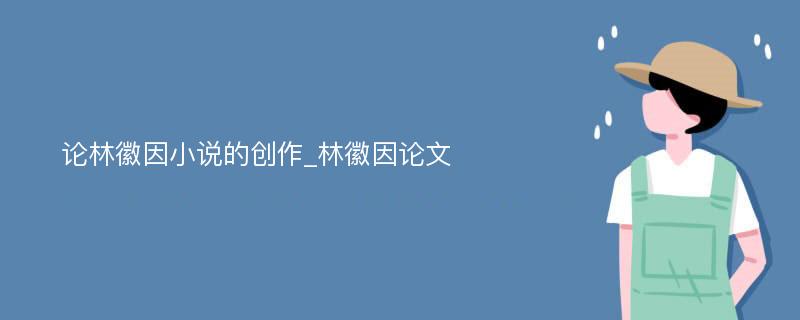
林徽因小说创作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林徽因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04)05-0066-04
提起林徽因,人们会想到她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学家。作为中国现代建筑学的先驱,她 曾参加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建筑学界做出了卓越贡献。 林徽因生前未出过文学作品集,写作只是她的副业,但她却为我们留下了诗歌、散文、 小说和剧本等诸多体裁的文学作品,以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为不可忽略的存在。
在现代文坛,林徽因通常被视为“新月派”的著名诗人。1931年陈梦家编选《新月诗 选》,她是入选的18位诗人之一。而在由学院派精英组成的京派作家中,林徽因其实是 “有实力有生气的作家”[1]和京派组织者之一。1936年,她曾受邀主持编选了《大公 报·文艺丛刊小说选》(第1集),并曾任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编委,京派的后起 之秀萧乾甚至称她为“京派的灵魂”。
作为京派小说家的林徽因,她留给读者的作品,只有6个短篇。它们是《窘》、《九十 九度中》和总题为《模影零篇》中的4篇作品:《钟绿》、《吉公》、《文珍》和《绣 绣》。这些作品创作于30年代,先后发表在《新月》、《学文》和《大公报·文艺副刊 》等刊物上。时隔半个多世纪,在历史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审视距离的今天,重读林徽 因的这些小说,你会觉得,它们虽为数不多,却可谓篇篇珠玑,不失为京派小说中的珍 品。它们负载着较丰厚的人文内涵,在艺术上作出了多方探索,既显示了京派小说的一 般风貌,又体现出作者鲜明的文学个性,至今仍然以其独特的文化品格和审美价值,散 发着诱人的艺术魅力。
一
京派的主要作家和理论家沈从文,1933年10月18日曾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 发表了引发“京派”与“海派”论争的《文学者的态度》。文中,沈从文引导文学者要 以“诚实”的态度对待创作,他认为伟大作品的产生,“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作家诚实 地去做”。与此相应,林徽因在《文艺丛刊小说选题记》中明确指出:“作品最主要处 是诚实。诚实的重要还在题材的新鲜,结构的完整,文字的流丽之上。即是作品需诚实 于作者客观所明了,主观所体验的生活。”从这一创作思想出发,林徽因在小说创作中 ,既着笔于她所熟悉的知识分子圈内的生活,又能突破自己生活的局限,去关注“窗子 以外”的大千世界,去描写自己“在理智上所极明了,在感情上极能体验得出的情景或 人性”[2]。她以精湛的文化观照,表现普通人的平凡生活和生存状态,展示人物的命 运图景和情感活动轨迹,进而表达着对时代及现实社会的思考。
刊于1931年9月《新月》杂志3卷9期的短篇《窘》,是林徽因小说的处女作。作品的主 人公维杉,是刚刚步入中年的单身知识分子。他在暑假“沉闷,无聊”的孤寂生活中, 感到自己是“四不像的落魄”。在朋友少朗家,他同少朗家的3个“活龙似的”孩子在 一起,彼此年龄的差异,使他明显“觉着不自在——不自然”!在和孩子们的周旋中, 维杉觉得自己“和他们中间至少有一道沟”。由于“代沟”的存在,维杉处处感到“窘 极了”。同时,小说还写到维杉在少朗的女儿芝面前“窘”的心理感受。目睹灵敏、秀 媚的芝“少女的丰神”,作品含蓄地表露了主人公朦胧的性意识的萌动,表现出人物的 意识和潜意识、“里比多”与自我、超我之间的矛盾境地。小说把主人公难以说出的“ 窘态”描绘得入木三分。而紧扣主人公暑假中在北京“窘”的心理感受,作品生动、细 腻地写出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的精神压抑和生存尴尬,把未完的思索留给了 读者。
如果说,短篇《窘》着笔于知识分子圈内的生活,还只是作者表现自己身边人物的“ 客厅题材”,那么,发表于1934年5月《学文》杂志1卷1期上的《九十九度中》,则是 林徽因“更热诚地来刻画这多面错综复杂的人生”,尝试写出“生活大胆的断面”,“ 剖示贴己生活的矛盾”[2],具体表现广阔的时代人生的佳作。《九十九度中》以近1.5 万字的篇幅,全景式、立体地呈现了华氏99度(摄氏37度)下,北平市民阶层“通常的人 生”。如果“把人生看做一根合抱不来的木料,《九十九度中》正是一个人生的横切面 。在这样溽暑的一个北平,作者把一天的形形色色披露在我们的眼前”[3]:汗流浃背 的挑夫,奔走在被太阳晒得滚烫的马路上担送筵席;装束入时的太太,打着油纸伞坐在 洋车上去赴“阔绰的应酬”;机关人员闲坐在点心铺借聊天以“消磨时光”;洋车夫仅 为14吊钱双方扭打而被巡警弹压;大户人家设宴做寿,厨房、院内一派“华丽的景象” ;饿着肚子的小丫头,耐着性子坐在老太太屋的门槛上“等候呼唤”;喜燕堂正厅内热 闹的婚礼上,心存疑惧的新娘“一鞠躬,一鞠躬地和幸福作别”;身染霍乱的穷挑夫“ 沉入严重的症候里和死搏斗”,数小时毙命……这单纯而又复杂的人生,贫富不均、哀 乐共存的世情,带“原味”的生活和人生本真,大千世界中“所有的活动的颜色、声音 、生的滋味”[4],都被作者摄取片断,精心而有序地组织在作品中。从中,不仅表现 出作者“人类的同情”[3],鲜明的是非观和道德感,也显示了京派小说家积极的入世 精神和人生态度,实现着京派作家讽喻现实、关爱人生的共同理想。
二
如同沈从文认为创作“是当前‘一切官能感觉的回忆’”[5]一样,林徽因则提出“创 作的主力固在心底”[6],而小说作者要想达到“活力真诚”的创作境界,他“在运用 文字的技术学问外,必须是能立在任何生活上面,能在主观与客观之间,感觉和了解之 间,理智上进退有余,情感上横溢奔放,记忆与幻想交错相辅,到了真即是假,假即是 真的程度”[2]。这一创作思想,正昭示着京派小说把写实、记“梦”融于一炉的共同 审美追求。在总题为《模影零篇》的4个短篇中,林徽因从自己年少时的印象中拮取生 活断片,在追怀和记忆中“体验”情感,叙写着普通人平凡而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生故事 ,刻画了一个个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正是在这“传奇”化的故事中,在对具体情景里 个体生命过程的展示中,林徽因传递着京派作家“纯美”的理想追求,发掘和呼唤着美 好的人性、人情,进一步流露出对现实的文化批判和人文关怀,以及京派小说家观照理 想人生的文化选择。
《钟绿》的主人公钟绿是一个有希腊血统的留美女学生,她是“我”“记忆中第一个 美人”,一生中所见到的“真正的美人”。随着作者娓娓动情地追溯,一幅幅钟绿的图 画——一张宗教画,一张风雨中的村姑画,一张古典的自画像,一张现代美女画——在 读者面前渐次展开。于是,钟绿在读者面前,由隐隐约约的印象,终于成为实实在在的 人物。她简单静穆,纯朴天真,自然和谐而又高雅脱俗。而作者还要进一步渲染:“她 的美当然不用讲,我惊讶的是她所有举动,全个体态,都是那样的有个性,奏着韵律。 ”她的美,并非“浅显的柔和及妍丽”,并非舞蹈班中美体的同学或人体画班中最得意 的模特能比拟。在作者笔下,钟绿这一形象无疑已成为美的化身,达到了美的极至。而 故事的结局却出人意料:钟绿的爱人在结婚的前一星期骤然死去,此后两年多,钟绿竟 死在一条帆船上。主人公悲剧性的结局,看似受偶然的命运支配,而细读文本,你又会 觉得,与其说作者是在叙写一个红颜薄命的故事,毋宁说是表达着自己对人生命运的思 考和生命的感悟:青春是美丽的;美成于自然,归于自然。小说究竟是要写出生命无常 ,还是要让钟绿青春的美的形象定格,让“美”永留在人们心中?林徽因把耐人寻味的 思索留给了读者,也传达着她对现实、人世的认知和理解。
在《吉公》和《文珍》中,林徽因继续任记忆浮沉驰骋,她以童年视角,回溯着“旧 家族中的宅第里面”“吸引我回想的”人物。吉公是外曾祖母抱来的儿子,中年的吉公 ,“是一个不喜欢做对子读经书的落魄者”,所以“在人前时,他便习惯于惭愧,谦卑 ,退让,拘束的神情”。但当回到他所住的跨院的旧楼上边——“我”心目中“浪漫的 去处”时,他会“恢复过来他种种生成的性格”,显露出内心的真率。在“我”和孩子 们的心目中,吉公是个有“科学的兴趣”的人。他自学照相并对“照相职务”是那样的 “兴趣、勤劳和认真”,他所懂得的丰富而具体的知识——从自鸣钟的机轮的动作、世 界地图到油画的外国军队军舰,他“想到上海去看一次火轮船”的憧憬……无不开拓了 “我们”的眼界,给了“我们”新的知识,以至于让“我们不止对他的感情总是那么柔 和,时常且对他发生不少的惊讶和钦佩”。“我”寄居了半年多的葟姊家的丫环文珍 ,是一个约摸17岁年龄的女孩子。在“混乱繁复”的大家庭生活中,“文珍随着喊她的 声音转”,楼上楼下,忙个不停。当7岁的“我”被送到葟姊家暂住,感到“孤单、怯 生、寂寞”时,“我”视文珍为“我所需要的中心,和骆驼在沙漠中望见绿洲一样”。 文珍和蔼亲切地招呼怕生的“我”去吃饭,拉“我”去喝热茶,与“我”面对面坐在树 荫下教“我”拆旧衣,带“我”到东书房去听讲诗……。她以一颗诚挚的心,给了“我 ”“所迫切需要的保护,温暖,和慰安”。作品既叙写着“我”同吉公、文珍的“特殊 的友谊”,也表现着醇厚、善良、美好的人性、人情。与此同时,小说还写出了吉公和 文珍不愿屈从命运的安排、不与命运妥协的精神,以及他们共同的生命态度和生命中发 生的转变。吉公终于舍弃了旧家族恩赐的生活,走出封闭的宅院和旧楼的小小角隅,去 开辟自己新的生活道路了。属于“外江”人家的一位照相的姑娘,给他的没有着落的日 子“骤然地点上希望”。他“忽然突兀地”决定了自己的婚事,毅然在世人眼中“很不 体面地”到外省人家去入赘。家里要把文珍嫁出去,已经说妥了人家。而曾目睹过同伴 不堪少爷凌辱而跳井身亡的文珍,对自己的命运有清醒的认识,她在与“我”的对话中 ,大胆地表白:“丫头小的时候可怜,好容易捱大了,又得遭难!不嫁老在那里磨着, 嫁了不知又该受些什么罪!”文珍终于在中秋节后、快要出嫁以前逃跑了,始终没有寻 着。“我”听说,还是同那住在后院的“革命党”跑的!吉公和文珍,各自以改变自身 命运的追求和行动,谱写着对灵魂自由和生命意志的赞歌,他们并不似废名等作家笔下 “不会骚动”的灵魂。在看似平静和缓的叙事中,正饱蕴着作者对人物与传统生命意识 抗争的赞赏之情。
《绣绣》叙写了13岁的“我”同11岁的绣绣“一把鲜美的友谊”。作者笔下,绣绣依 然是爱和美的化身。她聪明解事、乖巧可爱,“我”在“又佩服又喜悦”地目睹了她同 换碗的贩子一段交易的喜剧后,成为她的好朋友。“我总是暗暗地佩服她的能干,羡慕 她的经验”。而绣绣却生活在“灰黯”的生活环境中:“很阔绰”的父亲已另有家眷住 在别处,绣绣同黄病的母亲——一个“极懦弱无能的女人”一起,寄住在亲戚楼下的小 屋子里,“好像被忘记了的孤寡”。绣绣不只“习惯于母亲的无用”,更同情于有病的 母亲的遭遇和不幸,对母亲的“暴躁”,她报之以“温柔和平”。对远离自己的父亲, 绣绣渴望着父爱,她“私下曾希望着她爹去看她们,每次结果都是出了她孩子打算以外 的不圆满”。而当“惋惜着曾经领略过又失落了的一点点父亲的爱”时,她没有怨言, 甚至“追悔地感到自己的不好”。在互相仇视的父母的交锋和纠纷面前,幼小的绣绣, 只能“抱着破碎的想望,无限的伤心”;“蒂结在绣绣温婉的心底的,对这两人仍是那 不可思议的深爱”!作品在借绣绣展示出童心的真诚,呼唤和赞美人性的爱与美的同时 ,还以动情的笔触,表现了“漂泊不得于父母的寂寞孩子”心灵的无所皈依,写出了绣 绣心灵上遭受的压抑和伤害。特殊的生活氛围,使年幼的绣绣在向“我”忆起往事时, 竟会“伤心地对我诉说着委屈”,“挣扎着心里各种的羞愤和不平”。终于在那年的冬 天,绣绣逝去在一个初落雪的清晨里。作品结尾,在对人物不幸命运结局的诗化言说中 ,倾注了对无辜而弱小生命被摧残的无限同情。而从绣绣和“我”的“迷惑”中,作者 含蓄地表达了对现代人性缺失的忧虑,呼唤着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真诚与友爱,并且对 现存婚姻家庭关系作出了质疑,倾吐着对现实人生的不平。
三
林徽因的小说,不仅以文化观照和表现普通的中国人生,显示了内容的丰富性;而且 ,在艺术上体现了创新的勇气,为我们提供了成熟的小说样式。追求传统与现代的有机 融合,讲求结构的完整和精巧,是林徽因小说创作的鲜明艺术特色。这既体现出京派小 说家开放的眼光和试验小说文体的热情,也显示着作者对艺术美的追求和探索性的实践 。
短篇《窘》成功地将现代主义艺术手法与传统的写实方法相结合,生动地描绘出了主 人公在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窘”态。小说开篇,即置主人公维杉于“四不像的落魄 ”境地。接着,从维杉到少朗家中一次次地“不自在”,在孩子们面前的“不自在—— 不自然”、“觉得窘极了”,到北海游船上一次又一次地“窘”,再到少朗家书房中和 芝接触后的“非常之窘”、“窘到极点了”,主人公“窘”的心理,成为整篇小说结构 形式的主线。它重复迭现,层层推进,细腻地表现出人物的心理。“内心分析”、“感 觉印象”及西方意识流文学表现手段的成功运用,主人公的意识和潜意识的交织,生动 地揭示出人物的生存尴尬。与此同时,对人物窘态的言行举止、外部形态等的白描,以 及用环境气氛的烘托来刻画人物心理等传统艺术手法的运用,又使作品带上了传统文学 的鲜明印记。伴随着主人公的心理流程,作者将不同场景、情节片断自然联缀在一起, 把小说的6个自然部分组织得缜密而有序,使通篇结构和谐而完整。诚如杨义先生所说 ,“它把京派从容自如而内里约束得体的表现风格发展到极致”[7]。
《九十九度中》一改传统小说纵剖式的结构形式,创造了立体的空间结构。它采用了 现代性的拼链式的片断镜头重组的叙事方式,反映的是“人生的横断面”。现代电影、 摄影等艺术手段和技巧的运用,电影语言——蒙太奇式的镜头组接方式,将北平城内一 天中不同阶层的人生片断互相穿插、勾连在一起,不仅摄入了社会上不同阶层的生活景 象,而且记录了不同人物的内心活动、心理情感。类似电影、电视中的一幅幅活动画面 的连续展现,一个个场景和人生片断的互相对照和切换,巧妙的时空转换和过渡技巧, 叙述格局的自然变化,以及“内心独白”的意识流表现手法等等,将环境、气氛和人物 全部有机联系在一起。在看似纷繁、杂乱的小说结构中,隐现着贯穿全篇的主题线索, 显示出结构的统一与完整。而作品中不同的场景引出不同人物的心理情感,又带有中国 传统文学中特有的时空感。难怪李健吾先生会称赞它“没有组织,却有组织;没有条理 ,却有条理;没有故事,却有故事,而且那样多的故事;没有技巧,却处处透露匠心” ,“达到一个甚高的造诣”。[3]
如果说,在追求艺术完美形式和构架的营造上,《窘》和《九十九度中》较多地引进 了世界现代主义文学的经验,并在整体和谐的结构中显示着诗情画意的自然流动;那么 ,《模影零篇》中的作品,则更多地体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学的承续和依恋,可以说是用 传统的艺术传奇手法,与现代的自叙传体形式相整合,创作出的诗化小说。在《模影零 篇》中,作者以第一人称“我”的叙述者身份,追溯着少时的往事和生活感受。钟绿、 吉公、文珍等人物的命运,无不带上了传奇色彩。但小说虽以人物为着笔的起点,甚至 作品题目也以主人公的名字命名,却又突破了以故事或人物为主导建构叙事内容的结构 定式,而用“我”的意绪引领着作品情节的自然展开。作者笔下,昔日的印象,生活的 断片,追怀的情感,仿佛不由自主地自然流淌。正是在看似随意又充满情韵的抒写中, 小说结构形态的“自然”与现实人生的“自然”达到了契合,作者的思想和情感趋向, 通过整个文本完整地传达出来。《模影零篇》中的作品,既同样体现着作者自觉的结构 意识和出色的艺术功力,又表现了京派小说趋向散文化和诗化的特征。
四
作为出身名门、留学西洋,“在双重文化的教养下长大的”[8]林徽因,独特的人生经 历、知识结构和情感体验,又使她的小说和其他京派作家的小说同中有异,显得别开生 面。
和京派作家怀着共同的文学理想,同是赞美“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 人性的人生形式’”[9],同是对普通人平凡生活的体验和写照,林徽因的小说在题材 选择上,既不同于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废名的“鄂东山野”,也不同于芦焚的河南 “果园城”,以及汪曾祺的苏北乡镇。作为道地的城里人,林徽因给读者展示的,不是 “乡村中国”的艺术世界,自在、自足的生存环境,而是带有北京文化氛围的都市风景 。在小说《窘》中,那均衡而庄严对称的四合院建筑,夏日搭着天棚的大院子,院内的 金鱼缸、莲花、石榴,隔墙的枣树、海棠,充溢着白玉兰幽香的书斋,还有北海的牌楼 、白石桥、垂柳……都散发着北方古都特有的味道。而不论是《九十九度中》对胡同里 巷的形形色色人物生存状态的展示,还是《吉公》、《文珍》中从孩子眼里看到的旧式 大家庭的生活剪影,也都体现着鲜明的时代地域特征,无不透露出老北京日常生活中现 实的文化内容。
虽然与其他京派作家一样,在审美世界的建构中,都把“静穆”、“和谐”之境当作 始终的美学追求,在创作中注意到情绪的内敛、理性的节制,但生性直率、热情的林徽 因,在小说创作中却难以做到京派理论家朱光潜所主张的那样,保持“超然物表”的心 理距离;难以如沈从文等京派作家一样,始终保持恬静隐逸的心态和超然尘俗之外的审 美心境。林徽因在以诚实、平静的心态描述现实、回溯人生时,并没有仅仅将情感蕴含 在客观描绘中。她在含蓄蕴藉地抒情时,又时有难以抑制的冲动。于是,我们在林徽因 的小说中,看到了作者在宁静与节制背后的热烈的情感挣扎,看到了作者心情、性情的 不由自主地流露。这又是林徽因小说的独特之处。
《九十九度中》的阿淑受过新思想的影响,而旧式家庭的压力,却“触碎她那一点脆 弱的爱美的希望”,她不得不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带着疑惧出嫁。“五四” 自由恋爱的理论,留给阿淑的,只是一种空想,一种嘲讽。在看似不动声色地对阿淑婚 事和心境的叙述中,人物的心理,作者的议论,自然交织在一起。从中,既表达了作者 对女性解放、婚姻恋爱问题的认识和思考,对现实社会中一部分知识女性“梦醒了却无 路可走”的处境的深挚同情,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林徽因的直率和真诚。《钟绿》中,作 者在得知钟绿逝去的消息后,再难隐藏自己的一腔真情:“那天晚上对着一江清流,茫 茫暮霭,我独立在岸边山坡上,看无数小帆船顺风飘过,忍不住泪下如雨,坐下哭了。 ”《吉公》以童年视角回溯往事、描绘吉公时,同样时时自然变换叙述角度,自然地插 入作者的议论和感慨。在交待了吉公看似完满的结局后,作者从对二三十年前的追忆回 到眼前,由衷地发出了“人事的感慨”:“我希望他这个儿子所生的时代与环境合适于 他的聪明,能给他以发展的机会不再复演他老子的悲剧。”吉公的命运,映现着时代的 面影。在看似冷静地叙写中,作者明确地袒露着自己的心声,给予了那个压抑人才、埋 没人才,窒息生命力的旧时代和社会环境以批判,把思索和启悟留给了读者。正是在这 些传递着作者感情起伏的议论和感慨中,渗透着林徽因作为知识女性和学者的睿智,以 及对时代和社会生存状态理性的思考,使小说自然流露出一定的社会批评性和思想倾向 性。
收稿日期:2003-09-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