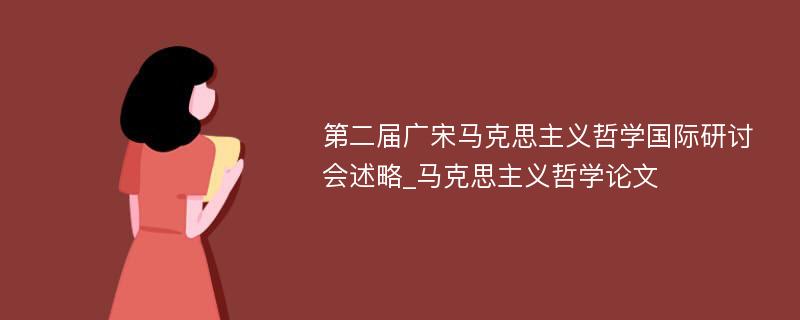
第二届广松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第二届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国际论文,广松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上的第一部科学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批判了黑格尔以后的德国哲学和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共同制定了唯物史观。《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在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为正是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苏联学者梁赞诺夫的主持下,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分别于1924年、1926年用俄文、德文发表了《费尔巴哈》章手稿。以梁赞诺夫的工作为基础,苏联学者阿多拉茨基根据苏联理论界当时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对《费尔巴哈》章手稿进行了新的编辑、删节、整理,并于1932年用德文、1933年用俄文将《德意志意识形态》全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订版第一版(MEGA1)第一部分第5卷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一版第4卷。这一版本流传非常广泛,是后来绝大多数版本的母本和长期以来人们理解、诠释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的最重要的文本依据。1962年,西欧学者巴纳在整理马克思其他遗稿时发现了属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的三页新手稿,其中两页属于《费尔巴哈》章。这成为国际学界批判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反思阿多拉茨基版的是非功过的一个契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也由此进入一个高潮。40多年来,围绕《费尔巴哈》章手稿国际学界提出了多种编排方案,日本学者广松涉1974年出版的新编辑版就是其中之一。为了纪念《德意志意识形态》创作160周年和广松涉逝世10周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南京大学中日文化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哲学系于2005年4月23日至24日在南京联合召开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及其当代价值暨第二届广松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名古屋大学、大东文化大学、早稻田大学、情况出版社等高校与机构的日本学者10余人,与来自中央编译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国内学者60余人出席会议,就《费尔巴哈》章的文献学研究史、广松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及其当代争论、恩格斯在唯物史观创立过程中的作用、《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唯物史观的当代价值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一、《费尔巴哈》章的文献学研究史
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倍倍尔、伯恩斯坦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先后保管过《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相关手稿。恩格斯和伯恩斯坦曾对手稿做过标记和编码。这些手稿中有的早已经散失,有的在发表后底稿被毁,有的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才找到。这给整个《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工作带来了巨大困难,其中《费尔巴哈》章的困难尤其巨大:《一、费尔巴哈》这一部分包括马克思从第1页编到第72页、并用一些笔记加以补充的一篇草稿,以及另外六篇手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中三篇上面加了《一、费尔巴哈》的标题,但没有明确注明它们该如何编排,根据学者后来的研究,另外三篇手稿也应当属于《一、费尔巴哈》。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国际学界先后提出了不下七八种编排方案,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梁赞诺夫版(1926)、阿多拉茨基版(1932)、巴加图利亚版(1965)、广松版(1974)和尚未正式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订版第二版(MEGA2)。
1926年,苏联学者梁赞诺夫在他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一册中首次用原文发表了《费尔巴哈》章,发表时的标题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费尔巴哈(〈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同时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945年原稿附在了正文前面。1938年,郭沫若曾根据德文(同时可能参照了当时已有的几个日译本)将梁版《费尔巴哈》章译出,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名刊行。在编排上,梁版遵循了伯恩施坦的编码顺序,但删除了伯恩施坦误编进去的内容,同时保留了恩格斯写的标题《一、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梁版正文有三个小标题:A.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B.唯物史观中的经济、社会、个人及其历史;C.国家与法同所有制的关系。第一、三个小标题是手稿中原来就有的,第二个则是编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后加的。除了将按照恩格斯编码的第3、4张手稿(即1995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8页第3段至第71页第3段)放到最后之外,梁版的编排基本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结构和排序以及马克思编注的页码。梁版力图如实反映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原貌,并在这个方面做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尝试,不过由于历史的原因,它在手稿的完整性以及文字的辨识等方面都还存在相当多的问题,但它却为以后的文献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以梁版的研究为基础,1932年,MEGA1第一部分第5卷发表了由苏联学者阿多拉茨基主持编辑整理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全文。这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个完整的、历史考证性的版本,也是1933、1955年俄文第一、二版等诸多影响巨大的版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三卷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就是据此移译的)的编辑基础。与梁版相比,阿版《费尔巴哈》章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阿版依据当时苏联学界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按照“意识/意识形态的基础/共产主义”这种强制结构将手稿划分为了三个部分,并根据编者自己的理解和需要增加了“B.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和“3.自然产生的和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与所有制形式”这两个标题;第二,为了逻辑完整性,阿版对手稿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改编”,将大部分标有马克思编注的页码的手稿主体部分(即1995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74-135页的[Ⅰ]、[Ⅲ]、[Ⅳ]部分和“国家和法同所有制的关系”)分割为几十个片段,除了将个别片段插入马克思恩格斯直到最后都还在修改的那部分手稿(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5-16页的“序言”以及1995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2-74页的[Ⅰ]部分)之外,对剩下来的段落进行了剪刀加糨糊式的拼贴,以至读者根本无法看出手稿的原貌;第三,为了使拼贴更加“自然”,阿版甚至在手稿个别地方擅自添加了连接语句,例如阿版将马克思编注的第28页和第8页中论费尔巴哈的段落拼贴在了一起,由于当时第29页散失了,因此第28页是以“如果他们的‘存在’”结束,为了使意义能够连贯阿版自行添加了“同他们的……相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页),而在第29页1962年重新被发现后,人们看到,手稿的原话是“同他们的‘本质’完全不符合,那么”(1995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97页第15行)。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范围的传播过程中,阿版《费尔巴哈》章曾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但在后来的深入研究过程中,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了阿版与斯大林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因而要求恢复马克思恩格斯手稿原貌的呼声也就越来越高。1962年三页新手稿在西方的发现和发表是一个转折点,它迫使苏联理论界正视阿版《费尔巴哈》章存在的问题,采取行动挽回不良影响。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在《哲学问题》杂志1965年第10期和第11期上重新发表了由巴加图利亚准备、勃鲁什林斯基编辑的新版《费尔巴哈》章,并于次年出版了单行本。由于巴版是对梁版编辑思路的恢复和完善,因此,不论是在结构上还是内容上它与阿版都存在明显的不同:第一,巴版按照手稿的结构调整了手稿的编排顺序,按照内容分为27段并按照自己的理解为其中的25段拟定了小标题(参见《费尔巴哈》第103-104页),并将手稿按照罗马数字分为4个部分(具体参见《费尔巴哈》正文);第二,巴版首次将1962年新发现的两页手稿按照其本来的页码编入《费尔巴哈》章(参见《费尔巴哈》第18-19页、第42-43页);第三,巴版恢复了手稿上的重要注释和说明,增加了相当数量的文献学说明,并保留了马克思编注的页码,但没有保留恩格斯编写的序号。巴版受到当时苏东理论界的高度重视,1965年的新德文版和1972年MEGA2的《费尔巴哈》章的试编本都基本承袭了它的思路。1988年,我国出版的《费尔巴哈》章的新单行本的原型就是巴版,只不过我们像新德文版一样将巴版增加的标题都放到附录中去了。经过修订后,新单行本的主体后被收录到1995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巴版的出现既满足了人们对新版《费尔巴哈》章的渴求,同时激发出了人们更高的要求,因为人们认为在文献学方面应当能够做得更好。在这个方面,比较著名的努力就是1974年的广松版(详见第二部分)。
尽管存在诸多差别甚至根本差异,但上述4个版本在一点上都是共同的,即认为现有手稿存在内容逻辑关联,它们应当按照一篇著作的形式加以系统编排。这种长期支配人们观念的系统编排思路在近年受到了MEGA2第一部分第5卷的分篇编排思路的强有力挑战。中央编译局负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中《德意志意识形态》翻译、编辑、出版工作的柴方国研究员在研讨会上对此问题进行了专题发言。根据柴方国研究员的介绍,早在1972年MEGA2的《费尔巴哈》章的试编本中,负责这一工作的民主德国学者英格·陶伯特就提出了各个手稿乃是七个“相当独立的部分”的说法,并将这七个部分依次排列,各部分之间用空行分开,编写异文表,除了手稿中原有的标题以外,不另设任何序号和标题,目的在于尽可能显示手稿的片段特征,包括边注和修改等,使人了解当时的写作进展情况。1997年,陶伯特等学者系统提出了分篇编排的编辑框架,并在2003年出版了一个预编本。这个预编本把流传下来的有关《费尔巴哈》章手稿作为独立成篇的文稿收录进来,并编成独立成篇的著作,其突出特点就是不再人为地编造一个体系,而是维持手稿或刊印稿的原貌。在详细比较了两种编排方式的主要异同点之后,柴方国研究员指出:两种编排方式体现了不同的编辑原则,适用于不同的研究需要,因此尽管分篇编排思路是对传统系统编排思路的一种否定,但它却显著拓展了文本解释的空间。
二、广松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及其当代争论
广松涉(1933-1994年)是日本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广松涉就开始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并对梁版和阿版存在的问题有所意识。在对梁版和阿版进行深入细致的对勘基础上,广松完成了一份探讨两者的异同及其编辑问题的报告,后以《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中存在的问题》为题发表在1965年《唯物论研究》春季号上,引起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广泛关注。由于广松对苏东理论界后来陆续出现的几个新版本都怀有不满,最终形成了一个按照自己确立的编辑方案编辑出版一个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念头,经过多年努力,这个想法终于在1974年得以实现。为了让国内学界能够真实地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的水平,在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的主持下,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了广松版的中译本。通过这个中译本人们不难看出,这的确是一个与以前的诸多版本有着质的差别的全新版本。用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广松版的文库版(岩波书店2000年版)的补译者小林昌人的话说,广松版是“划时代的”。小林着重从版式特点这个角度评介了广松版的三大特点。第一,手稿中的增补和删改情况得到了直观的体现。为了与经过增补或删除后的最终文句相区别,广松版用标有删除记号的小字体将被删除的字句恢复至原处,用斜体(日译文和中译文用波浪线)印刷写在行间以及栏外(正文以外的空白处)添加的字句,从而使手稿的修改、增删情况得到非常直观的体现。第二,用不同字体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笔迹加以醒目的区别。广松版用罗马字(日译文用明朝体、中译文用宋体)印刷恩格斯书写的部分,用粗体(日译文用黑体、中译文用加粗楷体)显示马克思书写的部分,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笔迹区别一目了然。第三,用双页联排印刷的方式使手稿中写在空栏外的增补文字、注释、笔记得到直观体现。手稿经对折页面分为左右两栏,左栏用以写作正文,右栏用来增补、做笔记等。以往的版本多用文字说明的方式来体现右栏中的内容,而广松版则采取双页联排印刷的方式使左右栏的内容得到直观的对照显示(以中译文为例,双数页码对应的是手稿的左栏,而随后的奇数页码对应的则是相应的右栏中的内容)。
广松版出版之后,在日本学界产生了热烈反响,有力地推动了日本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此后,日本还先后出现了三种新版本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服部文南的《新译〈德意志意识形态〉》(1996)、涩谷正的《草稿完全复原版〈德意志意识形态〉》(1998)和前面提到的小林昌人版(2000)。总的看来,广松版得到了日本学界普遍肯定和尊重,但批评的声音也始终不绝于耳。清华大学哲学系的韩立新副教授总结、归纳了日本学界对广松版编辑方针的不同意见,大致有三点。第一,批评广松版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整体的创作顺序考虑不足。按照巴加图利亚的研究,《费尔巴哈》章的写作是与《德意识意识形态》第二、三卷的写作交叉进行的,因此应当联系第二、三卷来定位、理解《费尔巴哈》的文本。批评者认为广松版对此问题显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第二,批评者对广松版的编排顺序提出了许多质疑,例如,人们认为广松版用恩格斯编码的第3、4张手稿来填充马克思编注的第36-39页手稿是不正确的(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80-89页),因为前者讨论的是所有制形式的历史变化,而后面讨论的则是分工的历史发展。第三,部分学者批评广松涉实际并没有看到手稿的原稿,而只是根据照片版和以往各种版本提供的信息来编辑的,其中不少信息是不正确乃至错误的。
就像在日本学界一样,广松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得到了与会中方学者的高度评价。广松版中译本的审定者、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比较系统地评价了广松版以及广松涉的文献学研究对中国学界的启示与价值:第一,广松版是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研究领域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它第一次让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了解到文献学在“回到马克思”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廓清了一些存在于文献学文本学研究中的理论迷障,为我们进一步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新基础;第二,它让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首次直观地看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创作过程,使我们对唯物史观的创立过程以及每一个具体原理的提出、确定和修订过程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并直接证伪了西方“马克思学”炮制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第三,广松涉严肃、认真、客观的研究态度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基础研究具有直接的示范作用。北京大学黄楠森教授、中央编译局王学东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奔教授等与会学者都对张一兵教授的观点表示了赞同。
在赞同张一兵教授的上述观点、高度评价广松版所取得的重要成就的同时,复旦大学哲学系吴晓明教授对广松涉的文献学研究的前理解定向中的形而上学残余提出了批评。吴晓明教授以充分的哲学史证据证明,广松涉在唯物史观形成时期马克思恩格斯所使用的唯物主义术语、科学逻辑和共产主义观点的理解是不准确的,他的这些不准确的理解直接进入他的前理解定向,在一些根本点上影响、制约了他对一些基本问题的理解和判断。在这个问题上,北京大学陈志尚教授、南京大学侯惠勤教授与吴晓明教授产生了共鸣。陈志尚教授指出,在我们重视文献学研究、尽可能完整地复原经典文献的同时,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研究目的是完整准确地把握《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科学观点,因此,不能孤立地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个文本,而必须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著作进行前后关联的统摄理解和研究。侯惠勤教授认为文献学研究存在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研究的立场和方法问题。立场和方法制约着我们对于材料的取舍和观点的形成,这导致文献学研究必然会有自身的盲区或局限性,此时,我们就必须依靠实践和历史,透过词句去把握文本的精神实质。侯惠勤教授还特别以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概念的相互冲突的三种理解为例说明了这个问题。
三、恩格斯在唯物史观创立过程中的作用
根据广松版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费尔巴哈》章手稿基本上出自恩格斯的手笔,出自马克思的手笔的只有修正、插入以及若干栏外的补充。在对恩格斯书写的文章和马克思修正、补充的文章比较之后,广松涉得出了一个非常惊人的结论:马克思当时的思想发展明显落后于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出自恩格斯的独创性见解!换言之,在唯物史观创立过程中,拉第一小提琴的不是人们原先认为的马克思,而是恩格斯!为此,广松涉曾于1966年写有专文阐述这一点(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附录二)。广松涉的这一观点引起了与会中方学者的一致反对。很多学者从各自的角度驳斥了广松涉的观点,对恩格斯在唯物史观创立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进行了深入阐发。
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对广松涉这一观点的反对立场。张一兵教授指出,广松涉仅仅凭借《费尔巴哈》章手稿的笔迹就断定恩格斯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创立者,是非常武断的。笔迹问题所能证明的只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理论合作的密切性和深度,除此之外不能说明其他任何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在梁赞诺夫及之后看过手稿的那么多学者都没有得出类似结论的根本原因。如果我们不仅仅局限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个文本,而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此前各自思想发展的完整历程和内在逻辑去审视恩格斯在唯物史观创立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就会看到:在1843、1844年间,恩格斯的确曾在思想发展上处于当时整个青年黑格尔派的最前沿,在1845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他甚至已经触摸到了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但唯物史观却毫无疑问是由马克思主导性地创立的。中央编译局王学东研究员指出,恩格斯是马克思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和长期合作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创始人。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仅就《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部著作来说,虽然主要作者是马克思,但恩格斯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过程中,恩格斯的作用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推动马克思思想前进,例如在1844年11月19日致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比较系统地评价了费尔巴哈,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恩格斯提供的这些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述;二、具体承担合作著作的写作任务。由于历史的原因,恩格斯思想中的亮点往往被马克思的光芒所遮蔽,所以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贡献确实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挖掘。但是,广松涉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这同样是不正确的。
复旦大学孙承叔教授追溯了《费尔巴哈》章的“小束手稿”(广松涉术语,即国内学界一般所说的第四、五手稿)的形成过程,强调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作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但就唯物史观的创立而言,马克思起了更加主要的作用,是最高意义的“第一小提琴手”。苏州大学王金福教授针对西方“马克思学”以及广松涉的观点,全面探讨了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关系,重申恩格斯与马克思不是对立而是统一的、不是“一体”而是存在个性化差异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过程中,马克思是“第一小提琴手”。北京大学杨学功副教授比较系统地评价了恩格斯晚年对唯物史观的解释,认为共同“创立”唯物史观和系统“阐释”唯物史观是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形成与发展的两大贡献。
四、《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唯物史观的当代价值
除了上述问题外,与会学者还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唯物史观的当代价值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些具体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中央编译局王学东研究员指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当代价值是一个常讲常新、近来在研究全球化问题的热潮中又再次引起人们热切关注的话题。许多学者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世界历史”的论述,实际上是对早期经济全球化的理论诠释和回应,体现了某种“全球化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思想是源于他们创立的新历史观——唯物史观。这种新历史观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基本矛盾,揭示了全球化发展的历史大趋势,指出资本主义在向全球扩张的同时,必将为自身的灭亡和共产主义新社会的产生创造日益充分的条件。所以,讨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当代价值,关系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正确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问题;关系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新境界的问题。
作为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当代价值的两个个案,名古屋大学西原和久教授和中央编译局鲁路副译审分别考察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广松涉后期社会哲学、现代西方社会学及知识社会学的影响与限度。
针对国内学界现实存在的力图彻底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理论倾向,北京大学黄楠森教授指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苏联传来的,其具体形态一直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此提出了异议,特别是怀疑甚至否定辩证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部分的地位。这样,是否还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或者说是否要以实践唯物主义来取代辩证唯物主义,近年来成为哲学界的最主要的争论热点。在这场争论中,如何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思想,成为关键性问题。具体说,有三个基本问题与《德意志意识形态》有关: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唯物主义是否有继承关系?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是否包含思维方式从本体论思维方式向实践论思维方式的转变?三是世界观与历史观是否有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对于第一个问题,黄楠森教授指出,在一般情况下人们是不会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唯物主义之间存在着批判与继承的关系,但一谈到一些具体问题时往往就抓住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有的人在谈到直观唯物主义或唯物主义的直观性、自然本体论或物质本体论时,就认为马克思完全否定了直观唯物主义、物质本体论,而事实情况是,马克思丝毫没有完全丢掉直观唯物主义、物质本体论的意思,而是要在继承它们的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前进一步。在谈到第二个问题的时候,黄楠森教授特别批评了那种将本体论思维方式与实践论思维方式对立起来、认为马克思以实践论思维方式取代了本体论思维方式的观点,认为唯物主义本体论思维方式是任何正常人的思维方式,也是科学的思维方式,不管是近代科学还是现代科学都离不开唯物主义本体论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自然不能例外。关于第三个问题,黄楠森教授重申了自己的一贯主张,强调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之所以能够将二者并列起来,是因为唯物史观是世界观与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中介,在哲学各部门中特别重要。北京大学陈志尚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奔教授对黄楠森教授的观点表示支持,认为必须坚持唯物主义本体论,正确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实践范畴。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分工与异化理论是与会学者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大东文化大学吉田宪夫教授介绍并再次确认了广松涉的异化超越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已经扬弃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的异化(versachlichung)理论,取而代之的是已经基本成型的物象化(Versachlichung)论的逻辑。物象化是广松涉创造的一个专门术语,它所要表达的是《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所有事物都再产生出了新的属性,并使它取代事物的自然属性成为事物自身,即资本使自己具体化在某物之中、成为某物,换言之,资本这个抽象的关系整体使自身形象化了、可见了,而生活在资本主义体制之中的我们则把这种物象化指认为了事物本身。在广松涉看来,这种物象化状态实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本质上不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存在的一种样态,为了克服它,就必须改造它赖以形成的关系总体,这也正是革命的出发点和主要任务。中国社会科学院魏小萍研究员研究相同的主题,但她反对广松涉的异化超越论,认为异化理论并没有被超越而是通过《德意识意识形态》中的分工理论得到了继续,并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得到发展。尽管清华大学韩立新副教授也不认同异化超越论,但他却指出了一个相当关键的问题,即物象化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物化,物象化与物化的分野在广松涉那里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此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物化理论来驳斥广松涉的异化超越论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南开大学王南湜教授也探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分工的异化问题,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从分工出发,唯物主义地说明了异化或私有制的起源问题,因而分工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中有着非常寻常的意义。但分工理论中隐含着两条使人的生存状况异化的理论线索,一是社会关系层面上的,另一则是生产的技术方式层面上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两条线索尽管没有得到充分展开,却为马克思以后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基础,他由此对这两条线索进行深入细致的发掘。
历史唯物主义的定义问题是与会学者比较关注的另外一个问题。苏州大学杨思基教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物”不是抽象的物质一般,而是由自然的且历史地形成的个人之间的关系所中介和构成的社会存在物。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部科学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不仅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研究方法的伟大变革,同时也实现了哲学关于“物”概念的全新解释。南开大学夏莹博士在讨论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实质后认为,“历史”与“唯物”有同义反复的嫌疑,她因此建议用“新唯物主义”来替代“历史唯物主义”。
标签: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德意志意识形态论文; 恩格斯论文; 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论文; 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读书论文; 费尔巴哈论文; 资本论论文; 本体论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