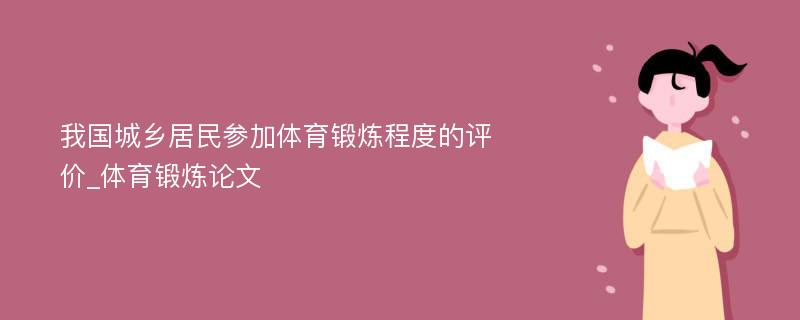
中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程度评价的辨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体育锻炼论文,城乡居民论文,程度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4.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7X(2009)05-0024-08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规定:“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国家提倡公民参加社会体育活动,增进身心健康。”由此可见,群众体育是体育事业的基础,群众体育事业的发展规模和水平是国家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志。试想一个国家的民众若能够积极投身到健身行列中,这不仅预示着国家群体事业的繁荣,而且鼓励民众积极地、经常性地参加体育锻炼,还将为增强国民体质,提高民众的健康素质奠定扎实的基础。
众所周知,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类,需要承受来自工作、生活和家庭等各方面的压力,其生活方式也将伴随社会发展和价值观的改变而变化。起源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在促使工业化城市形成的同时,人类的劳作方式也由手工劳动逐渐转变为机械化生产。以后,伴随电子计算机、生物科学和信息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革命的到来,进一步促使社会劳作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坐位工作时间的延长,导致人类体力劳动的付出越来越少;竞争的日趋激烈和工作节奏的加快,促使人类承受的各类压力越来越大,精神愈来愈紧张。现代化生产方式的改变最终导致了人类在现代社会中独立性增强,个体化程度提高,人类之间的交往减少,人际关系淡漠等。所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似一把“双刃剑”,在给人类生活带来舒适和便利的同时,随之带给人类的是自由活动空间的缩小,体力劳动减少,以及高脂、高蛋白质饮食泛滥等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是国家综合实力不断提升的30年,也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最快、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从1978年到2007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元增加到13 786元,实际增长6.5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34元增加到4 140元,实际增长6.3倍;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 400多万。人民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追求时尚、健康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人们余暇时间内的重要选择。但是,众多的研究证实,国民生活舒适度的提高与体力活动和体育锻炼严重不足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威胁当前国民“健康素质”的重要因素之一。
由此可见,在这样的形势下,如何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级阶段国情出发,在坚持政府对人民体质和健康负总责的基础上,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极大地提升国民参加体育锻炼的积极性,是普遍增强全民族健康素质的关键。实践证明,我国群众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来源于科学地制定群体发展的规划和政策,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来自于科学的调查数据。显然,如何科学、有效地了解现阶段我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行为,尽快确立评价城乡居民体育锻炼参与程度的指标和标准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理论问题。
1 我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现状
自1995年《全民健身计划纲要》颁布以来,国家体育总局为了解不同时期我国群众体育发展状况,先后于1996年、2001年和2007年组织了3次全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1996年的调查工作使国家体育总局在了解我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活动、群众体育活动点、各类体育场(馆)以及群体工作现状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一套群众体育概念体系和群众体育发展程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其中,以“体育人口”理论的提出和建立相应的评价标准为其代表性成果,并首次公布了1996年我国16周岁以上城乡居民中“体育人口”为15.5%(不含在校学生)。随后,国家体育总局提出了“要努力增长体育锻炼人口”等的工作思路。2001年,国家体育总局在获取1997-2001年间我国群众体育发展状况基本数据的基础上,对我国群众体育现状进行了纵向比较研究,发现城乡居民参与体育锻炼的意识在逐步提高,尤其是“体育人口”人数比1997年略有提高,达到18.3%(不含在校学生),比1996年增长了2.8%,并由此得出,我国体育人口增长速度高于人口出生率的结果。但这两次调查都局限在全国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内的以城市居民为主体的调查结果。
2007年是我国筹办北京奥运会的关键年,在“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主旋律的引导下,国家体育总局开展了第3次“全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本次调查与前2次调查有一个明显的差别,就是调查范围首次在31个省、自治区的84个城市和24个直辖市所属区县内进行。在采用与1997年和2001年相同评价标准对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程度进行评价时,发现2007年全国16周岁以上城乡居民(不含在校学生)中,“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以下简称“经常锻炼”)的人数比例占“全国16周岁及以上总人口的8.3%”。
当然,第3次群体调查中的“经常锻炼”人数比例,不能简单与前两次调查结果进行比较,但从上述3次全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结果中不难发现,在评估我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程度信息时,先后采用了“体育人口”和“经常锻炼”两种不同的表述方式。
2 评价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程度指标的确定
评价指标是建立科学评价体系的核心。一般是由综合反映社会现象某一个方面内容的、能够采用绝对数、相对数或平均数表示的因素构成,是社会学、医学、生物学、经济学等进行数据统计的基本术语。《体育测量与评价》要求,评价指标要围绕评价目标来选择,要依据目标的本质,将其分解为一些具体的、可量化和能操作的因素。实践中,通过对这些构成因素的测量和评价来反映目标的本质属性或整体特征。
2.1 体育、体力活动与体育锻炼
爱因斯坦指出:“如果没有界定范畴和一般概念,思考就像在真空中呼吸,是不能的”。人类在社会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和知识正是由某些范畴和一般概念框架所建构的。所以,建立概念既是建构知识和理论体系的前提,又是进行理论思辨的逻辑起点。
2.1.1 体育
据考证,中文的“体育”一词最早于1897年由日本引进中国,并见于文字。但日文中的“体育”却来源于对西语名词的翻译。早期相当于体育的原形词(英语)有:1)Physical education;2)Physical culture;3)Physical training/Exercise。换句话说,“体育”最初的含义是“以运动和卫生为手段,以身体健康为目的的教育”,以后体育的内涵扩展为包含“通过适当、合理的运动实践”、“促进身体健全发展”、“培养运动能力和健康、安全的生活态度”等3个不可或缺的要素。
“体育”一词进入中国后,其内涵和外延也随社会意识形态的改变而发生着变化。早期对体育本质最著名的论述来源于1917年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体育者,养生之道也”,“体育者,人类自养生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者”。强调体育乃一种教育手段。建国以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作为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方针,扩展了对体育本质的认识。1971年出版的《新华词典》指出:“体育指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教育”,强调了体育是社会文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是增强体质,促进身体健康的一种手段。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体育事业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体育”一词的内涵和外延也随之得到了发展。《中国大百科全书·体育》指出:“在中国,体育的广义含义与体育运动相同。它包括身体教育(即狭义的体育)、竞技运动、身体锻炼三个方面”;“身体锻炼是指以健身、医疗卫生、娱乐休息为目的的身体活动”。《体育概论》指出:“体育(广义的,亦称体育运动)是指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以增强人的体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社会文化生活和促进精神文明为目的的一种有意识、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包括体育(狭义)、竞技运动、身体锻炼和身体娱乐”。这一阶段体育内涵的扩展,强调了体育的“三分论”或“四分论”,其中,“身体锻炼”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明确了身体锻炼是增强体质,促进健康的重要手段。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体育的内涵和外延继续扩大,1995年8月29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将体育区分为社会体育、学校体育和竞技体育。一些学者还将体育划分为学校体育、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娱乐体育、休闲体育等。以后,按照参加体育的群体和活动区域范围,将我国群众体育事业划分为学校体育、职工体育、农民体育、社区体育、民族体育、老年人体育和残疾人体育等。由此可见,中国体育的内涵强调其作为文化、教育的组成部分,随社会发展不断扩展其功能;“人”作为实施体育行为的主体,积极参加身体锻炼是促使人类强身健体的重要手段。即体育是人类一种有意识的身体活动,它通过专门设计的身体活动来达到增强体质,提高竞技水平,丰富社会文化生活的目的。
2.1.2 体力活动
正如前述,随着科技发展,工业自动化生产和人们生活设施舒适程度的提高,人们的体力活动(physical activity)呈现明显下降的趋势。根据美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1995年公布的调查报告,美国有250,000的人因为“久坐”(sedentary lifestyle)造成体质明显下降;美国人中有30.5%人“不参加运动”(physically inactivity),28.5%的人参加“不规律运动”(irregularly activity),参加“规律运动,达不到强度要求”(regular activity,not intensive)的人为31.9%,而参加“规律运动,达到强度要求”的人仅占9.1%。“体力活动缺乏”(lack of physical activity)被认定是心脏病、高血压、高脂血症、糖尿病等的独立危险因素。2002年WHO的报告指出:体力活动缺乏被认为是导致发达国家人口死亡10大原因之一,每年大约有190万人死于体力活动缺乏。当然。经常性参加“规律的体力活动”有助于预防慢性疾病(如冠心病、Ⅱ型糖尿病、中风、结肠癌等)和早衰现象的发生,降低发病率,维持高水平的生活质量。由此可见,体力活动成为促进健康,提升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之一。
关于体力活动的内涵和外延,观点较多,得到普遍认可的是Casperson[44]等学者的观点。该学者认为,体力活动是指“任何由骨骼肌收缩引起的导致能量消耗的身体活动”(any bodily movement produced by skeletal muscles that results in energy expenditure)。体力活动具有3个主要特征:1)经由骨骼肌收缩导致的任何身体活动;2)引起能量由低到高消耗的连续状态;3)与体质水平呈正相关[34]。WHO从体力活动的时间和空间特征,将其划分为职业中的体力活动、交通中的体力活动、休闲时间的体力活动(含体育锻炼)及家务劳动等4个方面,其中,休闲时间内的体力活动成为目前的研究热点。
1993年出版的《社会百科词典》中,将“休闲”定义为“人们生活中除了工作时间、工作往返时间、家务劳动时间、抚养子女时间、满足生理需要时间以外,剩余的可供个人自由支配的时间”。对于个体和社会而言,休闲时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休闲时间内的活动内容大致区分为5类,即体育活动、业余学习活动、娱乐活动、旅游和公益活动等。除了业余学习以外,其余4类活动均伴随有大量的体力活动。由此可见,体力活动的内涵远远超过传统意义的体育锻炼,其增强体质,促进健康的功效已经成为共识。
2.1.3 体育锻炼
体育锻炼(physical exercise)是实现我国体育目的任务的重要途径。体育锻炼是以发展身体增进健康,增强体质,调节精神和丰富文化生活为目的身体活动。1984年出版的《体育词典》指出:“体育锻炼是指运用各种体育手段,并结合自然力来锻炼身体,以增进健康,增强体质为目的地从事体育活动过程”。在中国,体育锻炼/身体锻炼已经作为体育“三分论”的构成要素,已经成为人们以健身为目的的身体活动。
结合国外的研究现状看,体育锻炼有别于体力活动。Casperson等学者认为,“exercise”从属于“physical activity”,是“有最终和阶段目标,有计划,有组织,重复的,以保持和/或提高体适能(physical fitness)为目的的体力活动”[44]。Bouchard等学者认为:“体育锻炼是休闲时间内的身体活动”。1988出版《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将“exercise”解释为“Activity that requires physical or mental exertion,especially when performed to develop or maintain fitness”(锻炼身体:为发展或保持体适能而采取的运用心智或体力的活动)。由此可见,体育锻炼属于体力活动的下位概念,包括体力活动的两个要素,即“由骨骼肌收缩导致的身体活动”和“能量消耗”,但是,体育锻炼却是以保持和提高体质水平为目的,更有计划的、有内容安排的和重复从事的体力活动;是体力活动中最主要、最积极的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中国体育经过60年的发展,日益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中并发挥着重要影响。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02年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意见》中明确提出:“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增强人民体质是体育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利国利民、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体育工作一定要把提高全民族的身体素质摆在突出位置”。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不仅向世人展示了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成效,而且,“后奥运时代”推出的“全民健身日”更是清晰的显示了,中国政府在建设“体育强国”,实现体育事业的新发展、新跨越的征程上,将大力推进“体育生活化”进程,进一步提高全体人民的体育意识和健康水平,最大程度地鼓励和动员更多的人参加体育健身活动,让参与健身成为人民群众一种自觉的行动和生活追求,作为今后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目标。所以,体育锻炼作为人们主动改造和完善自身状况的一种有意识的活动,将在增强体质、促进身心健康,提高和保持机体的机能水平,延年益寿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但是,还需要清醒的认识到,在大力发展群众体育过程中,还存在“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较少,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的问题。所以,重新审视我国城乡居民体育锻炼行为特征以及确定评价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程度的指标和指标对构建我国群众体育研究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2 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程度评价指标
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或比例,经常性或偶然性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或比例,“有规律”(regular)或“无规律”(irregular)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或比例,体育人口,体育锻炼人口(physical exercise population)以及体育运动人口(sports population)等常被世界各国作为反映国民参加体育锻炼程度或水平(或称为“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程度”)的评价指标。其中,“体育人口”(中国)或“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使用率较高,尤其是在中国“体育人口”已经作为反映群众体育活动开展情况或群众体育普及程度的指标。
2.2.1 体育人口
“体育人口”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最早是由日本体育社会学家竹之下休藏和菅原礼提出,他们认为体育人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体育人口是指以任何形式参加运动的人口的总称,并且也包括新闻、无线电、电视等间接地将运动作为视听的人。狭义的体育人口是指直接参与运动的人数。以后前苏联学者也曾经提出过此概念,并对前苏联体育人口总数进行分类统计和比较研究。但有意思的是,欧美体育社会学家们并不认可这一理念,而更多的采用与体育人口接近的概念表述大众参加体育锻炼(exercise)或体力活动(Physical activity)的状况,如体育锻炼参与人数、参与体力活动人数以及经常(或规律)参加体育锻炼(regular exercise)人数等。
中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逐渐“引进”体育人口这一概念,并逐渐出现在国内各类报刊和学术杂志中,学者们从体育人口的概念、分类、特征、结构、数量和分布等方面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探讨,尤其是在1997年和2001年的两次《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中,采用“体育人口”作为评价我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程度的指标,使这一概念在国内得以广泛流传。但是,国内学者对体育人口的认识差异较大,不同学者观点各异。
20世纪80~90年代,国内学者更多从体育人口的概念和本质属性出发进行研究。高俊刚(1987)提出“广义体育人口”和“狭义体育人口”的概念,认为前者是指从事体育事业的工作人员和有目的地经常参加身体锻炼的群众及体育运动人员;后者则是有目的地从事一定频度、量和强度的体育锻炼,并保证在锻炼周期内锻炼时间具有科学的平衡时数的身体锻炼者和体育运动者。刘德佩(1992)认为,体育人口是体育社会学研究使用的一个概念,借用这样一个概念可宏观来描述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体育态势和体育发展水平,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与体育存有某种相亲关系的人群称为体育人口”。毛秀珠(1995)认为,衡量体育人口要从参加体育活动目的出发,所谓目的就是为增强身体素质、为健康而参加体育活动。为此,将体育人口界定为“是对有目的性的,经常用一定时间,达到一定量度的参加体育活动的人的称谓”。卢元镇(1996)认为,体育人口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体育指标,它反映了人们对体育的参与程度和亲和程度,体育人口是指经常从事身体锻炼、身体娱乐,进行专项训练,以及其他与体育事业有关的人在总人口中的数量和比重。张洪潭(1999)提出了“全时体育人口”与“半时体育人口”的概念。他指出“全时体育人口”是指惠得社会闲暇全力支撑的专业运动员,“半时体育人口”则是指完全是在个人闲暇时间进行体育锻炼的普通市民。仇军(1999)认为,体育人口应以广义体育为依据,涵盖群众体育、学校体育和竞技运动三个方面。体育人口是指生活在一定时间、一定区域,以增进身心健康或提高运动成绩为目标,以身体活动为共同标志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群体。
进入21世纪以后,学者对体育人口的研究转向为对其内涵和外延的扩展。徐忠(2001)把那些介于体育人口与非体育人口之间的人口称为“边缘性体育人口”,区分为积极边缘体育人口(对体育活动有很高的热情,能亲自参加体育活动但不能经常保持)和消极边缘体育人口(参加体育活动但不追求量和强度)。2001年《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报告》也提出“准体育人口”概念,指出准体育人口是介于体育人口和非体育人口之间,主要参加体育活动但没有达到体育人口标准的人群(称为准体育人口的参与层面)和没有参加体育活动,但有强烈意向去参加体育活动的群体(称为准体育人口的意向参与层面)。仇军(2002)以为,体育人口概念不仅是一个文本性定义,还是一个操作定义,体育人口的操作定义本质上就是体育人口的判定标准问题。曹坚(2003)提出了“消极体育人口”和“积极体育人口”的观点,认为消极体育人口是指那些自学校一毕业就不再从事体育锻炼,当年老体衰身体有疾,吃药打针医治无效或效果不大的情况下才又开始体育锻炼者;而从学校到工作岗位直至离退休都坚持体育锻炼者则应称为积极体育人口。张新萍(2004)对张洪潭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张洪潭的观点是一种“惟竞技运动论观点”,是错误的,混淆了体育人口和国民体质状况。强调如果将体育人口定义为通过体育锻炼来提高或保持体能水平的社会成员,那将使体育人口概念狭隘化,并将一个重过程、重参与的指标变成一个重结果、重目的的指标。张宁(2005)认为,体育人口是指经常从事体育锻炼、身体娱乐、接受体育教育、参加运动训练和竞赛,具有统计学意义的一个社会群体,体育人口可以区分为城市体育人口、农村体育人口、在校体育人口和社会体育人口等。肖焕禹(2005)再次提出,广义体育人口是指在总人口中以身心健康、休闲娱乐和以追求提高运动成绩为目的,直接参加身体活动和观赏、关心体育的一种社会群体;狭义体育人口是指以身心健康、休闲娱乐和以追求运动成绩为目的,直接参加运动和体育活动的社会群体。
由此可见,从“体育人口”在理论界的出现,到已经发表的数十篇文章中,甚至于在《体育百科全书》和《体育科学词典》的条目中,不难看出,“体育人口”似乎已经成为一项体育社会学统计指标,用于反映全国民众参加体育锻炼的程度或水平,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体育人口还曾被部分群体部门接受,出现在部分“工作要点”、“发展目标”、“发展规划”等文件中,部分地区还将“提升体育人口率”作为群体工作的重点。不过,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经典体育人口概念,到21世纪初期体育人口理论的演变和内涵的延伸,都可以清晰的看到,体育社会学界本身对“体育人口”的认识至今还停留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层面上,学者们还致力于对体育人口理论的“质疑”、“思考”及“评述”等。所以,将体育人口作为评价我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程度的指标,以及作为衡量群体事业发展水平或作为奋斗目标的指标之一,显然还有待于商榷。
2.2.2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
正如前述,中国的“体育”内涵丰富,是一个多义词。既包含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和社会体育,又具有教育(education)、训练(training)、文化(culture)、锻炼(exercise)、游戏(game)等属性。中国群众体育在60年的发展过程中,始终“面向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坚持业余自愿、因地制宜、科学文明的原则,促进健身活动的经常化、社会化、科学化和多样化,创造出许多群众喜闻乐见、灵活多样的内容和形式”[22]。“全民健身工程”、“晨晚练点”、“全民健身活动基地”、“五个亿万人群”健身活动等都是我国群众体育自推行“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所以,采用一个内涵和外延仍然争议较大,文字表述较为单一的“体育人口”来反映人们对体育的“参与度”或“亲和度”,尤其是作为反映我国群众体育事业发展的“硬指标”和“制订群众体育事业发展规划的一个重要依据”等,显然有些“任重而道远”。
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一直遵循“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方针,早在1954年,中共中央对体育工作的批示就强调:“在国家已进入有计划经济建设新的历史时期,更需要人民有健康的身体,但现在人民健康状况还远不能适应各项工作的需要。为了改善这种状况,除了加强卫生工作和改善劳动、学习等条件外,开展体育运动确是一种最积极的有效方法。”以后,在国家“第一个五年规划”中规定:“在全国人民中,首先要在厂矿、学校、部队和机关的青年中,广泛开展体育运动,以增强人体的体质”。历史经验已经证实,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倡导积极的参加体育锻炼”是落实体育方针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正如前述,在国内现行“体育人口”理论中“将以追求提高运动成绩为目的的人群”作为“当然体育人口”显然值得商榷。但是,强调“将休闲娱乐为目的的人群”也归属体育人口范畴,似乎与我国群众体育发展方向有悖。国家体育总局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努力“增加以追求身心健康,增强体质为目的体育锻炼人数”作为群体工作的重点之一。1995年颁布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中将“到本世纪末,经济、社会和体育发展程度不同的各类地区,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都应有所增长”作为主要任务之一。2000年12月,国家体育总局在发布的《2001-2010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中就将提高“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作为我国群体工作的奋斗目标之一。原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2001)在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指出:群体工作要“组织群众参加集体体育活动,努力提高我国国民素质”。原国务委员陈至立(2007)指出:“养成体育锻炼和讲究卫生的良好习惯对于健康和长寿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务委员刘延东(2009)指出:“全面小康必须全民健康”;“努力提升全民族体育健身意识,让群众充分享受体育带来的健康和快乐”。在2002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提高“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是今后群众体育工作“突破”的重要内容之一。
此外,在《2000年国民体质研究报告》中,就将20~69岁人群区分为“不锻炼”、“偶尔锻炼”和“经常锻炼”三类,用于分析和比较2000年国民参加体育锻炼的状况。各地区在公布“体育人口率”时已在悄悄的发生着变化,如《北京日报》2003年1月20日,公布了北京市民“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者”的人数比例,并将其作为反映北京市群体工作成就的重要指标之一。
由此可见,从党、政府、历任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和上述两个《纲要》中看出,提升群众的健身意识,全面提高全民族健康素质是新时期群体工作的主要目标。伴随国家、社会发展水平的进步,需要理论界本着从我国群体事业实践和发展角度出发,重新审视“体育人口”理论,实事求是,选择能够既科学、准确,又简单、通俗易懂的指标作为反映我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程度的指标。
本文认为,采用“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以下简称“经常锻炼”)人数或比例能够较为客观的、真实的反映我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程度。这既能满足我国群体事业的发展,也将通俗易懂的反映出我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状况。
3 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程度评价标准的提出
群众体育的发展离不开科学的决策,科学的决策来源于科学的群体调查,群体调查的发展离不开科学的评价。在已经确定评价指标的前提下,需要进一步确定相应的评价标准。如果评价的本质是价值的确定,那么,标准就是衡量评价主体价值大小的尺度或依据。依据体育测量与评价理论,评价标准可以区分为现状标准、理想标准和个体标准。制订评价标准时,除了要求评价指标具有良好的效度、信度以及定量描述的特征以外;还要求标准的“尺度”要能敏感的区别不同个体和群体在评价主体价值的差异,以及具备简便易行的特征。
3.1 体育锻炼的构成要素
体育锻炼的益处非常多,其强身健体的功效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体育锻炼的本质是人体运动,而人体运动是生命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能力。但是“生命在于运动”还是“生命在于适度的运动”却一直成为学术界争论的话题。归根到底,就是如何适度(或科学)的进行人体运动才能将其引发和积累的机体生物特征变化转化为“强身健体”和“延年益寿”的最终效益。所以,在制订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程度评价标准时,需要认真考虑何为体育锻炼的构成要素。
依据医学和生物学原理,当机体受到运动刺激时,将会引发一系列的生理、心理等变化,并在持续地、规律地运动刺激条件下,机体会出现“适应性”改变,使机体产生“超量恢复”后的“累加效应”,既发生所谓的人体运动效益或健身效益。多年的研究证实,与锻炼效益密切相关的要素包括:锻炼方法、锻炼频度、持续时间以及锻炼强度等。
3.1.1 锻炼方法
锻炼方式是指人体运动时,练习的内容或者肢体的具体运动形式。如俯卧撑、仰卧起坐、体操、太极拳(剑)、走、跑、骑自行车和球类运动等都是体育锻炼中常用的身体练习方法。这些方法与竞技训练中类似的方法明显不同,因为在体育锻炼中采用的练习方法不必要求采用“合理、有效的使用身体动作达到克敌制胜的目标”。
在体育锻炼中采用的各类锻炼方式,其基本要求就是通过身体不同部位骨骼肌的收缩,来完成各种身体动作,并促使机体对运动产生“适应性”变化,如消耗能量、提高心血管系统功能、改善神经—内分泌系统调节功能、增加肌肉力量,提高耐力水平等。所以,当人体运动时,无论采用哪一种锻炼方法,机体产生的“适应性”变化规律基本上是一致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不同练习方法之间,由于身体运动的特征不一致,“适应性”变化的程度存在明显的差异。如全身性运动的锻炼效益明显好于局部运动,周期性运动对心血管系统机能水平提高的幅度明显高于非周期性运动;对抗性练习方法比非对抗性更容易造成身体损伤等。所以,在进行体育锻炼时,不必过分强调和要求民众应该采用何种锻炼方法才能达到健身目的,正确的方法应该是鼓励民众因地制宜、选择自己喜爱的方法进行体育锻炼,这样才能保证体育锻炼行为能够长期、持久的坚持下去。
3.1.2 锻炼频度
锻炼频度(frequency)是指进行锻炼时,在一定时间内重复完成身体练习的次数。一般采用每周锻炼次数来表示。依据人体机能水平的变化要服从“用进废退”和“适应”原则,如果每周参加体育锻炼的次数过少或重复次数过低,无论采用何种锻炼强度进行练习,机体都不会产生持久存在的“累加效应”,而会发生“废退”现象。所以,锻炼频度是决定健身效益的关键因素,也是保障和落实体育锻炼原则的基础。
一般而言,锻炼频度的多少与锻炼目的、个人情况以及所选择的锻炼方法有关。如在职人员,由于工作和家庭等的原因,每周锻炼次数过多、过密也会加重身体的负担。由于每次锻炼之间的间隔时间过短,将会促使身体机能水平发展为“过度疲劳”。有研究发现,每周锻炼1次时,健身效益不累积,还会发生肌肉酸痛和疲劳,且锻炼后时常感到身体不适;每周锻炼2次时,健身效益开始累积,疼痛和疲劳减轻;每周锻炼3次时(隔日锻炼),不仅效益可以充分累积,也不产生疲劳等不良身体反应。所以,专家建议体育锻炼频度以每周3次为宜。
3.1.3 持续时间
持续时间(duration)是指每次进行锻炼时,身体运动持续的时间,相当于运动量。机体的各器官系统都存在一定的“惰性”,所以,当肢体运动时,它们的机能水平需要有一个时间过程,才能从安静时的低水平发展到较高水平或最高水平。这样,当身体运动维持一段时间后,才能产生较好的健身效益。据研究,机体各器官、系统的惰性差别较大,一般而言,运动系统动员较快,而内脏和心血管系统惰性较大。如骨骼肌的快速收缩可以使速度在几秒内达到最大,但是,心输出量却在开始运动后3~5 min才能达到最高水平。所以,专家们建议每次锻炼的持续时间以30~60min为宜。
3.1.4 锻炼强度
锻炼强度是指每次锻炼时,人体运动单位时间内的能量消耗量。一般与每次锻炼持续时间共同构成运动负荷。一般而言,强度如果太小就达不到锻炼的效果,太大容易造成伤害。综合国内外研究发现,确定锻炼时的强度是确保锻炼安全性和效益的关键因素,但是,要依据个体体质或健康状况,量力而行,选择适宜的强度进行锻炼。在确定最佳强度时,需要根据个体的年龄、性别、职业特点、体力状况、健康水平、体育基础、生活环境和锻炼目的等不同情况来决定。常用的方法为指数评定法、心率评定法、库珀评定法、疲劳评定法等。从多年的研究和实践经验看,选择“中等强度”进行锻炼得到了众多专家学者的认可。
总之,从对体育锻炼构成要素的分析中,本文认为,在积极鼓励和倡导民众参加体育锻炼的过程中,不必过分强调应该采用何种锻炼方法,制约和影响健身效益的关键因素是锻炼频度、持续时间和锻炼强度,这三者的结合将构成对“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评价的主体。
3.2 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程度评价标准
正如前述,评价标准要求在对评价主体进行价值判断时,“尺度”要满足科学性、可行性、实效性的要求。在充分认识我国群众体育发展方向的前提下,结合对群众体育内涵的认识和对体育锻炼功能、构成要素的分析,本文提出了评价我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程度的指标是“经常锻炼”,其评价主体包括锻炼频度、持续时间和锻炼强度。
世界各国对民众参加体育锻炼采用的评价标准差异较大,但是,常常采用反映体育锻炼的“要素”作为评价主体。如在亚洲国家中,日本评价民众参与体育锻炼水平是根据频率、持续时间和强度来确定的。“绝对体育人口”是指每周参与2次以上,每次活动时间超过30min,且运动强度较强,能坚持一段时间保持和提高自己的健康水平。韩国将参加体育锻炼的人群区分为“锻炼人群和非锻炼人群”,在锻炼人群中又区分为“大强度锻炼”(即每周≥3次,每次20min以上大强度运动)和“中等强度锻炼”(即每周≥5次,每次30min中等强度运动)两个等级。
在欧美国家中,苏格兰将参加体育锻炼人群区分为:“锻炼不足”和“锻炼充足”两类。前者包括“每周锻炼1~2次”、“每月锻炼不足1次”和“不锻炼”;后者是指每周至少4次,每次至少30min体育锻炼。英格兰对参加体育锻炼人群的界定不明确,但提出“每周至少3天参加30 min中等强度体育运动或娱乐活动”是“体育锻炼人口”的标准。加拿大将参加体育锻炼的人群划分为:“积极参加体育锻炼”、“适度参加身体锻炼”和“不参加体育锻炼”三类;但是评价标准不明。芬兰将参加体育锻炼人群分为“中等强度”和“高强度”锻炼人群,其评价标准类似韩国。
由此可见,世界上各国在统计本国民众参加体育锻炼时,均是结合本国实践,自行制订相应的评价标准。目前国际上还未有一个统一标准。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运动医学学会(ACSM)向美国民众推荐的体育锻炼量有一定的代表性。1978年推荐“为了拥有、维持健康的心血管功能和理想的体成分,成年人应该进行每周3~5次,每次15~60 min,运动强度达到60%~90%最大心率,节奏较强的大肌肉群有氧运动。如跑步、游泳、滑冰等耐力性运动”。此推荐量(标准)从锻炼频度、持续时间、强度、锻炼方式、性质等方面描述了如何评价体育锻炼是否充分,体育锻炼应该达到什么水平。但是,遗憾的是,此标准仅限于强度相对较大的有氧运动,对于强度的判断还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不利于在民众中推广。经过不断的研究和探索,ACSM分别于1990年和1998年两次修订了标准,1990年将锻炼持续时间延长到“每次20~60min”,补充了“每周至少2次,每组重复8~10次的中等强度阻力练习”[40]。1998年将锻炼持续时间修改为“每次20~60min”或“每次至少10min累积达到每天20~60 min”。此外,ACSM与CDC(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于1995年推出了具有预防疾病功效的锻炼标准,即“每周最好每天或每周5次,每次至少30min或每次8~10min、累积每天至少30min的中等强度以上的体育锻炼”;“能够促进健康,降低总死亡率,降低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发生危险”。
在ACSM和CDC对美国民众推荐的锻炼标准中看出,尽管伴随社会的进步,不断地增加锻炼方式,降低强度,但都需要持续一定的时间和维持一定的锻炼频度。显然,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而言,缺乏时间锻炼身体正是困扰现代人健康的关键。所以,ACSM又推出一个“简单锻炼”模式(simple exercise)即每周至少锻炼3次、每次30min、强度适中的身体活动。在我国,也有类似的标准,1997年全国群众体育调查报告中首次采用“每周身体活动频率3次(含次以上),每次身体活动时间30min以上,每次身体活动强度中等以上”作为“体育人口”的评价标准。以后,在2001年群体调查中采用了相同的标准。
综上所述,国际上普遍把每周参加1~3次以上锻炼、每次持续活动时间为20~60min,适宜运动强度作为“参加体育锻炼”的评价标准。尤其突出的是将把“促进健康、身心娱乐、预防疾病为锻炼目的,每周参加3次以上体育锻炼、每次活动持续时间为20~30min,适宜运动强度(中等以上强度)作为“积极主动参加体育锻炼”或“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评价标准。
本文认为,在参考前2次全国群众体育调查结果和国际流行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将“每周参加体育锻炼3次及以上,每次体育锻炼持续时间30min及以上,每次体育锻炼的运动强度达到中等及以上”作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评价标准。与此同时,将1)参加体育锻炼次数为“每月不足1次”、“每月至少1次,但每周不足1次”、“每周1~2次”,2)每次锻炼持续时间达不到30min;3)锻炼强度低于中等强度的成为偶尔参加体育锻炼(简称“偶尔锻炼”)。这样,就将我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程度的评价主体划分为两个等级,即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程度区分为“经常锻炼”和“偶尔锻炼”。
4 结语
中国的群众体育事业经过60年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不断发展的道路中,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次反思在工作中的失误或不足。本文采用文献资料的研究方法,运用理论思辨和分析比较相结合的研究思路,重点探讨了如何构建评价我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程度的指标和标准,并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成果,在参考了我国群体事业发展目标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下结论:
1.采用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程度可以较为准确、真实的反映出我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水平或现状,能够较为科学的为决策部门提供参考。
2.“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是评价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程度的指标,其构成要素锻炼频度、每次锻炼持续时间和锻炼强度作为评价主体,具有良好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3.本文依据我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实情,将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程度划分为“经常锻炼”和“偶尔锻炼”两个等级。
4.经常锻炼的评价标准是“每周参加体育锻炼3次及以上,每次体育锻炼持续时间30 min及以上,每次体育锻炼的运动强度达到中等及以上”.
5.偶尔锻炼的评价标准是:1)参加体育锻炼次数为“每月不足1次”、“每月至少1次,但每周不足1次”、“每周1~2次”;2)每次锻炼持续时间达不到30min;3)锻炼强度低于中等强度。
收稿日期:2009-02-04; 修订日期:2009-04-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