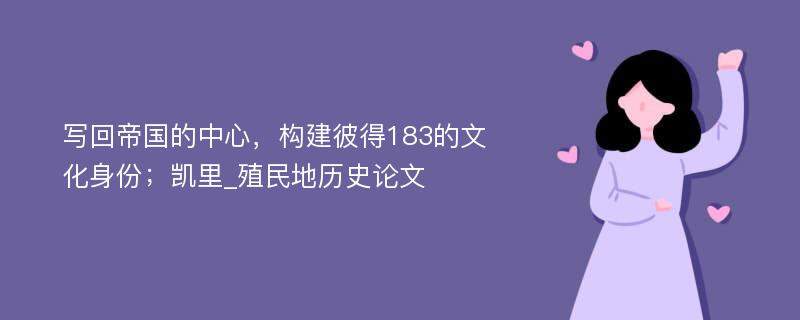
写回帝国中心,建构文化身份的彼得#183;凯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凯里论文,彼得论文,帝国论文,身份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是任何民族都无法绕开的,这对于后殖民国家澳大利亚来说更是如此。虽然在历史上澳大利亚只是英帝国的一个罪犯流放地,并没有像其它第三世界国家那样遭受被占领和奴役的命运,也没有像美国、印度那样经过民族战争而获得独立的经历,但在帝国的文本中澳大利亚常常被描写成“他者”,遭人“凝视”,忍受着“身份丧失”的痛苦。同时很久以来,澳洲原土著居民拒不承认移民到澳大利亚的英国人的主人身份。这种不是“他者的他者”——“非此非彼”的窘境令澳大利亚人迷茫而困惑,因此与英帝国之间的特殊历史文化关系,与土著文化的各种冲突和对美国文化爱恨交织的矛盾情感成为澳大利亚作家刻意探讨的主题。如何处理与英国、土著和美国文化的关系成为澳大利亚人建构文化身份的关键。
事实上,自美越战争,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 澳大利亚国内强烈要求重新审视“民族故事”的呼声日益高涨,并涌现了一批反映民族心理,建构民族叙事的“新历史”小说。(注:“新历史”小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题材小说,它们没有刻意忠实地重建历史,而是古讽今,以当代人的视角去阐释历史,彼得·皮尔斯(Peter Pierce)称之为“新历史”小说。详见Bruce Bennett and Jennifer Strauss,The Oxford Literary History of Australia,Melbourne: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ustralia,p.327.)其中较为典型的有托马斯·基尼利(Thomas Keneally,1935—)的《剧作人》The Playmaker,1987)和西·阿斯特利(Thea Astley)的《曼歌在下雨》(It's Raining in Mango,1987)等。不过与这些作家相比, 彼得·凯里(Peter Carey,1943—)在透视澳大利亚殖民历史方面做得更为出色。他曾两次获“布克奖”,已是享誉国际文坛的文学巨匠。(注:Anthony J.Hassall,“Preface”in Dancing on the Hot Macadam,St Lucia: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1998.)他的小说融历史和现实为一炉,深刻揭示了澳大利亚人建构文化身份的历史负荷与现实困境。在他出版的八部长篇小说中,有五部都与帝国相关,具有很强的历史感。从《魔术师》(Illywhacker ,1985)里所展现的历史谎言和民族困境,到《奥斯卡与露辛达》(Oscar and Lucinda,1988)的英国基督文化与澳洲土著文化的冲突;从《杰克·迈格斯》(Jack Maggs,1997)马格维奇文化身份的重塑,到《“凯利帮”真史》( True History of the Kelly Gang,2000)殖民神话的再现;从《特里斯坦·史密斯不寻常的生活》(The Unusual Life of Tristan Smith,1994)的帝国文化霸权,到《幸福》(Bliss,1982)里的“美国梦”,无不体现彼得·凯里“写回”旧殖民帝国——英国和新殖民帝国——美国的倾向。“写回”并不是“重写”而是比尔·艾什克拉傅特(Bill Ashcroft)提出的“篡改”, 即体现最有效的后殖民对立性,并使其自身成为一种主导后殖民话语的方式。“重写”只不过在“多重奏”中加了“甄别的声音”,而“篡改”则改变了“元叙述”本身。“写回”的效果比“把故事掰正”更深远。(注:Bill Ashcroft,“Against the Tide of Time:Peter Carey's Interpolation into History”,in John C.Hawley,ed.Writing the Nation:Self and Country in Post-colonial Imagination,Amsterdam:Rodipi,1996,pp.194—213.)本文以彼得·凯里的三部长篇小说为例,分别从“民族叙事”,“帝国远征”和“文化霸权”等方面来解读其后殖民主义历史观。
《魔术师》是凯里建构澳大利亚的民族叙事和文化身份的第一次尝试。它被评论家誉为“澳大利亚之歌”,(注:Karen Lamb,Peter Carey:The Genesis of Fame,London:Angus & Robertson,1992,p.33,p.37.)是“第一部能够帕特里克·怀特的《沃斯》相媲美的伟大小说”。(注:Karen Lamb,Peter Carey:The Genesis of Fame,London:Angus & Robertson,1992,p.33,p.37.)它通过讲述赫伯特·拜杰葛瑞一家三代试图建立民族航空、汽车工业,而最终梦碎人去,家园变成了“最佳动物商店”的离奇故事,表现了澳大利亚人追求个人、民族理想的现实困境:澳大利亚在历史上是英帝国的殖民地,随着历史的变迁,现在又沦落为美帝国的殖民地,所不同的是仅仅换了主子而已。澳大利亚人建立独立民族工业的道路是艰难的,当拜杰葛瑞试图说服几位有钱人投资他的宏伟计划时,他们反应冷淡,“我们还是一个年青的国家,我们在学会走之前不得不先爬”。(注:Peter Carey,Illywhacker,St Lucia: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1985,p.141,p.136,p.481,p.307.)尽管身为美国福特汽车多年推销员的拜杰葛瑞心里很想通过个人努力摆脱对殖民帝国的依赖,“我已经卖了两百多台福特汽车,也确实挣了很多钱,但我从没有开心过。”(注:Peter Carey,Illywhacker,St Lucia: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1985,p.141,p.136,p.481,p.307.)但他这种痴心妄想在当时的澳大利亚是不可能实现的。迫于生活的压力,他又不得不重操旧业,干起了推销美国汽车的旧行当。
他的儿子查尔斯·拜杰葛瑞也是具有强烈爱国情怀的“真正的澳大利亚人”。他曾想在二战其间参军入伍,以报效祖国,但无奈听力的残疾,而未能如愿以偿。其妻误以为他要弃她而去,倍受打击,从此就把自己关在鸟笼中。查尔斯致力于建立一个能向世界各地,尤其是能向美国、日本出口的“世界上最好的宠物商店”,“他不计较修复年久失修拱廊的费用,也不考虑储藏饲料所产生的额外开支,他的初衷是纯粹的爱国主义”。(注:Peter Carey,Illywhacker,St Lucia: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1985,p.141,p.136,p.481,p.307.)然而在一次有关澳大利亚国产车的争论中,他悲愤激昂,与父亲产生矛盾,并在事后不久开枪自杀。查尔斯的儿子希斯奥不喜欢宠物店,长大成人后,他把它卖给了一家日本公司,并在特安克溪——殖民监狱的原址上建造了供人娱乐的后现代动物园。
《魔术师》的叙述出自一个自称活了139岁的谎言家之口。这部家族史诗横跨澳大利亚现、当代史,展现了澳大利亚人追求民族经济、文化独立的艰难历程。从赫伯特的汽车梦,到查尔斯的宠物店,再到希斯奥的动物园,无不体现他们建构独立文化身份的强烈愿望。赫伯特因生活所迫,辗转澳洲各地,他渴望有一个安稳的家,也在行程中建造了很多的“房子”,但他没有家的感觉,因为正如他的情人利厄所言,“这片土地是偷来的。整个国土都是偷来的……她看起来像你的地方吗?……难道你看不出即使是这里的树和你有任何相干吗?”(注:Peter Carey,Illywhacker,St Lucia: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1985,p.141,p.136,p.481,p.307.)赫伯特最终未能如愿,他在监狱呆了十多年之后,又回到了生活中的监狱——一个破落的小阁楼。
彼得·凯里在这本小说里所要凸显的,是揭穿帝国历史中的两个谎言:即“澳大利亚过去是被人‘发现’的无人居住的大陆;现在是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和敢于反权威的民族”。(注:David Sexton,The Literary Review,June 1985,p.41.)事实上,在欧洲白人来到澳洲之前,土著人已在此生活了几千年。尽管澳大利亚已经建国一百多年,但它仍然不是一个真正自由独立的国家,而是英国、美国和日本的殖民地。虽然小说文本没有就第一个谎言追根溯源,但是赫伯特·拜杰葛瑞一家流浪汉般的生活对“家”的含义做了极好的注解。没有家何以有“归属感”和“身份”。好不容易在悉尼定居,但却又发现陷入了一个个生活困境中。赫伯特·拜杰葛瑞一家努力建立民族工业和“世界最佳宠物商店”的经历,是澳大利亚人建立独立文化身份的过程,同时也是解构历史谎言的过程。彼得·凯里把主人公塑造成一个“谎言家”,一方面是为了表明小说文本的虚构性,另一方面也暗示澳大利亚的历史充满谎言,从而也回应和印证了马克·吐温的经典名言:“澳大利亚历史几乎是奇特有趣的……它读起来不像历史,倒像美丽的谎言”。(注:Mark Twain,More Tramps Abroad,London,1897.)
如果说《魔术师》只是提到帝国殖民史谎言的冰山一角的话,《奥斯卡与露辛达》则是彼得·凯里对帝国“文明史”最直接的揭露。在帝国的意象中,澳洲大陆荒无人烟。在帝国的文本中,只记载大英帝国远征的英雄史,土著人无权拥有自己的历史。这种探险英雄的产生,是由于那些编造和鼓吹这种故事的人对土著人的存在熟视无睹而造成的。殖民远征所带来的残暴、杀戮往往被帝国抹杀、掩盖和歪曲。大英帝国的远征英雄,后成为好望角殖民地总督的哈里史密斯爵士曾这样说过:“向野蛮人开战不能按照既定的原则,必须按照常识行事才行。”(注:Elleke Boehmer,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Literature,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p.20,p.17.)这里所谓的常识,其实往往就是对土著居民生活的蔑视、冷漠和暴力。为还原历史之真,彼得·凯里通过《奥斯卡与露辛达》来再现帝国文明给土著人带来的灾难。正如评论家露丝·布朗所所说的那样,“(它)不是发现新的文化倾向,而是邀请人们重新审视一下旧文化。”(注:Ruth Brown,“English Heritage and Australian Culture:The Church and Literature of England in Oscar and Lucinda”,Australian Literary Studies 17,no.2 1995,p.135—140.)
彼得·凯里没有直接通过“重写”来“颠覆”历史,而是采用“重新描述”来“质询”历史,并让读者进行判断。他把对历史的看法融入在“故事”之中,并通过“故事”来颠覆历史。《奥斯卡与露辛达》讲述的是一对青年男女离奇的爱情故事,信奉上帝而又迷恋赌博的维多利亚牧师奥斯卡·霍普金斯,在去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的船上,与具有女权思想的露辛达不期而遇。奥斯卡向露辛达灌输赌博无害的道理,认为对上帝信仰本身便是一场赌博。下船分手后不久,两人再次相遇,便在奥斯卡的牧师住宅又赌了起来。奥斯卡便因此被剥夺了神职。潦倒中的奥斯卡幸得露辛达相助,找到了一份工作。奥斯卡又忽发奇想,建议露辛达建造一座玻璃教堂,赠给深深爱着她的丹尼斯牧师,并自告奋勇把教堂护送到丹尼斯供职的伯令格。露辛达表示同意,并与奥斯卡打赌,如教堂顺利到达,她愿以全部财产奉送。其实露辛达因为深爱着奥斯卡,有意要赠送财产,所以特意聘请杰弗里斯组成一支庞大的远征队伍,以确保奥斯卡获胜。路途中,杰弗里斯肆意滥杀土著人,忍无可忍的奥斯卡用利斧杀死了杰弗里斯。到达目的地之后,神情恍惚的奥斯卡,当晚受到了一个名叫朱丽安寡妇的诱惑,第二天又鬼使神差地同她结了婚。后来醒悟了的奥斯卡,懊悔不已,怀着对露辛达的内疚来到教堂祈祷,不幸因木筏松动而溺死在教堂里。寡妇朱丽安生下奥斯卡的遗腹子。(注: 黄源深:《澳大利亚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04,407页。)
虽然表面上看,玻璃教堂只是一个表白爱情的礼物,但在后殖民社会的语境下,当它穿越澳大利亚草原时,就被彼得·凯里赋予了巨大的历史意义。牧师、玻璃教堂、凶悍的探险队伍、土著向导构成了一副生动的帝国远征的画卷。当玻璃教堂与广袤的澳洲大陆相撞之后,便出现了一部关于这片土地的新历史,而奥斯卡的后人则用这个故事来解释他们的归属。正如空间历史学家保罗卡特所说,任何关于殖民的描述,任何从过去那个国家移来意义的努力,都将把一种意图、向度和层次感赋予未知的空间。最简单的、日常的象征姿态都在对存在进行地理定位,创造出一种供人生活的天地。从帝国的角度来看,殖民主义是法律层面,但同时也是一种喻象和图示层面的一种行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被“图形化”或借用故乡本土的意象对它进行空间的构想是实施殖民统治的具体表现。(注:Elleke Boehmer,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Literature,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p.20,p.17.)小说中邪恶化身的杰弗里斯一心要永垂青史,为此,“他会写出这个殖民地从未读到过的日记;每个山峰、山口的高度都会被精确地测量;连绵起伏的山脊会被优美地描述出来。他的文章有钢一样的筋骨,而他的描述则像紫罗兰的花瓣一样娇嫩。”(注:彼得·凯里:《奥斯卡与露辛达》,曲卫国译,重庆出版社,1998年,第509,545页。)他的描述显示了帝国殖民者的野心,“他认为每块玻璃都会穿过从没见过玻璃的乡村。这些玻璃将开创新的历史进程,将撕开遮蔽地面的白色粉尘覆盖物,揭示出下面的地图。地图上有山川、河流、地名、他出身地波罗姆雷街道,把它们与澳大利亚原始的河流连接在一起。”(注:彼得·凯里:《奥斯卡与露辛达》,曲卫国译,重庆出版社,1998年,第509,545页。)
在这巨大的历史意义背后,《奥斯卡与露辛达》实际上把19世纪的文化批判和对20世纪人性危机的刻画,自然地糅和在一起。小说中玻璃教堂的建造及运送,象征英国基督文化入侵澳大利亚,与本地朴实无华的土著文化发生了冲突,并用枪炮消融了后者,同时造成了其自身的堕落(如赌博),结果就像康拉德的小说《黑暗之心》所刻画的那样,原本要将“文明”带到殖民地的入侵者,自己也终于成为耽于杀戮和掠夺的堕落者。小说中野心勃勃的杰弗里斯肆无忌惮地杀害土著人就是一个明证。而当地的土著人密切注视着沿河而下的玻璃教堂,知道它潜在的破坏力,他们把它看作“白人的梦想”,而且也明白,“它(玻璃)会把东西切开,把树切开,把他们的种族切开。”(注: Peter Carey,Oscar and Lucinda,St Lucia: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1988,p.469.)这也就是批判英国基督教文化,指出它无视和颠覆了原有的土著文化,而小说中奥斯卡正是首批来澳的散布督教文化的先驱。难怪小说出版不久,有的评论家不无同情地说:《奥斯卡与露辛达》“是彼得献给这个国家的反英两百周年纪念的礼物。”(注: 黄源深:《澳大利亚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04,407页。)
殖民时期的澳大利亚人不得不为其文化身份而同大英帝国抗争,当代的澳大利亚人同样需要同新殖民帝国——美国作斗争。面对全球化浪潮,处于弱势的澳大利亚文化遭受强大的新帝国文化的巨大冲击,帝国的电影、电视、文化娱乐等充斥着澳大利亚的文化市场,民族文化面临着生存的危机。如何应对新帝国新一轮的文化入侵,建立独立的民族文化是后殖民国家面临的共同课题。彼得·凯里以其独特的视角,通过其小说《特里斯坦·史密斯不寻常的生活》再次向读者展现了帝国在政治上干涉,经济上剥削,文化上控制其它国家的霸权行径,以及弱小殖民地如何利用“招摇撞骗”的伎俩来颠覆帝国文化和对帝国文化爱恨交织的民族心理。
《特里斯坦·史密斯不寻常的生活》是一部有关文化殖民的小说,是边缘殖民地向帝国中心的呐喊。彼得·凯里以其丰富的想象力和独到的洞察力臆造了维拉斯坦国和埃非克国的文化冲突。埃非克国是一个人口只有近300万, 坐落在南回归线38度,有18个小岛组成的国家。虽然它已从一个罪犯流放地变成了一个福利国家,但它依然生活在宗主国——维拉斯坦国的阴影里。由民族主义者组成的福伊佛雷特剧团奋起抗争,努力建立和发展本土文化。该剧团经理菲蕾瑟特·史密斯早期从维拉斯坦国移民到埃非克国,并致力于发展埃非克国的文化事业,她强烈批评维拉斯坦国利用其强势文化,打压埃非克国文化的生存空间的新殖民主义行径。眼看作为“绿党”侯选人的菲蕾瑟特即将在选举中获胜,维拉斯坦国在埃非克国的特工们利用菲蕾瑟特和她情人的关系,制造绯闻,致使“绿党”在选举的最后关键时刻失利,“红党”政府继续执政,从而保证了维拉斯坦国在埃非克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利益不受影响。菲蕾瑟特在愤怒和绝望中自杀,留下了身体残疾,且生活不能自理的儿子特里斯坦·史密斯。特里斯坦奇丑无比,是一个发育不健全、讲话含糊不清的侏儒,但他聪明、勇敢,一心要成为一个演员。在他母亲自杀后,他继承了他母亲未完成的事业,并同养父沃雷·俳克思恩一起偷渡到维拉斯坦国。身无分文的他靠在大街上装扮维拉斯坦国的布拉德猫而挣钱糊口。由于布拉德猫是维拉斯坦国文化的象征,史密斯的表演大受欢迎,维拉斯坦国民纷纷解囊相助。但他们并未过上平静的生活,史密斯受到维拉斯坦国情报部门的监视和追杀。沃雷·俳克思恩为保护他中弹身亡,史密斯和其在维拉斯坦国工作多年的生父一起逃离了维拉斯坦国,从此开始了他不同寻常的生活。
彼得·凯里通过特里斯坦·史密斯的叙述控诉了帝国霸权的种种丑恶。小说的主人公虽然年少无知,但他通过其亲身感受深知帝国霸权已经渗透到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各个方面。“你们是凭借你们的魅力和技能征服我们的,通过你们的军队,没错,还有你们的情报部门。你们还凭借你们的笑话与舞蹈,死亡与美人,全息摄影术,激光,电视,以及操纵和编排的几乎完美无缺的悬念。”(注: Peter Carey,The Unusual Life of Tristan Smith,St Lucia: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1994,p.302,p.277,p.120,p.190.)史密斯的控诉和葛兰西的霸权阐释一脉相承。葛兰西认为资本主义的霸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教育,即通过对文化制度的大规模网络(如学校、教会、政党、报纸、传播媒介和民间社团)控制,而操纵着整个社会,使其不断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整合为一,从而最终达到“认同”。另一种是暴力,即通过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如军队、警察、法院等来实现“统治”。它主要是针对市民社会中那些不满分子、暴乱分子和拒不服从统治的人。(注:Teodros Kiros,Towards the Construction of a Theory of Political Action;Antonio Gramsci,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Inc.1985,p.100.)在《特里斯坦·史密斯不寻常的生活》里,维拉斯坦国对埃非克国实施多方面的控制,虽然没有对埃非克国实施军事占领,但它在埃非克国建立了军事基地、埋设了海底电缆,并占用大片土地作为核实验场所;在经济上,埃非克国饱受剥削,其丰富的水产被迫廉价卖给维拉斯坦国;在政治上,为确保其最大的利益不受损害,维拉斯坦国的特工肆意干涉埃非克国的内政。特工加布·曼曾尼在“绿党”即将获胜之际曾威胁说:“告诉你的人,他们死定了。”“我们永远不会让他们(绿党)在选举中获胜的。”(注: Peter Carey,The Unusual Life of Tristan Smith,St Lucia: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1994,p.302,p.277,p.120,p.190.)为此,他们通过散布谣言、暗杀等手段,把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绿党”搞得声名狼藉,从而使得保守的“红党”继续执政,帝国的利益也得到了极大的维护。
不仅如此,维拉斯坦国还利用其强势文化,挤压埃非克国的本土文化,以至于埃非克国人有文化身份丧失的焦虑感。“我们开始界定自己的民族身份了吗?没有人告诉过我什么可能是埃非克国的民族身份。我们本来是生活在北半球的却被扔到了南半球。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不像很势力的法国人,也不像野蛮的英国人。我们认为老鼠并不像维拉斯坦人那样有灵魂。但是,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这里’的。我们是跳蚤马戏团。”(注: Peter Carey,The Unusual Life of Tristan Smith,St Lucia: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1994,p.302,p.277,p.120,p.190.)菲蕾瑟特·史密斯的诘问反映出埃非克人面临着身份危机。但不可否认,即使是把创造埃非克民族风格作为其终身目标的人,有时也流露出对帝国文化爱恨交织的情感。“不管我妈妈怎么批评维拉斯坦国的霸权,她明显地表现出对布卢斯猫的复杂心情,而这一点,她从未向剧团的人承认过。”(注: Peter Carey,The Unusual Life of Tristan Smith,St Lucia: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1994,p.302,p.277,p.120,p.190.)即便如此,她也没有动摇过自己的信念。在她眼里, 马戏团担负着建构民族文化和改变国家命运的历史使命。
菲蕾瑟特·史密斯未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身体残疾的儿子更不可能完成母亲未竟的事业。于是主人公利用后殖民主义理论中的“江湖骗子”的手法,颠覆帝国文化的完整性。如果按霍米·巴巴所说,“殖民话语的目标就是把殖民地的臣民描述成劣等民族”,(注:Homi K.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4,p.70,p.44.)那么,后殖民话语的一个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质询它如此建构的论证方法。“江湖骗子”就是这样一种把殖民地的臣民建构成劣等人和骗子的方法。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指出,“江湖骗子”是殖民控制的一种运作机制,而知识目标的重新建构是通过相像实现的。例如,把穆罕默德说成是一个“骗子”,他佯装成我们熟悉的耶稣,但他不是耶稣。把穆罕默德塑造成一个“冒牌的预言家”,“他被赋予了某种谱系,得到了相应的解释,甚至获得了一定的发展。”(注:Edward Said,Orientalism,London:Penguin Books,1991,p.71.)对于赛义德来说,把穆罕默德描述成“骗子”是帝国主义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防止人们对已形成的看法提出质疑和挑战的方式。另一后殖民理论家苏姗·吉尔曼虽然对“江湖骗子”在帝国话语中作用不感兴趣,但她也认为“江湖骗子”这一手法使“追根求源”的问题复杂化了。(注:Susan Gillman,Dark Twins:Imposture and Identity in Mark Twain's America,Chicago &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p.6.)海伦·蒂芬指出,“江湖骗子”在特定的后殖民语境中是对殖民控制“强烈不满”的一种表露,因为它对殖民控制系统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注:Helen Tiffin,“The Tickborne Affair and Patrick White's The Twyborn Affair”,“And What Books Do You Read? ”New Studies in Australian Literature,St.Lucia: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1996,p.134.)《特里斯坦·史密斯不寻常的生活》里的史密斯把自己装扮成维拉斯坦国的布卢斯猫,从而成为一个“江湖骗子”,虽然他起初的动机只是为了掩盖他只有三英尺六英寸的残疾,但他客观上扮演了帝国圣像的角色,从而构成强有力的反殖民话语,因为它暗含着霍米·巴巴所说的“在殖民身份被抹去的部分刻上自我的他者的印记”,而且还形成了改变主人或模式的假想。(注:Homi K.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4,p.70,p.44.)这种从“内部颠覆”——扮演“他者的他者”的策略是一个弱小殖民地抗拒帝国霸权的有效途径。
彼得·凯里利用史密斯冒充布卢斯猫的行为不仅“戏谑”了帝国文化,而且还通过与帝国女富翁的性关系讽刺了帝国的道德腐败。邿格·克拉姆是维拉斯坦国一个高级女牧师,并拥有多个马戏团。她患有恐旷症,并深受传统的维拉斯坦国宗教文化的影响,多年来,她手下的二十多个马戏团一直轮演“伟大的历史”这一剧目。自从认识了身穿布卢斯猫服装的史密斯之后,她迅速坠入爱河,并与他同居了一个星期。史密斯利用帝国的高科技,使他能像正常人那样说话,又利用姵格·克拉姆的轻浮获得了性的释放,从而达到报复殖民者的目的。《特里斯坦·史密斯不寻常的生活》是殖民地弱势文化对帝国强势文化反击的写照。虽然彼得·凯里在文本中没有直接表明这是一部有关澳大利亚与美国文化关系的小说,但读者可以从小说的脚注和尾注的词汇附录中看出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影子。小说也从一个侧面彰显出澳大利亚文化的奴婢性。
除了以上三部小说之外,彼得·凯里的另外两部小说《杰克·迈格斯》和《“凯利帮”真史》也明显具有“写回帝国中心,建构文化身份”的特点。前者“篡改”了帝国文学——狄更斯的小说《远大前程》,后者“再现”了殖民时期的民族神话——内德·凯利。在彼得·凯里的笔下,杰克·迈格斯和内德·凯利都获得了新生。杰克·迈格斯不再是被狄更斯“边缘化”和“丑化”了的马格维奇,而是占据叙述中心位置,代表澳大利亚欣欣向荣未来的新人。同样,内德·凯利也不再是澳大利亚官方所认定的“杀人犯”和“盗马贼”,而是敢于反殖民、反压迫的“民族英雄”和“自由斗士”。
据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彼得·凯里的小说贯穿着很强的后殖民主义历史观:重新审视被殖民者歪曲的历史与文化。通过写回帝国中心——英美帝国,来探究澳大利亚民族曾经迷失的“根”和“文化身份”。“记忆历史”是一个民族经过岁月汰洗以后留下的“根”,是一个时代风吹雨打后所保存的“前理解”,是一个社会走向未来的反思基点。处于帝国中心“边缘地带”的澳大利亚,对宗主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依赖,使其文化记忆深深打下了“臣属”的烙印。为了消除帝国的影响,彼得·凯里进行了有力的抗争,正是在这种对帝国文本解构与建构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澳大利亚民族重新塑造文化身份的强烈愿望、历史负荷和现实困境。彼得·凯里没有告诉读者什么是澳大利亚的文化身份,但其解构的过程正是文化身份建构的意义,因此彼得·凯里“写回”“民族叙事”、“帝国远征”和“文化霸权”等方面的过程就是建构澳大利亚新文化身份的过程。其实质是颠覆殖民主义话语,建立具有民族独立性的后殖民“反话语”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