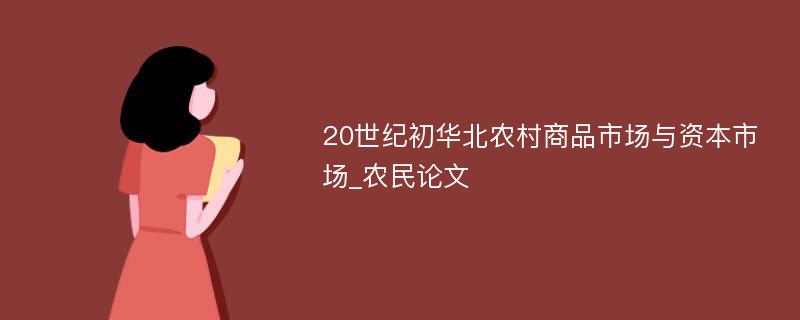
二十世纪前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北地区论文,资本市场论文,二十世纪论文,商品市场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力图从商品和资本两个方面来探讨清末以来的华北地区农村市场的发展与历史经验。
若完全按题目所限定的研究范围来看,这方面国内外尚未发现有专门的研究论著,但一些有影响的著作与本文研究领域颇有关涉,如美国学者马若孟(Raman Myers)、黄宗智(Philip Huang )和中国学者从翰香及其合作者对华北农村的研究。上述研究中,黄宗智与马若孟形成了两种鲜明对立的观点。马若孟主要以满铁的调查资料和卜凯的调查资料为依据,对河北、山东农村经济状况作了考察。他认为华北土地分配状况没有进一步恶化;农民能够对市场作出灵活反应,调整作物生产如种植效益高的作物,以及抓住非农雇佣机会、抓住对外贸易扩展给农村手工业所带来的发展机会;没有证据说明商人和高利贷者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进而,他认为农民生活水平并未下降,相反有改善的可能。〔1 〕从翰香新近出版的《近代冀鲁豫乡村》一书倾向于认为华北农村经济在本世纪前半期有很大发展,但除镇集外,无专章论述农村市场。黄宗智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先后发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及《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并均有中英文版本。黄宗智得出的著名结论是:商品化导致中国小农经济的进一步强化,是非趋于资本主义的商品化,即“过密型商品化”,实即“没有发展”。在论到华北农村时,他认为华北经营式农场也“未能导致农场生产力发生质的改变,则说明了农业经济的停滞。”〔2〕黄的著作实际上很多与农村市场问题有关, 但他并没有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重点只在农民的生产方式上,主要方法似乎是“解剖麻雀”,仅仅根据满铁几十个村庄的调查资料和他自己对几个村庄的调查资料就对近代中国农村几百年的历史下结论,这是否也算是黄宗智自己所批评的那样太过“模式化”的研究呢?
上述各位学者的论著都是对农村作综合研究,重生产轻市场,特别是没有对农村商品和资金在某一特定农村市场和整个大经济区域内(如整个华北)的进出流动作出定量分析,而这对判断商品化程度和市场发展是最重要的根据。有的学者,虽不研究华北农村,但却是专门研究国内市场的,并对农村商品流通作出了定量分析,因而与本文的研究对象关系很大。这方面主要是指吴承明先生的研究。吴承明在其所著《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一书中认为,“1936年埠际流通则连机制面粉不过26亿斤,加上铁路、木帆船运输也不会太多”〔3〕,所据为40个埠 的贸易统计(只限轮船运输);并进一步估计,中国粮食商品率在1920年为22%,在30年代不超过30%,因而20世纪前期中国农村仍处于“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状态”,既如此,农村市场当然是微不足道的了;对地方农村小市场,吴承明认为,只是“余缺调剂”、“品种调剂”,具有对“自然经济补充的性质”;不过吴承明似乎尚认为中国市场的发展方向是趋于资本主义的。笔者认为黄宗智和吴承明都对农村市场发展估计不足(吴承明是针对全国,当然包括华北),本文将对这二位的观点详加讨论。
一、华北地区的农村商品市场
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农村市场”有双重含义:一是指商品交易量有多大,即市场容量;同时也是指农村商品交易的场所,如下文将要研究的农村集镇即是这种交易场所——农村商品市场(当然包括要素市场)的载体。
(一)长距离贸易
在一个大的经济区域内,既有长距离贸易,也有近距离贸易,都是相对而言。是不是非得内地货运到沿海或北方运到南方才算是长距离呢?我想没必要作出这种苛求。长距离与短距离只是个相对概念。本文的计算只要农产品运出县境即算作长距离贸易。在后文研究中将说明这种划分的根据。运出县境的粮食必然包括进入出口贸易和进入国内土产贸易两部分。
华北的粮食商品首推小麦。小麦是著名的所谓“粜精籴粗”的粮食作物,因其为北方粮食中之上品,价格常较其它粮食高,所以华北农民常将其抛于市场,以便换取货币,并以玉米、小米、高粱等作为替代食物,因此小麦为一典型商品作物。小麦又不同于一般的经济作物如花生等,为华北平原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产量极大,种植面积很广。据1935年统计,山西小麦栽培面积在该省农作物中为最大,总计15,537,516亩;1935年产量为13,937,184担,约占该年全省粮食总产量55,337,649担的25.2%〔4〕。又据中央农业实验所统计,1931—1937年间河北与山 东的小麦平均年产量分别为3,651,900,000市斤和7,170,500,000市斤,在各该省粮食总产量的比例中均占第1位,小麦占河北省粮食总产量的23%,占山东总产量的32%〔5〕。 因此小麦作为大宗商品粮投放于市 场对华北农产品的商品化具有重要意义。
据山西实业志统计,93 个产麦县份中, 有外销者(运销县外的)37县,总数2,163,723担,其中输出省外者约500,000担。也就是说约占总产量15.5%的小麦进入长距离贸易。河北省小麦的外销量尚未查到全面的数字,不过下述24县情况已足以说明河北小麦进入长距离贸易的大部分情况。从表1看,获鹿县产量既丰,县外销量也最大, 超过产量的50%。另外还有平山、文安、满城等县外销量都超过了产量的35%,北宁路和热河等地也还有少量小麦运出。山东小麦产量为华北之冠,外销量也最大。据《中国实业志》(山东)统计,山东小麦常年产量为 48,928,224市担,1933年产量为51,934,715市担,外销量为11,923,373市 担,计占产量的24.4%。山东108县,小麦有外销者达60余县。 输出占产量比率最高者为章邱县,达80%,年销88万余担。外销占产量比率超过40%的多达18个县,年外销绝对量在30万担和30万担以上的即达12个县。
总计晋冀鲁三省运销县外的小麦总量达1,700多万担,约近20亿斤 。前文讲过,小麦运销县境外之后即进入长距离贸易。为何说小麦运销县境外即进入长距离贸易?只要看看这些运销县外的小麦的走向,即可证实这个结论。首先,山东的小麦主要向五大市场集中,鲁北小麦多输向天津,最后进入天津的六大粉厂;鲁南一带多输向徐州,最后有相当部分进入上海;鲁西、鲁中多集中于济南,最后被济南面粉厂吸收;胶济沿线及鲁东多集中于青岛,鲁东北则聚于烟台。总计济南有面粉厂7 家,青岛有3家,烟台有1家,泰安1家,济宁1家,1993年共吸收山东小麦4,682,733担〔6〕。另外河北小麦多经水运而达于天津,天津6 家面粉厂每年可吸收中国小麦350万担—400万担。平汉铁路沿线的面粉厂,如保定和新乡等粉厂,每年可吸收200多万担山西和河北的小麦〔7〕。总计冀鲁面粉厂共可吸收华北三省小麦约近1,100余万担。其余600多万担走向三途:一部分如前述进入上海;一部分进入山西的小型面粉厂和晋、冀、鲁三省的机磨坊、土磨坊以及酿造业等;另一部分进入各该省不产麦的地方及绥远等。上述数据表明小麦进入长距离贸易的数量是很大的。如果再加上小麦产量与山东同为中国之冠的河南省小麦的外销量,很明显仅小麦一项商品的长距离贸易量就已超过吴承明据1936年40个埠的数据所统计的国内土产贸易中的粮食商品量的26亿斤。更不要说大宗稻米的长途贩运以及花生、大豆等等了。须知绝大部分小麦的贩运是不用轮船的。
表1. 河北24县小麦产量及运销县外数量统计表 单位:石
县名
产量外销量县名产量外销量
定兴 60000 15000深县
85200025000
满城 30000 25000武邑
36900012000
容城 51000 1000任县25000 5000
河间3000000500000广宗 259000070000
大城 927000 21000衡水
42100021000
文安1800000800000冀县9000030000
新镇 55000 5000新河
105000 5000
获鹿2150000
1300000柏乡
74200042000
平山 80000 30000高邑
11700017000
深泽 45200 8000南乐3600018000
平乡 26000 6000磁县
206000 6000
/产量
13750200
总计\外销量 2968000
外销占产量比例21.6%
资料来源:河北省实业厅视察处编《河北省工商统计》(1992年度):“河北省大宗出产商品分县一览表”。
20世纪初以来,华北棉花生产商品化步伐较快,棉花市场迅速扩大。晋、冀、鲁三省的棉花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呈大幅度增长的态势。据河北1929年度工商统计资料,宝坻、滦县、东光等58个县共运销县外棉花达183,425,698斤,合183万余担。如同小麦一样,这些棉花销于县外,即意味着进入长距离贸易。这同样可从其贸易方向上得到证明,其中销于当地及附近县者不到7,500担,即还不到总外销量的0.5%。各县外销的棉花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进入天津市场。据日本学者研究,1925年进入天津市场的河北棉花达1,041,627担,价值达37,947,839元。1929 年可能比1925年多些,那么扣除进入天津市场的数字,剩余数姑且算作70万担左右,一般估计可能被河北当地的纱厂吸纳一部分,如保定、宝坻、滦县、石家庄以及河南安阳广益纱厂等,其余几十万担主要被各县用于手工纺纱、网制棉胎等。按以上产量、销量计算,河北1929年棉花长距离贸易量已占产量的68.6%。所以棉花的商品率是农产品中最高的一种。据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农业处关于华北农村棉花生产的调查,棉花商品率达90%,须知这已是在多年的战争之后,可证二三十年代有关棉花商品率的统计是有充分根据的。
山东棉花30年代初的最高年产量为217万担, 此数远过许道夫所辑数据。按吴知调查,山东棉花绝大部分供本省纱厂使用,小部分输出津沪等地及国外,与天津主要为出口不同。青岛有纱厂9家(华商仅1家,其余均日商),年均用棉130万担;济南3家纱厂1935年用棉160,468 担;另外济南棉花年均南运上海、郑州等地约15万担—20万担;北运天津10万担;从青岛转口他埠及国外,每年5万担〔8〕。总计进入长距离贸易的鲁棉约有180万担。此数比山东实业志的统计为高。
本世纪初以来,中国农村的家庭手工业非但不是如传统论者所谓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侵略下破产,相反有了蓬勃发展。揭开历史的真相,人们会惊异地发现,六七十年前华北农村手工业的兴旺景象几乎可与今日乡镇企业的腾飞相比美。
山东潍县与河北高阳、宝坻并称三大土布中心,闻名中外。潍县土布确曾因洋布输入而被淘汰过,但自购入新式铁轮机传习织造方法,出品精良,销路大开。至30年代,全县皆营此业,布机达5万架, 专营手工织布者达10万人。潍县土布品质细美,与工厂出品的机织布质量相近。1934年产布10,800,000匹,占全省产量的62.95%。 该年全省产土布达17,153,999匹,价值98,521,743元。潍县土布几乎全部外销,畅销河南等十几省。除潍县外,山东土布主要产地尚有昌邑(年产100 万匹)等多县〔9〕,全省外销量至少占产量70%—80%以上是没有疑问的。 高阳土布生产情况与潍县类似,年产量最高时达550万匹; 宝坻织布区最高年产量也达480万匹。高阳、宝坻土布运销至西北、 长城口外及长江流域。现根据1929年度河北工商统计对进入长距离贸易的河北土布作一个总计:1929年香河、宝坻、高阳、定县、清苑、完县、平山、任邱、新乐、玉田、唐县等63县共输出土布18,596,259匹。上列各县年输出量均在50万匹以上。若每匹布平均以6.5元计算, 则所输出土布总值约达1.2亿元。同年这63个县共产土布24,159,419匹, 则河北土布进入长距离贸易的外销率达77%。若与工厂机织布相比较可清楚地看出土布的地位,山东有现代形式纺织工厂257家,而产布仅450,717匹,价值1,839,271元。大概产值仅相当土布的2%。
笔者在这里还要提到一个几乎从未被经济史家所注意的农民手工产品,那就是山西的手工产煤。关于山西煤的产量有三个统计数字。山西实业志记载,1934年山西有采煤企业1,425家,年产量302万吨。但该志称:“尚有散处各地之小煤窑,时开时歇无法调查者,为数当属不少。”〔10〕而太原经济建设委员会统计处披露的数字表明,1933年全省采煤企业为1,954家,显见山西实业志的统计可能有遗漏。 因此作者暂以《山西年鉴》(1933)为依据。据该年鉴统计,山西有采煤企业共1,560家,年产煤4,127,305吨;其中机器采煤业仅66家,年产煤1,258,605吨,则各县土窑的产量为2,868,700吨;全省外销煤为3,840,892吨,即使机器采煤的产量全部外销,各县1,494 家小煤窑所产煤的外销量也达2,582,287吨,占其土窑总产量的90%, 而土窑产煤量占全省总产量的69.5%;近1,500家小煤窑平均每家工人不过10人左右, 但就是这样的小煤窑却创造了两倍于机器采煤业的产量和销售量。全省煤矿工人27,000余人,仅平定、大同、太原三家大企业就占去了万余名工人。
以上是华北地区农村商品长距离贸易的有代表性的或主要的情况。从根本上说来,进入长距离贸易的商品是农村产品中的剩余部分或完全为市场生产的产品,是农村为支持城市文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帕金斯估计,19世纪末中国农村产品进入长距离贸易的商品量仅占总产量的百分之七八〔11〕。但如前文研究,到本世纪30年代,华北三省小麦的长距离贸易量已达总产量的15%—25%;三省的棉花进入长距离贸易量更达总产量的60%至90%。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在20世纪前期工业与城市经济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美国学者罗斯基(Thomas Ranski )认为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同时期的日本,似乎也不能说是耸人听闻之谈。所以,说中国农业直到本世纪中叶仍只是一个“糊口”农业(黄宗智语),既不符合历史实际,也无法对历史的发展作出解释。
(二)地方农村市场贸易
农村县以下(包括县城)的集市贸易可称为地方小市场贸易,或者可用施坚雅的概念,将县以下的集市分为中心市场(包括县、大镇)、中介市场(镇)、村集市场(村集)。施氏认为中国农民的活动范围“并不是一个狭窄的村落,而是一个基层集市所及的整个地区”,可称为“基层市场共同体”〔12〕。
论者往往轻视农村小市场的贸易,认为那不过是“余缺调剂”、“品种调剂”,具有“补充自然经济的性质”〔13〕。这一说法影响颇大,常常被国内学者引用。但这一说法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首先,中国农业不是大农场生产制,或者也可用别人的话来说还未达到规模经营,因此产地市场(或初级市场)极为重要。长距离贸易的起点在产地的初级市场,在地方小市场。其次,长距离贸易从城市所换回的农民生活必需品、生产资料品等都必须经过农村集市的贸易交换才能最后进入农民的消费。因此从这一点说,农村小市场又是工业品长距离贸易的终点,是工业品的消费市场。最后的重要一点是,地方市场同时兼具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功能,它为农民提供了负债经营的方便条件。
本文研究农村小市场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先研究一些典型,二是研究农村交易场所即集镇数量的增长,以佐证农村市场的发展。
这两个典型是河北定县和山西榆次县。
定县可能是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有关民国时期县一级经济活动资料最为完整的县份之一。现笔者根据这些资料编制成下表。
表2. 定县市场商品销售量和人均购买力(1933年)单位:元
商品名称在本县出售的商品值人均购买力
县外输入品 3192777
粮食2190708
1930年全县人口397150
棉花 462223
牧畜 630356
猪
531124
手工业品2792476
总计979966424.7
资料来源:①手工业品销售额根据张世文著《定县手工业》资料计算。
②总计数和人均购买力系笔者自己计算。
③其余数据见李景汉等编《定县经济一部分报告书》,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1934年10月印行,第2、13、143、146—148页。
在本县市场上销售的商品总值即是该县市场容量,即居民的购买需求,即按一次性交易计算的市场商品的价值量。此数再加上输出县外商品的价值(3,157,072元)即是进出定县市场的商品流量。 需说明的是,这里的人口数是1930年的数字,手工业品销售值是1931年的数据,其余都是1933年的数据。
山西榆次县为山西省第一出口大县,年出口值达500万元, 而人口仅137,289。原因是该县有包括晋华纱厂在内的3家较大工厂,棉纱出口占有相当大比重,但该厂原料供应与产品销售等都与该县关系不大,因此笔者在计算该县商品量时都未将该3家工厂的销售计入在内。 该县全县商业营业额为4,315,925元,从资料细目上看,此数已将进口货值170多万元的绝大部分包括在内,因此,实际上本地市场消化的商品量值约在230万元左右。另外榆次尚有各种小手工业35家, 每家销售额不过几千元,总计约8万多元。榆次还有一家小电厂, 其电力销售可计入本县市场商品量中的不过为500余商家、机关用电及170多户居民用电,估计销售额最多不过10万元。总计商品值约为248万元,人均购买力约18.1 元〔14〕。
农村市场上的人均购买力只是部分地反映了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情况,反映了农民对市场依赖的程度和农村经济市场化的程度,反映了农村的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情况。例如很多地方调查表明,农民的生活费每月只需3元—4元,甚至2元—3元,则像上述榆次县和定县年人均18元—22元的购买力,说明农民的生活资料至少有45%以上需来自市场。这只是按一次性交易计算,如一年中有多次交易,再加上借贷等情况在内,则农民对市场的依赖程度更大。因此笔者的研究无意中,或可说是巧合,支持了卜凯(John Buck)的观点。卜凯调查了1921 —1925年间的中国北部和中东部的14个县2,866 个家庭农场农产品家庭自用和出售部分的百分比,其中中国北部农产品出售部分平均占产量的43.5%〔15〕。
无论怎样说,本世纪前期晋冀鲁各省的农村地方市场肯定是有较大发展,前文所研究的两个典型市场的历史资料中均有对清末情况的追溯,可见一斑。如前引山西实业志关于榆次县一节称“榆次在正太铁路未开之前,生活简单,商业仅有钱业、典当、棉、布、油、酒、米、面等数十家,散处城乡”,而到20年代,“城关商号约近400家”, 其间历时不过20年。最好的研究则是从农村集镇数量的增长来证明农村市场的发展程度。作者曾研究得知19世纪末山东有农村镇集(包括县城、镇和村集)2,150个,河北有镇集1,785个;而到20世纪30年代,山东已有镇集7,272个(106县),河北有镇集3,066个(河北当时有130个县,其中15个县的镇集数字是估算数),分别比40年前增加了238%和71.8%。 另外山西省104个县在30年代已有镇集1,326个(唯没有查到清末数字)。可见华北三省农村集镇发展的速度十分惊人。三省农村镇集平均每个吸附人口6,634人。 在山东省一般平均每七八个自然村就有一个小的集镇〔16〕。笔者的研究结果也可从其他学者的研究中得到支持。例如日本学者石源润的研究,以及从翰香《近代冀鲁豫乡村》一书的研究(该书所统计的集镇仅为“重要市镇”或“工商业市镇”)。
总体上来说,通过上述长距离贸易和地方市场的研究,我们已可清楚地看到本世纪前期(抗战爆发截止),华北的农村商品市场已有相当大规模的扩大。20世纪上半叶华北地区集镇的蓬勃发展与长距离贸易商品量的扩大一样,证明这一历史时期华北的农村经济已经具备了一般形态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也证明农业生产力达到相当水平。反之也说明正是由于市场的作用,才使华北地区的农村经济进入资本主义轨道,尽管在农业生产领域很多地方仍呈现自然经济的状态。这种情况其实同许多国家农业现代化早期阶段的发展情况相一致,即都是先开始农业商业化,商业资本主义率先打进农村,市场成为控制、指挥农村生产的龙头,农业生产惟市场需求马首是瞻,自发地调整种植业及其它各业生产结构,专业化生产日益扩大,在商品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市场系统日益完备、成熟。
二、华北地区的农村资本市场
关于近代农村资本市场研究,这在国内经济史学界还是一个全新的题目,因为几乎没有人去认真研究这一问题,如果有的话,也只是批判“农村高利贷”、“农村资金枯竭”(恕不引证,因为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太多了。事实上很多人根本不认为近代中国有资本市场)。但是值得人们冷静思考的是,如果没有一个相应的相当程度的资本市场的话,农村商品生产、商品市场何以会如此迅速地扩大呢?
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是互动的,互为基础的,商品(包括劳务)与货币是对流的。从上文长距离贸易和地方市场贸易可以看到,商品输出了,货币就回来了。农民收入被用以维持农村劳动力的生存、再生新的劳动力和扩大农村再生产,于是货币收入又变成新的资本。一个中心市场的含义实质上是双重的,即它既是一个商品市场,又是一个资本市场。
农民的收入不仅来自商品,还有一个重要的来源是劳动力输出,下文将研究。也有外来资金加入农村,这样农村借贷规模就扩大了。外来资本主要有如下三项:一是外国资本;二是金融资本,包括信用社(信用社并不单是农民的钱,外部组织投入了巨大的底本,例如华洋义赈会)、银行;三是私人集资。下面分述各种来源。
在本世纪前期,华北地区曾经历了移民史上最壮观的一幕——“下关东”。上千万移民每年将其收入的一小部分寄回原籍,就形成了一笔巨大的外来汇款。据徐慕韩研究:“每年山东农民由东北银行、汇款庄、邮局等汇兑机关汇至山东农村之款,可统计者在5,000万元以上。 农民由东北回鲁自行带回者,尚不在内。东北汇款,实占山东农村收入之最大数目。据调查,大县每年收入皆在一二百万,小县亦在二三十万。”〔17〕如按此数计算,20年间,山东、河北的农村获得高达10亿元以上的汇款。笔者经过仔细分析,认为这一数字是有根据的。清末以来,山东、河北农民闯关东者可达2,000万之众,此数可从海关10 年报告(1922—1931)以及最近张景岳等人的研究中得到证实〔18〕。10亿元汇款数的估计决不为高。其中受益最大者为山东农村。这是华北农村资本市场一笔巨大的资金来源,但长久以来却为学者所忽视。
劳务收入仍是农民自己挣的钱。外部资金进入农村占第一位的则是外国资本。这种情况最常见于烟草生产、棉花种植和西部的土地开发。如1935年英美烟草公司在潍县农村收烟5,700多万磅,价值300多万元;天主教堂在宁夏、绥远、察哈尔等地广占土地垦田,动辄数十万亩。其它如日本棉商、烟草商在山东、河北农村的投资案例,所在多有。
30年代,银行对华北的农贷极少,笔者估计不过1,000万元左右,但农村合作社有时可从其它渠道获得贷款,如从华洋义赈会手中。华洋义赈会十几年中共向中国农村投入了5,000万元的巨款〔19〕, 但大部分系赈灾。河北是华洋会活动最早、最重要的地区。
资金流入农村的另一条渠道是私人投资。一般地,中小地主主要活动在农村或集镇,而大地主则往往在城市里兼经商或从政,其中很多即是“不在籍”地主。这些人往往在城市中赚了钱之后再投资于土地。
农民借贷问题是农村资本市场的中心问题。下面根据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1934年在《农情报告》中所发表的两次关于农贷问题的调查数据编制成表,然后再加以分析。
农民贷款主要来自于私人(30年代初以后,合作社贷款在农贷中的比例逐渐上升),当然其中多数是地主、富农、商人,贷款又是高利贷。因此许多人认为这根本不是资本融通,而是“残酷剥削”。我认为对这个问题也要两方面看。一方面,剥削是肯定存在的,这主要是超越经济、法律之上的政治、宗族等特权的存在所造成的,以及在自然灾害、战争等特殊环境下产生的。Kenneth pomeranz《地方利益探究:1900—1937年山东资本市场中的政治权力和地区差异》(1988)一文强调了地方政府权力对资本流通的阻碍作用。但最根本的问题是资本稀缺,不看到这一点,从价值规律的供求平衡观点而言,很难解释得通农村高利贷为何会长期盛行。这一点从世界经济发展史上考察可说是一目了然,欧洲很多国家在资本主义初期阶段,利率都很高,随着经济发展,利率逐渐降低,这是很自然的。我国农村至今也广泛存在私人借贷和高利贷的现象,私人贷款年利率20%—30%。所以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另一方面,即农村资本需求的潜力,这就是所说的“隐形资本”。由于市场制度的不健全和外部环境的不良,使资本不得不处于“隐形”状态,但它也预示了资本扩张的潜力和前景。
表3. 河北、山东、山西三省农民借贷状况统计
各省所占百分比河北山东山西
分 类
农家负债占总 借钱 51% 46% 61%
农户比率借粮 33% 36% 40%
银行3.3%6.1%4.9%
借贷来源 合作社 11.9%8.4%1.3%
典当、钱庄、商店
29.6%
35.2%
43.4%
私人
55.2%
51.3%* 50.4%
10%—20%6.6%5.4%2.6%
借钱年利率20%—40%
90.5%
72.7%
57.6%
40%以上 2.9%
21.9%
39.8%
借粮月利率3.3%3.5% 6%
6个月以下 10.4%
18.7%
39.4%
借贷期限 6个月至1年84.6%
74.1%
51.2%
1年以上
5%7.2%9.4%
* 原文数有误,已改正。
我们上面是从借钱的角度去考察,如果反过来从农民存钱的角度考察也可以证明“隐形”资本的存在。1934年11期的《农情报告》上有“储蓄机关”一栏的统计,颇为发人深思。根据这栏统计,农民余钱都存在下列地方:银行占农民存款总额的0.4%;合作社占0.7%;典当占7.4%;钱庄占1.1%;商店占25.6%;私人占61.2%;其他占3.6%。农民储蓄60%以上存放于私人手中,这说明私人信用之强固,这是中国有异于西方的特点。
下面我们对华北农村资本市场的运行方式作一考察。
银行农贷一般是通过合作社进行,或是通过农业仓库。
钱庄、当铺、商店等放贷一般也都有成章可循,比较起来,以河北最为成熟。二三十年代,河北各县通行“银市”制度。一般较大镇集均定期举行银市。银市活动的方法是:凡属本镇集范围内的大小工商业户,均有权参加银市,个人也可参加银市,互相调济资金周转,开展借贷活动。对放贷数量和利息,由放贷双方协商议定。银市早晨由各商业户派员参加,届时开盘交易。放款业户口头宣布放款数目和利息比例,贷款业户也可口头公布贷款数目和付息比例。双方经过讨价还价,达成协议,由银市会计立契,双方签字,即为成交,现金当场点清。这就是合法手续,如今后有纠纷,由银市负责。二三十年代河北银市的活动充分反映了当时市场经济的自由程度。银市是自发形成的,一般秩序由商会负责,有的银市还有固定的组织。银市的职能类似现在的公证人和银行。银市放款也分信用与抵押两种,全凭双方当场协商敲定。现以滦县稻地镇银市放款大户玉盛德钱粮行为例作一说明。玉盛德钱粮行大股东系该镇大地主耿似兰,有地10万亩,玉盛德常年在银市放贷在10万元上下,年获息3万元—4万元之巨。它的经营方式以吸收农村的游资为主。当时当地的地主、富农大都把余钱存入玉盛德钱粮行,因为它财大气粗,可靠系数高。存入每月利息5%—6%,最高10%。玉盛德将游资集中起来到银市放款,月息12%—15%,甚至20%,一进一出,获利甚丰。农民遇有红白喜事、或翻盖房屋等而手中无钱,只得到银市借钱,将粮食等实物押给玉盛德而取得贷款,按实物的最近行市做价,贷给实物价值的60%的现金〔20〕。
据1929年河北工商统计,在34个有银市交易活动的县中,每日举行银市的有9个县,隔日举行一次的有7个县。一般每日有银市的县镇都是商业比较繁荣的地方。例如清苑县每日举行银市,民间自由借贷非常活跃,是因其商业繁荣,1937年该县有商号3,258家,庙会30余处, 集市61个(1934年数),粮商100多户,仅县城23家粮栈日成交量就达200担—400担〔21〕。
私人之间的自由借贷是一种至今仍广泛流行于我国农村的古老而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私人借贷的类别虽然纷纭复杂,但据通县、定县、滦县、山西屯留、山东邹平等地的资料,仍可概括出私人借贷大致有以下三种方式:
一是印子钱。放印子钱是一种短期、小额、整借零还、逐日还本付息的私人信用贷款。所谓短期,是指一般不超过两个月,短的只有几天。小额是指一般只有几元,甚至几十枚铜元,多者不过几十元。印子钱特点是整借零还,但利率很高,借100枚铜元,60天为期,每天还二枚 ,60天期满共还120枚,两个月期利率即为20%,年利则达120%。但印子钱整借零还的特点又使一些以按日计工资的工人(每日领取当日工资)不以为苦,如上例借100枚,每日还二枚。印子钱因额小, 且逐日还债风险系数小,因此一般不用抵押,是一种信用放款,每日归还一定金额后,即在底账上按一手印,故称“印子钱”。印子钱特点是灵活。有的放债者甚至带着钱袋在集市上游动,有买货者临时缺钱,即可当场借款。当然放债者也要看其资信情况,或所买之货是否可转手获利。
二是私人债。所谓私人债,与印子钱相较,不过是金额大些,整借整还,手续严格,既有信用放款,也有抵押放款。作抵押者,一般是地契、房契等不动产。信用放款则须有非常可靠且有实力的担保人。私人债如有不动产作抵押,往往可借得数额很大(例如1,000元)的款。 但私人债例须按月付息,到期还本。农村有以放债为专门生意、且经营数额巨大的,则在营业上还有帮手。上面所述,虽是私人之间的借贷行为,但都属于民间的正式借贷,都立有正式合同,保人须负有连带责任,有的保人称为代还保,即到期不还,保人须代为偿还,有的称铺保水印。法律上承认这种民间契约的有效性。但30年代初国民政府曾颁布法令,放贷月息最高不得超过2%,因而有些契约明面符合这种规定, 实则口头另有约定。亲友之间的相互帮助、不立契约也是一种民间融资行为,但尚不在上述之列。
三是钱会(合会)。钱会是中国民间的一种有悠久历史传统的自发的集资行为。总的来说,钱会的目的是入会者轮流为每个会员集资,只不过第一次使用钱者一定为发起人(会首)。各种名称的钱会的主要区别在于第2期以后使用集资款的顺序如何安排。 利用摇骰子的办法来确定自第2期以后使用钱顺序的称为摇会;通过协商, 按各人使用钱的急缓来确定以后使用钱顺序的称为轮会(摊会);通过投标方式来确定以后使用钱顺序的称为标会等等。各地农村钱会的名称复杂各异,不下千百种,但目的宗旨基本都是一样。每会参加者一般只有几人,最多不会超过二三十人,否则集资的期限会太长。每一个会组成后,一般是每月举行一次会,也有一年一次(很少)。每会集资数目大家事先商定好,例如数目是1,000元,则每期每个使用会款的会员都同样得到这1,000元,区别在于先使用会款者为借入方,后使用会款者为贷出方,越先使用会款的会员付利息越高,最后得会款者实际上是一位储蓄者,他得到本钱和全部利息(别人付给他的利息)。所以钱会虽是一种民间组织,但它在会款的安排上非常科学,原则就是先得会者每期要多出钱,按时间顺序依次降低。如一个会10人,每期一个月,一共10个月期限,集资款为1,000元,第1期得会的会首每期要纳145元,第2期得会的每期要纳135元,每会低减10元,最后得会的每期纳55元。结果是会首最先使用会 款1,000元,但他每期纳145元,10个月共出会金1,450元,多出450元,就是他缴的利息;末会共出会金550元,得到1,000元的会款,多得的450元即是他获得的利息。这样无论先使用钱、后使用钱,大家利益相等 。但是如果有的人争于用钱,他往往就会参加标会。标会是通过投标的办法确定使用钱的先后,而投标的结果往往会抬高使用钱的利息。但从市场经济的观点而言,标会也不是没有它的好处,起码它可救人之急。
钱会是一种民间组织,不是经政府允许组织的,但它在中国农村广为流行,是农村融资的一条重要渠道,值得人们认真加以研究。
三、结论
通过上述对农产品长距离贸易、地方农村市场贸易和资本市场的研究,可以充分证明,20世纪前半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市场有很大发展,其扩大程度远远超出前人已作出的论断,如华北一地进入长距离贸易的小麦的商品量就已超过吴承明用40个埠的资料所算出的全国粮食长距离贸易量;并且这种发展方向毫无疑问是朝向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黄宗智先生所说的“非资本主义趋向”。从农村商品交易的自由程度、特别是资本市场融通的自由程度、劳动力大规模迁移的自由程度、外国资本深入农村的自由程度、市场的自治管理程度等等,都可使敢于正视事实而不仅仅重视政治观念的人们毫不犹豫地作出这样的判断。当然市场被阻碍的情形是存在的,除陈规陋习外,这种阻碍主要还是来自于经济之外的因素,主要是军阀战争,Kenneth Pomeranz所说的地方政府对资本流通的阻碍也应属这种范畴之内。市场活跃必然带来农民收入的增加,据满铁调查资料,丰润县米厂村、平谷县大北关村和昌黎县的良各庄村在1936年底的储蓄分别比年初增加了4,705元、5,400元和2,934元;这三个村庄的储蓄率分别为29.4%、19.1%和14%〔22〕;李景汉在30年代初调查定县34户农家,其中年均每户收入在350元及350元以上的有9户(每户均7.7人),户均收入在250元—349.9元的有14户(人均6.1人),收入在250元以下的有11户(均4.6人)。 如以中等水平来看,人均年收入为50元,按货币购买力折算,至少相当今天人民币1,000元。应当说收入是不算低的。农民收入的增加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华北农村市场的发展。
华北农村经济与市场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形成,而不是哪一个政府的作用。由于中国农业分散经营的特点,也由于自清末一直到抗战爆发前中央集权的软弱,政府对农村经济的干预作用是很小的,甚至地方上的小规模的治水及农地灌溉系统工程等,地方政府也无力过问。笔者曾查阅山西年鉴,发现在30年代有100 多处农田灌溉工程均是农民自发联合起来集资所建。政府对市场的管理几乎只有收税一项,如定县对集市贸易共征收8种名目的交易税(牙税), 其它就无所作为了。但是农村的市场经济却在这种条件下自发地获得空前发展,这证明市场经济的活力。农村市场不仅和全国市场联为一体,也和国际市场息息相通。中国的棉、丝、茶的价格要取决于国际市场的价格,这是学者们早就承认的,只不过多是从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角度去看待这一现象。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不如此就不是市场经济,这说明当时的中国市场,包括农村市场,已卷入到国际市场当中。事实上内地农村市场的价格也常与沿海口岸的价格共相浮动,交通便利的地方(或者说多数地方)与沿海价格相差甚微,价格的趋同性证明了商品自由交换的畅通。仅仅20年间山东、河北近千万移民进入东北,而并无任何政府力量加以组织,这充分证明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这为农村创造了巨额收入。洋货、洋商、外资可自由进入农村,以往人们只是批判它的“侵略”性,却未看到它为农村创造就业与收入的机会的一面。
华北农村经济发展的另一主要原因是参与市场的农民都是享有完全独立自主产权和经营权的生产者(包括租佃者,他们大都享有永租或永佃权)。当时的农民,没有任何人去管理他们,他们完全是依据市场需求和自身的消费需要,自主决策,自己决定要种什么庄稼、做什么副业。二三十年代兴起的农民合作社是与50年代的合作社性质完全不同的。前者仍是个人私有制,土地、劳力、资本仍是自己的,生产也是自己进行,所谓合作只是在生产或流通的某个环节上,如信用社是指金融合作,运销合作社仅是在销售上合作等,这与今天日本农业上所通行的各种组合大体相似。这就证明国外二元论否认小农的生产力、甚至认为农村过剩人口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是没有实践基础的,起码在中国是这样。舒尔茨认为小农也是理性的小农,效率很高,能有效利用资源配置,从事均衡生产;传统小农经济将由均衡走向不均衡,经过现代化达到新的均衡。他说:“一旦有了投资机会和有效刺激,农民将会点石成金。”〔23〕半个多世纪前华北农村的经历为舒尔茨的理论提供了历史证明。农民的分散经营与现代化的供销体系的相结合可为农村生产创造高效率的范例,弥补非规模经营的不足。本文的研究以华北农村市场的蓬勃发展对黄宗智先生的“过密化”结论提出质疑。
返诸现实,当在农村实行强迫计划经济和追求所谓规模经济的大生产的时候,农村经济就走向衰落,如80年代前的30年中国农村的经历。再看粮食商品率和农民收入。按1991年统计,我国粮食商品率仅30%(五六十年代长期徘徊在百分之二十几),全国绝大部分县农民年人均收入不足千元(按1991年价格),1994年全国农民年均纯收入1,220元。 如前文研究,此数比30 年代定县的农民收入水平高出有限(定县农民30年代的生活水平,据我看属当时的中等或中等稍高点)。上述数字虽 是全国的平均数,但因华北(特别是河北)也属全国农村中等水平,因此这些数字应当是与华北农村情况相近的。这些数字充分证明市场经济应是我国农村经济的唯一取向,舍此没有出路。
我国农村在经历了十几年的改革之后,目前已显后劲不足,可能再次面临重大改革的抉择,其实质问题实际上仍是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一种既能使农民保持主体经营者积极性、又能使个体农民的生产产生规模经营的效益的制度是人们探求的目标。为此各种试点都在进行当中。我想,经济史上的创造性的探索可能会使在现实问题中陷入迷惘的人们独辟蹊径而达于豁然开朗。
注释:
〔1〕Raman Myers,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 Agriculturaldevelopment in Hopei and Shantung,1870—1949,Harvard Univ.1970,pp.123,212,288.
〔2〕黄宗智(Philip Huang ):《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72、 144、16页。
〔3〕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272页。
〔4〕《中国实业志》(山西)第4编第1章,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7年版。
〔5〕转引自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8页。
〔6〕见《中国实业志》(山东)第8编第3章,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4年版。
〔7〕陈伯庄:《小麦及面粉》,交通大学研究所经济组专刊, 第46—49页。
〔8〕吴知:《山东省棉花之生产与运销》,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报专刊,第66—69页。
〔9〕《中国实业志》(山东)第8编第2章。
〔10〕《中国实业志》(山西)第5编第1章。
〔11〕德·希·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58页。
〔12〕William 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4,1964-1965.
〔13〕前引吴承明书,第269页。
〔14〕参见《中国实业志》(山西)。
〔15〕参见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 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29页。
〔16〕慈鸿飞:《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分析》,见《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17〕徐慕韩:《山东省的农村经济概况》,见《国际贸易导报》第8卷第8号,1936年。
〔18〕见《近代中国》第3辑,1993年。
〔19〕阿瑟恩·杨格:《1927至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02页。
〔20〕见魏宏运主编《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村社会调查与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2页。
〔21〕《清苑县志》,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334页。
〔22〕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L.No.4,Dec.,1990,p.824.
〔23〕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