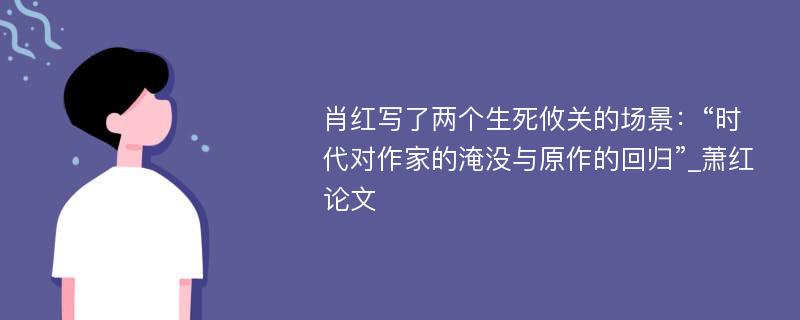
萧红写了两部生死场——作家被时代浸袭与原态写作的回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写了论文,两部论文,生死论文,作家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1年,是作家萧红诞辰100周年,如果她能活到今天,恰好是一位百岁老人。作为作家萧红的一生不停歇地抗争命运,并节节败退。作为作家,这一结局几乎应和重演了她作品的宿命主题。
1935年的上海,在鲁迅的奔波推动下,萧红的《生死场》在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叶紫的《丰收》之后作为“奴隶丛书”的第三本出版,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一套经过名家策划的丛书,同时也是一套“非法出版物”。出版者容光书店,是一个被杜撰的出版机构(参见林贤治《漂泊者萧红》)。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左翼文学的倾向,没有日本人踏入中国东北疆土的背景与萧红、萧军的流亡身份,鲁迅大概不会有兴趣特殊关照他们,更不要说为他们的书作序,并共同谋划“奴隶丛书”的结集出版。时隔6年,到了1941年,鲁迅已离世,《呼兰河传》在香港出版,这个时候的萧红已经久病。很快,日本人占领香港岛,萧红在日军入侵当夜病逝于香港玛丽医院。
《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一首一尾,作为萧红的成名作和落幕作,是萧红短暂生命中最重要的两部作品,它们都以位于东北亚冷寒凛冽之地的呼兰为母题背景,这两部作品,可以称为两部生死场。出版周期相隔六年的两部作品,作为作家个性风格和作家生存年代的关联研究也是很好的案例。
一、第一个生死场
《生死场》动笔在1933年的哈尔滨,完成在1934年的青岛。写作期间,萧红不断受到寒冷饥饿病痛动荡迁徙的侵扰。从不同选本的萧红传记中可以看到,《生死场》的风格形成受到当时聚拢在萧红身边的萧军,舒群等青年作家的影响。几乎在萧红写作的同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也在动笔,其时正逢日本人占领了中国东北,民意沸腾。这一重大事变激荡着文学青年的内心情绪,也自然地渗透到《生死场》的写作中。假设没有日本人在中国东北的出现,萧红写出来的一定是另一部《生死场》。
《生死场》取材于中国东北空旷辽阔的大地,全书只有8万字。作为长篇小说篇幅相当短小,但作家寄予其中的“野心”并不小,全书视野开阔,人物众多,有动作有对话的人物有29个,叙事跨度超过10年,布局从乡村扩展到城市。全书散点似的结构,明显透露出这位文学青年的“企图”:她要展示的是一幅辽阔的、多角度的全景画卷,她要书写那块土地上不同人物的不同命运,包括牲畜们的不同的生不同的死,书写他们无时不在的抗争。
读过《生死场》,有两个突出感受:
一、这位年轻作家有敏锐的捕捉生活细微处的能力。
她的着眼点总是那块土地上的最弱小者,包括女人、孩子、病残者和动物:罗圈腿、王婆、金枝、菱花奶奶、老马、羊、鸡鸭……无论是人还是牲畜,都在生死之间茫然地挣扎,生动活亮的生命们最终只能屈从于活着这一暗淡的本能。
《生死场》前半部,叙述节奏幽静、闲适。其节奏与那块土地本身的基调相当吻合,一切生命都被自然力量无形地推动,而一旦被书写于纸上,它们都成为作家悲悯的对象。萧红最擅长的是站在弱者一边,书写孱弱。这一特征在她后来的作品中越来越鲜明。而对于中国北方乡间农民的另一些生命状态,那些强势者们:乡村中的男人、恶人、入侵者日本人,萧红的笔墨不多。
二、小说的后部分,节奏大变。
10年时光被一笔带过。萧红似乎急于进入一种更切近的时态,进入她情绪激越的当下。小说中出现了突然闯入者:“日本旗子在山冈临时军营前振荡地响着”,这一以象征意味出现的形象急促突兀地强行插入,使得全书的前后两个部分处于不均衡的状态,前面是缓慢的,后面是急切的。前面是清晰可见的,后面是恍惚不定的。作为人物,无论入侵者“日本子”,还是反抗入侵的李青山、为抗日献身的王婆女儿和儿子,都面目模糊,概念人化,明显缺少鲜活的具体的实态,这样也就缺乏了对情节自然有效的推动力,他们的出现使得全书的前后两个部分处于失衡状态。
在《生死场》的后半部,萧红依靠抒情性的描述展示了一段急促的变奏。显然,她期待这部作品背负抗日史诗的使命,于是,这部处女作由于它富有的时代性“野心”而呈现出了另类变形的面貌,也泄露了一个文学青年急于跟进时代而脱离了原态写作的心态。
原态写作,即一个作家对自己能够把握的领域、积累、基调的控制力,即对于写作内存的暗中遵循。如果一位作家出现了偏离,而执意予某种观念或时尚,无论这观念时尚多么崇高或动人,他都会出离了自己的原态,陷入力不从心的写作境况中。
最松弛的写作,一定是原态的,也一定是最佳的。自由松弛,毫无被动,毫无理念的牵引与强加,作家才可能自如地释放自己的动人之处写作理念。也许,让我们得以谅解的是,《生死场》动笔那一年,萧红只有22岁,接近今天的“九零后”,还是个初写者。
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人们对于萧红的关注始终持续。2011年初,通过“当当购书”网络搜索可以看到,《呼兰河传》有21种不同版本同时在售,《生死场》有11个版本,如此出版密度,很多中外经典作家都难以达到。而在萧红写作的年代,知晓这位东北流亡作家的应当只限于少数人。显然,今天人们对萧红的关注超过了她在世的时代,除了对作家的钟爱之外,还混淆着人们对于悲剧命运所怀有的特殊兴趣,这一兴趣在今天似乎还在衍变升级成为某种精神上的消费观念,这无疑正无意地诋毁淡化着萧红的文本本身,因而对于这位作家作品个性化的细读和由此引发创作问题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二、第二个生死场
我说的第二部“生死场”,是萧红的落幕作《呼兰河传》。
从《生死场》面世后的1935年,一直到进入1940年代,从情感到写作到战事爆发,萧红经历了多重磨难。仅仅1937年到1940年的三年间,她就经上海到武汉到山西临汾到陕西西安,再折回武汉到重庆,最后落脚香港。《呼兰河传》正是在这一路的流落撤离和情感变故中完成的。《呼兰河传》1941年成书出版,从写作时间上看,它和日本人的入侵中国几乎同步,而整本小说的内容完全自成风格,孑然独立于步步紧逼的时世事态,成为一部纯小说。
《呼兰河传》的结构和节奏都不同于《生死场》。它始终舒缓、清晰。人物沉实、生动。《生死场》是散点印象式的,《呼兰河传》是线性写实的。依旧是关照最弱小的个体,而非集体群像,后者更为个人化,完全抛离了动荡年代的政治军事危难的直露笼罩。《生死场》是被嫁接了时代母题的写作,《呼兰河传》是原态的、放弃了非个人的理念、只听凭于作家内心的写作。
《呼兰河传》同样不长,人们习惯称它小说,我看它更像一部大散文。不知道把它划定为小说,是否与上世纪30年代萧红和好友聂绀弩的一段对话有关。她曾说过:各样的人有各样的小说。
写作《呼兰河传》时的萧红背井离乡已经多年。在1930年被父亲宣布开除族谱之后,她离开家乡再未回头。浓厚的思乡情结使得这部小说有了更舒缓的、老人般的节奏,从开阔无垠的土地到小镇上的风俗,从四季的转换到具体人物出现,始终贯穿着自如松弛的文风。在只属于她的那种持续着的涓涓细流般的语感中,没有突然的生硬闯入的“加塞”者,没有个人记忆以外的闯入者跳出来粗暴地说话。写作者的情绪成为唯一的推动,再没有任何外来的观念扰乱思绪的透明和清晰,这使得萧红的原态写作风格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对于她记忆中那块土地上的生和死,她都写得情感更深厚,人物更透彻、节奏更从容。
恢复了原态的写作,展现出来的才是真正的“萧红味儿”。支撑了《呼兰河传》的,是她被茫茫大平原浸泡出来的灰暗而灵跳的内心。像在梦中忽然飞临到故乡平原上空的一只候鸟,萧红带领读者俯瞰了曾经属于她的大地、小城、四季风俗、市井生活、幼年的自己、祖父、团圆媳妇、有二伯、冯歪嘴……所有这些,都自然而然,依仗他们的生命本能生活着、抗争着……而所有的抗争又都是无果的、无谓的。这一切和《生死场》的前半部多么相像。
发生在同一土地上的关于生和死的故事,同样写在逃亡和病痛中,都经历着内心的困扰纠结,都缺少应有的安宁,都深藏着作家的内在敏感、细微和对弱者的悲悯之心——不同的是,与写作《生死场》相比,六年之后的萧红更知道自己要写什么和能写什么。
短短六年间,萧红看清了“人间生死场”的本质:生就生,死就死,一切只有顺从,这就是人所能做的全部。也正是这种看透,使《呼兰河传》放弃了一切“野心”。在这本思乡之作中,萧红找到了对于生和死更有穿透力、更可感受触摸的惊跳描述和灵性感悟。作为一个大动荡时代中的弱者,萧红只有停留在她习熟掌控的文字语感间,凝视着她寄以浓深情感的弱者群体的时候,才能从中获得博大土地上生灵们本该拥有的自尊、自得、自负,随之找寻到她可寄存的精神家园。
即使是最松弛的原态写作,作家也不能完全抽离宏大的时代背景。相反,越是松弛,时代的印迹越是暗藏在全部的文字背后。正是战火的步步紧逼和流民般的迁徙,如同笼罩在萧红头顶模糊又强有力的阴影,才把敏感、脆弱的萧红一步步逼向自己的内心,时代以潜在的形态迫使她不断涌起强烈的“找寻家园”的祈愿。只有这时,无边的生命磨难和纠结,才脱离了具体概念,成为莫名的动力,渗透到萧红对那块大地的亲密的写作之中,才有了得以跨越时代局限的,有关生和死的著作《呼兰河传》。
三、每个作家都要挣脱时代
人们常常会拿卡夫卡日记说话,从他的“战争爆发,下午游泳”,看到作家的完全游离独立豁达于现实。可谁又拿得出确切的实证,说明战事对卡夫卡的内心没产生丝毫影响。谁能证实,记下那行简短日记的同时,卡夫卡的内心没感到格外的沉重和阴郁。或者,卡夫卡自有的濒临绝境感和战事的突降恰恰完全吻合,人与事英雄所见,惺惺相惜,身边惨烈的战事恰好契合了他内心晦暗低郁的基调。
任何人都不能选择他生命寄存的时代,对于身后宏大的背景,甚至丝毫无力抗拒。这样的挣扎境遇,离我们并没有多远,与萧红同年代的,就有郭沫若或沈从文,还有她身边的作家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聂绀弩……个个都可以充当最好的现身说法者。
借力,可能是一个真正作家超越时代最好的方式。以萧红为例,她遭遇了强加的婚姻、父权夫权的绝对霸虐、离乡、流亡、病痛、情感纠葛、战乱流亡……所有这些,超负荷地合力压抑着她,同时也塑造着她。从一切苦难中获得超越的力量,凝结成自己作品的本真品质,这是每一个写作者都能面对的美妙可能,但把这可能变成现实千般万般地不容易。是苦难与内心的合谋,协助萧红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写作者,而不是成为某一个时代的符号。
能够超越自我生存的时代的作家只能是少数的、稀有的,特别在那些风云急速变幻的年代。只有保有鲜明个性和超然底力,才能不被具体的某个时间段的关卡锁定与固留。好的作家总是从他的时代暗中汲取,而不是被他的时代强行介入,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世界,他的世界和另外那个别人的世界,既能潜在相通又截然隔绝。
东北,作为远离中原文化基源的偏僻疆土,有了作家萧红的出现,见证了微小生命个体才是人类精神传承接续的深远力量。渺小个体本身,可能孱弱敏感,但也恰恰从这孱弱敏感中,写作者获得了超越具体年代的不可见力量。一个作家的超越力有多大,在于他对自身创作内存的依仗力和对外界的挣脱力。也许作家本人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时时刻刻的挣脱,但这挣脱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并存在。这其实是生命本身自有的力,它只是不断地被磨损、被消解、被挤迫。显然,现实中这种力的解脱呈现得不多,人类文学史上更多的是无数挣脱者的累累伤痕。他是在不断的自我损伤中不断地自我生长、自我捏合。尽管这对于他的生命本身,是一个悲剧。
从萧红身上,我看到了一个作家被引导、被浸袭的文本扭曲。更看到了她的生命内力的重又复苏,并再次展现的整个过程。这过程的贯穿正是她的两部“生死场”。
四、被忽略的更多生死场
被时代扭曲的,绝不止一个萧红,更不仅限于作家。
在萧红的传记中,有过这样的记载:1930年,萧红被逐离家,再没有回到她的呼兰河,她的父亲张廷举宣布断绝父女关系,把她从族谱上开除。目前没有见到史料证明父女二人再有联系。
萧父张廷举,这位负载命运和时代双重磨难的老人,尝到了逼迫女儿出走的恶果。之后的16年中,继续领受着、扮演着被女儿命运暗中逼迫的恶果。
有资料显示,在萧红离世后的1946年,张廷举以开明绅士的身份参加东北人民代表大会,有人向他转述萧红已病逝于香港的消息,当时他面无表情。而另有资料说,张廷举老人曾叫人在张家大宅的门上张贴一副对联,以他做过县教育局长和督学的经历,对联很可能出自他手:
惜小女宣传革命粤南殁去
幸长男抗战胜利苏北归来
横批:革命家庭
1940年代末,在这幅“时尚对联”下每日进出的张廷举,比起那个曾经在十几年前把萧红赶出家门的老父亲更加难以理解。早年,张廷举的身后站着封建时代父权男权的绝对强势与纲常伦理。在那个年代,类似张父断然驱走女儿的故事并不鲜见,短短十几年过去,外力的突变和胁迫,使这个识过文读过书的“卫道士”原地转了一个180度的弯。他突然摇身一变,逢迎时事,竟然转口怜惜颂赞起夭亡于遥远异地的女儿来了。
另一个悲剧人物是萧红的弟弟张秀珂,他离开日本人占领的东北之后,留学日本。回国后进入新四军黄克诚部,上世纪40年代末曾经回到故乡呼兰河,衣锦还乡的他就住在萧红笔下的萧瑟宅院里。关于这个人物,相关文字记载惜字如金:张秀珂离乡回归部队,在50年代中期吞枪自杀身亡。
从老父亲张廷举的境遇到弟弟张秀珂的境遇,都是骨灰已经置于瓮罐,沉于华南红土中的萧红不可能写到的。只有我们后人知道,这亲情中的摇身一变与轰然夺命,都给萧红没有写出来的更新的、无尽无休的生死场添加着情节的丰富、芜杂和一声声叹息。
奋力挣扎于生死场,却浑然不觉的人永远是大多数。敏感的生命,获得了超越力的,只能是极少数。
1939年萧红在重庆说过:“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我说,真正的作家只是身体被寄存在于他那个时代的独立灵魂,他不是时代的产物,而是把他的精神产物,绵长地留给了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