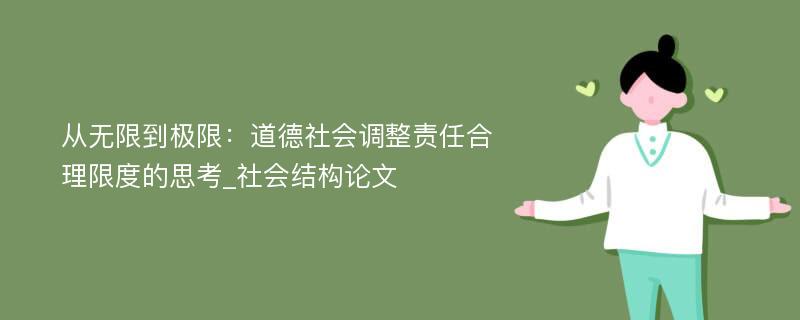
从无限走向有限:德行社会调适责任合理限度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行论文,限度论文,走向论文,社会论文,责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07)05-0120-09
古往今来,德行一直被作为避免、化解行为越轨和人生存发展困境等社会失调现象不可替代的社会调适资源,而着意加以开发。人们向来普遍认为,一个社会,人践履的德行责任愈深广,社会调适资源配置中德行资源的比重愈大,从而社会行为中德行愈密集、发达,该社会进步和文明的程度就愈高。然而,无论是从社会调适效率最大化角度来看,还是从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理念的角度来看,都要求改变这种施于德行以无限社会调适责任的传统认识。
一、德行社会调适功能的局限性与社会调适思路拓展的必要性
财富的稀缺性与生存发展对财富需要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是人行为越轨和人生存发展困境等社会失调现象的终极根源。由于该矛盾无法得到终极性消解,所以,德行是作为人通过自律来遵奉社会规范,以避免侵犯他人权利、扰乱社会秩序的越轨行为出现的社会调适资源;作为人无偿救助生存发展陷于困境者的社会调适行为,就必然是人生存发展的必要前提。但受多层面因素制约,德行的社会调适功能却有着严重局限性。
德行无偿求善的本质,决定了它在扶危济困的同时,往往会阻碍德行者自身的生存发展。①此外,德行负担必然要消耗德行者扮演其他社会角色所必需的时间、精力,降低其在社会分工协作中的绩效,影响社会分工秩序,降低资源配置效率,限制财富积聚水平的提升,从而贻误更多人的生存发展。显然,德行这种客观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德行追求的初衷。德行对人生存发展既然既具有促进作用,又具有阻滞作用,可见,其功能具有两难性特征。德行如此两难功能相互抵消的结果,未必能确保全体社会成员生存发展的总收益与总代价之差,始终有所盈余。再者,人毕竟是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矛盾统一体,而道德作为人对其有限性的特定超越形态,客观上却要求人由有限性走向无限性。这一过程客观上是对人上述固有矛盾统一属性的挑战和超越,势如逆水行舟,未必能普遍有效地获得成功。这决定了德行固然是社会调适的必要资源,但决非社会调适普遍有效的、根本性的途径。
由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有机结合而成的社会结构,作为人活动的基本前提,对人行为具有强制性约束作用。对此,马克思指出:“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线、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1]。“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较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2]社会结构对个人行为的这种前提性约束地位,决定了它对个人行为的道德属性以及个人德行社会调适功能的发挥状况,具有根本性制约作用。合理的社会结构,能够使社会资源得到最优化配置,使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的有效避免、化解所必需财富的创造效率,得到最大限度的提升;能够生成覆盖全社会的发达制度体系,来全面避免、化解行为越轨和人生存发展困境;能有效降低社会调适对德行的需求水平和人的德行负担,促进人德行能力、德行自信心和德行效率的有效提高,为人生存发展提供充分的机会和空间。相反,在缺乏合理性的社会结构中,社会资源必然难以得到优化配置,行为越轨和人生存发展困境的有效避免、化解所必需的财富的创造效率,必然处于较低水平;社会制度体系的完善程度必然较差,从而必然易诱发行为越轨和生存发展困境的出现;必然导致社会调适对德行的需要和人德行负担居高不下,阻碍人德行能力的有效提高,挫败人的德行自信心,诱发人对德行责任的恐惧感、逃避欲。社会结构对德行社会调适功能这种根本性制约作用,既决定了德行功能的开发绝不能离开对社会结构的相应治理而孤立进行,也决定了德行的社会调适功能的有效性绝不是无限度的。
除了社会结构对德行及其社会调适功能这种前提性约束之外,人德行能力的有限性,也决定了一些德行责任,必然超出人德行能力之外:其一,被救助者的生存困境过于严重,从而德行救助责任过于沉重,以至于超出了人的一般德行能力。人生存发生重大灾难时,往往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其二,人日常德行难以满足普遍存在的大面积的救助需要。由经济社会生活的结构性震荡所产生的大量失业和普遍贫困等情况的德行救助,就属于这种情况。
德行功能的上述局限性,决定了德行尽管是社会调适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但仅仅依靠德行,决非避免、化解行为越轨和生存发展困境的根本有效途径。因此,社会调适过分依赖德行,不但必然因德行代价而限制德行者的生存发展,而且必然使避免、化解行为越轨与生存困境的思路,陷入道德决定论的歧途。所以,必须降低对德行社会调适功能的过高期待,必须放弃“有困难,求道德”这种为人所普遍认同、习惯了的社会调适的传统思路,而去探求解决问题的根本有效路径。
二、社会调适路径的根本转换与惟德行主义调适路径合理性的幻灭
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的上述终极根源,决定了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得以有效避免、化解所可能选择的路径,无非如下几种:
其一,抑制人生存发展需要,消解德行存在的必要性,以非道德方式,来避免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的出现。先哲老子就持此观点:“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3]《老子》第46章所以,治理社会的根本途径就在于:“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3]《老子》第19章这种主张通过清心寡欲、结绳而治,以消除行为越轨的欲望基础和内在动机,使德行失去存在的必要性,从而在无须借助德行的情况下,实现社会治理的做法,固然有其深刻之处,但由于否定了人生存发展需要的合理性,从而也就失去了其理论和实践价值。
其二,肯定人生存发展需要的合理性,把避免、化解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对德行的需要,看做是必然的,但离开其他条件,孤立地强调通过德行,来避免、化解行为越轨和生存发展困境。这是迄今为止在该问题上人们所普遍选择的思路。“仁者道之纪,义者圣之学。学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4]卷上《道基第一》陆贾这种把仁德看做社会治理的本体性力量加以强调的观点,就是该思路的典型体现。该思路把德行资源的开发看做社会调适的决定因素,但因缺乏社会化、综合化的解决问题的自觉意识,因而实质上是一种惟德行主义的思路,并不能有效解决问题。
其三,肯定人生存发展需要的合理性及德行对避免、化解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的必要性,但认为德行的性质和功能,决定了它只是解决问题的必要的从属条件。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得以有效避免、化解的根本前提,则在于创造充裕的精神物质财富基础。显然,该思路是一种主张以创造充裕的财富基础为主,同时辅之以德行来解决问题的思路,故可称之为“综合调适”的思路。该思路这种以消解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生成根源为根本取向的内在特质,决定了它必然会普遍降低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的发生强度,使社会调适所必需的德行资源、德行代价,也必然随之普遍降低。可见,该思路不但能更有效地避免、化解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而且具有替代德行来避免、化解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的内在功能,使更多的人能够免于德行代价之苦。
由于第三种思路着力于消解导致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的终极根源,因而无疑比前两种思路能更根本地避免、化解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既然如此,加之德行社会调适功能的上述局限性,那么,从解决问题思路的根本有效性,以及追求以人为本这一和谐社会根本目标高度来看,就必须把社会调适的根本思路,由热衷于在德行层面来解决问题的传统思维定势,转向以最大限度地创造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有效化解所必需的财富基础为主,同时辅之以对德行调适功能适度开发的综合调适思路上来。
长期以来,德行因其通过无偿奉献来避免、化解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等社会失调现象的崇高本质,以及提高社会凝聚力、维持社会秩序的显著功效,不但使人对其社会调适功能普遍产生了依赖感,也使人普遍养成了关于社会失调成因及其调适途径道德化取向的问题意识,同时普遍抑制了人们关于社会调适综合化、社会化取向的问题意识的正常发育,以至于人们能够麻木地忍受对社会结构调适功能开发的种种欠缺局面,但却对德行疲软和对德行社会调适功能开发的任何不充分现象,往往十分敏感,并予以激烈声讨。人们习惯性地认为,德行就是用来避免、化解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的,而这种越轨和困境,也只有通过德行才能得以避免、化解。一旦出现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人们寻找解决问题出路的近乎本能的第一反应,就是对德行的呼唤和期待;一旦问题得不到解决,人们就习惯性地把其根源归结为德行的缺失。例如,人们对公交车上抢座位行为的普遍反应,往往局限于认为行为人道德素养不高,并希望通过道德教育来予以克服,却往往忽视了对作为问题根本成因的公交系统发展不力问题的谴责。再例如,人们习惯于从道德人格缺陷角度分析学术腐败根源,却往往忽视了对具有根本导向功能的学术评价体系合理性的反思。
总之,这种关于社会失调和调适的道德化取向的问题意识,以及惟德行主义的化解问题的基本思路,挤占了社会化、综合化取向的问题意识发育的契机和空间,忽视了社会失调问题的生成和普遍有效解决,与非道德的社会变量间更深刻、更本质的关联,必然使社会演变为一种过度道德化、过分依赖于道德的社会;必然赋予人们过于沉重的德行责任,导致社会调适资源配置比重失调,闲置和浪费其他社会调适资源,阻碍社会和谐程度的提高;必然导致人们对德行调适功能的过高期待,从而也就必然使人们因居高不下的德行负担的长期重压,而对德行产生一定的厌烦和抵触情绪。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德行的冷漠态度,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因此,解决问题思路的上述根本转换,不仅标志着德行资源调适功能的开发进入了一个具有更高效益、更人性化的时代,也标志着在社会调适问题上普遍存在着的惟德行主义的传统思路,或道德拜物教取向之继续存在的理由彻底终结了。
三、综合调适路径的内在构成与德行调适有效性的基本前提
“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5]上述综合调适路径的实质,就是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相互作用高度,全方位地创造行为越轨和人生存发展困境得以根本有效避免、化解所必需的综合性的基本前提。就该问题的有效解决所必需的综合性的前提条件来看,该路径必然由如下内容构成:
首先,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得以根本有效避免、化解对充裕财富基础的根本依赖性,决定了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是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得以有效避免、化解所必需的基本前提的首要内容。这一点,古人早有深刻洞察:“施教百姓,富民恒一。路不拾遗,国无狱讼”[6]《先醒》。若不通过发展生产力,而只是依赖德行来避免、化解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那么,这种越轨和困境的根源赖以消除所必需的财富基础就无以生成。这不但从根本上阻滞了人生存发展需要满足水平的提高,瓦解了人德行责任践履能力得以根本提高的财富基础,抑制了德行社会调适功能的有效发挥,而且必然导致本来就稀缺的社会财富,因社会调适对德行资源的过度开发,而不可避免地低水平平均化,从而必然客观地强化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赖以生成的根源,诱发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更普遍地发生。可见,大力发展生产力,是比一味开发人德行积极性更为有效的社会调适途径。
其次,生产关系的合理性状况,不但通过对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影响,而间接地约束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等社会失调现象得以避免、化解所必需的财富基础创生的状况,而且还通过对其赖以发生的经济关系前提状况的直接约束,而深刻地约束着上述社会失调现象存在的程度。具体来说,在生产领域,若生产要素配置机制不合理,就会导致资源浪费和劳动关系公正性的丧失,从而不但必然阻碍财富创造水平的提高,而且还会因此而激化财富的稀缺性与对财富需求的无限性间的矛盾,进而导致上述社会失调现象更普遍地发生。若交换机制发育不健全,不但生产和消费不能正常进行,而且会诱发交换越轨行为的严重发生。就分配关系而言,“基于市场规律的分配不可能使居民的收入结构最佳化,也不可能解决贫困问题”[7]。分配机制的缺陷所诱发的行为越轨(无偿占有他人财富等)和生存困境,必然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必然性,是仅靠德行所无法有效避免、化解的。若消费机制存在严重缺陷,那就会诱发通过消费侵权来牟利的越轨行为严重发生,导致消费灾难等生存困境更普遍地生成。总之,不合理的生产关系作为上述社会失调赖以发生的基本社会前提之一,既是一种制度性力量,也是一种物质性力量。基于这种普遍而稳定的社会前提的上述社会失调,是仅仅靠德行这种分散性、微观性个体力量的社会调适功能所根本无法普遍有效避免、化解的。可见,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诸领域,建立起完善的生产关系体系,是德行能力得以根本提高、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等社会失调现象得以有效避免、化解所必需的基本前提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
再次,上层建筑不但通过对生产方式的反作用,而且还通过对社会生活其他领域普遍发挥规导作用,而深刻约束上述失调现象发生、存在的状况。前人所谓“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8]就体现了上层建筑的合理性状况,对人生存处境及社会秩序状况突出的约束作用。因此,完善上层建筑体系,是避免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化解德行压力的普遍有效措施的基本组成部分。此外,德行作为上层建筑的内在环节,为上层建筑的其他部分深刻制约着。因此,德行要能有效发挥其社会调适功能,除了必须具备一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前提外,还必须具备由上层建筑的其他部分所组成的完善的支撑系统。
总之,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等社会失调现象,既然受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综合制约,那么,由这三者的结合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就构成了具有综合性、总体性、根本性特征的社会调适资源。其社会调适功能不但是任何单一社会调适资源所无法替代的,而且对其社会调适功能的开发,也是德行社会调适功能有效开发和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因此,孤立开发德行的调适功能,不但成本高、收益差,而且根本不可能有效实现所预期的社会调适目标。
四、德行负担弱化的历史趋势与社会调适对德行资源开发的合理限度
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社会结构替代德行发挥社会调适功能的程度必然会不断提高,从而社会调适所必需的德行及人的德行负担必然呈现出不断弱化的历史趋势。
原始社会初始状态的低下生产力,使得原始人生存所面临的挑战比此后一切时代人所可能遭遇的挑战要严峻得多。此外,原始社会尚不能发育出专门化解人生存困境的救助性的制度体系及专能部门。这就使得避免人行为越轨及化解人生存困境等社会调适任务,除过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所可能承载的部分外,其余的只能主要由德行来承载,从而原始社会就成为一切社会中人德行负担最重的社会。出现了阶级分化的自然经济时代,社会的进步促使统治阶级不同程度地建立了诸如中国汉、唐、宋、明诸朝曾分别施行的抚恤鳏寡孤独、假民田园、赈贷、平粜、施粥、居养等制度②。这就使得德行所承载的社会调适责任,比起原始社会来开始逐步收缩、降低。资本主义时代,社会福利制度逐渐普遍建立起来。这不但普遍地降低了德行救助的必要性和德行负担,而且也较为有效地弱化了行为越轨的外在诱因。这就使得德行所承载的社会调适责任,较之于其在此前社会形态中所承载的责任来更进一步减轻了。社会主义以消灭剥削压迫、追求共同富裕和人全面发展为根本诉求,因而,按照其内在逻辑,它必然能够比此前一切剥削制度,更有效地避免行为越轨和人生存困境的出现。这就必然使得德行所必需承载的社会调适责任,较之此前一切时代来,其负担的程度必然是最轻的。
德行负担弱化的历史趋势表明,随着社会结构的逐步进化与完善,社会调适对德行的需求水平在不断降低,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机会、空间在不断扩展。可见,历史进步的过程,就是德行负担弱化的过程,进而也是人解放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德行负担弱化的历史趋势对社会进步趋势的这种从属性、统一性表明,一个社会,德行在社会调适资源配置结构中所占比重愈大,德行所必须发挥作用的范围愈普遍、所必须发挥作用的力度愈强,从而人德行所必须负载的社会调适责任愈沉重,这个社会的内在结构就愈落后,这个社会文明的程度就愈低。在此意义上,一个社会中人所必须承载的德行责任的轻重走向,就是直接反映一个社会文明状况的晴雨表。
财富稀缺性与生存发展需要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不可能得到终极的消解。因此,德行负担弱化的历史趋势,并不意味着德行资源开发对社会调适的必要性会完全消失。但历史的不断进步,毕竟为德行负担弱化提供着愈来愈充分的条件,从而为人的解放发展提供着愈来愈大的现实可能性。这使得任何逆此趋势而强化人德行负担的做法,都与追求人解放自由的历史进程和以人为本的时代原则相对抗,从而不再具有任何合理性。这样,厘清德行资源开发的合理限度,就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理论课题。
首先,社会结构作为总体性、前提性、普遍性和稳定性的客观力量,通过对人赖以生存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基础发育状况的约束,而深刻地约束着人生存发展的现实状况。德行作为随机性、分散性、境遇性的个人主观行为,不但以人主观性的道德意志为支撑,而且不能像社会结构那样普遍有效地决定人生存发展的现实基础。这决定了德行尽管也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调适功能,但决不可能像社会结构的调适功能那样普遍、深刻、稳定、持久。所以,社会结构无疑是社会调适可资开发的最基本资源,对其开发的状况直接决定着社会失调发生、存在的普遍性、深刻性和复杂性的程度;德行尽管也是社会调适可资开发的重要资源,但其上述局限性,决定了它决不可能有效地避免和化解社会失调。可见,普遍地、深刻地避免和化解社会失调,既是社会结构所独有的社会调适功能,也是德行社会调适功能不可逾越的上限,进而也是德行所应承载的合理限度的社会调适责任的上限。要德行承载起超乎该界限之上的更多社会调适责任,不但必然会因德行力所不及而错失社会调适机会,而且也是对德行资源的无谓消耗和对德行主体价值的践踏。
其次,德行的主观性、随机性、分散性、境遇性、个体性等特性,尽管决定了它不可能像社会结构那样具有普遍而深刻的调适功能,而只具有相对普遍、相对有效的社会调适功能,然而,它却能够较有效地化解那些散发性、个别性、暂时性的生存困境,并以良心机制较为有效地防止、避免个人越轨行为的发生。而生活的复杂性、历史性、境遇性、开放性等特征,则决定了宏观社会结构所具有的社会调适功能,并不能够周延地覆盖和满足微观性、个体性、境遇性、历史性的日常生活对社会调适的一切特定需要。因此,避免和化解微观性、个体性、境遇性、随机性的社会失调现象,既是社会结构社会调适功能的盲区,也是德行社会调适功能的下限,从而也就是德行所必须承载的社会调适责任的底线。回避和拒绝这一底线层面的德行责任,那就是在为恶。
再次,社会结构的完善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因此,自觉避免、化解社会结构现有调适功能所无法克服的普遍发生的社会失调现象,自然是德行所必须承载的社会调适责任。在社会结构发生重大转型、变革时期,是溢出既有社会结构当下所具有的社会调适功能限度之外的社会失调现象高发期。此时,就迫切需要德行最大限度地承载起这种特殊时期的社会调适责任。虽然这种责任是一切人共同的责任,但这种责任却无法明晰地确定到个人,从而只能是一种无确定责任者的弹性的、开放性的责任。尽管如此,这种德行责任是任何人都不能回避的。德行主体与德行客体间这种非确定性、开放性的责任关系,客观地构成了德行必须承载的社会调适的弹性责任。
总之,由社会结构与德行各自内在特性所共同规定的德行所必须承载的社会调适的上述责任限度,既为合理开发上述两种社会调适资源提供了基本依据,同时也表明,德行社会调适功能的开发与人自由全面发展间的正相关关系,仅存在于德行责任的上述合理限度内。如果德行所承载的调适责任过重,以至于超出了这一限度,不但必然导致社会结构的社会调适功能的浪费,也必然由于让德行承载起社会结构所应承载的调适责任这种为其力所不及的负担,而摧毁德行良性发育的客观基础和再生能力。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德行恐惧感、冷漠感,就是过度开发德行社会调适功能所导致恶果的体现。因此,道德教育和道德评价必须把德行资源开发的合理限度确立为其基本依据之一。只有这样,才能促使人们清醒地监督对社会结构的社会调适功能开发的状况;才能够理直气壮地把人从超重的德行负担中解脱出来,使其更充分地享受自由全面发展的权利;才能够促使德行与社会结构这两种社会调适资源的开发,形成各秉其性、各处其位、各尽其能的合理配置和良性互动关系,最大限度地促进人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和谐进步。
五、德行调适责任合理化与德行主体性发挥最大化的统一:社会调适绩效最大化与社会和谐的内在诉求
社会结构和德行在社会调适中的上述不同功能表明,尽管前者和后者在社会调适中各有其特定的功能区间,尽管前者并不能完全取代后者的社会调适功能,但完善前者比起强化和开发后者来,不仅是社会调适的根本途径,比强化和开发后者具有更为有效的社会调适功能,而且对后者社会调适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替代效应。这决定了前者完善程度愈高,社会失调发生和存在的程度就愈轻,社会失调被有效化解的程度、从而社会调适的绩效就愈高;相应地,由前者不完善而不得不由后者来承接社会调适负担的可能性、必要性就愈小,前者替代后者发挥社会调适作用的程度就愈高,后者在社会调适中的必要性就愈低,社会调适对后者需求的水平就愈低,所必须支付的德行代价就愈小,人解放和发展的程度就愈高。而人解放和发展作为以人为本原则的核心内涵,乃和谐社会的根本诉求之所在。在此意义上,社会和谐实现程度自然也就愈高。
所以,无论从社会调适绩效最大化目标来看,还是从社会和谐最大限度实现的内在期待来看,都要求在社会调适过程中,实现德行调适责任的合理化,彻底改变人们已经习惯了的、且已近乎本能化了的赋予德行以无限社会调适责任的做法,使德行所承载的调适责任,由无限走向有限,并把其限制在由德行本质所决定了的可能的功能限度内。这就意味着必须把社会调适原则,由原来无限度、无条件依赖德行调适,转向以社会结构调适功能的开发为主导、以德行功能限度内的调适作用的发挥为辅从、社会结构调适与德行调适各秉其性、各处其位、相互统一的新原则上来,从而实现德行调适责任的合理化。具体来说,一方面把通过对社会结构的最优化治理,来实现社会结构调适功能的最大化开发,置于社会调适的主导地位,来最大限度地消除社会失调出现的普遍社会根源,最大限度地消除把本应由社会结构承载的社会调适责任转嫁给德行的可能性,最大限度地降低德行所承载的超过其功能限度的社会调适负担的压力,为德行有效践履其功能限度内的社会调适责任,创造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客观基础;另一方面,激励德行主体积极践履其合理限度内的德行责任,在社会结构无法有效发挥其社会调适功能的生活空间中,有效发挥其具有特殊优势的社会调适功能,从而与社会结构结合起来,构筑起覆盖社会生活一切领域和过程的完整调适系统,为社会调适绩效和社会和谐实现程度的最大化,提供所必须的调适机制的保障。
按照该原则进行社会调适,必须做到:首先,应坚持把对社会结构和对德行这两种社会调适资源的开发结合起来,使它们形成相互支撑、相互驱动的良性关系。决不能离开对前者社会调适功能的开发,来开发后者的社会调适功能。其次,应在最大限度地开发社会结构调适功能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开发德行合理限度内的社会调适功能。这就是说,追求德行调适责任的合理化、有限化,决不意味着不去开发德行的社会调适功能,而是要通过最大限度地开发社会结构的社会调适功能,从而创造必要的条件,来最大限度地开发德行合理限度内的社会调适功能。再次,开发社会结构的社会调适功能,是社会调适的首要选择,在社会调适中居于主导地位。对德行社会调适功能的开发尽管是必要的,但仅处于对社会结构社会调适功能开发的补充和从属地位。最后,社会结构社会调适功能开发对德行社会调适功能开发的替代,既是一个逐步深化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有其不可逾越的界限的过程。这就使得德行社会调适责任的合理化,既表现为一个必须通过对社会结构社会调适功能最大化开发而得以逐步实现的历史过程,也必然是一个相对的、有限的过程,决不可能完全取代德行调适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社会调适绩效的最大化实现与社会和谐最大限度实现具有内在统一关系:前者客观上不但为后者创造着所必须的特定品质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而且创造着后者所必须的特定生存发展状态和特定品位的社会成员。更进一步来看,社会调适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追求社会协调和和谐;相应地,后者也在客观上有效地供给着前者所必须的主客观社会条件。二者间的这种内在统一关系及其各自实现对社会调适所必须坚持的上述原则依赖,决定了社会调适所必须坚持的上述原则,客观地构成了评判一个社会中的社会调适有效性程度和调适绩效水平,以及该社会是否和谐及和谐程度的重要尺度。从该尺度来看,具有充分有效性和调适绩效能够最大化的社会调适,必然是符合上述原则的社会调适;相应地,和谐社会决非德行在社会调适资源配置中的比重占据主导地位,以至于德行责任不必要地沉重且其力度和广度不断强化拓展的社会,而是一种社会结构在社会调适资源配置中的比重占据主导地位,并能最大限度地消除德行所承载的超过其功能限度的调适责任,从而能最大限度地使德行所承载的社会调适责任合理化的社会;必然是一种社会调适对德行资源的开发需求逐渐弱化、德行必要的力度和广度逐渐降低收缩,从而人们必要的德行负担趋于合理的社会。
社会调适绩效最大化和社会和谐最大限度实现,不但都内在地要求在社会调适过程中实现德行调适责任的合理化,而且同时也内在地要求以人德性修养、德行意志、德行偏好、德行激情、德行自觉性、德行能力等内容构成的德行主体性最大限度的孕育和发挥。
首先,社会调适绩效的提高,既有赖于人有效践履其合理限度内的德行责任,也依赖于社会结构具有健全的社会调适功能及其社会调适功能的有效发挥。就人合理限度内的德行责任的有效践履而言,它显然直接有赖于人德性主体性的有效孕育和发挥。人德行主体性孕育和发挥程度愈高,人德行自觉性、德行能力和德行创造性就愈高,人就愈能有效地践履其合理限度内德行责任,社会调适的绩效也就必然相应地愈高。可见,人德行主体性孕育和发挥的程度,与社会调适绩效的高低,具有内在统一关系。就社会结构、社会调适功能健全状况及其社会调适功能发挥状况而言,除了受其他相关条件约束之外,也为德行主体性孕育和发挥状况深刻约束着。德行主体性孕育和发挥程度愈高,德行主体就愈有动力、能力和创造性去完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健全程度就愈高,其社会调适功能就愈健全,发挥程度就愈高,相应地,由它所支撑的社会调适绩效就愈高。这表明,德行主体性孕育和发挥程度,与社会调适绩效的高低,也具有内在统一关系。
其次,社会和谐以人行为越轨和人生存发展困境等社会失调现象最大限度地避免、克服和化解为前提。而上述社会失调现象最大限度地避免、克服和化解,则又以社会调适绩效最大化为前提。如前所述,社会调适绩效的最大化,则又有赖于社会调适以社会结构调适功能的开发为主导、以德行合理限度内的调适作用的有效发挥为辅从,使社会结构调适与德行调适各秉其性、各处其位、其相互协同过程和状态中,有效发挥作用。但这一切都不可能自发实现,除过需要求他相关条件外,无疑还内在地需要德行主体最大限度地孕育和发挥其德性主体性。只有德性主体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孕育和发挥,德行主体才既能义无反顾地、创造性地为社会结构的完善和其社会调适功能的最大限度发挥去奋斗;也才能积极地、创造性地践履其合理限度内的德行责任。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基础,社会结构调适与德行调适各秉其性、各处其位,并在其相互协同过程和状态中才能形成,社会调适绩效才能最大化,人行为越轨和人生存发展困境等社会失调现象才能得到最大限度地避免、克服和化解,人在现实社会中的价值中心和历史主体的地位才能得到最大限度实现,以人为本为根本取向的和谐社会也才能相应地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
再次,社会和谐既是社会调适有效实现的结果,也是社会调适进一步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二者间的这种内在统一关系,决定了它们各自最大限度的实现,所分别对德行主体性最大限度孕育和发挥的需求,并不是相互孤立、相互封闭、相互外在、相互脱节和相互冲突的,而是内在统一、相互协调的。因此,德行主体性的最大限度孕育和发挥,不但是它们共同的内在要求,而且能够同时促使社会和谐和社会调适绩效的最大限度实现。
最后,德行主体性的最大限度孕育和发挥,固然能促进社会和谐和社会调适绩效的提高,但这种促进作用的最大限度实现,则有赖于其他相关条件。离开其他相关条件,其作用程度就会降低甚至消失。相应地,孤立强调德行主体性对社会和谐和社会调适绩效的作用,就会陷入道德决定论。因此,通过追求德行主体性最大限度孕育和发挥,来实现社会和谐和社会调适绩效的最大化,必须与对其他相关条件的创造相协同,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社会调适绩效最大化和社会和谐最大限度实现,尽管既内在地要求在社会调适过程中实现德行调适责任的合理化,同时也内在地要求德行主体性最大限度的孕育和发挥,但这两种要求不但并不矛盾,而且还相互肯定、相互支撑,具有内在统一关系。
首先,德行调适责任的合理化的要求,与德行主体性最大限度孕育和发挥的要求,是基于德行的社会调适功能、社会结构的社会调适功能和德行主体性在社会调适中所客观具有的不同功能地位、不同功能性质,而对它们在追求社会调适绩效和社会和谐最大化实现过程中,所应发挥的作用的互补性配置。追求德行调适责任的合理化,是着眼于社会结构和人及其德行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力量,在社会调适中客观所具有的功能地位、价值性性质的根本差异,及由这种根本差异所决定社会调适绩效最大化的根本有效的实现途径,与人解放发展的最大可能性,所选择和确定的德行所应、所能够承载的社会调适责任的最佳状态。在此意义上,德行调适责任合理化,不仅仅是一个历史抉择,也不仅仅是一个价值抉择,而是历史抉择与价值抉择的统一。这一抉择决不意味着只突出社会结构而摒弃德行的社会调适功能,而是依据它们各自在社会调适中的功能特性,扬其各自所长,避其各自所短而已。
其次,德行调适责任合理化问题的实质,只不过是说,德行不能也不应承载起只有社会结构才能承载起的相应社会调适责任;德行如果承载起只有社会结构才能承载起的社会调适责任,不但会因超过其功能限度的德行责任而阻碍德行主体的生存发展,更重要的是会迷失社会调适的根本有效途径,忽视社会调适的主导性力量,从而在根本上阻碍社会调适绩效的根本有效提高。这就是说,德行固然不能承载起只有社会结构才能承载得起的社会调适责任,但德行必须也能够承载起社会结构调适责任限度之外的、与德行的个体性、随机性、灵活性、有限性等特征相契合的社会调适责任。既然德行必须而且也能够承载起与其特性相适应的范围内的社会调适责任,那么,有效地、最大限度地践履这种责任,自然就需要德行主体性最大限度的孕育和发挥。
再次,承上可知,德行调适责任合理化问题,本质上不过是德行所应承载的社会调适责任的范围问题,而德行主体性最大限度孕育和发挥问题,本质上则主要是德行能动性、德行姿态、德行力度等德行状态问题。它们显然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并不矛盾。此外,从二者功能关系角度来看,主张通过完善社会结构而最大限度地开发社会结构的社会调适功能,以最大限度地降低人们的德行负担,使德行责任合理化,强调的是社会结构在社会调适中居于主导性功能地位,以及德行社会调适功能的局限性;主张最大限度地孕育和发挥人德行主体性,强调的是人德行责任的不可超越性、德行与德行主体性对社会结构调适功能的有效实现及人解放发展的重要前提地位。显然,这二者仍然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本质上并不构成对立和矛盾。
最后,德行主体性最大限度孕育和发挥,也只有在德行所承载的社会调适责任合理化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德行超过其功能限度和功能范围,承载起只有社会结构才能承载得起的社会调适责任,未必一定能缓解社会失调的压力,但却肯定会对德行主体的健康生存发展造成消极影响,从而必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甚至摧毁德行主体性最大限度孕育和发挥的生理基础、机会资源与必要的综合性的素质保障,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摧毁德行主体性最大限度孕育和发挥的可能性。德行所承载的社会调适责任合理化程度愈高,德行主体生理与心理、自然与社会的属性的发育就愈健全,德行积极性就愈能避免被挫伤,德行主体性的孕育就愈健全,发挥程度就愈高。因此,把德行所承载的社会调适责任控制在其合理限度内,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德行主体性最大限度孕育和发挥的基础和前提之所在。
上述分析表明,德行调适责任合理化与德行主体性发挥最大化间的关系不仅不相互对立、相互冲突,而且还相互肯定、相互补充、相互支撑,因而它们间的关系客观地具有内在统一的性质。它们间的这种内在统一关系,把它们扭结为一个有机整体。而它们相互间客观具有的这种内在同一的有机整体关系,则直接构成了社会调适绩效与社会和谐最大化实现的重要基础,是社会调适绩效与社会和谐最大化实现共同所具有的内在诉求。
六、结语
最大限度地完善社会结构,必然能使其社会调适潜能得到最大限度释放,从而必然能最大限度地降低人所承载的超过其功能限度的过重的德行负担;而人德行负担的合理化,则不但能使社会调适走上以结构调适为主、结构调适与德行调适各处其位、协调一致的根本有效途径,同时也能最大限度地提升人解放发展的程度,使人德行能力得到最大限度强化,从而最大限度地提升人德行绩效;而人德行主体性的最大限度的孕育和发挥,则不但能有效促进人的解放和发展,而且能为社会结构最大限度完善和其社会调适功能的最大限度发挥,创造最佳的德性人格前提。这诸方面的有机结合,必然能以最小成本,获得避免、化解行为越轨和人生存发展困境等社会调适的最大收益,从而最大限度地促进人解放发展,使以人为本为根本取向的和谐社会得到最充分实现。
德行调适与社会结构调适间的上述地位关系,以及社会调适绩效和社会和谐的最大化实现,对把社会调适原则,由原来无限度、无条件依赖德行调适,转向以社会结构调适功能的开发为主导、以德行功能限度内的调适作用的发挥为辅从、社会结构调适与德行调适各秉其性、各处其位、相互统一的新原则上来的内在要求,客观地表明,一个社会中德行所承载的社会调适责任是否合理,不但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标志着现实生活中社会失调被有效调适的程度、进而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标志着该社会和谐的程度,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标志着该社会中人解放发展的程度,进而最终标志着该社会文明的程度。这不仅意味着伦理化取向的社会治理、社会调适思路的合理性、有效性是可疑的,而且也意味着离开唯物史观,忽视对社会结构的治理及这种治理对德行有效性一定程度的前提地位,抽象地、绝对地强调人德行责任的道德观的内在活力可能是贫弱的。
收稿日期:2007-03-27
注释:
①参见肖士英《论德行代价补偿》,《光明日报》1999年4月9日第5版。
②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社会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3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