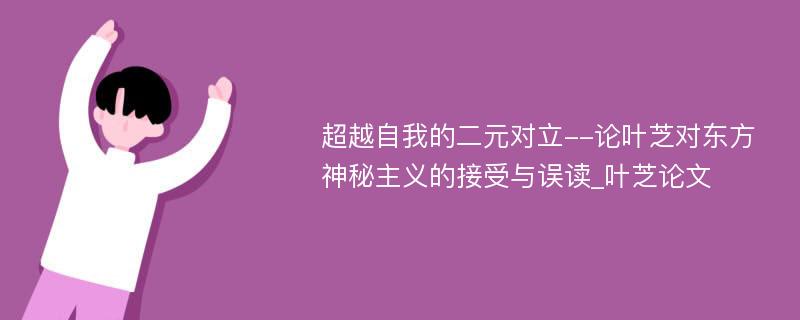
超越自我的二元对立——评叶芝对东方神秘主义的接受与误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叶芝论文,神秘主义论文,误读论文,对立论文,超越自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威廉·巴特勒·叶芝(W.B.Yeats,1865—1939)是近代爱尔兰文学史上最著名的诗人, 也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诗人”(T·S艾略特语)。他一生崇尚神秘主义并为之进行了不 懈的探索。在这个过程中,叶芝濡染于东方文化之中,汲取了大量的养分。“在叶芝的 作品中,东方成了一个历久弥新的主题”,(注:J.J.Clarke,Oriental Enlightenment ,Routledge,New York,1997,pp.101-102.)同东方文化的邂逅对叶芝的文学创作产生了 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以往西方评论界对叶芝接受东方神秘主义影响这一事实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在谈 及诗人神秘主义思想渊源时,一般只把它放在西方文化圈内加以分析,集中于探讨新柏 拉图主义、基督化卡巴拉教、布莱克(John Blake)和斯威登堡(Emanuel Swedenborg)的 诗意神秘主义对叶芝的影响,而淡化甚至忽略了印度神秘主义及禅宗思想对诗人的影响 。实际上,沿着诗人思想发展的轨迹做深入的文化探寻,便不难发现,对东方神秘主义 的探索乃是贯穿叶芝神秘追求的主线之一。艾勒克·博埃默在提到叶芝神秘哲学集大成 之作《幻景》的文化源头时就指出,“其最初的根据就是从东方传统中悟出的意义结构 ,那个孕育了他们祖祖辈辈的‘母体’。”(注: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 学》,盛宁、韩敏中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4页。)
一、时代背景与文化语境
叶芝受东方神秘主义的影响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因素,并与当时西方社会所处的文化 语境直接相关。诗人生活的时期跨越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叶,当时的西方社会正经历 着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这一文化转型,西方人的价值观正经历着一场巨变。悲观失望 的情绪弥漫于欧洲知识界,后期浪漫主义已呈颓废之势,人们对启蒙理性以及维多利亚 时期的传统已丧失信心,工业文明带来的物欲膨胀使基督教信仰正逐渐丧失凝聚力,对 现实语境的焦虑促使西方在寻求摆脱精神危机的过程当中,把目光投向了古老的东方, 希望东方能够再一次给西方带去全新的启蒙精神,拯救西方文明于衰落之中。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见证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第二次高潮,这一阶段的文化交流的 方式、规模和影响均超过了历史任何时期。仅从文化传播的媒介来看,就与过去有所不 同。其一,传入的渠道已经不再限于传教士、旅行家、商人和探险家,西方的东方研究 已经比较成熟,涌现了一批从事东方文化研究的专家和学者。《道德经》的翻译者阿瑟 ·韦利、《亚洲之光》的作者埃德温·阿诺德、《东方圣书》的编著者马克斯·缪勒、 《易经》的德文翻译者魏礼贤以及心理学家卡尔·荣格等都曾受到过东方文化的洗礼, 成了东方文化的积极传播者;其二,一些来自东方但又受过良好西方教育的东方学人, 如印度的泰戈尔、维韦卡南达、拉达克里希南、中国的辜鸿铭以及日本的铃木大佐等, 也在西方撒播东方智慧的种子。
从19世纪60年代起,西方掀起了一股研究秘宗、诡异之术和超自然现象的热潮,《易 经》、《西藏度亡经》、《禅佛教入门》等宣扬东方神秘思想的经典在西方相继出版发 行。詹姆斯·弗雷泽于1890年推出了人类学巨著《金枝》,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掀起了一场研究宗教仪式、巫术等神秘仪式的热潮。印度教、佛教、犹太卡巴拉教、 道教、藏传佛教、禅宗这些充满东方神秘主义思想的宗教哲学自然成了西方人梦寐以求 的精神食粮。一时间热衷于秘术、法术和宗教修行研究的各组织在欧美应运而生,西方 各国无不以追随东方神秘思想为“新时代”的风尚。在爱尔兰,新教徒为寻求摆脱天主 教传统势力的控制,也转而从诡秘之术中寻找力量来抗衡天主教。所以说爱尔兰文学复 兴也由此多少感染到了东方文化的影响,“在东方观念的激发下,有关精神危机和文学 复兴需要的主题最早见于那个时期同爱尔兰文学复兴运动相关的一些作家,如W·B·叶 芝、乔治·拉塞尔(笔名AE)和乔治·莫尔。”(注:J.J.Clarke,Oriental Enlightenment,Routledge,New York,1997,pp.101-102.)
二、叶芝神秘主义的多种来源
叶芝热衷于神秘主义的诡异之术最初只是为了摆脱其父亲的影响,叶芝的父亲约翰· 叶芝受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影响,信奉达尔文主义,是一个典型的怀疑主义者,而叶 芝的信条却是“事物只存在被感知中”,他坚信“近代科学已经流产,而希望有另一种 发现真理的手段。”(注:Richard Ellmann,The Man and The Masks,Penguin Books Ltd.Harmondsworty,England,1979,pp.119,145.)对叶芝而言,通过秘术实验可以帮助 他验证神性的存在,可以使他的个人价值得到彰显,可以帮助他重树人生信念。因此, 叶芝迷恋神秘主义主要是为了解决个人信仰危机,为了使自己从动摇了他信念的怀疑主 义中解脱出来,而非从根本上去反对基督教、反对上帝。叶芝对基督教“三位一体”的 说法不以为然,而认同东方神秘哲学的人神合一。他发现在东方哲学中,“人的灵魂与 肉体处于和谐之中,心灵可以在矛盾中,直接认识真理,而西方神学却排斥了这一点。 ”(注:W.B.Yeats,Essays and Introductions,Macmillan(London),1961,pp.451,437.)
叶芝最早接触东方神秘主义思想可以追溯到他刚刚念完中学时的1884—1885年间。188 5年,叶芝同乔治·拉塞尔等几个好友成立了“都柏林秘术学会”,叶芝担任会长。次 年他们便邀请了印度婆罗门莫西尼·M·查太基来都柏林演讲。叶芝通过这位印度僧人 接触了吠檀多学派,认识了印度教中轮回转世的观点。“那是我生平头一次遇到一种哲 学,它进一步确定了我的模糊臆想,显得既符合逻辑又宽广无边。”(注:W.B.Yeats,The Autobiography of William Bulter Yeats,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New York,p.61.)叶芝在1929年所作《莫西尼·查太基》一诗中回忆了查太基讲过的话。叶 芝询问来访者,他是否应该做祈祷,查太基告诉他,除了想象以外什么也不要做,而应 该认识到无论是从前、现在还是未来,自我都会显现于轮回转世中,“我曾经是一个国 王,/我曾经是一个奴隶,/我曾经是傻瓜、无赖、流氓,/没有什么东西/我不曾当过… …”(注:《叶芝抒情诗全集》,傅浩译,中国工人出版社1996年。《丽达与天鹅》, 裘小龙译,漓江出版社1987年。文中均有注明。)(傅译)这是查太基对转世轮回的形象 描述,叶芝从此便牢固树立了对这一学说的信念。
1887年,叶芝加入了成立不久的“神智学会伦敦分会”,该学会创始人布拉茨基夫人 是当时欧洲最具影响的神秘主义大师,她对叶芝系统地学习神秘哲学的形成起到了关键 作用。通过她叶芝系统地学习了吠檀多不二论教中关于“自我”的教义。“自我”(又 称神我、性灵、灵魂)与宇宙本体(梵)绝对同一。这一信条是印度神秘主义的出发点, “印度神秘主义者永恒的探究,是以最终完全实现其灵魂即内心深处的自我与梵的同一 为满足,这要通过精神上的修炼和冥思默想来达到。”(注:A.L.巴沙姆:《印度文化 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74页。)印度神秘主义的教义对叶芝启发颇大,在后来的 创作里,诗人一直都在尝试通过各种途径寻找“自我”与宇宙本体(梵)同一的证据。
进入20世纪后,叶芝对东方神秘主义的探求进入了一个更为成熟的阶段。印度诗人泰 戈尔和美国诗人庞德是这一时期叶芝接触到的两个重要人物。泰戈尔本身就深受印度神 秘哲学的影响,他的诗意神秘主义完美地体现了人和宇宙的神圣同一,展现了东方神秘 主义的崇高美学品质和诗性智慧。叶芝于1912年结识了泰戈尔并经常保持着和他的书信 往来,叶芝非常喜爱泰戈尔的抒情诗,并为其诗集《吉檀伽利》的英文版写过序。叶芝 曾坦言,泰戈尔的抒情诗“展示了一个他一生都在梦寐以求的世界”。(注:Keith Alldritt,W.B.Yeats—The Man and The Milieu,Clarkson Potter/Publishers,New York,1997,pp.297—298,232,317.)庞德从1908年起断断续续地做过叶芝的秘书,他对 叶芝的戏剧和诗歌形式及风格的文化,产生过较大影响。日本能乐中借用各种面具、鬼 魂以及程式化的舞蹈来增强戏剧效果,使本身就热衷于寻求各种新法进行神秘实验的叶 芝大为着迷。叶芝在诗歌中也广泛运用了“面具”理论,这在他的晚期作品“疯简”组 诗中表现特别突出。能乐剧中的面具恰好与叶芝早期的秘密实验契合,而程式化的舞蹈 在叶芝看来就是一种单一意象。但追根溯源,日本能剧本身也包含了某些禅宗思想的因 素,“禅佛教的确是一种具有奇特美学意义的哲学,与其说它影响了能乐剧的文本内容 ,倒不如说影响了它的风格形式……”(注:Wilson,B.(1982),From Mirror ofter Mirror:Yeats and Eastern Thoughts,Comparative Literature,pp.38,29.)
日本学者铃木大佐的《禅佛教入门》和《禅佛教论集》2本书在西方世界的译介曾引起 过强烈震动,被历史学家怀特等人称为可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希腊柏拉图、亚里斯 多德著作的译介媲美的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注:程亚林:《诗与禅》,江西人 民出版社2000年,第277页。)叶芝在阅读它们后,认定禅佛教思想代表了东方智慧的最 高境界,它“既能够把我们从抽象事物的各种形式中解放出来……又能创造一种令人兴 奋的艺术”。(注:Quoted by Ishibashi form a letter by Yeats to Sturge Noore,p.194.)1931年,叶芝结识了晚年的最后一位精神导师——印度传教士室利·普罗希特 。这位印度传教士的人格魅力深深吸引了叶芝,两人之间建立了良好的朋友关系。普罗 希特让诗人回忆起了年青时的精神启蒙导师查太基。叶芝在读过这位斯瓦米(大师)的自 传《一个印度僧人》初稿后宣称,这是“他从十七岁起就一直在等待的东西。”(注:Keith Alldritt,W.B.Yeats—The Man and The Milieu,Clarkson Potter/Publishers,New York,1997,pp.297—298,232,317.)1935年,叶芝还与普罗希特合作翻译了印度经 典《奥义书》,并以《十部主要奥义书》的名字于1937年出版。
三、对东方神秘主义的接受和误读
要正确评价东方神秘主义对叶芝创作产生的影响,就有必要首先弄清楚神秘主义同文 学创作的关系。过去我们在认识神秘主义时存在许多误区,习惯于把它同不可知论、有 神论、宿命论、巫术等一些形而上学的思想联系在一起,贬低其美学价值。神秘主义确 有反理性的一面,但是它作为人类认知世界本真的一种感悟性思维,也具有某种积极的 意义。它“代表着超然的文化纬度,其致力于人类心灵的提升”,“目标在于给人一种 ‘精神上满意的答案’”(汤因比语)。(注:毛峰:《神秘主义诗学》,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98年,第47—49、426页。)神秘主义表达了人类对宇宙无限奥秘 的终极关怀,表达出了一种人文精神。因而从这一层面上看,叶芝追求东方神秘主义的 主要目的同样还在于,寻求到人的“精神家园”,以实现自我提升和完善,抵消怀疑主 义的影响。
叶芝的诗歌、戏剧著述非常丰富,但其中直接涉及东方神秘主义的题材却并不多见。 究其原因,主要还在于,叶芝创作的主体仍然建构在西方文化的框架之内,他对东方神 秘主义的接受,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于解决个人信仰危机和满足创作手法的需要。无论在 艺术形式、典故的运用、意象创造诸多方面,叶芝依旧没有脱离西方文化的“模子”。 但笔者以为,又不能仅因为这一点,就断定东方神秘思想在诗人的创作中只起到了“零 部件或脚手架”式的陪衬作用。(注:Gordan N.Ray(ed.)Masters of British Literature:Volume Two,Houghton Miffin Company,1958,p.655.)相反,东方神秘主义 在诗人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应该享有不可或缺的一席。叶芝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能够 把东方神秘主义的精神实质融入艺术创作之中,并赋予它崇高的美学价值。在叶芝的文 学创作过程中,东方神秘主义的影响已经不再囿于简单的形式借鉴、题材的神秘化和异 国情调的营造,其影响已经消融于创作主体意识之中。诗人已将东方神秘主义上升到了 哲学和美学的高度,使它具有了诗意神秘主义的性质。如果说诗意神秘主义“主张以诗 意方式重建人类的精神信仰和人生的超越意义”,(注:毛峰:《神秘主义诗学》,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98年,第47—49、426页。)那么,东方神秘主义正好 帮助叶芝实现了这一人生和创作的超越。
叶芝对禅宗思想的接受与过滤颇能说明,东方神秘主义的影响已经和诗人的创作思想 和手法融为一体。具体地说,禅宗思想已经使叶芝找到了一个认识人的存在本体的新视域,从而提升了他对自我的理解,“的确,不理解叶芝寻求自我表现的美学实质,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东方思想在叶芝后期作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注:Wilson,B.(1982),From Mirror ofter Mirror:Yeats and Eastern Thoughts,Comparative Literature,pp.38,29.)在《一个年轻又年老的女人》组诗中,一首名为《创世之前》(1982)的诗歌头一段里,诗人写到:
要是我把眼睫毛涂黑,/我的眼睛更加有神,/我的樱唇更为鲜红,/或问一下是否一切 都行,/从一面镜子到一面镜子;/丝毫不显一点虚荣,/我寻找着这个世界/创造出来之 前我有过的样子。(裘译)
这一节诗句看似平淡,但里面却蕴涵了深刻的禅意。如果读者不把它们与禅宗神秘思 想合并加以考察,就难解其中奥秘。首先,诗中的镜子不是指用来再现客观现实的“镜 子”,而是喻指人心“清净”。在禅宗里,镜子是一个广泛引用的意象,有时“青青翠 竹”、“清潭”、“湖水”都能起到镜子的作用,它们常被用来象征心灵的纯洁和“空 明”。“心就像一面皎洁的明镜,世上一切美丽善恶一一呈现在上面,分辨得一清二楚 。”(注:《白话碧岩录》,许文恭译,作家出版社1996年,第56页。)人要真正认识自 我发现自性,必须做到“心如明镜”。禅宗的根本主张便是,“明心见性,立地成佛” 。在这里,叶芝使用镜子的意象自有他独特的用意。在叶芝早期诗歌中,诗人惯用水的 意象来反射周围的景物、动物和人。这是由于叶芝受新柏拉图主义影响造成的,“在新 柏拉图主义的神话里,水是产生意象的媒介。”(注:Daniel Albright,Quantum Poets ,Yeats,Pound,Eliot,and the Science of Moderni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 997,p.33.)而在诗人中、后期的创作里,镜子的意象便时有出现,“象镜子一样的梦” (《塔》,1925)、“那些恶意的眼睛的镜子”(《自性与灵魂的对话》,1928)等。这些 镜子的意象已经被赋予了新的象征意义。叶芝曾自喻为镜子道:“我们自己无非是一面 镜子,解脱取决于把镜子转开,让它什么都照映不了……”(注:Ursula Bridge(ed.)W.B.Yeats and T.Sturge Moore,Their Correspondence 1901—37,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3,p.68.)叶芝认为,禅宗关于自我的认知方式与吠檀多教义中“梵我合一” 的思想一致,禅佛教直指人的内心世界,“具有凿穿一切智性抽象的能力”;(注:J.J .Clarke,Oriental Enlightenment,Routledge,New York,1997,pp.101-102.)它能够较 好地把人的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协调在一起,使人的自我不再分离。
“我寻找着世界/创造出来之前我有过的样子”一句中“我有过的样子”到底是什么? 原来,叶芝同样借用了禅宗里表达自我认知的一种方法,来探讨本体论(ontology)的问 题。“父母(你)未生时,你的本来面目是什么(亦用‘你的鼻孔在什么地方?’)?”这是 禅宗里常常提到的一句话,它实际上就是要回答:“我是什么?”这一关于人存在本质 的问题。铃木大佐指出,“本来面目”就是“一个人最深的内在或自我或本来生命。” (注:铃木大佐:《禅风禅骨》,耿仁秋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第272页。)禅宗 、佛教都强调“梵我合一”的崇高境界,认识自我无需向心外求。叶芝的许多作品大多 在探索如何实现灵与肉和谐共处的自我关系,而东方神秘主义似乎使他找到了认识、完 善与超越自我,反对物质主义与近代科学“对生命的机械简化”(注:James Hall & Matin Steinmann(eds.),The Performance of Yeats,Macmillan,1950,p.217,转载傅浩 《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的最佳方法。
在《自性与灵魂的对话》一诗中,诗人似乎终于超越了生与死、灵与肉的二元对立, 达到了自我“存在的统一”(Unity of Being):
……/一股巨大的甜蜜流入胸中时,/我们必大笑,我们欢呼,/我们备受一切事物的祝 福/我们目视一切都有了福气。/(傅译)
这一首诗的绝大部分诗行里,诗人均采用第一人称单数“我”,来指“自性”或“灵 魂”,直至诗快结尾时,经过自性和灵魂的一番争吵后,“我”才变为复数的“我们” 。自性与灵魂才终于走到了一块,取得了和谐。叶芝创造性地借助东方神秘思想,来探 讨解决灵与肉、生与死的二元对立的途径,使他的思想和艺术都得到了升华,这不能不 说是他创作的一个绝妙之处。
叶芝在过滤东方神秘主义时也存在某些明显的偏颇与误读。这一方面是由于诗人本身 的现实语境和文化身份的局限,另一方面也有他个人的一些主观因素。在叶芝看来,东 方神秘主义思想仍服务于他创作的目的,是为了印证他对世界的看法。所以,他在接受 东方神秘思想时,进行了有意的选择,只将那些符合自己信念和主张的东西才“揉进” 创作里。
叶芝对东方神秘主义最明显的误读,可见于他对转世轮回学说的曲解。上文已经提到 叶芝从查太基那里了解了转世轮回学说,但诗人自有他的用意,在《莫西尼·查太基》 中,叶芝接着写到:
我加以补充注释:/“年老的恋人们还会有/时光所拒绝给予的一切——/坟墓叠积在坟 墓上头,/好让他们得到慰藉——/在这变暗的大地之上,/那古老的军队行进;/诞辰叠 积在诞辰之上,/好让这隆隆的炮声/可以把时光轰走;/生与死的时刻相遇,/或者,如 伟大的圣贤所说,/人们以不死的双脚跳舞”。(傅译)
在这里,诗人显然并未提取印度神秘主义的精义,佛教、印度教实质上都主张出世离 欲的消极人生观。轮回要经历生、老、病、死四大痛苦,超脱轮回归于寂灭,达到涅槃才是最高境界。而在叶芝心目中,轮回就意味着无限希望。对于执着于生命和 情爱追求的诗人来说,转世轮回当然是再好不过的期待了。“诞辰叠积之上”,自然是 生生不息,就连永恒的时光也被炮火声轰走了。在这里,叶芝有意识地误读了转世轮回 学说来附合他的需要。在诗人的另一首关于印度主题的诗《须弥山》(或译《妙高山》) (1934)中,叶芝同样按照自己的观点,“创造性”地误读了东方神秘主义思想,表达了 人类为追求现实、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按照佛教的观点,现实是虚无,人生不过是一 系列虚幻,但诗人却把西方式的激情掺入到了对现实的探索。佛教宣扬,人要灭欲,而 叶芝却认为,探索现实必定要充满激情,充满欲望。“尽管他充满恐惧,但他不能停止 /一个世纪复一个世纪,追求,/如饥似渴,狂暴无比……”
或许正是由于叶芝对东方神秘主义的“创造性”误读,他的诗才达到了不朽的境界。 在叶芝最著名的《驶向拜占廷》(1927)和《拜占廷》(1930)两首诗中,诗人对轮回转世 学说融会贯通的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东西方文化在诗中融为一体,创造出了一 个崭新的境界。这两首诗都表达了诗人寄希望于轮回再生,灵魂经过炼狱的净化后,不 再投入凡胎,而是借助艺术的力量成为不朽:
“哦,智者们,站在上帝的神火中,/……/把我的心烧尽,执迷于情,/附在垂死的野 兽身上,奄奄待毙,/它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将我收入那件永恒不朽的工艺精品”。(裘 译)
四、结束语
东西方文化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强力碰撞,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产生了巨 大的推动作用,造就出了叶芝、艾略特、泰戈尔这样的一代伟大诗人。叶芝无疑是他们 当中的先驱者。东方神秘主义对其人生哲学和创作产生的影响,所体现的美学精神,在 诗人的整个神秘哲学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可低估。“文学应表达信念,是崇高感情的 外衣”,(注:Richard Ellmann,The Man and The Masks,Penguin Books Ltd.Harmondsworty,England,1979,pp.119,145.)如果说这就是叶芝的追求,那么,东方神 秘主义对他树立起这一信念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使诗人从精神危机中看到了来自东方的 希望。当然,叶芝对东方文化的接受主要是为了迎合其对神秘主义、秘宗探索的需要, 这中间出现的有意或无意的误读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叶芝在英语文学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正好处于传统英语诗歌向现代英诗转变的十 字路口。因此,研究诗人对东方神秘主义思想的接受和过滤,将有助于了解西方现代派 产生过程中东方文化所扮演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