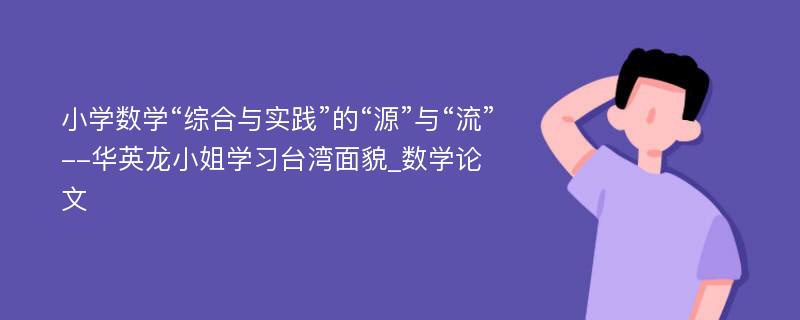
小学数学“综合与实践”课的“源”与“流”——学习华应龙老师的“台湾长什么样”之所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小学数学论文,所得论文,老师论文,华应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综合与实践”课程是《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以下简称“课标2011年版”)四领域之一的内容,所要求的课时数虽然不多,但设计并实施该课程的意义重大,其承载着重要的教育价值.在教学实践中如何落实呢?华应龙老师创设并执教的“台湾长什么样”(详见前文)定位为“综合与实践”课,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在研究本课的过程中,有教师提出的“本节课学生也没有画出‘非常像’的台湾地图”的观点不攻自破:学生是否能画出“非常像”的台湾地图不是本课的教学目标.也有教师提出质疑:学生都知道台湾、知道台湾的“样子”,还有进一步“画台湾”的需求吗?如果学生没有学习的需求,那么这节课是教师“人为”设计的,是教师一个人“感觉好玩”而不是学生“感觉好玩”.确实,产生学习的“真需求”是有效学习的基础和根本.在这里,学生真的没有“需求”吗?当教学目标不是看学生能否画出像样的台湾地图而是另有其他“企图”时,学生学习本节课的需求应该存在并能通过学习激发出更大、更深层次的学习需求. 因此,关键还是看本课的教学目标是什么.“综合与实践”课的教学目标不同于其他领域内容的教学目标,是多维多元的,且在短期内不容易实现.那么,哪些目标是本课的“源”,哪些目标是本课的“流”呢?把握好“源”与“流”的主次之分是设计并实施“综合与实践”课的关键.“一节课就40分钟”,确实“载不动许多‘思’”. 一、“综合与实践”课之“源”:发现、提出问题的意识与能力 “课标2011年版”指出,(“综合与实践”的学习方式)有别于学习具体知识的探索活动,更有别于课堂上教师的直接讲授.它是教师通过问题引领,学生全程参与、实践过程相对完整的学习活动.因此,设计“综合与实践”课程之本源是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批判与质疑精神”和“创新思想”,即用数学的眼光观察世界、研究世界,这个世界既包括自然界,也包括社会界. 在小学阶段,学生的“问题意识”更为根本,“课标2011年版”提出了“两能”(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到“四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转变,“四能”的培养需要贯穿于整个教育、教学活动的始终.其中,“综合与实践”活动必须承担重要职责. 教育实践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四能”,尤其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我认为,发现问题、提出问题需要教师的引导和示范.本课就以教师自身发现问题的历程为导引,师生共同经历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全过程.在本课中,教师不仅给学生发现、提出问题做了引导和示范,也给广大一线教师如何设计“综合与实践”活动的“问题情境”提供了借鉴. 例如,教学时教师向学生呈现了真实的事件与自己的思考过程,展示教师是如何发现、提出数学问题的: 去哪个地方旅游,我就先买一本专业的书看一看.当我们对某一个地方有些了解之后,就可以慢慢地欣赏它. 教师不经意地就发现了“好情境、好问题”: 台湾本岛南北纵长约395千米,东西宽度最大约144千米,海岸线长约1139千米,面积约为3.6万平方千米. 面对这样的信息,脑海中会提出哪些数学问题呢?于是,教师先让学生提出自己的问题,再呈现教师提出问题的过程与内容: 我翻遍全书,没有找到台湾的地图.于是,我就想:“地图上的台湾长什么样子?”我在书的空白处写出了算式……估计结果应该比实际的大,现在反而小了,说明了什么?3.6万与6万相比,说明台湾长得很“瘦小”.6×0.6=3.6,台湾实际面积只占那个长方形的60%.结合海岸线的长,台湾长什么样子呢? 去台湾考察访问前购买《畅游台湾》一书,准备做“旅游功课”,这也许与数学课没有直接关系,但却是一个对人生发展至关重要的好习惯:有目的、有预期地做事情.做“旅游功课”的习惯只是一句话一带而过,然后直奔本节课的目标“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发现数学问题”,这样处理自然而又真实、真切. 在上述交流的过程中,学生充分地提出自己的问题,教师也很自然地呈现个人的经历、感受,潜移默化地传递出教师发现、提出问题的全过程.虽然没有说教,只是事实性地呈现,但每个学生还是有对比、分析:学生的问题更多是从生活角度、从自身经验中提出的,其“数学味道”不浓;而教师的问题更多是从“数学角度”提出的,符合五年级学生的知识水平,只不过超出了学生日常所解决问题的范畴,即以往学生解决的数学问题都是“给出几何图形以及相关数据求图形的面积或周长”,而教师的问题却是“知道图形的相关数据,问这个图形的形状是什么”. 教师提出问题的角度不同于以往的角度,这既为学生如何提出问题做了示范,也激发了学生深入研究这个“另类问题”的需求.传统问题的答案是唯一的,而本课要探究的问题的答案不唯一,甚至能引发更深层次的问题,即神奇的“海岸线”问题(“海岸线”问题是一个特别好的“综合与实践”课程的内容,后文将稍作论述).因此,应该说本节课学生是带着强烈的学习需求进行的,当然大前提是教学目标不能定位为“画出很像的台湾地图”. 本课也为一线教师如何选择“综合与实践”活动的题材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和经验.“综合与实践”的活动离不开“好情境、好问题”,更应该以基本的“知识点”为载体,运用基本的知识解决综合性的问题,或者引发更多有探究价值的问题.在“课标2011年版”中,给出了一些“综合与实践”活动的案例:图形(纽扣)分类问题、生活中的轴对称图形、上学时间、绘制校园平面图、旅游计划、象征性长跑、估计高度、分类计数(小正方体几个面涂色).教学中,可以以这些案例为素材,进一步开发、设计出好问题、好活动,但更需要教师结合具体教学内容,以及学生的生活体验,设计好情境、好问题. 这需要教师真正意识到“综合与实践”课程的重要性,而非停留在理念的认同上;需要教师对学科基本概念、学科发展史有深入理解;需要教师对教学事件、生活事件(尤其细节)具有敏感性和洞察力,即如加拿大著名现象学教育学学者马克斯·范梅南所说:以现象学为方法论基础做教育研究有难度,需要研究者必须具备反思力、洞察力、对语言的敏感性以及对经验的持续开放性等.他的这一观点也同样适用于教师有效开发教学资源,有效设计实践课程. 二、“综合与实践”课之“流”:问题解决的综合能力 如果说培养学生的“发现、提出问题”意识与能力是“综合与实践”课程之“源”,那么“综合与实践”课之“流”就是提高学生问题解决的综合能力. 提高学生问题解决的综合能力,首要表现是综合运用基本知识解决问题.例如,在本课中,学生熟练地利用三角形“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判断“长方形的周长大于其内接椭圆的周长”.又如,计算长方形的面积时,学生习惯于笔算395×144的乘积,而教师却是:“哈哈哈,我没有为难自己.”(板书:400×150=60000)(同学们佩服地叫起来,“哦——估算”)在解决现实问题时,根据数据以及问题的具体要求,合理有效地选择“估算”,学生真正体会到了估算的必要性. 提高学生问题解决的综合能力,还表现在学生具有较强的概括与反思能力.这节课上,教师重视培养学生的概括与反思能力.例如: 师:杨明星这么画非常好的地方,第一,台湾岛不应该是一个规范的长方形……第二,……海岸线要比长方形的周长长,可以往外画,也可以往内画.她只是疏忽了南北纵长. 又如,在教师的示范和引领下,学生的概括能力有明显变化. 生:第一个就是不能超出长方形边框,否则的话面积会大;第二个就是一定要弯曲,增加周长,否则的话还是不比1100长. 师:这两点概括得真有水平,佩服!下次注意把话说准确就更好了.第一,不能超出长方形边框,否则南北纵长和东西最宽就不符合了.第二,要有弯曲,否则就不比1100千米长. 提高学生的概括与反思能力不是靠说教,必须通过学生的实践操作、表达交流来落实,尤其需要轻松愉快的师生、生生的对话交流. 提高问题解决的综合能力,还表现在学生能够在新情境中深入理解并灵活运用基本数学概念,这一点在本课中非常突出.“台湾长什么样”这节“综合与实践”课,主要涉及图形的长宽、周长与面积等基本数学概念.教学中常见这种现象:图形的“周长”“面积”都学完后,尤其到高年级,在做题或解决实际问题时,经常有学生混淆图形的周长与面积,如求周长时套用面积公式,周长与面积的单位混淆,面积单位不写“平方”等.如何真正让学生理解图形的这两个度量值? 以往在学习图形的周长和面积时,往往是“给定图形,测量或者计算这个图形的周长或面积”,图形给定,其形状、周长、面积都是唯一确定的.但是,若不给出具体的图形,而只是告知这个图形的周长、面积等数据,则这个图形的形状是不确定的.解决前面的传统问题时,学生容易混淆图形的周长与面积这两个概念.那么,如果只知道一个图形的周长、面积,再来画出这个图形,是否更有挑战性呢?是否更有助于学生对“周长”“面积”这两个概念的深层次理解呢?华老师的“台湾长什么样”一课,就是从这个角度让学生再一次深入理解图形的“周长”与“面积”概念. 通过分析本堂课教学中的一些细节,就能发现学生对图形的周长和面积的理解是有些混乱的.例如,在第一次画“台湾长什么样”时,有下面的对话和作品展示(作品展示略). 杨明星:通过老师讲解,我认为台湾岛应该要比长方形大出一些,但是它也不是完全都是大出一圈,于是我多加了一些凹凸部分. 生:我不同意你的话,通过老师给的资料,台湾岛的长是395千米,宽是144千米,现在长方形的长和宽已经是有点大了.应该是再往里画一点,不能凸出了. 由上述对话,可以看出杨同学在理解“周长”时表现出“时而糊涂时而明白”的特征:心里知道台湾本岛的周长比长方形的周长长,但表述出来就变成了“面积”,一会儿又说加了“凹凸部分”,好像又在说“周长”,即该同学对周长概念的理解是不稳定的,“头脑里想的”与“语言表达出来的”有些不一致,这是学生在没有真正地理解某个数学概念时的典型表现.学生的这个认识过程很自然,因为周长和面积这两个量是刻画同一个图形的两种属性,即一个是“线段(一维空间)”长短的刻画,一个是“二维区域”大小的刻画,这两个量同时“附着”在一个图形上,对于学生而言,“面积”相对来说易于感知和建立表象,“周长”却更为抽象.因此,本课“逆向”解决周长和面积问题,尤其是通过几次画图的对比,深化了对图形周长的理解. 三、“综合与实践”课之“长流”:不断质疑,开启探究之窗 批判、质疑的精神与习惯,激发学生对“学习”本身的激情与渴望,是“综合与实践”课之“长流”.只有学生不断质疑,永远对事物保持好奇与探究之心、之愿、之勇气,学生才能不断创新与发展.因为“学生们不是为他人而学习,不是为父母、老师或者名声和荣誉而学习,而是源于他们自己的渴望和热情,而这种内在的动力是稳定和持久的”. 培养学生的批判与质疑精神,激发学生的探究愿望,正是设计本课的重要目标,在实际教学中也达成了这一目标.例如,在呈现台湾地图(长方形内的台湾地图)后,立刻有学生提出问题. 生:我感觉海岸线的长比长方形的周长小? 师:能大胆地怀疑,真了不起!这是怎么回事? 观察地图,直观上感觉“台湾的海岸线确实比长方形的周长”小.实际情况怎么和计算的不一样呢?很自然就引发了学生进一步思考、探究的愿望与动力.因此,教师出示了面积不变、周长不变,但形状改变,以及雪花曲线等图形,拓展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为进一步探究开启一扇窗,即“海岸线”问题. “海岸线”问题蕴含着太多的奥秘.正是追问“英国的海岸线有多长”这个朴素而深奥的问题,使得一个新的数学分支——分形几何学得以创立.1967年,数学家曼德布罗特(B.B.Mandelbrot)提出了“英国的海岸线有多长”的问题,这好像极其简单,但其结论“英国的海岸线长度是无限长的”却令人费解.怎么会呢?与日常经验和感觉是矛盾的. 实际上,长度依赖于测量单位,假如以1 km为单位测量海岸线,得到的近似长度值是将小于1 km的“迂回曲折”忽略掉了;若以1 m为单位测量,则忽略掉了小于1 m的“迂回曲折”,测量结果将变大;随着测量单位进一步变小,测得的长度将越来越大,这些越来越大的长度将趋近于一个确定值,这个极限值就是海岸线的长度. 但曼德布罗特发现了不可思议的事情:当测量单位变小时,所得的长度是无限增大的.他认为,海岸线的长度是不确定的,或者说,在一定意义上海岸线是无限长的.这怎么可能呢?海岸线明明是客观存在着的,它的长度应该是一个确定的数值啊?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传统的测量方式以及测量单位不适合测量海岸线,传统上,我们将自然界大量存在的不规则形体进行“规则化”处理.例如,我们将海岸线折线化,得出一个有意义的长度,海岸线粗看起来是折线,但任意细看其中一段线段,发现它还是由折线构成,再细看其中一段线段,还是由折线构成的,如此深入下去,发现其结构总是相似的,看似直线的东西,其实细微之处并不是直的.测量得越细致,总长度就越大.你可以无限地细测下去,于是英国的海岸线长度只能是无限长的了. 因此,要定量地分析类似海岸线这样的图形,必须引入“分形维数”,经典的“维数”已不适用.经典维数都是整数:点是0维、线是1维、面是2维、体是3维,而分形维数可以取分数,简称分维.于是,曼德布罗特创立了新的数学分支——分形几何学.1982年,他出版《自然界的分形几何》一书,分形概念迅速传遍全球. 更值得我们教育者思考的是,曼德布罗特是一个爱思索“旁门左道”问题的人,这样的人不正是“创新型人才”吗?没有这样的人,数学、科学怎么发展?设计“综合与实践”课程的“长流”,也许就是给学生时间、空间以及具体的平台,让学生有机会成为思考“旁门左道”的人,给学生打开一扇探究与发现之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