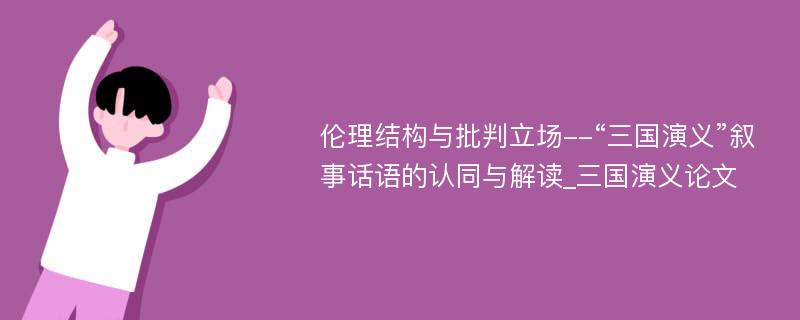
伦理架构与批判立场——《三国演义》叙事话语的辨识与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演义论文,伦理论文,架构论文,话语论文,立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
5293(1999)03—0128—08
所谓“历史演义”,简而言之,是作者在某种价值理性的导引下,对历史所作的情节设置和话语建构。一般而言,它是由相互关联的两个层面——由历史叙述所形成的“故事结构”和由历史阐释所形成的“意义结构”——熔铸而成的。这种将历史过程故事化、文本化的叙事,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对历史的话语重建。所谓“演义”,就是将历史上升到话语层面而形成的意义阐释和价值建构。就本文所讨论的《三国演义》(以下简称《三国》)而言,它所演义的主题,用一句简单明了的话概括,清溪居士所谓“意主忠义而旨归劝惩”一言,足以当之。它一方面根据“讲史”的传统(所谓“讲”,既是一种历史的通俗化叙事,又是一种文化精神的阐释),通过历史事件的敷衍和人物的类型化塑造,建构并维护人类的道德正义原则和基本的伦理准则;一方面又以此为架构,批判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切不合理现象。从而形成内含于《三国》中的两套叙事话语:一是从道义伦理的角度,对人物的行为与人格加以评判与归类;二是站在批判的立场上,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形式合理性作出反省。如果将前者视为贯穿于小说叙事之中的一种伦理主义话语,那么后者则是一种以批判为职志的知识分子话语。但二者又是紧密相联的,或者说是在同一语境中相互发明的两套话语。本文的讨论,就是通过对该小说叙事话语的辨析与转述,企图发掘出它深层的文化语法和叙事伦理,并可望对该小说的研究,注入一种人文关怀的内涵。
一、评判人物的伦理化取向
《三国》的叙事所遵循的伦理,是一种儒家的“道义伦理”。对“道义”的内涵,我们不妨作如是界定:其中“道”,是人之行为的最高规范和终极方向,代表精神的超越性诉求和信仰;“义”,则泛指人际交往和日常行为所应遵守的当然之则。前者仿佛一种宗教性伦理,后者是一种普遍的社会伦理。从行为类型看,遵“道”奉“义”的行为,无疑是一种价值合理性的行动:合乎儒家的价值理性或伦理准则。由对“道—义”的遵奉和信守所形成的叙事,就是《三国》小说的叙事伦理。小说入篇先从“宴桃园豪杰三结义”写起,正乃这一叙事伦理的形式敷陈和框架奠基。
首先,这一富于民间小传统色彩的“结义”形式,是他们之间共有的政治抱负和人生关怀的沟通:“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通过这一仪式的“阈门”,他们的行动便跨入了一个自觉的人格实现过程,历史使命的承当过程,具有了价值的合理性或合道性。
其次,这一“结义”形式,又是他们之间生死之谊和伦理关系的确立:“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经由这一仪式的定位,他们的行动便进入了一种角色的认同与扮演过程,并在认同与扮演中获得人生的意义,完成其人格的价值。在这一“信用共同体”中,遵守契约是每个人的“义务”,恪守忠义,是他们达成一体的认同基础。由此,我们又可将这一结义的表达方式,视为一种布思所说的“认同修辞学”的形式,在这种修辞情境中,恰如布思所言:我们“是在形成共同目的、价值和意义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实际上,我们相互之间相像胜过差异,我们存在于共性中比存在于个性中更有价值:离开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去考虑,我们事实上就变得什么也不是了。”[1](P81)就关、张而言,他们和刘备的关系,既是一种“弟兄”关系,又是一种君臣关系(日后)。作为弟兄关系,他们亲如手足,互相负责;作为君臣关系,关、张又甘当配角,忠心侍奉。按照蒂利希的观点,当一个人把自己看作是他所参与的社会集团的一个配角时,他就是在肯定他自己了。[2](P86)就刘备而言,不但视关、张如手足,甚至为了遵守契约,可以视江山如敝屣,为关羽报仇伐吴的行动便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这一行为虽如赵云所谏,是一种废公重私的行为,如秦宓所劝,是一种“徇小义”而“忘大义”的行为,但在刘备看来,“云长与朕,犹一体也,大义尚在,岂可忘耶?”“若不报仇,是负盟也!”“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所以从目的—工具合理性的角度看,这一伐吴行为无疑破坏了诸葛亮的统一战线政策,是一种“非所以重社稷”的非理性行为;但从价值理性的角度看,它恰恰具有形式的非理性而实质的合理性或合道性,是一种不计后果的激情、信仰和关怀所驱使的情感型行动,即使新创之业有所颠覆也在所不计。此外,如关羽于许田打围时不顾生死、挥刀拍马去杀曹操的行动是如此,于华容道又义释曹操的行动也是如此;张飞于古城更不答话,挺矛直刺关羽的行动是如此,待关羽死后急兄仇失去理智的行动也是如此。
相比较而言,如果我们把刘、关、张的行为仿照马克斯·韦伯的分类,归结为一种“价值合理性行动”,因而带有“道义伦理”的情感型特色;那么曹操的行为则是一种“目的—工具合理性行动”,而带有“工具伦理”的非情感型特色,在此伦理的支配下,“宁教我负天下人,
休教天下人负我”,便成为他奉守的人生信条和处事原则。此言之实质,是视天下人皆为实现我之目的的工具,为了达到我的目的,天下人应该也必须为我所用。就拿他的所谓爱才、惜才、养才来说,虽有折节下士之名(如对许攸),知人善任之明(如对郭嘉),但究其实质,乃是将人才视为他夺取天下的工具,用时奉为上宾,可做到言听计从,一旦用过之后,虽不至弃若敝屣,也定然置诸脑后,而且稍有违逆,便赐之以死,荀彧、荀攸便是两个最典型的例子。另如为赚来徐庶,不惜使用诡诈手段,这在刘备是决不肯为之事。当徐庶轻信伪书,欲离刘备而去时,孙乾密谓刘备曰:“元直天下奇才,久在新野,尽知我军中虚实。今若使归曹操,必然重用,我其危矣。主公宜苦留之,切勿放去,操见元直不去,必斩其母。元直知母死。必为母报仇,力攻曹操也。”若将曹、刘换位,此言必定奏效,然刘备却曰:“不可!使人杀其母,而吾用其子,不仁也;留之不去,以绝其子母之道,不义也。吾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读《三国》,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曹操的善“借”。毛宗岗评曰:“曹操一生,无所不用其借:借天子以命诸侯;又借诸侯以攻诸侯;至于欲安军心,则他人之头亦可借;欲申军令,则自己之发亦可惜。借之谋愈奇,借之术愈幻,是千古第一奸雄。”在如此等等“借”的行为中,我们可分明看到,他与人的关系完全是一种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既然连“天子”也可视为自己号令诸侯的工具,其他人更不言而喻了。不惟如此,他一生无真,宜笑反哭,宜哭反笑,连自己内心情感的表达也工具化、技术化了,此不赘举。
正因为曹操一生“谲而不正”,小说在第119 回中借贾充之口评道:“操虽功盖华夏,下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这显然是从伦理主义的角度作出的评价。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站在政治家的立场上看,那么,作为君主,“究竟是被人爱戴比被别人畏惧好一些呢?抑或是被人畏惧比被人爱戴好一些呢?”马基雅维里的回答是:“最好是两者兼备,但两者合在一起是难乎其难的。如果一个人对两者必须有所取舍,那么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是安全得多的。”[3](P80)曹操的选择,仿佛如此。他能在一般的情势下,尽可能做到二者兼备(如击败袁绍后,下令烧毁己方私通袁绍的书信),又在必须做出取舍的时候,置残酷之名于度外(如耿纪、韦晃等谋反事败,竟将三百余官员尽皆斩首),一切凭自己的意志办事。这正如马氏所言:“人们爱戴君主,是基于他们自己的意志,而感到畏惧则基于君主的意志,因此一位明智的君主应当立足在自己的意志之上,而不是立足在他人的意志之上。他只是必须努力避免招仇惹恨。”[3](P82)正是基于避免招仇惹恨的考虑,曹操才不惜玩弄种种手段,以掩盖其真实用意。此用马基雅维里的比喻来形容,他既是一头狐狸,又是一头狮子:“由于狮子不能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则不能够抵御豺狼,因此,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3](P83)由此可见,君主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的行为很难立足于道义伦理的基础之上,因为政治有着完全不同的任务,它与道德本就处在一种固有的紧张之中。[4](P114)即使刘备的行为,亦复如此, 尽管小说是将刘备置于道义伦理的框架之中加以建构与评判的,但他的许多基于后果考虑而采取的行动,则分明是一种工具合理性行动,也即遵循的是工具伦理或责任伦理,而非道义伦理或信念伦理。如许田打围中出于“投鼠忌器”的后果考虑而摇手送目、阻拦关羽去杀曹操;又为防曹操之警觉,不惜以“学圃”为韬晦之计。另如他的假哭荆州,也是以“泪”为工具,以“哭”为手段而达到其目的的。尤其是他起初本不忍以不义的手段谋取同族兄弟刘璋,当取而代之后,又握着刘璋之手泣曰:“非吾不行仁义,奈势不得已也!”既得益州,孔明提出一土难容二主,必得将刘璋安置荆州,刘备不应,孔明劝曰:“刘璋失基业者,皆因太弱耳。主公若以妇人之仁临事不决,恐此土难以长久。”为长久之计,只得从之。可见,为了达到目的,政治家不可能也不允许他奉行一种绝对伦理,“因为绝对伦理是不问后果的。”[4](P107 )这正如韦伯所指出的:“一切有伦理取向的行为,都可以是受两种准则中的一个支配,这两种准则有着本质的不同,并且势不两立。指导行为的准则,可以是‘信念伦理’,也可以是‘责任伦理’。这并不是说,信念伦理就等于不负责任,或责任伦理就等于毫无信念的机会主义。当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恪守信念伦理的行为……同遵循责任伦理的行为,即必须顾及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这两者之间却有着极其深刻的对立。”[4](P107 )正是由于这一对立,才造成小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的客观效果。也正因为如此,“即使在目的使手段圣洁化这个原则上做一些让步,也无法让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和谐共处,或是判断应当用哪一个目的来圣洁化哪一个手段。”[4](P109)换言之,“当什么时候、 在多大程度上,道德上为善的目的可以使道德上有害的手段和副产品圣洁化,对于这个问题,世界上的任何伦理都无法得出结论。”[4](P108 )儒家试图解决这一对立,提出一种变通的处理方法,这就是“经”(道德原则的绝对性)与“权”(相对性)的结合。这种“执中而权”的变通,显然是出于对境遇的理性分析,其作用“主要在于通过各种具体规范的适当调整使道(最高规范)的运用更为完善,而并不是从根本上偏离道。”[5](P77)但在实践中,这一“让步”,往往成为政治家玩弄“权术”的借口,“经”与“权”之间无法达成统一。就此而言,曹、刘之“权”,并无实质的区别,尽管小说为刘备的行“权”作“伪”,找了种种辩解的理由,力图将刘备塑造成一个“仁君”的典型,但道德和政治的内在紧张,使作者的目标很难实现,他忽略了的恰恰是韦伯所指出的:每一个领域都受着不同的定律支配,在政治领域中,真实的情况不是“善果者惟善出之,恶果者惟恶出之”,而是往往恰好相反,任何不理解这一点的人,都是“政治上的稚童”。[4](P110 )此用小说中诸葛亮的话来说,就是“妇人之仁”。
但是,我们也当看到,作为儒家知识分子的罗贯中,在《三国》叙事中,遵循的是儒家的政治理路,一直想以道德的力量来提升政治行为,使政治变成一个德化的政治,因而在理想君主的塑造上,自会极力突出政治家的道德风范,关注他行为的价值合理性,并以此为尺度来裁量人物,判别是非。于是,在这一叙事伦理的框架之中,曹操难免受到大力抨击。这就引出一个如何认识他和评价他的问题。众所周知,“奸雄”是小说对他的定位。奸和雄,分别是从伦理的角度和政治的角度作出的评判,“奸雄”连词,使“雄”的评判带有了伦理化的倾向。换言之。小说主要是从伦理的角度对他的行为作出评判的。但将他的“奸雄”置于马基雅维里的视域看:当君主既不能占有全部优良品质,也不能完全保持这些品质时,他“必须有足够的明智远见,知道怎样避免那些使自己亡国的恶行,并且如果可能的话,还要保留那些不会使自己亡国的恶行,但是如果不能够的话,他可以毫不踌躇地听之任之。还有,如果没有那些恶行,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的话,那么他也不必要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因为如果好好地考虑一下每一件事情,就会觉察某些事情看来好像是好事,可是如果君主照着办就会自取灭亡,而另一些事情看来是恶行,可是如果照办了却会给他带来安全与福祉。”[3](P74—75)所以,君主对残酷之名不当介意,曹操正是如此,陈琳的一篇讨曹檄文,乍闻虽使他感到震惊,却奇妙地治好了他的头风病,这说明他根本不介意于所谓恶名,这正如马氏所言,君主必须提防滥用仁慈,不然会自取灭亡,残酷的君主“比起那些由于过分仁慈、坐视发生混乱、凶杀、劫掠随之而起的人说来,是仁慈得多了,因为后者总是使整个社会受到损害。”[3](P79)曹操的平定北方,亦可作如是观。这自然会出现评价上的分歧:当我们从价值理性或伦理主义的角度看,曹操的许多奸诈行为理应受到贬斥;但当我们从工具理性或历史主义的角度看,他又在消除动乱的历史发展中作出了巨大贡献,诚如他所言:“如国家无孤一人,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小说在他死后曾引诗评道:“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这确乎是公正的评价。“功首/罪魁”两种角色的叠合,“遗臭/流芳”两种评价的统一,使否定者和(为之)翻案者的立论总显出偏狭。看来只有将判若两人的曹操合而为一,将历史评价和伦理评价集于一身,才能呈示出曹操的真面目。
我们还可看到,在小说中,凡是“义”的价值合理性行动,均无一例外地受到褒扬,如貂蝉的舍身报国就是典型的一例。尽管用现代的观点看,可将貂蝉视为男性政治斗争的工具,但是站在传统伦理文化的立场看,貂蝉的舍身,既是“报主”更是“报国”的“大义”行为,竟大到将汉家天下,系于她一人之身,从而赋予她的行为以价值的合理性。与这一“重扶宗庙,再立江山”的政治任务相比,个人之身(贞操)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当貂蝉完成任务后,小说便不去管她的结局如何,只言曹操杀了吕布后,“将吕布妻女载回许都”完事,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失却贞操”尽管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但毕竟是终身的污点,无法再给她一个合理的结局。
另外,对气节的强调,也是小说赋予人物合义行为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类叙事中,既注重突出他们“奋然勇决”的自主性和“特立独行”的精神,又为这种精神灌注了一种激昂天地的情感力量,正如墨子刻所指出的,在儒家的理念中,“气骨”、“气格”、“志气”、“义气”以及“气节”等用语,都反复使用到“气”这个字眼,“所有这些语辞,都含有从情感上激起的一种道德力量和勇气的意识。”[6](P40)这种富于情感的勇气,摒除了个人内心的恐惧和焦虑,使人获得了一种超越生死的力量。在小说中,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单就女性而言,如徐庶之母“不畏鼎镬,不惧刀斧”,“守节无亏”,“气若丘山”的精神(第37回); 姜叙之母临死“全无惧色, 指马超而大骂”的勇气(第64回); 马邈之妻耻于丈夫的“不忠不义”而自缢身亡的果决(第117回);夏侯女截耳断鼻,自残其体的贞烈以及“不以盛衰改节”、“不以存亡易心”的气节(第107回)等等,皆是如此。
唐君毅先生说,在描述一个成为行为典范的人物时,儒家传记作者的兴趣在于将传主的行为当作一种普遍道德精神加以表述,而完全不在于传主这些行为所由以发展起来的细节原委和经验。[6](P43)这在中国的讲史小说中,尤其如此。这种对普遍的道德精神的张扬和对人物之伦理主义的评判视角,又构成小说审视历史的批判性立场,而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定局看历史,它所关注的是权力的文化合理性和合法性,因而对历史采取的是“阐释”的方法,而不是对既往历史的“注释”。
二、审视历史的批判性立场
余英时先生指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开始就管的是凯撒的事,作为“社会的良心”,他们是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者。他们“不但代表‘道’,而且相信‘道’比‘势’更尊。所以根据‘道’的标准来批评政治、社会从此便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分内之事。由稷下先生‘不治而议论’的事观之,知识分子这种‘言责’早在公元前四世纪时即已为官方所承认。”[7](P107)所谓“不治而议论”的“不治”, 即“无官守”之谓也;“议论”则是今天所谓的批评。这样就把知识分子和批评完全等同了起来。[7](P105)三国分争的时代是一个天下无道、 诸侯争霸的时代,处于边缘位置上的罗贯中正由于脱离了体制的羁约,找到了一套属于知识分子自己的批判性话语,代道立言,批评故事,从而构成《三国》审视历史的批判性立场(这在毛宗岗的修订中得到更进一步的加强),充分体现出知识分子的身位自觉和独有的批判性、否定性的人文精神。
这种“士志于道”的精神,既折射在小说中塑造的那些“持道不屈”的知识分子身上,折射在那些“为王者师”的人格典范上,也表现在对历史之非理性发展的价值否定及对其形式合理性的文化批判上。
“持道不屈”最典型的人物,当为祢衡。在他身上,一者表现出自由知识分子“不治而议论”的历史性格和以“师”自重的身份自觉;二者体现了不枉“道”而从“势”的浩然之气和信仰承当。祢衡经孔融举荐初见曹操时,本意欲曹操以“师”礼相待,当遭到曹操“势”的相压后,面此轻蔑,他只有以自高身份的办法,来保持“道”的尊严,并以此抗“势”。这是因为在中国“政教合一”的体制中,“道统是没有组织的,‘道’的尊严完全要靠它的承担者——士——本身来彰显”[7](P101)此与西方上帝的尊严可以通过教会制度而树立与保障迥然有别,“中国的‘道’则自始即是悬在空中的。以道自任的知识分子只有尽量守住个人的人格尊严才能抗礼王侯”[9](P102), 此即所谓“不自高,人将下吾;不自贵,人将贱吾。”(《孔丛子·居卫》)祢衡不惧生死,挝鼓骂曹的行为,正乃知识分子“道”尊于“势”的理念信仰和以“道”抗“势”之宗教承当精神的体现。当曹操问他“汝有何能”时,祢衡答道:“天文地理,无一不通;三教九流,无所不晓;上可以致君为尧、舜,下可以配德于孔、颜。岂与俗子共论乎!”(第23回)这段自我表白,高度概括了“士”的品格及扮演的历史角色。但祢衡虽高估了道统之力,轻看了政位之势,可曹操也不敢遽然杀之,用他的话来说:“此人素有虚名,远近所闻。今日杀之,天下必谓我不能容物。”只好转借他人之手杀之。
从祢衡,我们又想到许攸。攸因向曹操献策立功之故,便以“师”的身份自居。当操凯旋冀州将入城门时,许攸纵马近前,以鞭指城门而呼操曰:“阿瞒,汝不得我,安得入此门?”此时操反大笑,而众将则俱怀不平。操之大笑,并非胸怀宽广,真将许攸视为“师友”,许攸在当时能逃其不杀,除过上述不遽杀祢衡之理由外,另有一着,就是有意放纵许攸的骄气,假他人之手以杀之,后果为许褚所杀。这表明,“知识分子与君主的结合只能建立在‘道’的共同基础上面”[7](P101 ),假如错看形势,重演稷下先生的故事,那就性命难保了。
对知识分子的吸引与重视,是三国分争时代各个军事集团和政体共有的特点,也是小说用笔的重心之一。问题很清楚,在互相争霸的情势中,统治者“除了需要知识分子的技术服务外,同时更需要‘道’对他们的‘势’加以精神的支持。建筑在赤裸裸的暴力基础上的‘势’是不可能有号召力的;政权多少都需要具备某种合法性(或者也可以说是‘合道性’)。”[7](P119)上述之曹操不遽杀祢衡、许攸, 正是基于后者的考虑。对此,他还有一段颇为重要的议论:他在克定冀州,于袁绍墓前吊唁时,对众官回忆道:“昔日吾与本初共起兵时,本初问吾曰:‘若事不辑,方面何所可据?’吾问之曰:‘足下意欲若何?’本初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沙漠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吾答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此言如昨,而今本初已丧,吾不能不为流涕也!”(第33回)这一段概括性的总结,深刻地揭示了曹胜袁败的主要原因。曹操不但明白“任天下之智力”是取得胜利的关键而不在占地之多寡;而且懂得“以道御之”更是关键中的关键。只有“以道御之”而不是“以势控之”,才能既得到他们的竭尽全力的扶佐,又可增加自己的政治号召力。所以当袁谭被杀后,曾因谏袁谭而被逐的青州别驾王修,竟冒着曹操“敢有哭者斩”的号令,亲来吊哭收尸,曹操叹息曰:“河北义士,何其如此之多也!可惜袁氏不能用,若能用,则吾安敢正眼觑此地哉!”(第33回)但也正由于他过分明白这一道理,反而流于某种表面上的敬重而实际上的利用,失去了真诚。在这一点上,刘备与之完全相反,“三顾茅庐”就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而被小说大肆渲染的典型例子。
刘备“三顾”之礼贤下士的敬与诚,固不待言,而诸葛亮之“隆中对”,也是以“王者师”的身份自居,纵论天下大事,指陈利害得失,使刘备“顿开茅塞”,“如拨云雾而睹青天”。自此,“玄德待孔明如师,食则同桌,寝则同榻,终日共论天下之事。”(第38回)不惟如此,小说还进一步写道:“却说玄德自得孔明,以师礼待之。关、张二人不悦,……玄德曰:‘吾得孔明,犹鱼之得水也。两弟勿复多言。”(第39回)从政统而言,刘备是主体(如鱼),从道统而言,则诸葛亮是主体(如水),也即“士与王侯在政统中可以是君臣关系,但在道统中则这种关系必须颠倒过来而成为师弟。”[7](P103)从此, 诸葛亮便以师、友、臣的关系,与刘备共处。这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知识分子(道)与君主(势)的关系。在白帝托孤中,刘备不但说出这样推心置腹的话来:“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而且亲嘱其子:“朕亡之后,尔兄弟三人,皆以父事丞相,不可怠慢。”为报此知遇之恩,诸葛亮“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这里“报”的观念,已超越了单向度的服从依赖关系,臣的忠乃是通过君对臣的信任、尊敬、礼待而获得的回报。这种名为君臣实乃师友的关系,正是罗贯中及众多知识分子心目中理想的关系而给予大力歌颂,并通过诸葛亮形象的塑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知识分子典范,以寄托作者自己“为王者师”的情结。
诸葛亮不仅是知识分子参与政治为王者师的优秀楷模,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身份自觉(这在他自比管仲、乐毅的形象认同中亦可充分窥见)与师道尊严;而且他又是儒家“内圣外王”之理想人格的光辉典范,是集知识(我)/道德(我)/政治(我)——三位一体(“三我”合一)的完人形象。台湾黄俊杰先生说:“在儒家传统的大经大脉之中,知识、道德与政治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历代儒者思考问题的一个通贯性主题。从传统儒家的立场看来,道德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根本,知识则是他的外在凭藉,政治则是他由内通向外,用道德与知识来美化人间的途径。我们如果用春秋时代的人的说法,则‘道德’就是‘立德’,‘知识’就是‘立言’,‘政治’就是‘立功’,同为人间之三不朽的盛业。”[8](P248 )就诸葛亮身上的“知识(我)”而言,小说更多地赋予他超常的军事才能,这一通天文、识地利、知奇门、晓阴阳、察阵图、明兵势的才能与智慧,有违历史真实,更多传奇色彩,以至于出现“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的现象。这种适度的“神化”,显然是小说为他之“政治我”的实现所附加的必要条件,于是“优秀的才智和神奇的法力共同刻划出典型的谋士形象,‘满足了目不识丁与知识分子所共有的成熟嗜好和原始需要’。由于作者自己通常也是书生,不免也反应了他们的某些理想和梦想。”[9](P436 )诸葛亮也就成了一个超越了个体存在和历史存在的文化符号。
众所周知,《三国》是罗贯中熔正史与民间文艺(讲史与杂剧)于一炉加铸而成的。由于一方面作者退守民间,处于边缘,因而比体制中人更具有“士”的独立精神和批判意识;另一方面,在历史的更替演变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的固守与传承往往是在民间。于是,大传统(文人)与小传统(民间)便有了相互融合的基点。这一大/小传统的融合,使《三国》具有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品位,其显著的表现,就是对正史话语霸权的突破,将“正统”赋予失败的蜀汉一方。对其正统地位的肯定,也就是对“道”的肯定,对其政权之文化合理性及合法性的肯定。余英时先生指出,中国知识分子从最初出现在历史舞台的那一刹那起,便与所谓的“道”分不开,是“道”的自觉承担者。中国的“道”源于古代的礼乐传统,这基本上是一个安排人间秩序的文化传统,这就决定知识分子主要是以文化秩序为其关怀的对象,在他们而言,文化秩序才是第一义的。正由于这样的原因,身为知识分子的罗贯中,对这一段历史的兴趣,并非在谁最后取得胜利上,而是将叙事聚焦在“道”也即儒家传统的价值合理性上,从而造成对曹魏及司马政权的否定与批判,并将司马之废曹,视为“依样画葫芦”的“果报”。
这一对历史之既成局面(形式合理性)的批判与否定,所追求的是一种实质的合理性或合道性。这也就是说,在三国分争阶段,取得胜利的一方虽占有“天时”而具有形式的合理性,但究其实质,则是一种在形式合理性遮掩下的实质非理性。这一非理性在小说中具有两层含义:一为历史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或价值理性为转移,它往往受“天命”这一非理性因素的支配,这在诸葛亮发出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浩叹中可充分窥见;二是在历史的发展中,往往是目的—工具合理性起着重大作用,我们常看到的事实是儒家所设定的“圣—王”理想,在历史上经常被演变为“王—圣”,因而统一天下的一方,虽在完结割据局面上作出历史贡献,但这一“形式”上的合理性(统一),并不代表或绝对代表权力的实质合理性或合道性,也即不一定符合儒家的道德政治,因为政权的获得并不意味着正义的占有。孟森先生指出:“中国自三代以后,得国最正者,惟汉与明。匹夫起事,无凭藉威柄之嫌;为民除暴,无预窥神器之意。”[10](P13)这说明其他朝代之得国, 来路并不很正,经不起道德的检视。正因为儒家知识分子是以伦理道德为坐标对历史进程加以评判的,所以当道德理想失落之后,对历史的总结,只能往不可知的“天命”上靠拢,这是为不可预测的历史发展所能寻找到的一个唯一“合理”的解释。但我们又分明看到,在这一对“天命”的敬畏与困惑中,深藏着对历史之非理性发展(“治乱无常”)及其形式合理性(既成局面)的批判与反省。
这一批判意识,同时也表现在对历史价值的消解上。因为“天命”的归结,并不能真正解决作者思想上的困惑(它的不可知性,正乃作者困惑的表现),于是面对历史的定局和价值的失落,很容易滋生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感受,或者说这一虚无主义的产生,是道德理想主义破灭之后的必然结果。《三国演义》采用杨慎的〔临江仙〕作为篇首词,即是这一感受的艺术表达。它作为“隐含的读者”(这是后人加上去的,可视作附加者对小说中召唤反应结构的发掘,并使之具体化),以一种独特的寓悲壮于闲情的低调形式,叙说着作家内心的悲剧性感受和体验;它又作为“隐含的作者”(附加者对作者之“第二自我”的识别,并将之具体化),站在超然的立场上,提供了一种对历史的阐释。我们从它表层的解构性话语中,可读出其深层的对历史之非理性发展的批判与反讽。
收稿日期:1999—04—28
标签:三国演义论文; 刘备论文; 曹操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三国论文; 诸葛亮孔明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道德批判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君主制度论文; 道德论文; 儒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