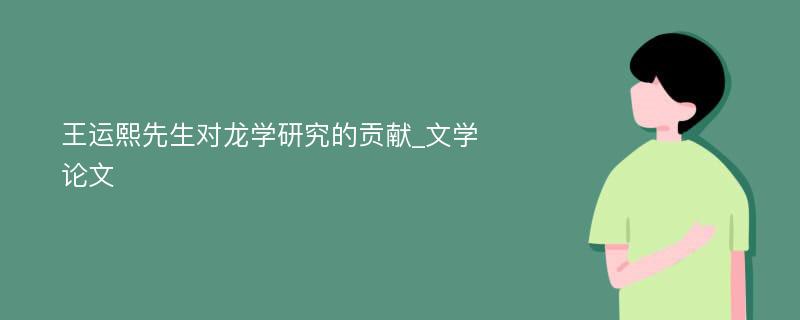
王运熙先生“龙学”研究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贡献论文,王运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刘勰《文心雕龙》的研究,称为“龙学”,早已成为显学,不但我国学者,而且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学者,都为之倾注了大量心力。这既是因其体大思精,包孕丰富,文辞精美,在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与其成书距今一千五百年、采用骈俪文体、今人不易彻底读懂有关。我校中文系教授、著名古典文学专家、《文心雕龙》学会前会长王运熙先生,对于该书的研究独有心得,做出了重大贡献。这里拟就笔者个人的体会,略加论述。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前期,学术界展开了一场规模较大的对《文心雕龙》“风骨”概念的讨论。王先生关于《文心》的第一篇论文,题为《〈文心雕龙〉风骨论诠释》,便是为参加那场讨论而作,发表于1963年。第二篇则是讨论《文心雕龙·辨骚》的文章,发表于1964年。那时刘大杰先生主编大学文科教材《中国文学批评史》,王先生也参加了。书中《文心雕龙》一章约三万字,系由王先生一人执笔。十年动乱之后,先生继续进行研究,于八十年代出版了《文心雕龙探索》,至本世纪初又出了增补本。八十年代中后期,王先生和顾易生先生合作主编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第二卷《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中的《文心雕龙》一章约十万字,也由王先生执笔撰写。此外先生还和周锋先生合作撰写《文心雕龙译注》,出版于1998年。 王先生的《文心》研究,前后历经数十年。他的有关论著,读来平易朴实,而观点新颖,实事求是,力求深入、准确地阐发刘勰的原意,很有自己的特点,为“龙学”发展做出了卓越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本文不可能作详尽的论述,只就关于《文心雕龙》的性质、基本思想和结构、对于风骨等概念的解释以及刘勰对文学作品艺术特征的认识三个方面,略作介绍。 (一) 关于《文心雕龙》的性质、基本思想和结构。 学界一般将《文心雕龙》视为我国古代最有系统的一部文学理论著作,相当于今天的文学概论。有的学者还称之为一部古代美学著作。王先生则赞同范文澜先生所说“《文心雕龙》的根本宗旨,在于讲明作文的法则”,指出《文心雕龙》原来的宗旨是指导各体文章的写作,谈论作文的原则和方法,是一部文章学、文章作法的书。他写过《〈文心雕龙〉的宗旨、结构和基本思想》、《〈文心雕龙〉是怎样一部书》两篇论文,①专门论述这一问题。 王先生说,《文心雕龙·序志》开宗明义,说道:“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明确指出该书是讲如何用心作文章的。这就是《文心雕龙》的宗旨。这一宗旨贯穿全书,在全书的结构安排上也体现出来。开头的五篇《原道》、《征圣》、《宗经》和《正纬》、《辨骚》,刘勰自称是“文之枢纽”。王先生认为所谓枢纽,就是讲作文章的总的原则,亦即关于如何写好文章的基本思想。以下从《明诗》至《书记》二十篇,一般被称作“文体论”,王先生认为,确切地说,应称为各体文章写作指导。王先生认为这二十篇的内容,都是所谓“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其中“敷理以举统”的篇幅远少于“原始以表末”、“选文以定篇”,却是一篇的结穴所在,地位最重要。它的任务,是阐明各体文章的体制特色和规格要求。《序志》所谓“上篇以上,纲领明矣”,“敷理以举统”就属于“纲领”。刘勰称之为纲领,显示出对此项的重视。《神思》以下至《总术》十九篇,是打通了各种文体论述写作。这些篇目与前二十篇相辅相成,都是谈如何写好文章,只是一则分体而论,一则打通了加以论述,角度不同罢了。再往下《时序》、《物色》、《才略》、《知音》、《程器》五篇,王先生认为在全书中属于杂论性质。刘勰感到还有一些问题,虽非直接论文章作法,但从创作修养看,也很重要,故加以论述。 王先生指出《文心雕龙》的性质是讨论如何写好文章,不是如今日所谓文学理论,但他也赞同从文学理论的角度研究《文心雕龙》。因为刘勰视野开阔,在讨论如何写作时加以展开,涉及不少文学理论问题,见解精辟,因而具有了文学理论的性质,而且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刘勰花了许多篇幅论述各体文章的作法,那些文体的很大一部分今天已经不再使用,因此《文心雕龙》在今天的价值和作用,主要是在论及文学理论之处。但就还原历史原貌而言,《文心》的性质不应混淆。 与宗旨、结构相关的一个问题,即刘勰关于写作的基本思想是什么,也是王先生着力加以讨论的。王先生说,刘勰的基本思想,是宗经与辨骚相结合,即雅正与奇丽相结合。亦即以五经的雅正文风为根本,同时“尽量采取楚辞的优长,做到奇正相参,华实并茂”。②也就是说,刘勰是要求文章写得美丽的,只是不要过分而已。正如黄侃先生《文心雕龙札记》所说:“实则彦和之意,以为文章本贵修饰,特去甚去泰耳。全书皆此旨。”③王先生对此作了具体深入的论述。他说刘勰是华美的骈体文学的拥护者,对于骈文所讲究的声律、对偶、用典等语言美都加以肯定和论述,《文心》全书也以精致的骈文写成。但是刘勰也看到了当时某些作者过分追求新奇华艳带来的弊病,因此指出在雅正与华美二者之中,必须以雅正为根本,从而形成了其关于写作的基本思想。这一基本思想不仅在“文之枢纽”五篇中予以集中论述,而且贯穿全书。 王先生的这一表述,其意义尤在于能不为时风所动而坚持实事求是的立场。“五四”时期,倡言打倒“《选》学妖孽”,虽自有其意义和必然性,但骈文从此便笼而统之地被归于扫荡之列。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学术研究为“左”的风气所笼罩,无论什么问题都得讲“阶级分析”,骈文更被视为腐朽的贵族阶级的文学,骈文所讲求的文辞之美被斥为“形式主义”的表现。因此,当时的学者往往有意无意地强调刘勰批判“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的一面,而忽视其主张华美的一面;甚至将刘勰对于当时写作中流弊的批评理解成刘勰是反对骈文,反对六朝文学发展的。王先生则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从研究对象出发,因而能透彻掌握《文心》本意,不受当时风气的影响。 对刘勰写作基本思想的认识,涉及对《文心雕龙》第五篇《辨骚》的认识问题。曾有一种意见,认为《辨骚》论述《楚辞》,应同以下二十篇一起归入“文体论”。王先生为此而作《刘勰为何把〈辨骚〉列入‘文之枢纽’?》一文,④认为刘勰设置该篇的用意,实际上并非就《楚辞》论《楚辞》,而是有着更深层的目的,即为了提出关于写作的基本思想。王先生说,刘勰既主张在雅正的基础上追求新奇美丽,便不能不强调《楚辞》。因为经书虽然被刘勰称赞为“圣文雅丽”,其实经书的大部分是质朴少文的,是不能涵盖汉魏六朝以来文学向奇丽方向发展的,刘勰也明白这一点,因而他于《原道》《征圣》《宗经》之外,还要设立《正纬》和《辨骚》(《辨骚》的地位当然在《正纬》之上)。十多年后,王先生进一步说,刘勰实际上肯定《楚辞》在艺术上超越《雅》《颂》,有重大的创新。他说:“这种不囿于经书的旧传统、大胆肯定艺术上的发展与创新,是刘勰对文学创作总要求的一个重要方面。”⑤总之,《辨骚》是体现刘勰基本思想的重要篇章,而不仅仅是《楚辞》论。除了从《文心》本身出发加以论述外,王先生还结合南朝时的时代背景,指出与刘勰同时的沈约、钟嵘都把《楚辞》与《诗经》并提,视为经典作品,是汉魏六朝文学家取法的渊源,刘勰不过将《诗经》扩大为“五经”而已,刘勰的做法与时代风气一致。 《刘勰为何把〈辨骚〉列入‘文之枢纽’?》发表于1964年。由王先生该文可以看出,虽然上面提到的《〈文心雕龙〉的宗旨、结构和基本思想》发表于20世纪八十年代初,但他关于刘勰基本思想的观点,早在六十年代上半期已经成熟。只是在关于《文心》结构的问题上,当初王先生还将《明诗》以下二十篇作为文体论,后来则觉得应视为“分体论文章作法”,才更加确切。 (二) 王先生的《文心雕龙》研究,是建筑在一字一句精读文本基础之上的,因而他对于书中某些词语所表述的概念、范畴,对于某些文句,尤其是一些难懂的、有争议的地方,予以特别的关注。如“风骨”、“大体”、“先哲之诰”、“雅俗”、“物”、“研阅以穷照”等,都有文章进行阐释。这里只介绍先生关于“风骨”和“物”两个语词以及“研阅以穷照”的阐释研究。 “风骨”是《文心雕龙》中的重要概念。20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前期,以及十年动乱之后的七十年代后期,对此曾有过两次热烈的讨论。王先生《〈文心雕龙〉风骨论诠释》发表于1963年,《从〈文心雕龙·风骨〉谈到建安风骨》、《〈文心雕龙·风骨〉笺释》分别发表于1980年和1983年。历时二十年的三篇文章,其基本观点却一以贯之。那就是:“风”指思想感情表现得明朗,“骨”指语言质素精要而劲健有力,合起来就是指一种鲜明生动、精健有力的优良文风。 对于王先生的论述,有一点应该予以强调:先生认为,无论“风”还是“骨”,都不是就思想内容的高下邪正而言,而是就作品的艺术风貌、表现效果而言。也就是说,“风骨”不是指说什么,而是指说得怎么样。这与当初不少学者的观点很不一样。当初许多学者的说法尽管各不相同,但有一共同点,即认为“风”或“骨”的内涵包含着“文章的内容”、“作品的中心题材和中心思想”、“纯洁的思想”、“合乎儒家道德规范的情感和意志”、“端正得体的观点”等等。有的学者还说,刘勰的“风骨”论是对文学正确反映社会生活并积极作用于社会生活的基本特点的理论总结。王先生则明确表示不同意这样的见解。他说:“风的清与杂都是指作者的思想感情在作品中的表现效果即艺术感染力而言,而不是指思想感情本身的美恶邪正。有的同志在论文中把风的清明和思想内容的纯正密切联系起来解释,我认为这样做不符合刘勰的原意。”⑥与此相承,在论建安风骨时,王先生对一种常见的理解加以澄清。那种理解认为,建安风骨的内涵,主要是指那些表现社会动乱、人民苦难的诗,是指建安诗歌具有进步充实的思想内容。王先生认为此说不确。他说南朝批评家刘勰、锺嵘、萧统等对建安时期那类内容的诗作其实并不特别重视,他们喜爱、看重的乃是刘勰所谓“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亦即昭明《文选》中公宴、赠答之类诗作。王先生认为,南朝人论及建安诗时所谓“慷慨任气”、“风力”等,是指建安诗富有爽朗刚健的风格特征;也就是说,不是着眼于建安诗写了些什么,表现了什么,而是着眼于表现得怎么样,是否表现得鲜明有力。笔者认为王先生关于风骨的论断是十分正确的。试看《文心雕龙·风骨》举以为例的具备风力的作品,是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司马相如作此赋,本意是要讽谏汉武帝,希望武帝不要迷恋于求神仙。可是由于将神仙生活写得鲜明生动,汉武帝反而受到感染,“缥缥有凌云之志”。从内容看,《大人赋》的主体是描绘神仙生活,其劝谏的主旨毋宁说是表现得失败的,但是表现神仙生活明朗活跃,在这方面倒是颇具艺术效果,因而刘勰说它有风力。这充分证明刘勰所谓“风”不是指思想感情的纯正,王先生文中也曾举此为例。他说:“有的同志为了保护自己的论点,硬说《风骨》篇所举《大人赋》的例子不恰当,态度也是不够客观的。”⑦确实如此。 关于“物”,学者们很重视《神思》篇“神与物游”以及《物色》篇“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诠赋》篇“睹物兴情”、《明诗》篇“感物吟志”等提法,认为它们表述了创作主体与客观世界的相互关系。这样说当然并不错,然而有一个问题:刘勰所谓“物”,能否完全对应于今日所谓客观世界呢?王运熙先生进一步加以阐发,他在《读〈文心雕龙·神思〉札记》中说,《神思》、《物色》等篇中的“物”,首先是指自然风景,其次也指鸟兽草木等自然物(它们不一定被当作风景看待,比如是作为“咏物”的对象),还有出于人工之可见可触摸的具体的外界之物(如宫殿等),总之都是有形貌的具体的外物。至于人们活动所构成的事实、事迹,是不包括在刘勰所说的“物”之内的。根据王先生这一说法,我们便感到,在讨论《文心》关于创作主体与客观世界的论述时,应该有所限定,应该说得更准确一些,防止过度地阐释。 王先生在论述中还联系到一个文学史、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事实:汉魏以来,诗赋创作日益发达,而写景状物是诗赋中的重要内容,它们与抒发情志密切结合在一起,而此种情况也鲜明地反映于批评家们的言论之中。《文心雕龙》之言心物交融,正是此种言论的体现、升华。 读王先生关于“物”的论述,我们感到,先生研究古代文论,不是一般的、空泛的,而是具体的、切实的;不是仅作从理论到理论的逻辑推导,而是与古代文学创作相联系的。 关于“研阅以穷照”,王先生的解释也见于《读〈文心雕龙·神思〉札记》。不少学者将“阅”解释为阅历,则“研阅”便是指研究生活阅历。这样的解释,与现代某种文学理论重视生活阅历、提倡深入生活的观点合拍,因而颇能获得首肯。但是王先生认为,把“阅”字释为阅历或生活经历,在词语运用习惯上是罕见的,在《文心雕龙》全书其他篇章和魏晋南北朝其他文论中似乎都找不到类似的例子。他认为这里的“研阅”两字都是动词,是指阅览、钻研前人或他人的作品。“积学以储宝”指博览他人作品,吸取各方面的知识和材料(包括题材、词语典故等);“研阅以穷照”则指钻研他人文章,重在吸取其艺术方法和技巧。 王先生进一步指出,六朝文人大多不重视反映社会现实,不重视叙事类作品,他们重视的是情感的动人和文辞的美丽。因此,作家有没有丰富的阅历,在他们看来并不重要,也就无须作为创作准备的一个必要条件。刘勰同样也是这样。刘勰在评论文学史上某些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时(如评论建安文学、评论刘琨作品等),注意到时势和作者经历对作品的影响,但注意到这种影响,并不等于就自觉地提倡深入生活、了解和反映现实。前者只是对文学史上某种特殊现象的一种因果关系的解释,与提倡主动深入现实、以之作为创作的必要准备,不是一回事。王先生说,强调生活经历对写作的重要性,那是唐宋以来文论中才出现的新现象。王先生还联系对“物”字的阐释,说道:《神思》谈创作与外界的关系时,突出的是自然景物而不是广阔的社会生活;谈创作准备,只强调阅读观摩前人、他人的作品而不注意作者的生活经验。这里不仅反映了刘勰和其他文论家的局限,而且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文学作品的具有普遍性的局限。理论和创作是紧密联系的,即使其局限也是相互联系的。 注意创作与理论的联系,并且由字句之微而敏锐、准确地观照整个创作和理论背景,这正是王先生治学的特点。若不是学养精湛、眼界开阔而又好学深思,岂能做到这样呢? (三) 王先生有多篇论文,论述《文心雕龙》对于文学作品艺术特征、艺术标准的观点,并且结合《文心》对历代作品的评价来讨论这一问题。 古人不像我们今天这样,对于“文学”有清晰的概念,因而在论述“文学”作品时,往往和实用性的、“文学”性质薄弱的那些作品混杂在一起加以讨论(笔者这里将“文学”加上引号,表示这里的“文学”是表示今人的“文学”概念。古人也用这个语词,但含义有别)。但这不等于说古人对作品的“文学”特征(或云“艺术性”、“艺术特征”、“审美性质”)没有日益明确的认识。刘勰处于“文学自觉”意识相当发展的时代。王先生认为,刘勰心目中的“文学”特征是较为明确的。在众多体裁、范围极广的作品中,他最重视的是诗、赋和富有文采的各体骈散文,而诗赋尤占首位。 那么诗赋和骈散文的“文学”特征即艺术特征是什么呢?王先生说,很重要的一点是语言文辞之美,即讲究声律、对偶、藻采、用典以及比喻、夸张、含蓄等语言文辞的形态、色泽和声韵之美,甚至还要讲究文章用字的字形之美。这其实就是骈体诗文高度发展时期所讲究的文章美。刘勰是积极赞赏骈体诗文的。当然,他也看到了过分追求美丽而带来的弊病——主要是繁冗和奇诡,因而要求奇丽与雅正相结合,要求文与质相结合,因而他在“文之枢纽”中要提出“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御楚篇”的基本思想。 除了文辞的声色之美,王先生说,刘勰也谈到作品的形象性。但先生着重指出,刘勰对作品中表现人物形象是不重视的,甚至抱着鄙薄的态度。先生以刘勰对汉代乐府、史传、小说的态度为根据,着重论述了这一点。刘勰所称赏的形象描写,都是对“物”(以自然风景为主,也包括动植物以及宫殿等)的描绘。 第三,刘勰对于作品抒情的真切动人,也很欣赏。表现情感,也是刘勰对作品艺术性认识的一个重要方面。 王先生总结道:“可见刘勰认为文学作品诗、赋、骈散文的艺术特征,主要是语言文字的形态色泽之美、声韵之美,诗赋和一部分骈文则又是表现在抒情的真切、状物的具体生动方面。”⑧在这里,王先生说语言文辞之美是刘勰心目中的“主要”的艺术特征,这给我们很大的启示。现代的文学理论,常常将形象和情感二者视为作品主要的艺术特征,而刘勰所代表的当时人的看法却有所不同。他们非常重视语言文辞的美丽。这当然与如下情况有关:很多体裁的文章,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应用性文字,但在古人眼里,它们除了实用之外,也可以供观赏,可以作为审美对象。它们的美,主要不在于情感和形象,而在于文辞的美丽。讲究文辞之美(当然不同时代的审美标准有所不同)、讲究实用文章的写作艺术,成为我们的优良传统,也成为古代文论民族特色的一种表现。 王先生又指出,刘勰对作品艺术特征的认识,与同时代的论者是一致的。刘勰没有脱离、超越自己的时代。“魏晋南北朝时代,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作品日趋繁富,人们对文学特征的认识和要求,也有了新的发展,这个特点也鲜明地反映在刘勰的理论中间。……但他不重视人物形象,他所谓语言之美,主要是指骈偶、声律等骈体文学的语言要素,则又表现出很大的局限,反映了当时骈文盛行、小说没有成熟并受轻视的时代风气。”⑨ 有的学者出于对《文心雕龙》体大思精、成就卓著的敬仰和喜爱,有时便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它“拔高”了,认为它几乎已经无所不包,似乎凡现代文艺理论具有的内容,在《文心雕龙》里已经都谈论到了。王先生不是这样。他还曾指出,刘勰对通俗文学是轻视的,刘勰也绝没有提倡反映现实、表现下层人民生活的意思。先生一方面推崇《文心雕龙》代表了一个时代文论的高峰,一方面又非常实事求是,使自己的论断符合历史的真实。先生的研究鲜明地告诉我们:求真求实,是科学研究唯一的职志。 (四) 通过以上的介绍,不难看到,王先生的《文心雕龙》研究,既富于独创性,又坚持科学精神,求新和求真相结合。在求新和求真之间,当然是以求真为基础。先生不仅在许多具体内容上,提出或发展了新颖独特而实事求是的观点,而且在治学态度、研究方法上,先生也给我们很多启示。这里只简单地谈两点体会。 一是目光开阔宏通。先生研究一个问题,哪怕只是解释一个词语,也都是顾及《文心》全书,而且与刘勰同时代其他文论家的言论、与时代风气联系起来考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观察文学理论,一方面观察作品实际,自觉地将理论与创作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比如判断刘勰对骈文的态度,便联系刘勰本人的作品、联系《文心雕龙》的文体,从而得出刘勰拥护骈文、主张骈体文学之美的结论。然而当年有的学者却论断刘勰是反对骈体的。究其原因,除了如上文所说,心存骈文是“形式主义”、“贵族文学”的偏见之外,也与从理论到理论、缺少对六朝文学作品的了解有关。又如刘勰批判当时文风,究竟批判的是什么,如果不联系当时文坛的实际,不多读一些当时的作品,又怎么能得到比较具体的正确的理解呢?那就很可能对刘勰的那些批判性的言辞作空泛的解释,甚至任意发挥。又如刘勰论心物交融,如果不结合当时作品实际,那就很可能将刘勰所谓“物”理解为指整个客观世界,那么尽管可以谈得很“深奥”,可以从主客观之关系方面做哲理性的一般性的发挥,但对于准确解释刘勰本意,却用处不大。科学研究,首先要具体,要研究个性,然后才谈论一般,研究共性。不然的话,拿了“一般”的尺度到处套用,又有多大意思呢?王先生的研究,重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所以能谈得具体,解释得准确。王先生曾反复告诫我们这些学生:研究古代文论,一定要与古代的文学创作相联系,互相参证;应该先对古代文学作品有相当的了解,然后才进入古代文论的研究。先生的话,确实是非常值得体会、咀嚼的经验之谈。 二是坚持从研究对象出发,从资料出发,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不以今释古,不受某种现成观念的影响和束缚。此点似为老生常谈,然而要真正做到并不容易。因为我们都处于一定的时代条件之中,都受过某种思想、某种文艺观的熏陶,有意无意地会先入为主。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还不仅仅是受到“熏陶”,还承受着压力。比如当年为什么许多学者认为刘勰所谓风骨的含义包括思想内容的纯正呢?想来那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文艺观有关。那种文艺观强调文学艺术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因而重视内容远远超过艺术形式,动辄指斥所谓“形式主义”。这样的观念,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之下深入人心,不可能不影响到古典文学研究。人们“甚至一提到形式问题,就担心会犯形式主义的错误”。⑩那么很自然地,讨论“风骨”含义时,就指向了思想内容的纯正、教化作用等,而不愿相信刘勰这里所谈的只限于艺术风貌方面。又如创作构思中的主客观交融问题,如文学之特征在于形象的问题,确实都是文艺理论中的重要内容。人们看到《文心》中某些论述可以与之挂钩,便轻易地用现成的理论去解释那些论述了。那么王先生为何能不受影响呢?我觉得就是因为王先生坚持从文本资料出发、实事求是的缘故。坚持实事求是,本是我国古代学术的一个优良传统,也是一个学者应该坚守、必须坚守的底线。从王先生的著作里,我们看到了这一优良传统所放射的光芒。 注释: ①前者原载《复旦学报》1981年第1期,后者原载《语文学习》1984年第10期。二文均收入《王运熙文集》第3卷《文心雕龙探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②王运熙:《文心雕龙的宗旨、结构和基本思想》,《文心雕龙探索》,第10页。着重点为笔者所加。 ③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序志第五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76页。 ④原载《光明日报》1964年8月23日《文学遗产》副刊第475期,收入《文心雕龙探索》。 ⑤王运熙:《文心雕龙的宗旨、结构和基本思想》,《文心雕龙探索》,第11页。 ⑥王运熙:《文心雕龙风骨论诠释》,《文心雕龙探索》,第80页。 ⑦王运熙:《文心雕龙风骨论诠释》,《文心雕龙探索》,第80页。 ⑧⑨王运熙:《刘勰论文学作品的范围、艺术特征和艺术标准》,《文心雕龙探索》,2012年,第182、183页。 ⑩曹道衡:《可否也谈谈形式问题》,《中古文学史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