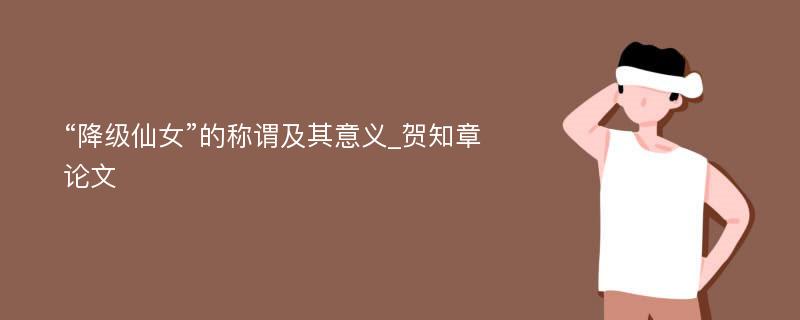
“谪仙人”之称谓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称谓论文,仙人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019(2000)01-0026-06
1
李白作为“翰林供奉”和作为“宫廷诗人”在事迹上有相互重合的部分,与此相类,他的“谪仙人”事迹也有与其“翰林供奉”和“宫廷诗人”事迹相重合的部分。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李白以“谪仙人”的赞辞为契机,得到了翰林供奉、宫廷诗人的地位,既然如此,那么他在此地位的言论行动就不可能与谪仙人的形象全无关系。
就李白研究总体看,“翰林供奉”与“宫廷诗人”的核心是各有差异的,而“翰林供奉”、“宫廷诗人”与“谪仙人”的核心不用说也就存在着更大的差异。可以认为,前二者不过是被限定在第二次在京期的一个短时期的社会性角色,与之相对,后者却贯穿李白一生,与其作风有着本质上的关联。
在现在的有关资料中,最早提到李白与“谪仙”关系的,是李白自己的作品《玉壶吟》。
值得注意的是,李白在此一时期的诗作中,常有对已经成为“金门”“谪仙人”了的自我的描写。我们知道,“谪仙人”这一称呼,是天宝元年晚秋之际亦即第二次在京的初期,李、贺二人在长安紫极宫会面,由贺知章对李白作出的赞赏性的评价。这一词语不只是出现在两年后的《对酒忆贺监》等作品中,它作为诗人的代名词,在仅仅一年后的这首《玉壶吟》中已被使用,而且其中并无与贺知章的关联。由这一事实可以确认,在这一年间,“谪仙人”的称呼已开始作为李白的代名词而在长安的士人社会中通行。如果考虑到东方朔的故事虽与“金马门”有关,即与“谪仙”无关这一事实[1], 则李白对此一称呼的自负和满足,恐怕就更加明确了。
李白在京期的作品提到“谪仙”的只有上述一首,而在其卒后的有关传记中,却有不少史料将此一时期他作为诗人的事迹与“谪仙”联系起来加以记述。作为基本史料,如下几条较为重要:
(1)又与贺知章,崔宗之等自为八仙之游,谓公谪仙人。 朝列赋谪仙之歌凡数百首,多言公之不得意。[2]
(2)故宾客贺公奇白风骨,呼为谪仙子。 由是朝廷作歌数百篇。[3]
(3)在长安时,秘书监贺知章号公为谪仙人,吟公《乌栖曲》云:“此诗可以泣鬼神矣。”时人又以公及贺监、汝阳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为酒中八仙。朝列赋谪仙歌百余首。
铭曰:……嵩岳降神,是生辅臣。蓬莱谴真,斯为逸人。晋有七贤,唐称八仙。应彼星象,唯公一焉。[4]
这里有对所谓“酒中八仙”的有趣记述,并包含着与杜甫《饮中八仙歌》的关系。在李白这里,饮酒和作诗,特别是与酒友的集团性的饮酒和作诗,无疑构成了李白研究本身的有意义的论题[5]。
然而,就“诗人李白的长安体验”而言,不可欠缺的是,李白将“谪仙人”的称号与自己的本质作为相吻合的东西而予以积极地受容,并且在此之后,他的诗作活动作为与“谪仙”形象不可分的部分,而被自己和他人所意识到,从而“酒中八仙”的事迹实际上也就和“谪仙人”的称号密切地关联在了一起。
2
关于此问题首先应注意的一点是,在上引的传记史料中,无一例外地将“谪仙人”(谪仙子)的称呼和作于朝廷的多首《谪仙之歌》直接联系起来加以记述。
那么,这《谪仙之歌》具体指什么呢?在现存的李白作品中,没有哪首诗的诗的诗题中有“谪仙”二字。因而从其所记数量来看,“数百首”也好,“百余首”也好,要点在于:在李白前后约三年的在朝期中,创作出了具有“谪仙”诗风的众多作品——这样解释是妥当的吧。
进一步需要考虑的是,为什么“谪仙”这一称呼,无论对李白而言,还是对他人而言,似乎都是那么适当的一个评语而为之接受?这一点作为李白论、诗人论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与李白富于变化的经历相应,“青莲”、“翰林”、“酒仙”、“醉圣”等不少称呼都成了他的代名词,但从李白性格与诗风关系这一意义看,却只有“谪仙”才具有最适当贴切的象征性。据上引第(1)条“多言公之不得意”之后的记述, 所谓《谪仙之歌》多半是指李白第二次在京期后半的饱含失意、愤懑的作品。
天宝元年秋,贺知章在长安的紫极宫(太清宫、老子庙)与李白初次见面,接触其人其作后即呼为“谪仙人”。这件事情,以有关此一问题之第一手资料《对酒忆贺监》序中所记“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为中心,综合其它相关资料来判断,其真实性是可信的。
那么,为什么贺知章要从应有许多的赞辞中选择了“谪仙人”一语呢?作为直接明了的原因是:(1 )评论人贺知章两年后将成为道士而归隐于故乡四明(浙江)的道观,他与道教信仰有着深厚的亲近关系;(2)被赞赏者李白也在爱好道教的玄宗治世下, 经由成为女道士的玉真公主的推荐而参与了人才登用的选拔,也就和道教世界有了亲近关系;(3)进而, 两人相见的场所乃是紫极宫这样的最具道教色彩的环境,等等。——应该指出,易于联想起被视作道教思考之象征性观念形象的仙人形象的诸种条件,已是非常齐备了。假如不存在这些道教色彩的条件,即使使用同样程度的激赏语言,恐怕也不会选择“谪仙人”这种意象。
另外,李白也还在与道教世界直接关联的文章中,记述了对来自贺知章“谪仙人”称呼的体验。与贺知章会面十多年后,五十余岁的李白于第二次游历期的后半,在金陵(南京)作有《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
吾希风广成,荡漾浮世,素受宝诀,为三十六帝之外臣。即四明逸老贺知章,呼余为谪仙人,盖实录耳。而尝采姹女(水银)于江华,收河车(铅)于清溪。与天水权昭夷服勤炉火之业久矣。……群子赋诗以出饯,酒仙翁李白辞。
这里,被送的友人权昭夷是与李白有共同求仙修行之体验的道友,此点决定了该作品的倾向。然而,“或希风广成,荡漾浮世,素受宝诀,为三十六帝之外臣。即四明逸老贺知章呼余为谪仙人,盖实录耳”所记述的“谪仙人”的形象——即使将上述共同求仙的个别条件考虑进去——,应该说与当时的道教世界是直接相关的吧。
也就是说,李白所描绘的“谪仙人”的自画像,乃是“希求仙人广成子凤,接受道教修炼的宝诀,作为道教三十六天,三十六宫之主的三十六帝[6]的外臣”而被流谪到地上的唐朝诗人,因此, 也就形成了“四明山逸老贺知章呼我为谪仙人,乃是实录”的说法。可以认为,所谓“谪仙”不只是语言上的修辞,而是被玄宗朝的道教信仰以至道教世界观所支撑的更具有实感性的观念,这就是关于此称呼之思考的一个要点。
然而,历史性地来看,“谪仙”的称呼并不只用于李白身上。比如,《水经》卷十三“漯水”注中引用的班邱仲和南齐的钟山隐者蔡某(《南齐书》卷五十四《高逸》、《南史》卷七十五《隐逸》上)的例子,即发生在李白之前,这是在辞典[7]中能够检索到的早期的称呼。 后来宋朝的苏轼也曾有此称呼,已广为人知[8]。另外, 笛曲中的《谪仙怨》[9],传说即玄宗因对张九龄之左迁感到后悔而赠与他的曲名,作为广义的“谪仙”意象,这也能引起人们的兴味。白居易对他的进士同年吴丹所说:“不知有何过,谪作人间仙。”(《酬吴七见寄》)似亦可予留意。
不过,对当时的贺知章和李白来说,更直接地被意识到的,应是如《魏书·释老志》中所载成公兴[10]那样的仙人。在他们看来,在狭义的道教世界中,大概存在着像“谪仙人”文字所表述的那种因什么罪而从天上被暂时流谪到人世的典型的谪仙人吧。进一步说,将到此为止未被查到的用例和已经散佚的用例等也包含在内,可以认为:将“谪仙”一词作为对优秀人才的赞辞和对所谓具有仙风道骨之士的通称,这种用法,恐怕并不罕见。
尽管如此,但仅就中国文学史而言,“谪仙人”之名,只有在李白这里,才具有独占性、代表性。无疑,这一方面是因了李白自身在文学史上的代表性,而作为更本质的原因,则是在“谪仙人”的意象结构中,存在着与李白性格和诗风共通的要素(亲近性)。这一点,必须明确地予以指出[11]。
“谪仙人”这一观念的意象结构非常复杂,但其主要属性可以集中在下面三点:(1)才能上的超越性、超俗性;(2)社会关系上的客体性、客寓性;(3)言论行动上的放纵性、非拘束性。这三者相互关连,因而正好具有结构性的品格,即欠缺了哪一个都难以形成典型的“谪仙人”的形象。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哪一个都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属性。第(1)点,指其才能资质本来就是属于天上世界的属性。 ——“谪仙人”成了绝妙赞辞方面的不可欠缺的要素。第(2)点, 指从天上界(别一世界)被暂时流谪到人间界的属性。——“谪仙人”成了社会性(地上性)诸关系(政治、经济、家庭……等)中不能成为恒常主体者(恒常的责任分担者)方面的不可欠缺的要素。第(3)点, 指具有本来的放纵性(因违法行为而被天上流谪)和超越的才能而成为非定住的客体者所被容许的属性。——“谪仙人”成了不被人间世界之常识、仪礼、权威所拘束构成飘然、奔放之行为方面的不可欠缺的要素。
如此看来,“谪仙人”的形象构造,不能不说与诗人李白的形象构造非常类似。关于李白那里存在的类似性格和诗风,笔者已在此前多种场合论及,其中以更客观性的论据为基础的要点,可以指出下面五条:
(A)在具有“视点的第三人称化、场面的客体化、 表现意图的未完结化”之机能的古乐府系列作品[12]中,以及以“形象的未完结性(对他性)”为基调的绝句作品[13]中,展示了特别超越的才能。
(B)在实际创作手法中,由于日常性、 自我性之被抽象化表现和客体化倾向得到增强,李、杜、韩、白等主要诗人中,制作年代不明的作品占有显著的高比率,其结果,作品的独立性提高,解释的幅度扩大。
(C)作为李客这位客寓者之子, 李白不仅在客寓中度过了自我的形成期(5岁~25岁),而且其一生都是作为各地的客寓者度过的, 因而难以特别指定在旧士人社会中成为社会恒常性、主体性根源的“坟墓之地”[14]。
(D)(1)在安陆(湖北)期屈身地方长官门下所产生的纠纷磨擦[15];(2)在玄宗朝作为朝臣的极度放恣;(3)连倾慕他的人也在褒词中如此记述了他的傲骨:“平生傲岸,其志不可测,数十年为客,未尝一日低颜色。”[16]——等等,由于这些史实史料展示了李白放纵、傲岸的性格,一个享乐者的形象便被浓墨重彩地突现出来。
(E)从文学史来看,有关李白性格,诗风的代表性评语, 无疑是飘然[17]、飘逸[18]、奔放[ 19]。
于是,与此相关的一些事象便贯穿于诗风、传说、享受史等各个领域之中,从而展示出“谪仙人”的意象结构与诗人李白的心象结构大致上是原封不动地重合着的,结果“谪仙”一词专门由李白来代表,便不能不说是一种必然的现象。
3
以上,我们以“谪仙”的称呼为中心,对李白的长安体验作了考察。最后,再就这一称呼产生的各种事象及其意味,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探讨。
首先要指出的一点是,“谪仙”这一称号乃是构成李白作为“翰林供奉、宫廷诗人”之生活体验的直接契机,而这种朝廷体验,就李白的主观意念而言,是具有优先的价值的。
在此之前,经世济民这一重要理念只不过是李白的抱负和主张而已,至于这种理念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的可能性,则与其日后作为朝臣之地位相关。李白供奉翰林后,前半的荣光和后半的挫折所形成的对比,乃是其产生更大失望和愤懑的原因。在《玉壶吟》、《还山留别金门知己》、《初出金门寻王侍御不遇咏壁上鹦鹉》等诗中,明确涉及到李白心情变化。换言之,李白由于经历了第二次在京期身为朝臣的体验,可以说已开始具有在野与在朝的宽广视野,而他被放逐后的不少作品,都在反复歌咏其在朝时的荣辱体验。这一事实说明,大约三年的朝中体验对李白的诗和人生来说,该是有着何等大的意义!
第二,应该指出,此前对李白来说较为漠然的只是在形式上被意识到的自己的诗风,由于得到了“谪仙人”的赞辞而被更明晰地自觉到了,与此相关的实际创作活动也明确化了。
其中可以认识到的最确实的因果关系,应是在李阳冰《序》、魏颢《序》、范传正《碑》等史料中所记述的《谪仙之歌》的实际创作吧。这些在朝期的丰富诗作,至少是由李白自己赋予其“谪仙之歌”的品格,并传给了传记作者们。对李白来说,“谪仙”这一称呼乃是涉及诗人本质的令人满意的赞词。
综合杜甫《寄李十二白》、范传正《新墓碑》、孟启《本事诗》等相关记述的说法,可知所谓“谪仙人”是在贺知章读了《蜀道难》、《乌栖曲》、《乌夜啼》等乐府作品后,与“此诗可以泣鬼神矣”的评价一起发出的赞辞。这类古乐府作品,乃是李白最得意的体裁之一,而且因了其日常性和现实性之抽象(对日常具体表象的舍弃)的表现机能,而有着与“谪仙人”的心象构造密切关联的亲近关系。“谪仙”之评,不仅关乎李白的性格,而且与其诗风也紧密相关。应该看到,正是因了这一点,所谓“谪仙之歌”的多部作品被更加自觉地明确化了。而“谪仙人”的称呼,则成了李白对李白式性格、诗风予以自觉增幅的重要契机。在评价长安体验后的李白诗歌风貌时,杜甫特别指出“飘然思不群”(《春日忆李白》)一点,就上述情况而言,这一评价确是意味深长的。
应指出的第三点是,由于对“谪仙人”的自我承认,导致李白在朝期的言论行动在谪仙式的放恣、放纵方向得到发展。
比如,以贺知章和崔宗之为主要伙伴的“饮中(酒中)八仙”的醉态,恐怕就是其中的一环,而“酒仙”、“八仙”的自称,恐怕正是以“谪仙人”的称呼为前提的。尤其是被当做李白式风貌而广为流传的一连串记述,亦即(1)“天子呼来不上船, 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八仙歌》);(2)“时公已被酒于翰苑中, 乃命高将军扶以登舟”(范传正《新墓碑》);(3)“尝沈醉殿上, 引足令高力士脱靴”(刘昫《旧唐书·文苑传》),等等,都不能不说是只有被视为“谪仙”的客寓者才能展开的、显著的放纵行为。——当然,这其中表述的李白的言论行动,不用说有夸张、润色等因素。可以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玄宗对李白的拔擢,是以“谪仙人”的称呼作为直接契机的,而由此导致的李白的自觉意识,便成为促使他这种言论行动增幅的一个主要原因。
然而,贯穿于谪仙式言行中的,无疑是放弃成为持续性主体者(社会责任分担者)一事。在短期内伴随着一种清新感而被容许的这种言行,也由于长期化而失去了重要的客寓性自体,逐渐成了排斥的对象,这一点,在社会性的组织体内恐怕是必然的。“谪仙”李白在进入朝廷这种最稠密的社会性组织体后,只经过短短三年时间即被放逐,正说明了这种必然性。用象征手法说,“谪仙”为了持续做“谪仙”,如同他被从天上三十六帝的宫廷所流谪一样,他也不能不在地上长安的宫廷遭到流谪。
当然,关于李白被从长安放逐的原因,他自己的解释是“白璧竟何辜,于蝇遂成冤”(《书情赠蔡舍人雄》)。另外,还有来自传记作者立场的带有同情性的价值判断:“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李阳冰《草堂集序》);“以张垍谗逐”(魏颢《李翰林集序》)。然而,若将客观性的事实判断放在首位的话,那么可以说,这种来自善恶正邪的论断,因过于片面而不一定能传达总体的实情。
应予指出的第四点是,从批评史的角度看,“谪仙人”的称呼,在形成中国诗史上诗歌评价的典范——李白式顶点和杜甫式顶点——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文学史上,李白和杜甫是最优秀的诗人,对此,历来的评价几乎从无异论,而且,其风格上的鲜明对比也是被人广为承认的。也就是说,虽然同为最高层级的作者、作品,但李白诗风更多地在客体化、第三人称化、一般化的方向达到顶点,而杜甫诗风则更多地在主体化、第一人称化、个别化的方向达到顶点。从二者的总体——个别作品不用说也存在例外——来看,可以说存在着极其鲜明的对比,而且这种对比由于存在着下述一系列确实的基准,即(1 )对古乐府类作品的适应性和对新乐府类作品的适应性;(2)对离别、 闺怨类题材的适应性和对时事、咏物类题材的适应性;(3 )创作年代不明确作品的多寡度和创作年代明确作品的多寡度——所以几乎毫无疑问地可以得到客观的承认。
这种对比性,在批评史对两者的称呼上,也得到了集中表述。在那里,诗仙、诗圣的称呼在其对比性性格的整合性一点上,可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东西。也就是说,虽然同样是最高水平,但在天上性、非日常性、超俗性方向上成为规范而难于模仿学习的诗仙观念,与在地上性、日常性、现实性方向上成为规范而易于模仿学习的诗圣观念,正反映了李白和杜甫各自作风中的一连串倾向,这种倾向是根据中国思想中两个对照性的观念形象而明确把握到的。进一步说,诗仙、诗圣观念的形成,不只是限于李白、杜甫的问题,它在文学乃至艺术的实际创作中,在指示着应有的两个顶点方向这一点上,可以说具有更大的意义。
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在这种对比性评语的形成史上,只有“谪仙”的称呼发挥了重要的起源性的作用。例如,在李白卒后百余年编成的《本事诗》(《高逸》第三)中,“谪仙”和“诗史”成了代表性的评语,而诗仙——诗圣的对比尚未出现。作为表征杜诗之现实性、个别性、日常性的诗史也还是准确的评语,但这是一个比诗圣早出现的称呼。另外,在一段时期中李白以外的诗人也有被称为诗仙的[20],而李白自身有时则反而被视为诗圣[21]。相比之下,在杜甫批评史中诗圣一词的常被使用,时代就要靠后些了[22]。
据上述情况作一判断,可以认为:首先,“谪仙”是对李白作出的恰当的意象批评;其次,与此意象的恰当性相关联,“八仙·酒(中)仙·天仙[23]·谴真[24]”等类词语也被使用;第三,作为对上述评语的统合,“诗仙”[25]成为常用的词语;最后,与“李白=诗仙”相对应,“杜甫=诗圣”,这一整合性称呼也得以确定。总之,必须给予充分注意的是,在这些基本情况中,首先有了“谪仙”的称呼[26],这乃是批评史上意象批评赖以展开的要点。
未必常能见到,但一旦将把握到对象本质的真正适当的批评加诸其上的时候,这评语便会在作者及读者的内在精神方面持续地发挥作用,并由此导致自身也发挥了丰富的创造性机能。李白长安体验中的“谪仙”称呼,确实具有如此意味。
严密地说,贺知章的评语,不过是天宝初年面对李白诗风、人品而作的直观印象式批评,然而,由于其对象把握的适当贴切,遂使这一评语不只是对李白自身,而且对同时代和后世的人们也持续发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是一种“称呼=意象=观念”的独立作用,而这种作用恐怕应该说早已超出了贺知章自身的意图。我们在此能够看到的,乃是批评(被批评)这种行为的一个幸运例证。
而且这位贺知章在此后仅仅一年多就离开了长安,并于半年后即以86岁的高龄永远告别了这个世界。李白与“谪仙”的结合,应该说也是一种时代的、时间上的幸运吧。
(译文经松浦友久教授审阅,发表时有删节。)
收稿日期:1999—1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