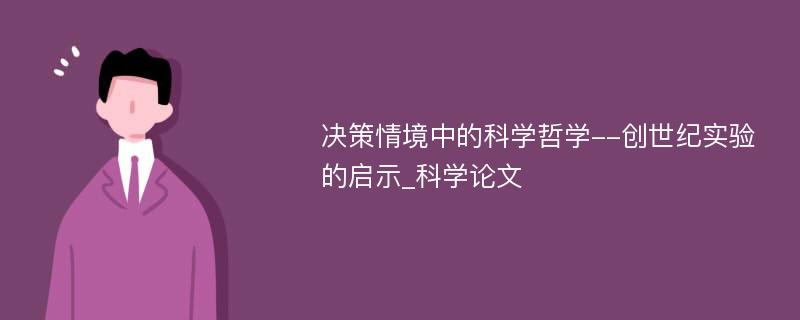
决策情境中的科学哲学——创世学审判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境论文,启示论文,哲学论文,科学论文,创世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志码:A
近年来,我国国内涉及到伪科学的事件频繁发生。其中,以1994年判决“邱氏鼠药案”、1997年判决“王洪成水变油案”、1999年处理“法轮功事件”影响尤大。但是,这些事件均未直接涉及到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问题,因此司法过程也并没有涉及到科学哲学所关注的问题。
但是,随着科学与伪科学之间斗争的深入,我国司法部门乃至立法、行政等决策部门,必将面临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伪科学或非科学理论以科学面目对社会意识形态空间的抢占。
随着我国社会思想领域趋于多元化,各种思想或理论竞争社会意识形态空间的努力,日益凸显,法轮功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现代主流社会,一个思想或理论如果被判定为“科学的”,则有其存在的合法性依据;如被判定为伪科学之类,则至少会遭致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感或排斥。因此,在各种思想和理论在争夺意识形态空间之时,必然存在以“科学”为名证明其存在合法性的现象。因而,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代表者的立法、司法和行政等决策机构,会越来越多地面临判定理论或思想的“科学”地位之问题。与此同时,由于社会民主化、法制化建设的逐步深入,决策机构在解决这一问题时,也需要应用得到社会普遍承认的“科学”地位的判据。因此,这个问题的解决,就需要科学哲学的介入,因为科学与伪科学、非科学划界的问题,正是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但是科学哲学如何介入这样的决策情境,本身就是个值得理论界深入探讨的复杂问题,至今尚未得到很好的解决。
1981年,美国一场关于“创世学”的审判中,就突出表现出这样的复杂性。尽管美国社会和中国社会在政治、文化、经济等领域存在重大差异,但是该审判中牵涉到的科学哲学如何介入决策情境这一问题,以及美国司法界的处理过程和学术界的讨论,对于中国的决策界和学术界,仍然具有很强的参考和借鉴意义。本文拟对这场审判及美国学术界的相关讨论,进行简要的介绍和分析,希望能引发一些有益的思考。
1 创世学与进化论的斗争
在当代美国,基要主义(fundermentalism)是一支重要的社会保守力量。由于基要主义者认为《圣经》和达尔文的学说水火不相容,因此他们强烈反对进化论。20世纪20年代以来,他们对进化论开始进入美国各州公立学校的课堂,一直持厌恶和反对态度,并试图阻止这一趋势。
1925年,在基要主义者的游说下,美国田纳西州通过不许在公立学校讲授进化论的立法。代顿镇的科学教师约翰·托马斯·斯科普斯(John Thomas Scopes)被指控在公立高中教授进化论而被指控,后败诉。此后,美国很多州的教科书出版商都尽量避免涉及进化论这一有争议的主题。
但是,美国社会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了一场课程改革运动。其结果之一,便是生物科教材中,开始涵盖进化论的内容。基要主义者对此进行了反击,但是以往的教条显然明显违反科学教育日益发达的时代潮流。使得基要主义者们在60年代后期,作为一项新的策略,提出了所谓的“创世学”(creation science),并争取以创世学进入公立学校科学课程的方式,抵制进化论思想的传播。这就是所谓的“创世学运动”。这些运动都被美国法院根据美国宪法予以抵制。其中,1982年的麦克莱恩诉阿肯色教育委员会(McLean v.Arkansas)一案,当代著名科学哲学家拉里·劳丹(Larry Laudan)、菲利普·奎因(Philip L.Quinn)和迈克尔·罗斯(Michael Ruse)等人都介入其中,对创世学-进化论争论以及这场审判中牵涉到的科学哲学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论争。
2 创世学审判
(1)590号法案的通过及其引发的诉讼
1981年3月19日,美国阿肯色州州长弗兰克·怀特(Frank White)签署了“同等对待创世学和进化学法案”。该法案的核心内容是要求在该州公立学校科学和认为是科学的课堂教学、教科书和图书馆的资料以及其他教育计划中,对“凡是涉及人类、生命、地球和宇宙起源主题的内容,予以同等对待”。这个法案又被称为“590号法案”。
在590号法案看来,“进化学”和“创世学”是物种起源的彼此竞争的科学模型,并提出了下述对创世学的定义:
“创世学”指的是支持神创万物的科学证据,以及从这些科学证据中得出的推论。创世学包含这样一些能支持如下观点的科学证据以及与之相关的推论:(1)宇宙、能量和生命从无到有的突然创造;(2)突变和自然选择不足以解释所有生命种类都发展自一个简单的有机体;(3)变化只发生于一开始创造出来的有限的动植物种类中;(4)把人类和类人猿的血统断开;(5)用大灾难,包括世界性洪水的发生,来解释地球的地质;以及(6)地球和生命的出现相对较晚[1]。
该法案强调,科学的起源模型应予以介绍,而且不允许“介绍任何宗教内容,或是参照宗教著述”。它并没有要求公立学校在其教育中,一定要对起源问题予以介绍,而所谓的“同等对待”,主要在于只是要求“如果公立学校选择传授进化学或创世学这两种科学模型的一种,那么二者都必须予以介绍”。
虽然590号法案被认为是代表了去除创世学中宗教因素并定义其为科学理论的一种执着努力[2],但是5月27日,美国公民自由协会(ACLU)向州地方法院递交诉状,宣称590号法案违宪,因为其触犯了政教分离原则,而且,该法案还违背了学术自由原则。创世还是进化的争端,在美国法庭上并不陌生,但是这一次审判,却有一个独特之处,因为这是第一次,创世模型作为科学受到司法的挑战。
(2)奥弗顿法官的裁定
1981年12月7日,州地方法院开庭审理此案,主审法官是威廉·奥弗顿(William Overton)。
尽管590号法案声称创世学是一种“科学模型”,但是奥弗顿法官认为,他审判的根本法律依据仍然是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第一条不得确立国教条款(TheEstablishment Clause):“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活动自由;……”
因此,奥弗顿的首要任务是决定590号法案是否违背了美国宪法。他的推理是,只有当该法案满足了第一修正案的不得确立国教条款,才与宪法相一致。
1971年“莱蒙诉库尔茨曼案”之后,根据其判词,美国最高法院对不得确立国教宗教条款的解释,当裁决牵涉到政府和教会力量的关系的政府法案是否合宪之时,逐渐发展起对任一涉及宗教的立法的合宪性进行三部分考查的基本考量标准,即所谓的“莱蒙检验”:“首先,该法令必须具有世俗性的目标;其次,它的首要效果或基本效果,必须既不促进也不阻碍宗教;最后,该法令不得导致‘政府过多的牵入宗教之中’”。
于是,590号法案,能否通过“莱蒙检验”,便成为其是否合宪的关键。
1982年1月5日,奥弗顿法官作出裁决。在其判词中,奥弗顿认为,阿肯色州议会通过的590号法案显然具有特定的支持宗教的企图,而这一行为本身——缺乏世俗性目标——就足以使该法令无效。但是奥弗顿法官希望说明,590号法案也无法通过三部分考查的后两部分。为了说明590号法案无法通过第二部分考查,他就有必要表明该法令将支持或阻碍宗教作为其“首要或基本效果”。为达到这一点,奥弗顿法官认为必须证明创世学不是真科学。因为,正如他论证的(在其裁定理由书第四(D)部分的最后),“既然创世学不是科学,那么不可避免地得到如下结论,590号法案的惟一实际效果是支持宗教”。
奥弗顿法官论证创世学不是科学之时,主要的依据是采用专家证人迈克尔·罗斯关于创世学的观点,但是由于另外两名科学哲学家劳丹、奎因对于罗斯的论证存有争议,所以,尽管奥弗顿法官的宣判结束,案件本身尘埃落定,但是几名著名科学哲学家对此案件的争论和思考,值得作一番回顾和思考。
3 罗斯与劳丹关于创世学审判的争论
(1)罗斯:创世学不是科学
罗斯是麦克莱恩诉阿肯色州一案原告ACLU的主要专家证人,在该案审理结束之后,罗斯撰文“创世学不是科学”,说明了他为什么“确信创世论不应该在公立中学教授,因为它不是科学”[3]。
在罗斯看来,“我们今天称之为‘科学’的,是一整套彰显突出的论点,它具有许多特征。”根据罗斯的概括,科学的几个最主要特征是:①“科学寻求完整的、隐蔽的、自然的规律性(定律)”;②“运用定律进行解释”;③“可检验性。真正的科学理论将自己置于真实世界的检验之下。”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包括确证和可证伪性;④“科学是试探性的”;⑤“好的科学,……预先要求一种可称之为专业正直性的态度”。
对照这些标准来考察创世论,罗斯认为:①创世学“显然乞灵于定律之外的事件和原因。比如,从590号法案可得到的惟一合理的推论是,对创世论而言,宇宙及其中生命的起源是不受定律限制的。创世学的定义包括“宇宙、能量和生命从无到有的突然创造”这样一个绝对陈述。②从解释和预测角度来看,创世学家们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可以检验的预测。他们在大部分时间里,自我满足于以与其教条相一致的方式描述证据。③从可检验性来看,一方面,创世论者们几乎不做真正的检验。④创世论者们绝对不会改变自己的立场。事实上,创世论的领导组织创世研究协会,就要求其成员签署一项声明,表明其承认圣经完全正确。而科学则不允许狂热的教条。⑤创世论者为实现其目的,在著作的推理中,也充满谬论。比如,这些创世论者们惯于运用不恰当或不完整引用的方法。
根据这几项考察,罗斯认为“创世论不具有构成科学的任何标志……实际上是一种教条的基要主义……”[4]
(2)劳丹:真正的问题在于是否拥有更多的理由
罗斯此文发表不久,劳丹撰写了“受到公开审问的科学:关注的原因”一文,严厉批评了罗斯的观点以及奥弗顿对590号法案的判决。
劳丹认为这些奥弗顿法官的判词中所概括的科学特征(见本文第三部分)可分为两类,“前两个与规律和解释力有关;其他三个与科学断言的可证伪性和可检验性有关”。
就第一类特征来说,劳丹认为“确立一种现象与用定律来解释这一现象之间,是有区别的……达尔文也是在遗传学家可以对自然选择所遵循的遗传规律进行阐述的近半个世纪之前,就确立了自然选择的存在”,所以,比如说,“对创世论者物种(相对)恒常性论点的真正反驳,不是这种恒常性没有用科学定律解释,而是恒定性的证据不如其反面即可变性那么有力。”不过这样一来,也就说明创世论并不是不可检验的了。
就第二类特征来说,劳丹认为奥弗顿判决指责创世论不可检验、教条以及不可证伪,也“是令人怀疑的”。比如,说创世论没有作出经验上的判断,以此论证创世论既不可证伪,又不可检验,这当然是错误的。因为创世论者们也对经验事实作出了一系列断言,比如说地球的起源很晚(6000到20000年);物种的有限多样性等等。“总之,这些论断是可检验的,它们已经被检验了,并且没有通过这些检验。”更进一步,劳丹提出罗斯和奥弗顿法官所概括的给科学划界的特征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一方面,劳丹否认罗斯-奥弗顿清单中的条目(2),因为其要求太强。
另一方面,可检验性、可修正性和可证伪性则是非常弱的要求。
因此,劳丹认为“核心问题并不在于创世论是否满足那些不严格且充满争议的关于科学的定义;真正的问题是现有的证据是否给予进化论比创世论更有力的理由?如果这个问题解决,我们就可以知道谁可以进课堂,谁不可以。而争论创世论的科学身份,则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那些不应困扰我们的话题之上”[5]。
(3)罗斯的回应:弱科学与伪科学
针对劳丹的反驳意见,罗斯又写了一篇“对评论的回应——支持法官”,论证“劳丹的指责并不能影响奥弗顿判决的正确性”。
首先,罗斯补充说明奥弗顿法官在判词中为什么要概括科学的特征。“因为创世论者们说他们的思想够得上真科学,而不是基要主义宗教。支持美国公民自由协会提起诉讼的律师们相信,证明创世学不是科学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种证明也就引起了创世学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但是,劳丹则说“核心问题并不在于创世论是否满足那些不严格且充满争议的关于科学的定义;真正的问题是现有的证据是否给予进化论比创世论更有力的理由”?由于美国宪法并不禁止弱科学的传授(宪法第一条修正案所禁止的是传授宗教),所以劳丹所说的结论和策略,完全不足以用于法律目的,因为劳丹的策略是论证创世论是弱科学,因而不应该传授。
(4)劳丹:应当区分羊和山羊、信条和信仰者
随后,劳丹撰写了“对创世论的进一步探讨”一文,对罗斯的“对评论的回应——支持法官”进行反驳。劳丹主要反驳了罗斯的论证逻辑。首先,罗斯“不知道怎么区分羊和山羊”,实际上,罗斯论证的逻辑是用满足奥弗顿判词的例子来说明,但是这并没有什么用,因为“我并不是说所有的科学判断都是不可检验的,而是有些”。因而,用例子来说明区分科学和非科学的标准,并不充分。
另一方面,劳丹还认为学说信条和学科的信仰者(beliefs and believers)也应该区分开来。不能以许多创世论者所表现出来的教条主义,来论证创世论本身就不可靠[6]。
4 奎因对罗斯与劳丹争论的反思
奎因对罗斯与劳丹的这场争论进行了反思,并撰写了“作为专家证人的科学哲学家”和“创世论、方法论和政治”两篇文章,对创世论审判中奥弗顿法官判词的论证逻辑[7]和罗斯作为专家证人介入其中,予以批判。
(1)创世学缺乏世俗目标并且是糟糕的科学
在这两篇文章中,奎因表示同意奥弗顿的决定,阿肯色州的590号法案是不合宪法的,因为它缺乏世俗性的目标。
但是,他所批评的是奥弗顿试图表明590号法案以支持宗教作为其首要效果。像劳丹那样,奎因也论证罗斯的条件,要么对成为真科学来说,并非必要(因为有些真正的科学并不具备),要么经过恰当的解释,创世学也可具备。在奎因看来,对于创世学的合理做法,不是我们表明它不是科学,而是充其量它只算糟糕的科学。因为,从研究纲领的角度而言,创世论是一个“各个方向上都在倒退的研究纲领”,而同时,进化论作为其竞争性纲领,却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正因为如此,创世论者的研究纲领,既没有什么科学成果,也不具备科学上的吸引力[8]。
(2)科学哲学家面临的三类基本危险
不过,奎因这两篇文章主要目的还是在于从罗斯作为专家证人介入创世论审判及其对审判的影响,反思科学哲学家应该如何介入司法审判、决策过程这样一个科学的社会研究中经常遇见的问题。
奎因认为,科学家在介入决策领域之时,应该认识到三类基本的危险。第一类是交流的危险。“如果专家不能与其他参与决策过程的人进行充分交流,说明他的专家观点对人们考虑的政策问题具有什么意义,那么他就不能影响决策过程的结果。”第二类危险在于被误解。“如果其他参与决策过程的人并不能领会专家观点的细节涵义,他们就可能对这些推论进行错误的解释,从而恰与专家的观点相反,以支持这些政策。”第三类危险在于专家的观点不具有代表性。“如果专家的观点并不能代表相关的学术共同体已经达成的一致意见,那么基于这些观点之上的政策,则在该共同体中缺乏可信度,其成员会认为这种可信度缺乏造成该政策存在问题,不可信任。”
奎因认为,就创世论审判而言,主要问题并不在于前两种危险。而是第三类危险。“罗斯的观点并不代表科学哲学家已经达成的一致意见。”
总之,奎因认为,科学哲学家在介入实际政策过程时,应该认识到这些基本危险,并且“小心谨慎地将危险程度降到最小”[9]。
(3)“脏手问题”
在“创世论、方法论和政治”一文中,奎因又补充说明了科学哲学家介入决策过程中会面临的“脏手问题”,做了进一步探讨。
所谓“脏手问题”,其含义是:当哲学家们卷入类似创世论审判这样的司法或政治活动时,其角色通常是为最后的决策者的论证服务——建议、作证或说服。而这些活动的规范和约束与他们学术环境下的活动迥然不同。在学术环境下,哲学家们应该遵循论证的方向——严肃地接受批评,只要反驳和反面证据有价值,就应该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修正或予以放弃,“我们使之内在化构成了我们智识正直性的一个部分”。但是,当哲学家走出学术范围,卷入决策过程之时,他们希望正确的观点,或者至少理性上值得支持的观点能够获胜并影响公共政策。但是,这种过程中,经常遇见的一个问题是,支持某个观点的好的论证却不是最有效的,而最有效的论证却并是好的论证。这时哲学家们面临一个两难境地。一种情况下,哲学家可以选择有效而坏的论证。尽管开始时他们对这种妥协会感到痛苦,但每做一次,手就变脏一点,最后当其习惯之后,其智识正直性受到很大破坏。另一种情况则是,哲学家们不惜代价以维护其智识正直性,从来不进行有效而坏的论证,而只提供好的论证,让自己的手保持干净。但是由于决策者们自身的偏见、愚蠢或忙碌,往往使得这样的论证方式并不具有说服力,从而这种哲学家的意见往往并不能得到采纳。
奎因认为解决这一困境的一个办法是哲学家只短暂地介入决策过程。
不过,就创世论审判而言,奎因也提出了一定的妥协。他认为创世论者企图利用公立学校推广其学说的活动是有害的,应该在政治领域对其予以有效的抵制。但是有些创世论者确实非常狡诈,使得政治或法律领域中,只有坏而有效的论证才能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使用坏而有效的论证,在道德上是可容许的”,但其条件是,“我们良知上怀疑自己的手已被玷污了”[10]。
5 结语:科学哲学家介入社会生活的两难困境
在现代社会秩序的确立过程中,宪法权利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法律法规体系是社会公民和各种意识形态集团解决争端,进行权力关系交易的基本规范和方式。不过,由于宪法和法律本身的相对滞后和其他种种局限性,总是存在一些其未触及的地带,使得意识形态集团可以对之实行一定的控制,如果社会力量不能够对之进行及时而且有效地管制和协调,人们便有可能为之说服,经过一段时间,这些意识形态就会获得社会和文化上的影响力,并树立起一定的权威。
和其他意识形态一样,宗教意识形态也总是要进入现实的世俗政治领域,以扩大其影响力,“占领思想阵地”。作为基要主义者代表的创世论者,利用美国法律的空白,自60年代以来试图在公立学校中宣传其创世论的努力,以扩大基要主义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即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
但是,美国政治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宗教侵入现实政权向来持非常审慎的态度。因而,美国联邦高级法院对创世论者的上述努力,一直予以坚决的回击。在其中,1982年创世论审判(麦克莱恩诉阿肯色)具有特殊重大的意义,因为正是这场审判,彻底否定了创世论的科学地位,使得基要主义者试图以偷袭方式在公立学校进行宗教教育的道路被封死了。
由于这场审判的核心问题乃是创世论到底是不是科学,因此,科学哲学家的介入其中,不仅应该,而且必需。罗斯作为主要的专家证人,他所提出的借以判定创世论不是科学的几项科学与非科学划界的标准,成为法庭判决的主要依据。但是,由于罗斯所提出的标准,在科学哲学界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所以,遭到劳丹等科学哲学家的严肃批判。而奎因对此的反思说明,科学哲学家应该根据何种理论、乃至以何种方式介入决策过程,对决策进行论证,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科学哲学家在介入决策过程之时,应该保持一种异常审慎和怀疑的态度,清醒地认识到其中存在的基本的危险以及“脏手问题”这一两难困境,在维护学术界所要求智识正直性和现实的决策过程中所需要的论证有效性之间,尽可能维持一个恰当的平衡。
总的来说,对于科学和伪科学以及宗教的争端问题,当其介入现实的政治领域,对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现实的社会秩序产生影响之时,坚持“宗教信仰自由”以及“政教分离”的信条的宪政国家,应该借助科学哲学的学术研究成果,及时通过司法、立法和必要的行政手段,防止宗教事务渗透现实政治,避免宗教问题成为政治问题;而科学哲学家也应该积极而恰当地介入其中,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防止智识未充分开化的普通民众不会在种种似乎“科学的”且逻辑的论证面前摇摆不定。但是介入此过程中的哲学家,也应该认识到这种哲学上的努力,在现实的决策情境中,由于学术发展所坚守的开放性论证的氛围和现实决策所需要的确定性和可操作性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所以他们还是有可能面临一定的智识上的危险或困境。因此,笔者认为,学者们无论在现实的决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大是小,一方面应该与决策者沟通,使其尽可能深入地了解决策的理论依据,一方面也应该提倡在学术界内部开展开放性的讨论,以在提高决策科学性的同时,使学术发展的所需要的开放氛围可得以维护。
这场创世学审判及其所引起的科学哲学界的争论,对于我国的现实政治决策和学术界,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反思价值。
收稿日期:2001-04-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