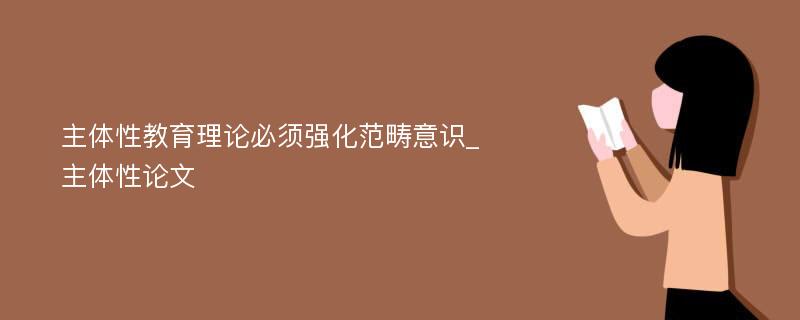
主体教育理论必须增强范畴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畴论文,主体论文,意识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教育中最热门的话题是主体,最混乱的话题也是主体。所谓的主体教育理论至今为止不过是个尊称而已。因为我们一旦步入这一领域,扑面而来的是一大堆模糊不清的概念。十分奇怪的是这一教育理论被学者们高度重视(被称为教育理论中的哥白尼革命,并成为教育热点中的热点),但在概念上却被“高度”忽视。以至于仅这一理论的称谓就有教育主体理论、主体教育理论、主体性教育理论等等,没有人对此区别解释,研究者对理论精确性的一丝不苟的精神在这里荡然无存。尽管称谓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话题(严格地说不是共同的研究对象)即关于教育中的主体问题,笔者姑且将这种理论称为主体教育理论。
这理论不论是什么称谓都离不开“主体”这二个字。然而什么是主体?又会碰到不同的含义问题。主体是一个哲学范畴,在哲学上,它有多重含义。一是“实体”,它被理解为属性、状态和作用的承担者,与现象等概念相对应。我们讲学校是办学主体就属于这种用法。二是指“物质的主要组成部分”,与“次要组成部分”相对应。某项大的教育计划中的主体工程、主体结构属这种用法。三是逻辑意义上的主体,指逻辑判断中的主语、主词。四是指人。其内部又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凡是人就是主体;另一种认为人只有作为某种活动的发出者才是主体,并认为主体为实践者、认识者,客体为被实践和认识的对象。这一概念的多义性,极容易导致研究陷入迷宫,即以含义A代替含义B,在理论研讨中有时人们各说各的,并不明白对方的理论是针对什么范畴而言的,论争成为盲人式的无谓的争论。
对此,研究者要有范畴意识,对主体概念的不同用法和含义必须严格区别。当然,主体一词在哲学上本来就是多义的,在教育中人们在多重含义上使用它已成为习惯,我们不可能也没必要让人们的思想都统一到一个含义上来。但研究者应明示在什么含义上使用主体这一概念,杜绝通篇研究论文对主体未界定的状况(这状况并非少数),这样可以避免造成理论研究中的混乱。
主体性概念也是一个难题。“主体性”是当今教育中的一个最时髦的高频词,人们对它似乎无需深究,谁都懂得。但事实上,它在哲学上并不具有昭如白日的自明性。只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在教育中谈主体性问题,除个别文章谈教育的主体性,将教育本身视为实体意义上的主体外,大多数文章都是指人的主体性,而不是实体或逻辑意义上的主体性。主体性中的“主体”指的是前文分析的第四种含义:(行为发出者的)人,是师生(人)的主体性。但主体性究竟指什么?仍然是一个问题。哲学家黄楠森说:“主体性不过是众多主体的根本共性,……‘性’一般指根本共性,而不是任何共性,如果把任何共性都包括在‘性’中,那就太滥了。……主体是人,但不等于人,人只有作为某种活动的发出者才是主体,因此,主体性不等于人性,而只能是作为主体的人的根本共性。……我认为它就是人在自觉活动中不可缺少的自立性、自为性、自主性、能动性等。”(注:黄楠森:《七对概念辨析》,《人文杂志》,1993年第1期。)他并没说清何以“性”就必然是“根本共性”, 何以根本共性就是自立性、自为性、自主性、能动性等。这是一个“悬案”。有趣的是,翻开任何一本关于主体、主体性的著作,都找不到对此问题的明确回答。但主体性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黄楠森说:“围绕主体性问题有七对概念需辨析,它们是:存在和思维、物质和意识、自然界和精神、主体和客体、主体性和客体性、主观和客观、主体性和客观性。”(注:黄楠森:《七对概念辨析》,《人文杂志》,1993年第1期。)这些问题哲学家难以理清,对教育家恐怕更难。
笔者认为与其陷入哲学的荆棘丛林,不如避开此问题,干脆称主体能动性。因为主体能动性不仅涵盖了自立性、自为性、自主性、创造性等特性,而且它在表达上比主体性清晰。“主体性”并非就不能用,可以把它理解为主体能动性的简称。
对主体能动性还需要加以界定。有一种观点认为主体就是能动的,甚至将主体与主动、客体与被动简单划等号,以至于有人认为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就必须承认学生是主体而不是客体。“能动性”这一主体教育中的高频词并不具有十分明晰的概念。能动性有两重含义,这两重含义往往被人们所忽略。一重是从行为的发出者和接受者意义上划分的。发出者为主体,与之相对应的接受者为客体。在教育中,确立教育对象的主体地位,就是要在教育过程中使教育对象由单纯接受式教育(单一客体)转变为教育者引导下的自我教育(主体)。不可否认,这对改变以往“你说我听”的单项灌输教育有着积极的意义。但仅凭这点就认为主体就是主动的,认识未免太简单。作为主体(行为发出者)的人,其行为既可能是主动的,也可能是被动的。
之所以我们认为主体就是主动的,是因为我们认为人有这种能动性的“潜能”,甚至有人认为从发生学的意义上看,人生来就具有主体性,这是人类进化的结果(注:黄崴:《主体性教育简析》,《中国教育报》,1995年11月3日。),而且似乎人就只有这种“潜能”。“潜能”从来都是一个褒义词。认为人的主体能动性的未彰显或主体性的失落是被(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所谓的“集体人崇拜”的传统文化与这种文化在今天的积淀)压抑、剥夺的结果,如认为中国传统的人生哲学湮没于家庭、血缘、氏族、社会等各种不同形式的“集体人崇拜”还难以消除,个体性的“人”的觉醒一直受到种种“人伦关系”类型化的价值观的支配。消除这些影响似乎是越不过的历史阶段。不可否认,传统文化中过于重集体的倾向压抑了人的个性,弘扬人的主体能动性无疑应消除这些消极因素。但是,被动性、盲从性等所谓的主体性失落状态并非简单地是“压抑”、“剥夺”的结果。
因为自我失落状态就是主体生存的一种真实状态,自我的“非我”状态是主体的一种确定的存在方式。海德格尔认为,此在(指人)一向就在“非本真”(自我失落)之中。他说:不能“把‘非我’说成是本质上缺乏‘我性’的存在者,这意指着‘我’本身的某种确定的存在方式,例如自我失落。”(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3页。 )这就是说自我失落就是此在(人)的一种存在方式。人不是他自己或者说“丧失自我”正是人的“别具一格”的在世。因此,如果说人有主体能动性的“潜能”,同样,人也有盲从性的“潜能”。作为主体的人并非就是主动的。
人的这种自我失落状态即使是在西方个人主义文化熏陶下的人也表现得十分严重。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有许多篇幅是专门描述人是被“常人”牵着鼻子走的。“常人展开了他的真正独裁。常人怎样享乐,我们就怎样享乐;常人对文学艺术怎样阅读怎样判断,我们就怎样阅读怎样判断;竟至常人怎样从‘大众’中抽身,我们也就怎样抽身;常人对什么东西愤怒,我们就对什么东西愤怒。”“常人把自己暴露为日常生活中的‘最实在的主体’。”(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56页。 )这个“常人”其实就是人云亦云的公众意见。
值得注意的是,人被这种“最实在的主体”常人(公众意见或权威意见)牵着鼻子走的现象,却又往往以能动性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在我们的生活中也绝非少见。如在“文革”中,在大一统的教育模式下,“响应”成为“一呼百应”的对应物,人们积极响应号召,主动参加活动,其行为越积极实质上就越消极,越主动就越被动。在一切人们认为在“响应”中表现出了能动性的时候,他们都陷入了一种缺乏自我控制的盲目发动状态。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识别这种被动性,但在当时相当多的人都认为它是能动的。甚至在主体性最需要的地方——主体教育理论中也有“常人”宰治的现象,常人对主体性怎样高扬,我们怎样高扬;常人对传统怎样批判,我们怎样批判;常人怎样反对人云亦云、鹦鹉学舌,我们也怎样反对人云亦云、鹦鹉学舌。对主体性,谁都可以振振闲谈!
弗罗姆区别了异化的能动性和非异化的能动性,并感叹:能动性“在当今之如此难以理解,是由于能动性的大多数类型都是异化的被动性。”(注:弗罗姆:《占有或存在》,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80页。)异化的能动性是非理性的盲从,这种能动性较难识别,是越积极就越消极的被动性。非异化的能动性是植根于理性思考的自我选择、自我决定的行为。因此,在主体教育理论中讲主体能动性必须将理性的(非异化的)和非理性的(异化的)两种不同性质的能动性区别开来。主体教育不仅要在教育中确立教育对象的主体地位,使其成为自我教育(即行为发出者意义上的)主体,更为重要的是培养理性的主体。
主体教育理论的研讨要形成自己的概念、范畴。拉卡托斯认为,每一个科学研究纲领都有一个“硬核”。所谓硬核,就是这个科学研究纲领的基础理论部分或核心部分。它是“坚韧的”、“不许改变”和“不容反驳的”。如果它受到反驳,整个研究纲领就受到反驳。主体教育理论不可能形成拉卡托斯的“硬核”或库恩的“范式”,但却应该有共同的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范畴也可以称为“硬核”(但不是科学共同体共同态度、信念和共同接受的理论框架即范式意义上的)。主体教育理论缺少这样一个“硬核”,整个理论就处于支离破碎状态。
在主体教育理论中,围绕教师和学生谁是主体、谁是客体问题有一场大论战。有教师唯一主体论、学生唯一主体论、师生双主体论。各种观点内部又是“同室操戈”、各自立异。仅双主体论就有“主导主体说”、“主导主动说”、“轮流主客体说”、“双主体主从说””、“三体—双中心人物说”、“教育主体的滑移位错”说、“同时主客体”说,等等(注:魏立言:《教育主体性问题论争述略》,《上海教育科研》,1994年3期。)。而在以上三种主要观点之外, 后来又有“超越主客体”论(注:金生:《超越主客体:对师生关系的再阐释》,《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1期。)。每种观点都言之成理、持之有据, 谁也说服不了谁。
这种状况对后继的理论家来说,无法高屋建瓴,无法用一种框架将本质上矛盾的各论各说统属整合为一体,更不可能在师生主客体关系理论基础上,去探索出一个行之有效的师生主客体教育模式去指导教育实践。对教育实践工作者来说,若要接受这些理论的指导,只能象做单项选择题一样,在A、B、C、D等项中任选一项,然后,还可能进行第二次选择,如选择了双主体“论”后,再在a、b、c、d等“说”中任选一项,但没有最优选择,每一种学说都有被其它学说所指出的“严重”失误,指导实践带来的“消极”效果都是不可避免的。这样,对教育实践工作者来说,似乎放弃选择无疑就成了最佳选择。
产生这种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们并未严格地遵循范畴。主客体本是一对哲学概念,引进到教育中来固然具有了教育学的特殊含义。但不管怎样,它们应与哲学概念相一致,而不能随意赋予它们含义。
如学生唯一主体论认为:“在教育过程中,学生始终处于主体——内因的地位,而教师则始终处于客体——外因的地位。按照‘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原理,必须提出学生主体论即学生是唯一的主体论。”(注:燕国材:《再论学生是教育过程的唯一主体》,《少先队研究》,1993年5期。)这里是将内因和外因作为划分主客体的标准, 但主客体与内因和外因是根本不同的两对范畴,不能以内因和外因代替主客体,以这种划分来确立学生唯一主体论缺乏根据。
再如超越主客体论认为:“不论是主体与客体,还是主导与主体、双主体等观点,都没有脱离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这就是主体与客体对立的模式。……这种对象性的师生关系,使教师与学生成为互相利用、互相占有、互相估算的对象,更可悲的是,这种对象性的教学关系,也只能使学生形成对象性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即努力成为一个思维主体或实践主体,从而把自身之外的一切都看作是对象性实在,进行控制、解析、计算、占有,不论对人生、对社会还是对于自然,都是如此,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都是对象性的,这必然造成自然与人、社会与个体、他人与自我的对立。”(注:金生:《超越主客体:对师生关系的再阐释》,《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1期。)这种观点认为, 师生都是主体,他们之间不能有主客体之分,一分就会产生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甚至能导致学生世界观的畸变。除非将客体赋予被利用、占有、估算的对象这一特殊含义,否则,认为一分出主客体,师生双方就会成为利用、占有、估算的关系未免过于牵强。超越主客体论也游离出了主体本身的含义。
本文在一开始指出了主体具有多种含义,除非不谈“主体”,否则,讨论应明示自己是在哪种含义上进行的,并严格遵循范畴进行。范畴不清或随意赋予其含义会使讨论失去准星,陷入剪不断、理还乱的窘境。只有遵循概念的讨论才会使认识不断深化,对共同对象的探讨的不同认识才能互补、融合。
主体教育理论要形成自己的范畴,一是上面讲的要严格遵循范畴,二是要形成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内容。现在这个理论象个“大筐”,素质教育、个性教育、创造性教育、愉快教育、终身教育等等,全装得下。抽掉了这些,主体教育理论不复存在。任何好的教育理论和成功的教育实践都可以称为主体教育。这种高度概括性的主体教育反映的不是概念的深刻而是贫乏。一谈到主体教育就给人以开天辟地的划时代感,所谓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即是主体性教育。所谓人(教师、学生)的主体能动性都得到充分发挥,主体意识充分觉醒,主体的精神世界和意志的充分拓展,主体素质的全面发展,主体潜能的全面实现,已成为当代教育关注的中心。听起来令人激动,冷静下来分析一下就发现,全是些空洞的口号。
范畴在学术研究中是十分重要的,有时新范畴的引进会引起人们思维方式的变革,导致新的认识和发现。主体教育理论是一个明显的例外,它的轰轰烈烈是表面性的。借用禅宗的话:成道前,山是山,水是水。成道后,山还是山,水还是水。主体教育理论并未给教育理论增添什么内容。甚至可以问一句:“主体教育理论在哪里?”
主体教育理论应该形成自己的特定的概念、范畴和体系,否则,用一种无个性、无主体性的理论去倡导培养主体性的人就是一个悖论。而这理论的创建需要教育理论家们的艰苦劳动。首先是理清范畴,其次是在共同范畴的基础上去提出有创造性的概念、范畴,进而形成理论体系。这种体系、理论框架可以是多样的,但它必须是“主体教育的”。
收稿日期:1998-1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