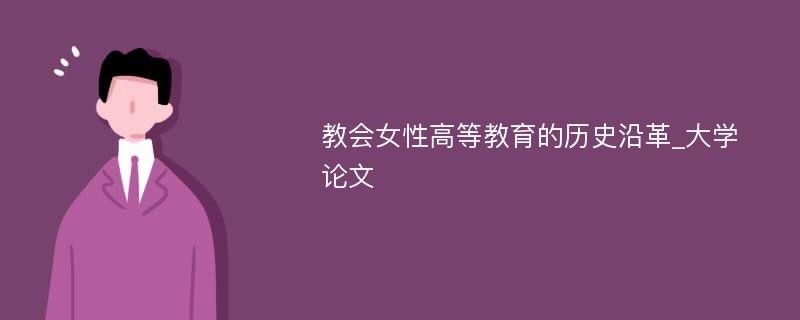
教会女子高等教育的历史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教会论文,女子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收稿日期:1996-01-15
近代中国教会女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是教会女学步履蹒跚的初创时期,数量少、程度低是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第二阶段从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期,是教会女学狂歌猛进的发展时期,数量增多,规模扩大,办学重心由初等教育转向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教会学校不仅开创了中国的女子高等教育,而且当中国人自办女学兴起和发展使得教会女子初等和中等教育变得无足轻重之后,教会女子高等教育依然保持着领先地位和第一流的水平,为中国第一代知识女性的成长提供了一块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三四十年代,教会大学培养了占全中国女大学生总数的30%左右的学生。
以往研究教会女学史的学者大多将重点放在第一阶段的女子初等教育上,对第二阶段教会女学的发展,尤其是对这一时期的女子高等教育涉论不多[1]。而教会女子高等教育作为教会女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其中最具特色和影响最著的一环。本文试图对近代中国的教会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演变及其在中国第一代知识女性的成长过程中所充当的母体角色作一概述。
1
20世纪上半期的教会高等女学以“五四”为界,呈现出前后不同的格局。在“五四”以前,普通的教会大学只招收男生,女子大学单独设置。“五四”以后,只招收男生的教会大学先后对女子开放,而原有的女子大学则继续保持其单性大学的性质。因此,“五四”以后的教会大学实际上是一种混合双轨制。
1905年5月,中国基督教教育会在上海召开会议。会议决定要在中国建立4所女子大学:华北、华中、华西、华南各1所[2]。但直至“五四”以前,教会女子大学总共只建成3所,即1905年创办的华北协和女子大学,1907年创办的华南女子大学和1915年创办的金陵女子大学。华西女子大学始终未能建成。1920年,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并入燕京大学。此后,基督教女子大学只剩下两所。1937年又有一所教会女子大学创办于上海,即震旦女子文理学院。该院为美国天主教会主办,其组织仿效金陵女子大学。但因创立较晚,而且十分保守,毕业学生多数没有从事社会工作,在近代中国影响甚微。
同早期教会大学男校一样,早期教会女子大学的规模都很小。图书馆和实验设备简陋不堪,教师人数和所开课程十分有限。虽然如此,早期教会女子大学的创办者们却自许甚高。华南女大自称是“迄今在上海以南,为妇女设计的唯一大学”[3]。华北协和女大校长麦美德则更骄傲地说:“南至长江,北至北极,东至太平洋,西至堪司炭厅,以偌大地点,仅此女子大学一处,其责任亦云重矣”[4]。当时,国人尚未设立女子大学,教会首开先河,自然有独占鳌头之感。
早期教会女大学生有这样几个特点:
(1)入学人数少,毕业率低。早期教会女大普遍感到生源有限,招生困难,而且只有部分人能自始至终坚持学完4年课程,学生中途辍学的比例甚高。如金女大第1期招收新生11人,读完大学一年级的只有9人,读完大学四年级的只有5人;第2期招收新生近20人,毕业时只剩8人[5],毕业率为40%—45%。华北协和女大自1905年创办至1920年并入燕京大学,前后毕业学生共计72人,共中本科31人,专科41人[6]。
(2)学生年龄偏大,起点较高。当时,教会女大要求新生必须具有高级中学毕业程度。在那时,中国女子教育兴起不久,女子入学晚,待到高级中学毕业时,不仅年龄偏大,而且相当成熟了。不少学生在上大学前曾任过教师甚至校长。如金女大首期学生11人中有10人曾教过书[7]。由于年龄大,自律性强,认识到自己是中国第一代女大学生,所以都认真读书,渴望求得学问。
(3)毕业后深造率高。如华南女大首届5名毕业生中,有4名留学美国和加拿大[8]。金陵女大前4届毕业生33人中,赴美深造获得硕士博士学位者有20人[9]。她们大都事业有成。她们的成就及其所担当的角色,为初期教会女子大学赢得了较佳的声誉。
对教会高等女子教育来说,“五四”前后的变革具有重要的划时代意义。其中一个最重大的变革是教会大学男校相继对女子开设。通常认为,中国大学开女禁,肇始于1919年国立北京大学。实际上,在北大之前,广州岭南大学曾一度招收过女生,招收对象多为本校教员的女儿。1920年,岭南大学正式准许女子入校学习。是年,该校共有女生28人,而北大只招收了9人。翌年,岭南第一个女毕业生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成为中国男女同校后毕业的第一名女大学生。可以说,在中国大学开女禁史上,教会大学岭南与国立大学北大共同扮演了开路先锋的角色。
继岭南之后,其他教会大学也先后向女子开放了。到1929年,全国34所大学中,兼收女生的有29校[10]。13所基督教大学中,只有圣约翰大学开放女禁较晚。1936年,上海圣马利亚女中12名毕业生因政府规定已立案的大学不得招收未立案中学毕业生而升学无门,遂向属同一差会的圣约翰大学提出申请。该校无奈,才被迫开放女禁[11]。在教会大学中,两所天主教大学开放女禁最晚。辅仁大学和震旦大学直到1938年前后才开始招收女生。
多数教会大学男校向女子开放后,教会女子高等教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入教会大学的女生人数成倍地增长。1920年,教会大学在校女生总计117人,1925年增加到530人[12],1931年复增至825人[13],1934年进一步上升为1236人[14]。14年间,教会大学女生人数增长了10倍以上。在“五四”以前,教会女子高等教育由3所女子专门大学独力承担,“五四”以后,发展为全体教会大学共同肩负。1920年,金女大和华南女大两校学生人数约占教会大学女生总数的60%,到1934年,这一比例下降到23.4%,其余76.6%分别由燕京、岭南、金陵、齐鲁、沪江、东吴、华中、华西等大学培养。在这些教会大学中,以燕京招收的女生人数最多,其次为沪江、齐鲁、岭南,金陵、华中、之江、福建协和等校较少。
燕京在“五四”以后的教会女子高等教育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924年,燕大在校女生113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的25.8%;到1935年增至274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的31%[15]。在20年代,金女大人数在教会大学女生人数中一直独占鳌头。从30年代起,燕大女生人数跃居金女大之上。1922—1936年间,燕京共毕业女生393人[16],与同期金女大毕业生403人不相上下。
抗战时期,教会大学辗转内迁,图书和教学设备损失惨重,办学条件十分艰苦。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教会大学女生人数在战时不但没有减少,相反得到了较快发展。如圣约翰大学在1936年刚开女禁时,只有7名女生,到1941年竟增至400名女生,占全校学生总数的1/3[17]。战争将传统的陈规陋习一扫而光,为女子教育的发展扫清了道路,而且这种趋势在战后也不可逆转。据1947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部分教会大学女生人数,其中辅仁大学929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的38.9%),沪江大学471人(44.3%),震旦大学520人(41.9%),华西协和大学688(38.5%)[18]。各校女生所占比例之高,已接近有的甚至超过同期美国大学女生的比例[19]。
2
“五四”以后,金女大和华南女大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教师和学生人数逐年增加,系科和课程设置日趋完善。两校均募得大笔款项,营建了各具特色的新校舍。当时教会大学大部分在国外注册,金女大与华南女大亦分别于1919年、1922年向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申请注册,均被该校核准立案。自此,两校毕业生可以不经考试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留学深造。1927年以后,中国政府提出收回教育权的要求,规定外国教会在中国办的大学要建立以中国人为多数的校董会,并由中国人担任校长。两校均顺应时势,改选中国人当校长。金女大校长吴贻芳,华南女大校长王世静,两人均曾留学美国纽约密执安大学,吴贻芳获博士学位,王世静获硕士学位。吴执掌金女大23年,王执掌华南女大近20年,是近代中国大学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两位女校长。两人为基督教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30年12月,金女大由南京政府教育部核准立案。6年后,华南女大亦核准立案。依照当时南京政府教育部制订的大学组织法,高等院校必须有三个学院才可称为“大学”,金女大和华南女大均只有文、理两个学院,乃分别改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不过习惯叫法仍称之为“金女大”和“华南女大”。
学校名称由“大学”易为“学院”,名义上降了一级,但实际上,无论是教师和学生人数、系科及课程设置,还是图书实验设备和校产规模,两校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其中金女大发展较为显著:1924年在校学生135人,1926年165人,1934年238人,1936年259人,1937年350人。抗战初期,因受战争冲击,学校西迁,入学人数一度减少,但至抗战中期逐渐恢复,1944年在校学生为320人,1945年为348人,1947年达440余人,1948年超过480人[20]。金女大刚开办时,只有教职员6人,1927年增至46人,1945年增至86人。图书及教学设备也添置较快,到抗战前夕,金女大中外文图书已达10万册,教学仪器设备可供400名学生实习之用,另有钢琴20余架[21]。校产总值在150万元以上[22]。
抗战期间,金女大辗转上海、武昌,最后集中迁至成都,借地自建校舍办学。华南女大则迁往闽西北山城南平。
抗战胜利后,两校相继迁回原址复课。1951年,金女大与金陵大学合并,华南女大与福建协和大学合并。至此,结束了两所教会女子大学的历史。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在金女大和华南女大基础上分别改建成“南京师范学院”和“福建师范学院”。
从比较中审视两所女子教会大学的办学特色,不难发现两校的相通和相异之处。
华南女大的创办比金女大早8年。前者由美国美以美会独家资助;后者由美国美以美会、监理会、浸礼会、基督会和北长老会等5个差会联合资助。对早期中国教会大学来说,各差会的资助是学校得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经济来源。在这方面,华南女大一开始便比金女大稍逊一筹。此后,金女大在经费筹措方面始终走在华南女大的前面。金女大创办虽较华南女大为晚,但因经费比较充足,很快后来居上。1919年,金女大首届毕业生5人获得学士学位,而华南女大直到1921年才首次有3名学生修完大学本科课程毕业。其后,金女大人数逐年递增,声誉日隆;相比之下,华南女大显得捉襟见肘,步履蹒跚。据1934年统计,华南女大的系科设置和图书藏量不及金女大的一半,在校生和毕业生人数仅及金女大的1/3。
华南女大发展缓慢,生源不足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该校地处福州,主要面向福建招生,生源有限。相比之下,金女大地处首都南京,学生以江浙地区为主,面向全国招生,生源充足。金女大建校20周年时统计,其学生来自全国17个省和南洋地区的80所中学[23]。作为教会大学,金女大和华南女大都收费很高,非社会中上层家庭无力负担,而华南女大所处的福建不如金女大所处的江浙一带富庶。此外,华南女大严格要求学生须出身于教会女子中学,并且宗教信仰甚笃,而当时福建一省教会办的女子中学毕竟有限,要从中挑选出合乎要求的高材生更非易事[24]。在这方面,华南女大为了保持其教会学校本色,秉持着宁缺毋滥的原则。
由于华南女大发展慢、规模小,学生来源和毕业生的去向主要面向福建一隅,带有强烈的地域色彩,其影响也始终未能超过“华南”,走向全国。相对而言,金女大无论是学生来源、毕业生的成就,还是社会知名度,在当时中国均具有比较广泛的影响。
作为教会大学,具有宗教色彩自然是两所学校的共同特征。但金女大向国民政府立案注册以后,宗教色彩逐渐淡薄,世俗化特征日趋明显。从30年代初开始,金女大将宗教课改为选修,一切宗教性质的活动改为自由参加。金女大宗教系从设立到取消,只存在了3年(1926—1929年),前后主修宗教教育的毕业生只有1人[25]。信教的教师对不信教的学生从不施加压力。金女大学生在前期以来自信教家庭和教会女中为主,到后期,特别是战时西迁成都后,来自信教家庭和教会女中的比例明显下降。金女大学生毕业后,献身宗教事业的也很少。据1947年统计,在金女大已毕业的1至29届703人中,只有11人从事宗教工作,仅占1.5%[26]。
华南女大则不同。在13所基督教大学中,华南女大以始终保持浓厚的宗教色彩而著称。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该校所有的教育教学活动一直紧紧地围绕着传播基督精神,培养高级女教牧人员和虔诚的女教徒这一中心目标来进行。即使在30年代教会大学世俗化的浪潮冲击下,其办学宗旨依然一如既往。在该校的课程和课外活动中,宗教灌输和宗教活动始终列为首位。据称该校宗教教育系这一学科开设的课程曾多达11项,共34学分[27]。该校课外活动,诸如每晨礼堂聚会、晨间礼拜(后改为课间礼拜)、主日教堂礼拜、耶稣受难周、查经班以及邀请教会名人演说等,宗教氛围非常浓郁。在教会的控制和支持下,该校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教会的培养目标。到1926年,该校共毕业38名学生,全部信奉基督教,其中有24人在教会学校任教[28]。在该校以后的历届毕业生中,总有相当比例的人在教会所属学校、医院或其他教会机构工作。资助差会对此感到非常满意和自豪。据1936年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统计,华南女大在校学生信奉基督教者占80%以上,成为教会大学中学生信教比例最高的3所大学之一(其他两所是齐鲁和福建协和)[29]。据称,在当时国内外宗教界,该校师生也颇为活跃。1922年春,该校派代表参加世界学生基督教同盟大会。1924年该校校友又应邀参加了在伦敦召开的国际基督教女青年会议。诸如此类,使华南女大在基督教教育界享有相当的声誉。但在另一方面,该校由于浓厚的宗教色彩而与中国民众相隔绝[30],大大减弱了该校在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界的地位和影响。
华南女大和金女大尽管在办学规模和社会影响方面差距甚大,但同为教会女子大学,两校在办学形式和校园文化等方面,仍具有一些相通和相似之处。这些相通和相似之处恰能反映出教会女子大学的特色。
(1)学校生活家庭化。在两所女子大学中,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老师之间、学生与学校领导之间,人际关系都比较融洽,并呈现出温馨的家庭生活氛围。特别是金女大校园中,这一氛围十分浓厚。该校“每一宿舍有交谊室及饭厅,教师于课余之暇,与学生相处如姊妹,师生之间,仿佛一家之人;同学之间,更有姐妹班之组织”[31]。高年级与低年级结成“姐妹班”为金女大所独创,这一制度对培养学生之间互助友爱精神,消除低年级与高年级学生之间的隔膜,颇见成效。在师生之间,金女大推行导师制,每位学生可找一位教师作自己的导师。一位导师带八九个至十余个学生不等,用小组活动或其他方式帮助学生解决学习、生活及其他方面的问题。导师制的推行,密切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这一制度直到三四十年代才在全国高校中比较普遍地推行,而金女大在成立后的第二年(1916年)便已实行了。“五四”以后,中国国立大学学风普遍有“嚣张”之势。学生与学校领导之间经常处于一种紧张对立的状态。而在金女大,学生与学校领导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大的冲突。校长吴贻芳犹如一家之长,关怀和爱护校园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她执掌校务20多年,对数以百计的毕业生不少能叫出她们的名字。在她的主持下,金女大就像一个温馨和睦的大家庭。许多金女大毕业生在回忆学校生活时,都认为金女大同学之间亲如姊妹,师生之间如同母女的校园氛围给她们留下了良好深刻的印象[32]。
在华南女大,虽然没有推行类似“姐妹班”之类的制度,但因为学校规模小,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彼此接触十分频繁。几乎每一个学生都能得到教师的个别指导。据1934年统计,该校教职员与在校学生的比例为2比5[33],即平均5个学生可以得到2个教师的指导。师生之间来往频繁,关系亲密。大部分学生毕业后对母校有着强烈的感情,不少毕业生愿意作出经济上的重大牺牲而回校任教[34]。诸如此类,都表明家庭化的校园生活对学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2)校风严谨、保守,毕业生独身率高。教会女大初创之时,中国女子高等教育尚未兴起,为了能在中国传统势力尚十分强劲的情况下求得生存,减轻保守观念的阻力,教会女校当局有意识地强化对学生的管理,以免给反对者以借口。那时学生大多来自上流社会,学生家长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在教会女校既能学到西方现代知识,又能保守中国传统规范,以便日后能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女婿。教会女校为了维护自身在中国上流社会中的良好声誉,只得顺应这一要求。另一方面,来华女传教士自身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也还不够开放,有的还秉持着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些保守观念。因此,在初创时期的教会女子大学里,校风严谨有余,偏于保守。尤其在师姑主政的华南女大,学校对教师和学生的管理非常严格,男女授受不亲被学校当局视为戒律。多数课程由笃信宗教的师姑担任。国学一门不得已须聘请男教师时,也尽量选聘科举出身又受过教会洗礼的老先生担任。女教师有专用的备课室和休息室,男教师不得入内。男教师还不能进膳厅和女教师、女学生一起用饭。连工友也多聘用一些信教的农村贫苦女性担任[35]。
在金女大,男女界限虽不如华南女大森严,但学校对师生的管理也很严格。金女大初期教职员均为女性,以后虽陆续聘有男教师,而女教师仍占绝对多数,据1945年统计,在86名教职员中,女性占67位[36]。这种情况在国人自办女子大学中是看不到的。金女大西迁成都后,对学生的管理已较战前宽松。尽管如此,相对于男女同学的大学而言,女子大学显得单调、沉闷,缺乏男女社交机会。加之教师中独身老处女多,对学生也不无潜移默化的影响。各种资料显示,两所教会女子大学毕业生晚婚和独身的比例甚高。早在20年代末,就有人注意到金女大毕业生晚婚和独身者多。他们统计金女大1919—1927年毕业的9届105人的婚姻,发现已结婚的仅占16%[37]。金女大早期毕业生如此,后期毕业生亦同。据1947年的抽样调查,在165位金女大毕业生中,已婚者74人,占44.8%;订婚者11人,占6.6%;未婚者80人,占48.4%[38]。笔者查阅1947年《中华全国大学妇女会会员登记表》,在262名会员中,有80人毕业于金女大。统计这80人的婚姻状况,除4人不详外,已婚者48人(60%),未婚者28人(35%)。未婚者中,年龄最小者为26岁,最长者为59岁,平均年龄为40岁[39]。在当时中国社会背景下,金女大毕业生晚婚和独身的比例无疑是相当高了。据称这一情况在华南女大毕业生中也同样存在。
(3)政治参与意识淡薄。“五四”以来,中国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极强,每一场大的政治抗争和救国活动,无不以学生为先导。在这方面,教会大学学生的情绪和行动,常常不如非教会大学学生之高昂激烈。在教会大学中,女学生又不如男学生之主动积极,两所女子大学学生对政治尤为淡薄。金女大学生虽然参加了“五四”运动,但当“五卅”运动发生时,金女大学生便开始分成两派:一派主张参加,一派反对参加。“九一八”事变时,金女大学生虽然成立了抗日救国分会,但没有举行示威[40]。抗战爆发后,虽有学生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并作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抗日救亡工作,但参加人数有限。1946年金女大从成都迁回南京后,学校的政治空气非常沉闷。是年美国兵强奸北大女生沈崇,全国学生群情激愤,金女大校园却异常平静。其后,南京“五二○”事件及浙大学生于子三在狱中被杀事件,虽有外校学生前来串连,而金女大学生却没有走出校门去参加[41],直到1948年秋,金女大才正式建立中共地下党支部[42]。
在华南女大,学生的政治意识更加淡薄。据说该校学生连“九一八”抗日救亡运动都根本没有参加[43]。完全与当时中国政治生活相脱离。
金女大和华南女大学生政治意识淡薄的原因,一是两校学生的家庭背景所致。两校均有“贵族学校”之称。学生多为政府官吏、自由职业者、地主和资本家的千金小姐,生活比较富裕。在通常的情况下,富裕往往使人保守;二是学校的教会背景使学校当局对学生的思想控制比较严密,宗教教义的灌输逐渐消弭了学生的“异端”观念。此外,女子温和柔顺的性格和传统观念对女性的束缚,也是导致其政治意识淡薄的因素之一。
(4)重视社会服务和社会实践。教会大学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办学特色。其中各个学校的校训往往高度概括了各自的办学宗旨。金女大的校训“厚生”和华南女大的校训“受当施”,用词虽然不同,涵义却颇有相似之处。“厚生”一词源自《新约》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要丰盛。”其意与耶稣所说:“我来不是要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的含意相近。金女大用“厚生”作校训,涵义又作了进一步的引伸:“人生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自己活着,而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帮助他人和社会,这样不但有益于别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更丰满”[44]。金女大以此为培养学生的宗旨,时时告诫学生:“为人处世,是施予,不是取得;是宽容,不是报复;是牺牲,不是自私”。
华南女大的校训“受当施”亦是教导学生怎样处理自己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以及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施予比获取更可贵,义务比权利更重要。帮助他人,服务社会,人生更富有意义。两所女大不约而同地以此精神作为培养学生的指导思想,并通过学校生活的各个方面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引导学生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在“厚生”和“受当施”精神指导下,两校学生均特别重视社会服务和社会实践,这些看起来琐屑、不起眼的工作,却深受下层民众的欢迎。近代中国女权运动的最大缺失之一就在于上层精英女性与下层平民女性相脱离。上层女性只顾争取自身的参政权、选举权和职业权,不屑或不愿深入下层工农妇女民众,不了解也不关心下层平民女性的需要和困难。早在1923年向警予就痛切地指出:中国知识妇女开展的女权和参政运动缺乏群众基础,反不如“基督教妇女能深入群众比较有力”[45]。两校通过开展社会服务和社会实践活动,加强了学生对服务人生的信仰,并使学生从实践经验中体认到社会服务的意义和价值。“厚生”和“受当施”的精神种子,就在这样的实践活动中像春雨一般滋润和植根于每个学生的心田之中,并演化为一种人格力量,终生伴随着她们,渗入到她们的工作、生活和家庭,乃至浸染她们的后代。“为社会服务”成为近代教会女子大学毕业生的共同追求和生活信仰。
3
在20世纪上半期的教会高等教育中,女子高等教育究竟处于何种地位呢?
首先,教会大学最早开创了中国的女子高等教育。在“五四”以前,中国政府一直无视女子高等教育。直到1919年4月,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改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立女子大学才正式面世,比第一所教会女子大学创办晚14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成立后,发展十分艰难。由于受当时中国动荡政治的影响,这所国人自办的唯一的女子大学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对此,我们只要从该校校长的频频更换和学校所属关系的一改再改即可窥其一斑。在1919年4月至1924年2月不到5年的时间里,该校校长先后六易其人[46]。1924年5月,该校改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次年8月,因校内发生风潮,被当时教育总长章士钊下令解散。同年12月,段祺瑞又下令恢复。1926年9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将其改为女子学院师范大学部。1927年8月,复改称国立北平大学女子第一部。1928年11月,再改称国立北平大学第二师范学院。1931年7月,并入北平师范大学[47]。从此,这所国立女子大学不复存在。在民国时期,国人自办的女子大学还有两所。一所是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一所是重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前者由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发展而来,1929年6月正式成立;后者创设于战时陪都重庆,正式成立于1940年[48]。这两所学校因为是半路起家,历史都不长。因此,在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没有一所国立女子大学自始至终地办下来,或中途夭折,或半路起家,只有华南女大和金女大相对独立地持续稳定地发展了三四十年。
其次,3所国立女子大学均是师范性质,系科和专业设置不如金女大宽泛,毕业生出路更不如金女大广阔。在3所国立女大中,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要算是历史最长的了。就规模而言,该校在校学生人数在30年代初即已超过了金女大,但其校产设备、图书资料、师资力量、办学水平、校园文化环境以及毕业生的成就等,均不可与金女大等量齐观,其声誉和影响远逊于金女大。2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人自办大学的迅猛发展,教会大学的主角地位开始受到挑战,渐渐退居配角地位。而两所女子教会大学尽管在13所教会大学中处于少数,但因国人自办女子高等教育一直十分薄弱,所以始终处于领先地位。
除专门性的女子大学外,一般男女同校的教会大学对近代中国的女子高等教育也作出了重要贡献。20年代初,教会大学女生约占全国大学女生总数的40%。进入30年代以后,教会大学所培养的女生在全国大学女生中所占的比例有所下降,一般保持在25—30%之间。这个比例高于同时期教会大学学生总数在全国大学学生总数中所占的10—15%的比例。
再从男女生的比例来看。1922年,国立大学女生(537人)占其学生总数(30860人)的1.7%,而教会大学女生(350人)占其学生总数(4020人)的8.7%。到30年代,教会大学女生占其学生总数的比例上升到20—25%,到40年代,进一步上升到30—35%,均高于同期国立大学女生所占的比例。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教会大学比国立大学更加重视妇女教育。尽管“传教士教育工作者未必一定是男女平等主义者,但他们为妇女在更大程度上的独立奠定了基础”[49]。可以说,在第一代中国知识女性的成长过程中,教会大学扮演了十分重要的母体角色。
大学不仅是一个传播文化、灌输知识的场所,也是一个塑造人格、濡化品性的场所。一个大学的校风对其学生的思想品德、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均具有一定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教会大学出身的知识女性,其品行自然或多或少濡染了一些异于非教会大学毕业生的成份。一般认为,教会大学毕业的女性多半能刻苦耐劳,对于社会服务事业有浓厚的兴趣。她们中多数具有较强的职业意识,事业心强,勤业敬业,能发奋自励。缺点是生活方式欧化,不谙国情,政治意识淡薄,具有优越感。这些看法虽然有的难免以偏概全,但也多少道出了教会大学毕业女性的某些群体特征。笔者曾根据《古今中外女名人辞典》和《华夏妇女名人辞典》中收录的出身于教会大学的223位妇女名人进行统计,发现她们绝大多数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学者,学有专长,事业有成。她们成名不是“妻以夫贵”,也没有那种“暴得大名”的新闻式人物。她们主要靠自己出色的工作实绩以赢得社会的承认。她们中政治活动家较少。
从223人的年龄结构来看,她们绝大多数出生于20世纪一二十年代,就读于三四十年代。新中国成立时,她们大多正值年富力强和事业有为的黄金时期。她们的工作业绩主要是在1949年以后中国的建设事业中树立起来的。这一格局虽然与辞典收录人物的标准不无关系,但仍然可以说明,教会大学所培养出的众多女性人才,不仅在民国时期发挥过重要作用,而且也在1949年以后中国走向现代的过程中,贡献了她们的一份力量。
注释:
[1] [美]杰西·格·卢茨著,曾钜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黄新宪:《中国近现代女子教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两书中各列小节有所介绍。
[2][3][8] [美]华惠德著、游捷译:《初创时期的福建华南女子大学》,载《教育评论》1990年第1期。
[4] 麦美德:《中国基督教女子高等教育概论》,载《中国基督教会年鉴》第4辑,1917年。
[5][9][20][21][26][36][42] 孙海英编:《金女大大事记》(金女大校友会印)。
[6] 《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935页。
[7][25][41][44] 吴贻芳:《金女大40年》,载《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1983年。
[10] 俞庆棠:《35年来中国之女子教育》,载《最近35年之中国教育》,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
[11] 阮仁泽、高振农主编:《上海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26页。
[12][17][28][30][34][43][49] [美]杰西·格·卢茨著,曾钜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7、356、125、125、125、312、497页。
[13]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丁编,第34—37页。
[14][33] 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全国高等教育统计》,1934年度。
[15][16] 《私立燕京大学一览》(1936—1937年度),第182、183页。
[18]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高等教育篇。
[19] 美国大学内女生所占的比例:1900年19.1%,1910年22.7%,1920年34.2%,1930年39.9%,1940年41.3%,1948年35.2%。引自赵文艺《我国近20年来女子高等教育发展之研究》(台北,1970年),第110—125页。
[22][23][31]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20周年纪念特刊》,载《申报》1935年11月2日。
[24][27][35] 郭肇民:《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历史概述》,载《福建文史资料》第20辑,1988年。
[29] 中华基督教育会:《关于在华教会大学宗教生活的报告》,上海,1936年,第6—7页。
[32] 《吴贻芳纪念集》(南京,1987),第141—178页。
[37] 江君:《配偶问题的两点》,载《金陵周刊》1928年第24期。
[38] 刘义馨:《毕业同学就业调查》《1947年金女大学生毕业论文》,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668,案卷号156。
[39] 《中华全国大学妇女会会员登记表》,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648④,案卷号308。
[40] 德本康夫人:《金陵女子大学》,引自《中国教会大学史》,第312页。
[45] 向警予:《中国最近妇女运动》(1937年7月),载《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3页。
[46][47]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一览》(1934年8月),第25—27页。
[48] 《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五周年纪念特刊》(1945年12月),第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