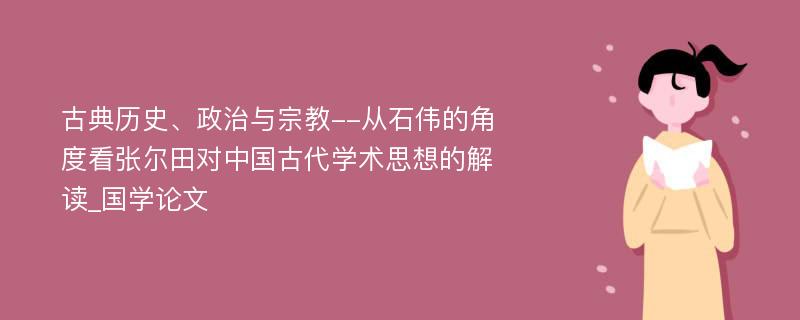
经史与政教——从《史微》看张尔田对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教论文,中国古代论文,学术论文,思想论文,看张尔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6)06—0177—10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界出现了明显的断裂,由于新文化派学人占据了思想学术舞台的主流,与其观点相异的学人往往被排斥到边缘,以至于在后人编述的近现代学术史中鲜见其踪影。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为全面总结学术历程,寻找学术方向,国内学界出现了“重写学术史”的热潮,《学衡》派等非主流学术群体首先进入学者的视野。近期桑兵先生《民国学界的老辈》① 一文更是进一步追溯到民国学界的“老辈学人”群体,并凸现其在“回到历史现场去认识中国历史文化”工作中的意义,其意可嘉。然老辈学人固然共同特色鲜明,但也有差别,因此为复原学术史全貌,群体的研究固然重要,个案的分析也不可少。张尔田为清末民初学术界重要一员,桑文中亦多处引述,然其人、其学作为整体却至今鲜为人所知。本文简述张尔田生平并评述其代表作《史微》,以期为研究近现代学术思想史者之一助。②
一 张尔田生平、著述简述
张尔田(1874—1945),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原名采田,字孟劬,晚号遁堪,是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张尔田出生于一个累世仕宦并以文词知名的家庭,由于家世的熏陶,他自幼笃好文史之学,并很早便以辞章显名。22岁时,他遵父命出仕为官,任刑部广西司主事。在京期间结识同乡夏曾佑,成为讲学之友,并一同钻研佛学。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改任苏州试用知府。在苏州任职期间,他与王鹏运、朱孝臧、郑文焯等过从甚密,共同讨论词学。后来在上海又结识了况颐周,这样“晚清四大词人”对他都有了直接的影响。他也成为清词后劲,词作后结集为《遁堪乐府》出版。③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他出版成名作《史微》4卷。当时学界有人把此书与《史通》、《文史通义》并举,张尔田也因此获得“海内治会稽之学两雄”之一的称誉(另一雄为孙德谦)。同年,他还与孙德谦合著出版了《新学商兑》一书,批驳梁启超的《支那宗教改革论》。
1911年辛亥鼎革,张尔田以清代遗老自命,隐居上海,研究学问,勤于著述,出版《玉溪生年谱会笺》。1912年10月,孔教会在上海成立,他成为孔教会的一员,并为《孔教会杂志》撰稿鼓吹孔教。当时的上海,学者文人会集,他与王国维、孙德谦因年辈相若,齐名交好,时人有“海上三君”之美誉。
1914年北洋政府设立清史馆。张尔田于同年应聘入馆任纂修,直至1923年脱离,前后近10年之久。在馆期间,他与夏孙桐共同商定康熙朝大臣传目,撰写《图海·李之芳列传》一卷,《乐志》八卷,《刑法志》二卷,《地理志·江苏篇》一卷,后来印行的《清史稿》就是用的张尔田的原稿。《后妃传》一卷未被采用,离馆后他修改增补,定名《清列朝后妃传稿》,于1929年在上海梓刻问世。
在清史馆任纂修的同时,曾一度任教北京大学。1923年返沪后,先后任教中央政治大学、光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1930年秋,胞弟张东荪北上任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尔田同时受聘该校,教授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
教读之余,他勤于著作。除了在《学衡》、《史学年报》、《学术世界》、《同声》、《词学季刊》等杂志发表大量文章之外,晚年大量精力用于整理校订沈曾植的遗著。其中《蒙古源流事证》一书,张尔田在校订文字之外,予以大量增补,还把王国维据另一版本的校语选择加入,使此书成为一部三家注本,并改名为《蒙古源流笺证》出版。
1945年2月19日卒,葬于北京香山万安公墓,享年72岁。1948年,遗著《遁堪文集》,由张芝联在上海刊行。
综观张尔田一生,除短时间出仕为官之外,基本上在学术研究和教学中度过,并与新旧学者多有交往,门生弟子众多,与中国近代学术有深厚密切的关系。他著述丰富,治学领域广泛,经、史、子、集四部皆有传世之作。钱仲联称之为“近代著名的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④,齐思和称之“于义理辞章考据之学皆造其极,为当代大儒”⑤,应非过誉之词。
二 《史微》的内容
《史微》先后行世有3个版本,1908年初版为4卷本,1912年再版重定为8卷本,均署名张采田撰,为多伽罗香丛书之一种。两个版本大同小异,除由4卷析为8卷外,部分篇章亦有增加、合并和顺序调整。1912年8卷本曾于1926年重刊,增附作者“覆校札记”。之后,作者还曾不断修订数处。2006年黄曙辉点校本《史微》⑥,把作者后来的修订搜罗进来,是目前最为完备的版本。本文以1912年的8卷本为基础来介绍它的内容。
据书前“凡例”所云,此书仿刘知几《史通》之例分为“内篇”和“外篇”,“内篇为古人洗冤,为来学祛惑,本经立义,比次之学居多。外篇发明天人之故,政教之原,越世高谈,论断之学居多”,但先后3次刊刻的都只是全书的“内篇”。据吴宓《空轩诗话》云:“张孟劬先生著述宏富,……诸书以《史微》为最要。然先生生平精力所萃之二书,迄今尚未作成。(1)曰《新览》,古有《吕览》一书,故名。拟仿诸子之体例,阐述先生独立综合之思想,成一家言。《史微》评述前人,为中国古来学术之总结算。《新览》则宣示自己独到之见解,志在创造。《史微》为《新览》之基础,《新览》则《史微》之外篇也。”⑦ 可知作者原计划的外篇部分又名《新览》,最终没有完成。
《史微》全书8卷,正篇38篇和附篇4篇,共42篇,十余万言。第1卷《原史》、《史学》、《百家》、《原艺》四正篇和《史官沿革考》、《郑学辨》两附篇,是全书的总纲,其中《原史》篇,简明扼要地提出了全书著述宗旨和主要观点;第2卷《原道》、《原墨》、《原杂》、《原法》、《原名》5篇,第3卷《原纵横》、《原儒》、《原兵》、《子余》、《宾孔》5篇和一附篇《诸子文说》,分别论述诸子百家的源流及各家宗旨;第4卷《征孔》、《经辨》、《案易》3篇,第5卷《案春秋》、《案礼》、《案诗书》、《原纬》、《原小学》、《经翼》6篇和一附篇《今古文问答》,主要根据今文家的说法阐述孔子的思想并辩明其与六艺相关的问题;第6卷《博观》、《祖道》、《宗旨》、《宗经》、《口说》、《流别》6篇,综合论述诸子百家之间、诸子和六艺之间的关系;第7卷《觗异》、《争讼》、《易论》、《春秋论》、《礼论》5篇,第8卷《古经论》、《明师》、《明教》、《通经》4篇,进一步从多个方面阐述本书的宗旨。全书虽然分篇数十,每篇各有宗旨,但是首尾呼应,结构紧密,以一个主要观点为统领,是一部系统的、以六经诸子为中心的古代学术思想通论性著作。全书主要内容和观点,可综合为递进的三个重要命题予以叙述:
一、六艺皆史也,百家道术,六艺之支与流裔也
作者在“史微凡例”自称此书“盖为考镜六艺诸子学术流别而作也”,而“名曰《史微》者,以六艺皆史,而诸子又史之支与流裔也。”因此,“六艺皆史也,百家道术,六艺之支与流裔也”是此书立论的基石,为全书首要命题。这一命题以“六艺百家的源流”和“六艺百家之关系”两个层面为支撑。
1.六艺百家的起源和流行
作者在《原史》篇中开宗明义,提出了“六艺皆史也,百家道术,六艺之支与流裔也”的论点。作者是从学术思想与政治的历史关系来展开论述的,其具体内容是指在诸子未分以前,学术政教,皆聚于官守,并由各官所配置的“史”一职掌管。其中“太史”是天子之史,掌管的是“君人南面之术”,而“百官各有史,史世其职,以贰于太史”,百官之道术皆由百官之史所掌。其中太史所掌之书就是“六艺”。六艺是上古的通史,“周易为伏羲至文王之史,尚书为尧舜至秦穆之史,诗为汤武至陈灵之史,春秋为东周至鲁哀之史,礼乐为统贯二帝三王之史”(《史学》),其中记载有“天人之故、政教之原、体国经野之规、宰世御民之略”(《史学》)。总而言之,后世所谓的六艺,“皆古帝王经世之大法,太史守之,以垂训后王”(《原史》)。
降至东周,天子失官,由官府所掌握的道术流到民间,成为诸子百家学说。其中太史所掌的“君人南面之术”降为道家,百官所掌的辅助君王治国理民之术则衍为其他诸子学说,“司徒之官衍为儒家,羲和之官衍为阴阳家,理官衍为法家,礼官衍为名家,清庙之守衍为墨家,行人之官衍为纵横家,议官衍为杂家,农稷之官衍为农家,稗官衍为小说家,司马之职衍为兵家,明堂卡史之职衍为数术家,王官一守衍为医家。”(《原史》)因此,作者总结道:
盖先王设官也,有政焉有教焉。儒道小说,圣人之教;兵及医方,圣人之政。政为有司所职,教则史官掌之。故百家学术可一言以蔽之曰:原于百官之史而已。(《百家》)
通过以上叙述,可知“六艺皆史”的论断袭自章学诚“六经皆史论”,而“百家道术,六艺之支与流裔”的论断本诸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诸子出于王官论”,为二者的混合并有所修正。《汉书·艺文志》认为道家原于史官,《史微》则指出六艺和诸子百家皆原于史。
2.六艺百家之关系
既然六艺和诸子百家都源于“史”,两者必然有密切的联系。关于六艺与诸子百家的关系,他有如下的论述:
六艺者先王经世之迹也,百家者先王经世之术也。(《百家》)
六艺者先王经世之迹也,诸子者先王经世之意也。古无所谓政也,经而已矣;古无所谓经也,子而已矣。(《子余》)
古所谓经,史而已。古之治史者,无所谓传注,子而已。故诸子实古经说也。(《宗经》)
综合起来,即是说六艺是古帝王治国理天下的历史记载(“迹”、“政”),诸子百家则是古帝王治理天下的理论(“术”、“意”),因此六艺和诸子二者互资为用。同时六艺与诸子百家之关系还有如下几个方面:因为百官辅助帝王治国理民,而六艺“皆古帝王经世之大法”,因此原于百官之百家学说皆“宗经”(见《宗经》);因为由太史所掌的古帝王的“君人南面之术”降为道家,因此百家在思想上皆“祖道”(见《祖道》);因为六艺为古帝王经世之书,由太史所掌,而太史之术衍为道家,因此在思想上“六艺与道家相出入也”(《史学》)。
在百家之中,道家因为是太史所掌之“君人南面之术”流衍而成,所以地位最为重要,具体而言:
是故道家者,君人南面之术,六艺之祖,百家之宗子,而我孔子所师承也。(《原道》)
道家所明者,君道也;百家皆出官守,所明者臣道也。君道者天道也,臣道者人道也。(《原道》)
盖六经皆先王经世之粲然者,而道家则六经之意也。(《原道》)
道家而外,墨家次之。“大抵百家中最大者,有二家,一曰道家,一曰墨家”,其原因在于“二家皆原于史,皆以言天立教者也”。至于道、墨两家的区别,则在于道家出于太史,太史主知天道,故道家以法天为宗旨;墨家出于史祝,史祝主事天鬼,故墨家以顺天为宗旨。(见《原墨》)
二、史统归于孔氏,定于一尊
诸子百家之间互相觗异攻讦,出现了互争“史统”的局面。出身于儒家的孔子,在这个百家争鸣、互争“史统”的时代,“以儒家思存前圣之业,观书于周,问道于老聃,追迹三代之礼”,删定六艺,所谓“因史记旧闻,加吾王心”,“自是六艺之文,咸归孔氏矣,七十子后学因相与尊之为经。”至汉武帝时“废黜百家,表彰六艺”,“自此以后孔子之史统定于一尊”(《原史》)。经过这样的历史过程,六经的性质有所改变:
由前而观,六艺皆王者之史,根据于道家;由后而观,六艺为孔氏之经,折中于儒家。(《原史》)
也就是说,六艺就由古帝王之史书,成为孔子为后王立法之经书。六艺的内涵或者解释,亦有了前后之不同。同时,作者认为蕴含在六艺中孔子思想实合儒道两家之统,非单纯的儒家思想:
是故孔子删订六艺也,所以备天人也;其备天人也,所以兼儒道两家之统。惟其兼道家之统,故高出乎儒家;惟其兼儒家之统,故又不纯乎道家。(《征孔》)
六艺未归孔子之前,君人南面之术,根据于道家。六艺既归孔子之后,君人南面之术,皆折中于孔子。夫孔子,儒家也,以司徒一官上代史统,则儒家而实兼道家矣。(《征孔》)
那么儒道两家宗旨又有何不同?简而言之,道家明天者也,儒家明人者也。道家先法天道,孔子则修人道以希天。儒家先尽人道,孔子则本天道以律人。“其于道也,未尝不明天而必推本于人,未尝不明人而必推原于天。”(见《征孔》)
但是孔子传授给弟子所谓“七十子后学”的只是其整体思想的一部分,即儒家思想,其具体经书是孝经和论语。“《孝经》、《论语》也,孔子以儒家嗣绪寄诸弟子之书也。”(《经翼》)
归纳起来,关于六艺与百家的关系大致有以下要点:1、六艺百家皆源于百官之史;2、六艺为君人南面之术,衍为道家;3、孔子为了给后王立法,以儒家而学于道家,于是六艺成为孔子的经书,孔子实兼有儒道两家思想;4、 孔子传授“七十子后学”者仅是其思想中之儒家部分。
三、六艺由史而经
通过以上叙述可知,六艺因为孔子删订的关系,于是有了“经”与“史”的区别。接下来作者提出,“经”与“史”的分别,导致“今文经”和“古文经”的区别。而“经”与“史”的根本区别,在于“政”与“教”的区别。
1.经、史之别
本来六艺只是古代的史书,但是六艺经过孔子的删订,就由记载古代帝王的事迹的史书,变成了孔子为后王立法的,体现孔子思想的经书。经与史的最基本区别在于:
史主于记事,经主于明义。(《明教》)
由于六艺本身存在经与史的区别,对六艺的解说也就出现注重于“事”和注重于“义”的不同,于是产生经学上“今文”和“古文”两大派别。
2.今文、古文之别
六艺由于经过孔子的删修而有了双重属性,即一方面是古代的历史记载,一方面是孔子思想的载体。但是,孔子在通过删订六艺阐发自己的思想的时候,并没有像多数今文经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变乱古代历史的记载,而是把自己的思想通过“口说”的形式传授给弟子们。这些“口说”后来用文字记载下来,就成了“今文经学”的各种解经之书,而那些根据古代史官的记载解释六艺之书,则成为“古文经学”的诸种作品。(见《口说》)他是这样论述的:
虽然六艺者其先皆史家之旧籍也,自归孔氏以司徒之官上祧柱下之统,先王之迹虽存而口说流传则大异矣。故六艺有两大派焉,一曰古文,一曰今文。古文者,旧史说经之言而孔子采之者也,今文者为孔子说经之言而弟子述之者也。纯乎明理者今文也,兼详纪事者古文也。(《原艺》)
夫六艺皆周公之旧籍也,而有经孔子别识心裁者,则今文诸说是也;有未经孔子别识心裁者,则古文诸说是也。今文为经,经主明理,故于微言大义为独详;古文为史,史主纪事,故于典章制度为最备。(《古经论》)
因此,今文和古文虽然不同,但相资为用,同为明道所必须,不能偏废。
3.政、教之别
六艺中史与经的区别,其根本在于蕴涵着政与教的不同。“夫典章法度所谓政也,孝亲敬长所谓教也”。
经与史之区分,政与教之所由判也。由前而言,六艺皆三代之政也,故谓之为史;由后而言,六艺皆孔子之教也,故谓之为经。(《明教》)
相比于“政”,“教”更有长久的意义,因为“周公之政,历代沿袭不同者也;孔子之教,天不变道亦不变者也。天下有敢于更张周公典章法度之人,必无敢于灭裂孔子名教之人。周公创制典章法度,以为一世致太平;孔子本周公之典章法度加以王心,以为万世立名教。”(《明教》)所谓“教”也就是孔子通过删订六艺,以为后王立法的“大义”。因此,儒者“通经”应该以大义为先,领会孔子删订六艺之大义,以裨世用,不应专务于名物训诂章句之间,而不能领会大义。(见《通经》)
如此,作者以如上三个命题统贯全书,为我们阐述了六艺和诸子百家同原于“史”、六艺由古帝王之史书转变为孔子之经书的过程。此为《史微》的大旨所在。此外书中各篇章,往往围绕一个主题博辩详说,牵涉到先秦两汉学术众多问题,有很多作者的一家之言。如《史学》论及古今史学之不同,《史官沿革考》详述汉代以前史官之沿革,《诸子文说》缕述两汉子学之余波,《原纬》、《原小学》分别论述小学、纬书与六经之关系,《易论》、《春秋论》、《礼论》推阐六经之微旨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此不详述。
三 《史微》在清末民初学术思想史上的意义
《史微》是张尔田的成名之作,也是其研究古代学术思想的代表作。当时学术界有人把此书与刘知几的《史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相提并论,⑧ 并且东传日本,京都大学列之为研究文史的必读之书。⑨ 据说夏曾佑看了此书,惊叹以为“载籍流传,支离纷杂,考订虽多,而综合为难。是书成,不啻收拾零玑断璧于荒残灭没之余,一一合之,复还其旧,我且师之矣。”⑩ 钱基博在《近代提要钩玄之作者》一文中分类介绍“博综群书,钩提玄要,有宗旨以自名家学,有条贯以启示途辙”的著作13部,其中“通论”类推介三家著述:章学诚《文史通义》、张尔田《史微》、章炳麟《国故论衡》。他认为“张尔田《史微》,绍述文史,匡谬拾遗,不为墨守。然章氏文史,以周官为门户,媲于古文;张氏此书,以《公羊春秋》为根极,所主今学;而张氏调停其说,颇多新义”。
在但同时似乎又有很多人对之不以为然,这点在张氏的自道中可见一斑。他曾把此书与唐代释神清《北山参玄语录》相提并论,认为“神清书逼于世趋,禅宗仇之,排佛者目笑之,其晦也千余年,时节因缘,今日复显。余之书亦不为竺古者所喜,而为灭圣者所诽,其晦固宜,而其显也正不知何日。抚卷增喟,实在兹乎。”(11) 可以看出此书又颇受冷落。其原因大概是两面皆不讨好,“不为竺古者所喜”,大概是因为此书“越世高谈,不守章句”,不合乾嘉考据学的家法。“为灭圣者所诽”,则显然是因为此书提倡六经之道在现世仍有指导意义并且宣扬孔子的神圣地位,而与当时积极引进西学并以西方思想批评中国传统的“新学”潮流背道而驰。
《史微》自1908年初刊,行世已近百年。但在现代学者的学术史著作中,却鲜见其踪影,可谓声名暗晦之极。据笔者所见,董朴垞《中国史学史长编目录》(12) 把张尔田的《史微》列为拟论述项目,可知作者已从史学史角度注意到《史微》的价值与地位。但是因为此文为“目录”,仅列出作者将要论述的相关人物与著作,对于《史微》的具体评述不得而详。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亦提及《史微》,但仅列举书名,简单地定性为是民初封建史学回潮推波助澜之作。(13)
笔者认为无论是在近现代学术思想史上,还是在近现代史学史上,对于张尔田及其《史微》一书的关注都是不够的。在此不揣浅陋,结合清末民初学术思想界的状况,对此书的撰著动机和主要观点略作评析。
一、调和经学今、古文之争
“今文”和“古文”本是两汉经学的不同派别,后来由于古文经学大行,今文经学几乎失传,因此唐宋元明历代学者并没有多少人注意二者的区别。一直到了清乾嘉时代的庄存与才开始阐发今文经学的学说,但正值考据学兴盛时期,一直没有大彰。(14) 晚清道咸以降,由于学术思想的演变和社会的变迁,今文经学得到很多学者的青睐,并通过龚自珍、魏源到廖平、康有为的阐扬,达到了鼎盛时期。今文经学的最大特点是注重义理层面的发挥,讲求所谓的“微言大义”,这与考据学有明显的区别。它的兴起一方面是对考据学忽视义理的纠正,一方面是力图架起学术与经世的桥梁。
但是今文经学的兴起也带来了思想界的混乱,使中国学术界对传统的解释出现分裂,其矛盾焦点就是对六经如何理解。二者争论的焦点是对六经的性质看法不同。古文学派认为六经是经过孔子整理的古代官方典籍,而今文学家则认为六经是孔子的创作,目的是为后王立法。按照古文经学的说法,孔子只是一个文献整理者和教师,六经只是古代的史料;按照今文经学的说法,孔子则是“受命”的素王,六经是孔子“垂教后王”的经书。(15) 二者可谓针锋相对,不可调和。尤其是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书,斥古文经为刘歆所伪造,认为六经中的古代事迹皆为孔子为“改制”而“托古”所造,如此一来,连古代历史也无从考信了。今文经学到了康有为可以说讲到了绝路。而同时的古文大师若章太炎,又以坚持古文壁垒为手段,以达其“经学拆散”之目的。(16) 到了这个地步,对于先秦典籍已经没有统一的意见了。而正在此时,张尔田另辟蹊径,借助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提出了一套可以弥合今古文的讲法。(17)
在《史微》中,张尔田首先认为“六经皆史”,坚持古代学术在于官府,六经在其起源上是古代的官方典籍,由政府中“史”这一官职记录和保存,其中体现了古代的历史和古代帝王治国理民的思想。这是对章学诚观点的继承并在结合《汉书艺文志》的基础上更加细密罢了。这是古文家们基本认可的。但是以上的说法显然统合不了今文学的观点。因此张尔田又进一步对“六经皆史说”进行修正,提出了“六艺”一方面是先王之史,一方面是孔氏之经。他认为章学诚的局限在于“祗知六艺乃三代之为史,而不知六艺之由史而为经”(《明教》)。
他为我们描述了这样的一个过程:东周时官失其守,学术流落到民间以后产生了诸子百家,本来“史本道家”、“六艺与道家相出入也”。但是经过孔子的删修,六艺就成为儒家的经,“六艺既归儒家,而经之名始立”。孔子在修订古代流传下来的官书时加入了自己的思想,因此六艺就由古代的史书变成了孔子的经书。“不知六艺为史,无以见王者创制之本原;不知六艺为经,无以窥孔氏删修之大法。”
“史”详于古代的典章制度,是所谓“政”;“经”包含孔子的微言大义,是所谓“教”。于是对于六经的解释就出现了今文和古文的区别,“古文”记载周公的典章制度,“今文”则传承孔子的教义。作者一方面坚持,经今古文学各有所本,“一为旧史说经之言,一为孔子说经之言,其异同盖不容乱矣”,一方面坚持两者可以互相为用,不必互相攻击,因为:
非考古文不足知孔子删削之原,非考今文不足知旧史损益之善,道故相须而成也。(原艺篇)
夫孔子大圣人也,周公亦大圣人也,周公之圣为一代致太平,孔子之圣为万世立名教,孔子之微言大义莫备于今文,周公之典章制度亦莫详于古文,古文明而后周公致太平之道明,周公致太平之道明,而后孔子损益旧史、垂教万世之义亦明。苟知此义,则古今文之哄可以不作矣。(《古经论》)
这样今文和古文各有功用,本没有必要互相攻击。但是两汉之时今文经和古文经互相争讼,古文经学兴盛,今文经学衰微,导致孔子垂世立教的心传晦暗不明,经学的经世作用也不得发挥。(见《争讼》)张尔田晚年自云“余向纂《史微》,颇救正今、古文家末流之失”(18),道出了此书的主要学术目的。
但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既然六艺中蕴含着“政”与“教”的区别,相比之下,阐明孔子的教义更为重要,因为“周公之政历代沿袭不同者也,孔子之教天不变道亦不变者也”。儒者“通经”的目的在于“明教”,而为了“明教”则不得不借助于今文经学。因此张尔田在《史微》中虽自称于今古文无所偏废,但无疑更重视今文,因为今文经学才是孔子的真传。所以钱基博认为张尔田、孙德谦“专意述学”,康有为、梁启超“好为政论”,但有共同的特点,即同样是“要归于扬西汉之微言,薄东京之古学”(19)。
二、提升“诸子”学术地位
先秦诸子百家是中国文化的璀璨成果,但是随着后世儒家定为一尊,出现了经的地位越来越高,子的地位越来越低的趋势。清代考据学的兴盛为诸子学的逐渐被关注创造了条件,因为虽然考据学主要的对象是经学,但是随着经书的考证渐趋完备,考据学者也随带着把考证的目标涉及到诸子百家,使一直处于暗晦状态的诸子逐渐被人注意起来。(20) 但是诸子学说的意旨究竟如何,考据的方法却无力回答。
《史微》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把六经和诸子百家联合起来考察,并在经与子的关系上具有新的看法。本书的基本命题之一是“百家道术,六艺之支与流裔也”,这是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提出的观点,并非创见。但是张尔田进一步的论述,则实发前人所未发。他提出经与子实是一种互补关系,应该相资为用,不可尊此卑彼。必须会通二者,才能真切理解传统经典的全部意义。如果六经真是“道”之所在,理解它就必须依据于诸子百家学说,因为六经只是“迹”,百家才是“术”和“意”。这样我们看到,原来一直在下降的诸子百家,现在被提高到了与六经一体而二地位,为后人充分理解这一部分传统扫除了部分障碍。
此外,他还提出“诸子原于六艺,而不缪与孔子”,“百家既同为六艺之支与流裔,则亦同为我孔子所不废”(21),以及孔子之道兼包儒道两家的崭新观点。这些都扩大了正统思想的范围,提高了诸子百家的学术地位。虽然按照现代的观点,先秦诸子并不需要六经和孔子来抬高身价,但是《史微》的这种观点,仍不失为在传统之内进行创新的努力。
三、宣扬孔子之教
《史微》另一个重要观点是尊崇孔子。大致来说,自汉武帝以来,历代对孔子的认识与评价虽略有不同,但基本上孔子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中一直处于崇高的地位。这种情况在晚清由于两种对孔子的新认识而出现重大的改变。对此唐君毅有简明的评说:
廖平、康有为对孔子之教之开未来世的意义,说得太夸大;并以六经皆孔子托古改制之著,而只表现孔子个人思想者。此却使孔子之学,反成‘前无所承’者。章太炎初年本佛学以贬责孔孟中庸易传,而轻视宋明儒学;只视孔子为传布整理古代文献之史家,则使孔子之学,若成‘后无所闻’者。章太炎与康有为之弟子之梁任公,在清末,更以孔子不过诸子之一,其地位或尚不如老子、墨子。(22)
可以说,以康有为和章太炎为代表的对孔子的新认识,虽然针锋相对,一欲“尊孔”一欲“订孔”(23),但同样对后世思想有重大影响,一开“疑古”之风,一开“整理国故”运动,并导致一共同的结果,即孔子地位的降低,以至于“以孔子不过诸子之一,其地位或尚不如老子、墨子”了。
张尔田《史微》问世之时,以上两种言论都已出现,并广为人知。而张尔田为我们描画的历史图景,既综合了以上两种看法,又与两者都有不同。首先,他利用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解决了康有为理论中孔子之学‘前无所承’的问题,同时又勾勒了“六艺由史而经”、孔子由儒家上承“史统”的过程,解决了章太炎看法中孔子之学‘后无所闻’的问题。这样孔子的道术前有所承,后有所闻,兼有儒道,包容诸子,为中国文化思想之大宗,其地位就确乎非诸子可比了。可以这样说,虽然同样主张“六经皆史”,但是章学诚提出此说目的在于提倡“即器明道”、“经世致用”的学风,张尔田进一步提出“六艺由史而经”,其结果则在于宣扬孔子之教。故钱基博说他“恢史统以绍孔统”(24),可谓得其微旨。
同时,虽同样宣扬孔子之教,张尔田和康有为又有不同。康有为心目中的孔教,偏重于“通三统”、“张三世”等社会政治方面的内容,孔子更像一个政治思想家,而张尔田则认为“孝亲敬长,所谓教也”,偏重于从伦理道德规范方面理解,孔子更像一个道德家和宗教家。(25) 历来对今文经学的认识, 多注重于康有为等“好为政论”的一派,而缺少对“专意述学”者的注意。对于民国初年“孔教运动”,也仅注意康有为的影响。固然“孔教运动”深受康有为的影响,但其中集合着很多与康有为思想差异很大的学者。对于“孔教运动”的透彻了解,还需要对其中不同思想流派的梳理和分析。
四、抨击考据学,提倡注重大义、经世致用的学风
清代学术最大的特色是“汉学”的兴盛。所谓“汉学”,是清代学者对自己所从事的学问的称谓。因为他们以尊崇东汉郑玄、许慎等人的治学方法相标榜,所以自号为“汉学”,又因为这种治学方法讲究“实事求是”、“言必有据”、不主张空发议论,所以又号称“朴学”。不论其号称“汉学”还是“朴学”,由于其主要工作是对中国传统经典的考证,所以后人一般又称之为考据学。
考据学的思想基础是顾炎武提出的“经学即理学”思想。(26) 这一思想通过戴震得到进一步理论提升:
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27)
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28)
这一治学路径的理论基础是相信通过“经学训诂”可以求得“道”。顺着这样的思路,考据学者们尽力于古代文献的整理和考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随着考据学的发展,“由训诂以求道”的学术路径逐渐显露出弊端。
首先是“义理”的缺场。虽然考据学的大师,如戴震等,很重视义理的阐发,但是一方面考据学的末流,循流而忘源,根本忘了义理这回事;另一方面,考据学方法的内在局限所致,人们发现清代的“小学”可谓发达,但是在义理上却鲜有发明。所以,认为考据学“琐碎饾饤”,无关大义的看法逐渐流行起来。其次是学术与经世的疏离。本来考据学的理论基础是通过考据的方法可以求得“圣人之道”,掌握了“道”则可以经世致用。但是由于“义理”的缺场,学术与经世之间的联系也切断。当晚清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极为险峻,应付现实危机的任务也极为迫切,考据学者考订古代文献的工作就尤其显得迂远无用了。这都表明了考据学已经走到末路,学术到了必须变换路向的时候了。晚清道咸以降今文经学的大兴以及汉宋调和思想的出现,最主要的就是对乾嘉考据学的反动。
张尔田由于家世的关系,少小喜读龚自珍文集(29),并“少闻乡先生谭复堂绪论”(30),成学后终生服膺章学诚学说,在这样的环境中,张尔田亦形成了注重大义、宣扬经世致用的学风。他在《史微》中多次抨击考据学,认为清代所谓“汉学”对六经的研究只局限于名物训诂,而对其中体现的古代先王先圣经世的大义毫不理会,正与经世致用的治学宗旨背道而驰。要通经致用,必须批判考据学家的治学方法,以恢复西汉经师的传统。他强调“凡学者大义为先,物名为后,大义举而物名从之”,但是清代的考据学正反其道而行之:
然鄙儒之博学也,务于物名,详于器械,考于训诂,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以获先王之心,此无异乎女史诵诗、内竖传令也。是则今之所谓汉学,正古之人明诏学者,悬为厉禁者耳。以古人厉禁,举世趋之而不知变,此六艺所以薄而寡要,劳而少功也。(《通经》)
针对汉学家们“实事求是”口号,他提出“实事求是”应该如此理解:
故河间献王有言‘实事求是’,是谓即所讲颂验诸行事之实,以求其至当不易之归耳。今汉学家所考皆古人陈迹,事既不实,又何从证其实哉。能言而不能行,谥为俗儒殆不诬矣。”(《通经》)
而且所谓“实事”与“空言”的区别在于是否能够实行,“凡不能起而行者,皆谓之空言无实”(《通经》)。他认为“六经之所包广矣,上佐人君而明教化,下昭来学而起多闻,内圣外王之道举于六艺焉。征之所谓通经致用者,此物此志也,岂徒资为华藻鞶帨之美观而已。”如果做到“著书必归之于实践,立躬必束之于中庸,勿以驰骤词章诬圣经,勿以破坏形体侮圣言,如是又何患经学之不昌明哉?经学昌明又何患不能致用哉?”(《通经》)
“通经致用”的号召固然陈腐,贬低考据、注重大义的学风却昭然可见,并为张尔田所终身坚持。他对胡适等人所提倡的“新考据学”的批判,亦与此有关,当另文详述。
五、余论
张灏曾说:“固然,晚清不像思想鼎盛的南宋或晚明时代,但忽视传统领域里的思想发展,也是错误的。仔细的考察表明,儒家学者在继续进行着这样充满活力的争论,如汉学和宋学,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乃至新儒家的程朱一派和陆王一派。因此,19世纪末的学者来说,儒家,更不用说整个中国文化传统,绝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一个巨大复杂、学派林立、彼此竞争的思想天地。”(31) 通过对《史微》的解读,我们也许会对此有更深入理解。
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中心是从西方引进新思想、新理论,使那些坚持中国传统的学者大都退居边缘,成为所谓的“失语群体”,(32) 张尔田可谓这“失语群体”中的一员。《史微》是张尔田总结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通论性著作,其中的思想,体现了近代一部分守护传统并坚持传统学术语言的知识人重建传统的一种努力。他构筑了一幅六艺“由史而为经”的历史图画,以弥合经学今、古文的争端,不失为在传统之内对先秦学术的一种颇具特色的解释。书中关于孔子思想兼有儒道两家的论述,显然深受晚清佛学以及西方宗教思想的影响,亦体现出扩大传统思想资源的努力。书中观点是否符合历史的真相,有待商榷,但其中表现的学术活力却值得肯定。虽然作者的“尊孔之见”以及“通经致用”的号召都已略显陈腐,但是其中对于先秦学术的某些具体论述,对我们理解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有启发意义。
注释:
① 桑兵:《民国学界的老辈》,《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
② 本文写作受封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编号:06SJB770003。
③ 关于张尔田的师友交游情况,张克兰:《张尔田学术·师友叙论》(《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12月,第6期)有较详细叙述,可参看。
④ 钱仲联:《张尔田评传》,《梦苕庵论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48页。
⑤ 齐思和:《〈遁堪文集〉书评》,《燕京学报》第35期,第267页。
⑥ 张尔田著、黄曙辉点校《史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
⑦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空轩诗话》,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85页。
⑧⑩ 钱仲联:《张尔田评传》,《梦苕庵论集》,第449、450页。
⑨ 王钟翰:《读张孟劬先生史微记》,《燕京大学图书馆报》第128期;邓之诚:《张君孟劬别传》,《燕京学报》第30期。
(11) 《史微》扉页,《民国丛书》影印本。
(12) 董朴垞:《中国史学史长编目录》,《史学史资料》,1980年第1期,第48页。
(13) 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56页。
(14) 周予同:《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9页。关于今文经学在晚清的发展历程,请参阅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9页。
(15) 参见周予同:《经今古文学》,《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9页。
(16) 姜义华:《章太炎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152页。
(17) 《史微》与章学诚《文史通义》在思想上有密切关系,此处不能详述,笔者将另文论之。
(18) 张尔田著,王钟翰录《张孟劬先生遁堪书题》,《史学年报》1938年第2卷第5期,第394页。
(19) 钱基博:《〈茹经堂外集〉叙》,《钱基博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12页。
(20) 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总序,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
(21) 此论首发自孙德谦,而为张尔田采用,见《史微·宗经》。
(22) 唐君毅:《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地位之形成》,杜维运编《中国史学论文选集》第2辑,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3年版,第62—63页。
(23) 章太炎有《订孔》篇,收入《訄书》重订本及《检论》中,载《章太炎全集》(3),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4) 钱基博:《〈茹经堂外集〉叙》,《钱基博学术论著选》,第612页。
(25) 张尔田对孔子思想的阐释,颇受佛学以及西方宗教的启发。例如他认为孔子学备天人,思想兼有儒道两家;孔子“端门受命”,为万世垂教,类似于“异邦之宗教家”;纬书是孔子的“内学”等等,已经显露出“孔教”的端倪。这也就无怪乎当康有为弟子陈焕章在上海成立孔教会时,张尔田会成为其中积极的一员。
(26) 钱穆:《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商务印书馆1997年新1版,第148页。
(27) 戴震:《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戴震文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8页。
(28) 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戴震文集》,第9卷,第140页。
(29) 龚自珍家与张尔田家为“世姻”,见钱穆:《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商务印书馆1997年新1版,第613页。
(30) 谭献,字复堂,晚清著名学者,亦服膺章实斋“六经皆史说”,喜谈今文经学。参阅谭献:《复堂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31)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
(32) 罗志田:《新旧之间:近代中国的多个世界及“失语”群体》,《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标签:国学论文; 孔子论文; 明教论文; 周公论文; 汉书·艺文志论文; 原道论文; 百家论文; 今文经学论文; 儒家思想论文; 古文论文; 六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