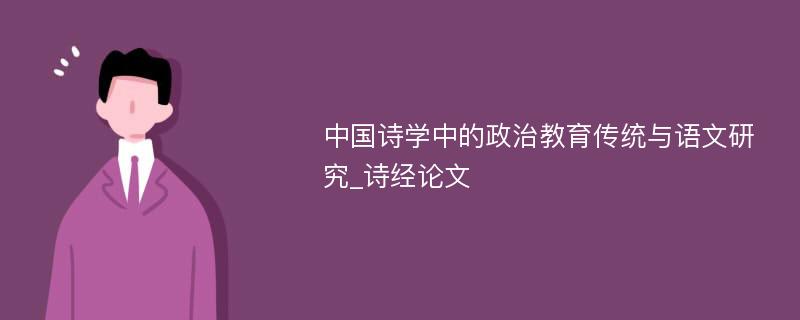
中国诗学的政教传统与国学治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政教论文,国学论文,中国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3)07-0234-10
政教中心——中国诗歌的一个主要传统
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中,有导源于汉代的几个重要论点,影响着两千多年的诗歌评论,也指导着两千多年的诗歌创作,这就是所谓“风雅”、“比兴”、“美刺”、“讽谕”。这几个论点,分析起来,既有所区别,又互相联系。大体上说:“风雅”是创作的准则,“比兴”是创作的方法,“美刺”是创作的态度,“讽谕”是创作的目的。而这几个论点,又围绕着一个中心——政教,即政治和教育。换句话说,就是诗歌要为政教服务。以政教为中心的原则,假如说还不能概括两千多年中国诗歌的全部传统的话,那至少代表着总传统中的一个主要传统。那么,这一主要传统是怎样形成的?该怎样评价?这就是本文想要探讨的问题。
以政教为中心的诗论的形成,既源于《诗经》一书的经典化,同时也是以儒家的政治哲学成为统治思想为基础的。本来《诗经》中的诗歌之所以和政治发生极为密切的联系的原因,是由春秋时期各国之间朝聘会享中,使用诗歌作为外交辞令这一事实而来。孔子论诗,一则说:“不学诗,无以言。”①所谓“言”,即指外交语言,而非日常生活语言;再则说:“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②“诵诗”就是为了出使时的“专对”(独立应对),而不是为了其他。孟轲、荀况和《礼记》以下各家引诗,都承袭着外交场合“赋诗断章”③的办法,而不管是否违反原诗的本义,这就逐渐产生了借用原诗的某点意义,使它成为自己言论的依据或佐证的现象,从而提高了《诗经》诗歌的权威性,使《诗经》一书越来越上升到经典的地位。
在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中,儒家作为一个政治集团,虽未取得太大成就,但以他们的学徒之众、影响之大,在文教事业上却占有绝对优势。他们以政治为目的,以文教为手段,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曾经设计过各种统一全国的政治方案:除孟、荀二大师,各有以“仁义”、“礼”为中心的专著外,其他像《孝经》的“以孝治天下”,《大学》的“格、致、诚、正、修、齐、治、平”,都是自成体系的一种政教学说。这些政教学说当时虽无法实践,但对后来封建王朝的统治影响很大。尽管法家曾以富国强兵为根基,用武力统一了全国,取得了空前胜利,建立了秦王朝,但秦王朝的建立标志着法家的最大胜利,也标志着法家的最大失败。法家的失败,关键在于它重政轻教。汉初“改秦之败”,曾有以道家(黄老)来统一思想的企图,④但没有成功。儒家继之,政教并重,在武帝刘彻的支持下,以“六经”、“仁义”为中心,而吸收道、法以次各家的优点,“舍短取长”,形成“于道最为高”⑤的统治思想。而《诗经》一书,也成了统一的封建王朝统治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有关《诗经》的注释、说明、评论和依附《诗经》而提出的诗歌论点,都不能不为这一现实所左右。这便是以政教为中心的诗论的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
在汉王朝封建统治思想指导下,再看汉儒就《诗经》一书所提出的几个论点:
其一,“风雅”。“风雅”本是“风雅颂”三部分诗的简称。“风”是十五个地区的地方乐调,“雅”是周朝首都镐京一带的乐调,“颂”是伴随着舞蹈的乐调。这些名称和诗歌理论本不相干,但到了汉儒手中,却赋予了重大的理论意义。《毛诗序》把“风”解为“风也,教也”,即讽刺和教化,“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雅”是“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是正面谈政治问题的;“颂”不解为舞容,而解为“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⑥,成了后世“歌功颂德”的先导。从此,“风雅”不但可以从意义上代表《诗经》,同时凭借《诗经》作为经典的权威,而成为诗歌创作的典范。
其二,“比兴”。“比兴”是“赋比兴”的简称,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大师》。那里把“风、赋、比、兴、雅、颂”平列,称为“六诗”,但没有作意义的解释。到了《毛诗序》,仍把“赋比兴”和“风雅颂”并列,而呼为“六义”,对“风雅颂”作了解释,如上所举;但对“赋比兴”却仍没有作任何说明。只有在一些经师的遗说中,才多少看出一点“赋比兴”的性质。比如:《周南·芣苢》,《韩诗·薛君章句》指为“兴”,《毛诗》则指为“赋”;《鸡鸣》,《韩诗》指为“比”,《毛诗》仍指为“赋”;《伐檀》,《韩诗》指为“赋”,《毛诗》则指为“兴”⑦。不管他们之间的说法如何矛盾,但把“赋比兴”看为写作方法,却是一致的,所以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谓:“‘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⑧概念虽还不够明确,但把“赋比兴”和“风雅颂”从性质上区分开来却是很清楚的。“赋比兴”属于写作方法,和政治本来挂不上钩,可是汉儒郑玄却说什么:“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故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⑥这样,就把写作方法和政教拉在一起了。尽管刘勰等理论家,从写作方面大大发展了“比兴”理论,可是一直到白居易,还要说:“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⑨用政治意义淹没了写作方法的意义。
其三,“美刺”。“美刺”最早见于诗人的自白,像《魏风·葛屦》末两句:“维是褊心,是以为刺”,就提出了“刺”字;而《小雅》中的《崧高》、《烝民》、《节南山》等篇,都明确提到“作诵”,“诵”即“颂”,实际就是“美”。说得具体的还是《毛诗序》,《毛诗大序》除把“风”解为“风刺”,把“颂”解为“美盛德”外,在不少单篇诗的《小序》中,还随时指出某诗“美”某,某诗“刺”某,像《甘棠》“美召伯也”,《江有汜》“美媵也”;《雄雉》“刺宣公也”,《谷风》“刺夫妇失道也”之类。“美刺”观点,是贯串在《毛诗序》(包括大小序)中的重要论点之一。到了郑玄,把“美刺”的意义更提高了一步,说:“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郑玄的说法不只是总结已然,而且要影响未然。这种歌颂什么(美)暴露什么(刺)的问题,是写作态度,也是政治态度。
其四,“讽谕”。“讽”是暗讥,“谕”是晓喻。义源于“风”,而与“谲谏”一致。“谲谏”的目的是:“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11),“讽谕”则是《春秋》赋诗“以微言相感”,“称诗以喻其志”(12)的发展。班固认为诗赋的任务之一,是“抒下情而通风谕”(13),郑玄认为“诗者,弦歌讽谕之声也”(14),是由于“尊君卑臣,君道刚强,臣道柔顺,于是箴谏者稀,情志不通”,所以才需要“作诗以诵其美而讥其失”。所以“讽谕”和“美刺”相交通,和“风雅”“比兴”相联系,而成为容量较大、概括诸论点的新论点。这就是唐代白居易的诗歌理论中强调“六义”,而称他的政治性最强的150首诗为“讽谕诗”(15)的原因。
综上所述,可知汉人诗论,都是就《诗经》一书立论,而实质上则是在作为统治思想的新儒家思想支配下,适应当时政治教育要求而建立的诗歌理论。无以名之,姑名之为“政教中心”。
《毛诗序》直接谈诗歌和政治的关系时说: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由于“诗三百”都是可以“弦而歌之”(16)的,所以诗歌音乐结为一体。这里要说明的就是,从歌乐中可以判断政治好坏。换句话说,就是歌乐是政治的反映,也是能反映政治的。所以“王道衰,礼义废,国异政,家殊俗”,便产生了“变风”、“变雅”。惟其如此,所以:
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17)
诗歌在政治教育上的效果,竟如此巨大!但这还没有超过孔子的看法。孔子曾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18)诗的作用,包括了政治、社会和博物。汉儒所论,反而有被政教局限的倾向,这也可以看出汉儒是如何强调政教而不及其他。
问题是这种就《诗经》一书提出的以政教为中心的论点,是否可以算是诗歌理论?用这一论点作指导,是否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起了积极作用?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因为汉儒在封建统治思想支配下,戴着有色眼镜来看《诗经》,就不能不有所蒙蔽,因而在《诗经》中诗篇的具体解说上,就出现了大量的牵强附会;但另一面,他们既熟读“三百篇”,终身寝馈于其中,那也就不能不有所发现;因而在对不合自己尺度的诗予以曲解的同时,对合于自己尺度的诗也会正确地撮其要而会其义。所以他们对“风雅颂”用政教来概括,虽属穿凿,但“风雅”诗中有不少政治诗却是事实;对“比兴”的解释,虽有所附益,但“赋比兴”的方法,在“三百篇”中却普遍使用;“美刺”的具体对象,虽说得十分荒谬,但“三百篇”中表现“美刺”的诗也大量存在;而以“讽谕”为目的或能起“讽谕”作用的诗,更不可胜数。因此,我们如果为了理解原诗,则对汉儒所加于《诗经》的迷雾和所造成的混乱,必须彻底排除;但他们借《诗经》而建立的一些新的诗歌论点,却很有可取之处。而这些论点,在后来的诗歌发展上,正是突出地起着推动作用的。所以尽管汉儒错误地把内容十分丰富的《诗经》这一部诗歌总集,强行纳入政教范围之内,把部分具有政治内容的诗,以偏概全地代替了全部诗作,而且在总论诗歌和政教的关系中,片面地夸大了政教作用,但他们所建的诗论,还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诗歌创作的一些现实状况。
作为文学的一部分的诗歌属于意识形态,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但现实的反映并不就是现实主义,只有自觉、积极地反映现实,才是现实主义的开始。迄今几千年的中国,政治在社会中无所不在,是最大的现实,也可以说政治是现实的最主要方面,而为政治(包括教育)服务的诗歌,是关心现实、干预现实、积极地反映现实的重要表现。因之毫无疑义,政教中心诗论与现实主义的要求是相通的。然而,现实主义的理论,不但要求作家的作品自觉、积极地反映现实,而且还要求全面地、真实地反映现实;不是肤浅地反映现实的表面现象,而是通过典型形象来反映现实的本质特征;哪怕是朴素的现实主义呢,也要通过现象而接触到某些——即使很少——现实的本质。以此为准,再看以政教为中心的诗论,是否能达到这一高度?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它的理论体系还很粗浅。但从创作实践上看,则从《诗经》、“汉乐府”,以至陈子昂、杜甫、白居易的诗集中,却存在着大量的可以称为现实主义的作品。理论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西方现实主义的理论不也是到了19世纪才完善起来的吗?所以,汉以后,政教中心思想影响下的作家们,他们所举的旗帜,总不出“风雅”、“比兴”、“美刺”、“讽谕”的范围。因之,把这些论点作为现实主义的先行或现实主义的基本因素来看是可以的,虽然它还不够完善。这就是政教中心论之所以能代表中国诗史上主要传统的原因。
政教中心既然是中国诗歌史上一个主要传统,那也就是说它没有、也不能代表全部传统。它虽然要求关心现实、干预现实、反映现实,但却局限于现实中的政教方面,而和政教无关的种种现实问题,就不一定涉及了。这和孔子所说“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多识”相比,广度上已有所不及,和面向一切现实的现实主义理论相比,更有范围广狭的区别。就反映现实来说,反映政教的作品,固然是反映现实,而反映非政教的作品,却不一定不反映现实。《诗经》、“汉乐府”中大量的具有现实主义特色的诗篇,并不一定都反映政教;杜甫、白居易之所以成为伟大诗人,也不单由于他们所写直接反映政教的那部分诗,而是由于他们创作的全部。所以,政教中心的诗论,只代表中国诗歌史上的传统之一,尽管它是主要的。政教中心论本身还存在着一个缺陷:因为它可以为革命的、进步的政治服务,也可以为反动的、落后的政治服务。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可以正确地、真实地反映现实,也可以虚伪地、欺骗地歪曲现实。我们不是亲眼看见几个把“政治第一”、“政治挂帅”口号喊得山响的野心家,拿文艺当作罪恶活动的武器,对人民进行了空前的迫害吗?而历史上的此类事例,也大量存在。“汉乐府”中有一首《上留田行》,开头三句说:
居世一何不同。富人食稻与粱,贫子食糟与糠。
一下子就接触到社会现实的本质——阶级对立,但下文一转却说:
贫贱亦何伤。禄命悬在苍天,今尔叹息欲将谁怨!
很巧妙地用天命把真实掩盖了起来,这是被统治者篡改了的民歌,(19)把为被压迫者呼喊的歌子,篡改成为统治者辩护的歌子了!但都是为政治服务。好在政教中心论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诗史的主要传统,则在于历史上的一些进步集团和进步分子,运用这一合法的、以“圣经”为掩护的口号,通过“风雅”、“比兴”、“美刺”、“讽谕”等具体论点,用大量创作,为人民利益、为政教改革,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从而取得丰硕成果。与此相反,那些直接为反动统治者效劳的东西,却自然地为历史所淘汰。
与政教中心论并行,中国诗歌发展史上还有两个具有理论性质的诗论,和政教中心论互相关联,互相渗透,但却各有侧重,形成传统。一是言志抒情说,一是好辞尚丽说。“言志”说起自先秦,而《毛诗序》本之,提出“诗者,志之所之也”,接着便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可见情、志是一回事。《毛诗序》虽从诗歌起源上谈到了情、志,而篇中却以政教为中心。只是言志抒情(包括性、意)说以此为起点,便发展为另一传统而已。司马迁称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20),提出了发愤著书说。此后像阮籍的“咏怀”,陶渊明的“真意”,韩愈的“不平则鸣”,白居易的“感伤”、“闲适”诗,都是这一传统的继续和发展。好辞尚丽说,从司马迁称宋玉等人“好辞”(21)起,刘歆也说宋玉等人“竞为侈丽宏衍之辞”(22),从扬雄所谓“丽以则”,“丽以淫”(23),到曹丕所谓“诗赋欲丽”(24),到刘勰、锺嵘,虽情辞并重,而所代表的南朝诗歌发展趋势,一直向好辞尚丽前进。上举两点,都是政教中心论所不能代替的。
书注与读书之法
古书之难读,由于古语古事之不明;古语古事之不明,由于训诂考据之不备;训诂考据之不备,是书注之未臻完善也。是以欲明先哲之精神,则必先读先哲之书;欲先哲之书读之溥,则必先使其书昭然著明,怡然理顺,而注疏整理为首要矣。
然此大业,未能猝成,于注疏未经整理之前,而欲学者之不废简册,则于此困难之中,犹当有其读之之法,庶不至因难而退,荡灭旧贯,使民族之精神,竟坠于地也。今更申整理古注与读古书之法于次。
自昔注书者,或曰传,或曰笺,或曰解,或曰诂,或曰训,或曰说,或曰记,或曰微,或曰述,或曰学,或曰章句,或曰解诂,或曰说义,或曰注疏,或曰通释,或曰义疏,或曰正义,皆其流也。语其阙也,则汉氏之传注,尚未明经之什伍;(25)语其芜也,则释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26)阙则晦而不明,芜则劳而少功,此其所以未善也。予尝论经传以下书注之失约分三端:
一曰:但明典故,而不详本义也。如郭璞之释《尔雅》也。于“哉”、“俶”、“落”、“权舆”,“始也”之下,则云《尚书》曰:“三月哉生魄”,《诗》曰:“令终有俶”,又曰:“访予落止”,又曰:“胡不承权舆”;于“林”、“烝”,“君也”之下,则云《诗》曰:“有壬有林”,又曰:“文王烝哉”。此皆但言其出处,而“哉”、“俶”、“落”、“权舆”之何以训“始”,终未明也。“林”、“烝”之何以训“君”,亦未明也。又如李善之注《文选》也,于卷三十八傅季友《为宋公至洛阳谒五陵表》“伊洛榛芜,津涂久废”下注云,“《蜀志》许靖《与曹公书》曰:‘袁术方命圮族,津涂久塞’。”于“伐木通径,淹引时月”下注云:“《东观汉纪》曰:‘岑彭伐树木开道,直出黎丘’。”此皆广采群书,而于“榛芜”、“津涂”、“淹引”之旨,固未明也。
二曰:但录事实,而不求诂训也。如《文选》卷二十五于刘越石《答卢谌书》“国破家亡,亲友凋残”下注云,崔鸿《前赵录》曰:“刘聪谮即位于平阳”,又曰:“聪遣从弟曜,攻晋破洛阳”,又曰:“遣子粲攻长安陷之”,而于“凋残”之义则不言也。又如裴松之注《三国志》,则备采异文,详录佚事,文语之释,初不涉及(文繁不俱引)。
三曰:但诠大旨,而不问字诂也。如王逸注《楚辞》屈平《卜居》“屈原既放三年”下云:“违去郢都,处山林也。”“不得复见”下云:“建造策谋,披胸心也。”“蔽障于谗”下云:“遇谄佞也。”“心烦意乱”下云:“意愤闷也。”“不知所从”下云:“迷瞀眩也。”而于各句之文字,竟不释矣。
以上三失,皆非作注者之学识不博,用力不勤,乃因其注意点之不同,故遂失解书之本旨。至于训诂之未精,考据之未确,与夫“望文生义”、“增字解经”之类,此属于作注者本身之功夫与其本书之优劣,此不俱论也。
上既言古昔书注之失如彼矣,则读之者,自不易了。而整理之方,不可不求也。盖注书者,欲其意不明者,固注而遂明也;事不知者,固注而遂知也,故必训诂考据,二者并备而后可。兹拟作注之要点如次:
一曰字音:凡本读、异读、叶音之属属之。
二曰字义:凡本义、引申、借义、通用之属属之。
三曰名物:凡草木鸟兽、典章制度,异名同实、同名异实之属属之。
四曰故实:凡史实、掌故之出处、始末之属属之。
一二为训诂之事,三四为考据之事,若以此为例,就各书之所涉及者,依次而释,则整齐划一,条理井然矣。清季朴学者流,学博力勤,于此二事,皆优为之;然其弊也,又多失之繁芜,故以王伯申、郝兰皋之博精,其所为书,犹多冗辞。此则剪裁之功,亦注书之要事也。如:《释诂》“哉”训“始”,郝氏疏之云:“哉者,才之假音。《说文》云:‘才,草木之初也。’经典通作‘哉’。《尚书大传》卷一云:‘仪伯之乐舞鼚哉。’《诗》(《大雅·文王》)云:‘陈锡哉周。’郑俱以‘哉’为‘始’也。郭注下文‘茂勉’,引《大传》‘茂哉,茂哉’,《释文》或作‘茂才’。《书》(《尧典》,古文作‘舜典’)云:‘往哉汝谐’,《张平子碑》作‘往才汝谐’。(《康诰》)‘哉生魄’,《晋书·夏侯湛传》作‘才生魄’。是才、哉,古通。”案此一段,除明“哉昔为才”外,但举一有力之证即可,不烦多引。而正续《经解》诸儒之著述,繁冗尤甚,所以不免“支离破碎”之诮也。(27)此言为注者,但当求其义之昭晰而已。
上既明各书注之短矣,而其长亦可得而论。故读之之法,必先明其短长。盖各书之注,以其注意点之不同,故必偏废。然亦其偏废之故,而有偏长。约而言之可分四类:
一曰详训诂:(包括考据而言)汉儒之书是也。
二曰明大义:宋儒之书是也。
三曰备掌故:《文选》李注之类是也。
四曰重文法:世俗之文注是也。
因此四长,衡以所需而用之,自异于盲目求之者矣。盖世之读书者,其目的所在,亦不外四端:
一曰欲求深造也,二曰欲求应用也,三曰欲求多闻也,四曰欲学文章也。
如欲求深造,则当先求训诂之通。欲求训诂之通,则当精研于文字形声义之学,而后可以据之以明大义,而后可以因之以获新义,而后可以明前人之所未明,通前人之所未通,而后一经群经,至于诸子百家,无不淹贯,要必以一名一字之彻底始。
如欲求应用,则当首以大义为重。虽训诂之事,仍不可废。然于古注之中,但择其善者为依据,固不必一言一物,事事研讨之也。故一篇之内,要义不过数点,一卷之中,精华亦自有限,取其助我而已,何必尽详。
如欲求多闻,欲学文辞,则习掌故以储其材,别文法以利其器可矣。然此于读书之事亦末矣。且为文者,首须“言之有物”,次须“言之有序”,亦即所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而有物,有序,有故,成理者,必先预之以学。故留意于掌故文法者,仅可为初学言之而已。
要之,整理书注,为发扬固有文化中刻不容缓之事,唯与民国以来整理国故者之所为有别。盖整理书注,欲其“简”、“当”,而整理国故者,犹绎其余绪也。(28)至于书注既善,学者易攻,其效之大,可不待言矣。今学者苦无善注,但能先定本身读书之目的,而后因其所需,以定进行之途径,庶亦不至徒劳少功也。
此文特就平居读书所感之困难,加以思索整理而成,所引之书,取当发凡,不赅不备,自所难免。识者倘就其意而教之,则幸甚!
论治诸子
诸子初兴之时,各尊所学,各行所知。其所言论,皆与当时社会相切合,虽各家注意之点不同,而其人俱存,则与世无隔阂之忧。即其人云亡,而其党徒或皆亲见闻而知之,虽有改易,其大体不至隐没也。及旷日既久,传授都绝,“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此指语言文字之流变言),而后人所处之时势,又与古迥不相侔,于是诸子之言,“暗而不明”。后之人,或理其训诂,或征其事迹,虽用力之勤,而其能否得诸子之真,未可知也。韩非有言:“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相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韩非子·显学篇》)况居二千余年之后,而尚论二千余年之前者哉!然学术之进展,在于因故而创新;学者之任务,欲其穷源以竟委。惟其得真之难,而治之之术,乃不可以不究。爰以所见,略陈于次。
论前人治诸子之得失
1.两汉以来
秦火而后,诸子销声。向歆父子之《七略》,乃有整理诸子之专篇。然其言仅曰:某家者流,出于某官,其长何在,其弊如何而已。(《汉书·艺文志》即袭《七略》者)其渊源当否,今所不论。即其所论“长”、“弊”,亦仅视某一流派之趋势,于各家固未能一一深究也(刘向《别录》间有存者,亦仍止概括各书之大意而已)。
魏晋人偏好《老》、《庄》,平叔、辅嗣与阮、嵇诸人,偶有妙论。然每与《老》、《庄》本旨不合,以其思索多而用功少也。郭子玄唯以自然解《庄》,亦殊蔽于时习,虽成一家言,亦不免“六经注我”之嫌。故其成就,未为多也。自兹以下,迄于宋、明,研习诸子者,诚亦有之,殊少创获可言。
清儒于经典而外,旁及诸子,校勘辑佚,以至注疏,一时称盛。其著述之大者,如《孟子正义》(焦循,原属经部,今以入子部)、《庄子集释》(郭庆藩)、《荀子集解》(王先谦)、《墨子间诂》(孙诒让)之属,所长乃在名物训诂、考据之事。寻其义理,每不贯澈。其见于《读书杂志》(王念孙)、《诸子平议》(俞樾),所谓“豁然冰释”、“怡然理顺”者,亦特在章句之间,不及一书之通旨,一人之学说也。故即搜绍绝学而言,清人之功,为不可没。然其成就,亦适至是而止。
2.现代各家
胡适之曾言:“至章太炎,始于校勘、训诂之外,别成一有系统之诸子学。《原名》、《明见》、《齐物论释》,皆为空前著作。其所以如此精至者,以其精于佛学,先有佛家之因明学、心理学、纯粹哲学,为比较印证之资,故能融会贯通,于墨、庄、惠、荀学说中,得一系统”云云(《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此言太炎先生之成就,在其于诸子之能作系统之研究,而其所以能得系统,则在以佛学、心理、哲学比较印证。胡氏所评当否,今所不论,唯胡氏之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实即欲采用此法,而以西洋哲学为比较印证之资也。
近人治诸子,皆喜比附西洋哲学,观其书中,充满“宇宙论”、“本体论”、“方法论”等名词可知,而胡适之、冯芝生实为其冠(胡、冯二氏尚不拘泥其名词)。不知于中国各家学说无深刻之研究,则比附大未易言也(以下就哲学史立论,以哲学史中诸子为主要部分故也)。
蔡孑民之序胡氏《中国哲学史大纲》也,极推重其“倚傍西洋哲学”,“以构成适当形式”之为难能。冯芝生于其《中国哲学史》之《绪论》中,首即谓“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是胡、冯二家皆以西洋哲学为骨干以研究中国哲学,而周秦诸子部分,彼等亦即以此法治之也。
然所谓“倚傍西洋哲学而构成适当形式”者,以中国本无此形式,而不得不倚傍西洋以构成此形式也;夫以本无此形式之诸子,而加以外来固定之形式,其吻合与否,与吻合之程度如何,与是否有削足适履之弊,至足虑也。且其可以此形式括之者,为全部?抑一部?为主体?抑枝节?其不能以此括之者,皆为无价值?抑尚有价值?此皆首宜注意之问题也。
又所谓“就中国历史上各种问题中,将其可以西洋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录之”者,是先承认中国学问仅一部分可以西洋哲学名之也。此言极有分寸,而吾人更宜注意者,则在除此一部分外,是否尚有高深精要,最可宝贵之学问在也。
就中西哲学之实质而言,其不同至为显著。其同者非枝节,则其表面也。西洋哲学中之宇宙论、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之属,诚皆可以由中国诸家学说中抽出之;然此所抽出者,显非诸家精神之所在。盖彼主于求“知”,此主于求“用”,基本态度即不同也。如老、庄、孟、荀之言宇宙(即言天、言自然等),非以求知宇宙之底蕴,乃在于说明“人……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天地与我并生”(《庄子·齐物论》)、“存心养性以事天”(《孟子·尽心》)、“天有其时,地有其材,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荀子·天论》)之人生行为而已。以其目的之不同,故其论宇宙之处,皆就直观所得之自然现象而为言。若以此类材料为某家之宇宙论,则其不如西人之博大精深,固其所也(西人宇宙问题之复杂,及派别之多,皆远非中国所可及)。至于本体、价值、知识、方法等问题,则中国亦从无此等纯粹之学说。中国之所重,唯在所谓“内圣外王”之道,亦即“修己治人”之道也。虽间有偏重,而大较则不出此范围。道家然,儒家亦然,其他各家亦无不然。而西人与此等问题,则远不如中国之博大精深也。故胡、冯二君之方法,即使于其所画范围内,可以自圆其说,然绝不能以此而得诸家学说之精神,亦不能视为治诸子之方法也。至二君之著作之成就如何,则亦非此文之所能论矣。准上所言,是古今各家于治诸子之学,虽所得深浅不同,然其治之之法,实未臻完备也。
论治诸子应有之基本功夫
1.入与出
荀卿有云:“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荀子·天论》)又云:“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夫唯其有见,故有卓特独得之知;唯其有蔽,故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而不能相通也。
今欲见诸子之所见,则必登其堂、入其室而后可。汉学尊师承而重家法,其蔽良深,然欲知汉学之底蕴者,则非求助于师承家法不可。诸子虽无明显之师承家法,然一家之学,不容以别家之观点观之,亦不容以别家之思想乱之也。尽捐成见,“不以所已臧、害所将受”(《荀子·解蔽》)。寝馈游息其中,然后可以“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庄子·齐物论》)。吾人每初读一书,即辄以好恶私意是非上下之,则于昔人卓特独得之知何由得见,终亦一无所得而已。
至欲去诸子之所蔽,则又必出其藩篱,尽脱羁绊而后可。儒墨之是非,儒墨不能自定也,而必兼知儒墨,不囿一方者始能定之。各家之是非,各家不能自定也,亦必兼知各家,不囿一隅者始能定之。若“学一先生之言,则暖暖姝姝,而私自说”(《庄子·徐无鬼》),终必“见笑于大方之家”而已。故“大知观于远近”(《庄子·秋水》),而后能知“道通为一”,而后各家之得失,乃有可言。故凡世人之固陋者,皆能入,而不能出者也。
2.异与同
庄生有言:“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庄子·德充符》)此为治一切学术之常法。盖天下无绝对相同之二物,亦无绝对不同之二物也。故自其异点观之,无物不异;自其同点观之,亦无物不同。惠施所谓“万物毕同毕异”是也(《庄子·天下篇》)。故极异之中,有其同;极同之中,有其异。求其异,所以得其特点;求其同,所以观其会通。能异则精深,能通则博大。
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之不同,前已言之。而宋明理学,复与周秦诸子不同。儒、道、名、法,又各不同。孔、孟、荀不同,老、庄不同,商、申、韩不同,惠施、公孙龙不同。同一“道”也,老、庄、孔、孟、荀、墨皆不同;同一“仁”也,儒、道、墨各家亦皆不同。即就诸子中任提一问题,无二家绝对相同者。孔子之言修己也,以“忠”、“恕”为本,盖以己为度而以行为实践者也。《大学》之言修己也,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本,是先以知识心理之修养为基,而后见于行为也。孟子之言修己也,以“存心养性”为本,而后及于“居仁由义”也。老子之无为也,乃“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老子·六十四章》)。庄子之无为也,乃“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庄子·应帝王》)。韩非之无为也,乃以法为准,而不用私智也。此其相异之处,正其特点所在,亦即其学说所以能独立者也。能求其异,斯得之矣。
孟子言性,荀子亦言性,其注意之问题同。孟子称“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称“涂之人可以为禹”,其结论同。孔子之“信而好古”,老子之“执古之道”,其法古同。孔子云:“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论语·阳货》),老子云:“礼者,‘忠信之薄”(《老子·三十八章》),其务本同。孔子赞大舜之“无为”,尧之“民无能名”,老子、庄子并称“无为”,其理想同。孔、孟崇仁义,墨子亦崇仁义;儒家尚贤,墨家亦尚贤,其用以治世之术同。墨子尚功利,宋銒亦尚功利,荀子亦尚功利,韩非亦尚功利,其所尚同。荀子重礼,韩非重法,其实质同。周秦诸子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荀子·非十二子》),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亦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其皆占学术史上之重要地位同。中国诸子以下,为文史诸学外独一学术,其议论各有其理则,其思想各有其系统。西洋哲学亦然,其学术之性质同。哲学所以领导人生,科学所以扩大人生,其为人生同。凡此不可殚举。此其相同之处,正其学与他学息息相关之处,而其学之价值与应用,亦于此始能表见也。能求其同,斯得之矣。
荀卿论制名之要曰:“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而后止……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而后止。”(《荀子·正名》)名固如是,实亦宜然。此即异同之术,亦即今世所谓“分析”与“综合”之术也。
3.参验与默契
韩非云:“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韩非子·显学》)孟子云:“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盖昔人之情,与今人之情,有其同;而昔人之时势,与今人之时势,有其异。有其同,斯有可通之理;有其异,斯有隔蔽之忧。唯其异,故必取于参验;唯其同,故可会以默契也。
孟子攻杨墨为“无父”、“无君”,征之杨墨之书不然也。荀子谓“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征之庄书不然也。以立场之不同,非有古今之差也。王弼以“自然”解《老》,以《老》解《易》,征之《老》、《易》,不然也。苏轼谓“李斯以荀卿之学乱天下”,征之荀、李之书,不然也(李斯无书,散见于《史记》各篇)。邹衍称“儒者所谓中国,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儒者所谓九州,乃九州之一(《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征之事实,非尽唐大无凭之词。禹平水土之事,诸子所称与其他经籍,皆可参互印证,而今贤以欧美运河拟之,而不置信,细案诸书揆其情理,未见有可疑之点也。故于时移世异,异说杂陈之际,所可以为依据者参验而已。
“知其不可为而为”(《论语·宪问》),“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孔子之人格,即见于此。“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今也以天下惑,余虽有祈向,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庄子·天道》)庄子之胸怀与忧世之情,亦皆可见。孟子以齐宣、梁惠,皆可王天下,世人皆可以为圣人;于修己,则“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于治人,则“以齐王犹反手也”(《孟子·公孙丑》),其乐观之状跃然在目。荀子言修养,则“化性起伪”(《荀子·性恶》),言行事,则“端悫诚信”(《荀子·修身》),言为学,则“锲而不舍”(《荀子·劝学》),言治国,则“礼义节奏”(《荀子·强国》),其戒惧之貌,亦俨然可见也。故荀子“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荀子·劝学》),因其言语行事,以体会其心情与人格,与其学说之动机,与其所感之问题,则对其人其书,皆可有具体之认识,亦即所谓默契也。如上所云,虽不必能得诸子之真,亦固当免于浅尝固陋之诮,而亦庶可以得攻错之益。至于校勘、训诂、考据、整理,斯皆另有专攻,此所不及也。
注释:
①《论语·季氏》。
②《论语·子路》。
③《左传·襄公二十八年传》卢蒲癸语。
④《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
⑤《汉书》卷30《艺文志·诸子略》。
⑥《毛诗序》。
⑦今本《毛诗传》只标“兴”而不标“赋比”,此依魏源所考。
⑧《毛诗序·疏》,《十三经注疏》本。
⑨《毛诗序·疏》引郑玄《周礼·大师·注》。
⑩白居易:《读张籍古乐府》,载《白居易诗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8页。
(11)《毛诗序》。
(12)《汉书》卷30《艺文志·诗赋略》。
(13)班固:《两都赋序》。
(14)《诗谱序》引郑玄《六艺论》。
(15)白居易:《与元九书》,载《白居易诗文选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68-191页。
(16)《史记》卷47《孔子世家》。
(17)《毛诗序》。
(18)《论语·阳货》。
(19)原诗每句下,都有“上留田”三字和声。此诗或署曹丕作,或为曹丕所改。
(20)《史记》卷84《屈原列传》。
(21)《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
(22)《汉书》卷30《艺文志·诗赋略》。
(23)《法言·吾子》。
(24)《典论·论文》。
(25)章太炎先生常云:“马、郑注《尚书》,能解者仅得十分之五,至清代孙星衍、江声,始明其六七,王引之、孙诒让始明其七八,余始明其八九,余一分尚须诸生勉之也。”
(26)班固《汉书》卷30《艺文志》:“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颜师古注云:言其妄也。桓谭《新论》云:“秦近君说《尧典》篇目,十万余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
(27)自魏晋义疏以来,迄于清季,疏证日繁。一字之释,往往数十百家,连篇累牍,转相钞录,若一一分析之,而其字之义,或仍未解,此最宜剪裁者也。
(28)时贤之整理国故者,恒以科学方法为标帜。然考其所为,亦仅为古书多增数解,而此数解,又未必能合于原意也。至其造说不根,牵强附会者,尤不在少。所为益多,繁芜益甚,是国故终未能整理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