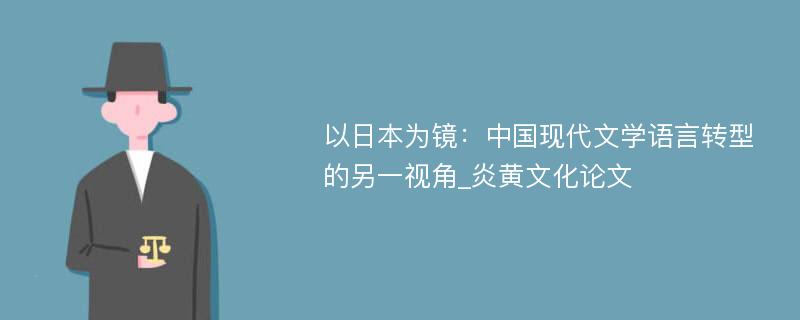
以日为鉴:近代中国文学语言转型的他者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语言论文,视角论文,日为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5)02-0183-06 语言是人类的生存之本,人的存在首先就是一种语言的存在。对人类而言,对一种文化的感知首先从其载体语言开始的。随着清末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日本文化的近距离接触,日语所展现出的对于西方文化的引进、消化吸收以及转介,给初来乍到的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如王国维所说:“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若谓用日本已定之语,不如中国古语之易解,然如侯官严氏所译之《名学》,古则古矣,其如意义之不能了然,何以吾辈稍知外国语者观之,毋宁手穆勒原书之为快也。余虽不敢谓日本已定之语必贤于创造,然其精密则固创造者之所不逮也。(日本人多用双字,其所不能通者,则更用四字以表之。中国人则习用单字,精密不精密之分,全在于此。)而创造之语难解,其与日本已定之语相去又几何哉!”[1]日语有王国维所谓之转介西语之便利性,在于其经历了对于汉语的适合本国特色的改造。而其在改造过程中对于传统汉语的态度和选择方法,值得我们深思。 在西方现代性思想随着坚船利炮强化植入前,中国和日本曾长期处于言文分离的局面。同为儒文化圈,中日两国旧有的书面语表达方式曾经有其辉煌时期,但也因与西方现代文化的格格不入而存在一定的弊害。19世纪西方列强的闯入使中日两国都面临着巨大的民族危机,同时也都不同程度地选择步武泰西这样的走现代化途径以谋求国家的富强和现代民族国家的振兴。正是在此种向现代激烈转型的背景下,中国和日本先后都掀起了影响深远的言文一致运动和白话文运动,而且表现出一定的共性,即“思维方式的变革、话语权力的平等化,文学的解放和参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2]。 汉字大概在公元三四世纪传到了日本。汉字是随着儒学文化和佛教文化进入日本的,因此,汉字的传入,不能仅看作是记录工具的传入,更应该看作是汉文化的传入。正是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强大影响力和优势,才将汉字推广到了诸如日本、朝鲜这样的东亚儒文化圈。经过漫长的历史,汉字已逐渐融入日本固有的生活、文化中,被作为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具有崇高的地位。德川幕府250年是日本历史上相对较长的和平时期,受宋明理学和乾嘉考据的影响,日本的汉学此时也走向了新的高峰,儒学成了幕府的官学,儒生模仿汉土训释经籍。要注意的是,日本在其近代化之前,由于对于中国的依赖关系,同样存在中国汉语所持有的言文相左现象。直至明治初期,日本的文章仍是沿用汉文、和汉混同、古雅文等所谓正统的雅正文体,这样的文体势必与口语不相协调。 汉字的优势地位,因其承载的文化优势而得以在日本推广。但是,当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日本的国门,汉文化所拥有的优势日益被消减的情况下,汉字也就因其不切时弊而在日本进入被改革的行列。自从但丁写了《论俗语》,路德用德语翻译了《圣经》以后,近代世界各国的文字改革一般都和文体改革联系在一起,东亚各国也不例外,近代以前,东亚各国通用汉字汉文,虽然口语各异,但一写成文字就互相通用了。这种情况与欧洲中世纪以前通用拉丁文很相似,所以,在西洋人看来,仍然使用汉字就意味着尚未脱离中世纪封建社会、建立民族国家。而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就需要建构独立的民族共同语,也就要首先解决语音的问题。周有光指出:“共同语需要有语音标准。语音标准是否确定是共同语‘成年’的标志。”[3]明治维新初期的日本,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同时也面临着民族共同语的建构问题。而要建构民族共同语,就要抛离汉字文化与汉字语音。因此,汉字的存废就关乎日本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对此,柄谷行人指出:近代日本文化民族主义把日文的“表音性”置于特别突出的位置,以抵制中华帝国汉字文化的影响。他们选择未受汉字影响的日本典籍《古事记》《源氏物语》,并以日本“国音”诵读,就含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意味——意图在此些作品中发现汉字以前的日语以及与此对应的“古之道”[4]。 后来研究者多将日本的言文一致运动与晚清的白话文相比附,但实际上,汉语在日本与晚清存在着同样的命运,即日本要学习西方而消灭汉字,而晚清要实现现代性就要提倡言文一致,达到启蒙救亡的目的。不同的是,汉字并不是日本的本国语,因而汉字的增减并不能动摇日本的传统;借助消减汉字而引入西文,日本成功实现了言文一致,并达成了现代性的转型。中国则不同,汉字是母语,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伴相生,即便要言文一致,也不能放弃汉字,放弃了汉字,就等于放弃了文化。作为一个没有过多自己文化的国家,日本消减了汉字,但其本有的日本文字却保留了传统。而中国要废除汉字,则就等于放弃了传统。这对于有着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而言,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也就是日本的语言变革相对而言较中国进展得顺利的原因之一。 一般而言,汉字经历了废弃汉字论和削减汉字论两种命运。单就废弃汉字论而论,也可分为两种路径,一种是废弃汉字,专用日本的假名,一种是废弃汉字,用罗马字来代替。 对于近代民族国家而言,国家的语言问题始终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虽然江户时期就已经有人批评汉字,但那还只是说说而已。真刀真枪地要废汉字,改用表音文字是明治以后的事。而首先提出废除汉字的,晚近的日语学界一般都认为始于前岛密。 1866年12月,前岛密向江户将军德川庆喜递交《汉字御废止之议》,揭开了近代日本文字改革的序幕。前岛密的建议总结起来,有以下三点:(1)日本正值国事多端之秋,救国之本在于教育,而要普及教育,就需要简便易学的文字、文章,而汉字“繁难不便”不利于普及。(2)传统的儒家教育看不起百工之艺,搞得国弱民贫。(3)学校的德智教育,应该针对的是儿童的爱国心的培养和科学知识的增长,特别是历史,应该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手段。但受汉字文化的影响,日本的学校教育只从四书五经中学习中国的文物制度和“治乱兴亡”之迹,日本自己的古典和历史却成了可有可无的学科,读书人从小就养成了人尊己卑的心理,一开口就是“令我民成尧世”。汉字的繁难以及儒家文化的教育阻断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思想的普及下达,妨碍了日本人智力的发展,因此,应该废除汉字,一改而为假名这种“日本固有的文字”;废除汉文,创造“言文一致”的日语口语文。[5]1873年,前岛密在与山田敬三、平野荣等人共同起草的《兴日文废汉字之议》中,拟定了废除汉字的具体办法:第一,编撰辞典和文法书,订正东西土语之偏讹;第二,设立师范学校,毕业生根据能力分头翻译和、汉、洋各种书籍,或编写初级教科书;第三,师范生分成等级,派到各地普及教育。 公允地说,这样的以教育普及促成文字改革的思路很好。但是,华顶宫亲王却认为应该先创造实行文字改革的条件才行,并打算组织废汉字会,但因华顶宫亲王的死亡而未果。 1873年,日本组织了以大久保利通为首的保守政府。1875年,明治政府公布了压制言论自由的新闻条例,向民众开放语言文字也被视为有议论自由民权的危险。于是,在政府的压制下,1876-1878年三年间,有关文字改革的言论归于沉寂。1881年,自由民权运动高涨,10月颁布开设国会的诏敕,民权运动变成政党活动。社会言论重归活跃,文字改革的议论再次出现。并且受社会风气的影响,个人议论逐渐变成建立组织的社会运动。1877年以后开始出现推进文字改革运动的团体。1881-1882年之间,出现了主张废除汉字、使用假名的假名之友、伊吕波会和伊吕波文会三团体。1883年,由假名之友牵头,三会合并组成假名之会,聘请明治天皇的弟弟栖川威仁亲王当会长,该会主张,为了使学问更加简便易学,先取好懂的单词,不管它起源于日语、汉语还是其他外语,也不管它是古代还是现代的词汇,用假名书写,向全社会推广。 实际上,假名之会表面上是一个统一的组织,但是在究竟采用哪种假名的用法的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月部主张使用历史假名用法,雪部主张按实际发音修改假名用法,花部主张增加假名的数量。1888年,假名之会拥有5009名会员,为最盛期,之后就逐渐衰落了,而假名学会提出的“平假名和片假名并用、各自选定一种字体、分词连写,竖行直写”等基本方针,对后世影响极大。此后许多报刊采用级汉字注标音假名、小学语文教从分词连写的假名开始等习惯,都和该会有关。可以说,提倡使用平假名不仅和普及教育有关,与明治维新的复古主义也是一致的,因而得到文化教育界的广泛支持。 提倡采用简便易学、国际通用的罗马字来代替汉字的议论,是以1869年5月汉学生南部义筹的《修国语论》为开端的。南部义筹曾学过兰学,服膺于罗马字的简便易学。但南部义筹这篇文字是用汉文写的。他说:“学问之道,西洋诸邦为易,皇国支那为难,而皇国为甚。”究其原因,“夫西洋之为学也,唯知二十六字,解文典之义,则无不可读之书,是其所以为易也。”明治时期日本人刚开始接触西文,以为学会了26个字母就可以读尽天下之书。而汉字字数多,笔画多,读音复杂,难学难用。而“自中古募仿汉制以来,诏敕制诰之文必假力于汉籍而修之,日用之文亦如此者居多。”由是,“不学汉籍则不能成用也。”而明治以后,学习洋务则成为国家的当务之急。甚至有人提议要尽废日语而改用英语。认为“和学则不关今日之人事,而殆属无用,唯为歌词之具而已”。因此,“解国语、通于国典者,鲜矣”。因此,南部义筹大声疾呼:“如此而不止,则堂堂皇国之语或变为汉,或为英、为佛(法语)、为荷(荷兰语)。”因此,为了挽回颓势,他主张要“假洋字而修国语”,也就是用罗马字书写的日语书面语。而其时国际关系紧张,攘夷之风时起,提倡使用洋字也会被视为有伤国体之学。南部义筹也认识到此点,他辩驳道:“自皇国见之,汉与洋同是他邦也,何其择焉。今欲假字而修国语,较之併字语而假之,失皇国固有之语,则何啻霄壤。”因此,在南部义筹看来,比起不仅使用汉字,连词汇、文化都汉化的问题,使用洋字也就算不了什么了。1872年,南部义筹在《改换文字之议》中认为废除汉字应分三步走:第一步,审定发音,制定文字;第二步,分析文章,议定词语的种类;第三步,编写文法书和辞书,并用于儿童教育,将重要、有用的书改写成罗马字。而且,还说明,开始时可以暂时保留汉字。五年以后,辞书和文法书编好以后,就可以以此为依据写书了。这样,要不了十年,完全废除汉字也不要紧了。南部义筹还写下了《用罗马字书写日语》,比较了罗马字与假名的优劣。第一,罗马字是音素文字,比音节文字的假名更科学,更符合音韵学的原理。第二,假名有五十多个,罗马字只有二十六个,更便于记忆。第三,假名没有表示浊音、拗音、促音、鼻音的记号,繁杂易错。第四,表示词形变化时,假名要依五段变化,罗马字只检录变动元音就行,简便易懂。第五,假名局限于一国,罗马字万国通用。不仅便于书写日语,也便于学习外语,符合“广求知识于世界,博采万国之长”的明治维新精神。 从以上可以看出,日本的言文一致的语言改良问题中,存在着欧化主义(罗马字)和国粹主义(假名)两种模式。这两种模式有着共同的两点:(1)两者都主张将表意文字的汉字从国字中排除出去,也即坚持汉字废除论。(2)两者都主张将声音视为语言的本质,借口汉字是野蛮原始的象形文字,遗毒甚深,致令日本“贫弱至极”。这显然是一种社会进化论式的汉字否定论。但是,透过语言改革的表象,究其社会意义实质,乃是日本“为了尽早吸收欧洲启蒙主义知识,谋取国家独立,追求文明开化,主张洋学的知识分子,在‘统一语言’的前提下,于废除汉字或削减汉字方面取得的共识”[6]。这并且得到了19世纪在欧洲形成的比较语言学的理论支持。 比较语言学认为,语言是声音,音韵变化反映于文字之中。汉字是象形文字,这种不将音韵变化表现于文字的象形文字,是语言的化石。从社会进化论的角度,这种主张貌似自然科学的文字进化论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无论在哪一种表记体系里,表音性与表意性其实是混在一起的。两者的区别只是哪一个特征表现得更明显罢了。但是,囿于时事的逼促,以所谓欧洲先进文化作为底蕴的罗马字,因其能恰切记录所有声音,并且可以见字识音地达到言文一致,其文字也就当然地在其时被当成是最为先进的了。出现这种情况,时代因素起着决定作用。中国在鸦片战争的失败,让日本看到了清朝帝国的衰弱。而在1883年的中法战争中,清朝的正规军也遭到了败绩。对于日本而言,曾经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国如此连败,简直令人费解。但是同时这也表明,“在朝鲜半岛爆发壬午军乱之后,中日战争中处于敌对立场的清政府已经开始弱化,情势向对日本有利的方向发展。然而,另一方面,这也就意味着欧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深入亚洲内地[部]”[7]。而清朝的节节败退命运让日本有了兔死狐悲的不安,生怕自己会步大清国的后尘。也就是说,为了不像清政府那样被人击败,就必须摈弃自己身上的亚洲性。这里,亚洲性也就代表了落后与野蛮。为了掩饰这一危机意识,日本竭力装出一副与西欧列强享有同样的理论武装的样子。并且,为了摒弃亚洲性,也即脱离败退的大清帝国影响,福泽谕吉提出脱亚论。在脱亚这个文化选择的起点上,中国形象被赋予否定性,成为“亚族东方之恶友”。脱亚表征了日本对于现代性身份的选择。而在中国沦为战败国的同时,在日本的国家语言中,曾经占据主流优势的汉字也就有了天生的原罪:原始性、野蛮性。 至近代,汉字东渡日本已历一千余年,其在日本语言中的文化优势及地位却随着坚船利炮的冲击而陆沉,在脱亚论的日本国家现代化的形象建构中,“原本属于‘内部’的汉字突然被视作身为‘外部者’的中国的文字了”[8]。尽管实际情况是,其时以日本士族阶级为中心的广大的社会阶层拥有读写汉字的能力,但是,汉字一直被认为是难记难学。这在罗马字主张者和假名主张者的论述中已有共识。究其实质,这种看法的观念是,只有将该文字在现实中的具体使用情况割离开来,它才能达到言文一致的语言使用目的,更可借剥离这种难写难记的汉语,彻底实现日本脱亚入欧的兴国梦,更好地向现代社会进一步迈进。 吊诡的是,其时《朝野新闻》《东京日日新闻》以及《邮电报知报》的记者们都站在文明、进步的立场,批评假名会的主张,而更多地认同罗马字的观点,但其所发表的支持罗马字的言论都是用“汉字假名混合体”写成的。这就形成了一种悖论:他们使用汉字假名混合体支持罗马字的倡导,却没有意识到这一文体正代表了他们所批判的“停滞的亚洲”。这是因为,该时期大量的双音汉字词组为了翻译欧美新概念而被创造出来,这种汉字词组被称作“欧文直译体”①,这就造成了一种矛盾:“在实践上,作为翻译词汇的汉字越多,那么它就越能成为文明开化主体的标志。”[9]这种新式的汉字假名混合文体几乎完全支配了其时的杂志、报纸等铅字媒体。而且,这种认为文明开化的欧文直译体,在明治以降通过包括学校教科书在内的铅字印刷物教育熏陶了新一代,成为他们进军知识领域必不可少的音读式双音节汉字新词了。1887年5月,迁伯伦(Basil Hall Chamberlain)在罗马字会的《言文一致》演讲中指出:现代日语如果缺乏了双音新词,在意思的传递上便很难成立。因此,“为了改善人民的教育现状,提高人民的知识水平,废除从前的晦涩文体,是第一良策”[10]。也许,迁伯伦所不自觉的是,这一句话中的“人民”“改善”“教育”“知识”“文体”等日文单词,其原来概念都袭自英语,但其书写形式却是双音汉字新词。就这一点,李妍淑指出:“主张罗马字的外山正一等人的文章也不过是原封不动地将汉文训读文体转换成罗马字而已。‘无论其多么地醉心于极端的欧化主义,其文章依然是汉文训读文体。这里明显地反映出了明治时期日本知识分子共同的矛盾心理,只是他们当时丝毫不觉得这是一个矛盾。’”[11] 但也正是这种看似矛盾的语言操作,实际上成就了日本的现代性,日本知识分子在短时间内便在国内引介、推广了欧美列强的文明、进步的知识概念与体系。因为,如果没有汉字的复合式效果,“没有一种像盒子一样能将极富扩张性的意义收集在一个类似容器的文字里的话,如果没有这些可以将意义包含起来,并借此表达各种概念的文字效果,对于西方科学、民主知识新概念的大量引进,日本的现代化就缺少了文化与思想上的动因,由此也就缺少了现代社会技术进步的基础”;“文化的现代化,是社会整体现代化的基础,这是因为,科学世界观的确立,被认为是现代社会技术进步的基础。现代化的一个表现和动力,就是科技的进步。”[12] 从1884年到1885年,面对着欧美列强的帝国主义侵略,日本包括自由民权派人士在内的精英阶层对于传统文化的维护以及对于民族独立性的渴望日趋加重。与此同时,包括报纸、杂志以及学校教育等铅字媒体被欧文直译体所控制,这就注定了罗马字会以及假名会对于汉字的废弃与取代的主张的先天不足。也可以说,“这两个学会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因此他们未战先败”[13]。之所以会出现言文一致的幻想,因为其时出现的“一种有别于罗马字表记和假名表记的表音符号体系——‘速记法’得到了确立,并且在铅字印刷市场上取得了商业成功”[14]。正是速记法的“以语言之实录法录之”,故能使人读之“皆以能亲临之表演之所,以亲耳聆听为一乐事”[15]。但其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白描语言的速记法”,就整体性而言,若以普通小说文体规则相比对,往往不成文体,不便通读。因为,在将速记法的记号翻译成汉字假名混合文时,速记者头脑中所想的是文体是否经得起默读。因为是白描,所以在这方面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就是使用速记法的后果。这一点,坪内逍遥在《怪谈牡丹灯笼》第二版的序篇中就谈到,速记法“将自然的感情充分表现了出来”,但他又不得不指出:“此间幽默大师三施亭公所表演底被称做牡丹灯笼底故事,以速记法如实记录,虽说可视做草纸小说,然通篇皆为俚言俗语,虽不觉其式样华丽,然字里行音,颇有栩栩如生之趣。”[16] 如此,通过这种速记法和民众广泛接受的讲演小说,利用速记法将声音如实抄写下来,并由速记者翻译成汉字假名混合文的流程,日益成为其时的媒体的主流手段,也就产生出了大众娱乐读物这种新式铅字商品。“幕府末期人情本这种书面语文体就是通过圆朝的口头表演转化成声音,并通过速记及表音性和表意性相结合的符号系统将声音如实描写出来的。他就是在这么一种幻想的基础之上,将速记符号翻译成汉字假名混合文的。这样一来,就会使人产生一种错觉,误认为它的文本已经实现了言文一致。……言与文、声音与文字、表音性与表意性,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与作为表音文字的假名与字母等,这一连串的二元对立中所隐蔽的是:速记法这一将表音性与表意性混为一体的中间性符号体系的存在,将速记符号翻译成文字时所产生的一种崭新的文体。这一汉字假名相混合的文体最有效地支持了近代日本的出版资本主义,并令读者在默读这一复合形式的文体的过程中,高度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出了一种以假乱真的现实感。”[17] 就这样,到1880年代的后半期,报纸、杂志等铅字印刷媒介借助于速记文这种新文体,开始成为一种专门提供娱乐的新的商品。作为一种娱乐性读物的主流体裁,获得了与报纸主流话语平起平坐的位置。这些报纸的目的主要是从政治/学术中心,以新闻报道/论说文/叙事文等形式,向处于边缘的社会大众提供信息。而且,以速记法这一语言技术媒介,1890年以开设国会为目标的政治性主体话语最终选择了比欧文直译体较为平易的方向。于是,作为娱乐主体媒体的汉字媒介,通过讲谈/单口相声的速记文打开了市场。但是,“它们并未特别意识到所谓的言文一致,它们只是在以故事娱乐读者而已。但是,速记文这种新型记录系统会使人产生错觉,从而认为活生生的声音在文章的背后。对于知识分子而言,这一表记体系使得他们对一种以欧美为典范(实际这也是幻想)的、‘文明’与‘进步’名义下的言文一致持有某种幻想”[18]。由是使得主张罗马字者单纯地呼吁排除汉字汉语了。 在以上废除汉字、改用表音文字成为一种时髦和思想进步的象征时,也有一些人持反对意见。他们抨击欧化主义,主张回归传统,力主汉字不可废。并提出了相对来讲可行性较强的削减汉字的方案。1873年11月,福泽谕吉仿照西洋的初级教科书编写了《文字之教》。在《第一文字之教》的序言中,福泽谕吉指出,对于日本文字而言,既有假名又有汉字的杂用现状非常不方便。但是,考虑到实际情况,即自古积累下来的书籍都是用汉字写的,如果突然一下子废除汉字会很不方便。因此,废除汉字应该缓行。当今之计,应该为将来做准备,写文章时注意不用难写难认的汉字。作为实践,福泽谕吉的《文字之教》三册书总共用汉字802个,是日本限制使用汉字最早的小学语文教科书。 如果说福泽谕吉的提议只是理论提倡,那么其弟子矢野文雄1886年3月撰写的《日本文体文字新论》一文,则将福泽谕吉的理论变成了一种实际可行的方案。矢野文雄将文章分为普通书和文学书两种。普通书以任何人都能读懂、广泛通行于社会为主要目的,可以使用常用文字。包括政府的布告、命令、训状等公用文书;公私学校的教育用书;以大多数人为对象的新闻、杂志类(不包括学术性的专门杂志);日用书信类。而文学书则面向受过充分教育的阶层,以汉文为主,各种文字、文体都可以自由使用。矢野文雄指出,因为汉字的字数多、不好学,所以一有人提倡废除汉字而使用简单易学的假名就应者云集。但是,汉字与假名的文章哪个更好懂呢?80%的识字人都会认为汉字好懂。所以,人们还是喜欢用汉字写文章。在日常应用中,号称数万的汉字实际上常用的字并不多,学会三四千字也就够日常所用了。因此,矢野文雄提议政府设立专门委员会,选定3000汉字,以供日常普通书籍之用。并在其主笔的《邮电报知新闻》社论中宣布,自1887年10月1日起,除了小说和布告外,该报所用汉字限制在3000字以内。同时,给社论等文章标注假名,标在字行左边的表示字音,右边的表示字义,隔周交替。1887年11月27日,该报刊行了《三千字字典》,分为实字即名词、代词1000字,虚字2000字。原则上一字一音一训。这是大报使用汉字的最早实例,因而在日本汉字改革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在明治时代的众多言论中,真正可以付诸实施的是矢野方案。后世的文字改革,不管其终极目标是什么,真正做到的也未脱出矢野方案的窠臼。 由上可知,明治时期日本有关文字改革的议论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一是以前岛密为开端的“处士横议”阶段。二是1881年后的民间组织的社会运动阶段,出现了假名之会和罗马字会等旨在促进文字改革的民间团体。第三阶段是1900年以来,一批人借助政府的力量实行自上而下的文字改革。把废除汉字作为终极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从当时起就尽量少用汉字,以求渐进地达到最终目标。考虑到废除汉字非一朝一夕之功,强行废除汉字并不符合实际,也会带来诸多不便。可以借用政府和舆论的力量,逐步消减、最终废除汉字。早年的加藤弘之、原敬等人也一度担任政府要职,于是他们上下呼应,书生议论也就渐次转变为国家语文文字政策了。 中国日本同为汉文化圈,随着儒家文化的影响传播,中日语言有着较多的一致性。不仅文化传承上,而且在针对西方现代化而提倡的言文一致运动中,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关联性,因此,中日语言运动中的言文一致也就有了一定的比较可能。 19世纪后叶,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趋势日益加剧,政治制度、科技等相较之下较为落后的东亚各国普遍面临着国族破灭的危机。因此,为救亡图存,各国开始学习欧美进行改革。而中日在此的共同性即掀起语言文字运动,以之为全面引进西方思想和政治制度作铺垫。封建时代,中日两国语言普遍存在着口语和书面语两个体系,这两个体系在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合而为一,完成了文体的变革。这种文体的变革并非如有些人所说的是为适应社会对启蒙和开化的需要,而是建设民族国家的内在需要。可以说,语言文字起着精神纽带的作用。进入近代后被迫接受西方文化的中国、日本等国,在启蒙开化以及救亡图存的过程中,文学语言成为必须通过“运动”这种轰轰烈烈的政治方式才能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 近代日本所推介的言文一致运动,究其实质而言是为了通过对汉字汉语的变革进而达到驱除中国文明影响的目的。在古代,日本文化、文学以中国文化为核心产生和发展。“隋唐时期汉语书籍传入日本,其时日本尚没有独立的书面语。平安时代后,由汉字演变而来表音文字平假名、片假名虽得以迅速发展,但与汉字相比,仍居从属地位”[19],且假名的使用局限在非正式场合。而且,汉语在日本文化影响颇大,7世纪后期,日本以中华政治体式为样本,建立了一套完备的官方政治文化体系。但是,中日两国在西方炮舰下的节节溃败,让日本意识到了危机感,日本由此推出了脱亚入欧策略,要断然放弃东方的中华文明,转而学习、效仿西方。因此,消除深入日本文化骨髓里的东方文明因素,就成了其时日本的要务,废除汉语就成了一项得以摆脱亚洲东方文明的举措。但是,从历史发展的实际来看,这种以政治意图为导向的语言变革运动最终却以折中的结局告终,汉字仍在日语中发挥着内在的重要的作用。 注释: ①如果说,因发达的印刷而形成的新闻媒体即报纸与杂志的消息、叙事文、论说文等,是一种只能采用以双音汉字新词为主的欧文直译体,那么就不得不承认,所谓言文一致而产生的废弃汉字说,从其刚刚拉开序幕的时候,就带上了一种绝望的色彩。这只需考察一下当时的媒体即可知。因为用铅字印刷的媒体,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供默读的新型媒体,它在符号性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标签:炎黄文化论文; 日语汉字音读论文; 日文字论文; 汉字演变论文; 日语汉字论文; 朝鲜汉字论文; 汉字废止论文; 日语学习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福泽谕吉论文; 片假名论文; 文体论文; 日语论文; 速记论文; 江户日语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