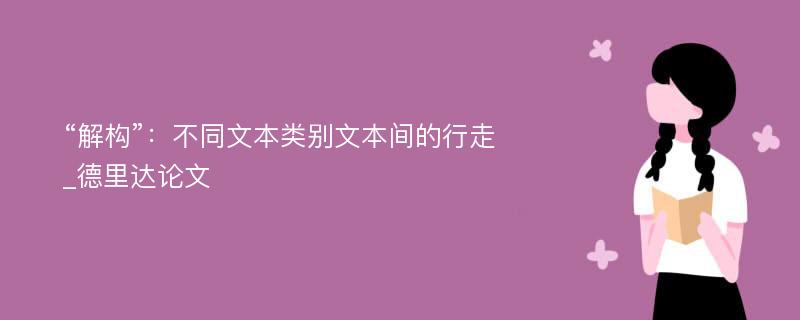
“解构”:在不同文类的文本间穿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本论文,同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次“当代外国文学学术研讨会”的论题中,有一个“当代外国文学理论的新视角”。论题的言外之意,显然是想对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涌现出的各种外国文学新理论作一些解说,看看这些理论为我们外国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什么新的视角,而按照这样一些新的视角去看外国文学,我们又能够获得哪些迄今未曾发现的新的意义。
这样一个想法对不对呢?可以说没有错,我们通常也都这么认为的。但我们是不是还应该想一想,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大行其道的那些新理论,果真是旨在为我们注入某种新的思想,或能让我们从文学作品中获得迄今未曾发现的意义吗?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乔纳森·卡勒( Jonathan Culler) 教授,也许可算得是对上个世纪西方文论思潮把握得最透彻的理论家之一,他曾在那股理论热的鼎盛时期说过这样的一段话:
英美批评家通常认为文学理论是佣人的佣人;其目的是为了辅佐批评家,而批评家的任务是通过对文学名著的阐释为文学服务。……可是近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文学理论已经发生了变化,不论它们对阐释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文学理论著作却与一个迄今尚未命名、但权且可以简称为“理论”领域的那些著作,有着密切而生动的联系。这个领域并不是“文学理论”,因为它的许多极其有趣的著作并不明显地诉诸文学。它又不同于时下所谓的“哲学”,因为它既包括索绪尔、马克思、弗洛伊德、欧文·戈夫曼和雅各·拉康,又包括黑格尔、尼采和汉斯-乔治·伽德默。倘若文本可以被理解为“以语言表达的任何东西”,它或许可以被称作“文本理论”,不过,最方便的称谓莫过于“理论”这个最简单的绰号了。(注:Jonathan Culler,On Deconstructi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2,pp.7-8.)
然而,这种“理论”,卡勒这样解释说:
……基本上不是一种阐释性的批评;它并不提供一种方法,一旦用于文学作品就能产生迄今未知的新意,与其说它是一种发现或派定意义的批评,毋宁说它是一种旨在确立产生意义的条件的诗学。它将新的注意力投向阅读活动,试图说明我们如何读出文本的意义,说明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学究竟建立在哪些阐释过程的基础之上。(注:Jonathan Culler,Structuralist Poetics:Structualism,Linguistics,and the Study of Literature,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5," Preface" ,p.viii.)
如此说来,是不是说我们即使掌握了这些“理论”,也并不能使我们从所阅读的文学作品中获得这样那样新的意义呢?是的。那么,我们使劲地学习这样那样的文学理论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不妨再来好好地琢磨一下卡勒的话:“与其说它是一种发现或派定意义的批评,毋宁说它是一种旨在确立产生意义的条件的诗学”。(注:着重号系笔者所加。)这种理论所关注的,其实已不再是具体的文本,而是我们的“阅读活动”,它所要说明的,是我们如何才能读出 (获得)这已知的文本的意义,要说明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学究竟是建立在哪些阐释过程的基础之上。换句话说,即这些“理论”能够把我们提升到一个新的认识层次(不再是作品本身的层面),让我们对于我们在阅读过程中所领悟到的“意义”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为什么会获得这样的认识等问题有一个更加清醒的认识,让我们对自己的阅读行为有更加自觉的意识。
学术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我们往往不仅会对所研究的对象是什么感兴趣,而且还想知道它为何如此这般,还想知道那深藏在事物的背后、深藏在我们认识的背后的道理,也就是说,想提升到一个" meta" 的层面,对我们已有认识的成因发问——从而对我们之所以会有现有这样的认识作出一种解释。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认识论中有" physics" 和" meta-physics" 两个不同层面,即所谓“物理”的层面和“形而上”的层面。“物理”研究的是客观事物和现象,格物致知,而“形而上”的学问,则是要在各门学科的知识和道理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从中引出我们对于整个世界的认识规律。
为此,有学者把当下这种“理论”称之为“第二层次反思的混合物”( the congeries of second-order reflection) 。(注:Stefan Collini," Introduction:Interpretation terminable and interminable," in Umberto Eco,Interpretation and Overinterpreta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Reprinted,1994,p.5.)大家不妨对这个“第二层次”好好琢磨一下。把这一点琢磨透了,我们也就会明白,为什么这么些年来,我们搞了这么久的理论,却总是摆脱不掉一种半生不熟、磕磕绊绊的窘状:要么是学了理论之后仍把“理论”束之高阁,好像它总是不能为我所用,如解构主义;要么,则是要不要两可,觉得理论像是个鸡肋似的劳什子,有没有它都能读出同样的意义。如读者反应批评或叙述学的理论。
问题恐怕出在我们对“理论”的期待上,“理论”的位置究竟在哪里,它究竟能发挥怎样的作用?我今天就想以“解构”为例,讲一点我对“解构”理论的认识。
2001年9月,解构哲学大师雅克·德里达访问了中国。在北京期间,他到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做了演讲和座谈。9月10日,他又来到南京大学,就“解构”、“全球化”等问题与南大的部分学者和师生进行了座谈。按说,你们都得了“解构”的真传,可是,话又说回来,诸位即使得到了大师的亲炙,即使从原理上懂得了所谓“解构”的要领,我们就能手到擒来地对所阅读的文本玩上一圈“解构”吗?或者用卡勒的话说,就能从文本中获得某种“迄今未知的新意”吗?我看绝大多数的人恐怕都没有这个本事。为什么?我觉得,“解构”即使从纯粹的批评方法角度而言,它其实也只是对德里达以及数量很少的一些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的批评家们所采用的一种非常特殊的阅读文本的方法的归纳和命名。我刚才说了,“解构”作为一种“理论”,为的是要对我们所从事的阅读、阐释行为作出解释,那么它所针对的是一种什么样的阅读阐释活动呢?在我看来,那必须是在受过语言学、语义学、词源学以及文献版本学等多方面良好训练的基础之上,在熟练的掌握了“新批评”所最擅长的文本细读的本领之后,才能掌握的一种在文学文本中穿行、甚至上下翻飞的能力。这里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通过专业的文本阅读训练而获得一种“文学能力”( literary competence) ,这其实是我们能够从事“解构”阅读的一个前提条件。关于这一点,我们下面将结合具体的实例来加以说明。
俗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我们今天就选德里达本人的一个“解构”阅读的实例,来说明这种“解构”阅读的运作要领。我手头有两本书,一本是德里达于1993以法文出版,1994年被译成英文出版的著作Specters of Marx:The State of the Debt,the Work of Mourning,& the New International,(注:由于德里达本人一直在美英学界直接用英文发表演讲,他的法文原文的论著亦几乎全都被翻译成了英文,而英美学界的学者通常也都引述英译本与德里达进行直接的交流,因而他的著述的英译本基本上被认为具有与法文本同等的表意合法性。)另一本是它的中译本《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我先买的中译本,一看书名就不懂——“马克思的幽灵”怎么与“债务国家”、“哀悼活动”等搞到一起去了?中文译本读不懂,只好托人到美国买了一本英文本。
英文本有一篇由伯恩德·马格努斯 ( Bernd Magnus) 和斯蒂芬·卡伦伯格 ( Stephen Cullenberg) 撰写的编者导言,对德里达这一著述的来历作了简要的介绍。
1989年柏林墙倒塌,接着是苏联和东欧的解体,西方世界被一股乐观主义的欢呼声所笼罩。这种乐观主义的最突出代表则是弗朗西斯·福山所谓的“历史终结论”之说,认为未来世界肯定是自由市场经济一统天下。但是,二位编者又写道,也有很多人隐隐约约地有另外一种预感,一种忐忑不安的感觉,觉得国际范围内如此巨大的变化很可能将引发——至少在一开始,或许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既坏又好、好坏参半的转变。总之,西方思想理论界中一个比较普遍的看法就是,首先应该对1989年之前的意识形态和冷战时代的世界结构重新认识,重新建构。其中有许多亟待回答的问题。例如,苏联和东欧的解体(许多西方政要称之为“共产主义的崩溃”),是否就意味着过去150年来人类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之一的马克思主义将彻底消亡?而马克思作为人类历史上一位极为重要的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也将随之而被彻底地忘却吗?再者,福山所谓的“历史的终结”是否就真的指日可待了呢?而世界范围内的多元化的民主、资本主义经济的绝对统治等,也都很快就要实现了吗?而世界的未来是否真的就要在斯堪的纳维亚式的社会民主和不受任何限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两者之间作出一个简单的选择呢?还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对于以上所发生的种种全球性的变化,又将作出怎样的回应呢?全世界那么多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社会革命家为之奋斗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目标——收入的平均分配,工作环境的改善,经济剥削的终止以及消灭阶级差异等——其未来的地位又将如何呢?所谓“历史的终结”是否还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终结呢?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中,哪些还会有生命力,而哪些则会死亡?等等。
该书的二位编者说,1991年的10月,他们正是带着上述种种问题,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思想与社会研究中心商议,商议的结果是召开一次国际性的、跨学科的研讨会,议题为“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从国际视角审视各种全球性危机”。1993年4月 22-24日,研讨会召开,与会代表来自中国,俄罗斯,美国,波兰,罗马尼亚,墨西哥,德国,法国等。德里达在开幕那天和次日的晚上,分两次做大会发言,报告的题目叫作“马克思的幽灵们:传承、追思和新英特纳雄耐尔”。
大家或许已经注意到,我现在已经悄悄地将德里达讲演报告的副题作了改动,将该书中文译本的副题——“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改成了“传承、追思和新英特纳雄耐尔”。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改动呢?我就是想通过对这一改动作出解释,来对德里达所谓的“解构”这样一种特定的释读文本的方法展示我的理解和认识。
一位来华讲授当代文论的法国学者高宣扬曾这样描述德里达及其“解构批评”:
德里达是一位不断穿越文本并在文本中到处“流浪”的思想家,他以古往今来的著名著作的文本作为他思想和创作的“田野”,从中他一再地得到启示和灵感,进行无止境的反思和创造……。(注:[法]高宣扬《德里达的‘延异’和‘解构’》,见冯俊等著《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8月,第290页。)
这段话是我所看到的对于德里达和他的“解构”阅读法的最好解释。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们》( The Specters of Marx) 中是如何实施他的“解构”操作的。
说到“在文本中穿越”和在文本中“流浪”,我不由想起了另一位法国的解构大师米歇尔·福柯,他在一篇题名为《话语的秩序》的文章的开头这样说道:
我希望我能够以一种不为人注意的方式,悄悄地滑入到我今天以及在今后许多年里所必须讲述的话语中。我宁可自己被言语包裹起来,远远地离开那所有可能的开端,也不愿成为始作俑者。我更愿意自己意识到,早在我之前即有一个无名的声音在诉说着,这样,我只需要加入进去,接过已经开始的话头,让自己置身于谈话的间隙之中,而不引起人们的注意,仿佛它稍事停顿,招呼我加入。这样,就不会有任何的开端,不会成为某个话语的发起人,相反,我则完全受一个偶尔开启的、小小的机会的支配,那是稍纵即逝的一个点。(注:Michel Foucault," The Order of Discourse," in Robert Young,ed.,Untying the Text,Routledge & Kegan Paul,1981,p.51,p.51.)
福柯还说,
……很多人都有一种规避开端的欲望,以求从一开始就已在话语的另一边。这样便无需再从外部考虑话语的奇特、可怖和邪恶之处。体制对这一常有的愿望却以反讽作答,它将开端神圣化,用注视和沉默将它团团围住,并强加给它某种仪式,仿佛要使它在远处亦能容易地辨认。(注:Michel Foucault," The Order of Discourse," in Robert Young,ed.,Untying the Text,Routledge & Kegan Paul,1981,p.51,p.51.)
正如福柯所说的那样,在如何开启话题这个问题上,德里达显然也表现出了一种“规避开端”的倾向,他不愿意由他自己跳出来,开启关于马克思主义当下之命运这样一个讨论,因为这是一个当下很多人都正在谈论着的非常重要的话题。那么,如何进入这样一个话题、而不要显得好像是由自己挑头提出,如何再一次切入这个话题、而避免重复以往的讨论,回避迄今为止在这个问题上的所有的争论,如何才能不理会别人的既定看法径直切入正题,讲出自己所想讲的想法呢?德里达于是就采取了一种迂回的办法,他在报告的第一部分“马克思的训诲” ( Injunctions of Marx) 中,并不是由他自己来提出问题,而是找来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剧本第一幕第5场中哈姆雷特与鬼魂的一段对话,以此来作为他讲演的开场白:
Hamlet:…Sweare.
Ghost[beneath]:Sweare
[They swear]
Hamlet:Rest,rest perturbed Spirit! So
Gentlemen,
With all my loue I doe commend me to you;
And what so poore a man as Hamlet is
Doe t' expresse his loue and friending to you,
God willing,shall not lacke:Let us goe in
together,
And still your fingers on your lippes,I pray.
The time is out of ioynt:Oh cursed spight,
That ever I was borne to set it right.
Nay,come,let' s goe together.[Exeunt]
-Act I,scene v(注:Jacques Derrida,Specters of Marx:The State of the Debt,the Work of Mourning,& the New International,Routledge,1994,p.3,p.3,p.3,p.5, pp.3-5, p.9.)
关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剧本,国内有不少译本。我们选了两个在遣词造句上略有不同的译本:一个是朱生豪的散文译本,另一个是卞之琳的韵文译本。
朱生豪译本中的这段道白是这样的:
哈姆莱特:……宣誓吧。
鬼魂[在下]:宣誓!(二人宣誓)
哈姆莱特:安息吧,安息吧,受难的灵
魂!好,朋友们,我以满怀的热情,信
赖着你们两位;要是在哈姆莱特的微弱
的能力以内,能够有可以向你们表示他
的友情之处,上帝在上,我一定不会有
负你们。让我们一同进去;请你们记着
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守口如瓶。这是一
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楣的我却要
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来,我们一块儿
去吧。(同下)(注:《莎士比亚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10月,第33页。)
卞之琳的译本在形式上更忠实于原味:
发誓吧!
[自下]发誓!
安息吧,安息吧,不安的灵魂!得,
我以满怀的热情信赖二位;
只要像哈姆雷特这样的一个可怜人、
对你们能表示情谊,托福上天,
什么都一定做到。我们进去吧;
你们要永远缄口,我请求你们。
时代整个儿脱节了;啊,真糟,
天生我偏要我把它重新整好!
来,我们一块儿走吧。
第一幕,第5场(注:《卞之琳译文集》(下),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 12月,第43-44页。) [同下]
我们如果对这几个文本加以比较,从莎士比亚原剧本中的诗文,到朱译汉语散文,再到卞译汉语韵文,我们就会发现,随着各个文本字句的变化,文本的意义也略有不同,从语义学的角度看,这中间的差别还不小。由此,我们或许能得到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即任何用语言文字对语言文字的解释,只要语言能指符号不一样,文本所指的意义肯定也就会有这样那样的变异。
那么,德里达为什么要选取《哈姆雷特》剧中哈姆雷特的这段道白,他又将如何在这段戏剧道白的文本内外穿行翻飞呢?德里达的讲演报告是这样开头的:
Maintaining now the specters of Marx.( But maintaining now [maintenant]without conjuncture A disjointed or disadjusted now," out of joint," a disajointed now that always risks maintaining nothing together in the assured conjunction of some context whose border would still be determinable.) (注:Jacques Derrida,Specters of Marx:The State of the Debt,the Work of Mourning,& the New International,Routledge,1994,p.3,p.3,p.3,p.5, pp.3-5, p.9.)
而《马克思的幽灵》中译本中的这段译文是这样的:
现在该维护马克思的幽灵们了。(但是现在的维护已经没有了关联。一个脱节或失调的现在,一个“颠倒混乱”、失去了连接的现在,却常常要冒险在某个其边界一直都可以限定的语境的确定关联中把根本不存在的东西维系在一起!)(注: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7-8、6、15-16页。着重号系笔者所加。)
我不知道有没有读者能读得懂这段译文。不过译者在“译者序”中早已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下堵住了读者们可能发出的抱怨:“同德里达的其他前卫性写作一样,《马克思的幽灵》也可以说是不可归纳和不可迻译的。他的论述并不是以一种逻辑的或推论的方式向前推进,而是以跨时空的异质性文本的互文性并置来打开文本潜在的意义维度,或者说是通过文字游戏来炸裂文本表层的叙述结构,在意义的不断延异中来显现那不可表征的东西的踪迹。”(注: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7-8、6、15-16页。着重号系笔者所加。)说得真是煞有介事。好嘛,德里达写的向来都是天书,既不可归纳,也不可迻译,尔等之所以读不懂,乃因尔等凡胎肉眼,当然不知所云。要怪就去怪德里达吧,是德里达没让你看懂。
如果说这中文译文实在没法懂,德里达的英文译本却并没有像“何一”译者所说的那样让人头痛。这第一句" Maintaining now the specters of Marx." 其实就是哈姆雷特那段道白的衍生。哈姆雷特在那段道白中说:" The time is out of ioynt:Oh cursed spight,/That ever I was borne to set it right." 中译本的译者在翻译这段剧本引文时大概讨了个现成,直接从朱生豪译本中下载了所需要的文字——“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楣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他也没再仔细地琢磨一下" The time is out of joint" 的含义,琢磨一下这一句话与德里达起笔之句的关联,于是也就没能看出" Maintaining now" 其实指的是" to set the time right" 的意思。这样一来,德里达讲演报告的开宗明义第一句话“修复现在吧,马克思的幽灵们”,就被译成了“现在该维护马克思的幽灵们了”这活活让人堕入五里雾的卜辞咒语。
译者显然是把这句中的" now" 误当作是副词“现在”了。可是,德里达不是紧接着在这一句呼语之后又作了长长的一番解释吗?将这一句后置于括弧中的一番解释翻译成中文,这“现在”( " now" ) 的意思应该是很清楚的:
但现在[maintenaun]要修复的是失去了关联的现在,一个“脱了节的”或“散了架的”现在,“榫头脱散了”,一个“七零八落的”现在,这样,即使在与一个边界尚可确定的语境肯定有关联的情况下,它总还要冒上什么也维系不住的危险。(注:Jacques Derrida,Specters of Marx:The State of the Debt,the Work of Mourning,& the New International,Routledge,1994,p.3,p.3,p.3,p.5, pp.3-5, p.9.)
现在,德里达的第一段话的意思不是很明白了么?那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呢?我想主要有两点:一是对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剧中那段道白的意思和作用不了解,二是对德里达的言说方式不了解。
关于第一点,哈姆雷特这段著名的道白中有几个关键词:一个是" Time" (时间,时代);一个是" Out of joint ( ioynt) " (脱榫,脱节),再一个就是" That ever I was born to set it right" (偏偏把我生出来,要我去把它修复好)。这是德里达马上要做自己的文章时的切入点。既然“时代”( the Time) 出了问题,“脱了榫”( out of joint) ,这“修复时代”( to set the time right亦即 maintaining now) 的使命就命定地( that ever they were born to) 降临到“马克思后代们”的身上。但是,现在这样一个时代,在德里达看来,是一个“脱了节的”( disjointed) 或“散了架的”( disadjusted) 时代,一个“榫头脱散了的”( out of joint) 时代,一个“七零八落的”( disajointed) 时代,因此,即使我们对所要探讨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所处语境都很清楚的情况下,我们也许仍会对这个时代把握不住而一筹莫展。换句话说,要使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真正得到解决,恐怕还不那么容易。
第二点,关于德里达的言说方式,即我们前面说过的他惯用的一种迂回的方式——借他人之口提出问题的方式。如前所说,他总要先找来一篇堪称经典的文本,他会进入到这个文本中,在这个文本中“穿行”、“流浪”,从中得到某种启示和灵感,然后申发出他自己的想法。现在,他找来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的一段道白,他挖掘出了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至为关键的词语,他抓住了这些词语,把这些词语一个又一个的词义让我们过目,而就在他像变戏法似的语义置换过程中,他把他所要讲述的话题一点一点地展开。
当他展示了哈姆雷特的那段道白之后,他就势便过渡到了“马克思的幽灵们修复当下时代”的话题。由于哈姆雷特的这段道白是与“鬼魂”的一段对话。所以由“鬼魂”( ghost) 过渡到“幽灵”也顺理成章。接下来,德里达在“幽灵”( specters) 这个词语上做起了文章。在西文中,表达“鬼魂”的词语很多,除了" ghosts" 以外,还有" phantoms" 、" goblins" 或" apparitions," 还有德里达用的“specters”,而“spirits”除了我们平时所常用的“精神”的意思外,也有“精灵”的意思。不过,这些词语在具体的含义上又有些许细微的差别,即所谓词义的nuance上有着这样那样的侧重。从“鬼魂”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幽灵”,按字面的意思说,两个词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德里达之所以要从" ghost" 转换到" specters" ,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共产党宣言》上的第一句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中用的是" specter" 这个字。德里达在他的这篇讲演中要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命运。然而,马克思早已过世,已经不在了,但他的“精神”( spirit) 还在,西文中的" spirit" 一词,本义就是“灵魂”,但也有“幽灵、鬼魂”的意思。今天要谈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其实只能是谈“马克思的灵魂”——正在四下出没并徘徊着的马克思的幽灵。为了更明确地表达这个意思,德里达选用了" specter" 这个字,因为" specter" 和" spirit" 有相通的涵义,但又稍有区别。" specter" 更加接近于那个具体的" ghost" 或" phantom" ,是一个" haunting ghost" 。而" spirit" 则更像我们中文中所谓的“精、气、神”,更接近“灵魂”( soul) 、“精神、本质”( essence) 。
那么,德里达接着问道:为什么要用复数形式的“幽灵们”( specters) 呢?他正是在对“幽灵”的复数这看似是对语词本身的分析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在当代以“多样性”、“异质性”存在这样一个特点作了阐述。德里达在呈述他的这一讲演报告时,我们作为演讲的接受者也在始终不停地在两种不同的话语方式中来回穿梭。他所有的讲述,在我们听来,似乎都是在对《哈姆雷特》的剧情,对哈姆雷特道白中的某些用词进行解读,他似乎是在对哈姆雷特为何会有这样那样的想法,为何会有这样那样的行动进行分析。然而,正当你沿着这一思路去把握莎士比亚剧本中的某个语词的时候,你又突然会发现,德里达此刻已经穿行或切入到了另一个语义层面——当下社会政治的语义层面。《哈姆雷特》剧中的“鬼魂”,在你不知不觉之中,变成了“出没、徘徊在欧洲的共产主义幽灵”。
就这样,从“时代的脱榫与修复”到“幽灵的出没”,再到《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再到“思想”和“精神”的代代相传——从莎士比亚,到马克思,再到瓦雷里;从但丁,到莱布尼茨,到康德,到黑格尔,又再回到马克思……。人类思想的传承,用德里达自己的话描述,那就是“在后代人影影绰绰的记忆中,莎士比亚似乎经常会引发出这种马克思拿手的戏剧化过程。”(注:Jacques Derrida,Specters of Marx:The State of the Debt,the Work of Mourning,& the New International,Routledge,1994,p.3,p.3,p.3,p.5, pp.3-5, p.9.)最后,德里达又引出了瓦雷里关于人和政治学的定义——他把“人”界定为“试图创造我所谓的精神之精神”,而政治学则“总是包含了人的某种思想”。(注:Jacques Derrida,Specters of Marx:The State of the Debt,the Work of Mourning,& the New International,Routledge,1994,p.3,p.3,p.3,p.5, pp.3-5, p.9.)
德里达在语言上做了如此令人目不暇接的置换,他究竟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在我看来,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这一系列的语言置换,为他自己铺垫好一个合适的谈话语境,这样,他就可以像福柯所说的那样,避免由自己挑头充当这样一个充满着纷争的话题的始作俑者,以一种不为人注意的方式进入他所要讨论的话题——在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消亡之后,我们如何对马克思主义的遗产进行再阐释。这也是德里达2001年来南京大学座谈时所特别提到的他一直给予关注的一个问题。
当我们明白了德里达的这次讲演的总体意图之后,他这篇讲演的副题" the state of the debt,the work of mourning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的中文译文显然就太有点令人生疑了。怎么成了什么“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了呢?德里达明明是要讨论一种思想的延续和承继关系嘛!在马克思死后,他的“精神”( spirit) 是如何传承下去的?它为何还会像“幽灵”一样继续“游荡、显现”?而我们后人,又以怎样的方式来继承马克思的思想,把握住他的精神?这里的" the state of the debt" 怎么就成了“债务国家”了呢?
德里达接下来在他的演讲中解释说,他所谓的“灵魂,精神”( the spirit) ,又可以被分解为三部分:(注:以下这部分的讨论请参照阅读Specters of Marx,pp.8-10;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15-16页;杜小真、张宁主编《德里达中国演讲录》,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4月,第93-94页。)
第一是" mourning" 。如果像现在这样译成了“哀悼”,读者的思绪就完全被引导到了我们通常向逝者致哀的仪式上。然而在这里,德里达更为强调的,乃是我们活着的人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对死去的人所进行的一种思想观念的建构,即他所谓的" to ontologize remains" (直译为“把遗物本体化”),使一个“过世者的遗物” ( the remains of a dead body) 抽象化、观念化,亦即“本体化”——化为一种“精神”。正因为这个缘故,这里的“mourning”其实与“哀”的关系已经不太大了,更多的是“追念”、“追思”的意思。
然而在中译本中,我们却看到了的是:
哀悼的意图常常在于试图使遗骸本体论化,使它出场,并且首先是通过辨认遗体和确定死者的墓地来进行。(整个的本体论化,整个的语义化——哲学的、阐释学的或心理分析的——发现自己已被卷进了这个哀悼活动,而它本身还没有想过这一点;……)人们必须有所认识。人们必须对它有所认识。人们必须对它有所了解。而此时必须知道的就是那是谁和在什么地方,即那实际上是谁的躯体和它处在什么地方——因为它应当呆在它的位置上。在某个安全的地方。(注: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7-8、6、15-16页。着重号系笔者所加。)
我实在不知道,这样的中文对于那些对德里达知之不详的读者,究竟能传递给他们什么样的意义。我也实在不明白,译者怎么会在一个讨论思想传承的语境中,竟会滑到了“辨认遗体和确定死者的墓地”这一语义可能性呢?
德里达讲演的英文本原文是这样的:
It consists always in attempting to ontologize remains,to make them present,in the first place by identifying the bodily remains and by localizing the dead ( all ontologization,all semanticization philosophical,hermeneutical,or psychoanalytical finds itself caught up in this work of mourning but,as such,it does not yet think it; we are posing here the question of the specter,to the specter,whether it be Hamlet' s or Marx' s,on this near side of such thinking) .One has to know.One has to know it.One has to have knowledge [Il faut le savoir].Now,to know is to know who and where,to know whose body it really is and what place it occupies for it must stay in its place.In a safe place.(注:Jacques Derrida,Specters of Marx:The State of the Debt,the Work of Mourning,& the New International,Routledge,1994,p.3,p.3,p.3,p.5, pp.3-5, p.9.)
我刚才说了,这里的重要的词语是——" to ontologize remains,to make them present,…identifying the remains and localizing the dead" 等等。
翻开一部词典,任何一个语词一般都会有好几种意义的可能性,然而,一个词语在某一特定语境中所呈现的意思,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仅要受到由它相邻语词所构成的语义张力的制约,而且还要由它所在其中的整个文本形成的那个语义场所决定的。我们究竟应该在什么样的语义层面上、在语义链的哪一个环节上去把握德里达的意思呢?是在语词的“本义”( literal) 层面,还是在语词的“象征”( symbolic) 层面?我们必须在逐次发现的这个语词的众多含义中,择取一个能够最恰切地纳入其所处语义场的意义,这本身其实也是“解构”批评最基本的操作。在德里达的上述话语语境里,所谓的" remains" 固然可以指死者的“遗体”,但也应指他的“遗物”、“遗产”,应该是指他“遗留下的所有的东西”。而在目下特定的语境里,不要忘记,还应该包括他的“精神遗产”。这句话中最为关键的一个意思,就是要把这些遗产“本体化”,也就是要从具体的“物”上升到抽象“理念”的层面,这样才能“使之在场”( make it present) ,在这里,顺便说一说,“使……在场”——其对立面是“不在场”( absent)——又是德里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而除此之外,德里达特别强调的是两点:一是" identifying the bodily remains" ,把遗物、遗产清点清楚了,把它的归属弄准确了,不要搞混了,不要把别人的——不是马克思的东西——加到他的头上;二是" localizing the dead" ,这里的" to localize" (被译者译成“确定死者的墓地”),是“使……明确其所由产生的地点和环境”,也就是“将死者(所处环境)加以还原”的意思。具体地说,就是要把马克思的思想遗产所由产生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搞清楚。这一点——即所谓“思想还原”的问题,非常的重要。我们在讨论对某种思想遗产的继承问题时,首先就是要将这一思想所由产生的历史和文化的语境还原,搞清楚是由于哪些具体的历史条件才产生了这样的思想。这其实也就是我们平日里常说的“要全面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题中之义。
这样,当我们在自己的语言库存中不断摸索,经过反复对比,终于找到了一个个最恰切的词义、并把这些词义串连起来之后,德里达所要讲的意思,就被凸现到了我们的意识的前台,用他自己的话说,也就是变成“在场”了,而用我们平日自己习惯的说法,那就是我们获得了一个恰当的、可以被接受的意义。
关于“灵魂、精神”的第二个要素,说的是“精神”的载体问题,即以“语言”或“声音”作为其存在的条件问题。“精神”尽管是抽象的理念,但它不能悬浮在空中,不能“魂不附体”,它仍需要有一个载体,一种使之成形的介质,这种介质就是“语言”或“声音”。
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就是那“东西”( the thing) 。德里达说,那“东西”——那“精神”,是要“做”的,要“起作用的”( it works) ,无论是它去改变他物,还是改变它自己,无论它是“成形” ( it poses) 还是“散形”( it decomposes) ,它一定得发挥它的作用:德里达说,这“精神之精神”(“要义”)就是“做”。什么是“做”?倘若它被假定为“精神的精神”,那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瓦雷里强调指出:“这里所谓的精神,我指的是某种变革之力……即精神……会起作用。”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马克思的那句著名的论断:“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这其实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思想理论”(即“精神”)的“能动性”。(注: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一版,第9页。)
德里达就是从这样的一个认识角度,先来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精神的当下处境,然后再深入一步,对“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作出他自己的回答。
当我们把德里达以上这段讲话如此这般地释读了一遍(这本身其实就已经是一种解构式的阅读)之后,我们就会明白,《马克思的幽灵》中译者们对于书名副题的理解出了多大的偏差。" the state of the debt" 中的" the debt" 指的是后人从马克思那里继承了他的思想遗产、因而是对他的一种“亏欠”;而这里的" state" ,显然也不会是“国家”——它无非是指我们继承了马克思的思想这样一种“状况”。
所谓“新国际”,德里达本人其实也是有解释的。当然,《马克思的幽灵》的译者在翻译此书时没有看到,所以他们按照字面的意义去理解当然也情有可原。就在南京大学的座谈会上,德里达也曾说到,他在加州大学滨河分校的那次演讲中提到的“新国际”,并“不是共产国际,它是超越国家,超越党派,甚至超越共和党和民主党传统模式的一种联盟,一种亲密的关系”。德里达此时用了" fraternité ( fraternity) " 这样一个词,座谈会的翻译将它译成了“博爱”,意思又稍稍有点偏了。我趋向于将它理解为相当于“同志会”那样的一种“亲密关系”。
德里达在南大的座谈会上是这样说的:
这个新国际应该提出一些具有促进意义的形式,互惠的或欢迎外族的形式——甚至超越斯多葛主义、基督教教义和康德学说中那种传统的共同的世界主义……新国际,将要求超越公民身份,因而必然超越民族国家。……(注:《德里达中国讲演录》,第94页。)
照此看来,德里达所谓的“新国际”,乃是他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一种认识,是他按照自己的理解,共产主义在当代新的历史条件下演变成一种新的形态:它超越了历史上任何形式的世界大同理念——斯多葛主义、基督教教义、康德的世界主义,也超越当下公民社会中的公民身份,超越了当下民族国家中的民族身份等等。所谓的“新国际”,于是就成了德里达对时下所谓共产主义已经消亡这一说法的一个回答。当年我们翻译《国际歌》中的" International" 一词,就没有把它译成“国际”,而译成了“英特纳雄耐尔”,为什么?因为它不是指一个“国际组织”,而是指一种世界大同的“理想”,一种相当于“共产主义”的理想,德里达在这里提出" the New International" ,看来还是译作“新英特纳雄耐尔”更好一些。当然,按德里达的说法,这里面还有许多复杂的情况,如关于“主权”的问题、关于“全球化”(世界化)的问题等等,限于篇幅,这里不再逐一详细地讨论。
现在,我们回过头再来简要地归纳一下“解构”批评(阅读)究竟应该怎么进行。
首先,与从事任何一种批评一样,要能够做到这一点,要能够对一个文本进行“解构”,最关键的一条是自己要有原创性的思想。这种思想其实并不是属于所要阅读的文本本身,而是你自己头脑中原有的。例如,德里达在这篇讲演中所表达的想法——他对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所发生的变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前途、它今后的走向,都有他自己的思考,形成了他自己的想法,比方说,他对于Francis Fukuyama(福山)提出的所谓“历史终结论”,所谓全世界日后都将发展为统一的市场经济;他对于丹尼尔·贝尔( Daniel Bell) 提出所谓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所谓后工业社会将成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的一统天下;对于这些观点,他都有自己的看法——与众不同的、独特的看法,原创性的看法。我在这里想要强调一点:这种看法其实与“解构”毫无关系——并不是说你懂得了“解构”,你就自然而然地会产生这样那样闪光的思想。思想是一个人的经验的产物,是我们对于自己所直接经历的——当然更多是对间接的经验进行思考,并将这种思考提升到一个新的思想层面,形成新的认识和判断。
那么,“解构”与原创思想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如果我们把包裹在“解构”外面的一层神秘性揭去,我们不妨说,“解构”无非就是对刚才我们所演示的在“文本中穿行”式阅读法的一种外包装。具体地说来,就是我们先前引用高宣扬所讲的,要学会一种在不同文类的文本中穿行的本领,把古往今来的各种各样的文学文本当作自己思想和创作的一片“田野”,我们从特定的文本中获得某种启示和灵感,对所面对的现实问题进行反思,通过对文学文本的释读来提出和表达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新的见解。
“解构”最令人眼花缭乱的绝技,其实也就是它在各种文学文本中的穿行。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德里达不断地返回到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的文本中,用阐释剧本的文学批评语言,来指涉、探讨我们所面对的对马克思主义思想遗产的继承和发扬的问题。而要能这样做,我在前面已经说了,首先就要有语言学、语义学、词源学等多方面的训练,从而能够熟练地掌握“新批评”所最擅长的那种阅读文本的本事。有了这一条,我们才具备了从事包括“解构阅读”在内的文字批评的能力。我们刚才不是对德里达的文本又做了一次逐字逐句的释读了吗,与此同时,我们对中译本的译文进行了批评,指出了其中的误读、误译,并分析了造成这些误读误译的原因。其中有宏观认识方面的原因,例如,译者没有把握德里达这篇演讲的基本主题,既然是讨论“马克思主义在今后的命运”,怎么能冒出“债务国家”的想法呢?其次,因为译者对具体词语的含义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例如" debt" 这个词,字典上给的基本释义的确是“债务”,但德里达这里谈的是“思想遗产的传承”,而那个“state”怎么说也不能是“国家”,而只会是指某种“状况”了。
在以上分析的过程中,我已经尽量多地给出了各个关键词语的理解可能性,这多种的理解可能,都是语词本身的语义可能性,德里达称之为" trace" ,即所谓“意义”的“印迹”,但是,阅读的过程其实并不仅仅是一个分解的过程,你必须在自己的头脑中不断地进行选择、比较,把不符合文本语义场需要的语义可能性摒弃,最后留下你认为能够最恰当地嵌入你所建构起来的语义场、最符合你的所要表达的意思的词义,然后,把这些词义串连起来,包括它们串连起来之后还可能申发出来的新的语义可能性,统统都汇总起来,加以综合,形成一个新的文本,一个能够表达你自己的原创性思想的文本。这才是文本的阅读和批评的全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