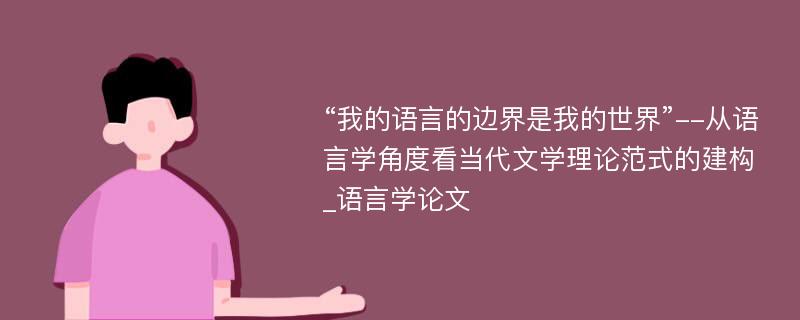
“吾语言之疆界乃吾世界之疆界”——从语言学转向看当代文论范式的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疆界论文,文论论文,范式论文,语言学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0;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0)09-0099-17
[主持人语]发生在20世纪西方哲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在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促使了把文学语言作为重心、把诗学与语言学结合起来的“语言学诗学”的产生。而作为一种语言实践的文学活动,实际上也是作家通过对语言的使用与读者进行有效交流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修辞行为。由此,“语言学转向”一方面促使了关注文学语言研究的“语言学诗学”的产生,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关注包括语言在内的“符号”有效使用的“修辞学复兴”。“语言学转向”与“修辞学复兴”的共同作用,已经对当代文学理论研究以至整个人文社会学科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后果,并共同推动着当今的语言学诗学研究。我们组织这次笔谈,就是想从不同角度考察一下在语言学转向这一大的背景下,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语言学、修辞学与文学理论研究相互关联的可能性有多大,以引起更多人对于这一问题的兴趣和关注,共同推进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
——主持人:赵奎英
20世纪是语言学霸权逐渐确立的世纪。语言学不但自身成熟了,而且雄心勃勃地征服了其他许多领域。也许因为文学向来是语言的家园,所以语言学与文学及文学理论的关系一直是令人感兴趣的话题。毫无疑问,回首20世纪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现代语言学对现代文学理论范式的建构作用。它既对文学研究具有启迪作用,提供了许多重要的观念和方法论;同时,语言学对文学研究也具有某种现代科学的奠基作用,进而成为现代文学理论的重要知识构架和基础。照美国文学理论家保罗·德曼(Paul de Man)经典性的看法,只有当文学理论家们抛弃了传统的非语言学方法,把文学研究完全建立在现代语言学的基础之上时,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学理论才出现。①依据这一说法,可以说,诸多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尤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为代表,都对文学理论范式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塞尔登直言,索绪尔的研究在建构现代文学理论的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②在我看来,就作为人文学科的文学理论而言,范式最重要的层面就体现在有关文学的基本理论假设上,它们构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学观念。
如果我们循着这个理路来考量20世纪的文学理论,那么,从俄国形式主义到布拉格学派,一直到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德曼的这一说法可谓一语中的。因为不难发现,今天有关文学的许多范式,从基本假设到概念范畴,从方法论到文本分析技术,相当多的资源都来自语言学。甚至有的学者断言,存在着一种作为文学理论的语言学,因为任何语言学都是一种解释的理论,不是说语言学有助于文学理论,而是从根本上看,语言学和文学理论是一回事。③
本文将围绕着语言学转向及其对现代文学理论范式建构的作用展开分析。
语言和世界之疆界
当我们说到现代语言学对各门学科和知识体系的影响时,一个频繁使用的说法是所谓“语言学转向”。诚然,语言学转向是从哲学史的角度提出的,它揭橥了哲学研究基本观念的深刻转变。或许可以把德曼的说法也看作语言学转向的一个重要说明,即这个转向不仅仅呈现为语言学进入文学研究,同时还表征为语言学对文学理论基本假设的建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语言学转向之所以在20世纪中叶被提出来,并引起广泛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其实还有更加复杂的含义。因此,回到提出这一说法的美国哲学家罗蒂那本影响深广的《语言学转向》(1967),回顾一下罗蒂如何界定这一概念的是很有必要的。罗蒂认为,“语言学转向对哲学的独特贡献……在于促成了如下转变,那就是从谈论作为再现媒介的经验,向谈论作为媒介本身的语言的转变”④。简单地说,语言学转向的深义就是从传统上分析经验本身的哲学方法,转向了对构成这些经验的媒介——语言——本身的关注和思考。传统上哲学家们热衷于谈论时代精神、世界观、文学观或文化经验等,并把这些经验作为哲学、美学、甚至文学研究的焦点问题。如今,在语言学转向的推动下,哲学家们意识到一个深刻的转型,那就是问题的焦点不是如何发现和界定经验,而是经验如何通过语言得以呈现,并借助语言加以讨论。即是说,经验是由其媒介——语言所建构的,假如我们一味地追寻经验本身,却忘记了构成经验的语言,此种研究理路无异于缘木求鱼。显然,这一重要的基本理论假设彻底改变了哲学,它彰明昭著地体现在分析哲学的理论中。
当然对文学研究来说,语言的重要性比较容易看到。因为文学本来就是一种语言或特殊的语言现象,讨论文学就不可避免地要讨论语言。但是,当人们把焦点集中在文学经验(意象、风格、主题、时代背景等)层面时,对语言本身的反思却悄悄地溜走了。因此语言学转向要求研究文学首先要转向语言,关注语言,搞清语言,在此基础上才能进入文学经验世界。所以说,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是否思考语言,而是一个观念性的根本转变,那就是语言是一切文学经验甚至解释这些经验的理论观念的建构路径。没有语言,我们既没有文学,也无法谈论文学。当这个观念引入文学研究时,则使后者的基本假设和范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我看来,语言学转向最为核心的观念并不在于谈论或关注语言,这一转向革命性的理念在于必须把语言看做是文学及其知识甚至实在建构的前提条件。关于这一点,维特根斯坦如下说法最为传神:“吾语言之疆界乃吾世界之疆界。”⑤维特根斯坦的这句话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首先,我们的世界不是无限的,它具有某种边界或疆界,是一个有限的世界。其次,这个世界的边界何在呢?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空间和时间的边界吗?古代山水画家师法自然,在其有限的生命存在中遍访名山大川,即便如此,他们的时间和空间仍是有限的。显然,维特根斯坦这句话所说的疆界并不是指这种意义上的时空边界,而是由语言所决定的我们身处其中无法脱离的文化。今天,我们可以乘飞机到达五大洲,还可以更快地通过网络来与远方的朋友实时交流,哈维所说的通讯和交通技术带来的“时空压缩”早已成为现实。⑥但是,不论你到哪里,不论你与谁交流,你都受到你自己的观念、价值、文化的影响。而造成这一影响的最重要的工具就是语言。所以维特根斯坦实际上是强调,你有什么样的语言,就会接受什么样的文化,这也就决定了你的世界的边界在哪里。语言学转向的要旨就在这里!如果我们用造型艺术语言来说明,可以明晰地揭示个中三昧。在解释为什么不同文化所熏陶的画家面对同一自然景观会画出不同的画时,艺术史家贡布里希说得很精彩:“画家是倾向于看他要画的东西,而不是画他看到的东西。”⑦这段话和维特根斯坦的说法相得益彰,互为阐发。画家不会看什么画什么,而是看他要画的东西。这要画的东西当然不是自然而然地建构起来的,按照贡布里希的说法,是一种艺术史传统中所形成的绘画“图式”使然,画家就是通过习得的“图式”来选择要画的东西。把这个原理转到语言学和文学研究上来,我们可以在同样的意义上说,任何人都是以其语言所建构的文化和认同的“图式”来理解世界和自我的,“图式”就是语言习得的必然产物,它决定了我们自己的世界之边界。更进一步,在文学研究领域,这些“图式”也就是我们有关文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假设。
那么,语言学转向究竟是如何改变了我们关于文学的基本理论假设的呢?
理论假设的语言学转向
语言学转向只是描述了现代哲学的一个大的语境。我们更为关心的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文学理论发生了何种变化?换言之,语言学转向是如何界划我们文学世界以及文学知识世界的边界呢?这些边界对我们的文学研究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知道,理论研究通常是以假设和命题的形式呈现的。所谓文学理论或文学观念,通常是呈现为一些基本的假设。科学哲学家库恩曾经以范式概念来表述科学知识系统:“一个范式就是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而反过来,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共有一个范式的人组成。”⑧具体说来,范式包括术语概念、形而上学、价值观和研究范例等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在文学理论中都存在,如果我们用更简单的表述来说,它更集中地呈现为研究者有关文学的基本理论假设。接下来,我们需要进一步考量,在语言学转向过程中,我们有关文学的基本理论假设有哪些重要的转变?
文学历来被认为是民族历史的写照和文化的史诗。诗人和作家笔下的作品通过富有诗意的文字记录过去,蕴涵了丰富多彩的意义。文学作品就像是一个容器,只要我们打开它,那意义便向我们敞开。页面上的文字或口传的文学,其书面符号或有声言语通过其物质性的符号,自身含有并传达出特定的意思。批评家们常说,某个作品中的某种思想和感情“力透纸背”,即是说,在页面文字后面,实实在在地存在着某种概念、思想、感情或意义。无论过去现在,无论张三李四,本土和异邦,当我们遭遇这些作品时,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并理所当然地获有并体验到那些意义。
在语言学转向中,这些看似合乎逻辑的文学理论假设经受了严峻的挑战,受到了强有力的质疑。语言学转向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许多看似自然合理的看法,使许多原本看似合乎逻辑的基本假设变得不合逻辑了。以下,我们通过分析当代文学理论的四个重要的基本理论假设,来审视语言学转向是如何转变了当代文学理论范式的。当代文学理论可谓学派林立,观点多元。尽管在比较的意义上说,不同学派有不同观点,但是,我们这里关心的不是某一学派的一孔之见,而是那些带有较大影响被文学研究共同体较多成员所认可的那些理论假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这些假设规定为基本理论假设。
基本理论假设一:意义不是给定的或预先存在的,而是由差异造成的。
我们知道,文学活动相当程度上可以视为一种意义的生产、传播和诠释活动。无论古典作品还是当代作品,无论诗歌还是小说,意义的生产是最重要的一环。如果说文学离不开意义,那么,接踵而至的问题是意义在哪里呢?它们又是如何形成的?
关于这个问题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看法,但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语言的意义是由差异构成的。这一论断对于当代文学理论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观念,它造就了今天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判然有别于传统文学理论。根据索绪尔的看法,不同的词语和声音,在特定的句子和语音关系中,形成特定的意义,这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重要发现。由这一原理进一步推论,符号的能指(物质形式)和所指(概念)之间并没有稳定的一成不变的对应关系。再往下推论就可以得出当代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假设:符号其实是具有任意性的,意义是人为地假定的。任意性指出了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关联是人为地形成的,词语、声音和概念之间的关系不是预定的和先在的。既然没有什么是预先规定好的,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那么,意义就像是隐而不现的幽灵,只有通过差异才能显现。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差异产生意义原理表明了一个重要的道理,那就是意义说穿了乃是某种关系的产物,这种差异关系决定了意义从根本上看是一种相对性的产物,并不存在固定不变的意义,由这一原理带来的转向是巨大的,它颠覆了那种把意义看做是文字背后的实体的传统观念。更重要的是,差异产生意义的假设彻底抛弃了任何绝对的、客观的和稳定不变的意义存在的形而上学。回到前面我们提到过的“力透纸背”这一常见的表述上来,所谓的“纸背”后面其实并没有先在的、恒定的意义。“纸背”后面有什么最终将取决于语句关系的差异性。如果我们更加宽泛地理解差异产生意义的原理,那么,差异性不仅是指文学文本语言关系中的差异性,它还包含了解读文本的更为复杂的多种差异性,从历时差异到共时差异,从个体差异到族群差异,等等。当关于文学意义的形而上学观念被差异关系的相对性观念所颠覆时,一系列更多的转向应运而生。
基本理论假设二:词语是多义性的,文学的词语更具歧义性和含混性。
由第一个假设可以推导出这个假设,那就是说,任何词语的意义有赖于特定的语境,更进一步,词语生动活泼的多种用法改变了其只有一个辞典意义的局面。实际上,在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里,日常语言中的词语所要表达的意思通常取决于特定的语境及其差异,它们通常会超越了辞典的意义而显得丰富多彩。这种现象在文学中更是如此,因为文学表述所以有别于日常语言和科学语言的表述,其所谓的文学性就在于越出了规范的辞典意义。从俄国形式主义到捷克布拉格学派,再到英美新批评,现代文学理论的基本观念就是建立在这一假设基础之上的。歧义、含混、多义、衍生、误读、多元等概念所以在现代文学理论中如此流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理论范式的转变。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强调诗歌语言“陌生化”技巧,捷克布拉格学派的穆卡洛夫斯基关注诗歌语言不同于规范语言的“突出”效果,英国新批评的代表人物之一燕卜逊的“含混七型”的分析,美国新批评派关心的反讽、张力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触及这个问题。语言哲学家们也发现了这个道理,比如法国哲学家利科通过比较发现,科学语言就是“系统地寻求消除歧义的言论策略”,而诗歌语言正相反;它力求保留歧义性,以使语言能表达罕见的、新颖的、独特的而非公众的经验,所以,(诗歌的)“目的在于保护我们的语词的一词多义;而不在于筛去或消除它;……同时建立好几种意义系统,从这里就导出了一首诗的几种释读的可能性”。⑨如果说差异产生意义强调的是意义取决于具体语境或上下文关系的话,那么;多义性则从内部彰显了语言自身的意义生产潜能。尤其是文学语言,它本身就存在着潜在的多义性,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歧义和含混现象的出现。当代文学理论对这一点非常关注,并从这一观念出发,避免文学解释中任何可能的独断论和一元论,这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理论的共识。
基本理论假设三:作品是一种物质存在,文本才是文学研究的表意对象。
既然意义不是预先给定的,既然词语本身就有多义或歧义的潜能,那么,对这些意义的解释就成为文学研究的焦点问题。就文学理论而言,语言学转向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文本及其观念的出现,如果用巴特的说法,就是“从作品到文本”。虽然有时我们仍在同义词上使用“作品”和“文本”两个概念,但这两个概念其实有很大的差异。晚近“文本”概念的流行,其要旨不在于它可以和“作品”概念互换,确切地说,是“文本”概念取代“作品”概念。历史地看,后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所以青睐“文本”概念而摒弃“作品”概念,其中观念上的重大转变是对两个概念作出了全然不同的规定,正是透过这一规定我们看到,语言学转向究竟转变了什么。
以巴特的说法来分析,所谓作品不过是放在图书馆书架上的一个物质性的东西,是一个自在的物品;而文本则全然不同,它属于一个方法论的领域,是一种语言活动的产物。借用克里斯蒂娃的说法,文本具有生产性,而作品则没有这种生产性。所谓生产性,就是意义的生产。巴特在追溯“文本”概念的拉丁文本义时,特别指出了它是指编织物,而文学文本在许多方面就像是一个典型的编织物。首先,文本从来不是孤立的自在的,它更多地呈现为编织物那样的网状结构,这就是今天我们用“互文性”概念所要表达的意思。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网状地连接在一起,因此,就像意义是差异产生的相对关系性一样,任何文本都是处在与其他文本之间的差异关系之中。脱离了这种互文性的网状结构,文学意义就不复存在。其次,在巴特看来,传统的中心化结构被网状结构的编织物观念所取代,这说明一个作品具有一个特定意义本源的形而上学观念寿终正寝了。于是,巴特惊世骇俗地提出“作者之死”的宣判。在他看来,“作者之死”同时就是“读者诞生”。因为现代“作者”概念是著作权之法律意义上的产物,但是他不能成为文本之起源或意义上的根源。换言之,巴特是通过打破起源意义上的神学—作者偶像,来进一步颠覆任何把文本意义归诸作者意图的传统文学研究方法。他特别指出,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到现代音乐对批评家阐释的依赖性,再到意义生产中无数读者的“多样性”,作者作为文本意义垄断者的观念失去了合法性,各种以作者意图来解释作品意义的方法也就变得可疑了。所以巴特特别关注他所说的“可写的文本”,即把读者的阅读同样视为写作一样的意义生产活动,这就赋予读者在意义建构过程中更多的主动性与合法化。如果说“互文性”概念揭示了文本之间的依赖关系所产生的网状结构是意义的场所的话,那么,把作者的起源和解释的特权还给读者,则是彰显了文本对阅读的依赖性和文本意义生产对读者的开放性。一个上帝式的作者被无数多元化的读者所取代,文本从可读的向可写的转变,读者从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文学的写作者,这无疑是语言学转向对文学知识体系建构的巨大贡献。
基本理论假设四:文学是主体之语言建构的产物。
从索绪尔关于符号的假定性和人为性出发,差异产生意义,意味着语言中并不存在什么永恒不变的东西。这一命题进一步的结论是,人创造了语言,同时也被语言所创造。今天,常被提及的一句名言是德里达说的“文本之外无他物”⑩。乍一看来这话有点不合情理,但德里达的意思并不是说文本之外一切都不存在,而是说我们关于一切的看法和理解都是通过语言活动的文本建构起来的。文本不仅仅指文学,还包括我们生活世界中的一切事物。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到晚近的后结构主义文学理论,语言学转向实际上已经发展成颇有影响的语言建构论,其原理可以广泛地用于诸多领域,当然更适用于文学领域。依据这种理论,任何人在使用语言时都在习得相应的观念和范畴,共享一种文化和语言的人每天都在再生产这些观念和范畴。这就意味着一个人的思考方式,提供给他的理解框架的概念和范畴,都不可避免地是通过他使用语言而获得的。因此,语言乃是我们思考的前提条件。(11)文学理论家们则把这个说法具体化为如下陈述:语言本身控制、限制和预先决定了我们所看到的东西。一切现实都是通过语言而建构起来的。所以,没有什么东西会以一种无可置疑的方式存在。一切都是语言学/文本的建构。语言并不记录现实,它是塑造或创造现实,所以,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文本的世界。(12)
如果以这样一种观点来看文学和文学知识,建构论实际上是把传统上我们认为是自然而然的,或者认为是必定如此的种种文学观念和范畴,看作是有语言运用的过程中所人为习得的,因此,对语言的思考,也就破除了自然而然和必然如此的许多先验的假设。回到索绪尔语言假定性和人为性的命题上来,可以说我们文化中的一切都是人为的和约定的,文学亦复如此!这一观念给我们带来了思考文学中的一切问题的革命性转变。当上帝式的作者死去时,当垄断文本意义的唯一本源消失时,当意义在差异中产生并总是呈现为多义性时,语言学转向把语言的复杂功能揭示在我们面前,文学解释这一文学研究最基本的活动变得异常复杂了。结果是文学研究者更加自觉地体认到,社会、文化、自我、他者、认同、族性、文学、意义、经典、解释、风格、文学史……这一切没有什么是预先给定、一成不变的,说到底,它们都是在我们的语言使用中被建构起来的。因此,文学研究的思考中心就不再纠缠于这些范畴是什么,而是这些范畴是如何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被建构的?这些建构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最后,我们再次回到维特根斯坦的著名陈述上来——“吾语言之疆界乃吾世界之疆界。”文学研究在语言学转向的启迪带动下,就是通过探究“吾语言之疆界”,来探索“吾世界之疆界”。看到这些“疆界”的存在,也就放弃了任何先在的、给定的预设。文学研究中一切都不过是暂时的、地方性的假设而已,有了这样一种观念,我们看待文学和我们自身的方式也悄悄地就发生了变化。古希腊人曾说“太阳底下没有什么常新之物”,透过语言学转向的视角来看,这种说法就变得大可质疑了,因为变化了的眼光看到的正是变化了的文学及其知识建构。
注释:
①Paul de Man,The Resistance to Theor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6),p.7.
②See Roman Seldon and Peter Widowson,A Reader Guide's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Lexingtong;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93),p.104.
③Allen Schauber and Allen Spolsky,The Bounds of Interpretation:Linguistic Theory and Literary Tex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2.
④Richard Rorty,ed.,The Linguistic Turn(Chicago..University Press,1967,1992),p.373.
⑤Ludwig Wittgenstein,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London:Routledge,1961),p.68.
⑥参见[英]哈维:《后现代的状况》,第300—303页,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⑦[英]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第101页,范景中等译,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98。
⑧[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159、158页,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⑨[法]利科:《语言的力量:诗歌与科学》,见胡经之、张首映主编;《20世纪西方文论选》,第3卷,第30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⑩Jacques Derrida,Of Grammatology(Baltimore: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7),p.163.
(11)Vivien Burr,Social Constructionism(London:Routledge,1995),p.8.
(12)Peter Barry,Beginning Theory: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 (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2),p.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