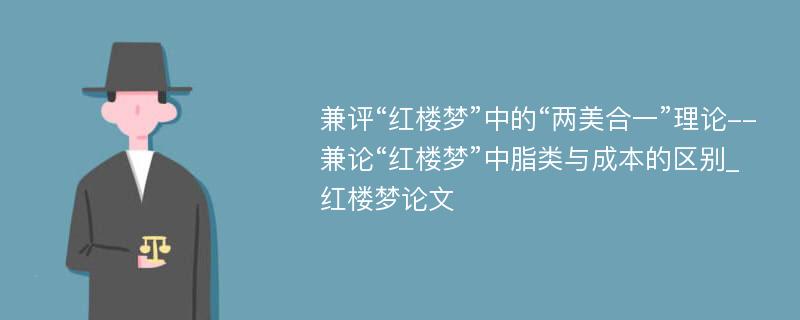
重评“二美合一”说——兼论《红楼梦》脂本、程本之差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楼梦论文,差异论文,二美合一论文,兼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美合一”说是《红楼梦》讨论中的热点之一。它牵涉到曹雪芹原稿的根本构思的思想倾向与审美情趣,是解读“文本”和探寻脂本、程本不同面目与性质及作者思想取向的重要命题。
百廿回程本《红楼梦》流行近两个世纪,这个“二美合一”观念一直被湮没而未能发现。本世纪初叶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发表倡立新红学,俞平伯在这个基础上所作《红楼梦辨》中提出了钗、黛二人“双峰并峙,二水分流,各极其妙,莫能相下”的“二美合一”说。50年代评红运动中此说受到了批评。时过境迁,直到八九十年代的有关论著,甚至在为俞先生平反的论著中,仍将“二美合一”说看作是俞的“局限”。这是很为奇怪的。足见此说误解尚深,有予以澄清之必要。
一、“二美合一”体现在八十回“文体”之中
首先,“二美合一”现象不是出于任何人的臆想或“伪托”,而是出现在《红楼梦》八十回“文本”之中,是曹雪芹原著的“原意”。
太虚境册子诗画中诸人都是一人一诗一画,惟钗、黛二人合一诗一画。画是钗、黛并列。诗中的“玉带”、“金钗”与“停机德”、“咏絮才”,难分轾轩。《红楼梦曲》的《终身误》中,作者将“金玉良缘”的“木石前盟”、“山中高士”与“世外仙姝”两两对峙,并在《引子》中唱出这套“声韵凄惋,竟能销魂醉魄”曲调的主旨是:
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
同回中,警幻许宝玉为“闺阁良友”,将其妹名“兼美小名可卿”的“许配”他。此女是“其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脂砚批云:“难得双兼,妙极!”“乳名兼美处”,脂批云:“妙,盖指林,薛而言也。”同回,介绍宝钗出场处,又有脂批云,“按黛玉、宝钗二人,一如春花,一如纤柳,各极其妙。”第五回是全书之总纲,作者用暗示、隐喻、象征的手法预示了书中主要人物的悲剧命运。作者这种“二美合一”构想,不抱成见的读者是能够看得到的,脂评不过起了“点破”的作用而已,并非对作者原意的“歪曲”。
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钗、黛二人展开了“各极其妙”的如火如荼的描写。如“比通灵”回写宝钗的“微露意”和黛玉的“暗含酸”;“省亲”回写宝钗教宝玉将“绿玉”改成“绿腊”和黛玉代宝玉作《杏帘在望》一诗;“箴宝玉”回写宝玉续《南华经》将“宝钗之仙姿”与“黛玉之灵窍”并比;“悟禅机”回写黛玉续成“无立足境,方是干净”,令宝玉惊服,宝钗比出五祖传六祖的两偈,使宝玉赞她“无书不知”;“滴翠亭”回写黛玉“泣残红”与宝钗“戏彩蝶”对比;“蒋玉函”回写宝玉在黛玉前为“金”、“玉”发誓,又写他见到宝钗“雪白的胳膊,不觉动了羡慕之心”;“情中情”回写宝钗见宝玉伤势“红了脸低下头去”,又写黛玉“两眼肿得桃儿一般,满目泪光”;同回写宝玉送手帕给黛玉,黛玉写了“定情诗”,又写宝钗代绣“鸳鸯戏水”兜肚“梦兆绛芸轩”;“海棠诗社”回写宝钗诗“含蓄浑厚”评为第一,又写黛玉诗“题目新,诗也新”而“魁夺菊花诗”……。这种写黛玉跟着必写宝钗,写宝钗跟着必写黛玉的现象,在八十回中随处可见,比比皆是,历来都从钗,黛对立、冲突着眼,如果换个视角,这种处处“林、薛二人”并称,一以“仙姿”,一以“灵窍”;一以“春花”,一以“纤柳”;一以“停机德”,一以“咏絮才”;一以“蘅芷清芬”,一以“潇湘碎影”……这不正是“双峰并峙,二水分流,各极其妙,莫能相下”么!
如果说,在百廿回程本长期流行影响下,我们对上述种种只看作是爱情角逐场上你争我夺、旗鼓相当的描写,而忽略了那“兰菊竟芳”、“晋楚争长”、“环肥燕瘦”各尽其妙——“二美合一”的构思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兰言解疑癖”(第42回)和“互剖金兰语”(第45回),这两回中大写特写钗、黛和好而非冲突的情节仍视而不见,甚至见而予以曲解,就显出了成见与偏见的误人之深与害人之甚。黛玉在筵席上说出:“良辰美景奈何天”和“纱窗没有红娘报”的“淫词艳语”,这是贾母所说“鬼不成鬼,贼不成贼”的“大罪状”,得入“贼情一案”(第54回)。在强化文化钳制大兴文字狱的当时,特别是在贾府这样所谓“诗书传礼之家”,黛玉所说《西厢记》、《牡丹亭》词句其性质之严重,与“文革”时期“反动言论”有近似之处。“无书不知”的宝姑娘深知此中奥秘,这样的“淫词艳语”出于“林妹妹”这个“主子姑娘”之口,如果她真以黛玉为敌的话,只需稍加扩散或通过袭人这条热线传入“太太,老太太”耳中,就可置黛玉于“身败名袭”,不能在贾府中“做人”的地位。这正是天赐宝钗的良机,但宝钗没采用“告密”或“扩散”的手段,而用“兰言解疑癖”——玩笑谈心的方式劝告黛玉,并坦诚相告自己也偷背着父母看《西厢》、《瑟琶》、《元人百种》乃至“无所不有”的“杂书”,再谈到自己的“读书观”,最后劝她不要因看“杂书”而“移了性情”(第42回)。这“一席话,说得黛玉垂头吃茶,心下暗伏(服),只有答应‘是’的一字”,并引出了《金兰契》回中黛玉的剖心相示的一番话:
“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有心藏奸。从前日你说看杂书不好,又劝我那些好话,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细细算来,我母亲去世的时候,又无姐妹兄弟,我长了今年十五岁,竟没一个人像你前日的话教导我……比如你说了那个,我再不轻放过你的;你竟不介意,反劝我那些话,可知我竟自误了。”(第45回)
黛玉在宝钗对这个关系自己身价性命至关重要的问题上采取的友好态度中,看到了她不是“有心藏奸”,而是“宽厚待人”。她说易地而处自己“再不会轻放过”她的。黛玉这种虚心自责,真诚待人的态度,显出一种罕有的思想、心灵美,宝钗这种与人为善,大度包容的态度,也显出了一种道德、精神美。撇开“封建反封建”观念,宝钗这是“君子爱人以德”,在大节上帮助人。黛玉也深感这是“善意的关怀”,故尽弃前嫌和她结成“金兰契”而“剖金兰语”,达到钗、黛和好——“二美合一”的境界。这一对爱情角逐中不可共存的生死冤家如此握手言欢,剖心相示的场面显出的美,为古今中外小说所罕见。
在“兰言解疑癖”、“互剖金兰语”两回中出现钗、黛和好后,双方矛盾冲突戛然而止,进入了一个“无差别境界”。钗、黛这种“化干戈为玉帛”关系的改变,引起了宝玉的纳罕,他借《西厢》“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一语相询时,黛玉表白说:“谁知他竟真是个好人”(第49回)。应充分理解黛玉在宝玉跟前称颂宝钗的份量。——薛姨娘还挪至潇湘馆和黛玉同房,“一应药饵饮食,十分经心,黛玉感戴不尽,以后便亦如宝钗之称呼,——连宝钗前亦直以‘姐姐’呼之,宝琴前直以‘妹妹’呼之,俨似同胞共出,较诸人更似亲切。”(第58回)王希廉评道:“钗、黛两人亲爱逾常,随地皆见敦厚。”钗、黛这种“和好”或者说“合一”的关系,仅仅用宝钗“扯起孔孟之道的破旗,气势汹汹地向黛玉进攻”,或者说是宝钗以“攻城为下,攻心为上”的心理攻势,“瓦解了黛玉的精神防御”,而使黛玉“上当受骗”,就可以解释得通吗?未免将复杂的生活艺术现象理解得过于简单了吧!
从上举例可知,大量“钗、黛和好”或“合一”的描写存在于“文本”八十回之中,并且关涉到作品整体性构思与思想、审美的取向。脂本、脂评所提示及学者考证、探佚及“新补”、“新续”、“新作”均是依据“二美合一”构思作为中心杠杆而生发开去的。毫无疑问,这是曹雪芹的“原意”,是非曲直,只能由曹承当。附带说一句,这也足以证明所谓脂本、脂评乃“伪托”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没有根据的。
二、平心静气论钗、黛
为进一步探寻“二美合一”构想,须对钗、黛二人作出实事求是、平心静气的探讨。就为“闺阁昭传”——“为十二金钗作传”的旨意来说,这两个女主人公的重要性,较男主人公贾宝玉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在《红楼梦》论争中,有关似褒似贬的贾宝玉这个“怡红公子”或“绛洞花王”的论辩,往往被“左钗右黛”与“右黛左钗”的声浪所淹没。而有关贾宝玉的评估又往往不能不牵涉到钗、黛之争这个纠葛点上来。自红学史最早记载的“一言不合,竟挥老拳”至今,钗、黛一直是《红楼梦》讨论的中心论题,“拥林”与“拥薛”双方往往夹杂着太多的情感因素及种种误解与偏见。程本流行后,焚诗绝粒,黛死钗嫁诸情节赢得了读者倾泻的热泪,宝钗处于尬尴地位,拥林派大为得势。尽管拥林评注家也说宝钗“有才有德”[①]、“小心谨慎、大度优容”[②],但自“败夫走卒”到“博雅君子”中,拥林派占着压倒的优势。“封建与反封建”观念引入后,林黛玉成为“反封建英雄”,薛宝钗成为“卫道夫子”,拥林派的统治地位愈来愈巩固,形成了固定的思维模式。
“二美合一”说的出现,犹如在平静的湖面上投入一块巨石,扰乱了一池清水。用俞平伯先生语言说:这个说法是大大“得罪读者”的,它无异是对占统治地位“拥林派”的挑战。50年代的评红运动剔除政治因素外,又是传统拥林派对这个挑战的反扑与围攻。70年代末以来又发生变化,“二美合一”说虽尚称为“局限”,薛宝钗的名誉却渐渐上升,在许多论著,尤其在“新补”、“新续”及电视剧中都得到较为肯定的评价,甚至成了“正面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作品中的林黛玉虽刻骨铭心地爱着贾宝玉,但在那“万恶淫为首”的统治观念重压下,男女爱情是“主子小姐”身份的最大禁忌和最危险可怕的东西。一旦涉及,便“满腹文章,也算不得是佳人”,堕落到“鬼不成鬼,贼不成贼”的“父母国人皆贼之”的地步。明乎此,则知黛玉虽深爱着宝玉,却不敢去踏这个雷区,不敢说,不能说,只能寄希望“外祖母”替她“作主”,让非法的“爱情”借合法的“婚姻”形式实现,否则只能以身相殉。所以出现了这种“一步一回头”的矛盾心理。这与其说是黛玉的软弱,不如说是“主子小姐”的软弱更为恰当。——这正是钗、黛间“金兰契互剖金兰语”的思想基础。她们是在认同传统礼法和应守“主子姑娘”身份的“共同点”上“和好”、“合一”起来的。这种害怕、禁忌男女爱情的观念,又正是出自创造钗、黛的“上帝”曹雪芹的思想中。他开卷宣称不写“淫邀艳约,私奔投盟”的“男女爱情”。对那并非“主子小姐”的尤三姐用“淫奔女”、“老辣无耻”、“嫖了男人”一类贬义词。在“十二金钗”的排列中,可以说,正册无寒门,副册无贵族。正十二钗只能由“主子小姐”充任,甄英莲虽出身世家因沦于“奴才”,也只能列入“副册”。这说明曹雪芹这个“曾经严父明师之教训”的“大家子”或“世家子”对男女爱情的禁忌恐惧,与其笔下的“林妹妹”有相似之处,故作品中出现了这样的矛盾现象:既写了“从未发泄”的“儿女之真情”的“大旨言情”——“颦颦宝玉两情痴”的男女爱情,又要把它纳入“风月鉴”反面“红粉骷髅”的“风月劝戒之旨”的轨道。这种“欲行而趑趄,欲言而颞飘”的态度,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即作者的思想是矛盾复杂的,故体现出那种“似谲而正,似则而淫”[③]的文风。
排除种种成见、偏见,以“文本”的形象实感出发,林、薛二人的“可爱”与“可恶”之处究竟是什么?撇开种种“灵窍”、“仙姿”或“停机德”、“咏絮才”之类,用最简约的语言来说,黛玉用一个“真”字,宝钗则用一个“贤”字可以形容。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赞美、向往真,从心底喜爱真。真,就是美,就是善,是价值判断的标准。“真”的反面就是“伪”,而伪和“奸”、“诈”是联系在一起的。黛玉的纯情率性,赤忱无私,有如孩子一样率真——即有李贽所说的“童心”,“童心者,真心也……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假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④]黛玉就是这样一个“真人”。宝玉也是个“真人”,他的种种“囫囵不解的小儿之语”(脂评)正是“童心”的流露,故只有“颦儿可与一对”(同上)。——他们之间爱情的感人之处就在这个“真”字上。但是,“假作真时真亦假”,如脂砚所说“一回卖去三个假,三天卖不出一个真”。绝对的“真”不但在当时,就是在任何社会,家庭或个人交往中也往往难以完全做到,有着相对的不可实现性,因为人,是“社会关系之总和”,不可能完全任性行事。宝钗的“贤”的性质比较复杂。相对而言,“真”是自我的坦诚流露,故黛玉孤芳自赏,绝世超尘;“贤”是人际的界定,往往自我压抑造成自我失落。宝钗八面玲珑,面面俱到,将少女青春的萌动扼杀在“礼法”的冰窖之中。我们在思想感情上都肯定“真”,但在生活实际中又不能不赞许“贤”。像涂瀛那样拥林大家。极度赞美黛玉的人品才情为《红楼梦》之最,但他选择配偶时却愿得宝钗“妻之”[⑤]。在人生审美追求上,优美纯情、率真的颦儿,成为我们梦想中的伴侣,精神上的情人;在生活实际中豁达大度、八面玲珑、并善于顾全大局的宝钗则又是更好的伴侣,愿得而“妻之”。从这个视角看,“拥薛派”也有其振振有词之“理”。
不过,文学是人学,写的是人。人的心灵之真、之美与人性之丰厚与芬芳,恰恰表现在人的心灵层次的自我觉醒与人生梦想幸福的执着追求,甚至不惜生命孤注一掷方面。黛玉同宝钗相比,不及她丰美,不及她博学,不及她豁达……但在对宝玉爱情的执著的追求上,虽带着扭曲的形态,但那以生命孤注一掷的勇气与决心,正如黑格尔论朱丽叶那样:“空然间我们看到这个心灵的全副坚强的力量……好像一朵玫瑰突然放蕊,每一片花瓣和每一条皱纹都显出来了,又好像潜伏在心灵深处的一股清泉突然源源不断地迸射出了……这是一点火星点燃的火炬,一朵刚刚用爱情触动的花蕾突然呈现为一朵盛开的鲜花。”[⑥]林黛玉在爱情追求上的热烈、赤忱、执著和以生命作代价,不亚于朱丽叶之热恋罗密欧,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是罕见的。何其芳说《红楼梦》的价值在于:“我们好像从里面呼吸到青春的气息”,它让我们的心灵“受过了一次洗礼,开始知道在异性之间还可以有一种纯洁的痴心的感情”[⑦]“它在描写爱情生活上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界。”[⑧]严格地说,历来小说所写男女相悦只限于生理和世俗层次的性爱和婚姻,而少触及心灵和思想层次的自由爱情,这又集中体现在林黛玉的爱情觉醒及其执著追求的动人描写上面。这是林黛玉思想性格的亮点,也是全书的亮点。薛宝钗尽管被曹雪芹赋予了很多的优点,成为“艳冠群芳”的“牡丹花王”,但作者却吝于给她一点黛玉那样的自我觉醒与追求。使之变得“冷面冷心”,把一切人欲规范在“循规蹈矩”的礼法之中,“待人接物不疏不亲,不远不近,可厌之人亦未见冷淡之态形诸声色;可喜之人亦未见醴蜜之情形诸声色。”[⑨]过多地压抑扭曲自己,封闭自己,好像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封建礼法而活着,与黛玉相比,就少了一点灵气、热气和活气。黛玉纵有一百样“缺点”,但在执著的爱情追求上打动了读者的心弦,也就赢得了读者的同情和爱。反之,薛宝钗哪怕有一百样“优点”,她的冷,她的“无情”和心灵的封闭,也许得到人们的敬佩,但无法得到人们的同情与热爱。从这个现象看,喜爱黛玉而憎恶宝钗就有其心理的依据。
宝钗认同、恪守的封建礼法随着时代的进步,愈来愈显出其负面意义,她的引起人憎恶的情绪也愈来愈强烈。如宝钗在贾母、王夫人前的奉承讨好在当时是当着“承欢膝下”——“行孝道”的“美德”而肯定的。但在今天的读者看来是向权势的趋奉,甚至是为争取“宝二奶奶的宝座”。有人说她“虚伪”,我们认为她主观上并不“虚伪”,而是恪守封建礼法,那是“主子小姐”的“本分”。她衷心服膺并身体力行做到“大德不逾闲”的地步,接济邢岫烟,团结史湘云,交好花袭人,劝戒林黛玉也属于这个“兼善天下”范畴之内。她的“虚伪”是封建礼法本身的虚伪。荀况说“善者,伪也。”庄周说孔子是“巧伪人”。宝钗的“虚伪”也应作如此观。
三、关于“二美合一”说的是是非非
从上分析可知,所谓“钗黛和好”——“二美合一”说,是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构思的中心枢纽。他要写的“大旨言情”是个礼法所禁的雷区:“万恶淫为首”,“知情即淫”,一涉及“淫”就堕入“万恶”的深渊。所以,他要将所写的“情”限制在“从未发泄”的“儿女之真情”,即天真未泯,两小无猜,耳鬓厮磨,坐卧不避,似觉非觉,似情非情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范畴之内,而不涉及“淫邀艳约,私奔投盟”的男女爱情。
基于此,钗、黛只应“和好”、“合一”而不应对立冲突。当然,这不是曹雪芹曲意散布的“烟幕”,而是出于他的道德观念与审美情趣。出身于江南织造之家的曹雪芹也和作品中的林黛玉那样:尽管每天情思睡昏昏地热恋着宝玉,却又否认着与宝玉有特殊情感,拒绝着他的调情,惟恐丧失了“主子小姐”的身份。所以他写了“情”又在否认“情”;写了“颦颦宝玉两情痴”的男女爱情及宝钗第三者介入造成了不可两存的悲剧冲突,但又极力淡化、缓解、调和它,将它制约在“怨而不怒”的境界,使这一对不可两存的人物“和好”、“合一”,这正是作者的“原意”所在。
程伟元、高鹗不知道,不懂得或不同意这样的构想,从作品的中心故事情节发展规律与人物性格的逻辑出发,因势利导,水到渠成地续成了宝、黛爱情悲剧,即将黛死钗嫁置于同日同时的大冲突的悲剧结局,并写了宝、黛最后诀别、焚诗绝粒一系列情节,将钗、黛冲突推向了高潮,完成了作为作品主体结构的宝、黛爱情故事和黛玉,宝钗两个人物的最终塑造。这是个发展,是个创造。没有“颦颦宝玉两情痴”的“传神千秋”的描绘,100个程伟元、高鹗也写不出《红楼梦》的一回、半回。曹雪芹“造物主”地位功在千秋,毋须置疑的。《红楼梦》八十回的珠玉在前,造成了“振衣千仞岗”的气势,却因为这样那样的思想、心理障碍受阻,创作受到限制,相形之下,程、高出身于较低层,不存在或较少存在“世家子”那样“优越”、“自尊”的思想和心理障碍,也就能有较大的创作自由,也就能后来居上续成了这部伟大的作品,并突出了呼唤婚姻自主、爱情自由的历史要求的主题,完成了曹雪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以“二美合一”构思为核心的《石头记》与钗、黛冲突为中心的《红楼梦》是两部思想倾向、审美追求大不相同的作品。前者将它制约在“二美合一”,怨而不怒的范畴内;后者将宝、黛爱情与钗、黛对立作为中心情节,突出了宝、黛爱情悲剧的主旋律,使其成为作品的最强音。因而,前者让宝、黛爱情淡化、消失在贾府败亡大局之中。后者则突出了呼唤爱情自由、婚姻自主这个历史必然要求的主题,揭示了在封建礼法禁锢下,爱情、婚姻这个最尖锐的政治问题。前者出自曹雪芹的“原意”,这是作品前八十回整体构思及红学家考证、探佚的辛勤努力所证实的,绝非别人所能“伪托”;后者为程、高所续,他们放弃了“二美合一”的构思,将宝、黛爱情悲剧一气写成,直奔高潮,是个创造,是个奇迹。脂本与程本这种因作品中心情节:“二美合一”和钗、黛冲突构想不同造成的两种不同面目的孰得、孰失、孰是孰非,或者各有得失,各有是非,非本文篇幅所能详述。这里仅提出以上想法,愿得到方家指教。
注释:
①王希廉:《红楼梦总评》。
②护花主人评本《红楼梦》第68回行间评。
③戚蓼生:《石头记序》。
④李贽:《杂述·童心说》
⑤涂瀛:《红楼梦论赞》
⑥黑格尔:《美学》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49-350页。
⑦⑧《何其芳文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88、198页。
⑨庚辰本《石头记》,第21回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