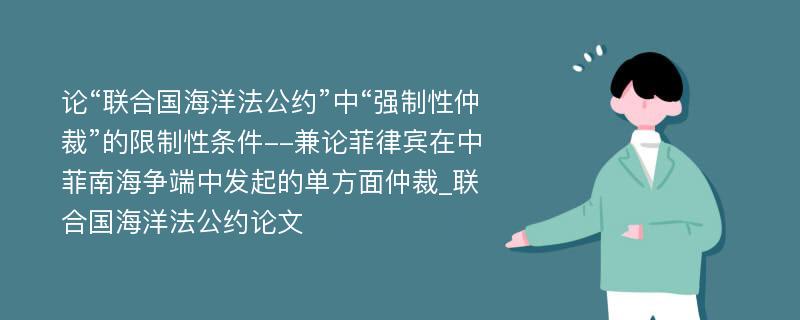
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强制性仲裁”的限制条件——兼评菲律宾单方面就中菲南海争议提起的仲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洋法论文,菲律宾论文,联合国论文,南海论文,公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512(2014)01-0146-07
菲律宾外交部于2013年3月25日对外宣称,由于中国拒绝回应菲律宾单方面提出的仲裁请求,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柳井俊二已于之前的一周任命波兰籍法官斯坦尼洛夫帕夫拉克代表中国出席法庭关于该争议的仲裁。同时,德国籍法官吕迪格·沃尔夫鲁姆被任命为仲裁法庭成员。2013年4月25日,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赫尔南德斯则进一步宣称,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柳井俊二已经任命完成全部5名审议中菲南海争端的仲裁员,接下来将择期开会讨论是否对此案有管辖权,但并没有明确的时间表。①菲律宾的仲裁请求主要包括以下三项:一是要求仲裁法庭认定菲律宾在海洋法公约下享有对南海其邻近区域的大陆架和经济专属区的相关权益;二是要求仲裁法庭认定中国对南海划界的“九段线”不符合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三是要求仲裁法庭认定美济礁、西门礁、南薰礁和渚碧礁都只是国际海洋法下的“暗礁”,不是领海。同时,菲律宾还要求认定黄岩岛的六个小岛以及永暑礁、华阳礁和赤瓜礁都只能称为国际海洋法下的“岩礁”而非“岛屿”,因此不能享有专属经济区。②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审理菲律宾仲裁申请的法庭实际上是根据“公约”附件七组成的仲裁法庭,那么,“公约”附件七的仲裁方式有何特征,又有何限制条件呢?中国在已经拒绝接受仲裁的情况下如何做好后续的应对工作。本文将结合菲律宾单方面提出的仲裁请求,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
一、“公约”附件七仲裁方式具有强制性
“公约”附件七仲裁方式的主要法律依据是“公约”第287条第1款、第3款和第5款的规定。“公约”第287条第1款规定:1.一国在签署、批准或加入本公约时,或在其后任何时间,应有自由用书面声明的方式选择下列一个或一个以上方法,以解决有关本公约的解释或适用的争端:(a)按照附件六设立的国际海洋法法庭;(b)国际法院;(c)按照附件七组成的仲裁法庭;(d)按照附件八组成的处理其中所列的一类或一类以上争端的特别仲裁法庭。“公约”第287条第3款规定:缔约国如为有效声明所未包括的争端的一方,应视为已接受附件七所规定的仲裁。“公约”第287条第5款规定:如果争端各方未接受同一程序以解决这项争端,除各方另有协议外,争端仅可提交附件七所规定的仲裁。综上,“公约”附件七规定的仲裁方式可以简单地描述为,除非争端各方事先或临时同意用其他方法解决争端,仲裁就是强制性的。③具体来说:“公约”附件七仲裁方式的“强制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仲裁管辖权的强制性。一般意义上的仲裁管辖必须以争端当事国的共同同意为前提条件,争端当事国可以在争端发生之前或争端发生之后达成协议将争端提交仲裁解决。“公约”附件七的仲裁方式则不然,只要争端各方未在事先或事后同意用附件七仲裁以外的方式解决争端,就必须采用“公约”附件七的仲裁方式。可见,“公约”附件七仲裁方式突破了“共同同意”这一基础,具有一定的强制管辖的色彩。其次,仲裁程序的强制性。就仲裁程序的发起来说,“公约”附件七第1条规定:“在第十五部分限制下,争端任何一方可向争端他方发出书面通知,将争端提交本附件所规定的仲裁程序。通知应附有一份关于其权利主张及该权利主张所依据的理由的说明”。这样,争端任何一方把争端交付仲裁,不需另一国同意,仅仅履行“书面通知”程序即可。就仲裁程序的进行来说,“公约”附件七第9条进一步规定:“如争端一方不出庭或对案件不进行辩护,他方可请求仲裁法庭继续进行程序并作出裁决。争端一方缺席或不对案件进行辩护,应不妨碍程序的进行。”该条说明即使争端一方抵制仲裁程序,也并不妨碍仲裁程序的继续进行。这就与传统仲裁制度有了重大区别,类似于国际法院的缺席判决了。④就仲裁裁决结果来说,“公约”附件七第11条规定:“除争端各方事前议定某种上诉程序外,裁决应有确定性,不得上诉,争端各方均应遵守裁决。”这意味着,除非争端各方事先协议排除,仲裁裁决是终局的,不得上诉。再次,关于仲裁裁决的解释或执行方式争议的强制解决性。争端各方之间对裁决的解释或执行方式的任何争议,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解决。根据“公约”附件七第12条,第一,“可由任何一方提请作出该裁决的仲裁法庭决定”;第二,“可由争端所有各方协议,提交第287条所规定的另一法院或法庭”。据此,如果争端各方关于仲裁裁决的解释或执行达不成协议的话,则只能提交“公约”附件七的仲裁方式。这样,此类争端不能被单方面提交“公约”以外的第三方程序解决。⑤
“公约”附件七为什么规定了这种具有强制色彩的仲裁方式呢?首先,仲裁是一种比司法解决更灵活有效且普遍适用的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仲裁不仅导致有法律拘束力的裁决,而且在仲裁法庭组成、仲裁法庭的程序以及仲裁裁决的确定性方面给予当事各方相当大的选择余地,从而保证了当事各方最大程度的参与。特别是与新成立的国际海洋法法庭、适用范围有限的特别仲裁以及当时不为发展中国家信任的国际法院相比,仲裁也是最适宜作为保底程序的导致有拘束力裁判的强制程序。⑥其次,从“公约”谈判的历史过程来看,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争端解决问题引起各国重视,并且主要产生了两种不同意见。一些国家如中国、罗马尼亚、印度、印度尼西亚等认为“公约”应该采取自愿为基础的管辖制度。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澳大利亚等则认为,所有有关的海洋法公约的解释和适用的争端都应适用强制程序加以解决,而不应有任何例外。⑦最终,强制性解决程序以折衷的面貌在“公约”中得以确立。可见,“公约”附件七的强制性仲裁是各国激烈斗争和博弈的结果。最后,仲裁的另一个优点是,仲裁审理可以秘密进行,由此避免当事方在公众面前丢脸。⑧
综上,“公约”附件七的强制性仲裁是诸多原因促成的,它可以说是“公约”的一大创新,但是它在具体适用时,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
二、“强制性仲裁”应受限制性条件约束
“公约”附件七的“强制性仲裁”所受到种种条件限制都与仲裁庭的管辖权有关。上述限制条件可以细分为仲裁前置程序限制条件、仲裁庭受案范围限制条件、争端方保留范围限制条件三个方面。从时间角度来看,上述三个限制条件分别着眼于仲裁庭管辖权的早、中、晚三个阶段。
首先,“强制性仲裁”必须是基于争端各方已经协议自行选择的和平方法且仍未能解决争端的前提下才能采用,这是“强制性仲裁”的前置性程序限制。“公约”第281条第1款规定:作为有关本公约的解释或适用的争端各方的缔约各国,如已协议用自行选择的和平方法来谋求解决争端,则只有在诉诸这种方法而仍未得到解决以及争端各方间的协议并不排除任何其他程序的情形下,才适用本部分所规定的程序。可见,强制性仲裁实属不得以之举,如果争端各方能够用自行选择的和平方法解决争端,则无须提交强制性仲裁。“公约”之所以设置这样一个限制条件,既是为了鼓励各国先通过谈判与协商等和平方法解决争端,也可以减轻仲裁庭的工作压力。因此,仲裁庭必须深入考察争端各方在提交仲裁之前自行寻求和平解决争端的努力及其效果。
其次,“强制性仲裁”所针对的案件必须符合“公约”第281条第1款所规定的受案范围,这是仲裁庭受案范围限制。“公约”第281条第1款规定,只有与本“公约”有关的解释或适用的争端才能提交“公约”附件七的强制性仲裁。该规定实际上指出了强制性仲裁的受案范围:“法律争端”的存在且与“公约”的解释和适用有关。如果没有“法律争端”的存在,或者虽有“法律争端”的存在但与“公约”的解释和适用无关,则均不属于“强制性仲裁”的受案范围。纵观各国国内司法制度、国际司法机构以及国际仲裁机构的章程,均有关于受案范围的规定。受案范围既明确了上述机构处理案件的范围,又可以避免争端方的滥诉缠诉,意义重大。而“公约”关于仲裁庭的受案范围强调了与“公约”的解释和适用有关,既紧扣“公约”本身,又简单明了。因此,仲裁庭必须深入分析提请仲裁的事项是否属于仲裁庭的受案范围。
再次,“强制性仲裁”所针对的事项不能属于争端方已经作出的保留范围,这是“强制性仲裁”所受的争端方保留范围限制。“保留”是指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在签署、批准、正式确认、接受、核准或加入条约,或一国发出继承条约的通知时所作的单方面声明,不论其措辞或名称如何,该国或该组织意图藉此排除或更改条约中某些规定对该国或该国际组织适用时的法律效力。⑨可见,保留具有排除或更改条约中某些规定对缔约国适用的法律效力。“公约”第298条第1款允许缔约国作出保留从而将特定的争端排除仲裁庭管辖范围。因此,仲裁庭必须深入考察争端方有无作出保留及保留的具体内容。
综上,“公约”附件七的“强制性仲裁”并非基于争端一方提起以后就必须由仲裁庭受理和审理,而是应该在满足上述条件以后才能确定仲裁庭的管辖权,然后才能进入实体问题的审理。
三、菲律宾单方面提出的“强制性仲裁”不符合仲裁前置性程序的限制条件
早在1996年3月,中菲发表《中菲外交部磋商联合新闻公报》,双方同意建立在南海地区探讨合作的双方磋商机制,包括成立渔业、环保和建立信任措施三个专门小组。⑩据此,菲律宾有义务尽可能通过双边磋商的方式解决争端。“公约”第282条进一步规定:作为有关本公约的解释或适用的争端各方的缔约各国如已通过一般性、区域性或双边协定或以其他方式协议,经争端任何一方请示,应将这种争端提交导致有拘束力裁判的程序,该程序应代替本部分规定的程序而适用,除非争端各方另有协议。据此,区域性协定的争端解决方式应比强制性仲裁居于更优先地位。中国和菲律宾恰恰都是2002年《南海各方行动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的缔约方。《宣言》第4条规定,有关各方承诺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包括“公约”,由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它们的领土和管辖权争议,而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显然,作为《宣言》缔约方的菲律宾有义务首先采取磋商和谈判方式解决其与中国的争端,在这种方式不能解决争端的情况下,才能提交强制性仲裁。因此,《宣言》理应得到全面、认真落实。菲律宾理应按照国际法的有关规定和《宣言》的有关精神,通过双边谈判解决领土和海洋划界争议。
进一步而言,“公约”本身也给争端方设置了诸多谈判和交换意见的义务。谈判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国家为使有关冲突、矛盾或争端得到谅解或求得解决而进行的直接交涉,以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法。虽然当谈判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存在即出现了僵局时,双方可以自行选择其他方式来解决纠纷,但‘公约”在某些特定问题上已将双方谈判解决争端作为当事国的必须履行的前置义务。比如海洋划界问题上,“公约”第74条“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专属经济区界线的划定”规定:“1.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专属经济区的界线,应在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所指国际法基础上以协议划定,以便得到公平解决。2.有关国家如在合理期间内未能达成任何协议,应诉诸第十五部分所规定的程序。”“公约”第83条“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大陆架界线的划定”也有相似的规定。由于海洋划界的方法在国际实践中的不确定,且海洋划界涉及众多复杂的因素,更适合于当事国之间自行商议解决争端。实践也证明,“缔约国之间已经抓住这一宽泛的框架提供的机会,在海洋划界问题上采用多种不同的解决方法,进而突破了传统的等距离原则与中间线原则。”(11)据此,由南海“九段线”所涉及的中国与菲律宾的海洋划界问题应该通过中菲双方的谈判加以解决。而交换意见的义务体现在“公约”第283条:其一,如果缔约国之间对本公约的解释或适用发生争端,争端各方应迅速就以谈判或其他和平方法解决争端一事交换意见;其二,如果解决这种争端的程序已经终止而争端仍未得到解决,或如已达成解决办法,而情况要求就解决办法的实施方式进行协商时,争端各方也应迅速着手交换意见。从该条的字面理解,交换意见的内容是选择一种通过谈判或者其他和平的方式争端解决的方式。(12)海洋法庭法官P.Chandrasekhara Rao在其独立意见中提到:“交换意见的义务并不是一套无实质内容的程序,不能凭借一方的一时兴起来加以决定,法院的职责在于审查交换意见这一程序是否被善意地履行。”(13)
然而,尽管中国从维护中菲双边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大局出发,一贯致力于通过与菲律宾的双边谈判和协商解决有关争议,菲律宾却对谈判与交换意见采取非常消极的态度,不顾中国的再三呼吁,将争端单方面提交仲裁法庭。这与《宣言》第5条第1款“各方承诺保持自我克制,不采取使争议复杂化、扩大化和影响和平与稳定的行动”显然是相悖的,也可以说,菲律宾没有完全履行“公约”中谈判和交换意见的义务。
四、菲律宾单方面提出的“强制性仲裁”不符合仲裁庭受案范围的限制性条件
“国际争端”是指两个国家之间“有关法律或事实的争执,法律观点或利益的冲突”。(14)国际争端可以分为法律争端、政治争端、混合型争端、事实争端四大类。(15)强制性仲裁所针对的争端只能是法律争端。因为“公约”第281条第1款规定,只有与“公约”有关的解释或适用的争端才能提交“公约”附件七的强制性仲裁。与“公约”有关的解释或适用的争端只能理解为是一种法律争端。法律争端是指争端当事国的各自要求以国际法为根据的争端,它属于可裁判的争端,即它可以通过法律方法加以解决。(16)政治争端是指起因于政治利益的国际争端,这种争端一般对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等问题有重大影响,很难用国际法和法律方法来解决。(17)中菲之间的争端不属于法律争端,它属于政治争端,因而根本无法通过仲裁方式加以解决。关于这一点,从历史、法理以及中国政府和外交部多次公开表示中都可以得到证实。例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2012年4月1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对此拥有充分的法理依据,希望菲方切实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恪守双方达成的不采取任何可能使事态复杂化和扩大化行动的共识。刘为民还指出,菲律宾在1997年以前从未就中国政府对黄岩岛行使主权管辖和开发利用提出过任何异议,并且还多次表示黄岩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1981年和1984年菲律宾出版的地图也都将黄岩岛标绘在菲领土界限之外。(18)又如,2012年5月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北京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在谈到菲方要将黄岩岛问题提交国际仲裁时,洪磊严正指出,中方对黄岩岛的主权具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不管菲律宾方面关于黄岩岛主权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都改变不了黄岩岛属于中国的基本事实。(19)再如,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2013年4月26日答记者问时指出:菲方以其对中国岛礁的非法侵占作为提起仲裁的基础,歪曲了中菲争端的基本事实。菲方企图以此否定中国的领土主权,使其非法侵占中国岛礁的行为披上“合法化”外衣。菲方谋求这种所谓“持久的解决”企图及其手段,是中方绝对不会接受的。(20)类似的发言和表态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由于仲裁的方式本质上属于一种法律方法,通过仲裁方式解决的争端显然只能是法律争端,而不可能是政治争端。因为后者根本无法通过法律裁判的方法加以解决。菲律宾方面也毫不掩饰此次仲裁的政治目的,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赫尔南德斯2013年4月25日称:“国际海洋法法庭的任何裁决都不能强制执行,但菲国借此寻求的是政治及法律胜利,届时国际舆论将对中国施加压力。”(21)因此尽管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仲裁,欲通过法律方法解决中菲之间的争端,但是其图谋终将失败。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深入分析菲律宾的第一项仲裁请求,即“要求仲裁法庭认定菲律宾在海洋法公约下享有对南海其邻近区域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相关权益”,甚至根本看不出它与中国存在什么争端。
提交强制仲裁的争端除了必须是法律争端外还必须是与“公约”的解释或适用有关的。但是仔细分析菲律宾的后面两个仲裁请求,可以发现其与“公约”的解释或适用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菲律宾的仲裁请求之一涉及中国南海“九段线”的合法性,仲裁请求之二涉及美济礁、西门礁、南薰礁、渚碧礁、黄岩岛的六个小岛以及永暑礁、华阳礁和赤瓜礁的法律地位。上述两个仲裁请求都涉及中国的历史性权利。从历史来看,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南海诸多岛屿,最早将其列入中国版图,实施主权管辖。南海上述岛屿的周边海域是中国渔民的传统捕鱼场所。自古以来,中国渔船就经常赴上述岛屿周边海域进行渔业生产活动。可以说,南海“九段线”所包含的民族文化和海洋文明是经过千百年中国人生产和生活实践积累、积淀形成的。(22)从现实层面来看,南海“九段线”内海域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重要的航运通道等利益对实现中国国家长远发展和战略目标至关重要。(23)更何况,南海“九段线”已经由中华民国政府于1947年在《南海诸岛位置图》中予以公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后,基本上将其继承和沿袭下来。60余年来,中国政府在立法和法律文件以及官方声明中多次重申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享有主权和海洋权益。(24)而“公约”是1982年通过,1994年生效,1996年才对中国生效的。根据“法不溯及既往”这项基本的法理原则,上述仲裁事项显然与“公约”的解释和适用无关。从国际法来看,关于某一争端是否是有关某特定条约解释或适用的争端问题,国际法院曾指出:“为了回答该问题,本院不能限于注意到当事一方主张存在此争端,而另一方予以否认。它必须查明所声称的对一条约的违反……是否属于该条约的规定。”(25)同样是在“公约”附件七仲裁法庭审理的“麦氏金枪鱼案”中,仲裁法庭更是明确宣称:原告主张而被告否认,以及该争端涉及公约的解释和适用本身并不构成本庭有管辖权的有关公约解释的争端。该法庭指出,在本案以及其他援引一个条约中的争端解决条款的案件中,按照其管辖权受到争议的法院或法庭的判断,为支持管辖权所作的主张必须合理地与有关条约的法律标准相关,或可以结合有关条约的法律标准加以评估。换言之,各方之间的“真实争端”应“与声称遭到违反的条约中所规定的义务合理地相关。(26)目前菲律宾披着“公约”的合法外衣干着不断挑战中国的历史性权利的“勾当”,菲律宾本身就没有基于“公约”失去什么,中国倒有可能因为菲律宾的挑战而失去历史性权利。这样的争端处理是完全与法理相悖的。
综上,菲律宾的仲裁请求没有满足限制条件之一:“法律争端”的存在,且与“公约”的解释和适用有关。
五、菲律宾单方面提出的“强制性仲裁”不符合争端方保留范围的限制条件
由于保留具有排除或更改条约中某些规定对缔约国适用的法律效力,中国对“公约”相关规定作出保留也将产生排除或更改“公约”相关规定对中国适用时的法律效果。根据“公约”第三节“适用第二节的限制和例外”所确定的规则,缔约国在某类事项上有明示排除强制程序的权利。该节第298条第1款规定:“一国在签署、批准或加入本公约时或在其后任何时间,在不妨害根据第一节所产生的义务的情形下,可以书面声明对于下列各类争端的一类或一类以上,不接受第二节规定的一种或一种以上的程序:(a)(i)关于划定海洋边界的第15条、第74条和第83条在解释或适用上的争端,或涉及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的争端,但如这种争端发生于本公约生效之后,经争端各方谈判仍未能在合理期间达成协议,则作出声明的国家经争端任何一方请求,应同意将该事项提交附件五第二节所规定的调解;此外,任何争端如果涉及同时审议与大陆或岛屿陆地领土的主权或其他权利有关的任何尚未解决的争端,则不应提交这一程序”。根据上述条款,海洋边界争议和涉及大陆或岛屿陆地领土的主权或其他权利的争议都属于允许缔约国明示排除强制程序的范畴。而我国正是根据上述该条款的规定,在2006年8月25日明确声明有关中国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的争议和基于历史的主权诉求不受“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管辖。
然而,菲律宾在其仲裁请求中直接挑战我国美济礁、西门礁、南薰礁、渚碧礁、黄岩岛的六个小岛以及永暑礁、华阳礁和赤瓜礁的法律地位,从而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岛屿主权权利,这显然属于中国的保留范围,仲裁庭理应无管辖权。至于菲律宾又将争议聚焦在“九段线”纷争上,也是不能避开中国所提的保留的。“九段线”实际上就是中国在历史上一直主张的与南海周边国家间的海域分界线,而这个海域的分界线确定与南海岛礁的领土主权归属是密不可分的。因此,“九段线”之纷争不仅涉及海洋边界划分,同时也涉及领土主权归属问题,完全属于我国保留声明所涵盖范围之内。在中国政府按公约规定有保留声明排除强制程序的情况下,菲律宾单方提交国际仲裁没有法律依据。这一做法既违反了国际仲裁的一般规则,也不符合“公约”的相关规定,其图谋最终一定会落空。(27)因此,即使菲律宾提出的仲裁事项是有关“公约”的解释或适用的争端,那也属于我国保留范围内,仲裁法庭对此并无管辖权。
六、余论
菲律宾自从提出“强制性仲裁”申请以后,就一直在国际社会叫嚣和宣扬其主张,甚至最近还在催促联合国法庭尽早对由其提交的南海主权仲裁案件做出裁决。其外长德尔罗萨里奥于2013年10月24日还宣称中国对南海的声索是“膨胀性的和过度的”。他坚持认为,在没有中国参与的情况下,裁定将更快宣布,可能在2014年宣布。(28)但是正如笔者之前的分析,菲律宾单方面提出的仲裁请求不符合仲裁庭管辖权的种种限制条件,依法应当被驳回。笔者认为,作为中国政府在后续对策方面应该着重从两个方面应对。第一,中国政府已于2013年2月19日通过外交途径退回了菲律宾的仲裁请求,至此中国缺席本次南海仲裁的结果已成定局。虽然中国无法通过法律途径向仲裁庭提出管辖权的抗辩主张,但是中国政府应该通过外交、国际社会和舆论、学界、媒体等途径广泛深入地阐述中国的主张,从而对仲裁法庭产生影响,促进仲裁法庭尽快驳回菲律宾的仲裁请求。第二,从目前来看,本次仲裁中最有利的结果是由仲裁法庭认定其对菲律宾的各项仲裁请求均无管辖权。同时,中国也有勇气面对仲裁庭作出的任何裁决结果,即使仲裁法庭裁决中国败诉,中国也完全有充分理由公开否认仲裁法庭及其裁决结果的合法性。
注释:
①《国际法庭组成南海仲裁小组》,《环球时报》2013年4月26日,第3版。
②郑叶青:《中国不应诉南海仲裁的应对之策》,《法制日报》2013年4月2日第10版。
③Alan E.Boyle,Dispute Settlement and the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Problems of Fragmentation and Jurisdiction,p.40.
④吴慧:《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强制解决争端程序的强制特性》,《法商研究》1995年第1期。
⑤高健军:《〈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4页。
⑥同上注,高健军书,第142-143页。
⑦同前注④,吴慧文。
⑧Peter Malanczuk,Akenhust's Moder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Law,P.293.
⑨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2011版《条约保留实践指南》(1.1)的规定。
⑩薛桂芳编著:《〈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国家实践》,海洋出版社2011年版,第273页。
(11)Alex G.Oude Elferink & Donald R.Rothwell,Oceans Management and the Law of the Se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and Response(Martnus Nijhoff Publishers) P.346-347.
(12)葛冠群:《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谈判”与“交换意见”义务》,《研究生法学》2010年第5期。
(13)Case concerning Land Reclamation by Singapore in and around the Straits of Johor(Malaysia v.Singapore),Provisional Measure,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Rao,paragraphs 11.
(14)Mavrommatis Palestions,Judgment of 30 August 1924(Objection to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1924 PCIJ Series A,No.2,p.11.
(15)王铁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568-569页。
(16)同上注,王铁崖书,第568页。
(17)同注(15),王铁崖书,第568-569页。
(18)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e/ceth/chn/fyrth/t924078.htm。2013年5月13日访问。
(19)同上注。
(20)同上注。
(21)同前注①。
(22)傅□成:《南(中国)海法律地位之研究》,台湾资讯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46-115页。
(23)黄伟:《论中国在南海U形线内其他海域的历史性权利》,《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24)贾宇:《南海U形线的法律地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2期。
(25)On Platforms(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v.United States of America),Pliminary Objection,Judgment of 12 December 1996,ICJ Reports 1996,p.803,para.16.
(26)Southern Bluefin Tuna Case(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v.Japan),Arbitral Tribunal Constituted under Annex VII of the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Award on Jurisdiction and Admissibility of 4 August 2000,reprinted in 119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p.508,para.48.
(27)丁成耀:《海洋法庭强行仲裁于国际法无据》,《法制日报》2013年4月2日第10版。
(28)侯涛:《菲律宾催促尽早完成南海仲裁?称中国的要求过度膨胀》,《环球时报》2013年10月25日。
标签: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论文; 法律论文; 民主礁论文; 中菲南海争端论文; 南海九段线论文; 菲律宾南海论文; 南海仲裁论文; 南海美国论文; 南海争端论文; 日本南海论文; 南海地图论文; 宣言论文; 仲裁法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