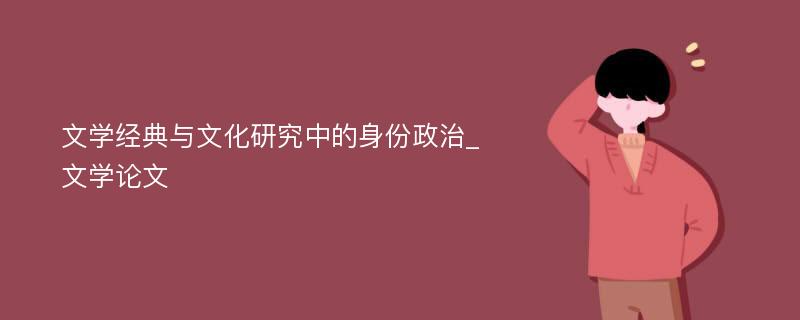
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身份论文,政治论文,经典论文,文化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
当代文化研究实际上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从传统的文学经典研究转向大众文化研究,二是用新的理论重新评估与阐释旧的文学与文化现象。在后一层面,文化研究企图包含并覆盖文学研究,从而引申出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并进一步引申出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的关系问题。
卡勒(Janathan Culler)在《文学理论:简短的导论》一书中指出,一方面,文化研究鼓励研究电影、电视及其他大众文化形式,而不是大力促进对世界文学中的经典作品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伴随着文化研究兴起的理论又给传统的文学经典增加了活力,开拓了更多的解读英美文学经典的方法,并且,文化研究的发展也一直与文学经典作品的扩大相伴。而对于分析包括文学经典在内的文化现象的适当方法这个问题,卡勒却不无担忧地认为:“从长期统治着文学研究的原则——主要的兴趣是个别作品与众不同的复杂性——中逃离出来,文化研究易于成为一种非量化的社会学,把作品视为某种别的东西的例证或表征,而不是内在于它们自身的东西,而且,文化研究也屈服于别的诱惑。”(注:Jonathan Kuller,Literary Theory: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London:Oxford University,1997,p.51,p.51,51,p.52.)亦即是说,文化研究热衷于在作品与反映对象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文化产品就是一种处于社会—政治结构之下的表征”(注:Jonathan Kuller,Literary Theory: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London:Oxford University,1997,p.51,p.51,51,p.52.)。卡勒将文化研究对文本的这种解释方法称为“表征性解释”(symptomatic interpretation)——与文学研究的“鉴赏性解释”(appreciative interpretation)相对应,并说:“如果文学研究被纳入文化研究名下,这种‘表征性解释’就可能成为规范,而文化对象的独特性就可能被忽视,与此同时,文学鼓励的阅读实践也会被忽视。”(注:Jonathan Kuller,Literary Theory: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London:Oxford University,1997,p.51,p.51,51,p.52.)卡勒围绕着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所提出的问题,特别是文化研究对文本的“表征性解释”问题,确实是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论争中的关键问题,而且都与文学经典有关:前者关系到何谓文学经典,后者关系到对文学经典的阐释。于是,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文学经典成了关注的焦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关系的论争,在某种意义上也就转变成了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关系的论争。这同样也可被视为当代中国关于文学经典的论争出现的背景。
在美国的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关系的论争中,布鲁姆(Harold Bloom)称得上是独树一帜的“浪漫主义骑士”,在文化研究正在全面质疑与摧毁传统的文学经典的时候,他起而维护“审美自律性”概念,维护传统经典的权威,反对大众文化,反对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对传统文学经典的颠覆。他将女性主义、非洲中心论、马克思主义、受福柯启发的新历史主义或解构主义都称为“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注:布鲁姆:《西方正典》,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第16页,中文版序言第2页,第411页,第13页,第412页,第17—18页。)。在布鲁姆看来,“憎恨学派的基本原则可以一语道破:所谓的审美价值也出自阶级斗争”(注:布鲁姆:《西方正典》,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第16页,中文版序言第2页,第411页,第13页,第412页,第17—18页。)。于是,身份政治成了他们评价并摧毁传统文学经典的基本原则。“现今世界上的大学里文学教学已被政治化了:我们不再有大学,只有政治正确的庙堂。文学批评如今已被‘文化批评’所取代:这是一种由伪马克思主义、伪女性主义以及各种法国/海德格尔式的时髦东西所组成的奇观。”(注:布鲁姆:《西方正典》,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第16页,中文版序言第2页,第411页,第13页,第412页,第17—18页。) 对此,布鲁姆深感悲哀:“诗歌、戏剧、故事和小说的教学正在被各种社会和政治讨伐的摇旗呐喊所取代。”(注:布鲁姆:《西方正典》,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第16页,中文版序言第2页,第411页,第13页,第412页,第17—18页。)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布鲁姆反抗的正是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所采取的政治化的“表征性解释”,而对“鉴赏性解释”的缺失深感悲哀与无奈。他所维护的,是经典作品与众不同的原创性与复杂性。在布鲁姆看来,出于明显的社会和政治目的对文学经典的政治化阐释,不能揭示文学经典的原创性与复杂性,是对文学经典的亵渎与损害。
在我看来,像布鲁姆这样全然否定大众文化的价值与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可能有的赋意作用,在今日显然太具有曲高和寡的精英色彩,也难免褊狭。然而,他所提出的文化批评的政治化阐释对文学经典的原创性、复杂性的忽视,确实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一个问题。对此,我想通过后殖民批评的一个个案加以阐释。
二、一种个案:萨义德的身份政治与叶芝的诗
后殖民主义称得上是布鲁姆所谓的“憎恨学派”的典型。对文学研究而言,后殖民主义就是一种典型的对文学作品进行政治化的“表征性解释”的文化批评。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对大量诗歌文本的分析就是明显的例证。就萨义德而言,还有另外一个相对完整也更好地表现出对文学进行“表征性解释”的例子。这个例子涉及爱尔兰诗人叶芝。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的“抵抗与敌对”一章中,萨义德专门用一节的完整篇幅讨论了“叶芝与反殖民主义”。使我惊讶的,不是从“反殖民主义”这个角度来解释叶芝的诗,而是萨义德对叶芝及其作品作支配性的身份政治解释中所体现出来的对叶芝的诗及其个人的整体评价与社会身份的期待和指责。
萨义德在讨论叶芝的这一部分文字中,首先为叶芝的文学确立一种与通常观点相左的非欧洲传统的坐标。他认为叶芝现在几乎被归类于现代英语文学和欧洲主流现代主义话语中。而他则认为,“尽管叶芝明显地存在于爱尔兰,存在于英国文化与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中,他的确还代表着另一个引人入胜的方面:他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伟大的民族诗人。他在反帝抵抗运动期间阐述了遭受海外统治的人民的经历、愿望和恢复历史的瞻望”。这样一来,叶芝存在于英国文化与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中,似乎只是一种浅显的表象,而其深层的意义却在于他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诗人”,“从这一角度来看,叶芝属于通常被认为不是他所属的那个传统,属于反对欧洲帝国主义高潮中的殖民地世界的传统”(注: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13—314页,第328页,第335页,第335页,第334页,第322页,第339页,第323页。)。在这个意义上,萨义德甚至将爱尔兰与印度、北非、加勒比、中南美洲、中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归入同一个群体,从而自然而然地将叶芝的文学归入“反帝抵抗运动的文学”,他甚至援引智利诗人聂鲁达的态度将叶芝视为“爱尔兰抗拒暴政斗争的民族诗人”。萨义德将叶芝视为致力于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复兴的诗人,并认为这样的民族主义复兴的显著特点是:“明确地认为欧洲即西方文化是帝国主义”。从论述的开始,萨义德就以一种典型的文化地理学的划分方式,从具有明显的二元对立特征的身份政治层面将叶芝从通常所属的英语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文学传统中分离出来,归入另一个与西方文化相对立的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文化传统。然而,只要完整地阅读过叶芝的诗的人,谁都不能否认,在叶芝的诗中体现出了对暴力的怀疑,进而对人类文明的失望态度,特别是在后期的诗作中。这无疑是与萨义德的上述判断相左的。为了解决这一困境,萨义德在认同叶芝的诗前后分期的前提下,对叶芝后期的诗歌写作给予了非议。萨义德将叶芝诗的前后分期的界线定在20世纪20年代。他说:“叶芝在20世纪20年代滑入了前后不一致、神秘主义、排斥政治和对法西斯主义(或是意大利或南美的集权主义)傲慢的、也许是迷人的赞美。从这个观点看,叶芝是不可原谅的,不能轻易地被诡辩为消极的乌托邦模式,因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评价和批评叶芝那些错误的态度而依然将他看作非殖民地化的一位诗人。”(注: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13—314页,第328页,第335页,第335页,第334页,第322页,第339页,第323页。)依照对叶芝诗歌写作这一整体评价,萨义德将叶芝诗歌写作的顶峰定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的一段时期,并将其中体现的“英国—爱尔兰冲突”作为“20世纪解放战争的典型”来加以看待,他认为叶芝“最伟大的非殖民地化作品是关于暴力的诞生或者通过暴力诞生而改变的”(注: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13—314页,第328页,第335页,第335页,第334页,第322页,第339页,第323页。)。为此,萨义德提到了《丽达与天鹅》、《塔》两首诗。《丽达与天鹅》一诗的主题被解释为对“殖民者”的塑造,这种塑造是关于暴力(姑娘被强奸)和“知识和力量”的获得的,他说:“叶芝把自己放在这样的岔路口:为了变革使用暴力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暴力的结果却要求必要的、如果不永远是足够的理性”。在以《塔》为顶峰的诗歌中,最伟大主题是“怎样调和殖民主义冲突中不可避免的暴力与不断的民族斗争的政治,怎样使冲突的各方力量与理性、说服、组织的话语以及诗歌的要求一致起来”。于是,叶芝被阐释成了阿尔及利亚的法农(Fanon)一样的思想家、革命者,他说,“叶芝有预见地认为,在某些时刻,仅有暴力是不够的。因此,政治的策略和理性必须起作用”(注: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13—314页,第328页,第335页,第335页,第334页,第322页,第339页,第323页。)。与叶芝前期这种“正确的”政治倾向不同,萨义德将叶芝后期诗歌错误的政治倾向称为“反动政治倾向”,并认为这种倾向“扭曲甚至掩盖了他诗歌中对解放者和乌托邦革命的刻画”(注: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13—314页,第328页,第335页,第335页,第334页,第322页,第339页,第323页。)。这种“反动政治倾向”在诗歌中的表现,用萨义德不多但又很概括性的话讲,就是“他在《视线》和后来的半宗教诗歌里创造出古怪、美学化了的历史,把这种矛盾(按:指爱尔兰民族主义与英国文化遗产之间的重叠造成的矛盾)上升到超世俗的水平,好像爱尔兰最好在超乎地面之上的高度被对待”(注: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13—314页,第328页,第335页,第335页,第334页,第322页,第339页,第323页。)。萨义德评论叶芝的非殖民地化诗歌的这一段文字的最后的结论,也很有意思,他说:“固然,他没有进一步设想完整的政治解放。但是,他对文化的非殖民地化做出了重大的具有国际意义的贡献。”(注: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13—314页,第328页,第335页,第335页,第334页,第322页,第339页,第323页。)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颇有代表性的文化研究学者处理诗歌文本的个案。在这里,诗人的艺术身份不是评论者首先考虑的问题,评论者考虑的是叶芝作为思想家和革命者的政治身份,甚至因此非议叶芝“没有进一步设想完整的政治解放”的可能。
在《文化与帝国主义》即将出版之时,萨义德在一次访谈中说:“一边是我的文学和文化的事物,另一边是我的政治工作,而我总是尝试在两者之间平衡。还有就是巴勒斯坦社群。我的意思是说,我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写作。”(注:萨义德:《知识分子论》,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31页,第139页。)富有戏剧性的是,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萨义德还说:“大多数人从文学或知识的议论一跃而到政治的说法,事实上是不可以这么做的。”(注:萨义德:《知识分子论》,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31页,第139页。)在我看来,就萨义德对叶芝的诗的评论而言,他自己何尝真正地做到了“文学和文化的事物”与“政治工作”的平衡?相反,他自己就是他所批判的“大多数人”中的一员,就是“从文学或知识的议论一跃到政治的说法”的。甚至可以说,他在挟持文学以达到政治批评的目的。在这里,叶芝是一个被挟持者,他被挟持着远离了他的欧洲和西方文化传统,而成了亚非反殖民化运动中的一员。只要对叶芝的生平有所了解,并对叶芝的诗有所了解的人,可能都有理由怀疑萨义德这一明显偏颇的提法。从1887年就随家迁居伦敦的叶芝,其文学创作深受英语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和现代主义传统的影响。在叶芝的诗中,确实体现出爱尔兰与英国的政治与宗教冲突,但这种冲突远非可以上升到爱尔兰与整个英国文化乃至欧洲文化相对抗的高度,至于“明确地认为欧洲即西方文化是帝国主义”的论点,更多地是出于萨义德的杜撰,而非叶芝诗歌写作的实际。无论是从叶芝的作品或个人经历中,想为这一点找到佐证都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在诗中寻求非暴力、非政治的文化解决的途径,不仅仅存在于萨义德所谓的20世纪20年代的叶芝的诗中,同样也存在于此前的诗歌写作中,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叶芝与他终生所爱的爱尔兰演员茅德·冈的一个政治分歧。就这个意义而言,神秘主义的、非政治的叶芝的诗歌作品,正是叶芝作为一个诗人在作品中处理现实政治的一种深邃的艺术方式,而不是对非殖民化的逃避。在诗中,如果叶芝不是将爱尔兰超越到萨义德所讽刺的“超乎于地面高度之上”的高度来对待,我相信,诗的高度则要大大地降低。
注意到叶芝的爱尔兰民族诗人身份是无可厚非的,确实,这不能不被视为是这个伟大诗人的诗歌作品的魅力的深层源泉。但是,以这种身份作为解读他的诗(准确地讲,只是诗人)的惟一正当的入口,甚至对之非议,认为他没有进一步为民族解放提供一个良方,则不能不说是对诗的非法干预了。如果诗仅仅是一种社会干预,那么,它的力量可能还不如一篇政治论文来得强烈,诗本身就没有意义。诗的意义在于它是鉴赏性的,或者说,鉴赏性是诗的意义的起点。让我们来看一下《丽达与天鹅》这首诗,看看萨义德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对这首诗作了怎样的阅读。全诗如下:
猝然猛袭:硕大的翅膀拍击
那摇摇晃晃的姑娘,黑色的蹼爱抚
她的大腿,他的嘴咬住她的脖子,
他把她无力的胸脯紧贴他的胸脯。
她受惊的、意念模糊的手指又怎能
从她松开的大腿中推开毛茸茸的光荣?
躺在洁白的灯心草丛,她的身体怎能
不感觉卧倒处那奇特的心的跳动?
腰肢猛一颤动,于是那里就产生
残破的墙垣、燃烧的屋顶和塔颠,
阿伽门农死去。
因为这样被征服,
这样被天空中野性的血液所欺凌,
在那一意孤行的嘴放她下来之前,
她是否用他的力量骗得了她的知识?(注:叶芝:《丽达与天鹅》,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183页。)
这是典型的叶芝式的神秘主义诗歌文本(注:关于叶芝的神秘主义,可参阅达摩尔、伯蓝《叶芝》(百家出版社2004年版)中的相关论述。)。按照叶芝的神秘主义体系,历史的第一循环为两千年,每一循环都由一个姑娘和一只鸟的结合开始,从公元起这两千年是由玛丽和白鸽(即圣灵受孕说)引出的。而根据希腊的神话传说,众神之王宙斯变形为天鹅,使丽达受孕产了两个蛋,蛋中出现的是海伦和克莱提斯纳斯,前者与特洛伊王子的私奔引起了特洛伊战争,后者与奸夫一起谋杀了从特洛伊战争中得胜后返回家乡的阿伽门农。无可置辩,这首诗确实与暴力有关,就字面意义而言,第一节写的是天鹅(宙斯的化身)对丽达的猝然袭击,这可理解为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萨义德似乎是从法律的意义上将之定义为强奸,有过度诠释之嫌),而第三节则叙述了上述这种暴力所产生的另外一种与战争(残破的墙垣、燃烧的屋顶和塔颠)、谋杀(阿伽门农之死)相关的人世间的暴力。全面地阐释这首诗复杂的意义,并非我的主旨,这里我只想指明:如果说,《丽达与天鹅》一诗表现了暴力,那也只是暴力的寓言,其意义不能被阐释为是关于殖民者的暴力的。像萨义德这样武断地认为这是一首关于殖民者的暴力的诗,只有像萨义德那样站在阿拉伯世界的立场,把宙斯所代表的整个西方文明视为与非西方文明相对立的殖民者才有可能。这样,在叶芝那儿,天鹅(宙斯)就成了英国(进而是整个西方)殖民者的化身,丽达就成了爱尔兰(进而是被殖民者)的化身。这是典型的文化批评对诗的政治性利用,而诗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与多义性被遮蔽了。这样的文化批评也使叶芝的这首诗仅仅成了可供利用的一份反殖民主义的政治纲领。
同样,《塔》也不是叶芝的政治演讲,其意义不能仅仅从政治的层面上加以理解。如果叶芝仅仅是一个政治诗人,一个萨义德所谓可以与法农相提并论的革命者、思想家,那么,叶芝可能就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作品可能就不会是文学经典。一个伟大的民族诗人之所以伟大,不仅仅在于他抒写了民族的传统与苦难,就某种意义而言,他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他将这种苦难作为人类的苦难来认识,这决定了诗人的全人类性,离开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叶芝诗中体现出的对现代社会与文明的困惑与批判。这种批判不仅仅是从萨义德所谓的殖民地生活经验出发的,而是从整个欧洲现代文明的生活经验出发的。就这个意义而言,叶芝在诗中所体现出的萨义德所谓的在“非政治的层面上”消除“政治与世俗的紧张关系的压力”(注: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13—314页,第328页,第335页,第335页,第334页,第322页,第339页,第323页。),不是一种反动政治,而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必然达到的超乎政治的一面所带来的像萨义德这样的文化批评者无法揭示的深刻。
萨义德对叶芝的诗歌艺术避而不谈,这样,他自然也有意地避免了对叶芝诗歌的“象征主义”特点的评价。萨义德只是略带贬义地谈及叶芝诗中的“神秘主义”。其实,就一般的阅读经验而言,这种“神秘主义”与爱尔兰的神话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亦即是说,这种神秘主义是叶芝的诗的民族性的一种渊源,这种渊源使叶芝成为欧洲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的后期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的同时,又与自己的民族传统深相联结。象征主义致力于营造一个富于暗示性的艺术世界,意象与意指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简单关系,而是复杂多义的。而萨义德的分析对叶芝诗歌的这种特点避而不谈,在其作品和意义之间进行了直接的单一阐释,这种阐释是政治性的,取消了文学现象的复杂性。面对这样的文化批评,确实应该重新审视布鲁姆的如下论断:“这样一来就把审美降为意识形态,或顶多视其为形而上学。一首诗不能仅仅被读为‘一首诗’,因为它主要是一个社会文献,或者(不多见但有可能)是为了克服哲学的影响。我与这一态度不同,力主一种顽强的抵抗,其惟一目的是尽可能保存诗的完整和纯粹。”(注:布鲁姆:《西方正典》,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第16页,中文版序言第2页,第411页,第13页,第412页,第17—18页。)如果将“诗的完整和纯粹”置换成“诗的复杂性和多义性”,我就能够完全地认同布鲁姆的这一主张。准确地讲,萨义德所看到的叶芝,只是从身份政治的角度所看到的一个侧面的叶芝,而作为诗人的叶芝远比这要复杂与多义,亦即是说,如果从一个完整的叶芝的角度反观萨义德的阐释,我们不得不承认,萨义德的阐释是肢体不全的。
三、走向开放的文学研究
保尔·德曼在写于1966年的关于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的博士论文中这样写道:
一旦遭遇他的时代,作家有理由质问,他是否应该把自己的精力首先投入他的时代而非他自己的作品?政治行动是否必须优先于诗意沉思?在我们那个时代,这个问题变成了“文学对时代的参与”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一个实际上关系到戏剧性的宣传工具而不是(如萨特《什么是文学》中所主张的)小说的问题,因为小说本身就是令人迷惑的和模棱两可的。对于这个问题,马拉美作出了非同寻常的、严肃的抉择。他思想上的成熟有利于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而这就使他免于犯下我们同时代的其他很多人的所犯的同样的错误,即在那个政治化的几十年里,人们求助于社会现实中的集体化和历史性的方面,以逃避个体自身思想意识中的许多问题……马拉美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是不妥协的、令人尊敬的:即以纯内在性的姿态面对时代,且并非出于对历史的冷漠,而是出于对清晰的自我洞察的迫切要求……(注:转引自林赛·沃特斯《美学权威主义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9—100页。)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像叶芝这样的诗人的立场理解成与德曼所描述的马拉美的诗歌立场相通的一种立场,他生活在一个“政治化”的“人们求助于社会现实中的集体化和历史性的方面,以逃避个体自身思想意识中的许多问题”的时代,却以一种“内在性的姿态”面对时代——这里我将叶芝的姿态描述成“内在性的”,而不是“纯内在性”的,与马拉美可能有量的程度上的分别。或许,我们可以说,一个诗人应有的立场是在“文学场”独立和自主的前提下,作为社会“最自主的动因”(而不是“转变为政客的文化生产者”),“用建立在场的自主和与此相联系的所有价值即伦理的纯洁、特殊才能等等基础上的权威”来“干预政治场”,而不是以牺牲个体思想意识的自由为代价直接参加到政治场中去(注:参见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98页。)。在我看来,这是理解作为诗人的叶芝及其作品的基础。而萨义德对叶芝的政治化解释,其前提即是否认这种文学场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的,他将叶芝的“文化生产”直接地转义为政客的政治行为,将诗直接转义为拯救社会(爱尔兰)的政治纲领。
从萨义德对叶芝的这一政治化解释中,我们无疑可以发现当代关于文学研究(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关系论争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正像《文化研究导论》的著者所言:“权力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关键概念。导源于‘文化政治学’观念的文化阐释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政治的,结果,权力无处不在。例如,在本书中,它被用来理解阶级、种族、性别和代际关系;它被用来阐释身体与对人和地点的表征;它被用来澄清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注:E.Baldwin and B.Longhurst et al.,Introducing Cultural Studies,Peking Universitg Press,2005,p.94,p.41,p.42.)因此,虽然众多的文学文本进入了文化研究者的视野,但它们都是作为例证出现的,文化研究者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文本所“给予”的阶级、性别和种族的种种意识形态内涵。正像卡勒所描述的,文化研究热衷于在作品与反映对象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系,而文学研究关注的要点却是每一部作品与众不同的错综性。这样,很容易变成卡勒所谓的“非量化的社会学”的文化研究,“把作品视为某种别的东西的例证或表征,而不是内在于它们自身的东西”,就恰恰成了文化研究在面对文学经典时的“软肋”。这甚至在一特定的层次上构成了作为“表征性解释”的文化研究与作为“鉴赏性解释”的文学研究的对立与不相容。
对文学作品进行身份政治分析,过于关注作品的政治内容、作品诞生的历史语境,有可能遮蔽作品多元的、复杂的内涵。萨义德对叶芝的诗进行政治分析的用意,就其本身而论,不能说是错误的,应被视为文学分析的应有之义,其不妥之处,在于他过于片面、极端地阐释了叶芝的诗,对叶芝的诗的多义性和复杂性构成了遮蔽。同样,在女权主义的文学分析中,占主导地位的身份政治既有遮蔽了一个女性诗人那种政治色彩不强的诗的可能,也有全面否定与遮蔽历史上男性作家的不实倾向。这里有一个真实、有趣、同样也意味深长的事例:一个留学国外的中国男性,在国内的一次会议上,申明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咄咄逼人地问一个国内的学者,在他编写的一本关于外国文学经典的选本中,有几个女性作家。这个学者先是“失语”,而后在对方再一次的质问声中,他终于有些胆怯地回答只有一个女性作家。这时,这个女权主义者马上就下这样的断语:“那你的文学经典还是男权的打老婆的经典!”于是,与会的诸多学者响起了掌声。这是典型的在政治正确、社会正义的名义下对文学所下的简单宣判。这个事例本身可以成为文化研究的个案。在这个个案中,“选本”应该具有的某种个性被忽略了。也就是说,在一个个人编造的文学作品选本中,编选者是否有这样的一种个性,这种个性使他在无意识中拒绝了几乎所有的女性作家?此外,在这个个案中,批评者甚至没有见到这个选本本身,就敢于给整个选本下这样的断语。也就是说,这个选本本身可能具有的复杂性在这里是不被重视的。这个个案饶有兴味的,是那些掌声。这是不是说,这种过于简单的从国外直接贩卖过来的身份政治的逻辑,确实能够起到哗众取宠的功效,以至于使许多学者趋之若鹜?
在文化研究占着相当重要地位的今天,对文学作品进行身份政治的分析似乎是不容置疑的。就此而言,我们似乎回到了一个空前政治化的时代。文化研究一直在以跨学科的名义从事各种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研究工作,并给人以能够包容这些领域的研究的假象。然而,以跨学科之名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往往是从文学研究者变化而成)极易成为布鲁姆所讽刺的“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注:布鲁姆:《西方正典》,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第16页,中文版序言第2页,第411页,第13页,第412页,第17—18页。)。从上述萨义德的这个在文化研究中颇有代表性的例子中,我们不难发现,文化研究想能够令人信服地包容文学研究,对其自身而言,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棘手之处,就在于文化研究极易为“文化政治学”的批评所左右,而不能(也不愿)充分地考虑文学可能具有的多义性与复杂性。早在1986年,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就已经意识到文化研究学术上企图“编集成典”(codification)的危险,他认为“文化研究的力量存在于它的开放性和因之而来的变形和成长的能力”。他主张让文化研究“反映它所研究的对象——文化——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品质”(注:E.Baldwin and B.Longhurst et al.,Introducing Cultural Studies,Peking Universitg Press,2005,p.94,p.41,p.42.)。上述萨义德的文化批评充分表明,对诗歌经典的研究而言,文化研究远未揭示出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品质”,相反,是过于单一地从政治的角度过度诠释了诗歌。《文化研究导论》的著者曾经这样倡导:“把文化研究视为一个活动的领域,它源自从相互作用和合作到产生新的和富有挑战性的观点和主题的进展。文化研究不是学科之海中的一座小岛,而是一股水流,它冲刷着其他学科的海岸,藉此产生新的变化着的组合。”(注:E.Baldwin and B.Longhurst et al.,Introducing Cultural Studies,Peking Universitg Press,2005,p.94,p.41,p.42.)这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建议。如果我们的文化研究者在文化研究学术经典化的意愿中产生一种幻觉,认为文化研究不是这样意图冲刷其他学科海岸的一股水流,就是囊括一切的海洋本身,那么,这种幻觉将会给文化研究自身带来难以解决的问题。换言之,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关系的论争中,文化研究的学者不应促进其学术研究的经典化,并以之排斥和贬低文学研究,相反,应在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局限的前提下保持其开放性,并能够承认和尽可能地修正自己的局限。
因此,在我看来,解决文学研究的问题,为了超越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有提倡一种新的开放的文学研究立场的必要。这种立场并非要刻意强调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对立,而是希望在卡勒所说的“鉴赏性解释”与“表征性解释”、萨义德所说的“文学的事物”和“政治的事物”之间寻求某种平衡。文学研究者不一定非得在上述二者之间取其一,而是考虑两者兼顾。当然,这种兼顾在我看来还得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在今日的语境中重审并强调文学的独特性。就此而论,布鲁姆的一些论断在我看来是如此高明,能够击中文化研究在摧毁文学经典时所遇到的要害问题。布鲁姆说:
经典的破解者和传统主义者都认为这种最高权威(按:指美学最高权威)只能在莎士比亚作品中找到。莎士比亚就是世俗经典,或者说是俗世的圣经,考察前人或后辈是否属于经典作家都须以他为准。这是憎恨学派成员遭遇的一个难题:他们要么否认莎氏的超凡品质(这是痛苦而费劲的事);要么必须表明历史和阶级斗争为何并如何产生出莎剧的这些特质,因为这些特质赋予他在西方经典中的核心地位。
我确信莎士比亚的卓越会是憎恨学派最终无法逾越的巨石。他们怎能两者兼顾呢?如果莎氏成为经典的核心实属偶然,那么他们应该表明为什么主导社会阶级选择莎氏而不是本·琼生作为那样一个随意的角色。(注:布鲁姆:《西方正典》,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第16页,中文版序言第2页,第411页,第13页,第412页,第17—18页。)
布鲁姆所谓的莎士比亚的卓越其实即是指经典的独创性,这种独创性内在地包含着自身的复杂性与多义性。文化研究在面对文学经典时的问题,正在于无限期地搁置了对这种独创性的体认与理解。而开放的文学研究则主张,在体认和理解文学(经典)的独特性、复杂性和多义性的基础上,关注文学在文化整体中的地位及其关系。在写于1924年的《文学作品的内容、材料与形式问题》一文中,巴赫金曾经指出,“如果不能系统地理解审美,既不理解它与认识和伦理的不同,又不理解在文化整体中它们的联系,那么,甚至连从大量其他语言作品中区分出诗学研究的对象,即用话语表现的艺术作品,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认为:“艺术的自主自立是以它同文化整体的关联,以它在整体中既特殊又必要,且又不可替代的地位为基础、为保证的。否则的话,这种独立性就纯然成了随心所欲;另一方面,又会给艺术强加上与它的纯事实性格格不入的目的和使命,因为艺术对此无以抗衡,单纯的事实只能任人利用;事实和单纯事实性的特征,是不会有发言权的……要克服艺术研究领域中方法论上纷呈的歧说,不能走创造新方法的路子,即再加一种独特的利用艺术事实性的方法,参与到多种方法的共同斗争中去,而应该在人类文化的整体中通过系统哲学来论证艺术事实及艺术的特殊性。”(注:巴赫金:《文学作品的内容、材料与形式问题》,《巴赫金全集》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07—308页。)文化研究据说在很大程度上也受惠于巴赫金,确实有重新审视巴赫金的这些论断的必要性。我相信,这种审视将有益于使我们的文化研究学者在避免成为“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或许还应加上“不合格的文学评论家”)时获益良多。
标签:文学论文; 萨义德论文; 布鲁姆论文; 艺术论文; 丽达与天鹅论文; 文化与帝国主义论文; 叶芝论文; 西方正典论文; 神秘主义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