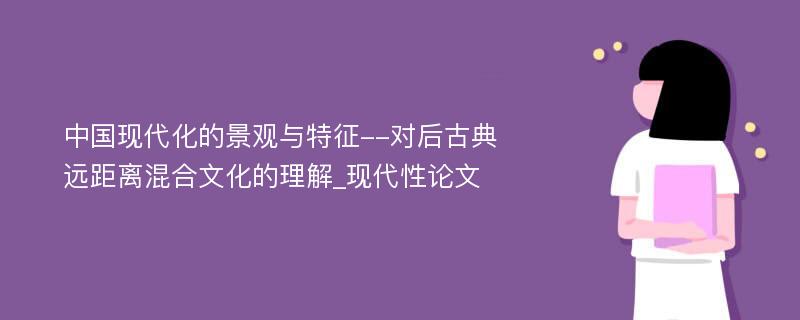
中国现代性的景观与品格——认识后古典远缘杂种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远缘论文,现代性论文,杂种论文,品格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几年来,现代性一直是文学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热门话题之一。人们对现代性理论及中国现代性问题提出了不少新鲜的看法,不过,有一个方面的问题仍旧被忽略了,这就是中国现代性究竟呈现出什么样的独特表征?或者说我们如何去把握中国现代性的独特表现方式?对此,我想从中国现代性的景观和品格去加以尝试性理解,而理解这个问题有助于回答中国现代性和中国文化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一、第三种现代思风
有关中国的现代性,通常存在着多种不同思考方式。我觉得尤其需要注意两种思风:一是现代肯定论,可称顺现代说;另一是现代否定论,可称逆现代说(或反现代说)。作为顺现代说的倡导者,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五四新文化闯将以《新青年》为阵地呼唤新的现代性变革,主张现代胜过古代,或者今天好于昨天,尽管某些古典性价值也让他们在无意识深处流连忘返。这种理论的有力根据之一是“进化论”:新的总是胜过旧的,强盛文明总会淘汰弱小文明。逆现代说是作为顺现代说的对峙力量兴起的,近20年来不少论者以同样激进的姿态质疑以五四为标志的现代,并试图加以全盘否定。他们认定,现代不仅没有迎来“中国的文艺复兴”,反而把中华民族文化推入全盘西化与辱没古典祖先的灾难的火坑中。取而代之,他们提出要从湍急的现代性河流中抽身而出,“回归古典”。这两种现代思风的出现是必然和合理的,但我希望走出它们而选择别一种现代思风——我暂且把它称作第三种现代思风:在反思中重构现代。这就是说,既不是一味地肯定也不是全盘否定现代,而是以冷峻的反思姿态重新回溯现代,在对现代的回溯中重构那被遗忘或忽略的现代性景观与品格。中国现代性,不是如顺现代论者所信奉的那样简单地意味着通过“西化”或“世界化”途径而寻求“中国的文艺复兴”,也不是如逆现代论者所批评的那样由于“全盘西化”而导致的一场中国古典文化灾难,在我看来,它是一种中国以往历史上所没有的新文化形态在同样前所未有的新的地球语境中、与西方他者相参照、在古典文化衰败的废墟上艰难地萌芽和生长的过程。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在新语境和古典废墟上、在与西方他者相参照中艰难地体验和生长的新文化形态,从中不难见出中国现代性的主要景观与品格。
二、现代性的景观
景观,在这里是指由特征和颜面综合而成的外在可感的面貌。现代性景观,作为现代性的外在可感的面貌,在各民族那里似乎都是相通的,正如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谓“时空分离”、“抽离化机制”和“制度性自反性”所论述的那样[1]。不过,中国现代性毕竟有自身的与众不同的独特呈现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现代性必然有自身的独特景观。这可以从下面几方面去看。
第一,扩张语境——地球视野。从古典“天下之中央”模式挪移到远为开阔的“地球”模式中,中国文化的语境完全变了。语境变了,全景必然紧跟着发生改变。这应当是其他一切变化的最根本的基础。在新的地球语境中,中国还能是“天下之中央”吗?鸦片战争以来发生的一次次巨变都不断地给中国人上课,迫使中国人接受了地球视野。接受地球视野,意味着接受由此而来的全部宿命,无论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
第二,强势他者——西方。这新西方已绝非旧西方可比拟,即远不是古代少数民族所在的“西域”可同日而语的,而是指位居地球西部的欧美所代表的现代强势文化。在文化的发展中,他者历来就是一面镜子,既映照出文化本身的面容,又成为文化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在唐代,如果没有西域各民族的臣服、参与或反叛,必然无法成全唐代帝国的盛世气象。而在今天,如果缺失了西方他者的各种方式的介入和影响,中国的现代性就必然不成为自身了。置身在地球上,就不得不从地球视野出发去求生存,从而就必然地与西方他者交往。这样,中国与西方的交往就成为中国现代性的当然景观之一。
第三,后古典——衰败后求复活的新古典传统。这一点在中国现代性诸景观中尤其特殊而又重要。中国古典文化诚然在新的地球语境中、在与新的西方他者的对撞中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败,但却时时渴望复活、君临现代,所以演变成古典传统衰败后的新传统,可称后古典。后古典是古典传统链条断裂之后在新的地球语境中重新创造的传统形态。中国古典文化作为一种现实的实在进程,在鸦片战争以来的现代已经逐渐地中断,取而代之、处于真正现实地位的是现代性文化。例如,现代汉语取代古代汉语,新诗取代旧体诗。不过,尽管如此,在作为实在的现代性进程中,古典文化并没有完全绝迹,而是作为古典残片生存下来,具体地说,是在现代因子的激活下生成为活生生的古典传统形象。这种现代性语境中的古典形象已不再是古代的古典文化本身,而是现代性中的古典传统,是现代性古典。不妨套用“后……”术语说,这是一种“后”于古代而在现代存在的古典传统,即是在古代文化进程中断以后而在现代性进程中重新创造或再生的古典传统,称后古典性,或后传统性(注:这里参照了吉登斯的“后传统性社会”(Post-Traditional Society)概念。)。后古典性是现代性的一种存在样式,是以古典风貌存在的现代性形式。以金庸的武侠小说为例,金庸对中国古代文化资源如史、地、易、儒、佛、道、兵、武、医、农、琴、棋、书、画、诗、酒、食、俗等的描绘,以及对中国文化精神如侠义、忠孝、名教、夏夷、穷达等的刻画,都并不简单地等同于中国古典文化本身,而只是它的现代性形式,即体现出浓烈的现代后古典性特征。
应当指出,后古典性并不是简单地指时间上的“后于古代”,而是指古典文化在断裂中的现代性再生形式。后古典性与古典本身不同。置身在古代文化怀抱而体验古代,与置身在现代文化语境而回瞥古代,必然会有不同的体验。在前者,当我们的古代先辈生存于其中时,他们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观照实等于一种自我体验,即是以自我视野观照自我;而在后者,由于古代文化流程已经中断,现代性已成生长中的实在,加上西方文化的强烈对照和实际撞击,现代人对古代文化的回瞥就不得不在切身体验中混合着一种旁观性成分,变成对已经消逝而又力求复活的陌生且熟悉的“他者”的旁观性体验了。回瞥那已消逝的古典,回瞥什么和忽视什么,张扬什么和抑制什么,都不是单纯取决于古典本身,而是从根本上取决于现代性需要。
第四,平常身份——地球国民。自晚清梁启超以来所思索的“国民性”,其实并不是指单纯的中国国民特性本身,这种单纯的中国国民特性是不存在的;而是指置身在新的地球语境中的新的中华民族特性。既然已经不再是“天下之中央”的高贵民族,而已变成地球上一国之民,那么,中国人就必然地具有了新的身份——地球上一国之民,简称地球国民。从天国臣民到地球弱国之民,这意味着从高贵身份向平常身份的转变。所以,“国民性”应当完整地表述为“地球国民性”。这种从“天下之中央”走向“地球”的过程,意味着中华民族的身份发生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剧烈变化。这是从高贵的天朝上国之民向平常的地球落后国民的痛苦的身份认同与转变过程。重要的是,这种转变的印记并没有很快消逝,而是直到今天仍在伴随着中国人。
第五,复兴之梦——国富民强。由于先前比现在“阔多了”,曾有过辉煌的祖先风光,生在当今时代就必然不自在、不甘心,渴望着重返过去的荣耀时光。中国现代性的许多问题都与这种民族集体无意识相关。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在地球上复兴中华文化、实现国富民强目标,就一直是中国的志士仁人的集体无意识梦幻。同处亚洲的日本和韩国,以及遥远的非洲和拉丁美洲各民族,由于不曾有过如此辉煌的往昔文明,因而不可能产生和体会到中华民族在现代的如此深切哀痛。即便是文明古国埃及、希腊、巴比伦的后裔,由于这些古老文明中断已久,所以也无法产生中国人这样强烈的怀旧意识。伟大而艰难的复兴之梦,这是独特的历史和现实给予中华民族的独特馈赠,同时,也是这种历史和现实留下的独特难题。置身在远为不同的地球语境中而渴望复兴中华文明,这是历史的必然要求,然而,又谈何容易!明知谈何容易也要梦下去并印证梦想,这就是当今的中国人。
扩张语境、强势他者、后古典、平常身份及复兴之梦,这五方面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独特景观的主要方面。
三、现代性的品格
从对上述独特景观的体验中,可以进一步辨析出中国现代性的哪些独特品格呢?品格一词,本来可以有若干含义和引申义,在这里仅仅用来指一种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气质或禀赋。相对于景观来说,品格较为内在和稳定,属于民族文化中与其他民族容易区分的内在层次。一般说来,当今世界,置身在同一个地球上的各种民族文化,必然地各有各的民族品格。但是,随着现代性或全球化触须在地球每个角落的深入伸展,各种民族文化的地方性必然地与全球性交汇到一起,形成罗兰·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所谓“球地性”(glocalization,或全球地方性)这一更为错综复杂的景观[2]。正是在这种球地性境遇中,我们不再可能见到那种似乎独一无二的民族现代性,而是见到全球性与地方性交融到一起的在地球范围内相互激荡的超民族现代性。在现代性过程中,无论是原发型现代性民族如欧美,还是后发型现代性民族如中国,都不得不生出这样一种超乎特定民族之上的更具一般特色的现代性品格。即使看起来不可一世的西方强国,在征服或影响其他民族的过程中也难免被反征服或反影响。超民族的球地性现代性,似乎正是中国现代性与其他民族现代性相通的现代性品格之所在。
不过,即便是同样的超民族的球地性现代性,不同民族文化在其具体呈现方式上却可能不尽相同。正是由此,可窥见这个民族现代性与其他民族现代性相区别的特殊品格:后古典远缘杂种。
从古典近缘杂种文化到后古典远缘杂种文化的演进轨迹,可以窥见中国现代性的特殊品格。中国文化历来就是在多种文化因子相互“杂交”这一开放的语境中生长与演化的,从先秦到清代都是如此,到现代也不例外。只是在古代语境中,中国文化主要是与近邻即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实行杂交,可称古典近缘杂交,形成古典近缘杂种文化。而在现代,则主要与遥远的西方展开杂交,可称远缘杂交,形成后古典远缘杂种文化。在古代,“中国”常常是“中原”或“国之中央”的称谓,四周民族通过复杂的杂交性发展入主中原,从而把异质文化中国化,成为主控中原的主流型文化。正是在这种异质文化主流化的过程中,异质文化本身与衰落中的原有中原文化产生杂交,生成新的杂种文化。随着时间的流逝,成为主流型文化的杂种文化会逐渐地削弱其杂交优势,依赖于新的杂交文化因子。例如,经过先秦时代各民族或区域文化之间的融会,秦汉文化诞生了。随后,印度佛教进入,逐渐地被同化成中国主流文化的一部分。唐代文化则由融会与整合四周多重文化因子而形成。元代与清代虽然由少数民族入主,但这里有着文化征服与反征服的新型融会过程(例如,被征服的汉民族恰恰反过来从文化上改造了征服者)。总之,在古代,中国文化主要还是利用地缘便利而实行近缘杂交,形成近缘杂种文化。
随着地球语境的形成、西方他者的强势扩张和中国自身在新语境中的不适应,这种近缘杂种文化日益显示其风雨飘摇的窘境。自此,中国文化不得不走上与西方现代性文化实行远缘杂交的新道路。来自西方的各种制度、主义、概念等等,从此风行华夏,形成陈天华《警世钟》所谓“欧风美雨驰而东”的局面。
但是,中国并没有像日本那样断然地实施“脱亚入欧”的现代性发展方略,而是坚持把发展奠基在古典文化的遗址或废墟上。也就是说,这种新的远缘杂种文化无法与中国自身的古典文化的影响或复活渴望分离开来。在这里,远缘杂交不能不发生在深厚的后古典氛围中,与后古典发生耦合,正像上面关于后古典所指出的那样。
中国现代性的独特品格就表现在,它是一种后古典远缘杂种文化。通过远缘杂交,它与中国古典性文化的近缘杂种品格区别开来;而通过后古典性,它得以与地球上其他现代性文化区别开来。这种后古典远缘杂种文化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考察。
第一,后古典语文。后古典语文在这里说的就是通常所谓现代汉语言文字。现代汉语言文字可以说是一种后古典汉语,因为它对古典汉语不是加以简单抛弃,而是作了后古典式改造。白话取代文言不必说了,就是汉字的由繁到简也是后古典语文的一个重要的保障和标志。如果按照一些激进的语言学家、思想家及政治家的设想,汉字的现代性道路应是首先实行简化字,最终走拉丁化或拼音化道路;那么,今天的汉字就应该类似英语字母或日文的假名形式了。但幸运的是,这一方案最终半途而废,让我们至今仍停留在简体汉字阶段上。简体方块字取代繁体方块字,当然对繁体字的传播意蕴、美学风貌和文化蕴含作了令人遗憾的删减,不过,它毕竟保留或部分地保留了方块字这一物质媒介基础,这就为现代性的后古典品格的形成提供了最基本的符号基石。可以设想,如果中国采取日文那种假名形式,那么中国现代性将会变得多么陌生和另类!同时,以横排标点书写方式取代竖排无标点方式,也体现了后古典风貌。自从《马氏文通》以来,来自西方的葛郎玛(Grammar)虽然通行于现代语文中,但古典“文法”(词法、句法、篇法等)仍然保留下来,尤其在文学中仍然显示其顽强的活力与卓越的表现力,从而实际上形成现代语法与古典文法杂糅的状况。
启功先生经过长期的研究,发现现代汉语(白话)虽然表面上显得“欧化”,但骨子里却活跃着自身固有的“血小板”。这一点正可以视为后古典语文的一个重要标志。启功指出,现代汉语中那些“地道的本土式的句子,有许许多多与古代汉语相同或相通的特点”[3](p.12)。他概括为如下七个方面:(1)有些词古今差别不大。例如,现代汉语中感叹词“呀吗呢的”,其实正是古汉语中“之乎者也”的现代转化形态。(2)沿用“上下句”形式。古汉语所谓“上下句”,在现代汉语中几乎原封不动地套用下来:“今天我来谈一个问题,就是汉语语法方面的事。汉语语法的范围太广了,从何说起呢?我要说的,只是古代汉语中的一部分语法问题。”这段话明显由三组上下句构成,体现出抑扬、顿挫和强弱分别。(3)古汉语中的平仄或四声在现代汉语中延续下来。“说起话来,无论操哪种方言的人,也没有平仄到底每字全是同一调类的。”[3](p.13)(4)语音抑扬的延续。如问答语往往是上下句,通常是“高问低答、低问高答”,一扬一抑。(5)词的用字可以伸缩加减:重字叠词可以加强语气,而减字也可以加重语气。(6)口语中有对句,如“明天如是晴天,咱们北海划船;明天如果下雨,那就不出门了。”(7)口语中局部词汇颠倒而大意不变。启功据此作出结论说:“从以上所列现代汉语的各种现象看,不难理解古典诗歌、骈文的句式构造、联式排列、音调抑扬、词汇伸缩颠倒,句法繁简长短,主、动、宾语的具备或省略……,都不太难摸着一些来龙去脉。”[3](p.16)这也就是说,上述古汉语的特征并没有在现代汉语中消失或衰亡,而是顽强地存活下来,并成为现代汉语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同时成为它的美的资源。
现代语文的后古典性进一步表现在,属于古汉语的那种“血小板”仍然在现代语文中存活和贯通。启功用“集成电路”和“血小板”来比喻这一点。他认为,汉语中有关“节拍”和“辙调”等传统模子,正是汉语的“血小板”:
……这类节拍、辙调的作用,在汉语中有多么大,这种汉语中的“血小板”,凝聚力又有多么强!……例如,“八股文”,内容上虽已臭不可闻,但它的形式上和手法上,又具有陷阱式的模槽,许多创作走着走着就不知不觉堕入槽中,因而出现“这八股”、“那八股”的批评和讽刺。但值得反省的是怎么就会形成这类槽子。律诗八句为什么那么摆,对联这种某些文体中的细胞,又为甚么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挂在人们的门口。[3](p.8)
正是来自古代汉语的那些传统模子,恰如人的身体所不可或缺的“血小板”一样,使现代汉语凝聚为活的整体。所以,那些看来“僵死”的古汉语形式,仍然可能蕴藏着对现代汉语躯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精华”——“血小板”。顺便讲,倘若吕叔湘等关于“要真正解决问题还是得搞拼音文字”的主张果真实行[4](P.115),那又如何能保障来自古汉语的“血小板”在现代拼音文字中继续存活、活跃而不致枯竭和衰亡呢?因为,如果把汉字换成拼音文字,那原本流动在方块汉字躯体中的来自古汉语的“血小板”,势必会完全流失。失去“血小板”就等于失去活的生命,这时还能有其他?
看来,不是走激进的拉丁化或拼音化道路而是采用后古典方略,这实在是汉语的现代生命力和表现力的重要保障,也因此而成为现代中国人在地球上的生存的基本保障。当然,中国人由此获得的并非全是恩惠,而是同时包括着巨大的代价。例如,人们常常抱怨或批评现代生活中的“封建”和“守旧”因素,这些是否可以最终追溯到最基本的汉语符号层面的后古典性?
后古典本身就是古典衰败以后与现代因子杂交的产物,是一种文化杂种形态。重要的是要看到,后古典语文对中国现代性工程的影响是基本的和深远的,它不仅影响到现代中国人的生存体验表达、文化建构,而且同时有力地参与塑造着中华民族的集体意识与无意识、个体意识与无意识,及其具体的教育和文化的再生产。
第二,双重时空体验。与后古典语文相应,公历纪年与阴历纪年、北京时间与古代十二时辰的并行,地球视野与古典天下观念、全球性与地方意识的重叠,为中华民族的现代生活编织起一个双重时空网络。这一中西杂交而成的双重时空网络的作用本身也是双重的,一方面使这个民族享受到现代时空的便利和欢悦,另一方面也使他们承受到因彼此冲突而带来的艰难与苦痛。黄遵宪在《今别离》和《八月十五日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等诗里所表现的古今冲突,正显示了中国人对于双重时空网络的切身体验。双重时空带来了双倍的节日及其庆典或仪式。中国人既要过阴历春节,也要过公历元旦;既要按公历纪年安排作息时间,也要看阴历的“日子”;过生日既有讲究公历的也有坚持阴历的等等。这既是错位又是兼顾,其间必然包含着冲突与调和的可能性。正是这种双重节日仪式有力地塑造着中华民族的现代民族心理。对这种双重时空体验需要做冷峻的反思。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有幅名画叫《记忆的持续》(1931),画面上,三具现代机械时钟被折叠起来,形成机械时钟被变形或扭曲的鲜明图景,而这种变形或扭曲正揭示了人的记忆被变形或扭曲的必然命运,从而传达出画家对现代性的深深的忧虑与恐惧。我这里想说的是,在现代中国人的体验中,不仅陌生的现代机械时钟被扭曲了,而且熟悉的古典时间也被挤压或撕裂了,如此一来,现代中国人遭受到的就是双重变形或双重撕裂。双重时空与双重变形是紧密相连的,你不能只要它的好处而不要它的坏处。这既是生存方式的双重变形,也是更深厚的意识与无意识的双重变形。
第三,硬抽软具机制。如果按照吉登斯所谓“抽离化机制”之说,中国的现代性的基本标志之一就是现代“抽离化机制”的建立。从政体的共和制到现代教育体制、从法律到金融、从工业体制到学术体制等,中国的各种现代“抽离化机制”可以说已经根据自身的需要而仿照西方建立起来,并且逐步丰富和不断趋于完善。然而,另一方面,与后古典语文和双重时空体验紧密相连,中国的现代性机制的正常运行同时还需要依赖于别一种隐形法则——不妨仿照吉登斯的概念说是古典具象化机制。具象化机制是与抽离化机制相对而言的,是指来自中国古代的一整套体制及其运作法则,它们往往讲究具体的形象表达。这种具象化机制虽然遭到抽离化机制的压制和打击,但却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在深层、隐性层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好比硬件是现代抽离化机制,而软件是古典具象化机制,两者居然就杂交起来,一硬一软地交汇着发生影响。例如,尽管有现代法治,但古典式人治的作用仍不可低估;现代共和制也需要具体的人格化领袖的魅力影响;在中国乡村,看起来严密的政治体制往往与具体的民间风俗或巫术一道产生凝聚力与控制力。
贾平凹长篇小说《浮躁》描写主人公金狗力图从农村走向城市。金狗是陕西商州州河边白石寨县两岔镇仙游川村“杂姓人”,是无权无势的“小人物”,他一心一意要创建个人权力地位。这样做,必然意味着向当地以田巩两大家族为代表的现成权力关系发起挑战。田、巩两大显赫家族是商州地区的两大霸主。田家靠战争年代田老六游击队打下的基业发迹,其后代田有善做到白石寨县委书记,田中正任两岔镇书记,在仙游川村有其代理人田一申和蔡大安之类。田老六虽然死去,但他的警卫员许飞豹却做了省军区司令员,成为田家在省上的靠山。巩家同样是“打江山者坐江山”,巩宝山任地区专员,其女婿则控制了地区的商业贸易网络。相比之下,金狗及其同道雷大空、福运、和尚等由于是“杂姓人”,处在家族权势集团之外,所以必然是无权无势的。很明显,田、巩两大家族已经把商州地县镇乡村的各级和各种权力瓜分完毕,构成复杂、严密而有序的现代家族权力关系网络。这个现代网络攫取或控制了当地的主要权力资源。这一现代家族权力机制的存在透露出一个事实:在80年代中国社会的某些基层,权力机制的主要存在方式表现为,少数家族权力集团瓜分权力,而多数平民则被这些集团任意摆布。
不过,另一方面,在仙游川村却存在着别一种统治机制——这就是民间风俗与宗教或巫术的隐性作用。和尚和阴阳师正是代表民间风俗或宗教的力量。他们是“方”外之人,完全放弃现实行动,但又被认为深谙世事、洞悉究里和未来,是非行动而拥有价值的化身。民间风俗虽为金狗所弃绝,却深得金狗爹矮子画匠、恋人韩小水和韩文举等大量村民的信奉。这表明,尽管“无神论”宣传自50年代以来便已家喻户晓,但在80年代中国农村,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村平民依旧信神拜佛,认定命运不是由自己把握而是操纵在神手中。小说结尾,写韩小水心忧金狗的未来,只能请和尚“拆梦”、向阴阳师“问事”,尤其能说明这一点。阴阳师说,“金狗要干的事业,都是社会上的大事,这就只能问三老了。三老是当今大神。”“三老”即已故伟人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阴阳师扶箩在沙盘上扎针写字,解释说:左上角大字系毛泽东所写,他说“没事”;中间的小字由周恩来写,是“事成”;右边的圆圈为朱德画出,表示“同意”。在阴阳师看来,有了“三老”的保佑,金狗就能成功了。那么,是神(民间宗教)的力量还是人(金狗)的力量能左右人们的命运呢?无论如何,神的力量是受到弱势群体信奉的。[5](pp.359-367)
硬抽软具机制的存在,既是必然的合理选择的结果,也体现了一种宿命决定的无奈:现代中国人难道还可以有更好的杂交选择吗?既然无法像胡适主张的那样“充分地世界化”,而是有节制地现代化;也不能像后来论者所倡导的那样全面复归古典,而是让古典呈现某种“后古典”面貌,那么,硬抽软具机制就注定了会伴随着现代中国人,走过这风雨飘摇的现代性里程。这也表明,中国的现代性不可能是纯种的,而只能是杂种的。
总之,与时下有关中国现代文化已经完全数典忘祖这类看法不同,我相信它与自身的古典传统具有内在的息息相通关联,例如,具有同样的开放、变化与杂交精神,善于融会多种异质文化因子于自身,形成新语境条件下的新的独特品格。只不过,正是顺应语境的变化要求,它从古典近缘杂种文化转变成今天的远缘杂种文化。认识这种远缘杂种文化还需要时间,这里只是抛砖引玉了。
